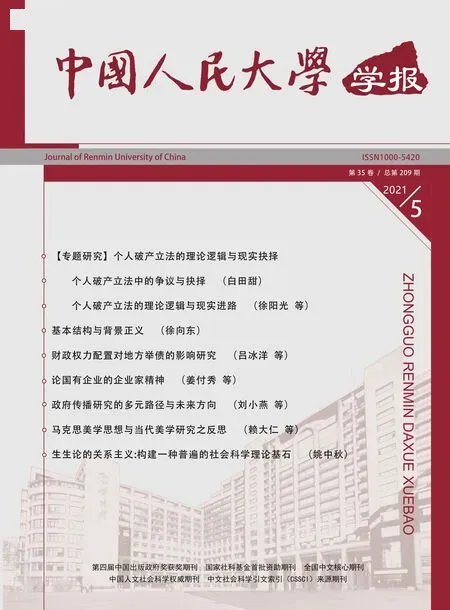中国人权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①
2021-01-03赵永华
赵永华 刘 娟
鉴于中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上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差异,西方国家多从国家利益、政治偏向和普遍性角度对中国人权进行批评和干预,中国有必要主动回应,以中国方式传播中国特色人权。目前,关于中国人权话语和传播的研究文献主要来自中国学者,国外学者对这一话题关注较少。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体系培育、话语权建构和具体的人权话语文本分析等层面,专门探讨中国人权国际传播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往往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角度,从规则制定等路径展开分析,或者结合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进行探讨,缺乏从跨文化传播、中西方文化差异角度对中国人权国际传播进行的研究。国外学者虽然对中国如何传播人权不感兴趣,但对中国人权却有较多研究,主要是:中西方人权理论和人权概念的比较、中国人权与其他议题的关系、西方媒体关于中国人权的报道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批评中国人权,主要缘于西方媒体惯有的新闻批评文化和中国国力上升给西方带来的威胁。西方学者带着焦虑的情绪将中国人权议题与中国追求软实力、参与全球治理、争夺国际话语权等议题放置在一起,并显现出西方学术话语的霸权底色。在他们看来,中国越是强调人权应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就越是背离国际人权标准。中国对人权的解释非但没有提升中国人权话语的正当性,反而成为西方学者给中国人权扣上违反“普遍性”人权帽子的理由,体现出对中国人权集体不认同的基调。
在西方学者、媒体、政府合力构筑的人权话语霸权下进行中国人权话语建构和国际传播,必须回答以下问题:第一,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实质和内在生成逻辑是什么,有何缺陷;第二,中国人权话语传播什么,是否具备了有关人权的自主话语;第三,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应该采取怎样的传播措施,包括如何建立合理的话语秩序,怎样与西方互动,以何种方式言说。
一、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非合理性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借助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和机制,将西方人权提升为全球人权标准,形成话语霸权,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显然,西方的人权话语并不能解释和回答中国人权发展的诸多问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理解必须放置于中国自身的现实语境中。然而,西方人权话语霸权是中国人权国际传播绕不过去的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其本质和缺陷的认识尤为必要。
(一)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本质
话语是演讲、书写构成的相关陈述体系,通过语言进行知识生产和意义生产从而对社会实践产生真实影响和效果。(1)Stuart Hall,and Bram Gieben.The West and the Rest:Discourse and Pow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165.人权话语作为与人权相关的陈述体系和意义生产,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对纳粹暴政的反思,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欧美人权话语模式。西方国家借助国际组织形塑了人权话语的权力、等级和能力分配,构建了人权话语的言说方式,确定了人权话语的边界,确立了人权话语霸权,进而对差异性和异质性人权话语进行管控(2)U.Baxi.“Voices of Suffering,Fragmented Universality,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In Burns H.Weston,and Stephen P.Marks.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New York:Routledge,1999,p.163.,且从国家利益和政治目的出发,以“普遍性”人权价值观为名,利用联合国等平台批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3)范国祥:《人权、主权、霸权》,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2)。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歪曲攻击,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制度偏见’,肆意炒作一些极端的人权个案,无理指责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政策。”(4)邱昌情:《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载《人权》,2018(3)。美国倡导“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以人权普适性为借口对中国内政外交指手画脚,以人权为名进行人道主义干涉(5)袁正清、李志永、主父笑飞:《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7)。,人权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政治工具。2019年底美国国会相继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20年初正当中国人民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时,美国媒体指责中国的防疫措施“侵犯人权”,某些国家还出现了针对中国和华人的歧视性言行,颠覆了平等、不歧视的人权价值观。美国政客和媒体将人权议题作为攻击中国的符号工具,中国人权屡遭西方话语霸权的“污名化”。
出于国际战略部署的需要,美国政府将人权视为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并将人权与商业利益和政治目的结合起来。老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时曾指出:要想取得商业上的利益,任何人都会更加重视人权。(6)黄友义:《美国是怎样把人权理念转化成公共外交工具的?——评〈完美的幻觉:美国政府是如何选中人权外交的〉》,载《公共外交季刊》,2012(3)。2000年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监控中国各个方面的人权状况,包括宗教自由、工人权利、民主管理的权利、知识产权、政治犯的待遇、西藏的权利和台湾的民主等,这些人权内容与美国的商业利益、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因此,对人权问题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将其视为西方人权全球化和普遍化的结果层面,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实现人的尊严和幸福生活的公民权利问题(7)M.Ignatieff.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and Idolatry.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而应认识到这是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贸等纠缠在一起的问题。
(二)西方人权话语的散溢化与普遍性人权话语的缺陷
传统人权话语围绕欧洲中心和国家中心逻辑展开,现代人权话语包罗万象,呈现散溢化(discursively)特征,并逐渐由NGO(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协商形成,人权话语呈现多元化趋势。(8)U.Baxi.“Voices of Suffering,Fragmented Universality,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In Burns H.Weston,and Stephen P.Marks.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ew York:Routledge,1999,p.173,p.183,pp.185-188.地方人权话语而非西方人权话语更具有意义,人权话语走向地方自我裁决。国际人权话语的主导者——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如今只能在服务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利益的话语中找到。(9)U.Baxi.“Voices of Suffering,Fragmented Universality,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In Burns H.Weston,and Stephen P.Marks.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ew York:Routledge,1999,p.173,p.183,pp.185-188.
阿根廷法学家爱德华多·拉博西(Eduardo Rabossi)认为人权话语的普遍性与人权实践的具体语境相冲突(10)Richard Rorty.“Human Rights,Rationality,and Sentimentality”.In Stephen Shute,&Susan Hurley (eds.).On Human Rights: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New York:BasicBooks,1993,p.116.,在现实世界中,推动普遍性人权话语落地面临诸多困难。在这个意义上,人权话语成为抽象的存在,很难将其落实到具体语境中。人权话语的全球化和普遍化进程并非伴随着人权话语的同质化和统一化,其中包含着矛盾性和自反性。因此,要警惕人权被西方国家以普遍性之名,以区分人性和非人性,从而获得西方人权话语的全球霸权。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的价值观、秩序观、体系观自成一格,中西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冲突和隔阂由此变得更加深刻,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两者在各自不同轨道上自我演进。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种体系有了正式的正面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对西方而言是主动,对中国而言则是被动。”(11)袁鹏:《我们正面临世界秩序的第四次变迁》,载《北京日报》,2018-03-12。世界互动秩序延续至今,然而,信息全球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将各国之间的距离历史性地拉近,使得共建全球新秩序的必要性在扩大。
在全球新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渐提升。与此相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正在从“规则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一方面,西方人权话语自身带有缺陷,例如普遍性人权观的不切实际,以及现代人权话语的多元化趋势对传统话语造成冲击,为打破西方历史形成的人权话语霸权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变化,面对西方的人权指责,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重塑人权话语秩序,成为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新秩序的应有之义。
二、以发展权确立中国人权话语主体性,更新人权话语体系
全球化将20世纪之前的海洋变成了“内海”,开始了“全球律则”时代,在方法论上讲,欧洲资本主义在海洋内海化过程中通过对无限性的消解和“祛魅”,以理性建构的方式,给世界强加一套规则体系。(12)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上)》,载《经济导刊》,2015(8)。显然,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强权是建立在中国缺乏主体性和不自信的结合体之上的,将中国主体性塑造成西方投射政治想象的载体”(13)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147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因此中国人权话语建构,首先要确立中国人权话语的主体性,这关涉突围西方话语霸权的核心问题:如何成为世界人权理念的主要输出者。
中国和西方世界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双方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缺乏充分有效的融通和对接。因此,面对西方人权话语霸权,“我们需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但是这个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他人的要素”(14)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下)》,载《经济导刊》,2015(9)。,我们要有自己的世界视野和关于世界普遍性的辩解,不是民族主义,不是把中国和西方对接,而是以另一种普遍性和现在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普遍性进行对话,突破二元对立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从中国立场出发,具有世界眼光。(15)参见赵月枝、胡智锋、张志华:《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2)。历史上,美国话语霸权确立的根本,在于其一方面挖掘自己的本土文化,与欧洲拉开距离,另一方面在与欧洲对话和交融中将自身价值进行输出。(16)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130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鉴于此,中国在确立人权话语主体性过程中,既要参照普遍性人权话语,也要考量自身特性,以包容和开放思维,全力挖掘中西文化中关于人权的价值共性、文化共性、道德共性,推动本土原创概念和特殊概念的国际表达,更新人权话语体系。
人权话语体系,是人权理论、人权观点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紧密相关,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人权诉求,对人权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同。(17)S.C.Angle.Human Rights in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人权话语无论是在概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无法脱离具体语境而存在,因此,不能也不应将某些国家的人权标准绝对化,要求所有国家遵照执行。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权的主要内容,区别于西方从“天赋人权”和“人人乃上帝子民”等角度阐发的人权话语。
1991年中国发布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突出人民的生存权。发展至今,白皮书作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侧重点也由生存权转向发展权。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是以概念人权到制度人权再到文化人权为基础,构建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人权理论、观点和思想。(18)刘志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表达》,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5)。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不仅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即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作为促进其他各项人权实现的保障,而且也是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的超越。发展权不是对西方人权话语的抛弃,而是将发展权提升至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并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实现发展权的支持性权利(19)常健:《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载《前线》,2017(8)。,以此确定中国特色人权话语意义来源的统一性以及言说的方法体系和命名体系,建构统一连贯且有体系的话语组合,从而对全球人权话语进行完善和补充。
2017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纳入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会议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的“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等理念作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思想支撑。习近平在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提出:“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习近平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载《人民日报》,2017-12-08。多年来,中国坚持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开放对话姿态,与全世界共享中国人权建设经验,就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权问题,积极发表中国观点(21)吴凡:《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创新》,载《理论月刊》,2018(12)。,尤其是“中国以‘不干涉内政’‘创造性介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超越西方人权观,赋予人权话语以更多的中国元素,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22)邱昌情:《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载《人权》,2018(3)。。
三、以制度方式成为人权规则制定者,确立人权话语秩序
西方人权话语霸权遵循着“理念—规则—机制—实施”的生成路径,首先以《联合国宪章》进行理念输出和理论供给,然后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制进行规则制定和规则解释,再通过人权机构实施监督和设置议题。(23)毛俊响:《国际人权话语权的生成路径、实质与中国的应对》,载《法商研究》,2017(1)。
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关涉的是理念输出,理念是话语权的基础,进一步循着“规则—机制—实施”的路径才能生成话语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英、美、苏等26国的倡导下,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逐渐成为抵抗法西斯势力的重要思想武器,随后西方国家对人权侵犯行为进行了反思,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1条规定将尊重人权确定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1946年成立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48年通过了国际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话语权的规则保障,基本上确定了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谱系,借此完成了人权从理念输出到制度建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主导了人权理念和标准的制定,还主导了国际人权机制的建立和规则的运行,掌握了法律优势、人力优势(尤其是规则制定和文件起草等关键岗位的人力优势)和监督优势,以法官和监督者的角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议题进行点名和羞辱,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话语劣势。(24)毛俊响:《国际人权话语权的生成路径、实质与中国的应对》,载《法商研究》,2017(1)。
因此,中国若想彻底改变在人权领域的话语弱势和话语劣势,需要从根本层面入手,以制度形式参与国际人权话语秩序的建立:切入世界人权规则的制定者圈层,主动提供人权问题的应对方案、规范,在成为人权理念输出者的同时,成为人权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通过身影的出现,就可获得话语权,各色形式的话语公关,暴露着自身的迷茫、不适应、焦灼和不自信的自以为是”(25)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486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不能停留在身影层面,而是要上升到制度层面,参与确立合理的人权话语秩序。
人权话语秩序需要在一定的规则、程序和规范内确立,“话语的秩序由一系列的约束规则构成:话语的外部规则、话语的内部规则以及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26)陶然:《从话语分析到权力分析——论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语言研究》,2011(10)。。中国日渐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以制度方式确立人权话语秩序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可能性需要与现实结合。在西方人权话语霸权下,西方人权机构主导着人权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意味着中国需要在西方既定标准内进行人权话语和秩序的建构。在国际范围内,通常国家会通过参考规范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以辩论、阐述和劝服等话语策略介入国际人权机构对人权规范的制定。(27)R.Foot.Rights beyond Borders: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8-10.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组织和国际议题仍以规则作为“绑在其背后的推手”来处理问题。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来看,全球议题的处理一靠大国、二靠平台、三靠规则,其中规则是合作机制的重要保障。(28)刘建飞、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太平洋学报》,2018(1)。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规则制定有助于重构话语秩序,增强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场域内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发展权”形成对国际人权规范的竞争性解释,去除西方人权话语霸权带来的制度成本和制度束缚。
四、在与西方人权话语对话和互动中,实现人权话语认同
在多元文化格局中,进行人权话语对话,需要面对文化差异问题。在尊重东西方人权思想、历史和现实差异的基础上,主动传播中国特色人权,既要承认人权作为人类共同理想和价值准则的普遍性权利属性,同时也要强调人权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文化传统,从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消解西方国家的人权偏见。“让中国文化以自身的历史价值、伦理哲学、现实连续性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西方强势的话语和思想体系中”(29)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代序,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以文化自主和自信打破西方话语背后隐含的单一性和压抑性。
强调中国特色人权话语,并非刻意强调它的特殊性,而是在与西方人权话语的对话和互动中,在与普遍性人权话语的联系中,争取建构自主话语。中国人权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在与其他人权话语的复杂互动关系中,并将其他话语带入自己的意义之网,确定人权话语言说的领域和范围,提供人权话语新的意义和认同的来源。
关于话语和认同之间的关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是一种与主体有关的话语,内含着认同,与规范内在化区分开来。(30)C.Epstein.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irth of an Anti-whaling Discourse.Cambridge,MA.:MIT Press,2008,p.15.因此,人权话语传播的起点是认同的构建,并非从外部强制灌输和强迫他人接受,而是他人主动的内化和接受,这取决于话语主体及其话语在多大程度被主动认可和承认。如果他者认同话语主体,会主动将自己塑造成支持者而非对抗者。
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主体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往活动中的协调、理解关系达成一种有关社会规范体系的理解,形成交往理性和规范共识。(31)傅永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述评》,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中国人权话语的建构与传播,需要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哈贝马斯的“话语中的权力”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关注人权话语权力关系网,思考权力关系网由哪些不同主体组成,不同主体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和博弈关系,有着怎样的人权话语结构,进而分析中国人权话语的传播存在怎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具体微观且策略性的层面入手,在交往活动中构建规范共识和意义共享,“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构建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实现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互联互通’”(32)邱昌情:《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载《人权》,2018(3)。。
这种“互联互通”首先取决于互动的可能性,没有互动,就无意义共享,也无法实现规范共识和认同的获得。由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具有理想化特征,对处于互动关系中的话语主体要求较高,而在国际利益博弈和政治力量失衡的话语场域内,审议性讨论和交往理性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由此,在国际话语场域内,中国要实现人权话语的意义共享和规范认同,构建人权话语共同体,就不能是人权内在秩序和意义内涵的简单重复,而应围绕人权话语秩序的形塑展开策略性对话与合作,这一过程包含以下四个步骤:第一,采纳(adoption)和战略性谈判过程;第二,道德意识提高,辩论、对话和说服的过程;第三,制度化和惯习形成的过程;第四,认同和行为规范的内化与制度化过程。(33)T.Risse-Kappen,S.C.Ropp,and K.Sikkink(eds.).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1.
在上述过程中,需要借助具体的对话机制和意义生产机制来实现意义共享,适时择机展开不同人权议题的对话交流。但是,由于我们“急于与欧美平行的运行系统和机制进行对话,往往由于过于明确的利益指向和价值诉求而流于空谈,由于缺乏微观的切入和从实际问题出发的思考,从而为实践者注入虚妄的幻想”(34)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179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人权对话需要的是:基于对现实人权问题的思考,提供一种真实的有关对错的人权话语,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有关人权的思维范式和言说范围,逐渐形成人权话语共同体和话语联盟。
“信任与说服,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思想或情感过程,这一过程在关系中确立,通过说服、议程建构和吸引力等同化方式来影响他人,塑造他人最初的行为偏好,进而实现价值认同。”(35)有关人权的价值认同产生于互动和关联中,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要锁定他国具体的言说对象,即受众,要“明确价值观和利益观的目标,列出可以明确言说的对象和可以利用的资源目录,评估言说对象的目标和偏好,选择可行的言说策略”(36)约瑟夫·奈:《论权力》,前言xiii、24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进行针对性传播,从而实现国际社会的话语认同,破解西方人权话语的污名化。
五、以共享文化破解西方话语的污名化,讲好中国人权故事
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受损的身份”概念,用于描述遭受污名体验的各类社会越轨者在其他人眼中被贬低和被贴标签的社会现象。(37)E.Goffman.Stigma:Note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3,p.155.西方一些国家站在自身立场上对中国人权进行指责和贬损,常以消极、冲突、专制和不平等的思维看待中国人权,凭借话语霸权进行“污名化”,以西方人权优越论区隔和贬低中国人权。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人权时多使用concern(担忧)、abuse(滥用)、violation(违背)、terrible(恐怖)、shortcoming(缺陷)、questionable(有问题的)、ruthless(无情的)等词汇,并将中国人权与战争、身体部位、自然现象、动物、儿童、妇女等话题连接起来。(38)朱海蓉:《美国媒体中国人权形象批评话语分析》,载《新闻研究导刊》,2018(11)。有学者总结得出西方对中国人权实施污名化的议题偏好包括:异见人士议题、民族宗教问题(主要是新疆、西藏、宗教自由等)、国际/海外议题、社会发展问题、法治议题,等等。(39)参见史安斌、王沛楠:《断裂的新闻框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与“人权”议题的双重话语》,载《新闻大学》,2019(5)。“推动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政治化’(如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人权化’(如西藏问题)”(40)邱昌情:《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载《人权》,2018(3)。是西方的惯常做法,以此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偏见。
目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是“西强我弱”。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15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我国突围话语权困境的基本策略。讲故事并不简单,是给周围世界和生活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过程。好的故事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可以确立归属感,组织人类经验,形成集体记忆。(42)Jerome Bruner.“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Critical Inquiry,1991,18(1):1-21.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近年来,中国为“讲好中国故事”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为什么效果却不如人意?中国向世界讲述的人权故事存在什么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致力于讲述中国在人权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讲述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实际上,中国人权话语劣势并非源自传播技术的薄弱和话语数量的不足,而是在讲故事时出现了思维误区和视野偏差,缺少世界主体性意识,只讲跟中国有关的人权故事而较少考虑世界普遍问题。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471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有内容上的创新,更要有思维和视野上的转换,贯通中国与世界:在世界中思考中国,在中国思考世界。世界主体性意识在于思考如何通过中国的努力,解决世界普遍存在的人权问题,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讲述中国人权故事离不开对世界其他国家故事逻辑和文化特色的了解,不同的新闻文化会产生不同的人权故事框架。了解受众的故事主题偏好,尔后进行定制传播,使用隐喻、典故和事例,激发一种新的思考方式(44)M.C.Nisbet.“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Why Frames Matter for Public Engagement”.Environment: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9,51(2):12-23.,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阻碍国外受众接受中国人权故事的并非是信息的不畅,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固有偏见。将故事嵌入传播对象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关照个人视角、普通人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在公众话语中进行转换(45)Annika Arnold.Climate Change and Storytelling:Narratives and Cultural Meaning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Houndmill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8,pp.21-23.,才能讲好中国人权故事。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认为,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更多的是准确地回应传播对象,而不是正确地传播信息(46)E.T.Hall,and M.R.Hall.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Germans,French and Americans.Maine:Intercultural Press,1990,p.4.,关键在于理解对方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理解这种语境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价值体系——包括种族认知、行为规范、信仰、审美标准、思维模式和交流方式等,这些都是特定群体为确保生存而逐渐形成的,传播对象以他们既有的思维模式、情感结构和行为方式来解读故事。(47)Brain J.Hurn,and Barry Tomali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Houndmill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pp.4-5.
传播关乎文化,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将信仰共享作为传播仪式观的核心,可见传播的起源及其最高境界并非是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是共享信仰的创造、表征和庆典,将人们以共同体或团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48)樊水科:《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载《国际新闻界》,2011(11)。这启示我们,讲故事的终极目标是要营造一种共享的信仰,创造一种共享的文化,要寻找到与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弥合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鸿沟。
总体上,讲好中国人权故事,要注意几点:一是要在传播对象的“文化地图”上寻找到合适的经纬线和坐标,精心选择能够在不同政治体系和文化主体之间达成互惠性理解的故事,选择人类普遍关注的人性、人道、人爱等主题(49)苏仁先:《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选择》,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2)。,将人权话题转化为有意义且容易掌握的故事;二是要讲述真实可信的故事: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有微观叙事,以具体的小故事回应宏观的大战略,将人权故事与普通老百姓及其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真实个体在实际生活中与人权相关的际遇和情节;三是要以传播对象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人权故事,充分考虑对方的信息需求和语言习惯,从而产生意义共享,形成积极正面的集体记忆;四是要将人权故事的讲述当作共识获取的过程,其中传递的价值观要符合传播对象的文化和世界观,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以文化间性和文化包容诉诸情感认同,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人权故事讲述作为一种新闻生产,不是填补信息空缺的工具性存在,而是将离散的事件转化为如詹姆斯·凯瑞所说的有意义的共享文化和信仰的叙述过程。(50)R.N.Jacobs.“Producing the News,Producing the Crisis:Narrativity,Television and News Work”.Media,Culture & Society,1996,18(3):373-397.如果没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支撑,人权故事的国际传播就只会是一系列数字、模式和事件的堆砌。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目前我国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由于“话语权长期受制于人,挨骂问题仍有待解决,这一点在人权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51)任丹红、张永和:《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1)。。
本文回答了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语境:中国人权话语处在何种话语场内,如何认识西方话语霸权的本质以及目前遭到的反抗,我们需要认清问题、困难和挑战。第二个问题关乎话语内容层面,更关乎传播自主性和理论准备层面,强调对西方人权理念和知识体系的解构与重构,这样才不至于在面对西方的指责和批评时,陷入“哑口无言、词穷理亏和词不达意”的困境。第三个问题关涉传播方式,在廓清西方人权话语霸权本质和做好自身理论准备的前提下,还要思考作为抽象理论的人权话语体系如何付诸话语实践,这关乎中国人权话语权的生成路径,须从根本层面入手,通过参与制定规则以制度的方式重构人权话语秩序;从话语策略来讲,用讲故事的方式以共享文化化解西方的人权偏见,二者都以构建认同为起点强调与西方的对话与互动。上述三个问题构成了本文论述的逻辑,也是中国建构人权话语并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取得制度性人权话语权的关键。
总而言之,国际人权话语权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并不存在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策略。具体而微的话语策略还需回归新闻传播、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综合领域内,回到切切实实的人权话语实践中去摸索、提高和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