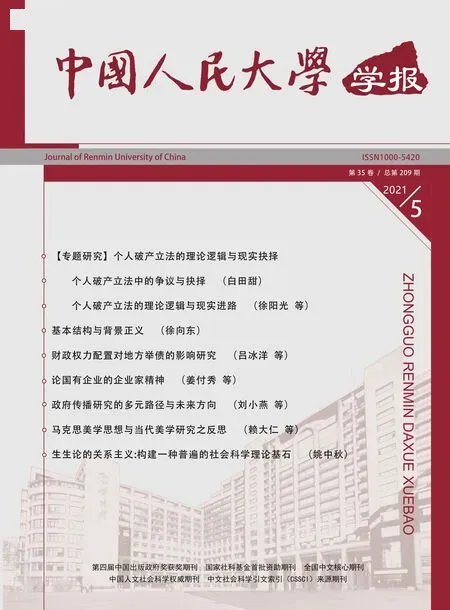生生论的关系主义:构建一种普遍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石①
2021-01-03姚中秋
姚中秋
一、研究缘起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首先需要确定其基础性理论预设。目前流行于全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为共同基础,它包含以下命题:人是原子化个体,拥有理性能力,通过理性选择与人互动,形成社会;或与人订立契约,构建国家。(1)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等人对方法论个人主义都有过专门论述,较为系统的论述可参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一直有人对此预设持有异议,认为其明显偏离人的存在真相,不足以构成思考人类秩序之基础。(2)耶克虽为米塞斯的学生,却不赞成其方法论个人主义,斥之为“伪个人主义”,而主张“真个人主义”:“真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a theory of society),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更使这一方法论陷入巨大危机。
大半个世纪以来,针对理性预设,学界不断放宽限定,从预设完备理性到预设有限理性,甚至强调人的普遍无知;针对个体性预设,学界提出的替代方案有两种:一种是与之相反的整体主义(Holism),另一种是关系主义(Relationism)。如果说个人主义是“不及”,整体主义则是“过”,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同样不足取。相对而言,方法论关系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onism)较为中正持平,西方社会学领域已初步形成“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范式:有学者断定人是“关系性存在(relational being)”(3)肯尼思·J.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有学者为强调关系的重要性,模仿《新约·约翰福音》说:“太初即关系(In the beginning is the relation)”(4)皮耶尔保罗·多纳蒂:《关系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有学者认为社会世界是由互动和关系之网构成的。(5)参见尼克·克罗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然而,囿于其文明和思想传统,西方学者在这个方向上普遍半途而废,没有追溯人类关系至其真正源头。
国内社会学者也在发展关系社会学。(6)参见赵汀阳:《深化启蒙 :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载《哲学研究》,2011(1);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边燕杰、杨洋:《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载《人文杂志》,2019(9);刘军、杨辉:《从 “实体论”到 “关系论”——兼谈 “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原则》,载《北方论丛》,2012(6)。另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关系转向”,有学者断定关系先于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国家(7)这方面的综述可参见季玲:《 “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代表性研究可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政治学者徐勇从人类社会关系的视角研究国家,断言关系构造国家,国家再造关系(8)参见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模式也是关系主义的。(9)参见李向平:《关系主义宗教模式:儒教中宗教的核心问题》,载《国际儒学研究》(第15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社会学者周飞舟总结中国学界之共识曰:中国社会中“关系”之发达程度及其对于社会运行起作用的程度远超过“social network”或者“personal relationship”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因为这种关系是以家内人伦为原点的。(10)参见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载《社会学研究》,2018(1);《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载《学海》,2019(2)。已有不少学者基于中国文明和社会的这一特点发展关系主义理论,老一辈学者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等著作中揭示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特征;费孝通在《乡土社会》(1948年)等著作中揭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其中都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并初步揭示了其生存论的基础。海外本土社会学、心理学者杨国枢、许烺光、黄光国、何友晖等人对华人社会中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11)这方面的综述参见黄光国:《论华人的关系主义:理论的建构与方法论的考量》,载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国内也有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12)参见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但是,这类研究普遍有中国特殊论倾向,视关系为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未对其进行普遍化理论构建。美国学者安乐哲有普遍理论意识,依儒家由亲亲而成就之伦理的关系性,对个人主义展开批评。(13)参见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第二次启蒙:超越个人主义走向儒家角色伦理》,载《唐都学刊》,2015(2)。总体上,上述研究多偏于伦理学、社会学理论研究,较少将其作为普遍的方法论议题进行探讨。
本文试图弥补上述两个缺憾,基于“生生论”深化方法论关系主义至其本体论层面。生生论是由“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生烝民”(《诗经·大雅·烝民》)等论述所构建之中国式宇宙论,其基本含义是,宇宙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生而又生,生生不已,此即“实在”或“本体”——这是一种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本体论。现代学者中,哲学家熊十力、方东美、张岱年等人发展或论及过生生论。(14)参见熊十力:《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载《熊十力全集》,第七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张岱年:《〈易传〉的生生学说》,载《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晚近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儒学、哲学领域学者超越了社会学所关注的人伦层面,探究本体论层面的“生生论”:李承贵提出“生生之学”(15)李承贵:《从“生”到“生生”——儒家“生生”之学的雏形》,载《周易研究》,2020(3)。概念,杨泽波发展“生生伦理学”(16)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丁耘和吴飞就生生问题展开讨论(17)丁耘:《生生与造作——论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载《中道之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吴飞:《论 “生生”——兼与丁耘先生商榷》,载《哲学研究》,2018 (1)。,孙向晨通过对家的研究探讨生生论(18)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217-27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笔者通过解读《孝经》,发掘其所蕴含的“生生之教”(19)姚中秋:《孝经大义》,284-28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生生论作为中国式的宇宙论,足以作为思考人与秩序问题之出发点。
本文尝试将哲学领域的生生论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关系主义接榫,为后者构建普遍而坚实的基础。首先,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预设进行批判性解读,进而解读《论语》《孝经》关键语句之大义,追溯关系至人有其生命之生物学事实,即人因父母之生养而有其生命;人生而在“亲亲”关系之中,“亲亲”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关系,因而是终极性的,并且是普遍的;在亲亲关系中,人生成、发育出普遍的合作倾向和组织倾向,从而构建各种社会关系和组织(包括国家)。基于生生论的关系主义足以作为研究人与社会的各门学科之出发点。
二、由生生理解人的存有
今日关于人和秩序的主流理论基本上发源于西方,由西方早期现代思想所奠基,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其中最为典型而重要者,其率先提出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思想,可谓现代社会理论大厦之基石。然而,这套思想在其根基处即难以成立。
在《利维坦》第13章论自然状态之开篇,霍布斯想象其中之人的状态如下:“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20)霍布斯:《利维坦》,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为自然状态概念辩护者说自然状态不在历史中,而是为展开理论思考所想象之预设。然而,想象亦须合乎情理,始足以为此后推理之可信起点。霍布斯所想象之自然状态中人在体力和智力两方面的“相等”合乎情理否?所谓合乎情理,标准十分简单:合乎人有其生命、且作为种群持续地存有之自然。一种理论,如果有悖于人有其生命之基本事实,因而否定了人,或者虽有人但不能生,其人群一世而亡,即为不合情理。
那么,人是如何得以存有的?人是被生而有其生命的,男女交合而生人,此为基本生物学事实。若确有必要在理论上构造所谓自然状态,则显然不能只有一人。可持续、可维系之自然状态,也即合乎情理的初始自然状态,至少由二人组成,且为一男一女;若有多人,其中之男女数量亦应大体相当。
借用霍布斯方法可以说,更为合乎情理的初始自然状态中有一男一女。果如此,则此一男一女是霍布斯所说的“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否?从生理构造上看,男女明显不同,两者至少在体力方面有明显差异,其心智亦有不同趋向。此一男一女相爱、结合,生出第三人,为生物学之必然,亦为人作为类而持续存有之基本保证。如果我们一定要想象一个稳定的“自然状态”,那一定是一男一女与其子女组成的“三人社会”。
所有人都知道,此第三人生而处在极为幼弱的状态,其与生他的两个成年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乎?此身心两方面均十分幼弱的婴儿将会发育、成长;相应地,其父、母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渐趋于退化;过了生命周期交叉点,强壮与衰老对比分明,其“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乎?
至此,我们在三人所组成的最为简单的人群、即人作为类维持存续所需之稳定自然状态中,看到了身、心两方面之两种明显的不相等:男女之别,长幼之别。此不相等贯穿三人生命之全部,在任一时间断面上,人类均存在这两种不相等。若放大此自然状态中的人群至百人、千人,其在身心两方面的不相等将更为多样而显著。可见,合乎情理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一定是异质的,至少有男女之别,由此自然有长幼之别,此为任何人群持续存在之基本前提,不论其在自然状态还是文明状态。此事实即是社会理论之可信的基点,而霍布斯关于人之同质的论断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不足以作为社会理论之基点。
再看霍布斯第二句话:“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其第三句:“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21)霍布斯:《利维坦》,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其所谓“丛林状态”说即由此而来。但此推论均基于人之普遍同质,且大体可以推测,其为同质的成年男子。(22)吴飞指出:“我们完全可以推测,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应该和基督教中的伊甸园一样,没有婴儿和养育的问题,每个人都是成年人,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和身体力量。”(参见吴飞:《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1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笑思则称西方文化有“成人中心主义倾向”(参见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73-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这显然是荒诞的。
而在我们提出的更为合乎情理的初始自然状态中,一男一女会相互成为仇敌否?当然不会。男女有别,其性相异,可以互感,以至于两情相悦,终于互爱而结合,决意共同生活,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两者所建立的关系可有多种,但无论如何,不会“力图摧毁对方”。两人与其共同的孩子也不会成为仇敌。相反,这两个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远超孩子的成年人会爱其孩子、保护其孩子、养育其孩子。
至此已可断定:霍布斯所想象的自然状态一点都不自然(natural),而完全是人为的(artificial),并且是虚妄的、不合情理的。霍布斯也认识到了人有其生命之自然事实与其所谓“自然状态”之间的不兼容,因而对人之有其生命的程序给出令人瞠目的解说:“我们假设再次回到自然状态,将人看成像蘑菇一样刚从地上冒出来”(23)霍布斯:《论公民》,88、“献辞”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这句话是霍布斯“自然状态”说成立之关窍所在。
霍布斯此语实源出苏格拉底用以教育城邦守卫者的“高贵的谎言”:他要这些城邦守卫者相信,自己不是父母所生,而是大地母亲所生,大地送其上来时即已为成年人,扛着自己的武器。(24)柏拉图:《理想国》,12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这一渊源清楚证明,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同质的、好斗的成年男子。(25)李猛对此和霍布斯蘑菇比喻有所分析,参见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169-17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同样作为霍布斯的思想渊源之一,《创世记》记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为神所造,被造即为成年人,被造即立刻结合。
总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霍布斯,西方两千余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经典《理想国》《创世记》《利维坦》共同忽视、甚至刻意否定人的生命来自其父母之基本事实,而相信人是被造的,被造而为同质的成年人,则谓此为西方文明之共同的主流认知,当不为过。
西方社会理论正奠基于此,其普遍预设人是彼此孤立的、有相等理性、共同偏好的成年人,乃至于成年男子。如此高度简化的预设确实便于理论推导,其命题、逻辑“像数字关系一样确切”(26)霍布斯:《论公民》,88、“献辞”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但这也意味着其非现实性、不合情理。据以形成之社会理论及其所支撑的各门具体学科理论,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难免有严重偏颇,不足以准确地理解人心、理解人的行为、理解秩序生成之道。比如,由于只见成年男子,其理论所关注的议题均为成年男子所关注者,如财产权的形成和归属、权力的产生和归属、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等。由此,霍布斯等人发展了纯粹的、同时也是狭隘的政治理论。财产、权力、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对社会之构造、秩序之形成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显然不是关乎人的生存和生生不已之全部,甚至也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必须重建社会理论的基本预设。以上批判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过程中,实已确认了关于人的基本事实:人分男、女,必结合生育孩子;生生不已,人类始得以存在。此乃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道之大本正在于此,关于人和秩序的理论须由此出发,由此即可构建基于“生生论”的关系主义社会理论。
关于人和秩序的所有理论,须先回答如下问题:人自何处来?如何有其生命?《孝经·开宗明义章》对此做出平实中正的回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27)对此句大义的详尽阐述,参见姚中秋:《孝经大义》,20-2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人的躯干、四肢、头发、皮肤,总之,人的生命得自其父母。人由其父母所生,此为关乎生命之有无的根本论断,此论断描述了最为简单、完全真实无妄而至关重要的事实。此事实颠扑不破,且为所有人可经历、体认、确定。儒家思想关于人和秩序的理论即立足于此。
当然,在中国思想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不是孤零零的,而有其深厚的天道论基础。《周易》并建乾、坤(28)这一点为王夫之所反复强调,参见其《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上》)。《周易》下经始于“咸”卦,乃男女两性互感也。《周易·系辞下》曰:“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的男女概指植物、动物之雌雄,也包括人之男女。《诗经》以《关雎》为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男一女,男女互感、相悦,“寤寐求之”,而成佳偶。《尚书》记尧舜之事,以舜娶帝尧之二女、正夫妇之义为枢纽。(29)《尚书·尧典》记:“师锡帝曰:‘ 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对此段经文的解读,参见姚中秋:《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129-13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可见,中国思想立足于天地、乾坤、阴阳、男女之有别、互感而生这一最坚固的事实,人生、宇宙就是阴阳交感、生生不已的过程。如果一定要用“本体”这个词,那么生生就是本体。
肯定了人是其父母互感所生,则必有如下命题:人虽同为人,但相互异质。首先,男女是异质的;其次,男女结合生其子女,其形貌、气质有相“肖”之处,也有或大或小的“不肖”之处,故为异质;最后,不同夫妇所生之人更是相互异质的。《孝经》之所以强调人之“发肤”,盖其为可供识别、区别之最明显体征也。身体发肤不同,其性情、气质、禀赋、能力也必定不同,是为人的普遍异质。
肯定人之普遍异质,即肯定人群构成之复杂性,社会理论才有可能是完整的。社会理论分析人的行为及其互动而生成秩序之道,但人之为人是异质的,则有效的社会理论必须完整地涵盖所有人,起码涵盖男女、长幼之别。男、女、长、幼的心智、行为有明显差异,社会理论须同时观察其人及其互动模式,由此所形成的理论才是全面而有效的。如《礼运》关于大同之世的论述清楚呈现了儒家社会理论之全面视野所造就的政治之全覆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是政治的基本原则;就不同群体分别提出相应关切:人有代际之别、年龄之异,各有不同需要:“壮”关心“有所用”,“老”关心“有所终”,“幼”关心“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关心“有所养”,则“选贤与能”所产生的治理者不能笼统地维护正义,而要具体回应不同群体之不同生命需求——或者说回应同一人在不同生命阶段、情境中的不同需求,使之各得其所。“男有分,女有归”即肯定两性之别,则有婚姻之需要,政府即应确保男女普遍过上婚姻生活,并有生活所需之财产保障。从纯粹政治角度看,人群中的男女是否普遍地过婚姻生活并保持基本生育率,完全无关紧要;但政治共同体要长期稳定、存续,这一点显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儒家社会理论将其纳入思考范围,认真对待,由此形成的理论体系比霍布斯式政治学要厚实得多、复杂得多。(30)翟学伟通过分析“伦”字的含义指出了这一点,参见翟学伟:《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载《社会》,2016(5)。
更为重要的是,三人社会是以生存论意义上的“关系”为纽带的:男女是相互定义、相互构成的;男女建立最深切的关系、共同生养子女,人类始得以持续存有。人生于男女关系中,此关系又造就亲子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人作为个体和群体赖以之存有。谓之生存论意义,意谓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不是人为构建的产物,而内在于人有其生命且继续其种群的事实之中。因此,方法论关系主义是自然的、“先验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反而是人为构建的。
在具有生存论性质的夫妇、亲子关系中,内涵亲亲、尊尊之义,从而内生出社会科学理论之两大基石:自然的、普遍的合作意向与组织倾向。
三、亲亲与人类普遍的合作倾向
确认人由其父母所生、且出生后将在其父母怀抱之中生活两三年的事实,即可建立方法论关系主义的第一个基石:在生存论意义上的关系中,人自然地有相爱相敬之情,从中发育出人类普遍的合作倾向。
从生理上看,人出生后一段时间处在极不成熟状态:不能行走、言语、自行觅食、保护自己。孩子已有独立的“身体发肤”,却不能不依附父母。孔子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提出如下命题:“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在生命最初两三年中,孩子与父母的身体虽分立而其生命实仍为一体。(3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张祥龙在《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四章《孝道时间性与人类学》中的详尽论述。
两三年之后,孩子仍需父母养育:父母为孩子提供食物、住所、衣物;教其辨析好坏,教其躲避危险;教其说话,教其认识各种人、物,教其与人相处。总之,在十几岁前,孩子始终依赖父母,经由父母的养育而成长,通过父母的教化而完成“社会化”过程。社会化是社会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其实主要完成于家内。
由此,父母与其子女建立起紧密关系:亲子之伦。男女两情相悦,有肌肤之亲,其关系至为亲密;亲子关系更进一步,关乎生死:父母悉心照顾孩子,孩子得以存活。反过来,孩子之存活和健康成长关乎父母之永生:从生物学上说,父母的基因遗传在孩子身上,其身体死去后,基因可保存于子女之身,呈现为活的生命;孩子继续生育,生生不已,则死者可得永生。
大约正是基于本能,父母对子女有深爱。前面我们已辨识出男女相亲相爱之情,正是由于此情,夫妇生育孩子,并生发第二种情:父母对子女之情。相比较而言,男女之情有情感交换的功利色彩,父母对子女之情却是慷慨无私的。不过,此情可能出乎遗传基因之本能,仍不够纯粹。最为纯粹的是孩子对父母之深情,即其爱、敬父母之情,合而言之即为孝,儒家乃立之以为普遍的仁爱之本。(32)唐君毅论孝之形而上学根据与其道德意义,见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29-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子女对其父母之深情,发乎前述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天地之间本无孩子的生命,是为无;由父母之相亲、生育,孩子得以有于天地之间。就此而言,父母是孩子的“造物主”,是其生命之本,则孩子必有报本之情,体现为爱、敬父母之深情。
第二,“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此处主语是“子”,人在有其生命后的最初行为是依偎于父母怀中。在孩子被孕生的事件中,主体是父母,孩子只是被动的“受”者,无以预其事。出生后依偎在父母怀中却是孩子的行为,从中可见其“本心”。且此为孩子的第一行为并保持相当时期,则此心的呈现可谓稳定而明白。
此心者,何心也?由孩子长时间依偎的行为可分解出其对父母之两大情感:爱与敬。此二情是与生俱来的,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此处谓敬是对兄长的,实际上最初的、也最自然的敬首先是对父母的。爱、敬父母之能和知是人生而即有的,故谓之 “良能”“良知”。《孝经·天子章》同样肯定此良能、良知:“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人皆有爱其双亲、敬其双亲之情,此为生而即有之情,自然就有的行为。
至此,我们辨析出人际自然生发之三种情:首先是男女夫妇相亲相爱之情,其次是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情,再次是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情。家人相互联结之纽带主要是情,而这关乎人的有无死生。由此可得出一般性结论:人是有情的。孟子所说的良能、良知,首先是情之能与知。人最初发育的能和知关乎情,并因情而生存、成长。尔后在人生各阶段,情都是其生存、生活、包括参与公共生活之基础性能与知。比如,面对陌生人之“博爱”即是情,人无此情,则无普遍秩序可言。
当然,人亦有理智,且于人相当重要。但相较而言,情对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男女有相亲之情,得以结为夫妇;夫妇人伦之成立,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基于对成本收益之理智计算。子女与其父母相互有深爱之情,其间人伦关系的维系同样不是基于对成本收益的理智计算。蒙培元提出如下命题:人是情感的存在(33)参见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李泽厚晚期思想之最大贡献也在于提出“情本体”(34)参见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中华书局,2015。。理性是在情感性关系中发育成熟的。其实,这不是中国思想所独有的,现代西方思想谱系中,苏格兰道德哲学传统如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休谟、斯密等人均十分重视情感的作用,并强调情感先于理性(35)参见张正萍:《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只是他们未追溯至情之本:亲亲。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由人生最初始处之情感倾向和自然行为可确认人之性:性本善。中国思想对此还有更高明论证,如《周易·系辞上》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但人人经历、可见、可知的生命得自其父母、生而依恋父母之事实,是最切身且可信的人性呈现,人性见于其爱、敬父母之情中。孟子谓爱、敬父母为“良能”“良知”,正是肯定人性善,谓之“良”者,或有四层含义:其一,爱、敬父母之能、知系与生俱来,自然而有,是先天的而非后天的;也因此,其为人人所有,遍在人心。其二,爱、敬父母之能、知是良的、善的、好的。爱、敬本身是善的,针对任何人都是善,针对父母当然是善。其三,爱、敬父母之能、知有良好功效,新生者因此而得以存活,因此得以成长。其四,爱、敬父母之能、知足以为普遍的仁之本。《论语》第二章记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就解决了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社会科学所致力解决的合作难题。霍布斯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人人“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则其后面的论述难免令人生疑:心中相互为敌之人何以产生相互订立契约之意向?即便理智的计算告诉其应相互订立契约,处在敌视他人心态中的人又何以相信对方是可信的?会有人迈出第一步吗?否定了互爱之情,霍布斯所期待于理智的解决方案,无异于期待人揪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后世据霍布斯式思想发展出来的“理性经济人”预设面临类似难题,而这构成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之基础。如此预设陷入理论困境后,这些学科不得不返回来重建其基础,研究利己的人如何开展合作。但此研究始终进展不大,因为其间面临一道鸿沟。(36)这方面的经典研究,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其第一句话即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3页)他的答案是:采用“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策略,利己主义者中可形成合作。此策略之第一规则是,第一步选择合作,据此,此策略有“善良性”;接下来则根据对方的选择,一报还一报(21-22页)。但他始终没有回答一个前设性问题:人何以在第一步选择合作?学界近些年来的最新发展试图超越这一问题,比如行为经济学通过试验论证,人本身有合作倾向。(37)参见叶航、陈叶烽:《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儒家思想为人类的合作倾向提供了本体论证明:人人生而皆有爱、敬父母之情,父母与其子女天然是合作的;爱、敬父母之情如同草木之根,可以生长:子生三年,在父母之怀抱中,养成爱人、敬人之心智习惯,习得爱人、敬人之技艺。最初的爱、敬之情是个别地针对父母的,随着其人伦生活范围扩展,其特殊性递减,可扩展及于对兄弟、对祖父母、对亲戚;当其可以独立活动时,则可以进一步普遍化,扩展及于对朋友、对陌生人,此即所谓“推”,就是把自身本有、但较为特殊的爱、敬之情,逐渐地予以一般化,升华为普遍的合作倾向。推是可能的,因为人都是人,都有其爱人、敬人之本;推又是必要的,因为人毕竟相互不同,爱、敬必定不同。因此,推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方法论。(38)参见王建民:《“推”与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学本土化视野下的理论与方法论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2020(1)。正是在推的过程中,理智发挥重要作用,辨别并制定不同行动策略,即《中庸》所说:“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由此,儒家找到了可扩展的普遍合作秩序之人心基础。这种扩展发育当然可能遭遇困难,也未必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很好,但其所遭遇的困难终究小于霍布斯等人所构造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想象自然状态,想象其中之人性恶,但又以此为已进入社会状态的人性预设,本身就犯了错置谬误。一旦预设人性恶,理论关切必然聚焦于人如何走出自然状态,即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社会的开端问题,却忽略社会的过程问题;或者更严厉地说,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想象的问题,却忽略现实的问题。
儒家避免了这一理论的失焦和资源浪费。人因父母之生而有其生命,生而即有对父母的爱、敬之情,此情即呈现人性之善;肯定这一点,则理论的关切就专注于此特殊的爱、敬之情如何发育、扩展,以生成和维护可扩展的人类普遍合作秩序。由此,儒家不仅讨论政府如何做,也讨论个体如何做,从而发展出道德修养理论,构成其社会治理理论之基础部分。由此,人被普遍地肯定为主体,参与秩序的塑造和维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从马基雅维利开始,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家普遍倾向于驱逐道德出政治,因而其普遍没有道德或伦理理论。(39)列奥·施特劳斯评论说:霍布斯为政治哲学奠定了新基础,“必定成为合乎理性的政治主张之基础的激情,乃是对横死的恐惧……在这种崭新的基础上,道德的地位必定会被贬低;道德无非是由畏惧所激起的对和平安定的追求。道德律或自然法则被理解成派生于天赋权利、自我保存的权利;根本的道德事实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这种新精神变成了近代的精神,也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见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册,326-32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在其所构想的社会中,个体完全无意主动参与良好社会秩序之生成和维护,只是被动地等待外在法律、制度之管理。在如此社会理论中,人丧失了主体性而完全对象化,从而让秩序成为不可能。
四、亲亲与人类普遍的组织倾向
父母生养子女而构成家,人生而在家中,人是家的存在者。家对人而言是自然而普遍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组织,由此事实即可建立方法论关系主义的第二个基石:从生存论意义的组织中发育出人类普遍的组织倾向。
人分男女,其性相异则必互感,以至于相悦而结为夫妇,两者形成有情意的关系,即为夫妇之人伦,是为人伦之始。由此,夫妇组成初始的家。因男女之异质,这个最小社会单位内生出自身可持续之机制:在共同生活中,两人皆可发现共同生活之优势;双方分工、合作,各自发挥优势,借用对方优势,共同生活、生产的效率必定高于单独一人时,比如两人合作养育遗传其共同基因的子女,可大幅降低其死亡率。男女有别、分工合作的高效率构成人们保持稳定人伦关系之强大内在动力。同时,夫妇之有情意的人伦有其生机,生养其共同子女,形成亲子之间的人伦。以夫妇和亲子之伦为双重纽带,三人组成完整的家,此为最自然、最小而又最稳定的社会组织。
借用西方学者用语,当在本体论层面上理解家。(40)参见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294-31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家不是家内成员依其自由意志、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外生性组织,而是与人有其生命、保有其生命之事实同在、自然而有之内生性组织。有人,就有家;没有家,就没有人。借用孟子之语,家可谓“良群”。谓之“良”者,其意有四:第一,家之为人群组织是自然而有的,且人人皆在其中,家是最普遍的组织。第二,家之作为组织本身是良的、善的、好的。家是以情感为联结纽带的,其中充满情意,不仅有同代人之情,还有跨代、甚至超越生死之深情,这些情都是善的。第三,家有良好功效。人于其最接近于生、死的两阶段均在作为良群之家中,仰赖其中之良序而活。第四,家足以作为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之本。由家可以扩展、转化、衍生出人类一切组织,从而增进人群之善。
人类组织的基本原则无非有二:“亲亲”和“尊尊”(41)《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春秋繁露·王道》曰:“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韩诗外传》卷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见,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亲亲即亲近自己的亲人,由此可结成有情意的紧密的组织如家、族。只要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即可以产生亲情,由此亲情即可联结成为亲亲类组织。至于陌生人之间的组织纽带主要是尊尊,其中之人有尊卑之别,卑者尊重尊者之权威。亲亲、尊尊作为组织原则,各有其适用范围:亲亲通常需要面对面长期共同生活,故其所能结成的组织之规模是有限的;尊尊的规模可以无限大,只要人们顺从某个权威即可。社会中大规模的组织比如大规模企业和更大规模的国家,普遍以尊尊为主要组织原则。尽管如此,大规模组织的尊尊之义,已内含于家这个亲亲类组织中。当夫妇组成家,作为组织,其有效运作必然要求其中有领导者、被领导者之别,方可就重要家务有效决策,只是这一点不甚明显。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则有明显尊卑之别,尤其是在孩子未成年时,心智、能力的明显区别让父母为尊、孩子为卑,父母教导孩子,命令孩子;孩子尊重父母,顺从父母。正是在此亲子之伦的生活实践中,孩子得以养成尊重、服从权威之心智习惯,由此即可发展出公共生活的尊尊之义。
此正为《孝经》要旨所在,如其《圣治章》所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重要的是“因”“本”二字。“因”者,就也,就已有者予以发育、扩充;圣人所因之本有二:父母对子女之严和亲,由亲可发育出仁爱之心,由严可发育出尊尊之义。《孝经》的论述也表明,亲亲与尊尊不可分,因为亲、严同出于父母。更进一步说,家中的尊尊是以亲亲为本:严以亲为本,父母教化、命令子女,系出于对子女之深爱;正因为此,子女信赖父母,乐于顺从父母。
由此引申,公共生活中的尊卑秩序得以建立并维护之基础也是在上位者、在下位者普遍有基本的仁爱之心,由此卑者信赖尊者,乐于服从其权威。(42)西方学者比如霍布斯也注意到家与国之间的联系,却否定家人之亲情,反向地把家内关系政治化,以为家长是孩子的主人,孩子类似于奴隶,可见霍布斯:《论公民》,93-10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此即《大学》所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忠”。当然,这种普遍的仁爱之心又是以普遍的亲亲之情为本。就尊者而言,要有“作民父母”之心,《尚书·洪范》最早提出:“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诗经》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大学》解释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君王以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情对臣民,此为国家得以建立并维系之基本条件。由此所构造的大规模的组织如企业或国家均为“人伦共同体”,意即成员之间、君臣民上下之间是有情意的。由此形成中国式国家观念:国家是有情意的共同体,国民生老病死于其中,互为“同胞”——这是一个凸显情意的隐喻。
因此,家是人类组织化生活之本。(43)肖瑛提出,家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总体性的和“根基性的隐喻”,主张以家作为“方法”构建中国社会理论,参见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11)。对此,有人以“古今之变”提出反驳:由于人员快速流动,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因而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本乎家,或许可以构造古代社会,却不足以构造现代社会。(44)比较常见的古、今二分说有英国法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中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中提出的共同体与社会二分法。但略加考察即可发现,此说不确,就社会而言,首先,不论古今,人都生于家中、生活在家中,不可能存在无家之人;家在族中,人也必定在其族中。在家中、在族中,人们相互之间是亲人,长期面对面生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大多数事务展开于家中、族中,也即在大多数时间,人生活于熟人社会中。其次,人始终在家内生活,由此养成其对人的最基本信任,可谓之“信任偏好”;当其遭遇陌生人时,不将其视为潜在敌人,而以情意对待之。以此为起点,其人可以迅速建立合作关系,进而组织起来。在组织内长期共同活动,相互熟悉,情意加深,即成为熟人或某种程度的“亲人”,此组织即演化为人伦共同体。此为陌生人的“熟人化”过程,可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也让人心“安”下来。可见,不论古今,只要人由其父母所生而有其生命,则社会必定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人们必定以在其中所养成之心智习惯构造各类组织,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家、族的性质,唯有如此,组织才是可持续的。因此,笼统的陌生人社会概念无益于准确地揭示人的生存状态。
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确实有较大区别。但是,现代国家也不是霍布斯所说的那样,完全由相互孤立的陌生人通过订立契约建立起来。事实上,洛克《政府论》(下篇)设想的自然状态中是有家的,家先于国家而存在。在现代个体性原则确立之后,黑格尔曾对家做过辩护。(45)参见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148-18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现代国家仍由人组成,人必定生养于家中。因此,家—国贯通的道理是永恒成立的。当然,在不同文明、国家中,两者的关系确乎不同,但思考国家问题之时无视家,则悖乎最基本的事实,而此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在家中,人们才养成了组织倾向、服从意识,这是国家建立并存在的前提。家、国在组织原则上确有巨大差异,但绝非性质上的截然不同,而是程度上的差异:人终究首先是家的存在者,以此生活在国中。生命存有的事实本身把家和国构造在人类组织的连续统中,因而家是国的构成性要素,并且是其“本”。即便现代西方人,也首先生活在家中。(46)家也没有从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退场,参见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11)。
儒家以为,至大如天下也可成为一家人,《礼记·礼运》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值得注意的是“家”字。天下秩序最为普遍,而其状态是所有人成为一家人,互为亲人,互爱、互敬。可见,家是天下秩序之范本,也是其基础,天下人相互善待之情感倾向和能力来自人人与生俱来之良知、良能、良序、良群。从最小的人群组织单位——家,可以直通最大的人群——天下。
今日中国倡导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本乎此“天下为一家”观念,本乎张载《西铭》之“民胞物与”观念。世人如同家人一样有情有义,互敬互爱,相互帮助,才可能生成、保持共同体之感。(47)参见徐勇:《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家户起源》,载《南国学术》,2019(2)。西方人构想的国际体系或世界秩序单纯依靠理性,实即单纯依靠利益计算,其结果是各国、各人貌合神离,甚至经常陷入霍布斯所欲逃离之战争状态。出于中国文化脉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则以家为本,以情驱动,推己及人,以义统利,故可行而可久。
五、结语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西方特定的宗教、文明背景而构建的地方性知识,遮蔽了人之为人的基本事实,或可谓之思想的“蒙昧”,因而赵汀阳把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转向关系主义称之为“深化启蒙”,安乐哲则称之为“第二次启蒙”。本文基于中国传统的“生生论”,从人之有其生命的自然事实出发,为超越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关系主义构造了一个生存论的本体论的证明,其基本主张可概括如下:
第一,研究“真实世界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尖锐批评“黑板经济学”,倡导发展“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一诫命适用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真实世界中,人是因父母之生养而存有的,这是全部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的出发点。
第二,“太初即亲亲。”
人分男女,男女必然结合,人类始得以存续;人被生在亲亲关系之中,此关系是超乎理性选择和意志自由的。因此,男女、亲子关系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是人和社会的“造物主”。这一生物学事实决定了人自然地是关系的存在者。
第三,人是有情的。
在生存论意义的关系中的人是有情的:男女有相悦之情,父母慈爱其子女,子女爱敬其父母。此为人所具有的三种基本情感,外“推”则有多种人际之情。人际秩序之维系纽带首先是情,理智是在有情的关系中发育成长的。情在关系中,情先于智。
第四,亲亲关系就是合作,人自然地有合作倾向。
男女相悦,必定结合;通过合作,生养子女;父母与子女之间通过跨时的、代际的合作,维系生命之存在、更替与族类之存续。亲亲的合作倾向是人的构成性因素,它使更大范围的合作成为可能。
第五,亲亲关系内涵组织,人自然地有组织倾向。
人因家而有其生命,是家的存在者。家是一个组织,其中有长幼尊卑之别,内涵公共性,是更大规模的组织之本。人在家内养成过公共组织生活之心智,习得构造和运作一般社会组织(包括国家)之技艺。
第六,生生不已是人类最高价值。
人被生而有其生命,生命之目的就是生和生生不已。文明、国家、各种组织之宗旨是“厚生”(《尚书·大禹谟》)(48)参见姚中秋:《厚生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载《文化纵横》,2020(1)。,即改善人的生活,让所有人共生,且生生不已。
由以上命题可以发展“经济的”、但又是“厚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它不去庸人自扰地讨论人为什么合作、组织等起源性问题,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讨论如何改进其合作和组织。为此,它会发展修身、道德理论;与之相配合,发展教化理论;探讨家的治理之道,进而探讨由家扩展而成的、具有一定社会自治能力的社会性组织的建立、维护和治理之道,以及其他陌生人“熟人化”机制等;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探讨政府如何积极地发挥作用,回应异质的民众的多样需求;最后探讨普遍的天下秩序的维护之道。
这套“厚的”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中国特色的,但不是特殊论的,而是更普遍、更“大”的,因为其立基于人有其生命的普遍事实,无关乎种族、宗教、国家等。这样的“大”理论与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预设而构建之西式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不是对立的,可将其视为对于边际性人类行动的研究,涵摄于内,加以利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