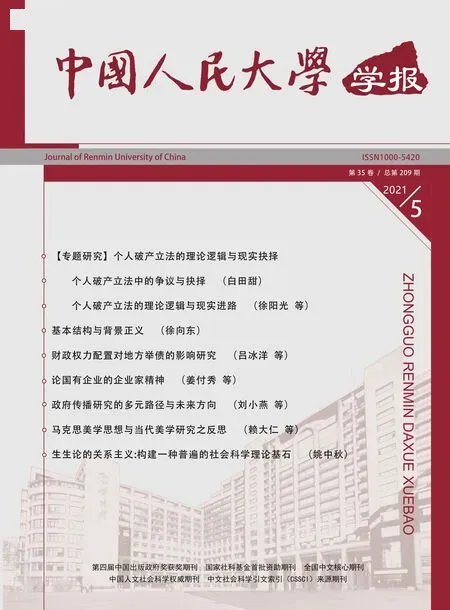政府传播研究的多元路径与未来方向①
2021-01-03刘小燕崔远航
刘小燕 崔远航
面对当前社会结构变革、国际政治变局、国际传播环境的复杂多元以及中国施政理念的与时俱进,有必要基于政府传播的经验或实践探索,讨论并构建适应于新时代的政府传播理论体系,并总结其实践规律。这也意味着需要对前人相关研究予以系统梳理与客观评估,了解当前学界已形成的多元认识(如所发现或挖掘到的政府传播规律等)、关注的热点与有待填补的空白点,从而为构建中国政府传播理论体系并探寻其实践规律奠定基础。
国内外学者虽早已在“政治传播”领域内对政府作为主体的传播活动有所论及,但若以“政府传播”或“government communication”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JSTOR等中外学术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则可见此类研究普遍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一主题的研究数量显著增加。在中国,2008、2009年后研究数量明显上涨,出现诸多研究者及相关论著。(1)如荆学民的《政治传播活动论》(2014)、《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巡检》(2014)、《政治传播简明原理》(2014),刘小燕的《中国政府形象传播》(2005)、《政府对外传播》(2010)、《政治传播中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研究》(2016)、《掌握话语权:政府传播基本问题研究》(2020),白文刚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2014),李彦冰的《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2014),苏颖的《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下的探讨》(2016),高波的《我国政府传播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6),黄河主编的《政府新媒体传播》(2012),谭玲主编的《政府传播——理念与实践》(2013),等等。
整体而言,研究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政府传播”研究位于政治学、传播学二者交叉重合之处(2)孙帅:《政治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回顾与展望》,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1)。,既不等同于政治传播,又不等同于大众传播或组织传播。尽管当前诸多政府传播研究得以覆盖传播“五要素”的所有环节,既有微观分析政府内部决策过程,也有宏观探讨政府传播模型,视角丰富,路径多元,但恰恰因其与两大学科之间边缘界限模糊,总体来看,当前研究无论从概念界定、研究对象选择还是对同一研究问题的基本判断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其背后也显示出交叉学科领域的困境:政治学领域侧重讨论政治行为、权力形式及关系,传播学领域侧重剖析信息传播过程,对于“政府传播”这一研究主题,政治学尤为关注政府这一传播主体的决策过程与功能实施、公众作为传播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将政府施政行为纳入政府传播活动;而传播学特别关注社交媒体等新兴传播渠道发挥的作用、政府形象有效塑造的方式和政策法规传播带来的舆情治理问题,并且政府对外传播活动也被视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这样的学科分歧进一步体现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则可见不同学科自说自话,仍缺乏普适性的效果评估研究。
由此可见,当前不同的学科视野已然在研究实践中发生摩擦乃至碰撞,导致诸多关键性问题难以达成共识,也难以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本文尝试梳理现有政府传播研究状况,比较分析其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上的共识与分歧,探讨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差异对现有研究路径的影响、未来的政府传播研究有哪些盲点或空白尚待关注或填补。
一、“政府传播”概念范畴的学科分歧
虽然研究者在政府传播的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即这一传播活动是为了增强公信力和维持政治合法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执政施政目标)(3)如Brooke Fisher Liu,J.Suzanne Horsley,and Kaifeng Yang.“Overcoming Negative Media Coverage:Does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Matter?”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2,22(3):597-621;Toni G.L.A.van der Meer,Dave Gelders,and Sabine Rotthier.“E-Democracy: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ge of E-Government”.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2014(4):489-506;刘小燕:《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高波:《我国政府传播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但对于何类活动可被视为“政府传播”这一问题则显示出鲜明的学科差异,概念界定出现根本性分歧,相应地在解释效力上都有所不足。
具体而言,在政治学角度下,政府传播被视为政治传播的一部分(4)如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载《政治学研究》,2001(3);李智:《论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载《现代传播》,2006(4);J.Strömbäck,and S.Kiousis.“Political Public Relations:Old Practice,New Theory-Building”.Public Relations Journal,2013,7 (4):1-17.B.McNair.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New York:Routledge,2011。,是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之一,表现为施加信息控制或实现社会治理,即执政者和公共机构官员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实行的一国国界范围内的传播”。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包括卡纳尔(Canel)和桑德斯(Sanders)、薛松岩、任景华、郑保卫、潘晓慧等。(5)M.J.Canel,and K.Sanders.“Government Communication:An Emerging Field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H.Semetko and M.Scammell(eds.).The SA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12,pp.85-96;薛松岩:《中国政府传播实践探析》,载《中国出版》,2018(10);任景华:《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信息传播策略建构》,载《现代传播》,2018(10);郑保卫、李鹏:《大数据时代的政府传播模式变革与理念创新》,载《现代传播》,2016(12);潘晓慧:《基于大型国际活动中的政府传播实证研究》,载《今传媒》,2015(12)。在这一界定下,“政府传播”不仅仅指信息类(话语)传播活动,政府本身的施政行为也同样被视为政府传播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笔者认为政府传播应主要由政府行为与解释政府行为两类内容构成,并非仅仅是政府传播客体所能接收到的信息的传播,同样也包括政府施政行为的传播。(6)刘小燕:《政府对外传播》,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刘小燕:《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刘小燕、崔远航:《政府传播与制造认同》,载《现代传播》,2011(6)。
从大众传播角度考察的研究者,则仅将政府传播视为能够依托某种渠道或媒介所展开的信息(或者说“话语”)传播活动,典型可见程曼丽的界定“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政府面对大众进行的传播”(7)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这一概念也多被人引用。部分学者甚至进一步将之等同于政府形象传播,即政府通过各类信息传播活动打造和维护(政府)品牌形象。(8)M.J.Canel,and K.Sanders.“Government Communication:An Emerging Field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H.Semetko,and M.Scammell(eds.).The SA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SAGE,2012,pp.85-96;M.Howlett.“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s a Policy Tool:A Framework for Analysis”.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9,3 (2):23-37;R.E.Hiebert.Informing the People:A Public Information Handbook. New York:Longman,1981;Brooke Fisher Liu,& J.Suzanne Horsley.Th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Decision Wheel:Toward a Public Relations Model for the Public Sector.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2007,19(4):377-393.
还有部分研究者选择接受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双重限定,采用了政治学中将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国内、大众传播学中将研究对象主要限定于普通民众的界定,将政府传播视为发生在国内、面向政府外部受众的传播活动。但是,主要遵循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学者,往往会更多关注政府内部决策过程以及新闻发布制度落实等问题,以探讨政府作为传播主体的功能角色;主要遵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学者,则将政府在国际范围内的形象构建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有学者在评述既有政府传播研究时认为,我国学界一般并不将政府面向国外的传播纳入政府传播范畴,而将之视为对外传播或国家形象传播;也一般并不将政府内部的传播活动纳入政府传播范畴,而将之视为组织传播。(9)王勇、李怀仓:《我国政府传播研究述评》,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由上述可见,仅在“政府传播”这一概念的讨论上,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不同视野导致了界定上的根本性分歧。若仅将研究严格限定在二者交叉领域,所界定的“政府传播”必然是窄化的概念:政府面向国内政府外部受众的信息(话语)传播活动。这样解释显然效力有所不足,体现在:
一方面,这一界定忽视了政府行政过程作为传播活动的意义,概念的解释效力有限。鉴于福柯等研究者在分析“权力”的表现形式时,提出“微观权力物理学”(micro-power physics)概念,意指社会系统中乃至牵涉个人日常生活,都无不显示出权力运作的痕迹。而作为权力运作的最直接体现,面向民众的政府行为无论有意或无意,都在点滴之间构建或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对政府作为的认同,乃至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因此,若割裂政府的行政过程与对政府行政予以解释的过程,仅将后者视为政府获得公众信任、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路径,则意味着将公众对政府的认知和态度仅来源于各方对政府行为的解释,这就忽视了公众在社会和生活实践中与政府部门及其代理人(如公务员等)直接接触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这一窄化的界定忽视了政府传播活动的多层次,分析停留于表层。于外部而言,在当前互联网环境下,政府对他国的传播活动能够被国内民众知晓,并构成其对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执政合法性认知的来源之一;政府对国内民众的传播活动亦能够被他国民众获知并成为其对该国政府印象的来源之一;政府对国内外传播活动的界限已然模糊,若强行区分以界定其外延,难免概念解释效力有限,出现部分政府的传播活动未能被囊括在概念范围之内的情况。于内部而言,考虑到政府内部的传播活动与其施政行为、对施政行为的解释同样具有影响,且政府工作人员的双重角色(既是某领域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也是另一领域政策的接受方或被影响方)意味着若将政府内部的传播活动与其对外部的传播活动相区隔、将内部传播活动排除在政府传播之外,则极易将开展传播活动的政府主体视为平面、单一、整体性的行为体,而缺失对这一行为体更深层的行为动机及其功能的分析。
因此,对于“政府传播”概念的讨论,采用单一学科视野或严格遵循学科交叉之处的限定,带来了明显的分歧,且其所具备的解释效力各有不足。这样的分歧也进一步体现在相应的研究对象选取及研究路径上。
二、政府传播研究路径的分歧
当前研究者对政府传播的研究仍可基本视为按照拉斯韦尔“5W”展开,集中在传播主体(政府传播者)、内容(政务信息与施政行为)、受众、渠道与效果等五方面。其中若具体考量不同研究对象下的研究路径,仍可见其显著的学科视野偏向:如政治学视野下更偏好对政府传播者、政府—公众关系的分析;对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传播渠道的研究多从传播学角度展开,即较少将之视为政府权力的承载渠道与表现形式,而是更多将之视为政府发布信息的载体;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则可见不同学科视野带来的显著分歧。上述分歧不仅意味着在同一问题的讨论上难以达成共识,还意味着对于“政府传播”这一领域而言,在学科未重叠之处有众多问题未能被深入系统性讨论,而在学科交叉之处又有众多问题难以被涉及。
(一)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偏向: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
1.政府传播主体研究
众多研究者对政府传播主体的研究主要采取政治学的视角,将各层级政府及其内部不同职级的成员视为传播主体。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政府的组织机构与权力运作角度宏观论述其在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政府传播主体进行分类,按照政府级别予以区分,如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层级高低直接影响了其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目标受众的差异,因此有必要按照层级区分为中央、地方、基层三级,地方政府在政府传播体系的地位不可忽视。(10)刘小燕:《多维视角下的政府传播主体》,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15;秦汉、顾桥孜、卢星吉:《政府传播主体探析》,载《青年记者》,2015(24);毛湛文、刘小燕:《新媒体环境下政府传播的新变化——基于传播主体视角的考察》,载《当代传播》,2015(2);刘晖:《中国政治传播体制与政府的多层合法性结构》,载《理论界》,2009(3)。其中认为在当前中国政治传播体制下,低层级政府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是至关重要的。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区分负责设计目标、决定方向等的政府组织与直接从事传播活动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等个体,并对应“政治人”的假设提出“政府传播人”的概念,认为面对政府传播“人性化”发展的要求,应从思维和行为逻辑等角度分析传播主体的动机、与公众的互动、对信息的反馈等。
二是具体论述中央政府或某个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内部决策出台过程、不同级别政府人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对具体传播活动的影响等。此类研究更多关注政府内部决策的出台、制度保障与人员互动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如阿格戴尔-海尔曼德(Agerdal Hjermind)、高波、所罗门森(Salomonsen)、杜艳明、霍斯利(Horsley)等,探讨了开展某项传播活动时政府的人员和制度配置、内部互动、负责人对此项传播活动的认知与践行方式、传播决策动因等。(11)Annette Agerdal-Hjermind,& Chiara Valentini.“Blogging as 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r Government Agencies:A Danish Case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2015,9(4):293-315;高波:《我国政府传播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6;Heidi Houlberg Salomonsen,Finn Frandsen,&Winni Johansen.“Civil Servant Involvement in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Mediatization and Functional Politic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2016,10(3):207-221;Yuehua Wu,and Johannes M.Bauer.“E-government in China:Deployment and Driving Force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Portals”.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3(3),290-310;Ni Chen.“From Propaganda to Public Relations: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3,13(2):96-121;杜艳明:《基层政府传播体系建设》,载《新闻研究导刊》,2015(18);Brooke Fisher Liu,& J.Suzanne Horsley.“Th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Decision Wheel:Toward a Public Relations Model for the Public Sector”.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2007,19(4):377-393。
第二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第一类研究,即无论中外,政府开展传播活动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既包括中央—地方层级带来的权力影响,也包括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内部负责人和公务人员个体因素影响。相较而言,国外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微观因素的研究更为多见,国内研究者更多从更宏观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舆论引导制度等角度予以论述。
2.政府传播受众研究
与大众传播领域中对受众的研究多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相较,政府传播视角下对受众特点及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采用了政治学“权力”视野。
如在对政府传播的受众分类上,诸多学者认为可根据受众与政府特定施政行为或传播的信息相关程度,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利益群体。早在2004年程曼丽就指出政府传播受众内部可以区分不同利益群体。(12)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刘小燕、崔远航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将受众区分国内、国际两类,并进一步划分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及潜在利益相关者三类,而在政府传播过程中这三类受众并非固定不变,其角色处于动态变化之中。(13)刘小燕、崔远航:《论政府传播的客体——“利益相关者”视角》,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基于对受众(客体)的分类,也有不少学者尝试深入探讨政府传播过程中政府与受众的关系,对公众的主观能动性予以认可,认为公众与政府之间并非简单的被动接受者与主导传播者的权力关系,在不同关系模型下,公众甚至能够掌握挑战政府权威、迫使政府反馈的权力。较之21世纪初期的学者,不少学者更加强调政府传播过程中公众的强主观能动性,认为在新媒体技术的辅助下,公众不仅能够对政府传递的信息进行自主反馈,甚至还能够通过自设议题形成舆论,以促使政府采取特定措施或发布解释性信息。(14)贾哲敏:《公众与政府网络传播—回应的过程、策略与动因》,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汪名鸣:《政府传播与政府形象》,载《求索》,2006(7);沈艳伟:《公共政策传播中政府、媒体与公众互动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如有学者分析了当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五种“传播—回应”模式及其后果,讨论传播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构成(15)刘小燕:《政府传播中的公众意愿回应模式》,载《国际新闻界》,2011(11);刘小燕:《政治传播中的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笔者以中国政治传播经验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政府—公众距离模型。;还有学者分析了“政治阐释”,认为公民对政治信息进行阐释和解读时固然受到意识形态、公共性和语义基础等客观影响,但也有其自身主体性的影响。(16)祖昊、荆学民:《政治传播中“政治阐释”之辩证》,载《青海社会科学》,2018(5)。还有学者在分析政府形象传播时,认为这一完整过程有赖于政府—社会、政府—公众之间的有效双向互动。(17)刘小燕:《中国政府形象传播目标模型》,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4)。
此方向研究已出现众多理论探索,但仍有待更多案例检验。并且,既有研究更多将政府传播客体限定于“公众”,而较少注意对社会组织、其他国家政府等主体的分析。鉴于不同主体的传播“权力”不同,不同政府传播客体的表现方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也不能套用政府—公众的模式与经验。此外,在明晰受众内部差异化的情况下,仍少见传播学视野下对公众的构成特质、心理等分析,而这一视角对于勾勒政府传播中受众特点必不可少。
(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重点:传播渠道与内容
1.政府传播渠道研究
整体而言,在以政府传播渠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中,传播学的视角占据主流,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电子政务上,且基本侧重讨论在当前传播环境下,社交媒体、电子政务等渠道如何辅助政府更好地开展对国内外公众的信息(话语)传播。如斯托伊利科维奇(Stojiljkovic)、塔格力柯兹(Tagliacozzo)、马格尼(Magni)、黄河、王斌、金苗等讨论了救灾重建等不同情境下社交媒体的功能(18)Rita Linjuan Men,Aimei Yang,Baobao Song,& Spiro Kiousis.“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Engagement 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Public Relationship Cultiv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aratgic Communication,2018,12(3):252-268;Ana Stojiljkovic.“Government Communication:Cases and Challenge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7,20(12):1786-1787;SerenaTagliacozzo,& Michele Magni.“Government to Citizens (G2C) Communication and Us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hase”.Environmental Hazards, 2018,17,(1):1-20;黄河主编:《政府新媒体传播》,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王斌:《政府传播2.0:微博的应用历程与发展理念》,载《对外传播》,2011(4);金苗、刘朝阳:《基于善治视角的国外社会化媒体政府传播研究评析》,载《对外传播》,2015(9)。,居恩(Jun)等分析了政府网站等电子政务的推广及功效,认为其能够有力提升政府与公众信息沟通效果,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19)Kyu-Nahm Jun,Feng Wang,&Dapeng Wang.“E-Government Use and Perceive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Service Capacity”.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38(1):125-151;Junhua Zhang.“Good Governance Through E-Governance? Assessing China’s E-Government Strategy”.Journal of E-Government,2006,2(4):39-71.程曼丽、周勇、尤曼斯(Youmans)、仰和、刘小燕、史安斌等关注“党代表通道”、招聘会、新闻发布会、智库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渠道。(20)程曼丽:《十九大“党代表通道”:政府传播的创新形式》,载《现代传播》,2018(1);周勇:《十九大“党代表通道”:政治传播的语态创新》,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William Lafi Youmans.“How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cruited Arab Detroit:Government Communication,Interpellation and Citizenship”.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7,20(1):26-49;仰和:《新闻发布制度与现代政府》,载《国际新闻界》,2004(3);刘小燕:《论政府对外传播中的“智库”与“第二管道”》,载《国际新闻界》,2008(3);史安斌:《微博时代政府新闻发布的理论探索、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载《全球传媒评论》,2013(12)。这些研究更多将政府的对外信息传播活动视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认为与传统媒体渠道相较,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渠道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增进政府与公众沟通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尽管传播学视角占据主流,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毫无政治学视野的体现。如有不少研究探讨基层政府与异见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认为微博等社交媒体在突发性社会事件中对政府合法性有双刃剑效果,社交媒体能够扩大抗议者、反对者的声音,可能挑战基层政府的权威性。在政治学视野下将政府施政行为视为政府传播活动的一部分(21)Jingrong Tong,& Landong Zuo.“Weibo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ment Legitimacy in China:A Computer-assisted Analysis of Weibo Messages on Two ‘Mass Incident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4,17(1):66-85 ;王勇:《论新媒介环境下的政府公共传播》,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也有部分学者,如刘小燕、韩召颖、仇朝兵、钟新等,将军事交流、经济谈判、孔子学院、民间交流等外交(或公共外交)行为,以及微博等新媒体渠道视为政府传播渠道加以研究(22)刘小燕:《政府对外传播载体解析》,载《国际新闻界》,2009(9);韩召颖:《美国公众外交与美国对外政策》,载《太平洋学报》,2001(4);韩召颖:《公众外交: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载《南开学报》,2001(6);仇朝兵:《“9·11”之后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公众外交》,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钟新、陆佳怡:《公共外交2.0: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博客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1(12);黄超:《微博外交理念及实践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钟新:《新公共外交:软实力视野下的全民外交》,载《现代传播》,2011(8)。,并同更多公共外交领域的学者一样,认为此类渠道对一国政府外交目标或国际公信力的增进有重要影响(23)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唐小松、王义桅:《试析美国公共外交及其局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5);齐前进:《公众外交: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载《世界知识》,2003(15);廖宏斌:《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6);郑华:《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4);莫盛凯:《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4);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田立加、高英彤:《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构建研究》,载《理论月刊》,2019(5)。。
无论传播学还是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对党际沟通、政府官方文件、政府机构内部上传下达渠道、政府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如社会动员等)等其他政府施政渠道的研究仍然少见。并且,在传播学视野下开展的研究多借由案例分析、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讨论新媒体如何有力促进了政府传播效果,但对于新媒体渠道如何被采用及其发挥作用的受限因素等讨论较为有限。尤其在当下舆论环境中,多元传播主体共存于同一新媒体平台、网络谣言极易滋生的情况下,仍然有必要讨论在政府实现其传播目标的过程中,新媒体平台所带来的优势大小。
2.政府传播内容研究
传播学视野下多见政府形象(传播)研究,讨论信息(话语)传播的有效策略。近年来此类研究专著、论文颇丰,限于篇幅,本文难以一一论及,整体而言,其大多将之视为政府传播的分支领域,即政府传播中的政府形象传播(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形象传播)或政府对外传播,多以作者各自的理解阐释中国政府(国家)形象传播、政府对外传播的主体、客体、内容、通道、策略等,以及传者与受者的沟通互动模式等;或从主体、渠道、内容等传播要素展开分析,或以具体的政府部门为案例展开研究,从而探讨政府形象如何形成、如何构建,或政府的对外传播活动应如何开展才能更为有效。(24)从“政府形象”角度阐释的,如赵劲夫主编:《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形象》,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徐家良:《政府形象与战略》,杭州,杭州出版社,1996;胡宁生主编:《中国政府形象战略》(上、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龙永枢、杨伟光主编:《领导者媒介形象设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曹随、陆奇主编:《政府机关形象设计与形象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颜如春编:《现代政府形象管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刘小燕:《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彭伟步:《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刘继南、何辉等:《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徐波:《跨文化沟通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中国外文局:《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论丛》,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传播学视域下还有部分学者关注政府政策、法规的传播问题。(25)郎劲松、樊攀:《政府认同差异化:对农政策传播的新困境——基于湖北省S市实地调研的研究》,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曾润喜、刘琼:《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贺霞:《社会认知对“精准扶贫”政策传播的影响》,载《科技传播》,2018(20);刘小燕、李泓江:《建国70年中国生育政策传播模式演变考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其研究重点多呈现为三类:一是基于对具体某类或某一政策传播效果的考察,讨论影响其传播效果的因素,如传播对象的自身特点、媒介的议题建构功能、政府与媒体公众之间的关系等;二是更宏观地描述当前政策法规传播环境、舆情生成特点及面临的挑战,以提供更好实现传播效果的对策建议;三是基于对某一特定政策传播模式变革的考察。相较后二者,前者数量更多,并且多数以问卷、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展开实证研究,注重讨论政策法规这一内容在媒体、公众中的反馈情况。
政治学视野下对政府传播内容的研究数量较为有限,主要体现为公共外交视域下的讨论,探讨一国政府借由公共外交渠道所传播的内容特征以及能够更好实现公共外交目标的内容策略。(26)早期代表性研究如赵启正:《向世界说明中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赵鸿燕:《政府记者招待会——历史、功能与问答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王莉丽:《公共外交:多元理论与舆论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陈先红:《运用公众外交塑造“文化中国”国家形象》,载《国际新闻界》,2008(11);赵鸿燕、侯玉琨:《韩国对华“新公共外交”框架》,载《国际新闻界》,2014(10);赵鸿燕、戴长征:《美国公共外交的传播瓶颈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1);赵鸿燕、何苗:《外国驻华使馆“微博外交”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8),等等。此外,还有一类研究典型表现为对政治话语(如宣传标语等)(27)Falk Hartig.“Political Slogans as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2018,24(1):115-137;李萍:《网络话语体系构建与政府传播实效性研究》,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8);于运全:《中国梦的国际传播》,载《公共外交季刊》,2014(1);于运全:《中国政治传播话语创新的机遇与挑战》,载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第I辑)——基础与拓展》,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还有张志洲、马胜荣、王秋彬、钟新、赵明昊、赵磊、余万里、王文的相关论述。、社会动员(28)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政治理念(29)荆学民、于淑婧:《关于民主传播的理论探索》,载《政治学研究》,2016(3)。的探讨,即政府的施政行为被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恰是在政府形象传播研究这一领域,部分研究者尝试从政治学的视野加以探讨,相对于传播学认为政府形象由政府通过大众传播途径发布的信息及其传播效果构成,政治学视野更倾向于从政府施政行为、政府公共管理实践角度分析政府形象的形成,大众传播渠道发布的信息内容仅是构成政府形象的一部分。(30)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5);袁曙宏:《政府形象论纲》,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3);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的本质内涵》,载《国际新闻界》,2003(6);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载《新闻大学》,2005(1);查春燕、崔松虎:《政府形象塑造中的CIS理论价值分析》,载《南北桥》(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10(2),以及不同作者近年各自推出的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等。这一研究取向再次印证了对于“政府传播”概念的学科“分歧点”,即政府的施政行为是否应被视为政府传播活动予以阐释。
整体来看,在以政府传播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中,传播学占据大半江山,或单纯从公众反馈、媒体报道评估政府形象和政策法规传播效果,或阐述政府执政理念的内涵及传播意义,呈现出对策研究的导向。但此类研究中极少见如系统性分析政府传播内容的生产、传播与反馈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关系及其如何互动,致使所提出对策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作为政策法规制定者的政府往往被视为内部统一的单一行为主体存在,政治学视野下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力差异及其在政策法规施行中获得的不同反馈等问题,则很少被论及。政治学视域下,也仍有待更多研究者具体分析特定政府施政行为的组织、开展与传播效果,能够从各层级政府权力关系与实践角度剖析政府形象塑造问题。(31)此类研究如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但此类角度文献数量有限。
(三)学科视野分歧的延伸:政府传播效果研究
多数研究中,政府传播效果并非是单独的研究对象,往往被嵌入对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受众(政府—公众关系)等传播要素的研究,且在政府传播效果良好与否的问题上往往彼此矛盾,在何种因素影响传播效果这一问题上各执一词。比如从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与提升策略出发予以论述,有学者分析社交媒体和电子政务等渠道带来的正面效果(32)徐虹:《如何在电视政治传播中说服受众》,载《现代传播》,2004(6);刘晓丽:《社会主义主流政治价值网络传播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8。;也有学者从政府—公众关系角度梳理网络时代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传播博弈过程(33)姜飞、侯锷:《政务微博中传播权力和传播信用的博弈》,载《现代传播》,2018(2);李淑芳:《全媒体时代政府传播的新变局》,载《现代传播》,2016(3)。,判定这一博弈引发了政府公信力危机,传播效果(“传播力”(34)吴献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传播力的发展变化及演变逻辑》,载《学术论坛》,2013(5)。)与之前相较大幅缩减;还有学者比较分析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在传播政务信息与施政过程中,对公众的影响力差异。有部分研究者尝试论述政府传播效果评估问题,但此类研究多为宏观演绎性分析,仅有少量尝试结合问卷调查、访谈与舆情分析等方式予以具体评估,并基于此提出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35)刘小燕、李慧娟等:《乡村传播基础结构、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4(7);陈思凯:《融媒体时代政治传播效果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17。
这样结论彼此矛盾的现状再次凸显学科分野在这一领域的投射:一是影响政府传播效果的要素尚无共识。尽管传播效果在多数研究中是普遍存在的议题,但往往各自依附于研究主题(如传播渠道、传播主体、受众等)。由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分野,致使学者未能准确定位影响政府传播效果的要素,更遑论对这些要素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互相作用或者博弈的分析。二是对政府传播效果的评估仍缺乏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估体系。从政治学与传播学视野对“政府传播”概念界定已有明显差异,而在评估政府传播效果时也秉持不同标准、注重不同要素。因此,即使将二者视角融合,尝试从宏观至微观、从中央政府至普通民众、从政府形象到政府执政力等综合考察,也难以厘清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各要素的正负面影响及影响力权重。
三、政府传播研究的未来取向
总之,政府传播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之处的研究领域,当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特定学科视野分析政府传播中的具体面向,从而带来了从概念范畴到研究侧重点的诸多分歧,呈现如下特点:当前国内政府传播研究仍多截面分析、少历时比较;多国内传播研究、少国际范围传播研究;多传播单要素分析、少传播系统性讨论;多话语性信息研究、少施政性信息研究。笔者认为,诸多研究盲点或空白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恰恰由于在当前政府传播研究领域,仍存在明确的政治学、传播学分野,在概念界定上仍将之限定于两大学科交叉重叠之处,即话语信息、在国境范围内传播活动。相应而言,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呈现出明确的学科偏好,其诠释论证也往往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要素或部分。因此,恰是在学科分野之下,存在诸多 “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未能注意”的问题,而其解决之道,需要真正融合两大学科视野,将政府传播视为动态“体系”的过程展开分析。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非传统媒体、非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的研究有待加强。如对海外民间交流、文化出版等政府外部传播渠道、政策制定中的内部组织沟通制度等政府内部传播渠道以及社会动员、城建拆迁的实施等政府具体行政行为,都较少论及。此类研究虽可散见于政府对外传播、政府公共管理研究中,但多被剔除在政府传播范围之外。现有研究难以回答下述问题:除了政府议程、公共政策等能够直接在媒体平台上予以显现的政务信息之外,政府的施政行为(如党际交往、行政立法司法过程)、政府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等同样被民众所认知并能够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认同度等信息如何被传达并发生作用?政府自有媒体、政府发言人以及专家学者对特定政策、特定政府施政行为的诠释解读如何作用于民众、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政府本身的政策与施政?此外,在众多研究分析政府对新媒体的运用如何增强其传播力时,对于政府为何决定采用某种新媒体手段开展传播活动、或采用某种新技术的决策过程等,同样存在研究不足的情况。
第二,传播内容研究欠缺政治学视野。在以政府传播内容为重点展开分析时,欠缺将政府内部层级结构、组织程序等纳入内容生产传播环节,而仅将政府主体视为铁板一块。鉴于政府本身内部存在不同层级和部门,传播内容的出台乃至传播过程既有制度法规与组织程序(如发文的顺序、重大主题宣传方向的要求等)的影响,也有个人化因素的作用(如政策执行者、政府部门新媒体账号运营者等),若将上述因素抛之不顾、仅讨论某一传播内容在媒体和公众中的反馈,那么在分析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时难免有所不足。
第三,缺乏对政府传播过程国内外信息互动情况的研究。当前研究中,政府在国境内传播活动与政府在国境外的传播活动往往被割裂,且后者甚至被排除在“政府传播”研究领域之外。而这样的研究取向忽视了当前传播环境中信息跨国界流动这一基本前提下,政府所传播的施政信息(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作为)与话语信息(如“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同时传播至国内外、且国内外媒体和公众的反馈互相作用乃至再次对政府决策以及政府传播决策产生影响的情况。
第四,缺乏对政府传播受众个体特征和非公民受众的讨论。在对公众个体展开的分析中,虽有问卷调查后的整体特点总结与描述,但对公众的心理动因、文化背景等深层因素讨论甚少。此外,当前多数研究将政府传播客体定位为国内民众个体,仅在政府对外传播研究时会将他国政府、他国公众视为研究对象。但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等非公民的受众研究仍然少见。
第五,缺乏具有规律性或者说普适性的效果评估研究。在论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对政府传播的影响时常见彼此矛盾的结论,在评估时也仅考虑公众和媒体的反馈,却难以将政府内部的决策效率纳入其中;更多是截面性统计与调查,而少见对某类具体政策或具体话语的长期考察。
并且,在学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也相应出现了研究要素彼此独立的情况,而未能将政府传播过程视为“做”“说”合一、“内”“外”统筹、体系化过程。无论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政府传播,还是日常内外形象“自塑”的政府传播,抑或利用电子政务等渠道向公众传达解释政策制度和理念的政府传播,乃至基层政府内部的政策拟定和理论学习等组织性政府传播,都并非相互割裂、独立存在的,尤其在当前信息传播环境中,若单纯以其中一两项为代表观察政府传播难免有管中窥豹之嫌。
我们认为,有必要意识到政府作为社会结构中的特殊行为体,其传播行为并非零散、个体性存在,而多是有组织、有计划甚至有制度规章予以确认的行为;其传播活动(包括对内、对外及政府内部)不可等同于传统的大众传播、普通机构或社会团体的组织传播、政治精英和媒体公众进行的政治传播,亦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图片等音视频等政务信息的传播,还应将其施政行为、执政理念等传播纳入其中;更需将之视为持续、动态、互动性的传播过程,而非短期、固定、单向的传播过程;不仅是政府对其传达信息内容的解释,更是该过程中其他行为主体对这一解释的理解与再生产,以及对政府原初解释的影响;不仅是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主体、渠道等要素,更需关注其制度人事等保障要素。从本质上说,政府传播是政府议程 ( 或公共政策) 、政府施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的扩散、接收、交互、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作过程。
对政府传播的研究有必要从“体系”的角度予以展开。充分融合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角,立体、综合、历时地考察政府传播整体情况,分析其中各个行为主体的角色和彼此关系,传播过程及其效果,将之视为有制度人事保障下的系统性过程;在进行具体个案性分析或对其中某一要素展开讨论时,同样在“体系”框架进行;并且也应考量这一系统的历史变迁,观察其传承与变革,剖析其背后原因,等等。
政府传播研究方兴未艾,诸多议题有待讨论,鉴于当前学科分野之下研究中的诸多分歧、争端与空白,“政府传播体系”视角或许是路径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