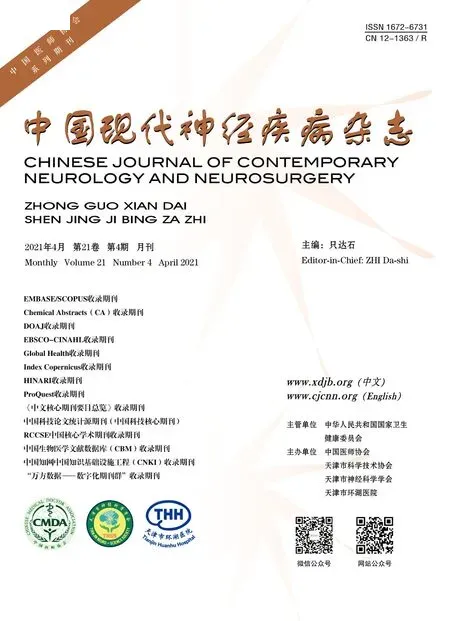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前伦理学问题
2021-01-02王金涛任汝静王刚
王金涛 任汝静 王刚
阿尔茨海默病是神经系统的慢性退行性病变,临床以慢性进行性认知功能下降为特征,病程通常为8~12年,最终进展为植物状态生存直至死亡[1]。1985-2018年,60岁以上老年人群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约3.20%,并预计此后5年可能达到6.17%[2]。2015年,阿尔茨海默病人均医疗费用约19 144.36美元,总计1.6774亿美元,并预计2030年达25.4亿美元[3]。随着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的日益上升,患者认知功能逐步下降导致的行为和社交能力的减退,以及对社会造成的沉重负担,使疾病的治疗和管理成为一个涉及医学、法律、伦理的社会问题;且由于其疾病特点以及广泛的人群涉及,伦理问题日益突显,这些伦理问题涵盖诸多方面,如医疗决定、财产经济决定、管理个人、独立居住、参与法律程序等。本文主要聚焦其中一些伦理细节,包括疾病诊断告知、负面消息告知、预先指示(ADs)、临终关怀(hospice care)和舒缓医疗(palliative care)、驾驶权力,并探讨这些伦理问题给临床医师的启示。
一、疾病诊断的告知
对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导致歧视、排斥和社会孤立的绝症[4],因其不良预后以及担忧被歧视、排斥等诸多社会因素,患者通常不愿接受、害怕接受诊断,家属亦不愿告知、不敢告知病情。但从伦理学角度看,疾病诊断告知体现了医疗人员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尊重。由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保留一定的记忆力和对诊断的自知力,可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故此基础上的治疗与管理可以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更大的获益。目前,大多数临床医师和医疗中心推荐告知疾病的诊断实情,且建议告知疾病的性质、预后以及现有的治疗方法,可减轻患者对自身痴呆症状的焦虑和疑惑;使患者在失去抉择能力前做出关于医疗、财产和生命规划的重要决定;给患者独立做出治疗决定的机会,从而保障其自主权。然而,随着疾病进展,患者认知功能进一步下降,对疾病认知和治疗抉择的能力逐渐丧失,给疾病诊断的告知带来挑战,因此,疾病早期进行诊断告知是较好的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科对175例受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14.2年)进行调查,157例受访者希望自身被告知是否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160例受访者希望疾病诊断告诉其家人;若家庭成员罹患阿尔茨海默病,136例受访者希望将诊断结果告知患者本人[5]。然而临床实践中,疾病诊断的告知可遇到诸多问题。一项来自德国的Meta分析显示,尽管有73%~75%的受访者认为早期疾病诊断告知可对病情预测和晚年规划有益,但同时也带来较大的精神压力(82%)和自我否定感(70%)[6]。因此,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诊断告知,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需要有良好医患沟通能力的临床医师指导。对于自知力较好,能够完全承认和接受自身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推荐告知疾病诊断;对于自知力一般,能够部分承认自身认知功能下降,但却强调家属夸大严重程度并认为仅是衰老表现的患者,可与家属商议后告知疾病诊断;对于自知力较差,完全否认自身认知功能下降,敌视陪诊家属和就诊医师,甚至部分表现为激惹的患者,暂时不告知疾病诊断[7],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类型患者需根据个体情况考虑不同的处理方式,应遵循因人而异的原则。
二、负面消息的告知
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透露负面消息通常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当患者不能理解或接受负面消息时,是否还应该告知?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应该告知患者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善意的谎言保护患者不受负面消息影响的需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接受负面消息后可出现一系列精神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等。业已证实,抑郁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8],可进一步加速疾病进展,不利于治疗与管理,因此,关于阿尔茨海默病负面消息的告知,同样需要临床医师的帮助。告知前,临床医师应提前了解患者的认知水平,对其理解程度以及理解细节能力做出判定,应注意的是,即使是疾病晚期患者认知功能较差的情况下,也不应假定其无情绪反应;关于告知的地点和时间,应保证隐私、保密,且有足够的时间叙述并处理患者反应。告知时可选择家属在场以获得支持并缓解痛苦,若预期可能出现创伤反应,应数小时内请心理科医师会诊并予以进一步的专业心理辅导;应注意的是,告知的内容包含必要细节,但不做不必要的过度详细阐述,同时应做好额外准备以回应患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安抚患者情绪、解答患者疑惑。
三、预先指示
预先指示系指拥有决定能力的患者对自身未来丧失表意能力时接受医疗照料而事先做出的合理、合法的安排和指示。最早称之为“生前预嘱”,由美国Luis K.Due博士于1969年首次提出[9],直至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自然死亡法案》,标志首部承认生前预嘱合法的法律出台[10]。我国尚未对预先指示进行特别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1]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相对保留,有足够能力对自身后期的医疗措施进行抉择,故应该在早期开展预先指示程序。预先指示的内容包括一份代理声明,指定一名代理人为个体在他(她)失去能力时做出决定,配偶和成年子女是最常被指定为代理人的个体,其次是父母、兄弟姊妹及其他亲属;一份生前遗嘱,指定个体在他(她)缺乏精神上的决断能力时做出医疗决定的选择,涉及以下医学问题,如宗教及人生观指导医学决策的意愿;发生心肺骤停时心肺复苏(CPR)和人工呼吸的意愿;个体无法进食和饮水时静脉补液和饲管的意愿;昏迷或持续植物状态时人工生命支持的意愿;参与研究、捐献器官或组织和尸检的意愿[1,12]。作为一种先进的法律思维,预先指示不仅适用于已罹患疾病的患者,所有个体均应考虑在痴呆发病前或最迟痴呆早期,在照料者的帮助下执行以下3种预防性法律程序:(1)预先指示,个体应准备一份生前遗嘱并指定一名长期的法律代理人代理医疗决定和研究参与,他(她)应指示法律代理人遵守生前遗嘱的方针。(2)财产计划,如果个体处于痴呆早期,他(她)应准备一份生前遗嘱并考虑包含一份能力声明(伴随一份录像带)。(3)选择代理人,向家庭成员告知自身意愿和代理人人选[12]。
然而,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患者及其家属缺乏死亡相关知识教育,对预先指示的知晓和接受程度均较低,大多数仍十分忌讳谈论死亡。此外,在传统道德伦理和舆论的影响下,患者仅能依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时家属仍不会选择放弃治疗。2019年关于天津地区社区老年居民对预先指示的调查显示,患者知晓率和接受度分别为6.47%(11/170)和41.18%(70/170),家属为10.56%(19/180)和58.89%(106/180),总体水平较低[13]。多项研究证实,社区老年居民及其家属的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均影响其对预先指示的知晓率和接受度[13-15]。因此,需从法律法规政策、健康宣教、媒体宣传等多方面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氛围,从而提高预先指示的知晓率和接受度,提高疾病的治疗与管理能力以及患者自主权的实现。
四、临终关怀与舒缓医疗
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Mitchell等[16]对一美国护理院323例痴呆患者进行为期18个月的随访发现,54.8%患者死亡。中国一项死亡与危险因素的系统分析指出,阿尔茨海默病的死亡负担已从1990年的第28位上升至2017年的第8位,成为死亡负担的主要因素之一[17]。阿尔茨海默病终末期(end of life)即生命的最后6~12个月,患者丧失交流、行走和吞咽能力,有规律地进入植物生存状态,最终因感染和营养不良导致死亡。随着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各种干预措施可将该终末期延长数月,随之产生的伦理问题逐渐突显,许多人质疑当患者处于认知功能极差状态时,延长临终过程是否有价值、是否增加患者痛苦;也有一些人相信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所有延长生命的措施都应该被采用,且受到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家属通常坚持延续患者生命。临终关怀系指对患病后已进入临终期的患者提供的护理服务。临终关怀是由多名工作人员组建的护理团队(包括医护人员、社工、心理医师、志愿者等)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的关怀服务,目的为达到减轻与缓解患者心理压力、身体痛苦,最终保持长时间平和身心的状态,安宁且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同时也帮助家属对患者的死亡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18]。舒缓医疗系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及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不适,从而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改善患者(成人和儿童)及其家属生活质量的方法[19]。2014年,世界卫生大会(WHA)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各成员国将舒缓医疗融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疾病早期即开始对患者进行舒缓治疗[20]。针对每个阶段的不同疾病特点和护理需求制定相应的治疗和管理策略,从而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活质量。相比临终关怀,舒缓医疗贯穿诊断至最终死亡的整个过程,除控制症状和给予患者关爱照护外,还继续对原发病进行治疗[21]。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舒缓医疗与治疗措施共用,有助于患者积极面对疾病、更好地接受专科治疗,贯穿疾病的全过程;进入终末期后,舒缓医疗的核心目标是减轻痛苦和控制不适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在临床工作中,由于衰老以及疾病所造成的认知功能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通常会遭遇更多的医疗问题,对终末期患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舒缓医疗理念则可更好地指导临床医师为患者提供适宜的治疗,例如,引起轻度不适的小问题如咳嗽、小创伤,可以提供确定性治疗方法;较易处理的较严重急性问题如雾化吸入治疗哮喘发作,需医疗人员积极处理;骨折、恶性肿瘤和心肌梗死等需侵入性治疗或手术的更严重问题时,则需姑息性处理。面对运动障碍时,通常通过一些非药物手段如限制运动、转移注意力、参与患者喜爱事物等进行处理[22]。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常出现因代谢异常、吞咽障碍等原因导致的体重下降以及厌食症、恶液质等,从而诱发慢性炎症反应,导致少肌症、功能下降等不良结局[23],通过人工营养或饲管予以营养是可行的措施,对于许多非终末期患者,管饲可延长生命,甚至在脑卒中或其他无法进食的疾病康复治疗中提供生存所需的营养支持;而对于终末期患者而言,并无相关研究显示进食和人工营养可改善生活质量,经皮内窥镜引导下胃造口管亦无法延长预期寿命、提高功能或生活质量,也无法预防晚期吸入性肺炎[24]。Mitchell等[25]分析2000-2014年共71 251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饮食情况,提出如果临床医师与家庭之间能够更好沟通、更加遵守护理目标,并通过家庭烹饪食物进行妥善喂养,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营养情况。
不复苏(DNR)指令是一种法律文书,患者平时或住院期间预先签署,表明当其面临心跳停止或呼吸停止状况时,不愿意接受心肺复苏或高级心脏救命术(ACLS)以延长生命[26]。患者通常为老年人或长期住院患者,患有预后不良的晚期恶性肿瘤或其他绝症。不复苏不影响除气管插管和心肺复苏外的其他抢救手段,患者仍可接受药物化疗、抗生素、血液透析等治疗方法。心肺复苏对终末期患者无明显作用,且该抢救手段可能造成潜在不良影响,损伤大脑或其他器官,导致患者永久性依赖呼吸机生存,使终末期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因此,部分患者或其家属可能不希望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而更倾向于自然死亡[27]。随着大多数家庭希望在患者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减轻其痛苦并获得最理想安慰,临终关怀和舒缓治疗在终末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驾驶权力
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遭遇机动车车祸的风险是正常对照人群的2~8倍[28]。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9]第十二条规定,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虽有上述规定,但并未规定医疗机构须上报或配合进行痴呆患者机动车驾驶证的审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疾病早期患者认知功能仍较为完善,故不应完全限制其驾驶权力[30]。大多数研究者和相关机构倾向保留轻度阿尔茨海默 病 患 者 执 照 驾 驶 的 资 格[31]。Fuermaier等[32]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主要在驾驶操作、决策和视觉方面与正常人群有明显差距,但由于缺乏对其认知功能的评估,通常无法准确确定终止其驾驶资格的时间,需采取适宜的方法以评估患者能否安全驾驶,临床采用的驾驶能力障碍预测因素主要包括短时记忆力下降和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减少[33]。Piersma等[34-35]通过临床访谈、神经心理学测验和驾驶模拟器骑行等多种方式对阿尔茨海默病进行评估,联合上述3种评估方法可以对患者的驾驶能力做出较好预测,总体准确率为92.7%。因此,应该通过多项认知功能测验的综合评估,对多种认知域进行全面评估,从而获得患者的驾驶表现[36],更科学、合理、人性化地做好保障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基本权利的工作。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患者及其家属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作为医疗人员应充分了解和尊重患者,充分实现患者及其家属的应有权利,与患者及其家属一起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案,共同提高治疗与管理水平;同时也应提高对预先指示、临终关怀等理念的宣教,树立合理健康的治疗与管理观念。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