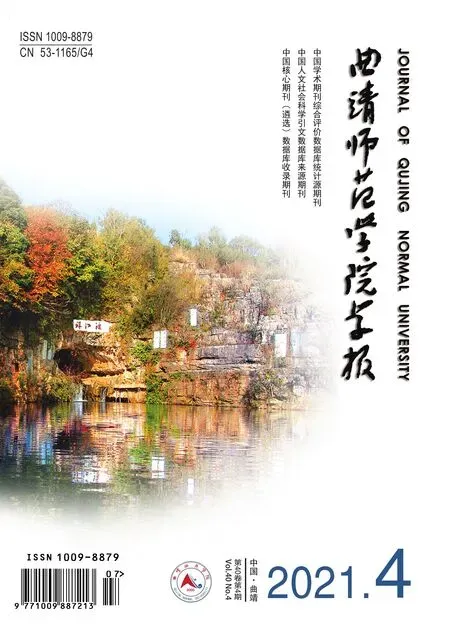“小萝卜头”文学形象的传播与时代价值的弘扬
2021-01-02吕洁宇
吕洁宇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小萝卜头是红色经典《红岩》中的人物之一,《红岩》通过对小萝卜头形象的塑造,揭露了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革命人士残酷迫害的罪恶行径,表现了革命志士与敌人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以及对自由和光明的追求。伴随着《红岩》的传播,“小萝卜头”也成为了经典的儿童形象,在对其人其事的不断挖掘之余,该人物也逐渐从《红岩》的边缘化叙述中独立出来,在红岩精神的不断阐释中,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形象意义。
一
《红岩》的成书经历了多次版本的修订,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根据自己关押在集中营的真实经历,在纪实文学《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的基础上几易其稿、反复加工,先后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并最终形成了长篇小说《红岩》。“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英雄情怀,《红岩》对英雄群像的塑造便是对时代风气的呼应。除此之外,《红岩》的创作也带有较强烈的“为英雄立传”的情感动机,“我们本来不会写小说。可是想起死难烈士的遗言‘只要这里能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座人间地狱的真实情况告诉全国人民!告诉人们,我们是怎样和美蒋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委托。”[2]因而,《红岩》立意深刻、情感浓烈,塑造了江姐、许云峰等一些各有其面、极具代表性的英雄形象。小萝卜头作为白公馆中最年幼的烈士,在书中所涉篇幅不多,且在文中更多的表现出了孩童的可爱、机敏及向往自由的天性,这些朴素而自然的书写溢于英雄叙事之外,却让文本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艺术张力。
作为深陷囹圄的儿童形象,小萝卜头在文中共出场三次,通过对其行为和语言的简单描述,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了这个儿童形象的丰富性。在《红岩》第十九章中,小萝卜头第一次出现是白公馆的“新来者”——刘思扬的视野中,他“又瘦又小”,“身体特别细弱,却长了一个圆圆的头”[3],长时间的监狱生活使其发育不良,呈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身体形态。这个孩子不惧生,对监狱的环境和氛围表现了异常的适应,“这个奇怪的孩子并没有被刘思扬的铁镣惊跑,相反地,孩子靠近一步,抓住门上的铁条,踮起脚尖,把又大又圆的脑袋伸进了风门”[4],大胆的同刘思扬攀谈。长时间监狱生活的经验,使他能通过刘思扬胡子的长度来判断其在渣滓洞关押的时间,在对刘思扬“深深地惊诧了”[5]及“完全被孩子的判断迷惑住了”[6]的描述中,小萝卜头的聪慧跃然纸上。
在《红岩》的第二十章中,作者通过对小萝卜头在狱中具体行为的描绘对该人物形象进行了更深入的刻画。一是通过放飞昆虫的细节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小飞虫的到来让小萝卜头释放了天真和快乐,而被关在火柴盒里的小飞虫又引起了他对于失去自由的生命的怜悯,在获得和放飞的行为中,小萝卜头的天真和善良得到了最大的程度的展现。“虫子终于轻轻扇动翅膀,飞起来,缓缓飞过栏杆,一会儿就不见了。小萝卜头高兴地拍着手叫:‘飞了,飞了,它坐飞机回家去了!’”[7]小萝卜头将他仅有的对外界社会的认知投射至这只飞虫,小萝卜头内心的充盈与现实生活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处便是通过幻想的梦境呈现了小萝卜头的认知世界,在虚与实的交错中暗喻了这个孩子生存的世界的黑暗,带着“山那边是啥地方”的憧憬,小萝卜头跟随着自己仅有的、对磁器口的零星回忆,进入了黄伯伯所提到的很大的“城”里,“那个城真大,墙很高,还有城门:两扇厚实的铁签子门。城墙上面有电网,电网烧得红红的,很是吓人。”[8]这里的街道和白公馆的巷道一样,街上的人穿着囚服,天上飞着活像老鹰的特务……小萝卜头梦里的城是白公馆的另一个影像,也是他所有的人生经验的浓缩。在小萝卜头九岁短暂的生命中充斥着黑暗、冰冷和杀戮,他的善良和纯真是黑暗牢狱里最温暖的色彩,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小萝卜头最后一次出场是伴随着离别的不舍而展开的,小说不局限于对小萝卜头单纯的受害者形象的描述,他在狱中革命前辈的关怀下成长,并将自己的爱和善良给予了更多的人。这个孩子对狱中人的苦难充满着同情,并会用“他自己最简单的纯洁的心灵,准确地辨别着人的种类”[9],用“好人”和“坏人”的简单分类来直接表达他的爱憎。他是狱中的“联络员”,在临行前还因为未能完成任务而深感愧疚。作为狱中最年幼的烈士,《红岩》并未直接描写小萝卜头的牺牲,只借徐鹏飞之口陈明了小萝卜头及家人已经被特务杀害的事实。小说通过小萝卜头的遭遇,表达了暴力对美的摧残,更凸显了黑暗社会所无法阻挡的爱与人性的光辉,“和孩子的交往里,给他带来了无限宝贵的启示:在牢狱里多年的共产党人,是那样顽强地、机警地抚育着这可爱的下一代。那些把自己的希望、理想和心血完全灌注在孩子心灵里的,是些多么可敬的人啊!他们用最大的热情和意志,永远培养着一个人珍贵的灵魂。”[10]在《红岩》中,小萝卜头作为英雄形象的一个侧影,更多的表现了革命党人的朴素情感。因为就《红岩》而言,“那些革命者之间所结成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关系,主要的不是家庭伦理的关系,而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贯注在他们之间的真挚感人的感情是远远超出亲子之爱的阶级的感情。”[11]共产党人高贵的品格和灵魂让这个生活在狱中的孩子依然能源源不断的感受到来自前辈的爱和温暖,而这也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命的不竭动力所在。
在雄浑悲壮的史诗性叙述中,对小萝卜头人物形象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与文本整体风格形成了断裂。艰苦卓绝、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与小萝卜头的人性之美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刚与柔、黑暗与美好的鲜明对比,使得文本呈现出了多层次的艺术效果。
二
在《红岩》文本的传播和“红岩精神”的不断传诵中,小萝卜头这一人物形象也逐渐被大家熟知,有关小萝卜头的儿童传记、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伴随着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复杂演变,对小萝卜头形象的认知、阐释也呈现了相应的变化。
1964年,宋振苏发表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这也是继《红岩》之后最早的有关小萝卜头的文学作品。文章饱含深情的回忆了弟弟跟随父母被捕入狱及小萝卜头在狱中的生活,着重记录了“他在那人间地狱般的牢房里,是怎样向共产党员和革命前辈学习的,是怎样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着的”[12],不同于《红岩》中革命先辈对小萝卜头爱的呵护,小说塑造了一个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不断坚定革命理想的小战士的形象。“他向长辈们学习,也懂得了对敌人要恨,对同志要爱”,[13]她拒绝特务的物质引诱,恨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杀死这批狗特务!”[14]小萝卜头在监狱里传递消息,机警的与特务作斗争,小说对小萝卜头在狱中活动的细节进行了大量补充,借助小萝卜头的形象寄予了作家对反动派的仇恨。因为受时代精神的感召及情感偏向的影响,为了获得更好的政治宣传效果,小说中很多细节被夸大,主旨突出,言辞激切,其主观情绪的充分流露导致了小萝卜头形象的单一和薄弱。
八十年代后,小萝卜头这一人物在文学作品之中多次再现,并逐渐摆脱了“革命者”身份的单一化叙述,而更多的还原了其作为儿童的真实。李林樱的长篇小说《小萝卜头》是一部描写小萝卜头黑暗生活的、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品,“生活在如此残酷、悲惨环境中的‘小萝卜头’的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当属绝无仅有;即便在汗牛充栋的世界儿童文学作品中,这朵‘监狱之花’也算得上一朵真正的奇葩”。[15]这部作品立足于史实,将小萝卜头作为情节发展的中心,以故事的连缀串联起对小萝卜头九年生活遭遇的描述,最重要的是补充了小萝卜头在狱中作为“小战士”的情节,小萝卜头和父母一起参与绝食,勇敢而机敏的去特务办公室拿报纸,传递情报,并慢慢的建立革命的信念:“快点长大吧,长大了我也要革命。我要把这些叔叔阿姨们全从牢房里放出来!”[16]文章并没有将小萝卜头塑造成 “小英雄”“小革命家”的形象,小说感叹“世上没有比这更惨无人道的地方;也没有比在这儿更令人同情的孩子”[17],在还原了他作为一个可怜的、可爱的孩子之余,也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品格的儿童形象。小萝卜头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判断,他在爱的教育下成长,爱憎是非观也在熏陶和感染中逐渐形成,他是一个被影响的、不失独立品格的、非“成人化”的形象。1984年周密创作的电影剧本《小萝卜头幻想诗》则是对小萝卜头美好生命的讴歌,剧本未拘泥于史实而将小萝卜头出生、成长的所有空间都局限于牢狱中。全文打破了沉重的苦难叙事,用诗性的语言将小萝卜头的天真、善良表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剧本细腻的呈现了小萝卜头视角下的自然,雨滴落在水潭里发出的悦耳声音、黄昏时分投在监狱灰黑围墙上的黄橙色的余晖、窗外枝叶摩挲、郁郁葱葱的枫林,所有常见而简单的事物都引起了小萝卜头丰富的想象,它们一方面投射出小萝卜头美好的人性,同时也揭露了美好生命横遭摧残的残酷。
小萝卜头从《红岩》中抽离出来,被作为独立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儿童文学中,源于八十年代儿童文学对既往儿童形象的颠覆,它经历了觉醒和嬗变,并促成了新精神的生成,儿童文学“只能根据生活,塑造出一个个活的艺术形象来,而不能强行使它成为教育工具。”[18]此时期对小萝卜头故事的重新叙述打破了十七年文学意识形态的约束,小萝卜头身上所附着的“革命”属性被削弱,更多地呈现对健全、真实人性的挖掘,而作品在进行真实的抒情之余,也使价值观的输出显现出了过于主观化、情绪化的特点。《小萝卜头》的末尾,小萝卜头惨遭杀害,在幻境中出现了一个美好而光明的新中国。“在红太阳的照射下,小萝卜头背着新书包,走进了学校,他的耳边响起了爸爸的声音:‘好好读书,长大了建设新中国!’”[19]小说发出了对青少年价值观进行培育的呼吁,感情激切直露,从而影响了文本对小萝卜头内心情绪的更深层次的开拓。
二十世纪末,创作者们立足于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渴求通过对革命故事的重述寻找精神价值的回归。此时对小萝卜头故事的讲述采用了更为多样的艺术形式,除文学作品外,在漫画、戏剧等方面都多有体现。通过不断的演绎和呈现,小萝卜头这一人物形象的精神意义也逐渐被凸显。
1996年薛家太创作的《小萝卜头》是一部歌颂“小萝卜头”的儿童传记文学,他立意于做“新时期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部生动教材”。全书对小萝卜头苦难的童年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语言平实,情感真挚,文章情感直露,在小萝卜头被杀害的章节中,作者的悲痛情绪溢于言表:“人们啊!请记着这个日子!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渐渐地,东方发白了。一轮红日从遥远的大海中升起,……这太阳鲜红、晶亮!是革命者和孩子们的鲜血凝聚成的吧?小萝卜头跨上了那颗太阳吗?是他滴的鲜血吧……”[20]作家将小萝卜头的牺牲和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从而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刘庆来的《小萝卜头》则是一部由《红岩魂》展览触动、有感而发的儿童话剧,“人民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愈来愈感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更加呼唤爱国主义、呼唤不为困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人们需要从革命传统教育中重新思考人活着的根本意义是什么?”[21]而“小萝卜头被众多少年儿童、老师、家长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小萝卜头生下来就过着铁窗生活的不幸遭遇和短暂人生足以震撼他们的心灵,还因为人们多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从他们年龄相仿的小萝卜头身上获取巨大的精神力量,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22]该剧有着较为明确的教育意图,以宋振苏《我的弟弟“小萝卜头”》《红岩》中的故事为蓝本,剧情还原了小萝卜头在狱中为韩子栋送衣服、传递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噩梦中的秃鹰等多个场景。戏剧用蒙太奇的手法将少先队员的生活与小萝卜头的生活连接起来,少先队员的朗朗书声与小萝卜头的读书声穿插出现,少先队员欢快的舞蹈与小萝卜头的渴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的歌声中,全剧主题得到了升华。剧作有意通过新旧时代少年的对比,呼唤新时代少年学习和继承小萝卜头坚强、刻苦的精神,以蓬勃之姿拥抱新生活。同时,该剧避免将小萝卜头的形象落入成人化的窠臼,而以捉虫子、吃糖、同李碧涛玩耍等情节还原了小萝卜头孩童形象的真实。
与儿童话剧《小萝卜头》相比,云南艺术学院出品的音乐剧《小萝卜头》则更忠实于历史事实和人物原型,集中展现了小萝卜头的生活环境:“他眼中的世界非常的小,小到只有高墙、电网和黑洞洞的牢房。小蚂蚁是他的伙伴,小蝴蝶是他的向往,孤单单地仰望,头顶小小的天窗,不知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23]剧中小萝卜和蚂蚁的对话、磁器口治病等场景都呈现了小萝卜头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和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音乐剧旨在以小萝卜头为主线,塑造了黄显生、宋绮云、徐林侠等共产党人的英雄群像,难能可贵的是,剧中借用石榴树的意象,穿插大量抒情性的独白和歌咏,对小萝卜头及革命者形象的生动刻画使该剧摆脱了生硬的说教,使育人效果的传达更为自然。
由此可见,小萝卜头形象内涵的变化与时代精神的变迁息息相关。《红岩》在60年代被称为“革命的生活教科书”[24],强调其对民众政治理论的指导性作用,在主流文化媒体的主导下,对《红岩》的宣传偏向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出,因而极大地约束了读者的文学想象,使之陷入了认知固化。随着文学回忆的深入和大量史实的不断挖掘,小萝卜头的“虚构成分经过意识形态化编码方式不断地做着扩大的调整,最终把原型和读者想象出的艺术形象重叠在一起,并让后者成为更深入人心的‘典型’。”[25]
三
经过时间的淘洗,红色经典因其对历史真实的反映和对革命精神的承载而被广泛传诵,成为当代文学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品的红色经典,如何超越历史时空的局限性,正视其文学性的不足,重新挖掘作品的当代价值便显得尤为重要。“评价作品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虽然说法不一,但作品的艺术真实感、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启迪价值应该是公认的尺度”[26],就《红岩》而言,该作品以英雄叙事及悲壮雄浑的美学氛围勾勒出了十七年文学风貌的大致轮廓,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读者从其中获得的思想启迪和精神鼓励。作为《红岩》中的次要人物,小萝卜头被抽离出来并不断地被阐述,其形象最终从文本脱离而被赋予了“教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侵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7]小萝卜头作为经典的儿童形象,其精神的阐释对当代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有着重大意义。在模糊了《红岩》故事中特殊的时代背景之后,小萝卜头人物原型本身所呈现出的勇敢无畏、敢于斗争、刻苦勤奋、理想坚定等精神的价值是极具普适性的,当下对小萝卜头形象的阐释力图在读者和人物之间搭建一道沟通的桥梁,对其价值观的输送是入微且多样化的。
小萝卜头作为教学内容在以往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已有体现,如人教版第五册语文教材收录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冀教版第五册语文教材和鄂教版第七册语文教材都收录了同名篇目《小萝卜头的故事》。前者节选自宋振苏《我的弟弟“小萝卜头”》,讲述了小萝卜头在狱中刻苦学习的故事,末段以“弟弟学习很认真,也很刻苦。他懂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牢牢记住妈妈的话:将来革命胜利了,还要建设新中国”[28]升华主题,以引导当代少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刻苦学习。冀教版篇目摘选了《红岩》片段,通过小萝卜头对小虫子“一捉一放”的情节来感知小萝卜头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鄂教版《小萝卜头的故事》则是作家李晋华根据《红岩》故事进行的改写,文章对小萝卜头在狱中刻苦勤奋的学习态度进行了着重描写,同时通过对小萝卜头学习内容的突出,意在对青少年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教育。文中小萝卜头通过学习建立了对共产党的初步认知,对叶挺《囚歌》的背诵、革命前辈和父母的教导都使小萝卜头坚定了革命信念:“要记住这笔账,把仇恨埋在心里,长大了为他们报仇”。[29]通过对比可知,多版教材对小萝卜头形象的描绘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其指向都在于展现小萝卜头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操及刻苦学习的精神风貌。教材意在通过学生们对小萝卜头故事的直观感受,使其获得对现有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认同,继而发奋学习,并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
除了在中小学语文课堂中开展经典的阅读教学,小萝卜头的事迹也被当作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进入到学生的课外拓展活动中。如重庆市开展了“小萝卜头”进校园活动,学校将重温“小萝卜头”的故事作为开学第一课;江苏省邳州市修建了小萝卜头纪念馆;重庆白公馆、西安莲湖区、贵州息烽、上海虹口等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有小萝卜头的塑像。学生通过聆听、阅读和讲述小萝卜头的故事,更为直观的感受小萝卜头对自由的渴望,理解小萝卜头的生命悲剧,在产生情感共鸣之余,达成陶冶情操,启迪心灵的目的。
由于《红岩》对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调和,后续作品对小萝卜头人物形象的阐释既可以摆脱人物原型的真实性束缚,又不失其作为文学形象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因而,小萝卜头的精神才能随着不同艺术形式的展现而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从这一层面来看,对红色经典中精神的挖掘应该注重多样性和多向度,一方面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红色经典,弘扬革命精神,小萝卜头作为儿童形象在连环画、木偶剧、音乐剧中的呈现即是对读者接受方式多样化的开拓。另外则是注重红色经典中精神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连接,将普适性的价值与当代的精神指向结合在一起,将抽象的精神赋予在真实的形象之上。同小萝卜头相似,《红岩》中的江姐也被不同时代的叙述者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例如张桂梅和江姐的关系勾连便是江姐精神在当代主流话语中的重现。随着小萝卜头和江姐形象不断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演绎,红岩精神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结 语
“小萝卜头”人物形象从“革命者”到“儿童”到“精神载体”的演变,让其所附载的精神价值更为彰显,而这也使《红岩》创作者的初衷得以实现,“为了告慰烈士的英灵,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为了让更多人从哪些为理想信念无惧生死的革命烈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他们义不容辞地拿起了笔,将英烈们用鲜血铸成的红岩精神展现了出来。”[30]小萝卜头故事的再讲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极具代表性,《红岩》具有较强的纪实性特征,使得这些小萝卜头这类艺术人物不仅仅只是虚构的文学创造,还具有原型追溯的深刻性,文本的艺术真实性是同期其他文学作品很难达到的。通过小萝卜头的传播史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十七年革命文学经历了时代巨潮的冲洗后所呈现的独特的、恒久的价值,它能超越当时的政治权利话语,在当代的时代语境下重焕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