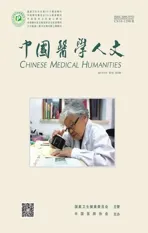医生与诗人日瓦戈的双重身份碰撞
2021-01-02林亭君
文/林亭君
医生与诗人: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治疗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第一部真正的作品”1,日瓦戈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具有多重身份。从宗教角度来看,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从俄国文化角度分析,他是一位俄国圣愚2;但从职业角度来看,他首先是一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即俄罗斯知识分子。
日瓦戈毕业于医学院,一生中三次成为医生,分别在一战中做战地医生、在游击队中当随军医生以及战后在莫斯科医院工作。医生这个职业,总是日瓦戈的选择。当身边其他战地医生不堪战争残酷,选择离开,日瓦戈则一直坚守在医生岗位。战争杀戮使他目睹无数真真切切的血腥事实,使他厌恶暴力,热爱人民,具有使命感;在游击队做俘虏使日瓦戈医生渴望自由,因为三次逃离游击队的尝试都以被捉住而告终,他的医疗助手也有几个是战俘。医生的身份使日瓦戈珍惜每一个生命,甚至是敌军。在红军和白军的战斗中,日瓦戈开枪打伤了一名白卫军,但他内心的念头却是“我为什么要杀死他呢?”3善念促使他救了这名敌人,护理他到完全康复又放他离开。
医者仁心,日瓦戈所具备的品质已经超出了医生的要求,所接受的教育与人生经历使他成为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日瓦戈双重身份的生成机制
生死体验
有学者称《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作品,也有学者称它是一部关于“生”的作品。生与死的主题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成为一组紧密联系的问题。小说以葬礼开始,又以葬礼结束,他的医生职业徘徊于生与死之间,他的一生中也无数次接触到死亡。
在母亲的葬礼上,年仅十岁的日瓦戈第一次对死亡产生体悟:请让妈妈进入天国。随着他的成长,对死亡的理解逐渐深入。在冬妮娅母亲生病时,他已经对于死亡、意识、相信复活产生了成熟的认知:“圣徒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您接受他的论据过于轻易了。死亡之所以不会有,是因为先前的已经过去。几乎可以这么说:死亡是不会有的,因为这已经见到过,已经陈旧了,厌烦了,如今要求的是崭新的,而崭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3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所言:“在自然的人常常视为罪过的那一切事情中,死亡对我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我脱离其结合的人们死亡;对我自己而言,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4
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而作为一名战地医生,日瓦戈的人生中充满了血腥与创伤、死亡与挣扎。虽然他并不畏惧死亡,但战场上的见闻经历依然使他厌恶杀戮与死亡。这违背了医生的天职。
死亡意味着新生。在日瓦戈眼中,冬妮娅在生产过程中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在痛苦中得到了新生。儿子萨申卡也经历了重生,他从无生命状态中来到“生命的大陆”,也是从母亲的“死亡之海”中航行过来的。不仅如此,新生命的诞生本来就是对死亡的胜利,这意味着生命的不断延续,在这种链条中,死亡失去了意义。
日瓦戈作为医生,也为无数病患带来了重生。但复活不仅是肉体的重生,也是人的精神在周围的现实中得到实现。在小说的结尾,日瓦戈死后,似乎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传递给了拉拉,使她领悟了生命,得到精神的安定。杜多罗夫和戈尔东也受到日瓦戈的影响,使其意识得以延续。日瓦戈的思想也通过他的诗歌保留于世,借助艺术的形式永垂不朽,例如《复活节前七日》《婚礼》等诗作就充满了复活精神。而受到舅舅的影响,日瓦戈相信生命重生的进一步意义在于实现永生,永生是人类对死亡的最终胜利。
因此小说从日瓦戈医生的人生经历引入生命与死亡的讨论,始终传递出乐观与坚持的深刻意义。
战争经历
《日瓦戈医生》在战争的背景下,产生了诸多疾病:“在游击队里医生的工作多得不得了。冬天是斑疹伤寒,夏天是痢疾。另外,战斗重新爆发,在这样的日子里伤员不断增加。”3斑疹伤寒和痢疾都是传染病,在条件恶劣的战场上极具威胁性。斑疹伤寒的病死率可达40%-50%。凡是卫生状况恶劣、通风设备闭塞、生活贫穷的人都容易染上此病,因此斑疹伤寒几乎成为战争的附属物。1812年,拿破仑发动侵俄战争,就是由于斑疹伤寒病的暴发,交战双方损失惨重,历史的进程由此改变。
苏珊·桑塔格将疾病看作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5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也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不同的疾病被赋予了不同的隐喻义。作家借助疾病书写,可以达到一定的叙事效果,或是隐喻人物性格与命运,或是制作压抑的社会环境等。
除此,战争创伤也对人的身体与精神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日瓦戈医生》中有关于一战伤员的描写:“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3
帕斯捷尔纳克借助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经历体验控诉战争与暴力,反对其对人体、对社会的伤害。“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3
由此可见,日瓦戈的身上除了医生属性,也闪耀着诗性与人道主义精神。在他反对暴力,厌恶创伤,但每次尽职尽责医治患者,表达出对和平的向往。由于战争因素造成了无数伤残,甚至是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使一位充满仁爱精神的医者深恶痛绝。
为了弥补这种身体创伤,文学与诗性可以给人以心灵慰藉。同样由于在一战中身心都受到残酷打击与创伤,美国作家海明威、派索思、菲茨杰拉德等失去了热情和理想,酗酒赌博度日,被称为“迷惘的一代”。文学创作使他们的内心愤懑得到发泄,借助笔下的人物充分表达自我,实现人生价值。例如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塑造因战争受伤的杰克·巴恩斯,丧失了性能力,被战争阉割。作者借此斥责战争使原本青春热情的年轻人陷入无尽的精神苦闷,这是时代的损失。
宗教影响
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信仰,《圣经》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由此“医生”承担着特殊社会意义和作家审美理想。
基督教在发源之初,是医治人类疾病的宗教6。教士通过治病救人传教布道、吸纳教众,早期的基督教堂通常会收留患者,由神职人员治疗、照顾病患,因此宗教场所成为医院的雏形。《圣经》中包括身体洁净、饮食卫生、健康保健的内容,造物主不仅赐予人生命,同时医治人类的灵魂。上帝本身就是一种医者形象:“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7福音书中则记载了耶稣治病救人的诸多事迹,如治疗麻风病人、瘫痪病人,治好睚鲁女儿和血漏妇女。除此之外,在他奔走传教的过程中,以各种律法、报复、爱仇敌、饶恕等理念唤起人们的明理,拯救人们的灵魂,使其在思想上得到升华。
宗教文化影响着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帕斯捷尔纳克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塑造了诸多仁慈博爱、道德完善、人道主义的人物。宗教的信仰也切实改变了日瓦戈的人生。母亲死后,日瓦戈由舅舅照顾。舅舅是一个还俗的神甫,他的思想与行为都深深影响着日瓦戈。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日瓦戈成长为一个善良博爱的人,心系社会国家。在血腥的战争中,他用医术拯救生命,也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慰藉和思想上的帮助,像耶稣一样带来新生。
文学与医学的交融发展
文学中医生职业隐喻
由于疾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附属品,医生这个职业也在人类诞生之初而产生。随着社会与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与观念不断进步,对疾病和医疗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医生这一身份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在远古社会,疾病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惩罚,而生病是由于人冒犯神灵,病人会因为莫须有的罪恶而遭到憎恶。因此医疗人员通常为牧师、巫士,也包括部落首领、法官、游吟诗人等,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古希腊社会,健康被认为是最高之善,而疾病则是导致人们低劣的万恶之物,人们认为医疗的目标和康复的痊愈永远不可能实现,因此医生是愚蠢的。但公元前430年雅典暴发大瘟疫,人们认识到宗教迷信的真实面目而重视医学,希波克拉底式的医生成为一种手艺人。直到中世纪基督教将治愈和救赎作为教义,病患不再背负罪恶,医生也开始扮演传教士的角色,获得了人们的尊重。16世纪之后,医生主要作为家庭医生从业赚钱,但到了现代社会,经过医疗改革运动,人们认识到医学已经从两个个体的私人关系迅速转变为一种社会体系,医学范围不断扩大,医生成为社会的一员,确保社会关系的协调,医生与教育、法律等相关联。正如医学史家亨利·E·西格里斯所说:“医生是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医生的社会角色就会变成治疗师,并且引导人们向着一种更加健康和更加快乐的生活前行。”8
在文学作品中,医生成为治病救人基础上的精神治疗者,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在《日瓦戈医生》中,作者同时赋予日瓦戈以医生和诗人的身份,不仅意味着在战争中身体疾病与创伤的治疗和康复,更是日瓦戈以个人素养、品格、精神对民族的救赎。因此,医生这种职业及其形象承担着厚重的国家、社会责任,要拯救病弱的家国,医生本人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英雄。日瓦戈医生致力于鼓吹革命,期待民族的新未来,打破了文学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壁垒,具有时代性,折射出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成为俄罗斯民族动荡不安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医生和医学也作为一种承担着社会意义和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性进入文学的视野。在以医生和医院为中心而辐射和建构起来的复杂医学体系中,医生—患者、疾病—治疗、治疗—康复相对应。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救国心切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将国家联想为沉疴缠身的病夫患者,而将救亡救国者比喻为医生,将救国者的行为比喻为医生为病人诊断治病的行为。
日瓦戈的身份行为和意义存在是双重的,表层与现实的内科医生身份和行为里隐含的,是抨击社会旧制度、呼唤新世界的救国者。因此,这样一位主人公形象突破和超越了现实医生身份角色,承担起救国济世和救治社会疾病的“社会医生”与“国家医生”的责任与使命。
医学困境与叙事医学
近代以来医学实现了长足、先进的发展,医学领域日益倚重试验和实验方法。在临床医学和解剖学中,医生成为一名观察者和实验者,观察患者、疾病,寻找治疗方法。这就导致病人被客体化、数据化,直至冷漠化。以疾病为导向的治疗与研究忽略了病患群体的身份、感情甚至是伦理道德,从修复医学所广泛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心脑血管指支架、人工关节、器官移植到基因编辑,甚至遗体或者器官冷冻后等待复生等,人的身体被注入过多“非人的”、可替代的、机械性和操作性的后人类元素。
那么以人性的消亡换取技术的进步是否真的可取?答案毫无疑问。医学的发展不仅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也要以人为本,关注患者。
20世 纪60年 代 至70年代,美国医学院最先将文学纳入医学领域的研究范畴,丽塔·卡伦受到影响,于2001年提出“叙事医学”理论。她主张运用文学分析的叙事技巧来倾听患者的讲述,设身处地地站在患者的角度,展开想象,达到与患者“共情”,并由衷地赞叹患者的勇气,和患者一起寻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的过程和经历9。她的主张,正是要建立医生与患者、治疗与疾病之间的沟通路径,使医患互相信任,在治愈疾病的过程中加以人文关怀。医生可以在文学阅读中寻找病患的影子,以沟通更好的理解病患的生活经历、身体症状、心理感受等,将其作为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特异个体进行治疗。
郭莉萍教授指出,在叙事医学的语境中,临床工作的本质不是医疗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流行为。通过叙事,借助文学技巧与人文关怀实现医学治疗,建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联系,也能够实现文学与医学的融通。
而医生与患者之间应当建立良性、平等的主体关系。如果医生成为患者的主导,移情就会异化为医生规训患者的手段。医生和患者必须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两个主体明确共同的目标、希望和风险,成为命运共同体,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正如《日瓦戈医生》,文学作品可以为医学治疗、医患关系等提供参考,从而帮助医生成为医性与诗性的结合体。除此之外,文学领域增加了对于疾病、医患的关注,以其为表达对象,探讨医患之间的新关系、医生新身份的构建,在疾病叙事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学者戴维·赫尔曼等曾说,“病人通过叙事疗法向医生诉说自己的病痛史,并再次建立起由于疾病干扰的原有身份,即病患叙事;医生通过叙事来反省自己的医疗实践过程,并总结叙事技巧,即医生叙事;在医院使用叙事作为治疗工具,促进医患交流,即治疗叙事。”10
结 语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医学和文学的相互结合和促进发展,学者逐步构建起一种完整的医学与文学交叉联系的理论框架结构。叙事医学理论倡导借助文学技巧倾听患者,提升医疗效果。而文学作品中的医生形象、疾病与治疗等话题也越来越得到学界关注。帕斯捷尔纳克赋予《日瓦戈医生》主人公医生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将其置于战争动荡的大背景下,不仅讲述对战争疾病与创伤的治疗,也突出人物对于民族和社会的救赎意义。日瓦戈所具有的医性,使他在战争与医院中尽责救人;而诗性赋予他更伟大的职责,让其为社会与民族的发展前进奋斗终身。
因此关注小说中的医学要素,从医学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跨学科批评,开拓了对小说研究的阐释空间。事实证明,文学和医学可以互相汲取力量。在现代,医生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在文学中会被赋予救亡救国的责任与使命。而文学也能够使医学注重人文关怀,提升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