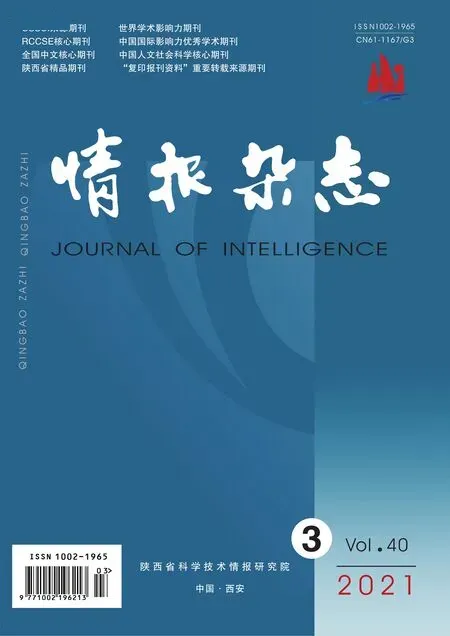亦师亦友情报人
——忆中国情报事业的追梦人包昌火先生
2021-01-02马德辉
马德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北京 100038)
0 引 言
2019年9月4日19时14分和21分,包昌火先生连续给我拨打了两个电话。我问先生:“包老师,您有事吗?”先生回答:“没什么事。”由于快到教师节了,我就顺便问候先生节日快乐。可万万没有想到,21时左右先生因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通话时长38秒和25秒的对话竟然成了我与先生最后的直接交流。后来,由于ICU的探视要求以及新冠疫情等影响,我只能通过相关方式向先生表达问候,遗憾的是,再也没有亲耳听到先生温和的声音,再也无法聆听先生不倦的教诲。经过长达16个月的痛苦和煎熬,2021年1月31日19时40分,我国情报学界的一面旗帜、卓越的情报学家包昌火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6岁。消息传来,我心情悲痛,心碎如麻,先生的音容笑貌许久恍若眼前。因学习情报,我与先生相识。因研究情报,我与先生相知。17年的相识相知使先生和我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情报人。先生是我的贵人,恩同父母,恩重如山。先生不仅支持和引领我的学术发展,在论文写作、前沿讨论、会议发言等诸多方面,指导我,启发我,推介我;而且每次去先生家,先生都非常热情,沏茶,端水果,像家人一样嘘寒问暖,离开时,先生都会送到电梯口,或者站在家门口,目送我走进电梯,有时也会让我带一些干果、羊肉等生活物品回家。2013年春天,先生和我、赵冰峰一起在向日葵花咖啡馆讨论问题时,先生还主动买单付款。2018年10月,李艳师姐和我与包先生同车次去上海参加华山情报论坛,在北京南站先生迫不及待地将装有文章稿费的信封塞给我。这些过往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先生的高尚品格、学术思想、求真精神却永远砥砺我奋进前行,故撰此文以表达对先生的无限怀念之情。
1 相识于静园三院
2004年季春时节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古色古香、庭院幽雅的静园三院,在黄蕾师姐的博士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情报学家包昌火先生。会前,我和几位师兄弟到三院门前迎候开题会专家成员的到来。大概一刻钟的时间,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前,走下一位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中等身材的老先生,他就是包昌火先生。69岁的先生说话慢条斯理,略带浙江家乡口音。1957年7月,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是北大的校友,到北大参加博士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自然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觉。开题会上,包先生对开题报告持肯定态度,修改意见不偏不倚,紧扣问题核心,对开题学生的鼓励和关心更是细致入微。后来,包先生成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开题、预答辩和答辩等环节的主席,我们的接触逐渐增多,日益熟络起来。可以说,先生是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第二指导教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遇到绕不过去的弯,无法自圆其说时,随时电话咨询先生,他都会不厌其烦地答疑释惑。而且对论文的谋篇布局、论据论证、数据处理、文献引用、标点符号等等方面,先生都会提出具体而中肯的修改意见,可谓面面俱到、一丝不苟,足见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2 相知于先生家中
2006年7月,我博士毕业,入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系,从事公安情报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由于在北京工作,常去车道沟10号院北区7号楼包先生家中,我们的联系便愈加密切,进而开始合作研究知识管理相关问题。在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撰写了“知识网络——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的重要平台”“企业知识网络探析”“论企业知识网络能力的培育”“构建企业知识网络的思考”“企业知识网络能力及其模型建构初探”等文章[1-5]。在《情报学进展——2006-2007年度评论》(第七卷)选题专家论证会上,先生大力推荐我撰写的“知识网络的兴起与发展”一文[6]。该文正文3万字左右,172条参考文献,在患有眼疾的情况下,先生仍耐心地审读,细致地修改。通过合作与学习,先生文章的行文方式、语言运用、逻辑关系等技巧也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真可谓受用终生。不仅如此,先生对公安情报学研究也鼎力支持。2012年12月,先生应邀参加我系主办的全国公安情报学研讨会。为了不耽误开幕式的致辞,先生提前一夜住在高级警官培训楼并且不让我照顾与陪伴。后来,我撰写的“‘Intelligence Studies’视域下中国公安情报学若干基本问题研究”“论中国公安情报学学科专业发展及研究框架”“中国公安情报学的兴起和发展”等文章[7-9],也均经先生通篇审读,提出宝贵意见。多年来,包先生和我也不断探讨和思考中国情报学是什么?每次去包先生家中,先生总会反复提及他对情报、情报学的理解和观点。
3 再出发于向日葵花咖啡馆
2013年,78岁高龄的包先生再次挂帅,受聘《情报杂志》编委会主任,继续引领我国情报学界深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3月1日,在海淀区紫竹院69号中国兵器大厦向日葵花咖啡馆,包昌火、陈峰、李艳、马德辉、赵冰峰共同商议《情报杂志》的改革方案,包括编委会成员、版面栏目、研讨会、论坛和培训等调整、改进、创新的具体措施。由赵冰峰负责与《情报杂志》主编张薇联系,征求改革方案(草案)的意见,并请她抽时间到北京进一步商议相关事宜。随后,参与人员又扩展到刘跃进、王延飞等在京老师以及张晓军、高金虎、沈固朝等京外专家。为了快速推进改革,参与商讨的老师都要撰写文章。我与先生合作撰写了“Intelligence视域下的中国情报学研究”“我国国家情报工作的挑战、机遇和应对”等文章[10-11]。每次撰文,先生怕我认不出他的“包氏字体”,都让我带笔记本电脑到他家。先生戴上老花镜,一板一眼地朗读修改意见,我一字一句录入电子文档,认真完善文章。“华山情报论坛”也是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2014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先生亲自参加过第二、三、四、五届,而且承蒙先生厚爱,在2016年论坛上让我代作主旨报告。2018年10月,参加完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论坛后,我和先生说,明年我陪您继续参会,先生则较为坚定地说,身体可能不允许了。当真应验了先生的直觉,先生因病无法参加2019年11月在洛阳举办的第六届华山情报论坛。在论坛结束总结陈词时,张薇主编倡议,所有参会人员共同祝愿广受尊敬和爱戴的包昌火先生早日康复。
4 先生情报思想永生
抚今追昔,听先生教导,和先生讨论,与先生合作,其乐融融,收获满满,可谓神清气爽的精神享受。先生为人谦恭,温文儒雅,很有耐心,很少看到先生发脾气。先生情商很高,无论学术,还是生活,总为他人着想,故志同道合者多且桃李天下。先生学识深广,有系统思维,善于把握问题本质与核心要义。先生思想独特,有战略眼光,敏于抓住学术前沿与研究趋势。先生自称是情报事业的追梦人,一生热爱并执着于国防情报工作实践、竞争情报推广和情报学研究,对情报、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内涵和规律有系统的认知和精准的把握。早在1996年,先生就撰写“Intelligence和我国的情报学研究”一文[12],呼吁我国情报学界应回归Intelligence研究。近年来,多次撰文竭力主张并积极倡导Intelligence Studies才是真正意义的情报学,而非Information Science或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0,13-18]。先生关于情报学的核心思想是:“中国情报学应当建立在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大基石上,并把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即把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非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后者是图书馆学的世袭领地。”[19]无论从事国防情报工作实践,还是推广竞争情报,亦或专注情报学研究,先生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实事求是、戒骄戒躁的学风,都毫不动摇地坚守情报、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根本理念和基本规律。耄耋之年,先生仍思维活跃并身体力行地奋战在情报学研究第一线,为我国情报学界树立了一面永远不会倒下的光辉旗帜。
5 先生千古 一路走好
包昌火先生对我国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情报研究方法论、竞争情报、信息分析、情报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先生的离世是我国情报学界的重大损失。2021年2月4日10时,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竹厅门前的挽联十分醒目。上联是“卅载执笔军工情报谋国防而今学苑失巨擘”,下联为“耄年治学燕大遗风树桃李乃有片言来名士”,横批:“包昌火先生千古”。这幅挽联是对先生一生钟爱情报事业、严谨治学精神、无私培养人才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多年来,先生十分欣赏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主题曲中的一句话:“留住所爱,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20]先生在文章中也曾引用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名句,以表达对情报学回归Intelligence本义的期望和信心。先生以情报为爱,相伴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情报事业践行者、探索者、追梦者。
先生千古,思想永恒!先生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