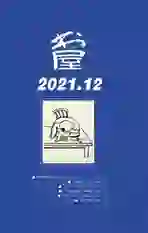深圳的“麦田守望者”
2021-01-01金钦俊
金钦俊
我得坦承,为刘中国君这部厚重的散文随笔、译文集作序并不是件容易事。这难处在于它触及面的阔大:有昔日乡居生活辛酸却又不乏甜柔的深情回忆,有童趣盎然的小儿“起居注”,有深圳特区“鲤鱼跃龙门”的历史观照,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文化名流大营救的记述,有宝安名人轶事详尽、迷人的介绍,有二十世纪上半叶长期在华传教、行医的外国友好人士回忆录与纪实作品的译作,琳琅满目,精彩纷呈,却也让我目迷五色,下笔为难。
难处之二,在于它契入历史本质的深刻程度。它不是史作,但在在都是为我们这东方大国近代到当代大潮激荡、风云变幻的大历史做注解与演绎。在它客观、真实、诚挚的事件叙述中时有精警的论断,用语不多,但却一语中的,令人会心憬悟。我们在感谢灯火为我们照亮的时刻,并不会也没有忘记那执灯的人。只是我有限的理论修养和笔下功夫却令我处于“手无网兜看鱼跃”的尴尬境地,虽爱极银光闪闪、欢蹦乱跳的鱼儿而终于怏怏而归。
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有语:“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读完刘君这部文稿,我既有“会心”,兼又“得趣”。所以,我还得再次坦承,此次阅读是一次美妙的精神漫游,一次舒心的心灵洗濯,使我更深切懂得高贵者何以高贵,英雄性格如何炼成;知道生命有不同的弧线,幸福有不同的香味;更知道许身学术者经历了何等的艰辛,又收获了何等的喜悦以及狂欢。开卷有益,诚不我欺!
揭开本书,一股浓浓的乡情便扑面而来。乡土情深的刘君入梦的常是故乡“大刘楼”“小刘楼”那方山水、亲人、乡邻、麦田和一座座泥坯茅草屋,小河边雀鸟欢唱的樱桃园,井台旁绿油油的白杨树,它们构成立体的永生难忘的田园图。当他人不无得意地诉说自己出身于名门、大都时,他直白“我是个农民的儿子”,那丝傲气令人肃然生敬。乡土是生命之所自来,刘君离乡上大学书包里珍藏的是一小袋“乡井土”,将它撒到他所住之地,希望中州沃土与岭南红土地融为一体,治愈初来者易患的“水土不服症”;大二寒假从老家带来两棵小小的樱桃树苗,悄悄地种在康乐园,以慰乡思。“别后与谁同把酒,客中无日不思家”(苏轼《寄高令》),潇洒、豪爽、豁达的东坡夫子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常人呢!
书名《牧歌》诗意浓浓。“牧歌”一译“田园诗”,起源于古希腊,是表现牧人及乡野生活的抒情短诗,其特点是将乡村生活理想化,讴歌在大自然怀抱中消磨时光的欢乐,具悠远、安逸、恬适情调,后世也用以泛指具相似格调的叙事性作品如小说、记叙性散文等。在过早走出“童年”的咱们中国自古时兴的是“苦难兴邦”,虽也有众多田园诗、山水诗如陶渊明、谢灵运、王维等人的诗作,但总离不开慨叹、沉哀格调。我猜想,刘君为本书取名“牧歌”,可能兼及中西两者情调,有旧日乡野生活贫困中不灭的欢乐天性。
还要特别提起的是书中《托梦的泥娃娃》这组札记文字,质朴、率真,清新如朝露,稚童的举止跳踉憨态可掬,老牛舐犊偏又不忘诙谐挤兑,一家子乐也融融,你系围裙我掌勺,动手烹饪幸福的美味,字里行间充盈着典雅的诗意与情趣,末尾的《天狗要吃月亮啦》更是一出短短的醇美人性的轻喜剧。这也难怪,刘君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是个文艺青年,曾在校园杂志《红豆》以及省内《南方日报》发表过诗文作品呢。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塞林格语)刘君的祖辈耕田种地,交公粮,交桥粮。他本人自述这四十年里自己只是挪了个地方种田种地罢了。那么,这本《牧歌》及以前的作品就是刘君交出的麦豆齐全、颗粒饱满的“公粮”或“桥粮”了。
刘君虽是笔散珠玑的散文高手,但让他声名远播的还因他是一位著作丰盈的文史学者,一位以深、港历史文化的发掘、研究为己任,出版了一系列专著的优秀专家。年前康乐餐厅雅聚,刘君对我说,苏炜君1987年刊发在《读书》上的《有感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一瞥》这篇学术随笔,介绍美国学者如何“用针尖挖井”的方法开展“中国学研究”,予人醍醐灌顶般的感觉。我对此文印象深刻,苏炜君宏论亦颇得我心。其实,刘君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又何尝不是在“用针尖挖井”?他胸怀讨轶搜遗之志,四出广搜志书史籍,每每携大号皮质拉杆箱奔波于广州、上海、北京、武汉、香港、澳门以至美国各地,遍访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书店、旧书摊,“上穷碧落下黄泉”,求索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文史原始资料及相关著作,每遇“奇货”必重金收购,豪奢胜于大富之人。有一次他在广州旧书店觅得宝安文献史料,兴冲冲来到我处报喜。我见那只是一册薄薄的印于民初的册页,置于书架恐也乏人问津,问其价格,居然两千有奇,令我咋舌再三。我想如果不是出于为深、港地区自建一份相对完整的文史方面“城市档案”的“野心”或叫作文化使命感的话,是绝对做不到这点的。送走刘君返深当晚,我梦见有一摞某县的旧县志在半天云里向刘君招手,刘君二话不说搬起家中摘桃果的梯子爬上去,三下两下便将它“摘”了下来。
班杰明·富兰克林说:“勤勉是好运之母,上天把一切事物都赐予勤勉。因此,在懒人酣睡时,你把田耕得深深的,这样你就有玉米可卖和收藏了。”也许是上苍感于刘君采辑的勤勉,他发送神奇的“漂流瓶”渡洋而来,赐予刘君好一批“玉米”——一批险遭时间镰刀割刈而湮没于荒草野径的仁人志士和国际友人的遗著。比如购到民国传奇女性、驻美大使魏道明夫人郑毓秀的一册1943年英文自传《我的革命岁月》(My Revolutionary Years:The Autobiography of Madame Wei Tao-Ming)“签赠本”,以及1926年美国出版的郑毓秀英文自述《来自中国的少女》(A Girl From China),一一迻译出版,郑毓秀的“娘家人”姚任在“光明网”撰文予以推介。此外,他还重金购到郑毓秀1920年出版的法文著作《童年与革命之回忆》(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Révolution)初版本,须知此书当初只印了五十本,而且是带编号的“毛边本”,刘君手头这册编号十七,这真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比如,刘君购到刘铸伯190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点校后编入《刘铸伯文集》,著名文艺评论家和文化学者黄树森先生说:“这是深圳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发现。”大学毕业三十年之际(2013)《容闳传》(与黄晓东合著)问世,地方政府举办首发式与研讨会,反响良好,几年后他重金购置了1909年美国出版的容闳先辈英文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大喜,请师友题笺,任教耶鲁的苏炜写了段题跋:“有幸成为容闳先辈的耶鲁传人,我任教耶鲁迄今已十数载也。‘容闳’的名字是我在课堂上重复频率最高的中文姓名,容闳此书的中译篇名《西学东渐记》,也是我在授课中要求学生记诵的中国现当代史的关键词之一。今天看到这本初版和原版的《西学东渐记》,有一种抚弄故人手泽的温润感和仰止之情。记得我常常在校园内向过往旅人指点介绍哪一栋楼、哪一扇窗曾染上过容闳的灯火,今天这灯火就在手下的这本珍本上持续燃烧,并将燃烧永远。”此外,苏炜还赋诗一首:“掀扉蓦见旧风神,鴂语乡音带土亲。投枕惟追搏海梦,守书犹见照灯痕。巉然湘棘存知己,幸也粤风有继人。愧欠先生三万里,迷津待渡尚初辰!”忻喜之状具见。在这本珍贵图书上题笺的尚有黄天骥、黄树森、易新农、袁伟时、蔡鴻生、陈炜湛、刘斯奋、陈继光、谭步云、陈美华、陈松南等名家,我亦题词:“开启民智之伟大先驱,值得我们后辈永远怀念。”
“漂流瓶”的一再到来,丰富了刘君的藏书,黄树森先生对此曾有精辟评说:“他的每一本藏书中,都潜沉着一个生动曲折的故事,一个时代的印记和密码,一份痴情、浪漫与想象。书籍的收藏是一种灵魂的渴求与满足,书的传递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布施’。”此言深得我心,前人说“千年的纸张会说话”,优秀的书籍虽然无声(当下的有声读本虽有声,但那只是朗读者的而非原作者的声音),但却有一个活跃的灵魂在活动、在倾诉。与书为友,即可夷平时间的悠长与空间的广漠,实现与灵魂的高贵者面对面的“对谈”。我想,久坐书城的刘君肯定是时时得此乐趣而文思振发、佳作续现的。
回看刘君主持编撰的《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民国时期深圳档案文献演绎》《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皇皇十二卷,五百余万言;他与黄树森、于爱成、夏和顺诸君编撰的《深圳九章》出版后,被学界誉为“开放之史记、改革之通鉴”;他与余俊杰编撰出版了《凌道扬文集》《刘铸伯文集》《刘铸伯家族档案》《大营救文献》,并且翻译出版《洪秀全的梦魇与太平天国的起源》《來自中国的少女:郑毓秀自述》《我的革命岁月:郑毓秀自传》《第三只眼睛看信阳》等,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针尖挖井”的“笨功夫”。
成功总会犒赏辛劳。正是由于刘君与协作者对深圳地区文史资料的勠力深挖与热情鼓吹,深圳一扫“文化沙漠”的无知妄说,迎来了文史领域与城市名望的“高光时刻”,一道耀眼的新兴移民城市的人文风景荣耀登场。刘君1997年出版的《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引发各方关注,大鹏所城从此逐渐为普通市民闻知;数年后,这座建于明代的岭南军事要塞更是入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深圳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与同窗好友黄晓东合著的《容闳传》出版后,珠海市把容闳博士当年创建的“甄贤社学”旧址辟为“容闳纪念馆”,并筹建“中国留学生博物馆”;他与余俊杰合著的《刘铸伯传》《凌道扬传》出版后,当地政府创建了“刘铸伯纪念馆”“凌道扬故居展览馆”;他执笔完成的《香港——宝安大营救》出版后,当地政府营建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我们可以想见,作为深圳市宝安区文化顾问,随着他策划编撰的“郑毓秀研究书系”陆续付梓,“郑毓秀纪念馆”也呼之欲出。
刘君不仅对粤港澳大湾区西学东渐史研究颇有发明,西洋文化在其故乡河南信阳的传播也同样纳入他的研究视野。中国近代学人自东徂西、沐浴欧风美雨,接受与传统教育迥异的近代西洋教育,借用容闳老博士的话说,他们负有“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使命,这在深圳学人凌道扬、郑毓秀身上无不皆然——凌道扬1914年学成归国后呼吁“森林救国”,创建林学团体,参与起草制定中国第一部《森林法》;郑毓秀1926年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首位女律师,1928年起参与起草制定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至于近代欧美人士的自西徂东,施医、办学、传教者有之,探险、经商、掠夺者亦有之。施更生医生与雷希圣、李立生、李敦礼等牧师在信阳劳作数十年,创建鸡公山美文学校、信阳义光中学(1900年创校,后易名“信阳市第一高级中学”,刘君是该校毕业生)等新式学校以及豫南大同医院(今信阳市中心医院),亲历过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兵燹、灾荒、瘟疫以及抗战时期信阳的沦陷,把信阳鸡公山当成了自己灵魂的家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施更生之子施钦仁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病理学教授、国际著名麻风病理学家)被聘为中山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其夫人施安丽女士则担任中山医科大学外语中心医学英语教授,双双工作了整整十年,深入常人不敢踏足的麻风村问诊治病,使沉疴多年陷于绝望的病患者转入正常生活,还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实验室,培养了中国首位麻风病理学博士。施更生的长孙女施丽姬(施丽姬教授是美国著名收藏家,曾以有关广东佛山石湾公仔的论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则被聘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教授。1992年9月28日,施钦仁博士荣获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友谊奖章与荣誉证书。1997年在美国逝世。1998年施夫人遵照其遗嘱专程来华,将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入珠江。有感于这位生于信阳、葬于广州的中国“义子”的感人事迹,我在2004年出版的中山大学校史大型纪事诗《山高水长》中为他献上《魂归故土》诗作。施家三代人与中国的血肉关系,一时传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佳话。《牧歌》第五辑收录了刘君与柳江南节译的施更生医生在华回忆录,以及雷希圣的抗战纪实作品《日寇铁蹄下的“新秩序”》译文,可补近代西学东渐史研究尤其是抗战史研究文献之阙。这里面既有刘君寻绎西学东渐历程、褒扬西洋贤达的一番苦心,也寓有一份游子反哺故乡的深情。
综合上述,则这本《牧歌》并非单一的乡风土语,而是农村风尚与城市格调、中土物事与外来仁人事略两个“声部”交织而成的“复调歌曲”,以丰富的谐和音和明丽的节奏群共同表现统一的主题。虽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散文随笔毕竟不同于声乐作品,但此书中那些低抑的生命倾诉,那些高亢的内心呼号,那些激昂的胜利格调,那些柔和的爱抚之声,都在我的阅读过程中不时响起,流风回雪,沁人心脾,慰我长时间阅读的疲劳,更鼓荡起我与书中人物声气相通、心灵共振的波澜。我得说,这是一曲引人入胜的“牧歌”,它为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从封闭贫困的农村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城市文明嬗变的历史进程留下侧面记录,虽格局不大,也是一支沉郁而又高扬、激情而又带理性沉思的时代曲。
(原载《书屋》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