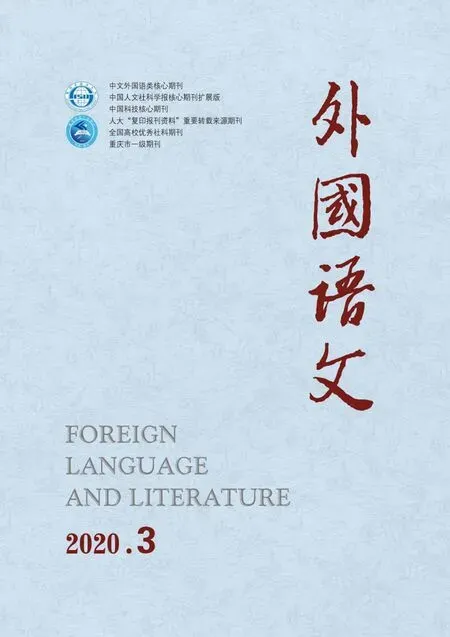演说术与教育
——从西塞罗、昆体良看古罗马教育品质之变
2020-12-31王双洪
王双洪
(北京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101)
0 引言
靠武备攻伐立国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继续以之长治久安。一个共同体的赓续,离不开文教制度对政治共同体精神的传承与形塑。所以,教育对于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以及存亡安危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罗马存在时间不可谓不长,从王政到共和国再到帝国,在西方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这得益于他的征服与扩张,也得益于面对异质精神品质时的不断调试。古罗马的智识阶层在处于文化强势的希腊文明面前,一直努力让希腊哲学为罗马接受,并且与古罗马固有精神品质形成合力,教育罗马新的一代。在这些努力当中,共和晚期的西塞罗功不可没。施特劳斯给了西塞罗很高的评价,称西塞罗在古罗马发挥的作用与柏拉图在古希腊发挥的作用相同(尼科尔斯,2018:37)。帝国早期的昆体良,对他的前辈西塞罗盛赞有加,试图承袭前辈的传统,但随着鼎盛的罗马共和国变为帝国,继而帝国衰落,智识阶层虽尽力匡救时弊,但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症候也或多或少对智识阶层产生了影响。
昆体良与西塞罗的文教理念有所不同(1)本文西塞罗《论演说家》的引文参照王焕生先生的译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演说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昆体良《演说家的教育》引文参照洛布本(Quintilian, The Orator's Educa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onald A. Russ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翻译,部分引自任钟印选译本(昆体良著,任钟印选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略有调整。出自这两部著作的译文,笔者只随文给出标准行段码。。从古罗马的共和时期开始,法庭辩论、元老院议事,共同体的内乱及冲突,演说在其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要踏入政坛、谋求职位,也不得不经过演说术的训练,演说术几乎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阐述关于演说家的培养,就是在探讨公民的教育问题,演说术原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包含了教育的原理。关于培养演说家,关于演说术,共和晚期的西塞罗和帝国早期的昆体良都著书立说,加以探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阐述了演说家的教育与养成,探讨了关于哲学、历史、法律、文法、数学、音乐、修辞、几何、天象学等的学习,即古罗马人所说的自由诸艺(artes liberales)。书中虽然也涉及演说术训练诸如声音、论题等等技术性问题的学习,但所占篇幅极少,西塞罗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理想的演说家,集哲人、政治家和演说家于一体的人。与西塞罗相比,昆体良《论演说家的教育》更倾向于一种普及的分段分层的教育。他探讨了从孩提阶段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应该教授什么内容以及怎样教授。昆体良给出了详细的教育方案。他把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初级教育教授识读、中等教育教授文法以及关于演说术的教育。昆体良用极大的篇幅讲述教学方法以及演说的技术性话题。他认为的理想演说家应是一个善于演说的好人。昆体良的教育理论对后来的西方教育影响深远。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作家、中世纪修辞学家和文法家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者都推崇昆体良的教育理论。西塞罗和昆体良同样著有关于演说家、演说术的著作,同样对西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西塞罗首先被誉为政治家、演说家,而昆体良却首先是后世人眼中的古典教育理论家。这种评价恰恰说明了二者思想侧重之不同,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传达出西塞罗和昆体良所处的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教育品质的差异。
1 西塞罗的《论演说家》
西塞罗的教育理想集中体现在对话体著作《论演说家》中。之所以选择对话体,他在另一部著作《论法律》中做出过解释——谈话可以寻求到最可能的答案。参加对话的人有当时的政治精英,其中主要参与者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并且都担任过执政官和监察官,也有未来的精英——杰出的年轻人。对话过程中,年届七旬的占卜官斯凯沃拉,由于年龄和体力,中途退出了谈话。这样的人物设置,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同样是年长者与优秀青年之间的交谈,同样是老年人中途退场。如果把这场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视为一场教育的话,那么,在《理想国》中,教育年轻人的是哲人苏格拉底,而在西塞罗这里,教育年轻人的是演说家兼政治家一身的长者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
虽然《论演说家》人物设置上与《理想国》相似,但是,西塞罗明确表示,这篇对话模仿的是柏拉图的《斐德若》(《论演说家》卷I.28)。为什么是《斐德若》而不是其他?柏拉图的对话《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斐德若》都讨论了修辞术,《论演说家》中主要对话人物克拉苏斯认为《高尔吉亚》在嘲笑演说家,希腊的修辞学家热衷的是辩论本身,而不是事实。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是以利益和说服为目的的,和知识与智慧无关。《普罗塔戈拉》也认同智术师教授的修辞术观点,认为旨在求胜逐利的修辞术与哲学的求真互相冲突。只有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对修辞术持“辩证”的看法,既有对政治修辞术的釜底抽薪式批判,也有苏格拉底用哲学的修辞术教育年轻人、引导年轻人的“爱欲”转向(刘小枫,2015:20-25)。哲学和演说术结合来教育年轻人,也许正是西塞罗模仿《斐德若》的原因。
《论演说家》两个主要对话人物的设置,体现了西塞罗如何处理演说家教育中的哲学与演说术之间的关系。克拉苏斯与安托尼乌斯最初对待哲学与演说术的观点并不相同。克拉苏斯并不同意柏拉图对演说家(修辞学家)的取笑,他说:
即使有人把演说家界定为这样的人,即认为演说家仅是能够在法庭上,在人民面前,或者在元老院里雄辩地说话的人,那他也仍然必须认为,此人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须知,一个人若无对各种公共事务的广博知识,若无对法律、风俗和权利的深刻理解,若无对人的禀赋和性格的全面认识,他便不可能足够敏锐而练达地从事这种活动。(卷I.48)
对各种事务都有智慧,对人性有深刻洞察了解的,无疑是哲人。开篇的地方,克拉苏斯曾表示,“真正的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仅能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卷I.34),这里表达的是政治家对于公民和国家的职责。随后克拉斯补充道,演说家是可以就任何需要语言说明的问题讲演的人。克拉苏斯将哲学分为三个部分,关于自然之奥秘、关于论辩术之精微、关于人生和风习,他强调,演说家最应该掌握的是第三部分,如果不理解人生和风习,“演说家便无从表现自己的伟大”。当有人指出克拉苏斯对演说家的界定超出实际演说家所能达到的限度,演说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技能、知识和智慧时,克拉苏斯表示,他描述的是理想的演说家。也就是说,在克拉苏斯那里,理想的演说家是集政治家、哲人与演说家于一体的人。
另一位对话的主要人物安托尼乌斯最初反对克拉苏斯的观点,在第一天的对话中,他提出,演说家并不需要掌握所有的知识,演说家和政治家、哲人并不相同。他强调演说家的实践。安托尼乌斯指出,如果哲人就是探索一切神界和人间事物的实质、本性和原因并努力理解和追求一切高尚的生活方式的人,演说家则是“在诉讼的和社会的事务中善于使用能令听觉愉快的语言,善于发表能使心智赞赏的看法的人”。那么,演说家凭丰富的经验,能够观察出自己的国民和那些需要他说服的人在“思考什么,体会什么,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期待”。在克拉苏斯那里通过修习哲学才能拥有的能力,在安托尼乌斯这里只要在实践中观察就够了(卷I.220-223)。但是,接下来第二天的谈话中,安托尼乌斯围绕演说家的任务和能力,演说术的任务和界限,演说的类型、历史、法律及哲学学习之于演说家的作用等等方面,表达了和克拉苏斯几乎相同的观点——演说家维护真实而不是模仿真实,能够鼓舞或者抑制民众的激情,可以培养美德避免过失,揭露和制服欲望。他开始称许克拉苏斯的理想演说家,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完美的演说家更美好(卷II.33-36)。安托尼乌斯之所以提出第一天所持的观点,是想驳倒克拉苏斯,展示演说术的力量,吸引年轻人。而接下来他用前后不一的两种观点表明,演说可以为求胜也可以为求真而讲。安托尼乌斯最终的观点与克拉苏斯走向和解与统一,也指向了哲学与演说术的统一。不同的是,克拉苏斯侧重理论的表述,而安托尼乌斯侧重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们二人殊途同归,也正是行动与言辞、修辞与哲学相结合的典范。
2 昆体良的《演说家的教育》
西塞罗的《论演说家》是对话体,主要内容是罗马的智识阶层之间的对话,是对年轻人的教育,是两种不同观念、行动和言辞、修辞与哲学的最终结合。昆体良的《演说家的教育》是论著,昆体良在著作的开头将自己的教育目标以及整本书的结构、所要处理的问题提纲挈领表达出来。这部著作共12卷,卷1论述演说家孩童时的基础教育,比如孩子应该由保姆还是父母来教,什么年龄学习什么内容等等。卷2论及演说术学校及有关演说术性质、教育目的等问题。接下来3—11卷是《演说家的教育》的主体,卷3—7讨论演说词创作,如构思和谋篇,8—11卷论及演说能力及技巧,比如朗读、背诵、宣讲等等。最后卷12描述理想演说家(Quintilian,2001::63)。从昆体良本人对《论演说家的教育》一书章节的划分及概括来看,这部书除了头尾部分表达昆体良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外,主体部分几乎都在处理教授演说术的细节问题。
关于理想演说家的论述,在昆体良《论演说家的教育》中所占篇幅不重,甚至可以说篇幅很短。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而忽视它。可能恰恰是关于理想演说家的观念决定了昆体良写作的篇章安排。关于演说家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理想演说家的问题,昆体良和西塞罗的写作有交集,但他们给出答案却存在差异。
昆体良几乎是在著作最开始的地方就强调他的教育目的。第一卷的前言中,昆体良提出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完美的演说家。而完美演说家的首要条件是善良,要是一位好人。
我要求他不仅有非凡的演说天才,而且同时要具有一切优良的品格。我并不承认有些人的主张,他们把正直的原则和高尚的行为看作只是与哲学家有关的事。一个管理公共及私人事务、能履行其公民职责的人,一个能够用自己的意见指导国家、用他的立法给国家奠定稳固基础、用他的判决消除邪恶的人,无疑地只能是我们所要求的那种演说家。(卷I.9-12)
昆体良在最后一卷开始的地方,用加图(Marcus Cato)的话重申自己的观点,他要培养的是加图所说的“善良的,精于演说的人”。如果有演说才能的人行恶,教授演说术就是给强盗而不是给战士提供武器。理想的演说家必须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善良的人,就绝不能成为演说家(卷XII. 1. 1-3)。
昆体良在《论演说家的教育》中强调德性。至于如何让他所说的理想的演说家拥有美德,在书中语焉不详,更没有像教授演说术那样有一个完整、详尽的方案。昆体良提到了通识教育,认为理想的演说家的教育要诉诸丰富的学习内容,这和西塞罗提到的自由诸艺看上去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却凸显了二人的差异。葛怀恩在他论述古罗马教育的著作中,比较了西塞罗和昆体良惊人巧合的一段话。昆体良在完成对演说家的语法和修辞教育之后,向更高的博雅人文教育过渡的时候,指出演说家需要有丰富的内容和词汇,这只能通过广泛阅读希腊和拉丁文学来获得。西塞罗的观点是,一位演说家要有丰富的内容和语汇,只能基于演说家对一般原则的高等研究之上——这里的“一般原则的高等研究”就是前述的哲学、历史、法学等等自由诸艺,而昆体良的更高的研究计划是“接续文化教师和修辞术教师已经给出的文学课程”。葛怀恩说“这位伟大的学校教师(昆体良)的文学建议显然让人想回到课堂”(葛怀恩,2015:181)。即便是昆体良在第12卷插入了三章关于哲学、法学、历史学习的内容,但他的最终目的依然是这些内容将“成为演说家的工具和武器”。“对于这些插入的章节,没有读者会注意不到这两者——西塞罗对这三门最喜欢的研究的热情辩护与昆体良对其价值的简要讨论——之间的差异”,昆体良偏离了西塞罗式人文的真正精神(葛怀恩,2015:179-184)。
从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著作内容来看,两个人谈论演说家教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西塞罗虽然也论及有关演说术的技术性细节,但是他的重点在于理想演说家的教育——即一位合演说家、哲人、政治家为一体的人,他整部书的结构框架就是建立在这一主题之上,在谈话过程中话题不断回到理想的演说家。昆体良的著作则是一部具体、细致的方法指导,内容从童蒙教育到学校教育,从最初的识读教育到最后如何写作、修改、发表演说词的高等教育,从论题的选择、声音、节奏的训练,几乎涵盖了培养演说家方方面面的内容。关于昆体良与前人的差异,昆体良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他在第一卷的前言中表示,之前有大量关于演说术的著作,而他本人的写作要另辟蹊径,避免落前人窠臼。之前论述演说术的人都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假定他们的读者已经在各方面受过完备的教育,他们的任务仅仅在于在演说术训练方面的最后点睛”(昆体良,2006:4)。他指责那些人轻视初级阶段的教育,或者不把初级教育当作自己分内之事。这种指责,同样适用于西塞罗,并且昆体良整本书里充满着对西塞罗的引用、回应,偶尔也有流露出的异议。昆体良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假定演说家的全部教育都由他负责,主张从婴儿时期开始设计培养演说家的教学(昆体良,2006,5)。
昆体良看似也论及哲学,也在谈论西塞罗所说的自由诸艺,但是他对哲学有微词,他不止一次要撇清演说术与哲学的关系。昆体良承认自己在著作中要处理哲学奠定的某些原则,但他不无矛盾地指出,这些原则之所以进入本书,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属于演说术。诸如勇敢、正义、节制等等德性会出现在讼案当中,说明它们需要的是演说家的例证、想象力和演说才能(昆体良,2006:6)。更有甚者,昆体良指出,谈论善良、有用和公正,是演说家独有的财富,演说家放弃了这部分,才有了哲学家的越俎代庖(昆体良,2006:133)。在卷10中,昆体良曾经把哲人著作列入青年的阅读书目中,但转而说其实他们本来不必阅读,只不过是演说家把自己工作中最好的部分交给了哲人(卷X.1.35)。昆体良排斥哲学,部分原因是帝国晚期哲学德性的败坏。修习哲学的人伪装严肃、特立独行,事实上却不谙世事,矫揉造作,远离公共事务。“没有别的行当要比哲学更显得疏于承担公民的义务和演说家的一切任务。”(XII.2.6-8)哲学的这种风尚导致了罗马上流社会青年的娇弱放荡之风,完全背离了简朴、务实、勇武的遗风。
3 演说术与古罗马教育品质之变
昆体良并没有像西塞罗那样赋予哲学那么高的位置,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是不同的知识人对于罗马面临挑战的不同认识。对于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罗马人的态度一向复杂而多变化。罗马人的精神传统里不存在哲学,“所谓‘罗马的’道德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为共和国时期那些强壮、固执、总是野性未驯的罗马人所信奉不渝的旧邦古训;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希腊人是那样文质彬彬”(马鲁,2017:4)。在没有接受希腊影响之前,罗马社会的风习不是来自公共教育,而是家庭的潜移默化,来自传统、榜样的力量。罗马人从小教育孩子要尊敬古代礼俗,尊敬父亲乃至先祖的权威。当希腊文化进入罗马人的视野之后,两种文化的冲突便一直存在,如何在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保存并延续自己的传统,是古罗马几代知识人面临的挑战。公元前2世纪,罗马文化阶层越来越为希腊文化所吸引,而此时罗马历史上发生了不止一次驱逐希腊哲人的事件。理由不外乎这些哲人能轻而易举地让人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事情,这无疑是对信奉祖制、古训的罗马教育的冲击。但与这种拒斥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一种努力,那就是要在文化的碰撞中形塑并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曾经下令驱逐希腊哲人的老加图,在晚年时也开始研究希腊的语文,他意识到,摆脱希腊影响的方法就是学习希腊(普鲁塔克,2009:619)。可见,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的政治人、知识人已经开始了形塑传统的努力。这种努力当中,最见成效的当属西塞罗。他的《论共和国》《论法律》都是在希腊哲人的基础上改写罗马的神话,建构罗马自己的政治及哲学传统。沃格林在政治思想史中也指出,西塞罗“在保存罗马的观念,并为有关政法和法律的神话奠定基础”(沃格林,2007:174)。法国古典教育史家马鲁同样认为,西塞罗的哲学作品“都与他的演说术著作具有对称的历史意义,即在拉丁语内部创造一种可以支撑、普及希腊思想学术的语言,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建立属于罗马自己的哲学教学传统也就有了可能”(马鲁,2017:47)。Humanitas一词很好地体现了西塞罗的这种教育理想,表示一个人兼有德性和智性上的优越。这样的教育既包含罗马也包含希腊的要素,就像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表述的,“我们从罗马寻找德性的范例,从希腊找来我们的文化范例”(卷III,137)。有古典学者做过统计,humanitas及其形容词形式,几乎出现在《论演说家》每一页(葛怀恩,2015:94)。西塞罗在另一个地方很好地回应了这种教诲,“我们都称为人,但我们当中只有那些经过严格研究人文之艺而得到文明教养的人才算作人”(《论演说家》卷I,28)。自由诸艺是培养理想演说家的基础,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多次提到,而排在诸艺之首的便是哲学,西塞罗将之作为道德和思想的指导。
西塞罗的教育理想是培养集演说家、政治家和哲人于一体的完美的演说家,这样的演说家也是罗马理想的统治者,他具有关于一切德性的知识,是国务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能在元老院和民众的演说中引导罗马人民。西塞罗时期的罗马虽然局势动荡,但古风犹存,西塞罗努力在罗马传统和希腊文化之间形塑新希腊-罗马文明。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足够成功。共和制走向没落,随之衰落的是公共生活的活力以及罗马公民传统,同时也伴随着演说术日渐衰落。公共演说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越来越微不足道,帝国时代,靠战争掠夺来的财富和奴隶使得罗马一派表象上繁荣,社会风气却不断败坏,政治演说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演说术沦为法庭辩论的技艺,或者成为取悦听众的娱乐,甚至成为以律师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一种职业训练。老塞涅卡在《辩驳集》中描述过奥古斯都时代末期的世风。
(年轻人)的天赋被挥霍,没有一个尊贵的职业使他们乐意夜以继日地辛勤努力。昏睡不已,无精打采,比这更糟糕的是对邪恶的兴趣,这些都已经进入人们的心中。他们唱唱跳跳,长得娘娘腔,卷着头发,说话女里女气的;他们懒如女人,用失礼的事物盛装打扮自己。你们的同代人(对他的三个儿子说话)当中哪个有丁点资质和勤勉?哪个在哪方面像个男人?毫无力量,毫无精神,他们活着没有给他们生而有之的天赋增加任何东西,然后抱怨他们的命运。但愿神禁止将雄辩的天赋赐予这类人!(葛怀恩,2015:103)
在这种环境中,作为智识阶层,昆体良接续与形塑罗马传统的需求与西塞罗应该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他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希腊文明和罗马传统之间的张力,而是如何重振罗马的古风。昆体良为他的学生写作,而西塞罗为同他一样的人(政治家、哲人、演说家)写作。昆体良的教育目的是一位好人演说家,西塞罗的理想演说家是培养集演说家、哲人、政治家于一体的人。西塞罗努力在希腊文化与罗马德性之间形塑罗马人自己的思想传统,昆体良虽然并未放弃这种努力,但他的努力也仅仅是退而求其次,罗马继承的文明随着时间而消磨稀释,西塞罗、塞涅卡、昆体良这些名字,表明了一个渐次下降的顺序(葛怀恩,2015:206)。
演说术在昆体良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实用、功利的技艺,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省青年到罗马谋求职位,学习演说术,成为律师。昆体良自己也说过,没有什么比律师更理想的职业了。塔西佗在《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中表示,西塞罗意义上的演说术已经不复存在,家庭教育和罗马传统影响式微,一切优秀的罗马品格也逐渐远离帝国下的罗马,西塞罗的时代,人们学习哲学、历史、法律等等自由诸艺,而帝国下的修辞术就是修辞术(曾维术,2010:80-81)。昆体良在帝国早期的语境下写下《演说家的教育》,讨论演说术各个层面的技术问题似在情理之中。他的著作在国内没有完整的中译,涉及这本书的译名,有的翻译为《论演说家的教育》,有的翻译为《演说术原理》,后者大概就是基于对昆体良著作内容的教育理论、演说术理论技术层面的理解。
4 结语
从共和早期到帝国早期教育品质的变化,让我们联想到百年来中国的文教状况或许并不牵强。西方的文化之于中国的传统,虽然远不能视为古希腊之于古罗马的文化强势,但是,经济、政治上的积贫积弱,导致了国族文明、文化上受到冲击却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在异质文化的影响下,如何保持或者说形塑我们自己的精神传统,或者,毋宁说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政治共同体如何保持自己的传统?显然,仅仅靠掌握各门专业技艺的人是不行的,帝国后期昆体良所说的拥有技艺的好人也同样有所欠缺,或许,西塞罗描述的兼有德性与智性卓越的精神精英能提供一些启发,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必然是朝向博雅人文的整体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