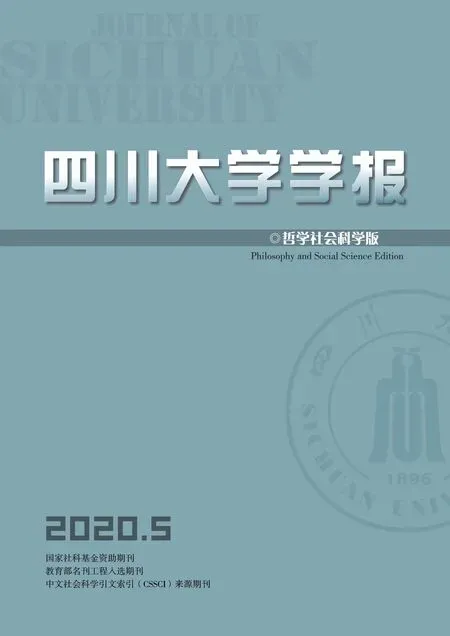双重反叛的新先锋理念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小说”再审视
2020-12-31张和龙
张和龙
《法国中尉的女人》(TheFrenchLieutenant'sWoman, 1969)是一部重要的后现代元小说。早期批评界对这部作品的“元小说”实验技巧褒贬不一,有人将其视作“岔离主线的无趣之物”,(1)Walter Allen, “The Achievement of John Fowles,” Encounter, No.35,1970, pp.64-67.有人斥之为“怪异”(eccentric),(2)Prescott Evarts, Jr.,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as Tragedy,” Critique, Vol.13, No.3,1972, pp.57-69.或觉得它“有趣,但不像是小说”,(3)Mary Conroy, “A Novelist on the Knowledge,” Times, 14 June 1969, p.22. Qtd in William Stephenson, Fowles'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London: Continuum, 2007, p.78.也有人认为“元小说”技巧是约翰·福尔斯为了让“传统故事”能够被读者接受而披上的一层“隐匿色”(cryptic colouration),是福尔斯施放的一道“烟幕”(smokescreen),以此做掩护来“延续传统叙事”。(4)Elizabeth D. Rankin, “Cryptic Coloration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Vol.3, September 1973, p.196.20世纪80年代,批评界开始将“元小说”视作后现代小说的重要创作特征,并用来重新评定《法国中尉的女人》,认为它是“典范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5)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New York & London: Methuen, 2002, pp.1-19.是“编史性元小说”,(6)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5.是“对维多利亚传统的后现代元小说式的戏仿”。(7)Susana Onega,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Novels of John Fowles, Ann Arbor and London: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p.91.这一“后现代”的批评视角一直延续至今,并对我国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国内早期曾对“元小说”的认识存在短暂的误区,如1985年《法国中尉的女人》首个中译本将很多元小说元素删除,尤其是第13章被删去了三分之二,1986年第二个中译本也对第35章中的元小说评论作了大量删节。此后,随着后现代研究的兴起,国内批评界普遍将《法国中尉的女人》认定为重要的后现代元小说。然而,在“元小说”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甚至从一个曾经代表前沿的术语变成一个被不加反思地使用的概念的当下,这部作品的反叛内涵,即其作为典范“后现代元小说”的先锋性和重要作用并未被完全发掘。
《法国中尉的女人》写于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之际,讲述的是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福尔斯一方面惟妙惟肖地模仿了维多利亚小说的叙述手法,另一方面又经常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让叙述者“我”介入叙事过程,对小说内容以及小说创作进行评论,甚至还让留着法式大胡子的叙述者“我”成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由此,整部作品在叙述结构上分为两层:一是“传统”故事层,一是元小说评论层。一直以来,元小说评论层都是批评界关注的重点,其原因正在于“元小说”是统摄全书主旨的结构性元素,相当于雅各布森所说的“主导元素”(the dominant),即“一件艺术品的核心元素,它统摄、决定和影响着其他元素”。(8)Roman Jakobson, “The Dominant,” Selected Writings Ⅲ: 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 Hague: Mouton, 1981, p.751.元小说评论层的存在,改变了“传统”故事层的性质和特征,保证了叙事结构的层次性与完整性,也决定了整部作品的先锋艺术特质,使它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也不同于此后兴起的“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Fiction)。同时,对传统叙事的戏仿性“回归”,又使它有别于现代主义或“历史先锋派”小说,以及二战后新兴的法国“新小说”或其他后现代小说。因此,《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采用“元小说”技巧的后现代实验小说,更是一部以“元小说”作为主导元素的“先锋理念小说”(the novel of avant-garde ideas)。“元小说”背后所隐含的新锐而超越时代的小说理念,是福尔斯小说“新”先锋性的独特之处。但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将“元小说”当作后现代实验技巧或创作方法加以探讨,对于福尔斯在作品中通过“元小说”方式所表达的具有反叛性的新先锋理念,国内外批评界迄今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即以此为学术命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新先锋理念:对历史先锋与战后先锋的双重反叛
作为一部“先锋理念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与西方的“理念小说”(Novel of Ideas)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文学理论与文学术语词典》中对“理念小说”有如此解释:“在此类小说中,对话、智性讨论与辩说占主导地位,情节、叙述、情感冲突和人物心理深度则受到刻意限制。”(9)J. A. Cuddon, e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London: Penguin, 1999, p.602.“理念小说”注重理念或思想的探讨,情节框架与人物塑造被降至次要地位,人物形象不得不服务于某个理念,甚至成为某个理念或思想的化身,因此这类小说也经常受到批评界的诟病。(10)Michael Lemahieu, “The Novel of Ideas,” in David Jam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ritish Fiction since 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77.的确,《法国中尉的女人》传达了福尔斯的先锋小说理念,也深刻审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先锋思想,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当代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结构主义文艺思想等,并与它们进行深层的对话,但是,它在整体思路与结构框架上以“讲故事”为主线,并没有沦为特定观念和思想的传声筒或发声器,尤其是它对维多利亚小说情节、人物、风格、语言、叙事等传统要素的戏仿,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与元小说评论层形成了结构上的张力。换言之,福尔斯并不是简单地表达先锋小说理念或直接呈现文艺思想,对小说的艺术性弃之不顾,而是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保持着动态而微妙的平衡。
这部小说共有61章,其中第13章被批评界视作文本内部的一个重要“音顿”(caesura)。(11)Onega,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Novels of John Fowles, p.91.在前12章中,福尔斯先以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法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另类”女性萨拉的故事,情节引人,形象生动,叙事典雅,描写入微。但是在第12章的结尾,叙述者突然提出了两个问题:“萨拉是谁?她是从什么样的阴影中冒出来的?”在随后的第13章开头,福尔斯笔锋一转,风格大变,突然让叙述者“闯入”故事,脱离此前的故事进程,讨论起小说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篇幅之大,内容之多,理念之新,极为引人瞩目。实际上已与小说作者合二为一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说:
对于上面两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所讲述的这个故事纯粹是想象。我所塑造的人物在我的脑海之外根本不存在。假如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装作了解我笔下人物的思想和内心世界,那只是因为我所采用的是我的故事进行的那个时代被广泛采用的传统写法(就连某些词汇和“语气”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小说家仅次于上帝,他可能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但他要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可是我生活在阿兰·罗伯-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的时代,倘若此书也要作为一本小说的话,那它就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了。(12)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刘宪之、蔺延梓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以下来自该译本的引文,均在括号内标出页码,不再另行加注。个别译文参照原文作出较多调整。
第13章共有15段,前11段都是叙述者“我”突然介入故事的元小说评论层,是小说家-叙述者对小说的本质及其与非小说的差异、小说家的地位、小说家与人物的关系、小说家的创作动机、自由与权威、真实与虚构等问题大加评论,完全背离了前12章中的“传统写法”。有学者曾经指出,“福尔斯在这部小说中所发表的对‘小说’的看法, 应该说表现出了一种‘先锋性’的姿态”。(13)盛宁:《文本的虚构性与历史的重构——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删节谈起》,《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10页。确如所言,元小说评论层既是这部小说“新”先锋性的重要表征,也是福尔斯先锋探索精神的重要体现。标新立异、别具一格的元小说评论不仅颠覆了西方文学叙事传统,而且挑战了英国乃至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主流,以及二战后兴起的以法国“新小说派”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创作。
从创作理念来看,《法国中尉的女人》首先是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即“现代小说”的自觉反叛。这一反叛主要体现在对已经成为正统和主流的现代小说观念的反叛。20世纪早期,伍尔夫提出“现代小说”的概念,以反对爱德华时代的小说创作,在英美批评界被视作具有先锋精神的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伍尔夫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与意识流手法,反叛英国现实主义文艺潮流,探讨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实,挑战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其作品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成为经典,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艺思潮的正统和主流。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意识流”等现代小说开始失去其新锐的先锋性,反过来又成为50年代新一辈作家即“愤怒的青年”作家的反叛对象。福尔斯延续了50年代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潮流,但是并没有简单地回归传统写实主义,而是创作了一部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现代”的先锋实验小说。在一次采访中,福尔斯认为“过去常常所说的先锋写作现在死了”,但他本人并不“拒斥实验写作”;(14)Katherine Tarbox, “Interview with John Fowles,” in Dianne Vipond, 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Fowles,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9, p.157.在另一次访谈中,他明确表达自己并“不反对先锋写作”,(15)Carol M. Barnum, “An Interview with John Fowles,” in Vipond, 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Fowles, p.114.而事实上,他是勇于突破现代主义传统的新先锋探索者。福尔斯新先锋理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维多利亚“旧传统”既借用又超越的态度和立场。换言之,福尔斯一方面反叛英国现代主义传统,即已经成为历史或已经“过时”的英国历史先锋派,另一方面又隐身于“旧传统”之中,或者说以“旧传统”作为叙事依托,通过元小说的实验手段表达他的先锋创作理念,从而达到颠覆“旧传统”的目的。如果借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内爆” (Implosion)概念来说,福尔斯是在“旧传统”中进行“内爆”,从而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打破。他的先锋姿态寄生在传统的肌体或血液之中,而传统的肌体或血液中又暗藏着充满破坏力的先锋性。这是福尔斯与50年代艾米斯(Kinsley Amis)等人至为重要的不同之处。后者在反叛实验、回归传统的艺术实践中,虽然展现出了一定的艺术反叛活力,但是因为缺少艺术的探索性与实验性,很难被认定是带有“先锋性”的小说家。
“闯入文本的作者”(the intrusive author)自称“生活在罗伯-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的时代”,表明福尔斯对欧洲大陆兴起的先锋文艺思潮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知。曾有学者指出,福尔斯在第13章对小说艺术形式所表现出的革新冲动,与同时代法国先锋派作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6)James R. Aubrey, “John Fowles and Creative Non-Fiction,” in James Acheson, ed., John Fowl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34.二战后,西方文坛涌现出了各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流派,后现代小说家们对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先锋派进行反叛,并取代现代主义成为新一代的先锋派。法国“新小说派”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新先锋派之一,也是二战后欧美十分重要的先锋文学流派,而罗伯-格里耶则是“新小说派”的领军人物。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们反叛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尤其拒斥19世纪巴尔扎克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同时也极力摆脱普鲁斯特现代主义创作模式的束缚与禁锢,在小说情节、人物、主题、时序等层面对小说进行了极端的实验与激进的革新。此外,“新小说派”也是二战后小说危机的背景下,理论与文学相互靠近而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先锋文学流派。具体来说,“新小说派”是伴随结构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而形成的进行自觉艺术实验的先锋小说流派,罗兰·巴特则是那一时期首屈一指的结构主义批评家。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先锋写作“与结构主义不期而遇”,他们对语言的关注与巴特所提倡的“零度文学”发生吻合。(17)François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2, trans. by Deborah Glass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200, 203-204.福尔斯通过“元小说”的方式对罗伯-格里耶和罗兰·巴特作出评说,既源于他在牛津大学所接受过的系统法国文学训练,也来自他对二战后先锋文艺动态敏锐的感知力。叙述者直白的评论充分表明,福尔斯的创作无意迎合二战后文学潮流或文坛主流,而是另辟蹊径,试图对新兴的激进先锋文艺潮流或理论思潮作出审慎的审美回应,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先锋艺术策略在于借用传统的外衣——在时空、人物、语言、文体等层面戏仿维多利亚小说传统,通过“回归”之举达到对现代与后现代小说的反拨或拒斥,以实现对历史先锋与战后先锋的双重反叛。
福尔斯在谈到《法国中尉的女人》时说:“在旧传统中写作让我在多大程度上沦为懦夫? 我又在多大程度上惊惶失措地跌入先锋派?”(18)John Fowles, “Notes on an Unfinished Novel,” in Malcolm Bradbury, ed., The Novel Today: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40.有研究者认为,福尔斯将关于传统与先锋的两个自问并置在一起,旨在“阐明自己的真实立场,表明他试图在两极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19)William J. Palmer, The Fiction of John Fowl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4, p.4.从表面上看,福尔斯似乎是对传统与激进先锋艺术采取修正式、折中调和式的态度和立场。其实,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说明福尔斯只是一个折中主义者、妥协主义者,其小说理念的先锋性就无从谈起。然而,“寻找中间地带”之说,即福尔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达成妥协,未免是过于简单的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典范性的后现代主义实验作品,所谓“妥协”背后隐含着强烈的先锋意识。简言之,福尔斯小说理念的先锋性在于其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悖论性并置。福尔斯身处文学城堡的内部,深知自己被西方文学传统、现代主义文艺潮流以及二战后法国“新小说”这样的新先锋派所包围,因而他所挑战与反叛的,就是这些现有的被普遍接受的小说创作理念或新锐的“新小说派”创作理念,而他所采用“传统”叙事与元小说评论并置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反叛历史先锋派,也不苟同于新崛起的以“新小说派”为代表的激进先锋艺术潮流。可以说,福尔斯给自己的先锋姿态披上了一层“传统”的外衣,因此,这也是一个悖论性的、容易被误读的先锋姿态。
二、作者与读者的共生:多重先锋主义小说思想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借助叙述者,亦即元小说评论者之口,表达了异于传统,或说不同于现代文坛主流认知的多重先锋主义小说思想。首先,在对小说本质的认识上,福尔斯突破了普遍存在的真实性、实在性的文艺理论,如现实主义文艺对生活真实的模仿和再现,现代主义文学对内心真实的揭示。如叙述者认为,小说是作家想象的产物,小说人物在作家意识之外是不存在的,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并且指出,尽管小说家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创作动机,但他们都“希望尽可能把世界塑造得如同现实世界一样真实,但又跟现实世界不完全相同,也不同于过去那个世界”。(111)于此,叙述者引用了二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腊人的名言——“虚构无处不在”,还以第二人称“你”的方式,就“虚构性”对想象中的读者发表看法:“其实,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过去并不真实,因此你装扮它,美化它,或涂抹它,删改它,修补它……总之是对它虚构。虚构完毕后,便把它搁在书架上——成了你的一本书,你的理想化了的自传。我们都在逃避真正的现实。”(112)叙述者的小说虚构理念充分反映了福尔斯本人的创作理念。1973年,福尔斯曾对小说的虚构性以及游戏性作出深刻的阐述:“现代小说的所谓‘危机’与它的自觉意识有关。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存在固有的缺陷,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是一种允许作品与读者玩捉迷藏游戏的巧计。严格地说,小说大体上是个很巧妙而且能令人信服的假设——也就是说它与谎言是最亲密的表亲。小说家因为意识到自己在说谎而感到不安,所以大部分小说孜孜不倦地描摹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揭穿这个游戏、在作品中让谎言即小说创作过程的虚构本质凸现出来,成为当代小说的特色之一。”(20)John Fowles, “Foreword” to Poems, New York: Ecco Press, 1973, p.vii.在《一部未完成手稿的笔记》中,福尔斯还说:“如果你想忠实于生活,那么就用谎言来书写现实生活吧。”(21)Fowles, “Notes on an Unfinished Novel,” in Bradbury, ed., The Novel Today, p.139.福尔斯将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想象、虚构、杜撰、游戏乃至说谎,悖论性地理解为是对生活的忠实,在“文学衰竭论”及“小说危机论”的背景下,这无疑具有引人瞩目的先锋性。
关于小说家的地位和作用,福尔斯的见解独树一帜,同样具有鲜明的先锋性。也可以说,对传统作者观与现代作者观的自觉反叛,是福尔斯先锋小说理念的另一个核心内涵。如叙述者说:“现在,小说家仍旧是上帝,因为他可以创造一切(即便是最任性的现代先锋小说,也不可能把作者排除在外)。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已经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上帝形象:无所不知、号令一切;而是新的上帝形象,我们的首要原则是自由,而不是权威。”(112)显然,福尔斯以作者闯入叙事的方式修订了全知全能的传统作者观,同时认为“最任性的现代先锋小说”也无法把作者排除在外。这是对二战后消解主体或者说“主体之死”的反对,更是对罗兰·巴特影响一时的“作者死亡论”的否定性回应。叙述者将小说家视作“新的上帝形象”,一方面消解了传统作者的绝对权威,同时将“自由”看作是文艺创作的“首要原则”,反映出福尔斯对现有的艺术圭臬的反抗意识,以及反叛各种文艺传统的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精神,代表了20世纪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种精神诉求。福尔斯虽然反对传统或现代小说的作者观,但也不认同“新小说派”的作者观,他坚持认为文本中的作者声音是无法抹杀的。在《哈代与巫婆》一文中,福尔斯直言不讳地说:“我无法相信‘声音’是已经死亡的技巧。没有任何技巧能够使我们摆脱‘全知作者’的罪名——新小说理论当然也不能,……罗伯-格里耶或许已经把作为作者的罗伯-格里耶完全从小说中抹去,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创作了小说,……如果一个作家仍然在从事创作,并且像罗伯-格里耶那样写得不错,那么他就会出卖自己的声音。”(22)约翰·福尔斯:《哈代与巫婆》,《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曾经有学者认为,福尔斯在创作《法国中尉的女人》时是一个“带有批评自觉意识的后结构主义者”。(23)Mahitqsh Mandal, “‘Eyes a Man Could Drown In’: Phallic Myth and Femininity in John Fowles'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Vol.19, No.3, 2017, p.277.不过,福尔斯虽然摒弃“全知全能”作者观,尝试打破传统的作者主导意图论,质疑作者对写作的绝对控制,但也明确反对巴特意义上的“作者死亡论”,他只是主张将作品的自由解读或阐释权,部分让渡给读者。批评界大都注意到福尔斯在小说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事手法,在作者闯入文本时又使用第一人称“我”,却很少有人关注其元小说评论中的第二人称叙事及其背后的意义。在第13章多个段落的开头,叙述者使用了“或许你认为”“你可能以为”“呃,你可能会说”“要是你认为”等措辞,显示出叙述者“我”无论是探讨作者问题,还是分析人物的“真实”和“虚构”问题,都面向着一个直接对话者,即这部作品的隐性读者,实际上也就是广义上的小说读者。叙述者直接向“读者”表述:“为了使我自由,我就得给查尔斯,给蒂娜,给萨拉,甚至给面目可憎的波尔蒂尼夫人以自由。何为上帝?完美的定义只有一个,即允许别人保持自由。”(111)此时的叙述者,亦即作者福尔斯从全知全能作者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赋予他的人物以“自由”,而这实则是赋予读者对人物的自由认知与阐释权。福尔斯将“自由”视作首要原则,尤其是他对读者“自由”的重视,明确强调了作品意义的开放性、作者有限决定权,以及读者对作品的参与权。元小说评论中所表达的这些先锋理念,即对读者的重视,对读者参与人物建构与文本创作的认同,不仅早于巴特所提出的“可写文本”概念,也早于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于1970年代提出的“文本召唤结构”论与“隐含读者”论。
福尔斯放弃作者对文本的绝对阐释权,力主赋予读者“自由”,承认读者对人物、对作品意义的创造性作用,其读者观在其所处时代的先锋性不言而喻,并且他的先锋理念实际上也与当时兴起的后结构主义读者观形成了对话。1968年,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它们来源于多种文化并形成相互对话、相互戏仿与相互角逐的关系;而文本的多重性却汇聚在一处,这一处不是人们至今所说的作者,而是读者。”(24)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trans. by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 p.148.在巴特看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赋予,而是由读者赋予的,是读者在各自的阐释中创造出来的,读者的诞生是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的。不同的是,福尔斯也认同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但是并不否认作者赋予文本意义的重要性,他反对传统的以作者为中心的绝对认知与阐释框架,同时也反对极端抹杀作者地位的后结构主义读者观。在他看来,作者不可能死亡,作者的声音也无法抹杀,尽管作者已经不是传统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但仍然是“上帝”,仍然是作品的创造者与意义的重要赋予者;读者的自由解读固然重要,但是作者的意图或声音并非无足轻重。换言之,在福尔斯眼里,读者的诞生并不能抹杀作者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鲜活的存在,作者与读者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共同赋予了作品以巨大的生命力。
三、面向读者:开放式的阅读理念
福尔斯在《一部未完成手稿的笔记》中表示,他在小说中所使用的第一人称“我”并不等于作为真实作者的他本人。他在创作时经常提醒自己:“你不是那个闯入幻象中的‘我’,那个闯入幻象中的‘我’只是幻象的一部分。换言之,在我的故事中经常作出第一人称评论的‘我’,甚至最终进入故事的那个‘我’,并不是1967年真实的‘我’;这个‘我’更多的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尽管这个人物与纯粹虚构的人物并不相同。”(25)Fowles, “Notes on an Unfinished Novel,” in Bradbury, ed., The Novel Today, p.142.福尔斯对作者与叙述者作出了区分,并且意识到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差异,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他让叙述者——留着大胡子的“我”摇身一变,成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由此对传统与现代小说人物观提出了挑战。福尔斯用第三人称手法“全知全能”地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故事,但是在元小说评论层中,叙述者“我”又自称对笔下人物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并不了解,还经常介入“传统”故事,对“纯粹虚构的人物”直接品评与解读,还时不时变身为虚构故事中的人物,对“纯粹虚构的人物”观察打量,或冷眼旁观。因此,福尔斯的人物观与其作者观、读者观是相辅相成、交错融合的,同样都具有超越时代的先锋性。
如果以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作为例子加以分析,更能清晰揭示出福尔斯具有强烈先锋性的人物观与作者观、读者观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他的先锋小说理念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化或艺术内化过程。福尔斯秉持开放式的阅读理念,对小说男女主人公人物形象和结局作出开拓性、实验性的构想。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读者自始至终跟随男主人公查尔斯的视角来认识女主人公萨拉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女性人物:从一个起初被小镇居民视作法国中尉的“女人”或“情妇”,到最后成为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和超前存在主义思想的“新女性”。与传统或现代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赋予人物单一的固定的性格和形象,而是通过叙事者查尔斯的认知视角为读者呈现一个多面性、可变性的女性人物。与此同时,福尔斯又在元小说评论层中对“萨拉是谁”以及女主人公的性格与行为表现作出评说和议论,消解“作者”的权威,赋予人物内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赋予读者对人物进行解读与阐释的“自由”。这样就使作品女主人公萨拉如同一个开放的文本,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自由进入,可以主动参与这一人物形象的建构和文本意义的解读。
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接受史来看,不同的解读者因为视角不同,对女主人公所承载的女性主义主旨及内涵的解读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一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女主人公是带有女性主义思想的新女性形象,视之为“时代的叛逆者”,(26)王佐良等主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687页。或具有“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独立的人格意识”,(27)盛宁:《文本的虚构性与历史的重构——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删节谈起》,《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14页。而《法国中尉的女人》则是“一部理想的女权主义虚构作品”。(28)Deborah Byrd, “The Evolu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Sarah Woodruf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as a Feminist Nov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No.7, 1984, pp.306, 319.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小说中的男权意识形态压倒了女性主义主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玛格丽迈克尔(Magali Cornier Michael)的观点。在迈克尔看来,《法国中尉的女人》并不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或者说只是一部失败了的女性主义小说,因为女主人公萨拉是被三重男性视角——作家本人、叙述者、男主人公的视角呈现出来的,而萨拉本人的视角偏偏是缺席和不在场的。(29)Magali Cornier Michael, “‘Who is Sarah?’: A Critique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s Feminism,” Critique: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 Vol.28, No.4, 1987, pp.225-236.此外,福尔斯还将女性人物“文本化”“客体化”,更是遭到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质疑和批判。(30)Gwen Raaberg, “Against ‘Reading’: Text and/as Other in John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Women's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30,2001, pp.521-542.不过,即便迈克尔也承认这部小说具有“内在的矛盾性”(internal contradictions)。(31)Michael, “‘Who is Sarah?’,” pp.225-236.换言之,《法国中尉的女人》虽然充满多重男性叙事视角和虚构声音,浸透着强烈的男权意识形态,但是其文本内外也存在着诸多对男权话语的抵抗。福尔斯在建构女主人公萨拉的形象时,主观意图上并不希望自己作为创作者是人物意义的唯一或者说是权威赋予者,因此他故意“留白”,让读者拥有更多的想象和更大的意义建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萨拉成为英国文学史中最具开放性和争议性的女性人物形象之一。借用美国后现代批评家哈桑(Ihab Hassan)所提出的“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概念,《法国中尉的女人》就是一部具有“不确定内在性”的后现代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福尔斯赋予人物以“自由”的理念,不仅在女主人公的身上得到了体现,而且在男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也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在小说第55章,叙述者以真实人物的身份出现在查尔斯赶往伦敦的火车上,并对男主人公的第一个可能结局予以设想。叙述者以元小说的方式评论道:“我曾想过,就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故事,把他永远留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模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开放的、不确定的结尾。我前面已经极力主张,必须给人物以自由。”(455)显然,福尔斯反对维多利亚小说单一封闭的结局,试图按照生活本有的选择偶然性为主人公构想一个“两难的结局”,并且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提供两种可能性”。但是线性叙述一次不可能同时提供“两个版本”,在叙述者下了火车,留下昏睡的查尔斯是一个版本,男主人公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而第二个“版本”,即查尔斯从昏昏欲睡中醒来,继续他赶赴伦敦寻找萨拉的既定行程。福尔斯通过叙述者之口,认为第二个版本才是最终“真实”的版本。叙述者给“真实”一词加上引号,一方面突出小说的虚构本质,另一方面诉诸读者对虚构故事与虚构人物的再创造可能性。此后,福尔斯又以元小说方式为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关系虚构了不同的结局,国内外学界对此多有评论,本文不再赘述。
人物的开放性、结局的多重可能性,通过这些具有先锋性艺术手法的探索和实验,福尔斯打破了传统的阅读理念。他以元小说的方式与读者对话,主动邀请读者参与人物塑造,让读者成为文本的共同创造者以及文本意义的共同建构者。简言之,福尔斯的先锋理念在于,作者的意图或意指意义并不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来源,人物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或独立性,文本内部存在着英伽登意义上的“空白点”或意义未定点,因此读者的积极参与和意义建构同样十分重要。实际上,福尔斯是以其超前的先锋艺术理念,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进行了对话。
结 语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二战后的一部“新”先锋小说,是福尔斯新先锋理念的产物,而福尔斯的新先锋理念又主要通过具有强烈先锋性的“元小说评论”来表达。这部后现代元小说超越了当时以极端形式实验为中心的其他后现代小说,在二战后的西方文坛特立独行,堪称是二战后“新”先锋小说的一个典范。法国戏剧家尤奈斯库说:“所谓先锋,就是自由。”(32)《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579页。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寻求的是一种在西方小说危机时期的艺术自由与精神自由,不过他所追求的自由更像是一种变革与创新,而不是绝对的艺术形式自由。福尔斯不是在创作“最任性的现代先锋小说”,而是从小说传统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从而与审美极端主义保持距离。这种悖论性并不会解构福尔斯创作理念的先锋性,反而代表了其先锋审美理念的开创性与独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