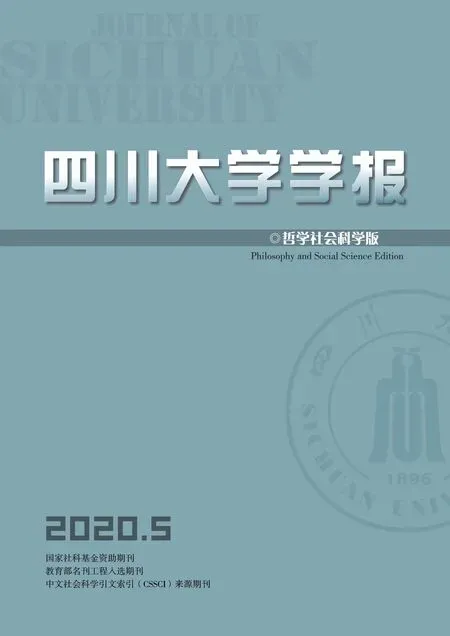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2020-12-31黄勇
黄 勇
本文取名“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而不是“宋明儒学:从美德伦理学的观点看”,是有意的。我想以此表明,美德伦理学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你可以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去看,从休谟主义的观点去看,也可以从儒学、特别是宋明儒的观点去看,当然你也可以从很多别的观点去看。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知道美德伦理学,你可以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看休谟的著作,也可以看儒家、包括宋明儒的著作,当然你还可以看很多别的著作。就是说,美德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的某个特殊的历史形态(如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的特权。另外,这个篇名也表明,本文所讨论的不是要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去考察宋明儒学,证明宋明儒学也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相反,本文要做的是从宋明儒学的角度去考察美德伦理学,虽然并不是要证明美德伦理学也是一种宋明儒学,但确实是要证明宋明儒学可以为美德伦理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尽管美德伦理学在当代西方获得了长足的复兴,成了自近代以来作为西方伦理学主流的义务论和后果论的有力挑战者,但它不仅经常遭到后者的批评,而且自身也确实存在着各种缺陷。对于前者,它需要作出恰当的回应,对于后者,它需要得到创造性的修正和发展,而宋明儒在这两方面都可以作出贡献。本文的讨论将以二程、朱熹和王阳明为中心。(1)本文是笔者为即将付印的《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书所写的导言的一部分,在这里先行刊出。本文提纲挈领地说明了该书的九个核心问题,以对应该书的九章,因此关于本文无法作出的详细论证,包括一些重要的文献,可参阅该书的相应部分。
一、 二程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贡献
关于二程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贡献,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在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即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间的争论,并说明程颢的美德伦理学可以如何帮助我们超越这两派之间的争论。在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亚里士多德主义是主流。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美德伦理学,这不只是因为它将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独特标志,而且还因为它试图对什么是美德作出一种理性的说明:美德是导致人的繁荣或幸福(eudaimonia)的品质。理性主义美德伦理学的问题之一是,在做了这样的说明以后,美德不再是首要的,而成了从属于人的繁荣或幸福的概念,而这样,这种伦理学是否还是美德伦理学便成了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美德伦理学复兴运动中的休谟主义。它是一种情感主义的美德伦理学,这不仅是因为它作为美德的是像爱(love)、关怀(care)特别是同感(empathy)这样的情感,而且是因为它拒绝给为什么这样的情感是美德提供一种理性的说明,理由是大家凭直觉就知道这样的情感是美德,是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令人羡慕的(admirable);而一些相反的情感,如仇恨、冷淡和无感等,则是令人厌恶的(deplorable),即是坏的、是恶德。但一种美德伦理学不告诉人们什么是美德总是一种缺陷。
这种情感主义的最主要代表是斯洛特(Michael Slote)。他认为同感是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的最重要美德。在说明这个美德时,他特别提到中国哲学家程颢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同感哲学家,因为程颢说仁者所具有的万物一体感实际上就是同感。大家知道,程颢在解释儒家最重要的美德“仁”时,同医家的“不仁”类比:“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2)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页。反过来,医家说的仁就是能够知觉自身的痛痒,而作为儒家的美德的仁便是能够将这种知觉痛痒的能力不断向外扩展,一直到万物,也就是将可以认作自己身体之一部分的范围不断往外扩展,一直到能以万物为一体。所以,在程颢那里,感到与某物为一体就是能感到该物的痛痒。我能感到自己手脚的痛痒,就说明我的手脚与我一体,我能感到我父母的痛痒说明我与父母为一体,我能感到万物的痛痒就表明我与万物为一体。当然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身体(而仁者将万物都作为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的某一部位有痛痒,就一定会很自然地去设法去除这种痛痒。在这个意义上,程颢的万物一体观即同感观确实与斯洛特的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非常一致。不一样的是,斯洛特是以其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来替代理性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但在程颢那里,这种情感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是与理性主义美德伦理学一致的。关键是,虽然同感即万物一体感作为一种美德在程颢哲学中占有核心地位,程颢为它作为美德提供了一种解释:同感就是儒家传统中最重要的仁的表现,而仁是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换言之,要成为一个人,就必须要有仁,而仁者便能以万物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程颢用来说明仁这种美德的人性概念本身就是由仁构成的,这样的说明保持了仁这种美德在其伦理学中的首要性,因而他的伦理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程颢的美德伦理学既有情感主义的成分,又有理性主义的成分,从而超越了美德伦理学内部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争。
至于二程对美德伦理学的第二个贡献,我将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去说明程颐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古老而又根本的问题。规范伦理学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人有道德。所以从古代开始,就出现了“我为什么应该有道德”这个利己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意为“我有道德对我有什么好处”或者“我有什么理由应该有道德”。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一个与“我们为什么要有道德”不一样的问题,因为后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回答:如果我们都不道德,如霍布士通过其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所表明的,我们都不能存在下去。这个问题的最早形式是柏拉图的“我为什么应该有正义”,而正义是一种美德,因此这个问题在柏拉图那里问的是“我为什么应该成为具有正义这种美德的人”。只是在近代以来,随着义务论和后果论伦理学开始占主导地位,这个问题逐渐变成了“我为什么应该做有道德的行动”。由于这个问题因此而变得很难回答,一些哲学家干脆将其看作是一个荒唐的问题而不予理睬。他们要么将其看作是一个同义反复的问题:道德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而问“我为什么应该有道德”就是问“我为什么应该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要么将其看作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道德就是要求我们不要将私利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而既然问这个问题的人关心的是做道德的事对我的私利有什么好处,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不把私利作为我的行动的出发点对我的私利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回答,还是要回到美德伦理学的进路,即“我为什么应该成为有美德的人即有德者”,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美德伦理学回答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柏拉图的问题是,真正能具有公正这种美德的人只是少量的哲学家,而问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不是而且(根据柏拉图的观点)由于缺乏恰当的出生和教育也不可能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是,虽然他认为理性是人的独特功能, 但如当代哲学家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和麦克道(John McDowell)所指出的,他没有在理性与实践美德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他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一个理性的人一定是有(实践)美德的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程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有道理。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有德者呢?程颐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你是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程颐看来,人的独特性即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者,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性,而是由仁义礼智构成的人性,而仁义礼智又是儒家的根本美德。例如,程颐说,“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而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虽然程颐在这里说,一旦失去了仁义之性、仁义之德,这个人就成了禽兽,但这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成了健全的禽兽,而只表示他成了有缺陷的人。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就其实际情形而言确实与禽兽无异,但就其潜能来说,他们还是与禽兽不同,因为后者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有仁义的人,而前者只要努力做好事就可以变成人。所以要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健全的、没有缺陷的人,这个人就必须是有德者。正是因为这样,程颐认为成为一个有德者即成为一个心体上健康的人,同成为一个身体上健康的人一样,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所以当有人问如何求道之大本时,程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23、187页。
二程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将美德伦理学扩展到解释学的范围、以形成美德解释学。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解释学的两种类型,我分别称之为作为为己之学的解释学和作为为人之学的解释学。(4)黄勇:《解释学的两种类型: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第46页。我这里用的“为己”与孔子在《宪问》篇第二十四章讲的“古之学者为己”中的“为己”意近但稍广,但我用的“为人”则与孔子在同一个地方讲的“今之学者为人”中的“为人”不同。孔子肯定为己而反对为人,而在我这里两者都是褒义词,它们表示的两种解释学服务于两个不同的目的,而这两个目的都是正面的。作为为人之学的解释学的解释对象是作为我们的行动对象的、即为我们的行动影响的他者,而解释活动的目的是要理解这些他者的独特性,从而使我们涉及到他们的行动具有道德上的恰当性。这是因为,我们对一个行动对象做的对的事情,如果对另一个行动对象做,就不一定是对的。相反,作为为己之学的解释学的解释对象也可以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他者,但更多的是古代的经典,而我们的解释活动的目的则是从他者那里学到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使我们自己变成更好的人,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几乎成为显学的解释学领域,有几位大师级代表人物,包括德国的伽德默(Hans-Georg Gadamer)、法国的利科(Paul Ricoeur)和美国的罗蒂(Richar Rorty),都提倡为己之学的解释学。例如,罗蒂认为, 解释学“主要不是对外部世界存在什么东西或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东西感兴趣, 而是对我们能从自然和历史中得到什么东西为我们所用感兴趣”,因此, “它不是把认识而是把修养、教育(自我形成) 作为思考的目的”;在他看来,“当我们继续去读书、继续去对话、继续去写作时, 我们就变成了不同的人, 就改造了我们自己”。(5)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59.为了与此形成对照,我在那篇文章中强调了几乎没有人谈论过的作为为人之学的解释学。
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二程的美德解释学则属于一种为己的解释学。根据这种解释学,我们的解释活动是为了作为解释者的自己。但与同样作为为己之学的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主要不同是,二程强调的是为后者所忽略的为己的道德层面,而不是他们所强调的知识的层面、趣味的层面、精神的层面。在二程看来,圣人作经,本欲明道,而这里圣人欲明之道就是成人、成圣之道,而要理解经典不只是要在理智上知道这种成人、成圣之道,而是要自己学习成人、成圣。所以程颐在其著名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就说,虽然孔子的三千弟子无不精通《诗》《书》等六艺,颜子所独好之处就是“学以至圣人之道”。程子认为,“学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见其进也”。值得指出的是,在二程那里,这种作为为己之学的解释学与作为为人之学的解释学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为人的解释学的目的是要了解我们的行为对象的独特性,从而使我们涉及他们的行为更加恰当。可是,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美德,他就不会有关心他人的动机,因而也就没有去了解他人之独特性的欲望。另一方面,有了美德解释学这种为己的解释学,一个学者就成了具有美德的人,而作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他一定会有帮助人的动机,而为了恰当地帮助人,他就要了解其行为对象的独特性,而这就需要有为人的解释学。所以程颐不主张“强恕而行”,因为强恕而行是“以己之好恶处人而已,未至于无我也”。说以己之好恶处人,实际上就是己所欲,施于人(所谓的道德金律),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的道德银律)。这假定了己之好恶就是人之好恶。相反,二程认为圣人无我。怎么实现无我呢?程颢说,如果“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同样,程颐也说,我们应该“以物待物,不可以以己待物”。(6)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75、125、165页。我在别的地方将二程的这种思想概括为与上述道德金律、银律不同的道德“铜律”: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 朱熹对美德伦理学的贡献
朱熹的伦理学思想非常丰富,也可以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发展作出多样的贡献,我在这里简单地提三点。首先我们看朱熹如何可以帮助美德伦理学回应主要是来自康德主义的一个批评,即认为美德伦理学具有自我中心的倾向。根据功用主义,一个人要做道德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幸福的总量;根据义务论,一个人要做道德的事情,因为这是普遍的道德法则的要求;而根据美德伦理学,一个人要做道德的事,因为这样他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比较下来,在美德伦理学中,一个人做好事是为了自己,因而具有自我中心倾向。当然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要成为具有美德的人就必须帮助人,因而具有利他主义倾向。但批评美德伦理学具有自我中心倾向的人所指的是更深刻的两层意义。一方面,具有美德的人确实会帮助人,但他帮助的是他人的外在福祉如福寿康宁等,而通过这种帮助活动他自己获得的却是内在福祉即美德,同时他又认为内在福祉比外在福祉更有价值。这就是说,他把不那么重要的东西给他人,而将更有价值的东西给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我中心的。另一方面,具有美德的人当然会帮助人、而且是为他人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自利而帮助人,但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为了自己成为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如果他不帮助人、甚至他帮助人但不是为他人之故而是为自身的利益(例如希望以后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他就不能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因此,虽然他在表面的意义上不是自私的但在基础的意义上还是自私的,因为他似乎将“无私地”帮助人作为自己成为具有美德的人的手段。我曾做过详细的论证,表明作为西方美德伦理学主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还是当代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都确实具有这两种意义上的自我中心倾向。
在此背景下我以朱熹为例,说明儒家的美德伦理学如何可以在上述两个深刻的层面上回应这样的批评。一方面,儒家具有美德的人不仅会关心他人的外在福祉,也会关心其内在福祉。对于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朱熹强调这不只指外在的方面,也指内在的方面,因此,他很赞成一个学生就其内在的方面的领悟:“如己欲为君子,则欲人皆为君子;己不欲为小人,则亦不欲人为小人。”(7)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71页。朱熹在解释大学一开头的“明明德,新民”时也强调,明明德就是明自己的德,即自己要成为有德者,而新民就是要帮助他人明其明德,即使他人成为有德者。更重要的是,在朱熹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去帮助他人明其明德,他自己的明德也不可能止于至处。另一方面,在明明德与新民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自己的德愈明,就愈能帮助他人明其明德,而一个人愈是帮助他人明其明德,自己的德也就愈明。这里不存在工具与手段的关系。一个人去新民不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有德者,因而他不是基础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同时一个人明自己的明德的目的也不只是为了去明他人之明德,因而他也不是基础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者。由于利己与利他在一个有德者那里完全重合了,你可以说他既是利己主义者又是利他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既不是利己主义者也不是利他主义者,但肯定不是只是其中之一而非其中之二。换言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不是对这样的人的恰当描述。
朱熹的伦理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回应外来的对美德伦理学的上述批评,还可以帮助美德伦理学克服它自身的一个问题,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瓦森(Gary Watson)在其非常有影响的一篇论文《性格的首要性》(Primacy of Character)中提出的美德伦理学的两个两难。美德伦理学是美德在其中具有首要性的伦理学,而不是所有具有美德概念的伦理学。那么什么是美德呢?在瓦森看来,面对这个问题便出现了第一个两难。如果我们对什么是美德提供一种说明,大家知道了什么是美德,这个时候,用来说明美德的东西便获得了首要性,而美德只具有次要性,这也就是说这种伦理学已经不再是美德伦理学了。而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美德概念的首要性并使这个伦理学成为美德伦理学,我们可以拒绝给什么是美德提供一个说明,但这样一来,我们对连在美德伦理学中具有首要性的美德概念都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假如我们决定对什么是美德做一个说明,一个最恰当的办法是诉诸一种人性论,即关于人之为人的独特性的理论,而在这个时候,瓦森认为,我们便遇到了美德伦理学的第二个两难。如果我们诉诸的这种人性理论是一种客观的理论,那么就无法从中推出具有规范性的美德概念;而如果为了推出具有规范性的美德概念而诉诸一种规范的人性论,它却失去了客观性,而如果没有客观性,我们怎么能证明它所说的真的是人性呢。我曾做过详细的考察,认为西方的美德伦理学家确实还没有对这两个两难提供恰当的解决方案。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的贡献。面对瓦森所谓的第一个两难,朱熹采取的是给美德提供一种说明,而且这种说明也诉诸一种人性概念。但是它诉诸的儒家的人性论认为,把人作为人的独特性、即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恰恰就是儒家的美德。也就是说,在儒家那里美德与人性是合一的,因此在用人性来说明美德时,美德概念在儒家伦理学中没有失去其首要性,因而儒家伦理学在提供了对美德的说明后还是一种美德伦理学,这样就避免了第一个两难。但这种避免第一个两难的方式似乎有循环论证之嫌:它用人性来说明美德,又用美德来说明人性。要确定这是否是一种廉价论证,关键是要看,当朱熹说人性就是仁义礼智的美德时,他有没有客观根据,而这涉及了瓦森提到的第二个两难。朱熹的人性概念由于认为人性是仁义礼智而毫无疑问地具有规范性,但朱熹怎么知道人性即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就是仁义礼智呢?朱熹没有简单地说,人应该有仁义礼智,而是提出了两个论证。一个是我们看到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情,而如果没有仁义礼智之性,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情的。另一个是即使有些人失去了这四端而成了恶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与禽兽无异,但所有这些人只要不自暴自弃都可以重新获得这四端而成为善人,但动物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善人。这就表明,朱熹的儒家人性观既有客观性又有规范性,从而不仅避免了瓦森提到的第二个两难,而且也表明朱熹用以避免第一个两难的论证不是循环论证。
朱熹对美德伦理学可以作出的第三个贡献则是扩展美德伦理学的视阈。美德伦理学本身是一种规范伦理学,我们这里将考察这种美德伦理学在元伦理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所能作出的贡献。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德性质的地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有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之间的争论。从直观上来说,如果可以得到证明,认知主义是一种比较可取的立场,因为按照非认知主义,我们所有的道德命题都不过是经过伪装了的情绪表达,因而只有恰当与否的问题、而没有真假的问题。认知主义又可分为道德实在论和道德反实在论。从直观上来说,如果可以得到证明,道德实在论是一种比较可取的立场,因为按照反实在论,判断道德命题之真假的标准都是主观甚至任意的。而道德实在论又可以分为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从直观上来说,如果可以得到证明的话,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比较可取,因为非自然主义的实在论往往只能通过类比告诉我们,道德性质是与(例如)数学性质类似的非自然性质,而不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但要论证在道德性质的地位问题上的这种认知主义的、实在论的、自然主义的元伦理学立场却因面临重重困难而鲜有成功者。这些困难至少包含这四个:(1)休谟的从“是”推不出“应该”的论证;(2)摩尔(G.E. Moore)的开放论证难题(不管你说道德性质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问:这个真的是道德性质吗?);(3)麦基(John Mackie)的怪异性(queerness)论证(如果道德性质是客观的,那它一定是一种非常怪异的性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行动之“对”和“错”这样的性质,而且如果这样的性质客观地存在的话,我们需要有一种与我们现在已有的不同的感觉器官才能发现他们);(4)麦基和哈曼(Gilbert Harman)的不可追踪的道德分歧论证(如果道德性质是客观的,那么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应该类似于在科学问题上的争论:在证据齐全后这样的争论就会自动消失,但道德问题上的争论往往与客观的证据无关)。
在我看来,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之所以很难成功地避免这四大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类实在论往往以行动为中心,试图确立呈现在行动中的道德上的“对”或“错”的性质。朱熹在这个元伦理学问题上采取的是美德伦理学的进路,它要确定其客观性的道德性质不是行动的对或者错,而是人的好或者坏。而要确定人的好与坏,我们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即将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是什么。好人就是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人性的人,而坏人就是没有很好地体现这种人性的人。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就是使人之为人者,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此(即仁)而已。一心之间,浑然天理,动容周旋,造次颠沛,不可违也。一违,则私欲间乎其间,为不仁矣。虽曰二物,其实一理。盖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别有仁也”;又说,“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则不见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见得道理出来”。(8)朱熹:《朱子语类》,第1459页。这就说明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有仁,没有了仁,一个人就不再是人了,或者是有缺陷的人了,或者只是名义上的人了,或者是与动物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段话中的“不可违也”的“不可”是规范意义的“不可”,意为不容许、“不应该”或“不应当”,而不是描述意义上“不能够”,因为这一段接下来马上就讲了人能够违仁。但既然一个人能够违仁为什么就不应该违仁呢?就是因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因此在朱熹那里,人性论是一种客观的理论,即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观察基础上的。
三、 王阳明对美德伦理学的贡献
王阳明的伦理学也可以对当代美德伦理学作出重大贡献,我们在这里也仅讨论其中的三个方面,而其中的两个方面都与其万物一体观有关。同感(empathy)是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而斯洛特(Michael Slote)是这种美德伦理学的最重要代表。同感与我们更熟悉的同情(sympathy)不同。同感是在看到他人有痛痒时,自己也能感到这个人的痛痒,就好像这是自己的痛痒,而同情的人并不感到他人的痛痒,而是在知道他人有痛痒以后而产生的像遗憾这样的情感。所以同感的人感到的与同感对象所感到的是一致的,而同情的人感到的与同情对象感到的不一样。虽然具有同感的人和具有同情的人都往往有帮助其对象解除痛痒的行动,但这样的帮助行动的性质很不一样。具有同感的人由于对其对象的痛痒感同身受,就很自然地有一种欲望要去帮助他人解除这样的痛痒,与我们在感到(例如)自己背上有痒时想去抓痒的行动一样自然,并且不仅因为这种行动的成功(即解除了痛痒)而感到快乐,而且在这个行动过程中也感到快乐。具有同情的人不一定有去帮助其同情对象解除痛痒的欲望,但出于道德的考虑还是会去帮助,因此他的帮助行为就不那么自然(有时候还得克服相反的不想去做这种帮助行动的欲望),而且往往也不能从其帮助行动中感到快乐。因此,在斯洛特看来,在我们面临他人的负面处境时,同感是比同情更加可取的一种情感。斯洛特注意到,在西方哲学史上,休谟(1711—1776)是最早具有同感思想的哲学家,不过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发现同感现象要早得多。他这里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以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因为以万物为一体,就是能够感到万物的痛痒,而这就是同感。这种同感思想不仅王阳明(1472—1529)有,而且程颢(1032—1082)也有。但斯洛特同时又认为,当代心理学和伦理学对同感现象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过了休谟、王阳明和程颢的同感观,因而后者只有历史的意义而没有现实的意义。
但我认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观可以对当代同感理论作出至少两个重大的贡献。在当代西方心理学和伦理学里讨论的同感都是对他人外在福祉方面的缺失的同感,而在王阳明那里,具有万物一体感即同感的人不仅对他人的身体上的痛苦感同身受,而且也对他人心体上的痛苦感同身受。前者是身体上有缺陷的人,而后者是心体即道德上有缺陷的人,而具有万物一体感的人不仅会帮助前者克服其缺陷,也会帮助后者克服其缺陷。关于这方面,王阳明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4页。这段文字开头部分提到的“安”“全”“养”可能让人觉得,王阳明这里所讲的具有同感的人,即以万物为一体的人,也只是关心他人外在的或者身体方面的福祉,但这里的“教”明白无误地说明,一个具有同感的人对他人的关心不限于他人的外在的、物质的、身体的福祉,而一定也关心他人内在的福祉。关于“教”的具体内容,王阳明在该段的后半部分说得更明确,因为在这里他所关注的、作为同感对象的不是那些饥寒交迫的、物质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而是那些自私的、其本心为物欲遮蔽了的、甚至将自己的父子兄弟当仇人的人。王阳明认为,儒家所讲的具有同感的人会竭尽所能地帮助这些人“克其私,去其弊,以复其心体之同然”,使他们也能以万物为一体,即变成对他人具有同感的人。正是在这个让他人恢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即让他人恢复其同感心的过程中,圣人才能“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我们上面的讨论表明,王阳明的作为同感理论的万物一体观可以克服当代同感理论的一个盲点。接下来我将要讨论的是如何将本身作为规范伦理学的同感理论扩展到环境问题并形成一种卓有成效的环境美德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可以看作是一种应用伦理学,它把某种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应用到具体的环境问题。换个角度,环境伦理学也可以看成是传统伦理学的扩展形态:传统伦理学的道德对象仅限于人,而环境伦理学的道德对象还包括人之外的存在者。不管怎么说,环境伦理学和一般或传统伦理学密切相关。因此,环境伦理学自20世纪以来的发展与一般伦理学相似:在初始阶段,在环境伦理学中居主导地位的是后果论和道义论,而现在则是美德论开始出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美德伦理学的吸引力,既包括它自身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的吸引力,也包括它在应用或扩展到环境问题时的吸引力;二是因为道义论和后果论各自的缺陷,既包括这些理论自身的缺陷,也包括它们应用或扩展到环境问题时所表现的缺陷。但环境美德伦理学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即它将人类对环境的关心、即使是为环境而不是为人类而对环境的关心,看作是人的繁荣生活的必要条件,因此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观不只关心人类,而且关心鸟兽、草木甚至瓦石,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环境伦理学;他认为只有仁者才能以万物为一体,而仁在王阳明看来又是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的根本的美德,因此这是一种环境的美德伦理学。王阳明的环境美德伦理学可以避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因为它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因为它的万物一体观把人类与人类之外的所有其他存在物看作是一个联结体,而对这个联结体的关心就既不可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也不可能是自然中心主义的,因为这两者都假定了人与自然的分离,而在以万物为一体的仁者眼里,人与自然已成为一体,所以问人类关心自然是为自然考虑还是为人类自身考虑就失去了意义、或者说问错了问题。不过虽然王阳明主张仁者以万物为一体,这样的仁者对万物,从父母到路人、到鸟兽、到草木、到瓦石,并非一视同仁,而是厚薄有别的。换言之,王阳明持一种道德偏倚论,即儒家传统里的爱有差等。虽然作为一个心理学事实,大家都承认,我们对亲近的人的爱甚于对路人的爱,对路人的爱甚于对鸟兽的爱,对鸟兽的爱甚于对草木的爱,对草木的爱甚于对瓦石的爱,但如何在道德上证成这种偏倚性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王阳明认为这种差等之爱自有其“道理”和“条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说明王阳明的这种道理和条理究竟何指,我们就可以为道德偏倚论提供证明。
我要提到的王阳明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第三个贡献是他的美德伦理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道德运气”概念所具有的矛盾或者悖论性质。本来道德与运气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道德属于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而运气属于我们不可控制的范围,因此道德运气,即使根据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两位哲学家,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和乃格尔(Thomas Nagel),也要么是一个矛盾修饰(oxymoron)(威廉斯),要么是个悖论(paradox)(乃格尔)。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不能将运气因素完全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为超出他控制范围的事负责。乃格尔还区分了道德运气的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结果性的道德运气,即一个人的行动结果受运气支配(如一个人不小心开车撞上人行道,但正好人行道上没有人,因而不需为其行动负责;而另一个人正常地开车,但突然有人窜上马路被他的车压死,因而需要为其行为负责。前者有好运气,后者有坏运气);第二种是因果的道德运气,即一个人的行动结果使人得到了帮助或者受到了伤害,但这个人的行动本身不是他自由选择的,而是由在先的原因决定的;第三是情景的道德运气,例如一个生活在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和生活在当今德国社会中的德国人的道德选择可能很不一样,而这是由他们所处的不同情景决定的;最后一种是构成性的道德运气,即有些是好人,有些是坏人,但他们的道德构成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不管如何,我认为,威廉斯和乃格尔主张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为他所无法控制的运气造成的后果负责是说不通的。在这方面,王阳明的美德伦理学可以提供帮助。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失去美德或者变成恶人有两个(并非必须同时出现的)必要条件。一是这个人禀赋的气之不纯,还有一个是这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恶劣。由于这两个因素都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里面,而这两个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道德品质,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也有道德运气概念,而且这里涉及的应该是乃格尔所提到的最后一种道德运气,即构成性的道德运气。但是,王阳明指出,“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者志也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1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983页。这就说明,在王阳明看来,禀有不纯的气和生活在不好的环境中,虽然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有深刻的影响,但并不决定这个人的恶。换言之,如果一个人禀赋的不是不纯的气而且也不是生活在不好的环境中,这个人固然不会成恶人、做恶事,但一个人禀受了不纯的气、生活在了不利的环境中,这个人也不一定会变成恶人,尽管这个人如果成为恶人我们也应该给以理解、而不应该完全责备他。这样看来,在王阳明那里,不好的环境或(这里的“或”也具有“和”的意思)气质是一个人变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这些不好的习和气之所以能够遮蔽一个人的本心或良知并使之成恶,在于这个人没有立志去抵制它们的污染。而这又很显然地表明,对于王阳明来说,一个人的意志既不同于纯善的良知,也不同于纯恶的浑浊之气与腐败的习俗及其产生的遮蔽良知的私欲,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就是说一个人的意志既不自动地使人成为一个善人或去做善事,也不会自动地使人成为恶人或去做恶事。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关键是看你立什么样的志。如果这是为善避恶的意志,那它就是善的意志;如果它是作恶避善的意志,那它就是恶的意志。另外,这也表明,在王阳明那里,人的意志并不是被决定的,而是自由的。不仅当不好的习气来污染良知时,一个人可以决定不作为,也可以决定加以抵制,而且即使良知被这样的习气及由之产生的私欲遮蔽时,一个人可以决定不作为,也可以决定消除这样的遮蔽:“志立而习气渐消”。所以,王阳明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为其意志决定的后果负责,因为这是他可以控制的;而不能要求他为其运气因素决定的后果负责,因为这是他无法控制的。另一方面,由于运气确实对我们的美德构成产生重大影响,一个禀有极度浑浊之气、生活于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的人成善了,他就比那些禀气较清、环境不那么恶劣的人之成善更加可贵。这样,王阳明就较好地避免了威廉斯和乃格尔道德运气概念所隐含的一些不可理喻之处。
四、结 论
我在上面试图表明,本文的主旨并非是要证明宋明儒是美德伦理学家,当然更不是要证明,要成为美德伦理学家,你就必须接受宋明儒学,而是试图论证,在帮助美德伦理学回应外来的批评、克服其自身的一些问题、扩展美德伦理学的范围方面,宋明儒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从宽泛的意义上,本文从事的也是一种比较哲学的研究工作,但不是简单地将宋明儒与西方的美德伦理学家做比较,看他们的异同,而是用宋明儒学的资源来解决美德伦理学本身的问题。关于这样一种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我在别的地方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此不再重复。(11)参见 Yong Huang, Why Be Moral: Learning from the Neo-Confucian Cheng Brothers, Albany, 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pp.1-18;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68-77页。作为本文的结论,我想非常简单地回应一下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对我这种研究方式的描述(如果不是抱怨):我是在用中国哲学的资源来解决西方哲学的问题,因此本质上我在做的是西方哲学,而不是中国哲学。我想说的是,把我在(例如)本文中讨论的所有哲学问题说成是西方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中国哲学的问题本身是在把中国哲学贫乏化。事实上,宋明儒能够在这些美德伦理学的关键问题上不仅有独特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如果我的论证成功的话)比西方的美德伦理学家在同样问题上的看法更有道理这个事实就可以表明,这些问题也是宋明儒甚至一般的儒家或者更一般的中国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我并不否认一个特定的哲学传统可能有其特有的、为所有其他哲学传统所忽略甚至排斥的哲学问题,但我可以断定这样的问题不会太多。当然,如果我们在对别的哲学传统做了深入研究,然后发现中国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与它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如果不是完全不同至少很不相同、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至少没有多大关系,从而主张我们应该关起门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那也许是说得过去的,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当然,每个哲学传统都会有其独特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往往很难简单地翻译成其他哲学传统中相应的概念,如中国哲学中的阴阳、理气、道器、名实、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等,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传统中的哲学家想用这些独特的概念解决的哲学问题(而同一个传统中用相同的哲学概念的不同哲学家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也不尽相同)往往并不是那么独特的问题,就是说往往是其他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也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跨传统的哲学研究不仅不能从语词出发,(12)万百安称此为词典谬误(Lexical fallacy)参见Bryan van Norden,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2.而且也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问题出发。当然由于不同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各自用其特有的概念来处理他们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往往很不相同,但这正是要求我们走出自己的哲学传统、而不是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哲学传统内部从事哲学研究的理由。
这使我想起了被公认为宗教研究之父的德国学者缪勒(Max Mueller, 1823-1900)的一句为今天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不只是从事比较宗教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的名言:只知道一种宗教(通常是自己的宗教)的人是不知道宗教的人。事实上,这是缪勒将歌德就语言所说的一句话(只懂一种语言的人是不懂语言的人)转用于宗教。缪勒在1870年2到3月在伦敦皇家研究所做了4个讲座,我们这里提到的这句名言是他在第一讲中提到的。他首先解释了歌德说“只懂一种语言的人是不懂语言的人”的意思:“难道歌德的意思是,由于他们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不懂别的语言,荷马不懂希腊文、莎士比亚不懂英文?当然不是!他指的是,荷马和莎士比亚都不知道他们各自运用得如此有力、如此机智的语言到底为何物。”然后,他说歌德说的话同样适用于宗教:“He who knows one [religion], knows none”,并继续解释说,“无数的人具有的信仰是如此强大以致能够撼动山岳,但如果问他们宗教到底是什么,他们便要么哑口无言,要么开始谈论宗教的外部象征而不是宗教的内在性、不是信仰的官能”。(13)Max Mueller,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of Religion: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e of London, Oxford: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2, pp.12,13.也许把缪勒就宗教研究说的这句话直接搬到哲学研究上来会有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似乎也对别的哲学传统一无所知(但这是否与缪勒在解释歌德的名言时所说的圆熟地掌握了自己母语却不懂什么是语言的荷马和莎士比亚类似,与他自己在解释把歌德的这句名言运用到宗教时所说的那些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强烈到能撼动山岳却不懂宗教的信徒类似呢?),有的甚至认为连对自己的哲学传统也没有必要知道。(14)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就认为哲学类似于科学,因此,就好像科学家不需要学科学史,哲学家也不需要学哲学史。但换一种角度看,这种说法也许对哲学比对宗教和语言更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懂自己的母语,而其中很少有人懂母语之外的第二种语言,但他们没有必要去懂什么是语言、因而也没有必要为此而去学另一种语言。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宗教,大多数懂自己的宗教的人也不懂别的宗教,但这些只懂自己宗教的善男信女也不会对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感兴趣、因而也没有必要因此而去了解第二种宗教。但哲学就不同。一般老百姓连一种哲学都不懂、也不需要懂,每个社会上都只有少之又少的哲学研究者懂一种哲学,但人们都会期望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哲学,而且他们也往往声称知道什么是哲学,而如果哲学与语言和宗教类似、因而只懂一种哲学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人,那么确实所有的哲学研究者都不能划地自牢,不越自己所属的哲学传统的雷池一步。(15)这里我们会注意到哲学与语言和宗教有一点不同。只懂一种语言的人都是只懂自己的母语的人,只懂一种宗教的人也大多是只懂自己所属传统的宗教的人。但哲学不一样,很多只懂一种哲学的人所懂的是其他传统的哲学。例如,很多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所懂的唯一一种哲学是中国哲学,而对自己所属传统的哲学即西方哲学则并不懂;同样,很多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所懂的唯一一种哲学是西方哲学,而不懂自己所属传统的哲学即中国哲学(这里我只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为例,事实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哲学传统,如印度传统、阿拉伯传统、非洲传统、日本传统、韩国传统等)。另外,我还在想,歌德和缪勒在讲只知其一便不知其一时都是就不同的文化传统而言的,那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其运用到学科内部呢?例如,我们是否可以说只懂一种伦理学(不管是美德伦理学还是义务伦理学还是目的伦理学还是别的什么伦理学)的人是不懂伦理学的人呢?不知道。
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懂”的标准。如果我们以荷马对希腊文的“懂”的程度和莎士比亚对英文的“懂”的程度为标准,那么大概我们很少有人能声称自己懂了一种哲学。但如果我们以一般人对自己的母语的“懂”的程度或者一般信徒对自己的宗教的“懂”的程度为标准,那么我想还是有不少哲学研究者有资格称自己至少懂一种哲学,而且还可能懂不止一种哲学。关键的是要具有向其他哲学的开放态度或者至少没有想把自己封闭在所属的哲学传统的态度,在此之后的问题才是如何加深这种“懂”的程度。如果歌德和缪勒的名言真的适用于哲学的话,那么加深这种懂的程度的方式就不一定是(如果不是“一定不是”的话)在完全懂了一种哲学以后才试图去懂另一种哲学。因为一方面,懂了另一种哲学以后可以帮助加深自己对原来那种哲学的理解,而另一方面,也许不懂其他一种哲学就不能完全懂自己的那种哲学(而如果这样,上面这句话中的“不一定是”就真的要改为括号中的“一定不是”了)。总体来说,在我看来,懂一种哲学与懂另一种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永无止境的解释学循环:对一种哲学的一定程度的懂可以帮助一个人懂另一种哲学,而对这第二种哲学的一定程度的懂又可以帮助这个人加深对第一种哲学的懂,如此下去,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可以不断加深对这两种哲学的懂的程度、从而也不断加深对哲学本身的懂的程度,而对哲学本身的懂的程度又可以帮助这个人加深对这两种哲学的懂的程度,如此下去,周而复始。但是,无论是就对这两种哲学而言还是对哲学本身而言,也无论是就研究哲学的某个个体而言,还是就哲学共同体(包括其横的即跨文化的层面和纵的即从过去到将来的历史的层面),上面提到的完全的“懂”的程度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我们可以不断地懂得更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