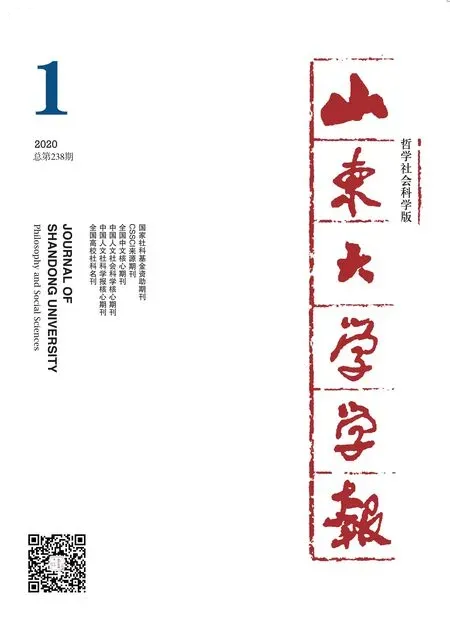帕通对康德伦理学的诠释及其影响
2020-12-30李科政
李科政
康德的伦理的实践哲学对近现代西方伦理的实践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对康德的伦理的实践哲学的理解形成一种重要的哲学经典诠释现象。在众多关于康德伦理的实践哲学诠释中,赫伯特·詹姆斯·帕通(Herbert James Paton;一般简称为H. J. 帕通)无疑是极重要的一位。帕通对康德伦理的实践哲学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定言命令式:康德道德哲学研究》(1946)。(1)两次世界大战以前,英语学界对康德哲学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熟悉。其时,英语学者主要通过诺曼·康浦·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释义》(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918)与他著名的英译版《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Immanuel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929)来了解康德的理论哲学;通过托马斯·金斯米尔·阿伯特的英译版《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与其它伦理学理论著作》(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Other Works on the Theory of Ethics, 1889)与《伦理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Ethics, 1895)来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帕通对康德在英语学界中的传橎与接受贡献很大,他的《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Vernunft,1936)虽然仅仅是对《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的释义,但在篇幅上却远远超过斯密的《释义》。尽管其中不乏对康德的批评,但却更多的是在澄清康德的思想,回应了许多流行的对康德的误解。怀着相同的使命感,帕通在二战的炮火声中创作了《定言命令式》(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 Study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1946)一书,并同期推出了一本题名为《道德法则: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The Moral Law or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1946)的新译本。《定言命令式》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是要澄清当时英语学界对康德的一个普遍误解,即认为他企图从“法则”的空洞表象中演绎出一切特定的义务。诚若如此,康德伦理学“即使不是病态的,也是无足轻重的”(2)H.J.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 Study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London: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p.1946., p.15.。因此,本文第二节主要从特征角度阐明帕通是怎样将康德伦理学诠释为一种“经验形而上学”,且对定言命令式与现实的人类行动之间密切联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本文第三节将介绍与讨论一些由帕通的诠释所引发的争论,它们是当代英语学界中的前沿论题。最后,本文第四节将着重讨论帕通提出的“三公式说”的诠释,指出,虽然帕通的诠释是当代英语康德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标准的诠释范式,但却从根本上曲解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学说。
一、道德行动中的经验性要素


然而,想要充分理解康德伦理学作为一种经验形而上学的特征,就不得不提及帕通对“定言命令式”(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与“定言的诸命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s)的区分。尽管康德本人对这一区分的强调似乎有些不足,但帕通的诠释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有助于把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引上正确的道路。在他看来:1.独一的定言命令式是“一切特定的定言的诸命令式的原则”(10)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34.。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的原则只有一个,但他实际上给了我们多个(帕通以为是五个)公式。当然,康德也解释说,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并且相互“都在自身中自行把另外两个结合起来。”(1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8页(4:436)。2.定言的诸命令式“是对定言命令式的应用”(12)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34.,它们是诸如“你不可说谎”“你不可杀人”这样的具体诫命(commands),也是道德法则对行动的具体要求。帕通说,定言的诸命令式以独一的定言命令式为原则,“并且从中被推导(abgeleitet)出来,但是,这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事实上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演绎的’”(13)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相反,定言的诸命令式(作为义务)不仅必须包含经验性的内容(以明确道德行动者必须做什么),而且它们显然只能来自直接地来自经验。因此,具体的义务并不直接从定言命令式中演绎而来,而是必须通过它的经验性的应用被推导出来,尽管这种应用本身并不是经验性上有条件的。


这就是帕通在《定言命令式》中提出的建构主义诠释,并且在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讲义》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述。而且,这种诠释作为一种道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的特征,还表现在帕通与罗尔斯的一个倾向之中,即用公式Ia(帕通把它说成是一个“感性的程序”(23)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46.)来诠释公式I。当然,这并不是说定言命令式的应用(或者这个理性建构程序)本身以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为条件,否则就会彻底有悖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精神。
二、目的论的法则与人格中的人性
帕通的《定言命令式》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当代英美康德学界,任何一本严肃的伦理学著作都无法绕开它。这不仅是因为帕通对康德伦理学的同情的与合乎情理的诠释,更是因为他的诠释为当代学者留下了一系列有待讨论的话题。当然,本文囿于篇幅的限制,无法逐一对它们做出讨论。因此,本节的讨论将集中在两个重要的话题之上:1.帕通对公式Ia的目的论的诠释;2.帕通对公式II中的“人格中的人性”的诠释。
正如前文所言,帕通把定言命令式解读为行动准则的可普遍性的检测程序,或者道德法则(作为具体的义务)的建构程序。而且,帕通相信,康德更建议我们使用公式Ia(而不是公式I),因为它“更接近直观,并由此更接近情感”(2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8页(4:436)。。这个公式要求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意志使行动的准则成为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2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0页(4:421)。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自然法则”理解为机械论的因果法则,康德给出的例子就会显得有些牵强。例如,“如果生活的痛苦多于快乐就应当自杀”为什么无法通过检测,它似乎符合趋乐避苦的原则。然而,帕通指出,康德在此使用的其实是目的论的自然法则。康德没有明确说出这个概念,或许是因为他对目的论法则的思考直到《判断力批判》才得以成熟,他甚至还为此重写了这本书的导言。(26)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刘作:《康德为什么要重写〈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无论如何,帕通相信:“当康德要求我们把一个待议的准则设想为一个自然法则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设想为一个自然目的论的法则;因为,它是一个行动的准则,而行动自身本质上就是合目的的。”(27)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51.而且,根据这个程序,准则总是通过我们的“愿意”被采纳为法则的。因此,公式Ia的检测标准实际上是:“一个致力于人类本性中的种种意图的一种系统的和谐的意志是否能够一贯地愿意这个特定的准则成为一个人类本性的法则。”(28)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46.
那么,根据这种诠释,“自杀”的准则就由于“凭借以敦促人增益生命为使命的同一种情感来毁灭生命本身”(2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1页(4:422)。,从而有悖于“人类本性中的种种意图的一种系统的和谐”,无法被一贯地愿意。同样,康德的其它例子——虚假承诺、浪费自己的才能与拒绝帮助他人——也必须以目的论的法则为标准而被拒斥。这种诠释有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刘易斯·怀特·贝克与布鲁斯·奥恩,但它也难免会遭遇到一些批评,较近的一次来自国内学者宫睿(30)宫睿:《康德的自然法则公式:以虚假承诺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当然,本文无意(也没有必要)在此参与到争论之中,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宫睿在他的论文中还考察了其它两种流行的诠释,它们是:1.以保罗·迪特李希森、奥特弗雷德·赫费与理查德·加尔文为代表的“逻辑矛盾的诠释”;2.以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奥诺拉·奥尼尔与芭芭拉·赫曼为代表的“实践矛盾的诠释”。(31)宫睿:《康德的自然法则公式:以虚假承诺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宫睿把它们当作对公式Ia的三种不同的诠释来分别加以考察,而且,就它们各有特点并各自包含一些(至少看似)互不相容的要素而言,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逻辑矛盾的诠释”与“实践矛盾的诠释”都可以看作是对“目的论的诠释”的修正与发展,因为它们都不可能单凭机械论的因果法则得到合理的诠释,而是必须诉诸“人类种种意图的和谐一致”。
康德伦理学中另一个广为人知却不易理解的主张是“人是目的”,即他在公式II中所提出的要把我们自己与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自身”来使用的要求,帕通对这个主张提出了一个通俗易懂又不失自洽的诠释。首先,他解释说,“人性”是指“我们具有理性,尤其是具有一个理性的意志这个人类的本质特征。”(32)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65.由于康德把“人格”定义为“理性存在者”(3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9页(4:428)。,这个解释自然是正确的。然后,他继续解释说,“目的自身”是指“纯然由理性自身,而不是服务于偏好的理性给与我们的目的”,它是一种“客观的”与“绝对的”目的,“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34)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68.这些说法与康德的文本是相符的,而且,由于他把“目的”定义为“意志的规定根据”(3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7页(4:427)。,说“实践理性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它也无需同时是欲求能力的一个对象。最后,帕通说,目的自身就是一个善的意志(36)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69.。由于康德确实说过“意志无非就是实践理性”(37)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30页(4:412)。,这个解释至少看上去是正确的。根据这些解释,帕通认为,把人当作目的自身来使用包含三个方面:1.敬重他人的理性意志;2.促进而不是阻碍他人的理性意志;3.他人的理性意志(与我自己的理性意志一样)都是普遍的定言命令式的来源。而且,在他看来,第三个方面是前两个方面的根本理由。(38)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70.

当然,由帕通的诠释所引发的争论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实际上,当代英语学界在康德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论题,几乎都与帕通及其《定言命令式》一书有关。而且,尽管针对帕通的质疑与批评很多,但他的许多观点(包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释)——虽然可能阐述得不够清楚明确,也可能忽略了一些更为细节的问题——都是正确的与富有洞识的。更重要的是,帕通为当代英语学界对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学说的诠释奠定了一个基本范式,尽管在笔者看来这个范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三、“三公式说”的诠释范式及其批判
帕通及其《定言命令式》对英语康德学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他为定言命令式学说提出的“三个相对独立的公式(三公说)”的诠释范式。也就是说,帕通相信,康德在《奠基》中一共提出了三个主要的公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48)当然,正如前文所言,帕通其实从《奠基》中找到了五个公式。但是,他认为公式Ia不过是公式I的一个变体,公式IIIa也不过是公式III的一个变体。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只有三个主要的公式。同时,说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像康德所说的那般“每一个都在自身中自行把另外两个结合起来”。而是说,它们没有“四公式说”所主张的那种从属关系。这种诠释范式与传统的“一个总公式+三个附属公式(四公式说)”的诠释范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在后来的70年中成为了英语康德学界的一个标准诠释。
帕通首先反驳了“四公式说”,而且,在他对“四公式说”的阐述中,并没有公式III的位置,被当作第三个附属公式的是公式IIIa——也就是说,公式I是总公式,三个附属公式是分别是公式Ia、公式II与公式IIIa。在他看来,由于“公式I和公式III乍看起来是如此的相似”,“四公式说”的拥护者们忽视了它,并且主张公式I有一个较高的地位。(49)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30.由此出发,帕通指出,公式I与公式III(以及其它公式)之间并没有一种从属关系,因为“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占据了显著地位的是公式III,而不是公式I”(50)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30.。而且,这几乎就是帕通反驳“四公式说”的唯一论据。然而,这个论据是高度可疑的。因为,尽管《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立法准则”(5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5:31)。——确实与帕通所说的公式III更为相似(52)帕通的公式III是指“意志能够通过其准则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5页(4:434)。然而,即使是“三公式说”后来的支持者们,也鲜有人把它看作公式III。罗尔斯也只是把它看公式III的一个变体。,但真正被康德说成是“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的,其实是“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5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2页(4:431)。而且,康德紧随其后的段落中,明确地把这个理念说成是“原则的目前这个第三公式”。参见第53页(4:432)。。换句话说,帕通的反驳只适用于一种错误的“四公式说”,他所谓的公式III不过是公式I结合了“意志的普遍立法”的理念之后的一个表述。而且,这个表述并没有为公式I增添额外的内容,因为它采纳法则的根据不过是行动者的“愿意”。
然后,帕通提出了他的“三公式说”——定言命令式共有三个主要的公式,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从属关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对独立的。康德在《奠基》中说:“三种表现道德原则的方式在根本上只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5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8页(4:436)。这句话依据(一种正确的)“四公式说”是指:公式I是一个总公式,而公式Ia、公式II与“意志的普遍立法理念”是它的三个变体。然而,依据帕通的“三公式说”,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总公式(55)康德确实明确地把公式I叫作die allgemeine Formel(总公式),并且说它是die allgemeineFormel(严格的方法)。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9页(4:436)。然而,allgemein一词的翻译与理解存在分歧,因为它与“普遍法则(das allgemeineGesetz)”中的“普遍”是同一个词。因此,帕通本人将其译作universal formula,从而只是公式I的一个名称,并没有表达出一种高于其它公式之上的地位。Cf., H. J. Paton, The Moral Law or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46, p.104.苗力田先生似乎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将原文中的“und die allgemeine Formel des kategorischen Imperativs zum Grundelegt”粗略地译作“以定言命令的形式为基础”。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杨云飞老师将其译作“并把定言命令的这条普遍性公式作为基础”,单就这个术语而言,他的理解似乎与帕通一致,尽管他本人并不赞同“三公式说”。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5页。总的来说,如何理解die allgemeineFormel中的allgemein,多少会影响对定言命令式学说的诠释。,“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无非是要强调三个公式的内在同一性,即“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自身中自行把另外两个结合起来”的关系(5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8页(4:436)。。甚至,在他看来,如果非要说哪个公式更具有优越性,那就是公式III,并且更为明显地反映在公式IIIa中。帕通说:“在公式IIIa中,我们达到了如是一个表象,即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作为目的自身联结成服从于一个普遍法则的一个完备体系。这个公式把其它两个公式联合在自身之中。”(57)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185.无论如何,帕通的“三公式说”后来成了英语康德学界的一个标准范式,罗尔斯、科斯嘉德、保罗·盖耶、艾伦·伍德、斯蒂芬·恩斯特龙、萨莉·西季威克、理查德·迪安与其它许多学者(尽管不无批判与扬弃)都是它的支持者。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坚持“四公式说”,例如延斯·蒂默曼(58)Cf., Jens Timmermann,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无论如何,尽管“三公式说”在当代英语康德伦理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康德的许多当代诠释者们也为它做出了诸多修订,但它依然从根本上曲解了定言命令式学说。当然,传统的“四公式说”也确实存在许多缺陷,帕通(以及当代许多学者)对它提出的批评也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一种修订版的“四公式说”完全可以克服这些缺陷。
四、小结
笔者曾在其它论文中提出过一种新的“四公式”说(74)李科政:《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诠释》,《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1期。,根据这种诠释:首先,公式I(普遍法则公式)必须被看作一个总公式与“严格的方法”,它并没有使用一个“自然法则”的类比概念,而是依据一个抽象的“普遍法则”的概念,从而完全可以克服那种叔本华式的质疑。而且,只要我们牢记法则的内容来自于“准则”,法则的规定根据是行动者的“愿意”,它就绝不缺少一个定言的命令式所必需的全部要求。其次,公式Ia(自然法则公式)、公式II(目的自身公式)与意志立法的理念是三个附属性的公式,它们不仅各自包含了一个类比概念——即“自然法则”“目的”“立法”的概念——而且,它们的应用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联合应用。这种“联合应用”的理念对于克服传统“四公式”说的种种缺陷来说至关重要,它要求以“目的”的概念来限制我们对“自然法则”的理解,用“立法”的概念来限制我们对“目的”的理解。最后,这种联合应用的理念集中地体现在公式IIIa(目的王国公式)中,尽管它并不能代替定言命令式的“严格的方法”。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当我们“通过上述三个概念来引导同一个行动”(7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59页(4:437)。,许多流行的质疑与批评将立刻被揭示为错误的与无效的。
当然,尽管帕通对定言命令式学说的“三公式说”是错误的(并且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但他的研究对于康德伦理学在二战以后的英语学界的传播与接受,对于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当代伦理学中的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在康德伦理学的诸多细节问题上,帕通的诠释都表现出了天才般的理解与卓越的洞识。而且,他对定言命令式的建构主义诠释,直接启发了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进而对当代政治哲学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