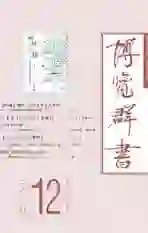“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吗
2020-12-28张佳
张佳
2018年3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简体译本正式上市,而早在出版前夕,上海译文出版社便以预购赠礼、提前试读等多种策略做足了声势,译者林少华更在微博中称小说的版权卖出“天价”。近年来,村上春树已经成为文学界、出版界的奇特景观,他庞大的粉丝群、世界级话题热度,尤其是居高不下的版税,似乎都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格格不入。
村上小说最早进入中国的,是1989年由林少华翻译、漓江出版社发行的《挪威的森林》,而他在大陆流行起来,要在新世纪以后。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89年版的《挪威的森林》遭到大量删节,且未能产生较大反响,直到1999年改版后,才引起轰动效应。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不断扩充品种,屡出新版,为无数年轻人狂热追捧。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推出“外国作家榜单”之后,村上春树的版税连续五年位居前五。而与畅销相伴的,是人们对村上的关注。尽管国内的时髦作家已更新了几茬,但村上春树的热度似乎从未减退。
厌女与恐婚
村上小说的“男权”色彩早已为很多人诟病。虽然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引发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村上春树的作品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型,但他后来的故事也依然没有摆脱前期小说的基本模式:一个独身男子,过着寡淡平庸却又不觉乏味的生活,某日为一件吊诡事由突然干扰,被迫卷入诸般奇幻冒险,最后回归往日。女性角色在其中往往不具备主观能动性(个别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除外),积极地与男主人公发生性关系,却又不得爱情之果,那些与男主产生婚恋关系的女性,要么婚外出轨,要么离奇失踪,要么面对男主的苦苦追求冷若冰霜,要么苦苦追求男主而遭到冷漠。总之,这些男主人公在爱情里往往十分无辜,女性除性行为之外的活动,都好像是对他们生活和内心的干扰。
如果细读文本,我们的指责还可以更加气势汹汹,且有理有据。例如,其中女性角色对待异性的表现过于反常,更像是男性作家的自我臆想。村上对女性身体和衣着的描写,往往从男性视野出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冷酷仙境”里的“我”第一次见到粉衣女郎时,作者写道:
女郎年轻体胖,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脚上是粉红色高跟鞋。套裙手工精良,光鲜流畅。她的脸庞也同样光鲜可人……女郎圓鼓鼓地胖。固然年轻固然漂亮,但她委实胖得可观……每当见到肥胖的女郎,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她喳喳有声地大吃大嚼盘中剩的凉拌水田芥,以及不胜依依地用面包蘸起最后一滴乳脂汤的光景……我不能不决定自己对她应取何种态度,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可能同她睡觉。(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P6-8)
从今天的文化语境来看,这样的描写无疑是把女性特征符号化,成为消费对象,也容易让人认同上野千鹤子对“厌女症”的解读:
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你发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P1)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大可根据作品中具体的描写和情节,在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予以统一的解读,进而将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作者进行一番猛烈抨击。然而这种分析的漏洞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固定、僵死的文本,并没有套出村上自己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在对一些没有反驳能力的文字进行一厢情愿的阐释,从作品本文跨到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作者潜意识,这惊险的一跃,实际上是阐释者主观推动的。
人的意识并非一块白板,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往往离不开阐释者的前理解,我们带着自己的偏见看待艺术和社会,得出各不相同的认知,而这种偏见是由历史、传统构成。事实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阅读作品,不难发现,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对两性关系的处理,都源自其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被普遍投射到作者笔下的一切主人公身上,无有性别之分。这表现在“青春三部曲”的独身信仰,表现在《挪威的森林》中,渡边与“学运”格格不入,更表现在《奇鸟行状录》之后的诸多长篇,人物在抽象之恶面前的孤身奋战。他们似乎都患上了某种“自我封闭症”,无可救药的孤独,莫名而生的惆怅,以及对封闭空间、静止事物的近乎病态的观摩。我们时常会在村上的作品中,发现主人公对着风景发呆,细数眼睛与对象之间的空气分子,感受环境的气味或阳光的温度,哪怕当电话铃响时,他们也像是遇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那样,优哉游哉地数数铃声响了几下。与寻常理解不同,他们对孤独往往采取一种积极态度。他们乐于经营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散步、购物,煮意大利面时总会充满仪式感,哪怕在黑暗中健身,也要放勃拉姆斯的《小交响曲》。他们会礼貌地和人交往,甚至会有亲密的朋友,但却绝对不会干涉彼此的生活,他们会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但是恋情的发生绝不会出现在文本之内,他们对婚姻唯恐避之不及,倘若男女罕见地走到一起,那小说也早就结束在温馨故事的前方了。林少华称:

孤独和无奈在村上这里获得了安置。就是说,这种在一般世人眼里无价值的、负面的、因而需要摈除的东西,在村上笔下成了有价值的、正面的、因而不妨赏玩的对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曰同一性的确认,一种自我保全、自我经营、自我完善,一种孤独自守、自娱、自得、自乐的情怀。(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译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P3)
资本的幽灵
当我们遇到一个不想结婚,甚至只想发生关系,连恋爱都不想谈的男人,往往会指责其没有担当、不负责任,然而村上却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且构建了一个,可以“为所欲为”,不用背负道德包袱的文学世界。与美国“垮掉的一代”相仿,这样的爱情观来自战后的迷惘思潮,这些“没有责任感”的男女,是由社会建构而生,他们“堕落”“荒谬”的言行,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因素。在小说《舞!舞!舞!》中,村上借主人公之口说:
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東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再不存在任何神话。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即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舞!舞!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P74)
资本和权力的寓言在村上小说中俯拾即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奇鸟行状录》《1Q84》,哪怕“爱情小说”《挪威的森林》里也能看见这样的影子。村上并非那种通常被认为只会单纯流露潜意识的作家,他积极、有意地在作品中安插资本元素,对之进行多角度的审视。作家很清楚,资本是造成现代孤独感的罪魁祸首,但与单向度的批判相比,村上所做的价值判断似乎更为暧昧和复杂。小说中既有被“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压抑得喘不上气的五反田,也有在社会缝隙间“苟延残喘”,寻找“异托邦”的小人物,他对人物的刻画并非是希求一个现代日本社会的典型形象,更多的像是在尝试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与存在下去的可能。
可以说,村上的写作无心插柳,描绘出日本独身生活的普遍现象。在他的作品中,婚恋问题已不再是性别偏见、道德伦理等单纯问题,其背后是对日本社会阶层的透视和解读。但与其他社会分析者不同,村上并不认为这样的独身后果是一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相反,他的态度更为乐观、积极,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造成这种乐观、积极的,是他对自我人格的肯定,和对自我内心的保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做出了经典分析。他历时地分析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作为资本贮藏单位存在的事实,并强调“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他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的“一夫一妻制”将真正实现两性的平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3-79)。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把村上春树所赋予笔下人物的婚恋观,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反抗。无论是校园中的渡边彻,还是居住豪宅、收入惊人的免色,抑或年仅15岁,游荡在大地上,那个“叫乌鸦的少年”,他们都从不为财物的多寡或喜或悲,亦无所谓担心身后的遗产流向何方。他们仿佛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毫不通晓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一些与现实隔阂的“局外人”。
在西方文学的传统中,“局外人”的形象可以梳理出一支鲜明又庞大的队伍,他们属于那些金光闪闪的名字:少年维特、哈姆雷特、拜伦式英雄、世纪末恐慌、多余人、地下室人、局外人、荒原狼。他们无不出自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手,具有高超的思考能力而行动力不足,他们是社会的不合时宜者,对体制采取叛逆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试图与现有权力对抗,但又往往为自己的性格困境苦恼。可以说,村上春树是这个队伍的一员,他和他的人物们,不知疲倦地和世俗常理大唱反调,他以自己的语言和故事,构建了一种独居生活的优雅可能,从而消解掉了婚恋生活的合法性,以一己偏见证明了社会常规的偏见,他没有告诉读者,在渡边们漫长的孤独生活中,资本将流向何方,现实问题要如何解决,这样的队伍壮大起来,我们的社会又何去何从。把这些难题加诸村上身上无疑是苛求,作家的职责并非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许知识分子的义务也并非如此。至少在那些文字里,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界,那里的人们拥有不可思议的自由,爱情与尊严共存,资本结构遭到丢弃,这个古老的幽灵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我们不知道它将前往何方,又会附体在谁的身上,至少在这些稀少的浪漫主义里,我们可以抱残守缺,做自己“又酷又野的白日梦”。
海的女儿
几年前,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登上微博热搜,原因是一个年轻妈妈在给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发现它在一味歌颂女性的牺牲,这让她愤怒无比。面对童话那个蹊跷的结尾,我们既可以认为这是女性对男性的牺牲,也可以认为是个人对概念的牺牲,可无论如何,现代理性都无法接受这场死亡的真实性。倘若放在涂尔干的系统里,小人鱼的自杀应当属于“利他主义的自杀”,多发生于“低级社会”。我们来看看命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无论是巫婆,还是人鱼公主们,甚至包括天真的读者,都认为黎明前死掉的会是王子。小人鱼在杀心摇摆的最后关头,听见王子的梦呓,他叫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按照常理,就算没有巫婆的把戏,小人鱼这一刻也应该果断下手,然而违背理性的是,她非但没有如此,反倒厚着脸皮在王子额头吻了一下,然后跳海自杀。结合故事的情感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安徒生的潜台词,小人鱼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存在着明确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未必是她对变成白色泡沫升到天堂的渴望,至少是,小人鱼清楚地知道,自己活下去的唯一条件是王子的死亡,反过来说,自己的死可以换取王子的幸福(因为他爱另一个女人)。这样看来,小人鱼是为爱情而死,对爱情的忠贞变成了一种道德,小人鱼的自杀成就了她烈士的美名,王子在故事结尾的梦呓,使之成为离经叛道之人。或者可以说,安徒生给巫婆安排这场吊诡的把戏,正是要树立这种婚恋道德。
小人鱼非理性行为背后是真正的理性,与之相反,村上人物看似理性的选择背后,却是深刻的非理性,是规律生活背后,存在主义的主观道德,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为此承担责任。他们打破了安徒生构建的伦理,因而为舆论诟病,他们享受孤独的自由,却又不得不为此背负重荷。如果说小人鱼的自杀是利他主义的,那么村上的人物们所进行的抽象自杀,就是涂尔干“利己主义的自杀”。他们困厄于繁复的思索,妄想追求个性和自由,他们为无限的梦想绑架,沉溺于理想主义的痴人说梦,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反叛”只能存在于虚构之中。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根据一系列量化分析,证明了“利己主义自杀”来自于宗教、家庭和社会归属的缺失。换言之,村上的人物和文学史上许许多多的局外人们,之所以负性带气、格格不入,社会的压抑固然不可否认,但其直接原因,或许只是因为缺少宗教、家庭、社会团结的安慰。可以发现,无论是少年维特还是哈姆雷特,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加缪的局外人还是黑塞的荒原狼,他们无一不和渡边一样,是情场上的失败者。这就造成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情感的失利导致了局外的性格,而局外的性格则会加重情感的失利。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题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的书,作者是德国的叔本华,腰封宣传语称其为“治愈系开山鼻祖”。这样的商业炒作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仔细一想,却也同叔本华有几分相符。村上春树让他的人物们选择了孤独,同时似乎也摆脱了庸俗(他们和村上一样,对西方小说、爵士乐、交响乐涉猎颇多)。婚恋和智识在叔本华的思想里表现为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他的论说文具有很强的价值倾向,强烈抨击谈婚论嫁的庸人,对知识和思想报以极高的赞许。然而,和村上的人物一样,当他们耽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构建自己的空中楼阁,追求自己的高雅和深刻时,又几时想过非洲六千多万难民的孤独和庸俗?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