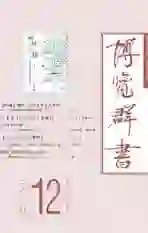《史记》、司马迁与中国共产党
2020-12-28赵璐璐
赵璐璐

《史记》是我国文化史上一部经典著作,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文学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这部巨著所达到的高度。自《史记》成书以来,不仅作为传统史学、文学的经典受到士人的诵读和研究,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遭遇艰难困苦,走向救亡图存之路的时刻,《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展现出来的价值追求,同样为当时国人提供了心灵滋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抗击侵略、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中,不断挖掘和阐释《史记》的文化力量和司马迁的人格风尚,使之转化和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当中,成为培育和构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传统资源,从而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史记》的成书及其文化意义
由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成书于西汉,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130篇,52万余字。司马迁在前代史书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这既是史学编纂方法,也成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五体本身是各自独立的系统,有不同的侧重和针对性,结合起来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构成了《史记》的各层面。这种新的史体主要以人物为中心,得到了后来历代史家的认同,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本模式,因此如宋代郑樵所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成为传统“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详细记录了历代帝王政绩、诸侯勋贵兴亡、重要人物事迹,以及历朝礼乐、天文、兵律、货殖、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无所不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开创了百科全书式的通史研究范畴。虽然《汉书》以下,中国古代正史均为断代史,但是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上沿袭了《史记》,使中国传统史学向着一种广义的文化史的方向发展。
《史记》所记述的一系列人物以及马迁本人的人生经历所展现出来的品德和精神,对中华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塑造,起到了深远的塑造和引领作用。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阐述了孔子作六经的重要意义: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并且认为:
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以接续周公、孔子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以“道之所在”自居,凸显了中国传统士人担当文化继承者的精神。延至后世,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将“道”总结为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而自己要承担起传承道统的重任,所谓“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同样以继承道统序列自居。可以说,《史记》在撰述中对文化本身作用和地位的凸显,以及司马迁表现出的追求接续文化传统的此种精神,对中国古代士大夫乃至近代知识分子理解文化的意义、自觉担当文化使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舍生取义:传统价值的近代转型
《史记》问世以来,自汉至清,对它的研究、注释从未停止,涵盖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近代以来,梁启超、顾颉刚、叶圣陶、郑振铎、范文澜、翦伯赞等文史大家,也都曾撰写过文章,研究《史记》的史学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尤其是日本不断加快侵华步伐,包括《史记》在内的传统文史著作中的价值观引领意义被更多发掘。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由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亲自编写的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张元济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选取了八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八篇故事分别是《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其中六篇都选自《史记》。
张元济认为国难日深,欲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在《中华民族的人格》里所选择的八篇中所包含的十几个人物,几乎都是勇于赴死、舍生取义之人。在《编书的本意》中张元济指出:
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底,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如张元济所说,他所择人物虽然原因不同,但都在人生的生死抉择中舍生取义,慷慨赴死,而张元济希望通过对“义”的阐发,使国人为中华民族大义而奋斗。《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激励更多国人像先民一样,舍生取义,保家卫国。《史记》叙三千年余年历史,司马迁在记述中塑造了不少“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些人都在生死抉择中将坚守的人生价值置于生命之上,这自然也反映了司马迁对生死的价值取向。但是,真正理解司马迁及其在《史记》中展现出来的价值观,并将其升华的,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超越“生”“死”: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毛泽东对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的学习,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司马迁20岁以后听从父亲建议,遍游名山大川,考察史迹,搜集史料,增加了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对司马迁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非常赞赏,因此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作的《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之后,更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而毛泽东最为推崇的是司马迁以及其在《史记》当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创作过程中,受汉武帝天汉年间李陵案牵连下狱。在生死抉择中,司马迁并未选择“赴死”而是接受宫刑,而后继续写作《史记》,这在当时汉代官员受到皇帝叱责或犯罪后大多选择自杀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是很少见的。因此,许多同僚表示对司马迁的不理解,认为他贪生怕死。司马迁在晚年写给朋友任安的信,即著名《报任安书》中,梳理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取舍原则。信中说,寄托他和父亲司马谈理想的史书编著还未完成,此时赴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完成书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并且写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名言,展示出自己的价值观和以此为标准对生死的取舍。这种从价值来看待生死的观念,也普遍贯通于《史记》的叙述中。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在被楚王冤枉的情况下,未选择和父亲兄长一样赴死,而是出逃之后发展实力,进行复仇。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中称赞他:“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认为伍子胥不轻言生死,忍辱负重,得报家仇,是烈丈夫所为。这都是司马迁重视生死所为何事的价值观的体现。
毛泽东非常赞成司马迁这种从价值追求来看待生死的人生观、价值观。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以司马迁的生死观为引,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将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用之所趋异也”以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给予了解释和升华。毛泽东选择为纪念张思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来阐述中國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十分有深意的。
随着长期抗日战争的消耗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的加剧,上世纪40年代初,根据地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在党和毛泽东主席号召下,根据地军民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缓解了根据地财政状况,改善了干群关系,但是当时仍旧有部分同志对大生产运动的认识不足。张思德因烧炭牺牲后,有人认为张思德的牺牲太不值得了,他们认为只有在战场上牺牲才有意义,才是英雄。因此,毛泽东选择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一个层面自然是坚定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坚决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心;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是阐明生死价值的判断在于是否为人民服务,只要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不论是否牺牲于战场,不论为之牺牲的事是看来所谓的“小事”还是“大事”,都是“重于泰山”的。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十天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讲话继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肯定和赞扬了张思德的牺牲和为人民服务精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错误思想,激励了其他如同张思德一样默默为人民利益无私工作的同志,也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司马迁不愿伏法受诛而将生命贡献给更具有意义的《史记》写作事业,到毛泽东为纪念张思德的牺牲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两人都在各自的历史时空超越了当时对生死意义的认识,将生死、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通过对《史记》的阅读和对司马迁人生经历的体悟,真正发掘出司马迁的生死观,读懂了《史记》、理解了司马迁,而凭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古典传统的深厚学养,毛泽东更是在吸收、升华司马迁价值观的基础上,以“为人民服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把它作为生死抉择的准绳、事业奋斗的最终目的以及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宗旨。抚今追昔,在远离了可见的硝烟的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路程上,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意义尤为隽永深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