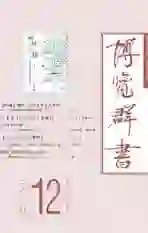爱与永恒的距离有多远
2020-12-28耿弘明
耿弘明
在阅读爱情悲剧时,我们常见到书中人的殉情之举,“殉情”是我们合上书页前所经历的最后一个事件。在漫长的文学史中,维特死了,安娜死了,杜丽娘死了,刘兰芝死了,梁山伯死了,罗密欧死了……他们的死因不尽相同,有的因爱人移情别恋,有的因世俗禁锢自由,也有的因幻觉业已破灭。如同一个爱情迷宫,无论之前他如何行走其中,他的出口却只有死亡一个。
如果再算上所有的通俗小说,这个名单的长度能超过爱情本身的长度,这些殉情者当然没有在另一国度相遇,但他们却在文学的名人堂里永久保留了一个席位,他们的自杀正是这个爱情名人堂的入场券。他们当然没有提前商量,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没有打过交道,但恰恰如此,才构成一种充满诱惑力的让爱情叙事走向终点的方式。
每当阅读这些殉情时刻,我们虽悲不能止,却又乐此不疲,虽感叹逝者如斯,却更坚信了海枯石烂,内心中不自觉地发生了情感辩证法与情感交响乐。这些殉情提示了人间种种美好终将离去,但又沟通了我们关于爱情记忆最纯粹的永恒部分。
在抒情与叙事中,爱情的呈现有所不同。在甜蜜而忧愁的爱情歌谣中,爱可以只是心头荡起的涟漪,没有行为,只有思念,不曾相见,只是暗中想象,当这种思念和想象发酵为镜花水月时,好的情诗便应运而生。晏殊的“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便表达了这种朦胧而遥远的触感。只有通过距离,通过行为的压抑,通过动作消失,才能让心灵的沟通与情话的缠绵去代替步伐,让我走到你的身边,由此,情诗中的爱欲才神妙起来。
爱有关的行为,包括甜蜜而羞涩的表白,孤独而忧愁的等待,精心而惊喜的礼物,激烈而决绝的反抗……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爱情行动矩阵,这些行动的终点,或者是婚姻——一种象征着永不分离的缔约形式,或者是死亡——通过远离尘俗,而获得在另一世界的永生。但这些行为,都没法和而“殉情”比较。其他行为,只是爱情中的小打小闹,殉情才使其上升到神圣地位。与之类似,在友谊、战争和宗教运动中,我们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祖国,舍生取义,为信仰,徒步万里,通过我的牺牲,某物才被放置于圣坛之上。
那么,在殉情事件的叙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才让我们如此眷恋?
爱情等于世界,爱人等于上帝
时至今日,恐怕谁都不得不承认,爱是人类一场伟大的幻觉,我们通过对爱的学习,能够以温柔和审美的视角看待一切事物和整个世界,一个茶杯,一本小书,一叶青草都重新显现,都蕴含无穷。道在一切中,爱也在一切中,这是人类“境由心造”的极致,这幻觉会赋予一切以光芒。
在这一视角看来,当殉情时,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而牺牲,也不是在为爱情而牺牲,而是为整个世界而牺牲,为这种奇妙幻觉而牺牲。这和战争中的牺牲于是达成了一致,因为我要维护的不是具体某人某物,而是它所带给我的整个崭新世界。
在爱情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爱情状态和爱情表达。《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结尾是爱情抒情的极致,维特死前,他这样说道:
我走到窗前,我最亲爱的,透过汹涌飞驰的云层,我看到永恒的天空中有星儿点点!不,你们不会陨落!永恒的主,他在心里撑托着你们,撑托着我。我看见了群星中最最可爱的北斗星。每当我夜里离开你,出了你家大门,北斗星座总是挂在我的头顶。我常常如此沉醉地望着它,常常高举双手把它看作我眼下幸福的标志,当作神圣的记忆的标志!还有——哦,绿蒂,什么都让我想起你!你无时不在我周围!我像个孩子,把你神圣的手所触摸过的各种各样小玩意儿毫不知足地全都抢到了自己手里!
这段话是我们解读文学中的殉情事件的第一把钥匙,它以一种奇妙的修辞,将情人和神灵画上了等号,在存在与虚无间架起了桥梁。或者说,它构建了一个爱的符号集合,这个符号集合里有天空、星斗、上帝、雨滴、露水、花草、河流……世间与光和水有关的事物被纳入其中,而爱人也随之加入。由此,她不只是一具肉身,而是与整个世界等值。或许,因为爱与上帝都在我心中唤起了共同的辽阔的空间,布置上了同样璀璨的星辰,也或许,如维特所说的那样,爱与上帝都是一种冥冥中难以道说的力量,将我托了起来,使我不至沉沦,给我的生存赋予理由。在这个世界的构建中,爱人也获得了神明一样的位置。这是殉情叙事之所以充满表现力的第一个理由——我虽为爱人而死,实为为世界而死,我虽殉情,实为殉道。
流动的爱与静止的爱
在蝇营狗苟的流俗生活里,我们活得清醒而算计,于是有醉生梦死之感,但在书中世界,我们突然触碰到伟大梦幻时,却格外清醒,如获光明。这是一种爱的理念的力量,它设想了一种完美的爱,无算计的爱,乌托邦的爱,超验的爱。
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爱情故事,男女双方虽然情投意合,海誓山盟,但由于贫富悬殊和阶级差异,或由于仇恨关系和家族纠纷,男女之爱受到整个社会的反对,而父母则会作为社会意志的代表而出现,成为戏剧中的“恶龙”,表达对二人婚姻的否决。于是,整个爱情故事成为一个情感版的“勇者斗恶龙”的故事。爱到深处,爱人都变成了诗人,罗密欧可以高喊“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然而,由于横亘其中的家族阻碍,罗密欧也就开始面对了夸父逐日的一般的难度和挑戰。
也就是说,所有的爱情,都是一种爱情观念与另一种爱情观念的冲突和融合。关于爱情,我们持有一种现实化观念,也持有一种理想化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消耗在流俗的情感生活中,为世俗观念左右。于是,超脱世俗的观念就显得尤为可贵,而为理念而死则尤其显得悲壮。几乎在所有的世俗时代,我们都企图为某种古老而神圣的爱情理念正名,在这种理念里,爱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自由,爱是神秘而不容还原的灵域。
具体说来,理想化爱情观念的反面是古典贵族爱情观念,或现代的中产阶级爱情观念。这些观念精于算计,通常来说,它有自己的固定疆域的,它内敛,封闭,且早已寻找到替代方案,以便当利益受损时迅速脱身而出。这里没有过多的戏剧性,平稳而顺利是它的最大期待,它期待爱情沉稳如同日出日落,安静如潺潺流水,它是后花园一样无聊却又为某个阶级所必备的商品。而真诚的,或者说理想化的爱情则是不顾一切的。在其中瞬息万变,我们无法捕捉到哪怕一丝丝固定的空气。从这个角度上说,殉情乃是因为害怕爱人被固定下来,我和我们都再也无法一同过上瞬息万变的生活了。无论你被固定在死亡里,在墓穴中化身为静止的尸体,还是你被固定在世俗婚恋里,在柴米油盐中蜕变为曾经的反面,爱情都腐朽并静止了,我们于是再无法一起投入伟大而无尽的变动之中了。安娜·卡列尼娜便是这样一个殉情者。安娜自杀时,我们不知道她为了什么。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某些流动的东西不复存在了。卡列宁是一种静止之爱,沃伦斯基也变得腐朽不堪,安娜失去了天平的两端,她只得通过呼啸而过的列车永久离去,成为爱情理念的标本,从而获得火车一样的流动性。
也许,爱情终究将以静止结尾,算计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死气沉沉,而理想爱情到了婚姻,也会变得死气沉沉。于是殉情也就成了一种唯一的仪式,爱情终将以死亡为结局,无论分手、婚姻还是坟墓。
这是殉情叙事充满表现力的第二个理由——殉情是一种对爱情流动性的无限追求。
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由于通俗文学的传播效力,有两句箴言人们耳熟能详。其一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像一个安抚创伤的狗皮膏药,可以贴在各种不可名状的情感伤口上,语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二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是源自爱情悲剧的永恒质问,是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中的感叹,经金庸《神雕侠侣》而发扬光大。
“终成眷属”貌似一种甜蜜梦幻,设想再无别离,再无阻碍,从此天长地久,皆大欢喜——我们无法实现的,他者代我们实现了。然而,婚姻制度之下,夫妻虽无别离,但都渴盼别离,虽日日同眠,却同床异梦,此类傀儡夫妻举不胜举,它不是炽热幻象,反而是冰冷现实。事实上,殉情反而是一种更伟大的梦幻,殉情不是对美好事物的毁灭,而是对美好事物的制造,是一种光明绚烂之极的倒错幻象。我们通过殉情叙事所得到的快感,比我们通过团圆叙事得到的还要多。
为何如此?因为,大团圆虽生犹死,殉情虽死犹生。诸多写殉情的作家中,莎士比亚把这种爱情与生死的关系,说得最为到位。“我梦见我的爱人来看见我死了——奇怪的梦,一个死人也会思想!——她吻着我,把生命吐进了我的嘴唇里,于是我复活了,并且成为一个君王。”由此,死亡与复活建立了联系。让我们再重新回到维特那里,在死前,他还曾说道:
绿蒂呀!我居然有幸去为你死,去为你献身!倘若我能为你重新创造生活的安宁与欢乐,那我就愿意勇敢地、高高兴兴地死。可是,唉,世上只有少数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人流血献身,并以自己的死激励他们的朋友百倍地生!
这是我们解读殉情事件的另一把钥匙,它构建了一种死与生之间的辩证法。维特设想,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死,让他人百倍的生。如果说在死亡之前,维特还只是一个满脑子诗情画意的家伙,居住在爱情诗国里,但到了他的死亡,他便走进了爱情悲剧的国度,因为他的死不只是自我抛弃,而带有一种惠及他人的牺牲感觉。维特之死成为了一个社会学事件,很多情感激荡的青少年开始以仿效维特的方式来追求永恒,在他们眼里,爱情是幻觉变成了真实,彼岸降临于此岸,这符合对于激进而盲目的文学青年的看法——这是一群活在精神病与艺术家之间的人。
与维特和罗密欧不同,在东方文学的世界里,殉情中死与生的关系更为具象。“化蝶”便是这样一个美丽的隐喻,梁山伯和祝英台终于相遇,而且获得了另一种生的形式,这是一种消除了死亡的宗教感和焦虑的东方式的飘飘欲仙。在此处,生死倒转,殉情给了我们阅读快感,因为它一方面有净化宣泄的功效,另一方面在潜意识里它成就了我们无限的生。这种“精神幻觉”的极致,就是设想通过死而达成一种永久的陪伴,使得我们想象我们的爱情变得永恒,因而活在我们所未曾体验和认知的另一维度的空间里,虽生前难以相伴,死后却永在一起。借用苏格拉底的句式,我们可以替这些殉情者辩护:你们生前在一起,我们死后在一起,到底誰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这是殉情叙事充满表现力的最后也是最强大的理由,一个可以俘获芸芸众生的理由——通过肉身的死,我们获得了永恒的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