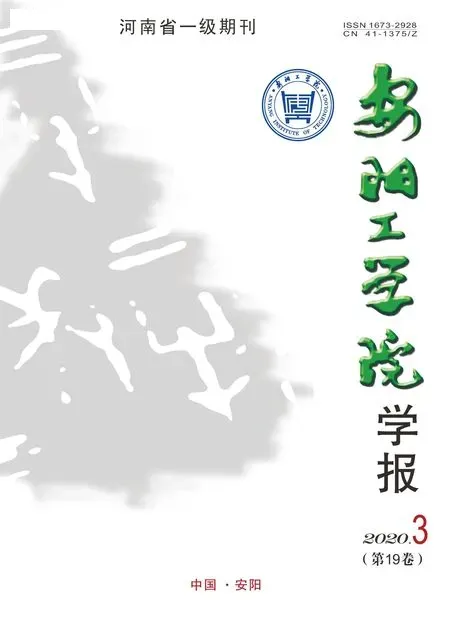陌生化手法在电影《魔童降世之哪吒》中的应用
2020-12-27曹爱娥
曹爱娥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安庆246003)
陌生化理论最初是由20世纪初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认为,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1]。陌生化的技巧将人们熟悉的事物变得不甚熟悉,甚至是惊奇,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延长了审美过程。陌生化手法在电影《魔童降世之哪吒》中的应用,打破了观众对哪吒故事的期待视野,使角色形象更加立体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给观众带来隐性的教育意义。
一、语言的陌生化
电影语言包括天然语言和非天然语言。天然语言包括人物独白、对白以及旁白等形式,而非天然语言指的是影片的叙事情节、拍摄手法、音乐、布景等元素。导演借助电影语言,用其个性化的手法向人们传达社会风貌、意识形态和审美价值等[2]。《魔童降世之哪吒》通过方言、网络用语等陌生化语言环境,增添了电影的趣味性、刺激了观众的听觉神经、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同时,对影片角色起到了立体化的作用,给电影带来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一)天然语言的陌生化
天然语言陌生化技巧的运用,使得影片中角色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体现一定的审美价值、社会风貌和意识形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首先,哪吒个性化的调侃语言体现一定的审美价值。调侃是哪吒最具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一吃七八个,吃完就拉屎。拉屎上茅房,发现没有纸。”和“关在府里无事干,翻墙捣瓦摔瓶罐。来来回回千百遍,小爷也是很疲倦。”等自我调侃的言语表达出哪吒被误解和被排斥之后的孤立无助和迷茫,并释放情绪,拉近了与生活在巨大压力之下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影片发展到后半部分,哪吒的身份重新建构,他幽默的话语里充满了正能量:“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哪吒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并鼓励观众积极面对生活,引导观众深入探讨友情和亲情等,主客体浑然为一。
第二,太乙真人个性化的四川方言体现一定的社会风貌。由于方言所具有的独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引起了很多人在观看时的共鸣和亲切感[3]。“你打我撒”、“不打脸要的不”等方言在带来幽默的同时,也反映出电影中人物的性格。四川人性格中的悠闲自得与影片中太乙真人随遇而安的心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影片中,太乙真人“只喝一口,我就只喝一口”的言语显现出人物身上的鲜明特质。正是因为太乙真人的嗜酒如命,使得各种与他相关的不靠谱事件接连发生,也让那些为了生活而挣扎的观众感同身受,笑泪与共。
第三,申公豹个性化的结巴语言体现一定的意识形态。口吃是一种习惯性的语言缺陷,牵涉到遗传基因、心理压力等多方面的复杂的语言失调症[4]。影片中,申公豹语言功能被弱化,结巴语言缺陷的设定构成了其话语行为的一大特征,从侧面感受到这个人物的卑微和其受消极的心理影响而产生的挣扎的内心世界。人的情绪是由客观事物激发的,当人们产生情绪之后随之产生行为反应[5]。申公豹不仅由于口吃而产生笑话,也限于口吃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随着电影情节的深入发展,观众逐渐窥探人物深藏心底的秘密,申公豹是“成见”的受害者,身上有着人性的弱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揭示了他内心渴望成功、却被出身限制了发展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
(二)非天然语言的陌生化
影片的拍摄手法、布景、配乐等非天然语言也采用了陌生化手法。
镜头是电影最主要的语言,实现电影的叙事和情感表达。从构图到色彩,从配乐到主题,导演一直在挖掘哪吒创新的可能性。导演十分重视镜头前的细节,比如人物服装上的素材、人物手中的物件、镜头角落里的玩具等。电影影像的逼真迫使观众顺利进入内容,并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角色服饰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物的性格,表现了不同的心理状态。申公豹身上的暗色、敖丙身上的素色以及哪吒身上的红色,都建立在人们视觉积累的基础上,引发观众的情绪波动。视觉的体验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心理体验,例如,海底的“黑暗”给人们带来压抑和恐惧感。另外,片中很多场景的配乐能更好地衬托影片情绪。虽然哪吒是中国传统故事人物,故事一般以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为主,但是片中融入了西方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独一无二的配乐。影片中的配乐在对角色的刻画和情感渲染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哪吒生性顽劣冲动,因此在配乐上,有他出现的画面会配以音色明亮的唢呐,以此来凸显他的活泼好动;而敖丙往往配以柔和的箫声以凸显他的温润如玉。片中,龙宫虽然庄严却黑暗,配乐不仅有低音弦乐,还伴有和尚念经。当哪吒得知身世真相后打开乾坤圈变身为魔丸时,配乐声势浩大,表达出哪吒的怒火冲天。这些配乐的陌生化使用使得观众能更好地接受影片想要表达的情感,更好地感同身受。
《魔童降世之哪吒》通过语言陌生化手法的巧妙运用,形象地刻画出电影角色的个性特征和心理变化,使观众沉浸于影片所传达出的意识流之中,与角色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二、题材的陌生化
关于中国神话故事题材的电影大多讲究艺术传承,更多地还原中国历史、记录中国故事,容易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哪吒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在各地成为世代相传且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从最早的记载至今,哪吒形象活跃于各种作品之中,其中包括《哪吒》《封神榜》《西游记》《南游记》《宝莲灯》和《莲花童子哪吒》等。这些作品中对哪吒司空见惯的描述使观众习以为常,容易审美疲劳。《魔童降世之哪吒》在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通过题材陌生化的手法,努力实现文化创新,并探索人性问题,引发思考,使观众自我意识得到提升并进行反思。
电影通过村民规劝哪吒的父母放弃哪吒、哪吒偶然寻得的小玩伴被其家人抱走、哪吒施善救人却被误解以及哪吒主动戴上项圈抑制魔性等故事情节的刻画,来说明哪吒生而为魔、惹是生非的行为是陈塘关居民的标签行为以及申公豹被天尊抛弃之下怀恨在心的行为所致,突出哪吒性本善的人物形象,与魔性形成鲜明对比。在故事的结尾,反面角色敖丙一改初衷,勇于和命运抗争,打破了观众的期待视野。最终,电影的结局既没有完美收尾,也并非以伤感落幕,而是留下悬念。
影片《魔童降世之哪吒》建立在“怀胎三年魔童生,龙族人族相争”的主线之上,更加注重当代受众的接受心理,契合了现代人对于自己命运自己掌握的憧憬,在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中,陌生化的题材给观众带来深层次的思考。
三、形象的陌生化
活跃在《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多部文学作品中的哪吒形象,是一个身穿红肚兜、手戴银镯、踏着风火轮、武装火尖枪的小孩模样。但《魔童降世之哪吒》中的哪吒年轻化的外形注入了凡人真实的人性,打破了观众习以为常的期待视野,驱走了人们的审美疲劳。带着两只乌黑眼圈、不时露出邪魅笑容的生而为魔的形象;两只手永远插在口袋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看上去是名副其实的恶童。作为家里的掌上明珠,却面临着不利于成长的外部环境,反英雄的哪吒具有很多的现代性特征,很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
与观众惯常思维习惯不同的众多陌生化形象也吸引了观众。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本应仙风道骨,却成了一个骑着猪并挺着啤酒肚,读《神仙的自我修养》的胖墩人物,甚至经常喝酒误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传统意义上善良的李夫人,刻画成了乐观开朗、巾帼不让须眉的陌生化形象。本是自私怯懦的李靖成了呵护妻子的好丈夫、耐心有爱的好父亲形象。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却是一个温润如玉、情感丰富的正面形象。
影片以更加平民化的表述方式,会让人物的行为更加贴近生活、真实可靠[6]。《魔童降世之哪吒》中正反人物的客观呈现,也增添了电影角色的真实性效果。申公豹作为最大的反派角色,虽曾和龙族密谋、偷换灵珠,但与太乙真人同等作为元始天尊的徒弟,道行高深,却未见师徒温情,被边缘化,引起观众的同情。影片一改其“善恶不分”的形象,而是从豹子精修炼成神仙,表现出历尽千辛万苦的坚韧性格。电影结局,哪吒没有打死敖丙,他甚至改变了敖丙,使他明白了要靠自己来决定命运。敖丙对于哪吒的救命之恩也一直铭记在心,哪吒和敖丙为一正一反的对立面,都在寻求认同,都视彼此为唯一的朋友,他们两人共同去承受电闪雷鸣的击打,迎合了观众心中协力合作、奋发图强的精神需求。故事发展到最后,既没有彻底的正面人物,也没有彻底的反面人物,打破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四、修辞手法的陌生化
影片运用了对比、隐喻等陌生化手法,给观众带来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使他们产生新的体验和感受,使哪吒故事更具吸引力。
对比手法贯穿整部影片。在电影的开头,通过太乙真人与申公豹的外形对比,增强观众心中的太乙真人矮胖的形象特征,具有讽刺意味。太乙真人的贪酒误事和能力一般与申公豹的教导有方和自我约束都表现了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另外,将正派家庭出生的魔童哪吒与邪恶家庭出生的敖丙进行了对比,身为魔童,哪吒顽劣、孤独和挫败,他人的眼光对哪吒造成了压力。在父亲的影响下,哪吒的自信并积极地影响了敖丙。哪吒从丧到燃,从视觉上能看到哪吒的身形变得高大,从心理上反衬出哪吒的自信和强大。跟哪吒形象产生对比的敖丙,温文尔雅,却身负龙族的希望,在使命中黑化,最终又被哪吒感动而成功洗白。在危险面前,善恶不再对立,两人超越了身份,牺牲自己的肉体去共同对抗天谴。影片也塑造了一些普通的成年村民,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形象,与将善意包藏在丑陋的外表之下的哪吒相对比,他们的形象愈加愚蠢与无知。从一开始,村民就对哪吒充满成见,即便是救人之后,村民们的偏见也不见消失。最后,影片很好地诠释了梦想和现实的对比。哪吒虽为魔童,却渴望有小伙伴,愿意帮助他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没能得到村民的认可,只是引来了更多的猜疑和打压。而敖丙虽为灵珠化身,却身为妖族,家族的使命始终将他隔绝在正常的社会之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哪吒和敖丙的个人梦想都被偏见和出身击得粉碎。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表象的喜剧故事激起了观众的怒吼与叹息,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隐喻在影片中无处不在。隐喻的实质在于通过一类具体的事物或经验来理解另一类抽象的事物或经验[7]。格雷迪(Grady)提出的相关性隐喻主要基于人的日常经验和亲身体验[8],而经验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身体理解,而是基于文化基础,在于认知和理解。以哪吒为隐喻的、一出生就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大多数一辈子都生活在偏见里,难以自拔;以敖丙为隐喻的、被社会群体所远离的人,在真实身份暴露时,往往会面对恐慌和排斥。剧中的龙王撕下自身最硬的一片龙鳞,为敖丙做了一件万龙甲,希望年轻一辈能完美地执行满足家族利益的人生规划,如同哪吒的父亲愿意替儿子遭天谴一样,都极好地隐喻到中国家庭所代表的权威、对孩子的深爱和限制。不过,哪吒拒绝了父亲的保护,敖丙放下了龙王灌输给他的执念,他们都做了自由的抉择,并遵从自己的价值观,极力地表达出当今社会年轻人的呐喊。观众从自身的角度认知世界、理解影片,这种隐喻为影片带来了丰富的意蕴。
影片还使用了大量物象来承载其讽喻使命,众多情绪都通过碎片化镜头陈述,让观众跟着人物开始一段定位自我角色的情感体验。碎片之后的留白给观众留下了很多悬念,也让观众去思考,进行多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