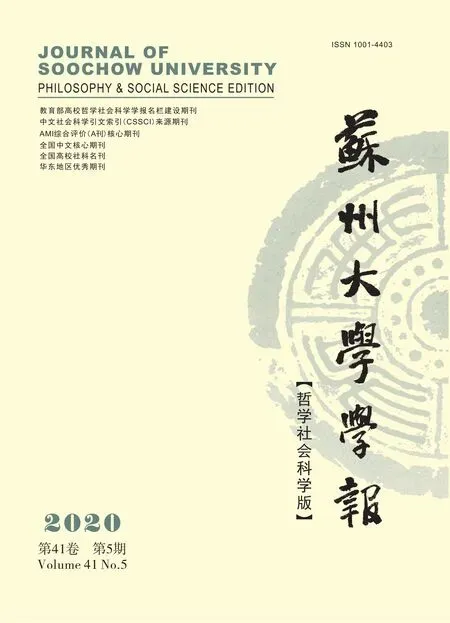中兴高流:论韩元吉的人生与诗歌艺术
2020-12-27曾维刚
曾维刚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开封(今河南开封)人,为北宋名臣韩维玄孙,得中原文献之传,又师承二程传人尹焞、张九成等学者,在南宋孝宗朝累官礼部尚书,享誉于时,为南宋中兴时期的道学高流,也是中兴诗坛的重要作家。宋人黄升称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1]216。宋元之际方回称其诗“自成一家”[2]643,“亦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相伯仲”[3]829。然而宋元以后,其文集就备受冷落。《四库全书总目》论“元吉本文献世家。据其跋尹焞手迹,自称门人,则距程子仅再传。又与朱子最善,尝举以自代,其状今载集中。故其学问渊源,颇为醇正。其他以诗文倡和者,如叶梦得、张浚、曾几、曾丰、陈岩肖、龚颐正、章甫、陈亮、陆游、赵蕃诸人,皆当代胜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师承。其婿吕祖谦,为世名儒。其子名淲字仲止者,亦清苦自持,以诗名于宋季……集本七十卷,又自编其词为《焦尾集》一卷。《文献通考》并著录。岁久散佚。今从《永乐大典》所载, 总裒为诗七卷、词一卷、文十四卷。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而湮没不传,殆不可解”。[4]1383韩元吉文集散佚,今其《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世纪以来韩元吉研究长期沉寂,改革开放后始有学者对其进行专文探讨,而研究集中于其生平与词作,有关其诗歌的研究还有待深入。(1)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德辉《试论南宋词人韩元吉及其词》(《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童向飞《韩元吉仕历系年考辨——兼补〈宋史翼·韩元吉列传〉》(《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邱鸣皋《陆游、吕祖谦、韩元吉关系考述》(《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韩酉山《韩元吉若干事迹补正》(《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南涧词漫
(2)谈》(《江淮论坛》2002年第1期)、《韩南涧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胡可先《韩元吉年谱》(载王水照主编《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68页),傅璇琮、辛更儒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南宋前期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探讨了韩元吉的生平和词作。韩立平《一代冠冕:韩元吉的诗歌成就及其影响》(《学术探索》2010年第3期)探讨了韩元吉的诗风、渊源与影响。因此本文拟深入特定历史语境,从韩元吉追求内圣外王的忧患情怀与诗歌表现、以清为美的人生旨趣与诗歌意境、平和与狂放之间的艺术张力等方面,就其人生与诗歌艺术展开讨论,拓展我们对南宋中兴时期文化精神与诗坛风貌的认识。
一、内圣外王:忧患情怀与诗歌表现
宋室南渡前后道学南传,进一步发展。自二程弟子尹焞和“从杨时学”[5]11577的张九成传至韩元吉的一脉,为其中重要一支。(3)关于南宋中兴诗人的师承问题,详可参看曾维刚、王兆鹏《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宋代道学是在与释、道二教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南渡之际不少道学家耽于释氏,学理未纯。韩元吉之师张九成“早与学佛者游,故其议论多偏”[5]11579。韩元吉则批评释氏之弊,《答朱元晦书》称“圣人妙处在合,故一以贯之。释氏之弊在分”[6]251,《敦复斋记》称“圣人之学,自治其一心,则推而至于治天下,本末先后,初无二致……自异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说犹以一身为可外,况于所谓天下国家,孰知可离则非道”[6]284。他揭示儒家之学自治一心,推而至于治天下,体用合一;而释氏虽亦治心,但以空虚寂灭为宗,割裂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一贯性,故而有体无用。强调内圣外王结合,成为韩元吉思想学术的显著特色。
南宋中兴时期一些道学家不仅在学术层面深入沉潜,还将学术进一步政治化,向君主推行其学。他们以道自任,在朝廷努力致君行道,在地方勤政泽民,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元吉即为代表,注重外王践履,讲求实务。孝宗乾道九年(1173)他权尚书吏部侍郎,有《癸巳五月进故事》论:
自周衰,道学不传,士之号为儒者,徒能诵说陈言,而不达当世之务,故听其语若可行,责其实则罔效。且复自处于优闲畏懦之地,以苟幸世之富贵,所以动见厌弃,儒者之名,殆为此辈污之……今中国之所以未操胜算者,正在人材太弱,士大夫虚名有余,而实用不足,其弊皆由儒者,无以自振……人材众多,要皆有用,而养其资力,俾无忘进之心,责其实效,俾无避事之意,庶几虚名之患消,将有真儒为时而出。[6]196-197
韩元吉向孝宗进讲故事,论士人名实风节与国家兴衰问题,结合历史批判徒诵陈言而不达世务的腐儒,针对现实揭示国家人材之弱,推崇“养其资力”“责其实效”的“真儒”。也因此,韩元吉一向忧怀国事。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宋金鼎立之际,他始终不忘外患,主张积极备对,以为国家长久之计。其《上张同知书》指出“今日之患,外患也……日夜以图之,假以数年,吾之事力既振,何往而不利”[6]240。淳熙三年(1176)他有《丙申五月进故事》称赞唐太宗对突厥的策略说“帝虽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敌”[6]199,提醒孝宗励精图治,勿忘金人之祸。又《论淮甸札子》说“中原未得,则淮甸吾之藩篱也。淮甸不固,大江岂可备御”[6]176。宋金之间长期划淮而治,江淮一带地理位置重要,但时人徒知恃江为险,恃和苟安,放松边防,韩元吉深感忧虑,建议朝廷加强江淮防御。他时时以金人败盟为戒,《上枢府札子》建议“明示远近,俾军民士大夫晓然预知国事,然后同心协力,共济事机”[6]182。他还有《十月末乞备御白札子》《上执政论千秋涧起夫札子》《与执政论千秋涧事宜札子》等,都是具体探讨边防措施。
鉴于国土分裂的现实,南宋中兴士人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规恢意概。韩元吉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即贯穿在其诗歌创作之中。如《送许侍郎知宣州》说“中原未复敌未灭,政成请公须著鞭”[6]33,《玩鞭亭》说“边兵已重朝士轻,中原有路何由行。柙中虎兕不可制,江左夷吾浪得名”[6]30,表现忧患中原未复的情怀。又《至日建德道中》写“佳节又看当警急,劳生底用较悲欢。腐儒忧国成千虑,强敌窥人讵一端。梦想淮南风雪里,可无消息报平安”[6]58-59,抒写对强敌窥伺的忧虑,企盼淮南平安。“腐儒忧国成千虑”,堪称其忧患情怀的自我写照。他与陆游、范成大、辛弃疾等爱国之士均为挚友,交往唱和,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如隆兴元年(1163)南宋筹措北伐,时陆游在枢密院编修官任,力主恢复,不久通判镇江,离开朝廷,但其爱国襟怀得到范成大、韩元吉等友人赞同,范成大《送陆务观编修监镇江郡归会稽待阙》称“高兴余飞动,孤忠有照临”[10]110,韩元吉《送陆务观得倅镇江还越》叹其“许国丹心惜未酬”[6]70。再如《寄赵德庄以过去生中作弟兄为韵七首》其四:“筑城始议戍,寓兵复言攻。二年大江南,兵戈在目中。忧时亦千虑,惟子与我同。诣阙请长缨,终军本儿童。”[6]18赵德庄乃赵彦端,字德庄,韩元吉《直宝文阁赵公墓志铭》称“与德庄游盖三十年,在朝廷同曹,在外同事,犹兄弟”[6]426-427。可见二人交情甚笃,同以边疆戎事为虑。他还常在与家族亲人的相处中流露忧国情怀。如《清旷亭送子云得有字》:“欢期苦难逢,离别乃易久。天涯老兄弟,况复亲白首……天威动江淮,狂寇行授首。努力幸驰驱,腰看印如斗。”[6]20诗言“子云”,乃其从兄,此诗感叹兄弟游宦天涯,聚少离多,表达对江淮边事的忧虑,希望兄弟为国驰驱。《次韵子云送儿女至昭亭见寄》也说“壮士志中原,边尘暗幽并。拟蹑冒顿居,端谋渭南耕”[6]22。《淲赴贵池簿》说“四十才生子,今年亦效官。国恩期共报,世路觉尤难”[6]42。诗题中“淲”,乃其子韩淲,字仲止,号涧泉,有诗名。韩元吉送别儿子之际,亦以国事相期,与友人陆游名作《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11]4542的忧国情怀异曲同工。
孝宗隆兴元年(1163),南宋为了收复中原,发动大规模北伐,却败于符离,宋金签订“隆兴和议”。随着宋金再次和议,南宋朝中主和势力又抬头,主张和议的汤思退复相位,一向意在恢复中原的韩元吉及诸多士人受到排斥。隆兴二年(1164)他在度支员外郎任上,被主和派人物王之望所弹劾,被诬“其向为宣谕司参议官,招权妄作”,因此被放罢。[12]3975至孝宗乾道初年,他复被召,除直秘阁、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历直敷文阁、权知建宁府、权尚书吏部侍郎等职。“隆兴和议”后,宋金双方重新维持和平,长达四十余年,其间使节交聘不断。南宋中兴时期一些使北士人心怀国家民族的大义和恢复中原的情怀,慷慨成行,并将使北经历、见识与感情形诸诗文,涌现出不少使北诗人。(4)关于南宋中兴时期使北诗人群体的活动与创作,详可参看曾维刚《南宋中兴时期士风新变与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韩元吉就是其中重要一员。乾道八年(1172)冬他试礼部尚书使金,贺金主生辰[5]654,撰《朔行日记》,今已佚。其《书〈朔行日记〉后》称“异时使者率畏风埃,避嫌疑,紧闭车内,一语不敢接,岂古之所谓觇国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觇敌者,日夜不敢忘。虽驻车乞浆,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之从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归因为圣主(孝宗)言……愿思所以图之……上深以为然”[6]322。他利用使金机会,冒险侦探金国形势,力主孝宗伺机而图。今其《南涧甲乙稿》中还存使金诗七首。如《望灵寿致拜祖茔》说“白马冈前眼渐开,黄龙府外首空回。殷懃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6]97,写故国景象和中原遗民,表达黍离之悲。《狼山》诗说“天外奇峰认九华,路人指点是狼牙。他年刻石题车马,会遣山前属汉家”[6]97,表现恢复中原的理想和慷慨驱驰的壮怀。南宋中兴时期,韩元吉等使金士人有机会深入中原,并用诗歌表现亲身见闻,其诗作比陆游等未到北方的诗人书写故国和遗民的作品更有真实感和写实性(5)胡传志先生尝探讨陆游诗中失真的北方。参见胡传志《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159页。,具有独特认识意义与文学价值。
韩元吉不仅心系外患,亦忧患民瘼。其《浦城县刻漏记》称“夫为政之道,贵不欺于民”[6]279,《答朱元晦书》称“江左苦旱,早晚稻皆损,岁事殊可虑”[6]251,均可见其民生关怀。这在其诗歌中也有表现。如《送谅弟丞邵阳》写“文史差无负,田园慨未余。常存爱民意,门户有权舆”[6]42,《永丰行》写“却忆吴中初夏时,畚锸去决田湖围。鸡惊上篱犬上屋,水至不得携妻儿。无田赴水均一死,善政养民那得尔”[6]29,或抒发爱民之意,或描写百姓苦难,表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与社会关怀。
二、以清为美:人生旨趣与诗歌意境
道学的宗旨是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之道,以建构理想的人间秩序,其发生发展的现实基础,乃在针对唐末五代以来世道支离和人心之危。宋承五代之乱,以文治国,儒风渐盛,士人以复纲常、正伦理为己任,道学应运而生。北宋后期,权奸当道,迫害善类,及靖康之难和宋室南渡,国土沦丧,士风不竞,生灵涂炭,世道人心再度混乱。因而南宋道学家比之北宋承担着更大拯救世道人心、重建内圣外王之道的责任。陈傅良《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一》称“圣贤事业,以人心为本。靖康之祸,诸夏陆沉而人不耻,君父播迁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岳之气分裂而人不惧,是尚为有人心乎?”[13]卷一九可谓南宋中兴时期一代道学家的呼声。因此,他们进一步加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深入开拓内圣之途,注重存心养性与持敬功夫,努力以身行道。(6)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即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一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3页)。值得注意的是,道学内圣的践履虽是一种精神活动,但它须从现实生活层面开始,要唤起道心,就须弃绝世俗物欲和人欲之私。朱熹《甲寅拟上封事》即指出“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8]627-628。在道学的践履上,韩元吉堪为表率。其《送李平叔序》论“今之士,咸耻于任州县之职……趋竞之风日益长”[6]269-270,批判士人趋慕荣华的奔竞之风。《上辛中丞书》自述“某也,北方之鄙人,守家世之训,不忍自同于流俗”[6]229。孝宗淳熙二年(1175)他知建宁府,作《比园艮泉铭》说“凤阳鹤之麓,有岏而伏。堂之麓,圃之腹,斯瀵而沃。束于渟,润于谷,可用而足。清如官,美如俗,是为建人之福”[6]355,赞扬艮泉清冽,寄托清廉惠民的美政理想。以“清”为美,成为其自觉的人生追求与仕宦生涯的政治哲学。
韩元吉久在地方和朝廷任职,耻于奔竞,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其《送元修归广东》诗称“十年门户苦凋零,屈指天涯几弟兄。羁旅可堪怀世事,典型谁与振家声。惊心朔岸秋风急,极目南溟瘴雾横。好过贪泉未应酌,少年游宦要冰清”[6]73。诗题言“元修”,乃其兄弟韩元修。韩元吉以“游宦要冰清”与兄弟相互砥砺,表明人生旨趣。就其诗歌作品来看,也创造出了一种幽远清和的美学意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我相信,我们将再次领导市场主导产品的大潮流,傲视群雄,开拓未来。”路德政表示,未来,先科将以更高的起点、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质量、更高的速度的治企方针,坚定不移地走质量之路、走品牌之路、走长远之路。迅速在全国倾情打造农资行业的金牌名店,争先在行业中,树立优质农资品牌的大旗,取信于客户,树信于同行,致信于农业,忠信于农民。
其一,以清为美的诗学追求。韩元吉《答金元鼎喜雨》诗说“几日云阴合又开,良田秋近起黄埃。一觞未致灵祠祷,半夜先欣好雨来。政拙自知容我懒,诗清要是得君催。不妨咳唾皆珠玉,渐喜新凉入酒杯”[6]75,明确以“诗清”来说明其创作的追求与特色,以能达此境而欣慰喜悦。他还以清为标准来评论他人诗作。如《次韵吴明可与史致道会饮牛渚》诗说“烟外笛声谁送晚,水边花影自迎春。风流三百年无此,况有清诗句法新”[6]80,描写了清丽的江边景致,称赞友人句法生新的“清诗”。《送沈千里教授邵阳》诗亦说“縠纹江畔得君诗,俊逸清新字字奇”[6]72,同样是称赞友人诗作的俊逸清新。可见,以清为美不仅是韩元吉的人生理想,亦成为其诗歌创作自觉追求的审美境界。
其二,清美之景的书写表现。源于以清为美的人生与文学趣尚,韩元吉注意在日常生活中 捕捉清幽之景,展开诗歌描写。如《寒岩分韵得 水字》:
青山如幽人,不肯住城市。客从城市来,一见消吝鄙。平时与周旋,况复非俗士。我初见南山,秀色纷可喜。谓言官尘埃,洗涤端在此。经时未一至,引望若千里。昨朝得休暇,佳兴难自已。秋原丽新晴,景物为清美。独游已不恶,更约二三子。初从涧壑危,稍入岩石倚。白云随杖藜,苍烟生屐齿。主翁亦好事,结茅修竹底。庭空百无有,屈曲但流水。客来了不问,花草自红紫。[6]11
韩元吉此诗写其政事闲暇之际与友人游山的经历,描绘出秋原新晴、景物清美之境,以涧壑、岩石、白云、苍烟、修竹、空庭、流水、花草等意象,表现清幽绝尘的山中世界及其脱俗情怀。又如《避暑灵泉分韵得水字》写“空山百无有,翠阜映清泚。幽泉俯伴月,盎盎真石髓。坐久得清凉,山缾还屡耻。一杯乐所遇,静胜有真理”[6]9,描绘群壑空寂、翠峰清泚、幽泉伴月、宁静清凉的山中景致,表现闲淡萧散的襟怀。《朱元晦清湍亭》写“青山足佳游,远睇欲无路。稍寻绝涧入,始辨云间树。泉声若招客,倚杖得夷步。惊湍泻乱石,激激有清趣。风微鸟哢幽,日彻鱼影聚。居然鱼鸟乐,正欠幽人住。野僧岂忘机,作亭以兹故。因君赋新诗,我亦梦其处”[6]14。朱元晦,乃其道学好友朱熹。孝宗淳熙中韩元吉有《举朱熹自代状》称“方今奔竞成俗,熹之廉退,所宜奖擢。臣实不如,举以自代”[6]169,朝廷召朱熹为秘书省校书郎,朱熹却自甘退藏。虽然韩元吉与朱熹在仕途出处进退问题上取向有所不同,但二人仍然相互欣赏。韩元吉尝有《送朱元晦》诗说“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来各千虑。君来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真谏疏。诋诃百事推圣学,请复国仇施一怒”[6]33,对朱熹表示期许。朱熹尝得韩元吉文集,一夜与门人陈文蔚同看,“读至五更,尽卷。曰:‘一生做诗,只有许多?’”[14]55可见其喜读韩元吉诗文,不忍释卷。韩元吉《朱元晦清湍亭》诗,即是集中描写朱熹清湍亭清幽脱俗的景致,并直抒胸臆,表达对其“清趣”的向往之情。
韩元吉有时携家人一道寻幽探胜。如《寒食前三日携家至丁山》:
春事已过半,豫怀风雨忧。苦无亲朋乐,自携儿女游。丁山峙城南,老稚载一舟。狭径登诘曲,轩窗居上头。遐观接去鸟,俯视临清流。溪花正烂漫,堤柳绿且柔。杳霭烟云间,前瞻帝王州。田野乱棋布,山川莽相缪。病妻不能饮,取酒自劝酬。鲜妆谁家妇,造席为我讴。风光亦可醉,景物似见留。惜无百金资,买此林壑幽。岁月实易得,里闾尚沈浮。归来暮钟响,苹风动沧洲。[6]8
此诗写其与家人春游丁山,描绘山中溪花烂漫、堤柳绿柔、烟云杳霭、林壑俱幽的境界,表现仰观飞鸟、俯视清流的游赏之乐,及至归来,已是暮钟回响的黄昏。全诗造景清绝,情韵自然,余味不尽。此外,如《梵隆大师乞诗隆能琴阮为鼓数行》写“空斋了无事,鸣琴对清泚。游鱼应朱弦,万籁入流徵”[6]7;《清明后一日同诸友湖上值雨》写“弱柳自随烟际绿,幽花还傍雨边明。嫩蒲碧水人家好,密竹疏松野寺清”[6]55;《种竹》写“香苞吹尽翠成围,墙角萧萧一径微,已喜轩窗无俗韵,更怜风月有清辉”[6]108;《灵隐冷泉》写“山涵水影两空明,水到山前百尺清。洞里臞仙应一笑,抱琴时为写寒声”[6]108,均以“清”为核心意象,描写自然清美之景,表现对清幽之趣的追求。
其三,清和心境的陶冶修养。周裕锴先生论,无论是“言志”还是“写意”,宋诗都进一步由物质世界退回到心灵世界。[15]86南宋中兴时期道学家关于心性义理的深入阐释与沉潜体验,成为其诗学生成的学理基础。韩元吉即常以诗表现其对清虚平和心境的陶养,建构了一个明心存性的文学世界。如《列岫亭用范伯升韵》写“自我来南溪,池塘几春草。结茅依云端,爱此山四抱。奇峰七十二,罗列景逾好。岂殊谢公窗,澄江更萦绕。孤城千家邑,一目可尽了。植葵思夏深,种菊待秋杪。物华静中见,至理得深造”[6]15,诗以池塘、春草、茅庐、白云、奇峰、澄江、孤城、夏葵、秋菊等意象,描绘出远离世俗、幽静清美的艺术世界,表现其静观物华、深造至理的心灵感受。《夜坐闻窗下水声》说“青灯又暗吹窗雨,流水长闻入夜声。玩世久忘荣辱累,定交谙尽死生情。翛然隐几焚香坐,不独心清境亦清”[6]52,写他在雨夜焚香独坐、静闻水声、荣辱皆忘、心境俱清的体验。《春日书事五首》其二说“晓猿夜鹤寂无生,春至山禽百种鸣。步绕新泉聊洗耳,由来心与地俱清”[6]91,刻画春夜山中猿鹤的寂静、禽鸟的幽鸣,表现其清和的心境。《秋怀十首》其十写“闭户跏趺意已清,炉香烧尽一灯明。空庭叶落知多少,一任西风百种声”[6]93,《夜宿玉虚宫小轩正对步虚峰道士云天宝三年有庆云见且山呼万岁始诏建黄帝祠封为仙都山敕书今亡》其一写“槛外风高霜月明,步虚山里步虚声。罢琴刻烛初长夜,又得人间一梦清”[6]99,均是此类作品。朱熹尝论韩元吉诗文“做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16]3316,即揭示出其诗文清雅冲和的特色。
三、平和与狂放:诗歌艺术的审美张力
韩元吉作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道学家,道学内圣沉潜的修养深厚,其诗表现出平和清美的特色。同时他又有一个显著的与众不同之处,即他是一位非常注重外王践履的道学家,主张励精图治,恢复中原,具有浩然壮气和坚忍志气。淳熙十年(1183)他作《建宁府开元禅寺戒坛记》说“天下之事,不患于人之不能为,而患在人之不肯为。使士大夫遇事而有坚忍不拔之志,则亦何功之不可成,何业之不可广”[6]302,可见其矢志于天下之事、士大夫之事的进取精神。其《孔明论》说“君子之事君也,必将告其君以所欲为者,而济其君之所未为者。君以为然耶,吾将起而就之。其不然耶,吾将引而去之”[6]345,可见其以身行道、与道进退的决心。乾道初年友人陆游有《念奴娇》词赠韩元吉,他次韵唱和说“离别经年,相逢犹健,底恨光阴速。壮怀浑在,浩然起舞相属”[6]121,以浩然壮怀相砥砺。淳熙十一年(1184)他六十七岁寿辰,友人辛弃疾以《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词相赠,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沈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17]119,以建功立业的“真儒”相期许,这与前述韩元吉《癸巳五月进故事》向孝宗推崇务实进取的“真儒”之论若合符契,词情的慷慨豪放也与韩元吉一致。可以说,平和与狂放这两种反差极大的气质,在韩元吉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韩元吉兼具平和与狂放的气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使其艺术风格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张力。前述朱熹称韩元吉诗文“做著尽和平”,揭示其诗文清雅平和的特色。韩元吉则有《溪山堂次韵四首》其一说“堂前松竹挺千军,堂外青山万马群。横策时来按文阵,要须笔力起风云”[6]99,描写溪山堂前松竹宛如千军万马,而自己仿佛是点检军马的将军,随即笔锋一转,讨论诗文,标举“笔力起风云”的创作,可见其豪壮狂放之姿及其推重“笔力”的文学观念。他还有《次韵陈子象十月惠牡丹》称陈子象“诗就只应开顷刻,先生笔力起千钧”[6]81。《答陈亮书》称陈亮“学力既博,笔力健甚”[6]253。《高祖宫师文编序》称其高祖诗文“笔力雄健”[6]261。可见论文推重雄健笔力,乃是韩元吉的一贯观念。如果说朱熹指出了其诗清雅平和的一面,那么他自己则道出了其诗雄健狂放的另一面,这种反差和张力,成为其诗富有个性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韩元吉的诗歌创作,时见清雅平和之气,时见雄健狂放之致,跳荡不拘,姿态横生。如《同叶梦锡赵德庄游牛首山》:“不辞扶病触春寒,及此新晴一日闲。云外经年见双阙,马头乘兴数前山。清泉细酌巉岩上,佛窟同探紫翠间。我亦无心话禅悦,衔花百鸟自飞还。”[6]58诗写他与友人游牛首山的自在心态,情怀平和澹雅。而《浙江观潮》绝句写“江翻海涌势难平,鳌掷鹏鶱自不停。端为君王洗兵马,参旗井钺万雷霆”[6]92,则笔力雄健,情怀豪壮。《过松江寄务观五首》其一说“四海习凿齿,云间陆士龙。酒狂须一石,文好自三冬”[6]40,《秋日杂咏六首》其一说“客少无尘语,官闲省吏文。醉眠千幛日,危坐一窗云”[6]37,均写酒酣醉眠的狂放之态。《送温伯玉二首》其一说“壮年豪气在,途路莫兴嗟”[6]41,《送张仲良二首》其二说“气概青云上,声华碧海边……功名第迟速,强饭且加鞭”[6]42,亦以“壮年豪气”“气概青云”与友人共勉。
韩元吉有道学家的平和谨严,也有狷狂之士的放达情怀。如其《少稷劝饮每作色明远忽拂袖去戏呈》写“坐中幸免沐猴舞,且复周旋非贵人。人言劝饮无恶意,君胡作恶使客起。少陵亦遭田父肘,况我忘形友君子。从今勿劝亦勿辞,我欲眠时君自归”[6]31。他认为与友人纵饮,当兴尽而罢,诗中“我欲眠时君自归”,化用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18]1074,表现放达不羁之情。《七夕与孟婿约汤朝美率徐行中游鹤山》说“起携东床友,况得下榻翁。青蒲有杰客,放怀适相从。一招云中仙,共呼潭底龙……高谈剧霏屑,壮气吹长虹。可无樽酒绿,遂使老颊红。醉语或不省,啸歌亦舂容。归欤兴难尽,月明照风松”[6]9,写其与婿孟植等人清游鹤山之际的高谈剧论和醉语啸歌,情怀放纵。《雪中以独钓寒江雪分韵得独字》说“相过二三子,共喜醅瓮熟。狂歌且暂醉,夜半还秉烛”[6]9,也是写与友人狂歌醉游的情景。他还有《远游十首》写游仙理想,其一说“我行蓬莱巅,俛首见月窟。谁言沧海深,涉之不濡袜。颓波惊鱼龙,起舞相荡潏。众真为一笑,黄雾生绛阙。独乘风中天,蹙踏波上月”[6]5,其七说“昆仑九万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兹惟众仙门。翩然两白鹤,道我前飞翻。问津牵牛星,濯足洪河源。九关幸方辟,乘之游紫垣”[6]6。作为一位道学家,韩元吉的放纵玄想可谓卓尔不群,独具一格。
值得注意的是,韩元吉诗歌的意象、情怀往往还能在一首作品中极尽放纵和跳宕。如《隆兴甲申岁闰月游焦山》写“荒村日晴雪犹积,系缆焦公山下石。江翻断崖石破碎,瘗鹤千年有遗迹。瘦藤百级跻上方,浮玉南北江中央。樯竿如林出烟浦,酒船远与帆低昂。老鸱盘风舞江面,杀气淮南望中见。神龙只合水底眠,为洗乾坤起雷电。观音岩前竹十寻,大士不死知此心。醉归更唤殷七七,剩种好花开鹤林”[6]36。此诗作于孝宗隆兴二年(1164),诗歌首先进入绵长悠远的历史时空,进而描绘焦山一带长江烟波浩淼,帆影如林。但接下来,作者并未继续描写如画的景致,而是笔锋陡转,以“老鸱”“杀气”“神龙”“乾坤”“雷电”等意象,营构出一片阴森肃杀的境界,抒发其一洗乾坤的浩怀壮气。全诗节奏由缓而促,情绪由低而高,历史与现实交织,正如浩瀚平静的江面风云突起,笔力劲健,读来令人猛然警醒。又如《溪山堂次韵》写“幽人谁与娱,作堂面溪湾。堂中有山色,朝暮来云间。正作杜老狂,颇异韩子奸。超然物外景,便觉非人寰。登临得遐瞩,似破天壤悭。诗成隐几笑,溪山亦开颜。缭绕明镜中,参差峨髻鬟。苦无俗客语,但闻鸟间关。出门曳藜杖,赖有此往还。虚名两蜗角,自斗触与蛮。时平众贤聚,君胡得长闲。会从车骑出,勒石燕然山。正恐万里途,高辕不容攀”[6]16。诗写其与友人的清游幽赏,抒发超然物外之情,而结尾二联诗意突变,以勒石燕然、平戎杀敌的功业自警,笔力陡壮,展现出诗人情感的跳宕和张力。
在南宋中兴诗坛上,与韩元吉及其子韩淲均关系密切的诗人赵蕃有《别韩尚书》诗说“南山之作险以壮,南溪之作闲以放。流风莫和况当家,南涧先生堪颉颃”[19]85。赵蕃以“险以壮”和“闲以放”称许韩元吉诗,揭示其诗兼容平和与狂放而极富张力的艺术特色,可谓切中肯綮之论。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韩元吉平和与狂放之间的个性气质与艺术张力,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基本是以清和之气为根本,而兼具豪壮狂放之致。与其身份属性相契,平和源自其作为一位道学高流心性沉潜、内圣追求的根底,而狂放则源于其作为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努力践行外王事业的士大夫的人生际遇与情志感发。其以清和之美为特征的人生追求、政治哲学与诗歌表现,前文已有阐述,下面进一步检讨其豪壮狂放气质形成的特定因素。大体来看,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其推崇浩然之气的内在个性陶养、习得。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0]56,以气言人的道德与精神修养。韩元吉继承了这种儒家传统的修养观念。他除了师承二程传人尹焞、张九成外,还师承南渡之际在政事文学上均富影响的刘一止、曾几、叶梦得等人。朱熹称“爰自国家南渡以来,乃有丞相魏国张忠献公(浚)倡明大义,以断国论,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安国)诵说遗经,以开圣学”[8]3660,揭示宋室南渡后张浚、胡安国等人拯救时势,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建构之功。一时以学见长的杨时、谢良佐、张九成、尹焞、胡宪、胡宏等人,以政事文学见长的王庭珪、胡铨、虞允文、汪应辰、曾几、叶梦得等人,均属于反对求和苟安、主张修学励政以图国家中兴的阵营。陆游《跋曾文清公奏议稿》即称“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曾几)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21]2279。韩元吉毕生尊崇师道,其政治上的取向与活动、学术上的习得与造诣,促使他形成一种刚大正直、豪壮放逸的精神气象。绍兴中叶梦得帅闽中,筑万象亭,他撰《万象亭赋》论“公以文章、道学伯天下,推其绪余,见于政事……某适以旧契之末,获拜公于庭……吾先生浩然之气,六合为隘。蟠万象于胸中,耿星辰而不寐。遇至美而一发,借佳名以自快”[6]1-3。他以“浩然之气,六合为隘”称许师友叶梦得,实亦是夫子自道,与之共勉。前揭其《念奴娇》词称“壮怀浑在,浩然起舞相属”,即可见其浩然豪放之气,这是其诗歌艺术生成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是外在时势激发,感愤于国家仇耻。如前述韩元吉《隆兴甲申岁闰月游焦山》诗以“老鸱盘风舞江面,杀气淮南望中见。神龙只合水底眠,为洗乾坤起雷电”等激壮之语,写展望江淮、缅怀中原的汹涌情思。此诗作于隆兴二年(1164),时南宋中兴之君孝宗即位不久,此前三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在长江采石大败,逃至扬州后被部下射杀,金人北还。次年宋高宗禅位于孝宗,孝宗登基翌年,就以张浚为枢密使出师伐金,惜败于符离,不得不与金人签订和议。不过孝宗君臣并未忘国家仇耻,未失恢复之志,在隆兴、乾道、淳熙年间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南宋一时士风振作,出现中兴局面,对诗坛创作产生深刻影响。(7)关于孝宗之治与南宋中兴诗坛主体精神的再造及诗学新变等问题,详可参看曾维刚《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南宋走向中兴之际的特定时势与精神激发,成为韩元吉及其诗歌豪放气质形成的时代因素。特别是在宋朝遭遇金人南侵或南宋筹措北伐等重大军政事件、时局跌宕起伏之际,韩元吉的此类创作尤其突出,上引《隆兴甲申岁闰月游焦山》诗即为代表。又如前述《过松江寄务观五首》,作于孝宗乾道之初,与陆游唱和,写其酒酣醉眠的狂放之态,也很典型。孝宗登基后建元隆兴,仅二年即改元乾道,宋人释《易》,谓乾为天、为阳、为刚(8)关于天地、乾坤、阴阳之说与社会性别及政治文化秩序的关系,详可参看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第一章“阴阳学说与宋儒理想的性别秩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5页。,可见南宋中兴君臣以阳刚之道重整乾坤的理想和精神气象。这种观念、气象也体现在他们的文艺思想与创作之中,可谓是一种群体的自觉。(9)如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有《苏轼赠太师制》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二四六,第23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乾道中王十朋撰《蔡端明文集序》论“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王十朋《宋王忠文公文集》卷一二《蔡端明文集序》,《宋集珍本丛刊》第44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3页)。周必大《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认为“文章以学为车,以气为驭”“挟之以刚大之气,行之乎忠信之途”“如是者积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笔端矣”(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二〇,《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78页)。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进《上殿札子》称“臣伏读御制《苏轼赞》……陛下之言,典谟也。轼死且九十年,学士大夫徒知尊诵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于气高天下者。今陛下独表而出之,岂惟轼死且不朽,所以遗学者顾不厚哉”(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02页)。从中,可以看出南宋中兴诗坛普遍崇尚浩然刚大之气的文学观念。陆游得韩元吉《过松江寄务观五首》后,有《次韵无咎别后见寄》赞其诗“龙蛇飞动无由见,坐愧文园属思迟”[11]81,正道出韩元吉诗歌的豪放之风。韩元吉之子韩淲有《涧泉日记》记载“陆游,字务观,先公友也。善歌诗,亦为时所忌。先公与之唱和,旧有《京口小诗集》,务观作序。今已作南宫舍人,居越上,自号‘放翁’”[22]17,又载韩元吉“称王荆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画,陆务观诗歌”[22]33。韩元吉于诗歌最推崇自号“放翁”的友人陆游,而陆游与其以诗文相互激赏,同声相求,这也是韩元吉诗歌豪壮狂放一面形成的特定因素。
四、结语
本文将韩元吉置于宋室南渡至南宋中兴时期的特定历史语境,结合其兼具道学家与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属性,探讨其诗歌艺术的生成与特征。从文学文化学角度来看,在南宋中兴时代,道学已发展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术思想,道学家的队伍空前壮大,如韩元吉、林光朝、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薛季宣、陈傅良、孙应时、彭龟年、陈藻等,在学术、政治与文学领域均有重要地位。道学的理想是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之道,道学家在学宦生涯及日常生活中以道自任,这种精神追求也表现在诗歌创作之中,他们以道为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以道论诗的文学观念、体道说理的普遍主题、古淡清美的艺术世界,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10)关于南宋中兴时期的道学诗人群体及其特征,详可参看曾维刚《论南宋中兴时期道学发展与道学诗人群体的形成》,《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4期。韩元吉作为南宋中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道学诗人,追求内圣外王的忧患情怀与诗歌表现、以清为美的人生旨趣与诗歌意境、平和与狂放之间的艺术张力,构成其人生与诗歌艺术的突出特征。可以看出,他不仅具有道学诗人的群体性特征,也极具个性,宋人黄升称其为“一代冠冕”,方回称其诗“自成一家”,伯仲尤、杨、范、陆等中兴四大家,洵为有见。其人生与诗歌艺术,对南宋中兴时期的道学发展及中兴诗坛多元艺术风貌的建构,均有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