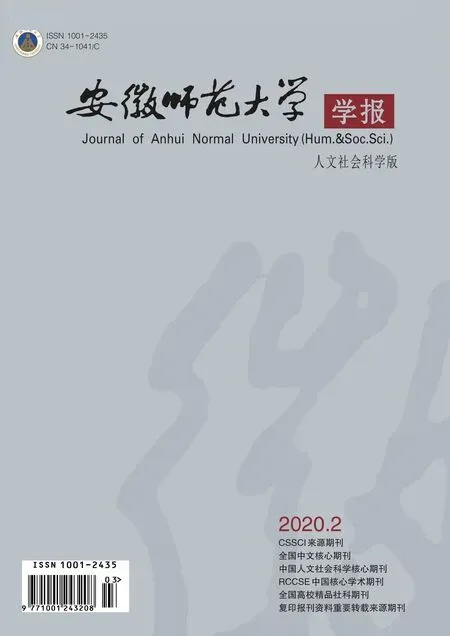文学公共领域与主体性
——基于《天路历程》的文本分析*
2020-12-27胡振明
胡振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100029)
约翰·班扬(1628—1688)是“漫长的18世纪”①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J.C.D.Clark)在《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姜德福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中指出,英国历史在宗教改革和当代之间存在一个拥有自身统一性和完整性的漫长时期,即“漫长的18世纪”,英国在此期间确立了成功的国家体制。克拉克将17世纪60年代视为“漫长的18世纪”之始。英国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他本是乡间一位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补锅匠(据说一生所读之书不超过五本),凭着时刻相伴的英文钦定本《圣经》成就了文学传奇。据后世学者考证,“班扬的作品是英语世界中阅读量最大的书籍之一,仅次于钦定本《圣经》与莎士比亚作品。”[1]2他的代表作《天路历程》(1678)发行量仅居《圣经》之后,并被誉为“当前英国文学中最热销的非通俗作品之一”。[2]37这位自学成才的清教徒作家将基督教的高深教义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生活化的场景、栩栩如生的描述呈现于同时代与后世读者面前。在他的笔下,寓言成为抽象概念的转化载体,作品借助得当的隐喻,营造了强烈的现实感染力,让读者感同身受。班扬不同于那些喜用夸张、奇幻想象转述教义的同时代作家,他的创作是一个世俗化表述过程,聚焦笔下人物主体性塑造,对小说叙事的兴起做出了贡献,因而也被视为“英国小说奠基人之一,是笛福的先驱”。[3]172
《天路历程》是一部宗教寓言作品,讲述的是一位基督徒为寻求个人救赎而走上征程,最终抵达天国的故事。相同题材与内容的作品在当时的英国可谓汗牛充栋,多数作品要么是以审判者口吻居高临下地对读者说教,要么是用蒙上帝恩宠的欢欣之语向读者论证神意的伟大。然而,班扬将读者视为自己的平等对话者,作者本人、作品中的人物、读者在同一认知层面去理解个人救赎过程中那些借助各类隐喻呈现的世事艰险与挑战。由此,班扬成为这样的一位作家,“其创建的复杂隐喻使其与现代性对话”。[4]3班扬与现代性对话的基础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基督徒”虽然是一类人群的统称,但他有独立的思考,是在救赎的历程中发现自我的力量,唤起自我意识的觉醒。整部作品是对“基督徒”人物个体特殊性的确认,以及对其个性的肯定,这也正是启蒙现代性得以建构的过程。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的标准基础,首先是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5]124也就是说,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构成的个人自由成为现代性的前提。这也意味着,个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现代性的成果。事实上,班扬之所以创作《天路历程》,也正是因其本人反抗英国国教会专制,不惜身陷囹圄,以此彰显个人对上帝理解与尊崇之故。该作本身就是“承受新兴现代性压力的寓言诗学日益深化之危机”[6]13的实例。
《天路历程》中的个人救赎是在俗世生活各种诱惑或逼迫中砥砺而成,“名利场”是集大成者,是“现代性的重要意象”。[4]2班扬笔下的名利场是数千年前堕落天使领袖引诱耶稣犯罪而特意设立的集市,也是追随耶稣重走永生路的基督徒必须经受的考验。尽管班扬本人对名利场予以严厉的抨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名利场正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是社会公共性的缩影。诚如利奥波德·丹姆罗什所言,“《天路历程》将个人考验置于超越自我的语境之中,并从教义的深层悖论中汲取生命力。”[7]155个人在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的多重关系中参悟基督教义之于现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现实生活中的悖论恰是个人经受考验,从而得以救赎的开始;同时,救赎在历经包括名利场在内的诸多社会考验后终得完成。《天路历程》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读者在这部以《圣经》经文与典故为依托的文本中见证了“基督徒”的信仰成长。喜爱这部作品的广大读者纷纷阐述个人观点,并在基于文学批评的公众舆论中建构了“文学公共领域”。①笔者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予以进一步阐述,相关成果请参阅胡振明《言说与论争:文学公共领域的流变》(载《国外文学》2013年第4期)、《作品、市场、社会:文学公共领域形成初探》(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本论文有意揭示书中的“基督徒”如何在“救赎”“名利场”两个命题中确立个人主体性,以及如是过程之于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的意义。
一、文学公共领域与主体性
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中写道,“在18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信心与现实主义结伴而行,而不是乌托邦空想的表征……启蒙运动既是一场人类心灵革命的产物和表达,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8]5他认为,18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这一事实唤醒了新的生命意识。当人类可以驾驭自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时,宗教思想以及乌托邦空想不再掣肘人类探求自我认知,现实生活成为个人认知的基础与目标。引领社会思潮的启蒙先贤们把现实生活的认知规律概括为基于批判性才智的理性,并视之为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他们提出涉及社会、伦理、政治、美学的种种纲领构想,其目的就是赋予人类思考与认知层面的更大自由。基于如是认识,彼得·盖伊将18世纪称为人类“重振勇气”的世纪,“这是一个神秘主义没落的世纪,一个对生活越来越怀有希望,对人力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世纪,一个执着探索和批判的世纪,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世纪,一个世俗主义日益抬头、冒险之风日益盛行的世纪。”[8]7
事实上,启蒙思想巨擘康德早在18世纪就总结了同时代思想运动的本质,即“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9]22在他看来,不成熟状态就是人类缺乏决心和勇气,需要依赖他人的指导,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世界。康德认为,长期的思想禁锢让人们怯于独立思考,习惯了由外在权威替自己感知世界。启蒙意图谋变,而这改变所需要的只是自由,即“在一切事务上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康德思想的核心在于,他用“理性”这个新认知消解旧有思想的权威性,并指出,“自由”是确保“理性”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基础。康德言及的理性基于个体心智的认知规律,其出发点是自我思考;理性的运用自由实际上是促使个人思考成为民众习惯,成为现代文明的标识,而这也正是个人主体性确立的过程。黑格尔进一步论述了个人主体性之于社会的意义,“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10]197黑格尔认为,立足于历史现实发展的市民社会强化了个人主体性,社会成为民众彼此之间的私利战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私人利益与社会制度的调和。黑格尔的观点说明,个人主体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因,进而颠覆了始自中世纪的宗教与社会的建构关系。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延续了黑格尔的相关思考,并对后者的思想进行了这样的概括:现代公共领域源于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在国家与社会的逐渐分化中产生的社会交往领域。主体性包括这样四种内涵: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以及唯心主义哲学自身。[11]20哈贝马斯认为,“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11]21在他看来,启蒙运动旨在建构基于主体性原则的现代社会交往体系,他在论证18世纪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就已明确指出,“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12]122
哈贝马斯把个人主体性视为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内驱力之一。他勾勒出文学阅读、文学批评、文学公共领域三者之间互为建构的轮廓:“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刊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12]55换言之,18世纪文学作品聚焦个人经验的书写,通过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人物、时间、地点的独特叙事吸引广大读者,并逐步培育了具有个人主义意识的读者群体。由读者构成的公众依托语言交往行为的实践话语,共同成就了公众舆论,并借助文学讨论与批评建构了文学公共领域,进而影响社会意识。追本溯源,个人经验书写是个人主体性的文本阐述,也是公共领域的创建之基,更是思想自由的具化。黑格尔曾这样论及公共领域:“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公共领域。”[10]331-332究其本质,个人主体性是对专制思想与意识的反制。在18世纪时代潮流推动下,昭示个人思想与言论方面的自由成为启蒙运动的目标,基于这种主观自由的公共领域改变了社会发展历程,塑造了现代思想。
启蒙先贤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个人自由的社会道德意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13]12在他看来,与生俱来的自由决定了人何以为人。同时,个人对自由的舍弃无疑是对人性与社会的背叛,从而也失去了个人道德性。卢梭以此明示个人自由具有社会道德价值,因为个人主体性奠定了社会公共性之基,并且是在其中实现价值。哈贝马斯进而指出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一种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在多大程度上为自由的公共领域提供强大的市民社会基础,立场鲜明的公众在日益激烈的争论中的权威就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加强”。[14]471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植根于个人主体性的自由是立意为社会公共性的权威之依托。源自专制的权威催生反抗,基于自由的权威固本发展。同时,谋求主体性的自由成就社会发展的价值,意在公共性的自由铺就社会进程的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是个人主体性的基因标记,也是社会公共性的指向航标。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由国家公民组成的民族,其自我理解和自我政治意识,只能通过公共交往的媒介形成”。[15]45这说明以自由为导向的现代文明依托于个人与社会政治意识两个层面的公共交往。在18世纪,由文学批评构成的公众舆论成为公共交往的事实媒介。
明了这一知识谱系有助于《天路历程》的重新解读。班扬笃信基督教,这常使国内外学界将其视为秉承传统的信徒。他们笔下的文本解读意在论证班扬如何谨从上帝话语,尊崇上帝权威,但普遍没有意识到班扬是借助虚构人物的个人自由选择以此强调个人主体性之于信仰的重要性。在班扬看来,没有主体性的自由只能成就顺从暴君的愚民,他们无法领受上帝的恩泽实现个人“救赎”,更不能效法基督,在“名利场”泥潭中践行社会公义。在基督教传统认知中,上帝的权威与世人的自由往往对立。选择个人自由往往意味着背离上帝的意愿,无视上帝的权威,《圣经》中已有不少喻证。然而,班扬意在校正这一认知,试图论证植根于自由的主体性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是效法基督的基础,并且在成就社会公共性的过程中彰显上帝的权威。可以说,班扬超越了自己宗教认知的局限,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这也就得以说明《天路历程》为何出版后倍受读者好评,因为它将个人信仰与自由选择、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融于文本之中。换言之,这部作品聚焦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救赎之路,尽管书中无所不在的上帝眷顾随处可见,但文中的基督徒是在彰显个人主体性的历程中抵达天国,并因此具有社会示范价值。迈克尔·麦基恩指出,班扬有意在基督教因信称义的信仰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选择之间寻求最佳融合:“《天路历程》旨在教导我们如何有信心,而不是如何过我们的生活。然而,要点就是,在班扬的救世神学中,这两者不能分离,因为如果没有训诫与神圣化带来的心理与社会确认,那么信仰是不可能的,也的确是空洞无物的。”[16]446班扬并不认同仅凭信心而无个人判断的信仰。在书中,各种曲解《圣经》经文,意图阻挠基督徒天国之旅的人与事比比皆是。基督徒需要在个人自由前提下,本着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与经文的理解,做出个人决断。班扬将本着个人主体性原则的选择视为信仰之基,这就使其信仰在认知论层面具备不确定性,在贝丝·林奇看来,“高度主体化的教义使得经文真理成为个人阐释事宜”。[17]76班扬分别在“救赎”“名利场”这两个命题中借助笔下人物的个人选择使基督教义“高度主体化”,由此证明个人主体性之于基督教的意义。班扬为此所做的创作尝试获得极大成功,引发了民众热议与关注,由此而生的公众舆论催生了一系列文本批评,这成为后世学人解读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的实例。也可以说,通过文学公共领域与主体性在《天路历程》文本中的互为建构分析,我们可以重现班扬朴实个人叙事背后的社会意图,而这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
二、《天路历程》中的“救赎”命题
在班扬生活的时代,“《圣经》不仅被视为宗教事务的核心权威,而且也被认作艺术、科学、政治、经济思想的绝对核心。”[18]20-21基督教认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文本,为信徒遵循永生之道指明了方向,其权威性不言而喻。然而,解读这部权威文本,理解上帝的意图需要处于非权威地位的普通信徒个人独自完成。个人是依靠自己的信仰,通过个体选择称义得救。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教会专职人员讲解《圣经》经文,肩负引领信众之责,由此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基督徒个人信仰生活中面临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如何看待权威,即在权威的《圣经》文本与权威他者的经文解读面前,信徒是愿意自建认知体系,成就个体权威,还是愿意让他者的权威解读替代个人的思考。对于这个问题,班扬选择了前者,并因此受到权威他者(英国国教会)的迫害,入狱达十二年之久。维拉·卡姆登指出,班扬“与权威的(内在及外在)关系都是矛盾的,这折射出因其所在社会的权威危机而起的动荡与不确定性”。[19]3班扬的选择看似是个体孤例,但事实上是英国内战前后社会权威重构过程中的必然。旧有权威的坍塌不仅催生了内战,而且也冲击了基督教信仰。有学者指出,班扬的绝望因宗教而起。[20]127-128权威他者的现实表现,以及对异见者的迫害让班扬深感失望,由此而生的不信任及随后的反抗说明,他有意基于个人主体性建立自己的权威体系,实现自我救赎,求得永生。
班扬笔下的基督徒是这样出场的,“穿着破烂的衣服,站在那儿,背朝着他的家,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负着重担”。[21]1基督徒打开手中的书,在个人阅读中意识到自己未来的万劫不复,因此痛哭不已,茫然无措。他回家后向妻儿吐露心事,却不被理解,在独自面临苦境之时得到传道者的指点,最终一个人选择生命之路。由此可见,基督徒是基于个人的认知,本着个人的渴望与信念选择一条不为他人理解,无人陪伴的信仰之路。如是个人选择在班扬所处的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英国王室权威在内战期间受到资产阶级议会的挑战,英国国教会的权威又被支持议会的清教徒消解与质疑。在这政治理念与宗教思想极具变革,权威重构的时代,个人阐述自己的宗教身份成为可能,这也是新的社会需求与压力使然。这样一来,“个人经验成为自主授权的原则,宗教身份突然成为个人自己的权责”。[22]30班扬本着这个认识,让笔下的基督徒不受俗世他者影响,选择自我建构宗教身份的天路。
基督徒独自上路后没多久,就遇上了一位叫“世故”的人。世故对一路负重前行的基督徒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劝你赶快自己把重担卸下。这担子一天不卸下,你的内心就一天不得安宁;神赐给你的各种福分和好处你也不可能享受到。”[21]9世故这番话切中基督徒内心所痛,同时基督徒对神赐福分的向往使其解除防备,愿意听从世故的高见。世故继而劝道:“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求解脱呢?没看见这里面危机四伏吗?更何况,只要你有耐心听我讲下去,我可以指点你如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能免去你在那条道上会遇到的种种危险。真的,回头是岸。此外,我还要说一点,你不仅不会遇到那些危险,还能尽情享受安全、友谊和满足。”[21]10基督徒的负担是因追求永生信仰,效法基督穿过窄门而起,是个人谋求救赎时必须经历的磨难,最终使个人灵性得以成长。世故貌似好意的劝说,即卸下重担,实则让基督徒放弃天路之旅,重回灭亡城的罪恶生活。世故的这些话对信仰尚不坚定的基督徒颇有蛊惑力,因为人性的弱点会让很多人为了逃避一时的苦而放弃一世的福。基督徒同样听信世故所言,误入歧途,幸得传道者相救,终回正道。在班扬看来,个人救赎的道路上类似世故的人不会少见,听信谗言迷失正道的事情比比皆是。班扬在书中写下“他自己的经验”,[23]137将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实际选择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基督徒与其说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虚构人物,不如说是直面生命各个方面挑战的自我。[7]162
基督徒重新上路后,遇上了恶魔亚玻伦。他趾高气扬地对基督徒这样说道:“这么说你是我底下的一个臣民喽,那一整片国土都是我的,我是那里的王,那里的神。你怎么背叛了你的王?”[21]42恶魔是既有“权威”的邪恶代表,曾为其臣民的基督徒本该恭顺效力,如今却因着个人选择决意另寻他路,重构权威。恶魔的这番质问在班扬所处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英国内战与革命昭示着“分裂的现代自我之诞生”,[19]6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时期,社会地位与道德权威是统一的,彼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身居社会顶层,且是“君权神授”的鼓吹者,将自己等同于上帝在人间的权威化身。然而,查理一世是被由清教徒为主体的议会军打败,且被送上了断头台。班扬本人曾是议会军中的一员,与拥护国王的保皇派有过战场上的厮杀。因此,班扬的亲身经历使其借笔下基督徒之口说出了自己的个人信仰选择与权威重构意图:“我是答应过你,可那是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如今,我是站在王的旌旗下,我相信他会宽恕我,也会赦免我屈从你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好了,你这行为败坏的亚玻伦,我对你实话实说吧,我喜爱侍奉他,拿他的工价,喜爱他的仆人、他的权柄、他的同在、他的国度,这一切都比你的要强。你休想再劝我了,我是他的仆人,我要跟从的是他。”[21]43此时的基督徒面对曾经的主人,恶魔之王,拒绝承认其权威,相反,明确自己对未曾觐见的救主之王的满心渴慕,并愿意选择接受这位新王的权威。在权势逼迫之前,基督徒坚持自己的选择。班扬此处的虚构叙事与宗教寓意融合在一起,将个人选择与属灵争夺外化为一场与恶魔的殊死搏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恶魔的斗争成为顺从救主的证明,班扬借此完美地概括了清教徒重要的双重性,即“外在的好斗性与内在的顺从性”。[7]161
班扬在论述“救赎”这一命题时向读者呈现了一位基督徒的个人成长历程。书中的基督徒从内心对永生的渴慕,立志得救,到听信谗言,误入歧途,再到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勇斗恶魔,这源自现实生活的属灵争战让读者有高度的认同感。争战的对象有时候是化身各种蛊惑人心的人与事的魔鬼,更多的时候是因信仰不坚定误信误判的自己。某种程度上来说,班扬的《天路历程》是普通基督徒的自传叙事,书中天国之路上的各种经历都是每一位基督徒基于个人认知所做的现实选择之投射,是众信徒“自我的文本表现”,[22]13这也就是为何这部作品深受各类读者欢迎的原因。然而,班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个人救赎在旧有权威坍塌,新兴权威重构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其社会公共性,书中的个人得救如何成为他人的效仿榜样,如何成为社会标杆示范。这也就不难看到,“班扬在自己艰辛痛苦,自觉自愿的救赎探求中预示了现代性的困境。”[19]4旧有权威的压制,催生了基于个人主体性原则的现代性;同时,现代性需要在重构权威的过程中与社会公共性保持良性互动,这一微妙的过程也正是现代性的困境。《天路历程》书中的个人救赎选择充斥着对权威危机、身份建构的思考,这是班扬本人代表的现代文化中的社会重构的探讨,在“名利场”这个命题中尤为明显。
三、《天路历程》中的“名利场”命题
班扬在《天路历程》中写下很多脍炙人口,经久流传的文学片段,“名利场”是其中的经典。书中的“名利场”是虚华集市,“那里售出和购进的每一样货物也都是虚空”,[21]70各种世俗牵挂和享乐在此兜售,各类欺诈罪恶不绝于耳,这既是邪恶世界的缩影,又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班扬借路过此地的基督徒、忠信两人之口对这集市的批判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用克里斯多弗·希尔的话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方面”[24]225予以抨击。班扬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与君权势力决斗的时期,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及相伴相生的资本主义是漫长的18世纪进步力量的代表。然而,班扬清楚地意识到,推翻君权专制的新兴力量并没有改变人性,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创造一个符合神意的世界或理想社会。因此,名利场的虚华买卖依旧,人心依旧,罪恶依旧,这也就是为什么名利场可以历经数千年而不倒的原因。破解名利场之困取决于个人的内在选择。可以说,个人选择是在名利场中得到考验,而考验的终极目标就是坚定自己的属灵生活,以此改造社会罪恶。科斯蒂·米尔恩指出,“名利场”一词是在“象征主义与特性之间游弋的混合物,是以各组成部分彼此影响的方式得到强化的张力。”[4]22也就是说,名利场既可以象征世间邪恶,又可以明指个人特定选择,其价值与意义是在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彼此建构的互动之中得以体现。书中的基督徒是在名利场中更进一步坚定了个人选择与信仰,同时还唤醒集市居民“盼望”的良知,后者追随同行。据盼望介绍,“集市上还有好多人迟早也要跟着来的”。[21]78一个充满希望的属灵社会正在逐步成型。
基督徒与忠信抵达集市时,惊动了所有人,因为他们穿的衣服与集市上任何一个买卖人的衣服都不一样;他们的言谈是天国的语言,与集市世俗世界的人不一样;他们对所有的商品都无动于衷,用手指塞耳,两眼望天,拒绝诱惑。[21]72这座集市的风物实为隐喻,此处深受欢迎的商品正是属灵争战的对象。班扬擅于把精神思考具化,用詹姆士·特纳的话说,班扬“把风景细节转化为普通时空价值观无法适用的精神世界”,[25]100名利场上的风物与其说是客观环境再现,不如说是精神探索的折射。两位天路客对待名利场人与事的鲜明态度表明,他们本着自己的选择,坚守信仰,以此清楚地告诉别人自己是谁,宣示新的权威建构的开始。班扬将可谓是俗世社会缩影的名利场置于个人信仰选择命题之中,意在让读者明白,个人的现实生活就是书中基督徒的天路之旅,每一个选择虽是个人决断,但和无数他者的个人选择一道共同建构了所在的社会。此时基督徒、忠信两人的信仰坚持既可被理解成应对指向他们考验之举,又可被视为唤醒集市陷于罪恶的他者良知之法,由此,改造罪恶世界成为可能。基布尔认为,班扬这位作家自我建构的权威就在于“经验真实性与神意启示”[26]19的融合,也就是说,故事中具有真实性的人、事、物无不渗透着神意启示。
罪恶集市上的人们对新到的异见者侮辱伤害,迫使两人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两位与众不同的天路客在暴徒面前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忍耐一面:“他们就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成为众人戏弄、怨恨、报复的对象。集市大老板对他们遭遇的这一切一直冷嘲热讽,但这两人存心忍耐,不以辱骂还辱骂,反倒祝福起来,以善言应答恶语,以仁慈回报伤害。”[21]73信仰属于个人选择,但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得以验证。班扬让笔下的基督徒、忠信不是和罪恶集市上的人那样以恶抗恶,针锋相对,而是效法耶稣,用祝福与仁慈待人,匡正他者的恶行。班扬生活的近代早期人文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个人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成就自我。[27]81两位天路客的祝福与仁慈是个人信仰在与他者关系建构过程中的现实表现,事关信仰的考验也是在此中得以完全。基督徒、忠信的坚忍与集市恶徒的狂暴构成鲜明的对比,这唤醒了部分人士的良知,集市上的人们产生分化,随后两派拳脚相加,引发骚乱,这意味着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理想社会悄然萌芽,最初是在原本身陷罪恶,现在心有盼望的若干人身上,但更多的人会逐步加入。由此看来,两位天路客在集市的言行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把自己与他者公共场合的表现转化为事关信仰的探索,这也意味着“天路客与敌对势力的争斗转为自我的个人思考”。[4]70
集市骚乱让当局感到警觉,他们意识到自己现有权威受到挑战,必须及时扼杀,因而他们罗织针对两位天路客的罪名:“这两人仇视、扰乱他们的生意,在镇上制造混乱和纷争,以极危险的言论蛊惑人心、网罗同党,公然藐视他们的王法。”这些指控意在置基督徒、忠信于死地,而已被关入大牢的这两位天路客“互相劝慰说,谁命定去受难,谁就有最好的结局,因此也都暗自希望自己有那份优先权”。[21]74对《圣经》有了解的读者不难看出此处情节与耶稣受难的关联性。耶稣为拯救世人之故受难。他一生行善,却因无根据的指控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效法耶稣的基督徒、忠信本着自己的信仰向身陷罪恶之人传播真理,同样也受到恶意诽谤以及当权者的迫害。忠信更是直接在法庭上宣示了光明与邪恶的对立、决斗,并因此被施以酷刑而殉道。两人是以普通信徒的身份,凭着自己的信仰,演绎了耶稣救世与牺牲精神,而这既是基督教教义的精髓所在,也是改造罪恶集市的有效方式。班扬将书中人物的个人主体性选择与社会公共性建构的紧密融合,使得《天路历程》一书“不仅是神意启示之作,而且是神意应许的证据或象征”。[28]182
班扬让笔下的基督徒、忠信两人明示个人信仰与宗教身份,进而效法耶稣,遵循神意与罪恶斗争,及至不惜殉道,以此预示名利场这俗世生活必将因无数普通信徒的个人选择而被改造,罪恶集市必将因此成为个人信仰与基督社会建构的试验场。名利场是全书最具戏剧化的情节,既有俗世生活的再现,又有邪恶思想的刻画,更有属灵争斗的描写,这足以揭示个人信仰过程中的复杂性。在审判忠信的法庭上,由盲心先生、弃善先生、恶毒先生等等组成的陪审团也是普通信徒经常遇到的信仰对立者、阻挠者和加害者。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有具体的化身,他们使信徒迷惑,使自我救赎过程充满挑战,融于现实世界的这一切也正是精神信仰天路之旅上的道道难关。然而,班扬让笔下的基督徒凭着基于个人主体性的宗教身份闯过了一切波谲云诡的考验,这使得《天路历程》一书用“回旋且不可预测的叙事展示了高度一致性的自我经验”。[7]177
班扬创作《天路历程》一书的前后正是英国历经内战、查理二世复辟、光荣革命之际,此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需要看到的是,旧有权威的分崩离析冲击了既有社会共识,造成了“全面的阐述崩溃”。[29]132此时的民众需要建立新的个人认知体系以解读正在发生的一切。同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即资产阶级日益取代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催生了新的权威建构需求。班扬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一道有意通过自己的作品为个人认知与社会权威的同步建构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也就使得此时期文本往往涉及“主观化与客观化、社会性与个人的方方面面”。[30]802对笃信基督教的班扬来说,个人信仰不仅是个人生命之本,而且是社会建构之基,他的作品是在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互为建构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班扬在“救赎”“名利场”这两个核心命题阐述中,一以贯之地强调了个人主体性在认知、信仰与权威概念层面的重要性,揭示了“权力与权威从上帝转至个人主体”这一过程。[31]25班扬认为,个人救赎是基于个人认知,自主选择的信仰之路,并在神意指引下,独自面对各种考验,直至灵性的成长;同时,个人救赎是在与他者,以及社会这类“名利场”的互动中得到验证,并以推动属灵社会的建构为目标。班扬个人的亲身经历使其愿意以平等友好的口吻向读者讲述信仰之于个体与社会的意义,整部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深得读者喜爱。广为流传的这部作品虽为宗教寓言,但它与新兴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深度契合,进而对漫长的18世纪社会精神建构有着深远影响。可以说,《天路历程》在文本传播与社会影响这两个层面揭示了个人主体性之于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