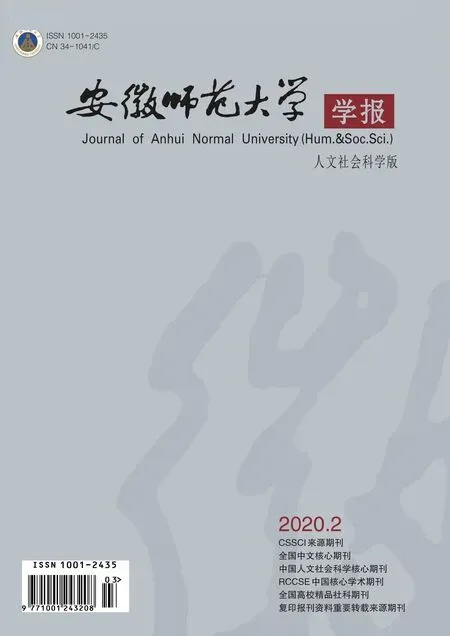诗词赋呈现音乐美的三重维度*
2020-12-27王云
王 云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上海200040)
《礼记·乐记》:“夫乐者,乐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1]1032这大约是世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推崇音乐的基本理由,然而,不同民族推崇音乐的深层理由各不相同。《论语·子路》记孔子语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522而《礼记·乐记》则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977音乐乃治国平天下的工具,这是儒家为其重视音乐而给出的深层理由。儒家思想在古代意识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而这一深层理由又契合“政治正确”,因而即使墨家“非乐”,也丝毫未能动摇儒家的音乐价值观,自然也未能动摇古代中国人对音乐超乎寻常的推崇。正因为如此,古代诗人创作了大量呈现音乐美的诗词赋。①从一些呈现音乐美的诗词赋中,显见它们受到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唐吴筠《听尹炼师弹琴》:“郑声久乱雅,此道稀能尊。”唐吕温《奉和张舍人阁中直夜思闻雅琴因书事通简僚友》:“忆尔山水韵,起予仁智心。”唐《箜篌赋》:“且礼则常履,乐焉可阙。”
不过,描述音乐绝非文字所长。美国音乐学家克丽斯汀·福尼和约瑟夫·马克利斯在其《音乐的乐趣》中说;“音乐语言不易被迻译成自然语言。你不可能从言说音乐的文字中推知某一段音乐本真的声音……”①The Enjoyment of Music:“The language of music cannot easily be translated into the language of words.You cannot deduce the actual sound of a piece from anything written about it….”[3]5文字无法还原音乐,哪怕在最小程度上,却又要让人领略音乐美,那唯一可行的便是以各种具体手法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这是诗词赋呈现音乐美的总纲。审视它们呈现音乐美的众多具体手法,不难发现这些手法皆出自以下三个维度。
一、以音乐的特征彰显音乐美
苏轼《前赤壁赋》写箫声:“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泣”“诉”和“呜呜”谓箫声所含有的音调之特色,“怨”和“慕”谓箫声所抒发的情感之特质。这似乎告诉我们,诗词赋所描摹的音乐特征不外乎此二者,前者形而下,后者形而上,且后者往往由前者所彰显。若没有猜错,上引“泣”与“怨”、“诉”与“慕”之间应该有着一一对应关系。与西方19世纪中叶之前的诗歌直抒胸臆这一抒情方式大异其趣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往往借景、事、物言情,因而有着高度的意象性。欧阳修《琴》:“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把音乐之“声”状写得具体可感总要比把音乐之“意”状写得具体可感容易得多。出于以上两个原因,中国古代诗词赋大多以具象的也即隐喻性的语言来描摹音乐的音调特色,甚至进而显示音乐的情感特质,鲜见仅仅以抽象的也即透明性的语言直接描摹音乐的情感特质。
其一,以自然声响描摹音乐的音调特色,从而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音乐的内容源自人们的思想情感,而音乐的形式则源自自然声响,用朱谦之先生的话来说,那便是“宫商虽千变万化,却都是大自然的音乐之流之一波”。[4]18说到底,音乐不过是音乐家从自然声响中提炼出来的,用以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音调化、节奏化了的声音,因而人们就有可能以比较和谐的自然声响(接近于音调化、节奏化了的自然声响)来模拟乐声的音调特色。
琴(古琴)既是地位最崇高的乐器,也是传说中历史最悠久的乐器之一,故呈现古琴声之美的诗词赋数量最多。北齐萧慤《听琴》:“弦随流水急,调杂秋风清。”唐刘长卿《幽琴咏上礼部侍郎》:“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唐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另名《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欧阳修《琴》:“飒飒骤风雨,隆隆隐雷霆。”因“高山流水”典和《风入松》曲,故以水声、松涛和山籁来模拟古琴声的诗句不胜枚举,但看多了,总觉得它们不如李白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气势恢宏;不如明高启的“应留西涧水,千载写余音”(《夜访芑蟾二释子因宿西涧听琴》)含蓄蕴藉;不如岑参的“此曲弹未半,高堂如空山;石林何飕飀,忽在窗户间”(《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余味曲包。琴声然,其他乐声亦然。欧阳修《生查子·弹筝》:“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明刘基《水龙吟·吹箫曲用东坡韵》:“露咽秋蝉,霜凄白鹤。”在以自然声响呈现其他乐声之美的诗词赋中,宋刘过《听阮》别具一格:“却将江上风涛手,来听纱窗摘阮声。”
如果说“西涧水”和“万壑松”等还都是大自然原本就有的声响,那么下引诗歌中的声响却大多是有了“人化了的自然界”后才产生的声响。唐张祜《楚州韦中丞箜篌》:“千重钩锁撼金铃,万颗珍珠泻玉瓶。”唐韦应物《五弦行》:“古刀幽磬初相触,千珠贯断落寒玉。”白居易《琵琶行》:“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苏轼《琴》:“风生瀑布已清绝,更爱玉珮声琅珰。”“钩锁”“金铃”“玉瓶”“古刀”“幽磬”“银瓶”“刀枪”和“帛”皆非自然物,因此它们受外力影响或它们之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声响,显然不是大自然原本就有的。
其二,以视觉形象描摹音乐的音调特色,从而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从创作角度看,文字塑造视觉形象和塑造听觉形象都是间接的,都必须借助于人的第二信号系统,在这两者之间,前者恐怕更容易。从接受角度看,用文字塑造的视觉形象要比用文字塑造的听觉形象赋予受众更大的想象空间。因此诗人在描述音乐形象时,往往将其诉之于一定的视觉形象。
王昌龄《琴》:“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意远风雪苦,时来江山春。”王昌龄《箜篌引》:“弹作蓟门桑叶秋,风沙飒飒青冢头;将军铁骢汗血流,深入匈奴战未休。”韩愈《听颖师弹琴》:“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任飞扬。”在这类以视觉形象状写乐声的作品中,以花状写乐声(尤其琵琶和笙之乐声)的并不鲜见,如南朝梁徐勉的“含花已灼灼,类月复团团”(《咏琵琶》);唐郎士元的“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听邻家吹笙》);唐殷尧藩的“玉桃花片落不住,三十六簧能唤风”(《吹笙歌》)。难道琵琶和笙的音色更易令人联想“红杏枝头春意闹”不成?
以视觉形象来呈现音乐美,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乃因为人类有着联觉(synesthesia)这一特殊的联想能力。钱锺书先生将联觉称作“通感”或“感觉挪移”,他的《通感》对中西文学作品中的联觉现象,尤其视听联觉(在声音作用下产生某种视觉形象)现象多有深刻阐发。实际上,中国人早就意识到这一心理现象。《礼记·乐记》记师乙语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勾)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孔颖达疏曰:“此一经论感动人心形状,如此诸事。……言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5]1340此言若换成汉马融的话,那便是“听声类形”。马融《长笛赋》:“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泛滥溥漠,浩浩洋洋;长矕远引,旋复回皇。”在他的笔下,长笛吹奏出的乐声忽而让人仿佛目睹浩浩洋洋之流水,忽而又仿佛目睹旋复回皇之飞鸿。《通感》评说道:“马融自己点明以听通视。”[6]67显见他在使用这一手法时颇具自觉意识。
在描摹音调特色时,自然声响和视觉形象难免拼合或糅合在一起。李白《示金陵子》:“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度西江水。”忽见天坠一片花,又闻西江流水声,故此为拼合。唐五代韦庄《听赵秀才弹琴》:“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晴波指下生;蜂簇野花吟细韵,蝉移高柳迸残声。”谁又能将雨、波、蜂、蝉的声音从巫山、湘水、野花、高柳的景象中彻底剥离出来,故此为糅合。有时要辨识一句诗是否糅合型还真不容易。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后一句无疑是视觉形象,前一句究竟是视觉形象还是自然声响,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也只能见仁见智了。《通感》援引了不少把乐声比作“珠”的中西诗句或文句,且说它们大多意谓乐声“仿佛具有珠子的形状,又圆满又光润”。若要挑选一种乐声最像珠子,那无疑是琵琶声了,因为琵琶的音色最具颗粒感。然《通感》却从语境的角度认定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行》)仅仅“是说珠玉相触那种清而软的声音”。[6]67-68如是判断大可存疑。
其三,以抽象概念直接点出音乐的情感特质,且辅之以视觉形象,从而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宋晏几道《菩萨蛮·筝》:“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这段筝声所传递的情感之特质无疑是“幽恨”,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幽恨呢?晏几道既未赋予其形象,也未暗示受众联想的路径。这终究不是注重意象性的古代诗词赋的主流写法。欧阳修《琴》:“用兹有道器,寄此无景情。”唐孟郊《楚竹吟》:“欲知怨有形,愿向明月分。”音乐所抒发的情感一定是“无景情”,然它却可能“有形”,即被赋予形象。
张祜《听筝》:“分明似说长城苦,水咽寒云一夜风。”唐顾况《听角思归》:“故园黄叶满青苔,梦破城头晓角哀。”白居易《五弦》:“又如鹊报喜,转作猿啼苦。”唐郑愔《胡笳曲》:“曲断关山月,声悲雨雪阴。”宋赵汝鐩《闻舟中笛》:“吹怨芦管惨,含凄雁影寒。”明何景明《吹笛》:“关山月落肠应断,楼阁秋生响易悲。”这些诗句中的“苦”“哀”“喜”“悲”“怨”“凄”等因有形象的烘托皆具体可感。在这类诗句中,最令人叫绝的应为明陈继儒的“有时弦到真悲处,古战场中蟋蟀声”(《鼓琴》)。以“蟋蟀声”来模拟古琴声实在俚俗得有点不伦不类,然以“古战场中蟋蟀声”来诠释古琴声的“真悲”却足以化大俗为大雅,它不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而且使“真悲”完全落到实处。
除了直接将抽象的情感特质形象化外,另有间接形象化之法,那便是用典。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意谓古琴声中的哀怨之情仿佛如远嫁乌孙国的汉江都公主和解忧公主、远嫁吐蕃国的唐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异乡哀怨之情。不过,这四位公主中唯有江都公主的异乡哀怨之情正史中有明确记载。江都公主即谋反未成后自杀身亡的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元封六年,汉武帝为笼络乌孙国以便与其联手抗击匈奴,便将她作为和亲公主嫁给乌孙昆莫(国王)猎骄靡。《汉书·西域传》:“公主至其国,……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7]3903今人称其歌为《悲愁歌》。
以典故使抽象的情感特质形象化之手法源远流长。韦应物《五弦行》:“燕姬有恨楚客愁,言之不尽声能尽。”唐杨巨源《宿藏公院听齐孝若弹琴》:“离声怨调秋堂夕,云向苍梧湘水深。”宋陈普《鼓瑟》之一:“凄凉楚客新愁断,清切湘灵旧怨多。”元赵孟頫《闻角》:“抑扬如自诉,哀怨不堪闻。……只今霸陵尉,那识旧将军。”明吴俨《听郑伶琵琶》:“江头商妇愁无限,塞外明妃恨不同。”上引诗句分别用了“燕姬”“楚客”①屈原有多次被流放的经历,故有此称。《史记·屈原列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娥皇和女英、“湘灵”②屈原《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此湘灵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湘夫人即娥皇和女英。、“旧将军”(汉李广将军)、“江头商妇”③江头商妇即《琵琶行》中浔阳江头那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塞外明妃”(王昭君)之典,有了这些典故,便在此文本与他文本之间建构起互文性,正是这种有意建构的互文性,让受众拥有了联想路径,想见了历史场景,从而间接地获得了形象感。
二、以音乐的效果映衬音乐美
以文字描述音乐形象之美勉为其难。对于世上任何难以描述的形象美,有时避免对其进行直接描述而代之以对其效果的描述不失为明智之举。莱辛《拉奥孔》说:“诗人就美的效果来写美。”“诗人啊,替我们把美所引起的欢欣,喜爱和迷恋描绘出来吧,做到这一点,你就已经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既然感觉到只有最完美的形象才能引起的情感,谁不自信亲眼看到那种最完美的形象呢?”[8]119-120
其一,以听者的反应描述音乐效果,从而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听者最典型的反应莫过于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甚至泪沾衣襟。白居易《琵琶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既描述自己流泪,也描述他人流泪,但大多数诗人仅执其一端。岑参《秦筝歌送外甥萧正归京》:“清风飒来云不去,闻之酒醒泪如雨。”此为自己流泪。唐严维《相里使君宅听惠澄上人吹小管》:“今夕襄阳山太守,坐中流泪听商声。”此为他人流泪。孟郊《听琴》:“闻弹正弄声,不敢枕上听。”为何不敢枕上听?难道怕泪水沾湿了睡枕,难道怕浮想联翩以至长夜无眠?
白居易《五弦》:“坐客闻此声,形神若无主;行客闻此声,驻足不能举。”欧阳修《玉楼春·琵琶》:“不知商妇为谁弹,一曲行人留未发。”宋王武子《玉楼春·闻笛》:“一声落尽短亭花,无数行人归未得。”如同驻足倾听,生发乡愁也是听者典型的反应。李白《春夜洛城闻管》:“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卢纶《湖口逢江州朱道士因弹琴》:“引坐霜中弹一弄,满船商客有归心。”比之于上引三联,同样写生发乡愁的以下三联皆意在言外。李益《从军北征》:“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明杨载《闻邻船吹笛》:“江山万里不归家,笛里分明说鬓华。”张祜《听李简上人吹芦管》:“月落江城绕树鸦,一声芦管是天涯。”一声芦管,便让听者有身处天涯之感,显见言外有乡愁。
唐常建《高楼夜弹筝》:“曲度犹未终,东峰霞半生。”一夜听不足的筝声该是怎样的筝声?如果说最夸张的是唐施肩吾的“却令灯下裁衣妇,误剪同心一半花”(《夜笛词》),那么最具奇思妙想的当属唐徐安贞的“银锁重关听未辟,不如眠去梦中看”(《闻邻家理筝》)。听者可以是经验世界中的人,也可以是超验世界中的神仙或鬼妖。岑参《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幽引鬼神听,静令耳目便。”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应读作:深山妖精来窃听——引者注)。”李贺《李凭箜篌引》:“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居然可让神仙鬼妖凝神倾听,吴刚彻夜不眠,显见古琴声和箜篌声之大美。
其二,以假想中的经验世界或超验世界的变化描述音乐效果,从而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曹丕《善哉行》:“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浮沉;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南朝陈江总《赋咏得琴》:“戏鹤闻应舞,游鱼听不沉。”唐李峤《笛》:“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惊。”经验世界或超验世界的变化不仅表现于动植物对优美乐声的反应,有时还表现于无机的自然物对优美乐声的反应。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李贺《李凭箜篌引》:“十二门前融冷光,①长安城四面各三门,共有十二门。此句意谓乐声的暖意仿佛消融了长安城里的寒气。二十三弦动紫皇。”上引两联的前一句皆描述了无机自然物的反应。孟郊《楚竹吟》:“昔为潇湘引,曾动潇湘云;一惊凤改听,再惊鹤失群;江花匪秋落,山日当昼曛。”动物、植物和无机自然物的反应三者齐全。在以假想中的世界变化来描述音乐效果的诗句中,想象最大胆,意象最奇诡的无疑是李贺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②这一类手法在西方文学中也不鲜见,如奥维德对俄耳甫斯歌声之效果的描述:“他的歌声引来了许多树木,野兽听了也都着了迷,石头听了跟着他走。”[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1页。
其三,以关于音乐的典故暗写音乐效果,从而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古代的音乐典故几乎都与音乐效果密切相关。李白《听蜀僧濬弹琴》:“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据嵇康《琴赋》中的“伯牙挥手,钟期听声”,显见此诗暗用了《列子·汤问》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伯牙和钟子期的典故。“高山流水”四字也因此典故而成了优美琴音之代称。此诗中的“客心洗流水”应读作“流水洗客心”,它有两层涵义:蜀僧濬的优美琴音洗涤了诗人的客中情怀;通过优美琴音这一媒介,蜀僧濬与诗人有了知己之感。虽用典,然文字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高超的语言技巧。
同样暗用《列子》中典故的还有李贺《李凭箜篌引》和苏轼《前赤壁赋》。《李凭箜篌引》:“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9]127“空山凝云颓不流”显然从“响遏行云”脱胎而来。《前赤壁赋》:“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列子·汤问》:“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9]127-128“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显然从“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衍化而来。伯牙的古琴声、秦青的歌声、韩娥的歌声如此美妙,那么,蜀僧濬的古琴声、李凭的箜篌声、“客”的箫声又焉能不美妙。上述三个典故都是为诗人反复运用的熟典。如李峤《琴》:“子期如可听,山水响余哀。”明常伦《琵琶》:“白雪调终宴,青云遏远天。”李白《拟古》:“弦声何激裂,风卷绕飞梁。”
北周庾信《和淮南公听琴闻弦断》:“一弦虽独韵,犹足动文君。”韦庄《听赵秀才弹琴》:“不须更奏幽兰曲,卓氏门前月正明。”它们皆使用了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典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李白《金陵听韩侍御吹笛》:“王子停凤管,师襄掩瑶琴。”元倪瓒《王都事家听周子奇吹笙》:“风流自有王子晋,留取清樽吸月明。”它们皆使用了王子乔(王子晋)吹笙作凤凰鸣的典故(《列仙传·王子乔》),李诗同时还使用了春秋卫乐官师襄子(孔子曾从其学琴)的典故(《史记·孔子世家》)。与王子乔一样,王母侍女董双成也善吹笙(《浙江通志》卷一九八),故唐曹唐在《小游仙》中说:“花下偶然吹一曲,人间因识董双成。”
三、以音乐的来源暗示音乐美
音乐从何而来?音乐自然是人演奏或演唱出来的。如果不是声乐,一定是人凭借着乐器演奏出来的。如果既非声乐,也非即兴创作,一定是人凭借着乐器和乐谱演奏出来的。此外,演奏音乐还与某种场所有关。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作为创作工具的乐器和乐谱,作为创作空间的场所都是音乐创作的因素,也即本文所谓的音乐来源。古代诗人有时正是利用了这些因素来暗示音乐美的。
其一,通过描述音乐家的内心情感和人生遭遇,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978音乐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否饱含情感对于音乐的质量至关重要。孟郊《听琴》:“闻弹一夜中,会尽天地情。”若音乐家无情,何以让受众“会尽天地情”?因而明示饱含情感的创作状态便成了暗写音乐美的一种手段。卢纶《宴席赋得姚美人搊筝歌》:“有时轻弄和郎歌,慢处声迟情更多。”李白《拟古》:“含情弄柔瑟,弹作陌上桑。”宋张炎《法曲献仙音·听琵琶有怀昔游》:“听到无声,谩赢得情绪无剪。把一襟心事,散入落梅千点。”比之于上引三联,以下诗句似更能让人获得现场感。南朝梁简文帝《赋乐名得箜篌》:“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白居易《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珠颗泪沾金捍拨,红妆弟子不胜情。”白居易《夜筝》:“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就暗示音乐美而言,具体明确的情感要比笼而统之的情感更具指向性。白居易《夜调琴忆崔少卿》;“今夜调琴忽有情,欲弹惆怅忆崔卿。”明王弼《赠庞生吹箫》:“秋来见月苦思归,不觉悲凉指间作。”因忆友而惆怅,因思乡而悲凉,音乐之美便愈加具体可感。
《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976人生遭遇也是一种“物”,音乐家的内心情感因此“物”而生,进而抒发于音乐。从“自言本是京城女”直至“梦啼妆泪红阑干”,白居易《琵琶行》以二十二句之篇幅“转述”了这位少为“长安倡女”,“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的琵琶女关于自己身世的“自叙”。她的身世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等诗句,有力地映衬了不时显现“幽愁暗恨”的琵琶声。同样,王昌龄《箜篌引》也以一个身经“百战”,而今却“颜色饥枯掩面羞,眼眶泪滴深两眸”的老兵之身世映衬了其弹奏出的以“苦幽”为基调的箜篌声。
如果说上引二诗以演奏家的人生遭遇来映衬乐声,那么,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则以作曲家的人生遭遇来映衬乐声。此诗两种标题中的“胡笳声”或“胡笳弄”即蔡琰(字文姬)参照胡笳调而写成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后汉书·列女传》:“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蔡)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10]2800由《胡笳十八拍》歌词(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和蔡琰归汉后创作的五言体《悲愤诗》可知,此曲抒发的正是蔡琰对自己的人生遭遇,尤其是归汉前“别稚子”这一经历的“愤怨”和“悲嗟”。《听董大弹胡笳声》开篇便说:“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沉沉飞雪白。”且不论作者有无主观意图,这些诗句客观上在蔡琰的人生遭遇与董廷兰的古琴声之间建构了互文关系。蔡琰的身世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等诗句,有力地烘托了以“幽音”为基调的古琴声。
其二,通过描述音乐家的演奏技能和容姿服饰,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11]2211没有起码的物化技能,就不可能有音乐;没有精湛的物化技能,就不可能有美的音乐。易言之,精湛的物化技能是产生音乐美的必要条件。既然如此,那么描述了这一必要条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音乐美。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中的董大(董庭兰,或董廷兰)是唐玄宗和唐肃宗时期的著名琴师。在李颀笔下,他的弹琴技艺十分了得:“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手法如此娴熟,古琴声焉能不美?白居易《琵琶行》序:琵琶女师出名门(“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且又“名属教坊第一部”,①此琵琶女年少时只是“长安倡女”,又常与“五陵年少”打交道,因此不太可能是宫里的“内人”(在宫内服役的歌舞伎),应该是“外供奉”(临时被召入宫内服役的歌舞伎),尽管这里说“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显见其演奏技艺之高超。《琵琶行》描述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居然可以“未成曲调先有情”,居然可以“信手续续弹”,却又“说尽心中无限事”,琵琶声之美则不言而喻。
以精湛技能暗示音乐美的适例很多。卢纶《宴席赋得姚美人搊筝歌》:“忽然高张应繁节,玉指回旋若飞雪。”元朱德润《和赵季文觱篥吟》:“缓急应节如解牛,清风席上寒飕飕。”元揭傒斯《李宫人琵琶行》:“一见世皇称绝艺,珠歌翠舞忽如空;君王岂为红颜惜,自是众人弹不得。”倪瓒《听袁员外弹琴》:“两忘弦与手,流泉松吹声。”明黄姬水《听查八十弹琵琶歌》:“抑扬按捻擅奇妙,从此人称第一声……据床拂袖奋逸响,叩商激羽高梁上……回飙惊电指下翻,三峡倒注黄河奔。”技艺如此精湛,音乐自然精美。
南朝梁沈约《咏筝》:“徒闻音绕梁,宁知颜如玉。”此联意谓,只闻筝曲之美,难道不知弹筝者之美?①此诗中的“宁知”即“宁不知”的缩略语。沈约《夜夜曲》之一:“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清张玉穀注:“星汉写夜景也,却即慨其不知心忆……”张玉穀《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沈约由音乐之美涉及或推知音乐家之美,然更多的诗人却以音乐家之美暗示音乐之美。音乐家的容姿服饰美,她弹奏出的音乐就一定美吗?诗人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宋张先《剪牡丹·舟中闻双琵琶》:“酒上妆面,花艳媚相并。”明王穉登《长安春雪曲》:“煖玉琵琶寒玉肤,一般如雪映罗襦。”明石沆《夜听琵琶》:“娉婷少妇未关愁,清夜琵琶上小楼。”在此类诗句中,最具秾艳香软之品质的,恐怕要数明许观的“六孔恍疑娇黛润,几斑还带粉香温”(《咏湘妃竹箫应教》)。
大多数诗人干脆连音乐之美也一并写出,真可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南朝陈吴尚野《咏邻女楼上弹琴》:“青楼谁家女,开窗弄碧弦。貌同朝日丽,装竞午花燃。”她的琴声果然不同凡响:“一弹哀塞雁,再抚哭春鹃。”白居易《筝》:“云髻飘萧绿,花颜旖旎红。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她的筝声果然美奂美轮:“猿苦啼嫌月,莺娇语泥风。”宋僧惠洪《临川康乐亭听琵琶坐客索诗》:“玉容娇困拨仍插,雪梅一枝初破腊。”那么她的琵琶声呢?“日烘花底光似泼,娇莺得暖歌唇滑;圆吭相应啼恰恰,须臾急变花十八。”写女性音乐家然,写男性音乐家亦然。王弼《赠庞生吹箫》:“青年白晢吹者谁,庞子风流妙音乐。”
其三,通过描述音乐家所使用的乐器和所演奏的乐曲,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此联不仅表现了蜀僧濬的非凡气派,而且还点出了他手中那把名贵古琴。晋傅玄《琴赋》序:“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绿绮原本就是四大名琴之一,更因为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和精湛琴艺,故“绿绮”在后世成了名贵古琴的别称。李峤《琴》:“风前绿绮弄,月下白云来。”倪瓒《听袁员外弹琴》:“郎官调绿绮,谷雪赏初晴。”琴好,抚琴的技艺自然也好,否则何以匹配?琴好,抚琴技艺好,音乐自然就美。音乐美就是这样被烘托出来的。与“绿绮”异曲同工的是李贺“吴丝蜀桐张高秋”(《李凭箜篌引》)中的“吴丝蜀桐”。蚕丝和桐木不仅是制作古琴的最佳材料,也是制作箜篌的最佳材料,而吴地所产之蚕丝和蜀郡所产之桐木又为优中之优,显见李凭所用的是品质优良的箜篌。刘禹锡《武昌老人说笛歌》:“当时买材恣搜索,典却身上乌貂裘。”价格不菲且千方百计搜寻而得,这自然是品质优良的笛子。
如同名器,名曲同样可以烘托音乐之美。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霓裳羽衣曲》即《霓裳羽衣舞》,是唐朝歌舞中的集大成之作。白居易似乎特别钟情于它,他在《霓裳羽衣舞歌》中说,“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绿腰》(《六幺》《录要》)亦为唐朝著名的歌舞大曲。元王士熙《李宫人琵琶引》:“琼花春岛百花香,太液池边夜色凉。一曲六幺天上谱,君王曾进紫霞觞。”作为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和《广陵散》也经常现身于呈现音乐美的诗歌。一首名曲,又遇上一个出色的演奏家,他会演奏出何等美的音乐?一切皆不言自明。
其四,通过描述音乐家演奏音乐的环境,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感受音乐美。在演奏音乐的环境中,主角自然是音乐,主要配角当为“江”和“月”。唐刘沧《江楼月夜闻笛》:“南浦蒹葭疏雨后,寂寥横笛怨江楼。思飘明月浪花白,声入碧云枫叶秋。”张祜《瓜州闻晓角》:“寒耿稀星照碧霄,月楼吹角夜江遥。”石沆《夜听琵琶》:“裂帛一声江月白,碧云飞起四山秋。”杨载《闻邻船吹笛》:“江空月寒江露白,何人船头夜吹笛。”如果说“江”和“月”是主要配角,那么,“树”(木)“云”(霞)“山”(峰)“风”和“花”等则为次要配角。李颀《琴歌》:“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树风入衣。”常建《江山琴兴》:“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唐丁仙芝《剡溪馆闻笛》:“山空响不散,溪静曲宜长。”宋韩维《再和尧夫饮杨路分家听琵琶》:“春湖水渌花争发,好引红妆上画船。”赵汝鐩《闻舟中笛》:“孤音起水面,余韵到云端。”金郭彦邦《秋夜闻弹箜篌》:“露重花香飘不远,风微梧叶落无声。”元郭钰《无题》:“游丝风煖飐飞花,窈窕箫声隔彩霞。”
借景言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抒情方式。描述的是美景,抒发的却是闻音听乐之后赞赏的情感;描述的是美景,抒发的却是因被音乐感动而生发的愉悦、惆怅和凄凉等情感。正是这样的情感令人在不经意间领略了音乐的美。在这类诗歌中,唐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省试湘灵鼓瑟》)最耐人寻味;刘禹锡的“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夜闻商人船上筝》)最含蕴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