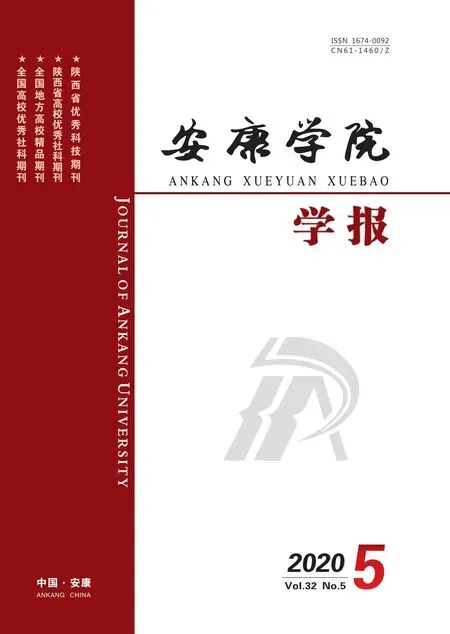吴大澂与晚清关学
2020-12-26米文科
米文科
(宝鸡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吴大澂(恒轩、愙斋,1835—1902),苏州吴县人,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师从湖北程朱学者万斛泉(1808—1904)。同治七年(1868) 进士,一生宦迹遍及西北、东南、东北等地,政声卓著,特别是其所著《说文古籀补》 《字说》 《愙斋集古录》等书,为学界所推重。虽然近代以来有关吴大澂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政绩的考察,如创设吉林机器局、中俄勘界和治理黄河等;二是关于吴氏的古文字学和篆书的研究;三是对吴氏信札的整理、考释等。然而,对吴大澂早年在西北任陕甘学政与晚清关学复兴的关系却没有提及,《吴愙斋年谱》在记录此段经历时也多是集中在金石瓦当古物方面,以及与左宗棠的书信往来等。本文则通过晚清关中学者贺瑞麟(1824—1893) 与杨树椿(1819—1874) 等人文集中所见吴大澂的资料和事迹来说明其对于推动晚清关中地区程朱理学“复兴”所起的作用,从而既可以使我们对吴大澂的生平活动有更多的了解,又可以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晚清关中地区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至光绪二年(1876)十月离任,在陕三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三年间,吴大澂与当时关中以提倡程朱理学、振兴关学为己任的贺瑞麟往来密切,二人一起为晚清关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大澂初识贺瑞麟是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也就是在他于十月抵达陕西三原履学政任后不久,就前往拜访贺瑞麟。对于吴氏的此次来访,贺瑞麟《清麓年谱》中记载道:
十二月,督学吴公来见,论学谈心甚相契合。去后赠以联曰:“以身教从,以言教讼;得经师易,得人师难。”又书林少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联语以赠,并为篆书《大学》经文及张子《西铭》两横幅,以悬堂壁。[1]1106
贺瑞麟,字角生,号复斋,学者称清麓先生,陕西三原人。其师为朝邑(属陕西大荔)的李元春(时斋,1769—1854),为嘉庆、道光年间的关中理学名儒。贺瑞麟对科举之学极为痛恶,他在二十八岁时就绝意科举,也从不以举业教人,不仅如此,贺瑞麟还对陆王、佛老和考据学等持批评态度,而唯独提倡程朱理学。贺瑞麟的这种为学倾向正好与来访的吴大澂相近。吴大澂虽然在金石学、书画等方面建树颇多,但他在思想上则服膺程朱之学,其《读书偶见录》和《愙斋自省录》中所记即多为存心、养性、居敬、静坐、未发气象等程朱理学之内容。如“夜气之清明,以心体言也;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以形体言之。”“吾儒静坐存心,即所以养性;禅宗静坐明心,而不能见性。”[2]贺、吴两人为学旨趣相近,相见之下,自然“论学谈心甚相契合”。吴大澂说:“大澂以同治癸酉奉使视学秦中,始交角生,心器之。”[3]16而吴大澂回去后又为贺瑞麟书写了两副对联,并篆书《大学》经文和张载《西铭》赠之,从中也可见他对贺瑞麟的器重。总之,此次的论学谈心为日后两人的交往和共同为振兴关学而努力奠定了基础。
第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初,贺瑞麟写信给吴大澂,请其在省内各学校提倡张载之学和在三原举行乡约。贺瑞麟在信中说:
惟横渠为关学之祖,今学者率不能举其名字,况知其学乎!若以之提倡,则承学之士庶识途辙之正,于以会归程朱而不惑于他歧,尤麟之私愿也。此在大人固不待言,然犹言之者,念辱与之厚,亦所以尽其诚耳!乡约盖欲各相勉励与人为善之意,今一举行,人知学宪亦且留心,信从必众,愿早示期。或令斋长召集同志,似不须通知地方,官师一有掣肘,或非其心之所欲,必不能长,恐无益也。[1]281
作为理学思潮之一的关学是由北宋张载(1020—1077)所创立,从贺瑞麟的信中可以看到,关学传衍至晚清,关中士子竟然连张载的名字都很陌生,更不用说其思想学说了。在贺瑞麟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士子只以辞章记诵为学,汲汲于科举功名,此外概不讲求,所以他认为应该在各级学校和书院中提倡张载之学,这样既可以振兴关学,也可以使学者知道正确的为学方向,而不被俗学、陆王、佛老和考据之学所迷惑。对于张载之学,贺瑞麟特别推崇的是张载的礼教。他说:“昔横渠先生以礼教关中学者,当时士大夫习礼成风,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即吕氏此书是也。诸君果设诚致行,人心风俗且趋于善,庶几不负先贤儒之教。”[1]93因此,贺瑞麟打算通过推行《吕氏乡约》来恢复关学的礼教传统,并借此来化民成俗。
对于贺瑞麟之请,亦即在三原举行乡约一事,得到吴大澂的赞成。是年春(同治十三年),贺瑞麟在三原学古书院讲行乡约,吴大澂不仅亲自前来观礼,而且在礼成之后,还为书院诸生宣讲人子事亲之道。贺瑞麟在为吴大澂之母所作的《吴母韩太宜人寿序》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同治癸酉,吴县吴公清卿先生视学秦中。首屈威重,辱访瑞麟于清麓山斋。明年春,瑞麟率同志讲行乡约于邑之学古书院,先生亲临观礼,众请讲书。先生辄为发明人子所以事亲之道,并引辛复元“子为贤圣,父母即为贤圣之父母;子为庸众小人,父母即为庸众小人之父母”,肫切恳挚,听者竦然,无不感叹。[1]122
在学古书院举行乡约之后,贺瑞麟又专门写了《学宪举行吕氏乡约序》一文,并在序中告诫参加乡约的士子要真正身体力行,而不是“只作一场话说”[1]93。学古书院之后,第二年即光绪元年(1875) 二月,贺瑞麟又在三原的宏道书院行乡约礼,吴大澂与三原县令赵孚民一起参加表示支持。《清麓年谱》“乙亥光绪元年”条云:“二月,行乡约礼于宏道书院,学宪吴公、邑令赵公偕至。礼毕,先生讲书,一时环而听者,堂舍几不能容。”[1]1107
通过吴大澂两次参加贺瑞麟举行的乡约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认为贺瑞麟的行为是一种迂腐之举,而是加以肯定和支持,而且他作为督学也不以贺瑞麟批评科举和只以程朱理学教授生徒为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大澂以理学经世的思想。正如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同治十三年正月和五月两次给吴大澂的回信中说的:“所示关中乱后,旧学旋荒,执事鼓舞振新,期至于古,不取其华而遗其实,正得古人兴教劝学之意,所为与凡俗异矣。佩悦何言。”“来书于教士之道,用心恳恻而有条理,意在关学嗣音,不取文艺之末,与古昔兴教劝学大指,实有合焉。由文艺而几于道,异时当有兴者。”[4]89从左宗棠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吴大澂以理学兴教劝学和振兴关学的想法。
二
同治十三年二月,吴大澂前往同州(今大荔)查考诸生学业,时朝邑学者杨树椿以诸生身份参加岁考,两人因此而相识。杨树椿,字仁甫,号损斋,与贺瑞麟同师从李元春,尊崇程朱之学,绝意科举,淡泊名利,曾主讲过朝邑的友仁书院。贺瑞麟称:“关中之学,国朝自朝邑王仲复先生恪守程朱,躬行实践,为不愧大儒。百余年而桐阁先生继之,又数十年而君(杨树椿) 继之。”[1]737后人亦曰:“(杨树椿)事亲至孝,雅志山林,不求闻达。前后读书太华几十年,其为学坚实刻苦,默契精思,养之深以醇,守之严以固,虽在草野,无一念不在天下国家。”[1]1089
吴大澂在读了杨树椿的文章后,并与之交谈,对杨的学问和品行甚为敬佩。此年秋,他即以贺瑞麟和杨树椿二人之名上奏朝廷,请求表彰其学其行。其疏略云:
贺瑞麟隐居教授,实践躬行,臣屏驱从,轻骑造庐。所居峪口距城十里,陶室数间,拥书自乐,学以《近思录》 《小学》为宗,辑宋元诸儒《养蒙书九种》教授生徒,循循善诱,恬于荣利,确守程朱。[1]1106
朝邑杨树椿隐居华山,潜心理学,除岁考外,不入官府,有古君子风。臣按临同州,适来应试,询其所读性理诸书,融会贯通,实有心得。平日涵养之功,一本程朱主敬之学,所谓笃行谨守,不求闻达,亦足为世风矣。[5]89
吴大澂的奏疏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回应,贺瑞麟与杨树椿被授予国子监学正衔。随后,吴大澂又手抄清初程朱理学名儒陆世仪(桴亭,1611—1672)的《志学录》一书向贺瑞麟请正,贺瑞麟则作《书陆桴亭〈志学录〉后》,对陆世仪思想中与朱子不一致和赞同陆王的地方进行了批评①贺瑞麟在《书陆桴亭〈志学录〉后》中说:“右书二册,为明太仓陆桴亭先生崇祯十四年辛巳日记,名《志学录》,而今学使吴县吴公清卿先生收录本也。”书末曰:“蓄疑既久,辄复有感,又不敢隐于有道之前,敬书册后而并就正于清卿先生,以为有当否?同治甲戌孟秋朔日,三原贺瑞麟谨识。”(《贺瑞麟集》,第19-20页)。
除了贺、杨二人之外,吴大澂还对当时其他一些关学学者的学行也进行了表彰,如大荔诸生赵凤昌(字仲丹,号宏斋),其与杨树椿一起学于李元春,又一同在华山读书,先后近二十年,“斤斤有守,温恭笃实,家庭之间,怡怡如也”[5]119。赵凤昌殁后,吴大澂题其门曰“笃学勤修”[5]119,进行表彰,以激励士风。
此外,吴大澂还多次将一些理学书籍赠予关中学者和士子,以提倡理学和鼓励士子积极向学。如他曾赠给贺瑞麟《朱子全书》和张伯行(孝先,1652—1725)正谊堂所刻理学书八十余种,以及张履祥(杨园,1611—1674)的《杨园先生全集》等②贺瑞麟在《吴母韩太宜人寿序》中记述道:“先生(指吴大澂) 之来也,尝辇致《朱子大全》、《文集》、正谊堂所刻诸儒先书八十余种、《张杨园先生集》及近世讲学诸公书。”(《贺瑞麟集》,第123页)。赠予杨树椿《杨园先生全集》。杨树椿在《与学宪吴清卿》中说:“《杨园全书》已拜受,不啻拱璧。前所求《弟子箴言》,尚希后惠。”[3]49在这里,杨树椿提到的另一本书《弟子箴言》,为晚清湖南理学家胡达源(云阁,1778—1841)所著,全书共十六卷,分为奋志气、勤学问、正身心、慎言语、笃伦纪、睦族邻、亲君子、远小人、明礼教、辨义利、崇谦让、尚节俭、儆骄惰、戒奢侈、扩才识和裕经济等篇目,融会孔孟与宋明理学诸儒之说,发明心得。仅从该书各卷标题来看,就可知非常符合吴大澂的学问宗旨和教育理念,故他对该书非常重视,后来还写有二万余字的批语。今光绪二十一年(1895) 重刻本《弟子箴言》中收有吴大澂为该书所作之序。他在序中说:“余于同治壬戌入都应北京兆试,得见此书于彭文敬公家,访诸厂肆,竟少传本,乃约同人集资覆刻于吴门。视学关中,时曾以给诸生之好学者。”[6]除了时常将《弟子箴言》赠予关中士子之好学者之外,吴大澂“又印发《小学》书数百部,散给生童”[1]123。对此,贺瑞麟说道:“诸生溺于科举之学也,久未尽知先生之意,为之探讨服行,然亦有闻风兴起者,其造于秦士何如也!”[1]123
同治十三年九月,杨树椿去世。第二年,即光绪元年三月,贺瑞麟前往朝邑会葬杨树椿,返回后又请吴大澂为杨氏的遗稿《损斋文钞》作序,并题其墓碑文。吴大澂之序作于是年九月,现保存于光绪十九年(1893) 刻本《损斋文钞》中。略曰:“余谓士子读孔孟之书,操觚为文,而不知身体力行者,比比皆是。即有志之士,知从事于《小学》《近思录》,识阴阳之原,辨理气之分,明穷理居敬之功,而或不能实有诸己,又恐有所知非真知,有所得非心得,宣诸口、笔诸书,与制艺等耳,于身心何与?观仁甫与角生及他友书,时时以真实心地相策勉,不欲以言语文字为长,仁甫可谓笃信好学之君子矣。……光绪元年九月,陕甘督学使者吴县吴大瀓序。”
三
在弘扬关学、激励士风方面,吴大澂所做的贡献还有:
一是上疏朝廷,请求将朝邑学者李元春的学行宣付史馆,列入《儒林传》中。
李元春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关学名儒,其学以程朱理学为宗,学者称之为桐阁先生。李元春通过阅读明初程朱理学大儒河东薛瑄的《读书录》而有志于理学的学习,并进而研读二程、朱子的著作及各种理学书籍,博学多识。嘉庆三年(1798),李元春考中举人,但随后却九上春官不第。道光十六年(1836),李元春以举人身份被授予大理寺评事一职,后因母亲年老,于是辞官回家奉养,讲学乡里,后曾先后主讲过潼关的潼川书院和朝邑的华原书院。李元春著述丰富,有《桐阁先生文钞》 《桐阁先生性理十三论》 《四礼辨俗》 《桐阁杂著》《关中道脉四种书》等书,并对明代冯从吾(少墟,1557—1627)的《关学编》进行增补,以延续关学之“道统”“道脉”。其弟子著名者有贺瑞麟、杨树椿等人。吴大澂在奏疏(今附于《桐阁先生文钞》卷首) 中说:
臣窃维关中素称理学之邦,宋时横渠张子倡明斯道,继往开来。同时有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及华阴侯仲良、武功苏昞、游师雄等闻风兴起,一时称盛。明儒冯从吾纂《关学编》,自宋迄明,渊源相授三十余人。国初,讲学诸儒自王建常、李中孚后,落落如晨星,数十年来,几成绝学。朝邑举人李元春独慨然有志于圣贤,绍述绪闻,恪守程朱格致诚正之功,教授生徒数十年,多所成就。臣所访举三原贡生贺瑞麟、朝邑生员杨树椿皆其晚年入室弟子。迹其生平,践履笃实,持论明通,卓然为关中儒者。……其论学必主程朱,于心学良知之说辟之甚力。其所纂述,无非扶世教,正学术,为世道人心计,而不务空言。……如李元春之读书明理,实践躬行,洵属近今所罕见,不愧纯儒之目,合行仰肯圣慈将已故大理寺评事举人李元春生平事实宣付国史馆,列入《儒林传》,以备采择。[7]3-4
另外,《吴愙斋年谱》“光绪二年丙子”条也记述道:“正月二十三日,具折奏请已故大理寺评事李元春明理笃行,请宣付史馆立传。”[4]102吴大澂的奏请很快就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并将李元春的学行宣付史馆,纂入《儒林传》中。
二是上奏朝廷请将清初关学学者王建常从祀孔庙。
王建常(复斋,1615—1701) 也是陕西朝邑人,清初关中著名的朱子学者,与有海内“三大儒”(全祖望语) 之称的周至的李颙(二曲,1627—1705)同时,其学恪守程朱,但因一生隐居不仕,也不外出讲学,故很少有人知其名。但顾炎武居住关中时,常与王建常书信往来论学。王建常虽然在世时名声不显,但他对清代关学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受到后世以程朱为宗的关中学者的推崇。如乾隆初期的关中学者华阴人史调(复斋,1697—1747) 就是因为中举后得王建常《复斋录》读之,然后知“读书非为科名已也,将以求其在我者”[5]116,遂一意于程朱理学的学习,曾先后主讲于西安的关中书院和临潼的横渠书院,成为当时的关中名儒。李元春也说:“复斋不如二曲之高才博学,然醇正精密当在二曲之上。”[7]831贺瑞麟更是称王建常为“国朝关中第一大儒”[1]679,认为王氏之学“规模稍逊桴亭,然纯正则稼书、二张之亚也”[1]842。不仅如此,他还于光绪元年致书吴大澂,请其上奏朝廷将王建常从祀孔庙[1]287。
对于贺瑞麟所请,吴大澂欣然同意。贺瑞麟在光绪二年(1876) 所作的《书〈复斋录〉卷目后》中说:“予服膺先生久,谓先生之功尤在尊程朱以斥陆王,间启告今学使吴县清卿吴公,宜以先生奏请从祀如稼书、杨园例,极蒙嘉诺。”[1]25另外,在《送学使清卿吴公序》一文中,贺瑞麟也说:“朝邑王仲复先生,讲程朱之学者也,公既奏请从祀,旨虽未下而天下已读其疏,必谓能奏请讲程朱之学之人,则亦能讲程朱之学”[1]94。吴大澂奏请王建常从祀孔庙的奏疏的一部分内容,后来被贺瑞麟附在光绪十七年(1891)所作的《书〈关学续编〉王复斋先生传后》一文中①李元春《关学续编·复斋王先生》附有贺瑞麟此文,参见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第105-106页。。吴大澂在疏中说:
王建常恪守程朱,躬行实践,与周至李中孚同时而学问之纯粹过之,精切严整直接明儒胡居仁。又当阳明学盛之时,力排异说,笃信洛、闽,其功不在本朝陆陇其之下。特因僻处一隅,不求名誉,名亦不显于世。然二百年来秦士大夫知有程、朱、薛、胡之学,皆建常笃守之功。……一生得力,实与胡居仁《居业录》一脉贯通,渊源无异。而斥邪卫道,与陆陇其《学术辨》不谋而合,实为宋以后关中第一大儒。……其所著书皆足阐明圣学,羽翼经传。[1]173
吴大澂高度称赞了王建常的学行,认为其学问纯粹过于李二曲,精切严整直接明儒胡居仁(敬斋,1434—1484),而其尊朱辟王之功则不在清初陆陇其(稼书,1630—1692)之下,并指出王建常对于清代关中理学的重要影响,认为清代关中朱子学一脉实为王建常所开创,并推崇王建常为张载之后的关中第一大儒,而其所著之书也都足以“阐明圣学,羽翼经传”。虽然吴大澂的奏议最后没有得到清政府许可,但从中亦可看到吴大澂对阐扬关学的努力。
三是为清代关学前贤王建常和张秉直题写墓碑文。
除了上奏朝廷将王建常从祀孔庙之外,吴大澂还为王建常和张秉直(萝谷,1695—1761) 的墓碑题文。张秉直是陕西澄城人,其学亦以程朱为宗,是乾隆时期关中著名的学者。贺瑞麟在《复吴清卿学使书》中说道:
王复斋、张萝谷二先生墓碑纸裁就呈上。昔雷翠亭先师鋐督学浙右,特题巨碑表张杨园墓曰:“理学真儒杨园张先生之墓”。窃谓复斋先生遯迹高蹈,力守程朱,深醇精密,不亚杨园,而阐明经学似又过之。萝谷生复斋之后,闻风兴起,奋然特立,真知实践,识力高卓,议论精纯,复斋俦也,亦可谓振古之豪杰矣,故敢援杨园先生之例而以是请。[1]286
当时,王建常的墓地已经被其后人抵押给了别人,贺瑞麟的弟子三原人刘质慧(1842—1888)不仅出钱将其赎回,重新交给王建常的后代管理,而且又请人凿石重新竖立墓碑,墓碑之文即为吴大澂所题[1]142。至于张秉直之墓重新立碑的情况未见贺瑞麟有记载,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想必吴大澂亦有题字。
四
光绪二年十月,吴大澂任满而离开了陕西。但他与贺瑞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书信往来,根据目前所见,如光绪三年(1877),吴大澂曾寄给贺瑞麟四幅画及为贺父所作的墓表,这是在其离任之前,应贺瑞麟所请所作①贺瑞麟请吴大澂为其父撰写墓表,事在光绪二年七月,见《清麓年谱》“光绪二年丙子”条(《贺瑞麟集》,第1108页)与《上吴清卿学使书丙子》 (第288页)。。贺瑞麟在《上吴清卿太仆书》中说:“先君家传已拜领,大德之赐,存殁均感不朽矣!画四幅亦收到,尚有所恳书画及社仓记,并冀不弃而终惠之。”[1]294另外,光绪十四年(1888),贺瑞麟弟子宏道和清麓书院学生三原人刘昇之(东初,1842—1888)病殁,因吴大澂在陕西时很赏识刘昇之,故数年后,刘昇之的夫人请贺瑞麟致书吴大澂请其为刘昇之撰写墓表。今《愙斋文稿》中保存有《刘君墓表》一文,即为刘昇之所作,其曰:
贺先生买山清凉之麓,与刘君东初居相近。东初笃信好学,终其身以贺先生为师法。凡四方有志之士负笈来游者,修缮之资皆东初优给之。其最有益于多士者,广求濂洛关闽遗书及先儒绝学孤本,锓版行世,几及二十年,孳孳不倦,搜辑既富,校勘尤精,秦土之得窥正学,而不惑于世俗功利之见,微东初不及此,于世道人心大有裨助,岂一乡一邑之善士可与同日语哉!……余因东初出贤者之门,心窃器之,不可谓“富而好礼”与?今东初之殁五年矣,其夫人瞿氏介贺先生作书,乞余一言以表其墓。……余故乐得而表彰之。……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抚吴县吴大澂撰并书,光绪十有九年岁在癸巳夏四月。[1]204-205
吴大澂之文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可他未想到的是,就在此年九月初五,贺瑞麟就因病去世,不知吴大澂此后是否曾得知过这一消息。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名普通学者与主管一省教育的学政之间的真挚友情及其共同为振兴理学、弘扬关学而作的不懈努力。尽管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吴大澂与贺瑞麟、杨树椿等人在当时仍然坚持“理学经世”的观点显得不合时宜,但却真实反映了晚清时代思想将变未变的转型期时儒家士大夫与普通士人之间的思想观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似乎并未从根本上撼动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的改变,至少对陕西关中地区来说是这样的,而这一局面的改变一直要等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了。甲午战争以后,在咸阳刘古愚(光蕡,1843—1903) 和陕西学使柯逢时、赵维熙等人的努力与提倡下,关学开始由重视程朱理学、强调“理学经世”转向注重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传统理学形态的关学从此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