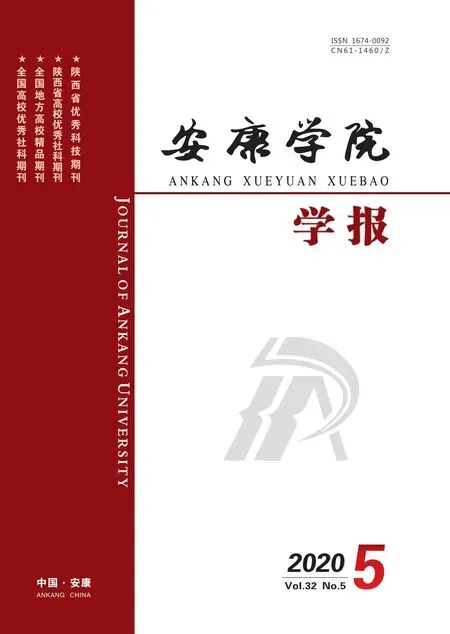《囧妈》: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的回归
2020-12-26余珊
余 珊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囧”系列是以“囧”为话题的公路喜剧电影,它包括了《人在囧途》 《泰囧》 《港囧》以及今年刚刚上映的《囧妈》。“囧”系列以徐峥为核心,囊括王宝强、包贝尔、宋小宝、贾冰等喜剧演员,通过旅途中建立的“伙伴型”关系展现中产阶级人到中年的窘态遭遇,将喜剧效果呈现给大众,从而形成风格鲜明的徐氏喜剧电影品牌。新上映的《囧妈》中的主人公徐伊万和之前的徐朗、徐来一样,面临中年危机,也通过旅途的见闻最终与自我和解。所不同的是,《囧妈》不再将草根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作为戏剧冲突的重点,而是着重呈现价值观念之争。在旅途过程中,争执的双方建立了平等意识,学会了尊重他者,开始尝试沟通和融合,这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的转变。
一、空镜头和特写镜头展现的自然生态危机
“生态共同体”的概念是由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提出的,在他看来,共同体是一个“土地金字塔”的结构,位于金字塔底层的是大地,没有大地,动植物甚至是人都不复存在。这种生态伦理观不仅强调共同体内部各成员间的地位平等,更暗示了充满生命与灵气的大自然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大自然存在于其本身,且自身能够彰显意义,并不需要他人赋予。人类对自然的审美应是表现其本身,而不是把它当成象征人的抽象意识的工具。但在《囧妈》中,它却被拟人化和人格化,在影片的空镜头中,它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配角。当车厢内有夫妻吵架时,窗外的空镜头是零星的白雪、裸露的土地以及突兀的发射塔,自然秩序凌乱不堪,毫无美感可言;当母子重归于好时,大地被厚厚的白雪覆盖,道路两旁是苍天大树,自然风光又充满了异域风情,美不胜收。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风景与人的心境的合二为一,但这种合二为一并非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交互,因为大自然始终是作为陪衬被动呈现出来,它仅仅是人类情绪的投射物。
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着必不可少的养料,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与动植物都生活在自然界,都依赖于它而存在,彼此地位平等,但人类中心主义却将人类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尺度。在他们看来,人类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在地位上理应超越自然万物。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之下,整个生态系统被看作是人类物质的源泉,这必然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动物的栖息地不断萎缩。在《囧妈》中,有一个熊出没的场景,在大特写镜头中,棕熊龇牙咧嘴狰狞可怖。“大敌”当前的时候,徐氏母子下意识地都采取了自我牺牲的策略,为对方争取逃脱的机会。千钧一发之时,棕熊被路人的麻醉枪打倒。影片通过这个场景想要表达的是患难见真情,在众人看来,“难”的制造者是棕熊,但棕熊只是出现在它本该出现的那个仅存的栖息地,作为不速之客的人类却理直气壮地对其进行射杀。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是“属人”的存在,人类以统治者的身份占据着绝对优势,动物不过就是他们的附属,只能任其摆布,生活在由人类“恩赐”的保留地之中。且对于影片而言,森林深处的原生态环境有助于主人公放松心情回忆往事从而推动剧情发展。所以,闯入动物栖息地是情有可原的,射杀更是理所当然,因为只有对立面出现的时候,大家才能放弃争端一致对外,动物理所当然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上。在特写镜头中,人类看似弱小,但他们却手握麻醉枪决定着棕熊的生死,工业文明的成果让他们变成了绝对的强者。实力悬殊的时候,弱者的主体性就会被漠视,所以被击倒的棕熊将何去何从,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徐氏母子最终因此冰释前嫌,即将开启新的旅程。
牛顿—笛卡尔的机械论世界观在近3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带来了辉煌的文明成果,让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但与此同时这种认识论也将世界割裂,严重阻碍了整体世界观的发展。自然界原本与人形成了相互感应的关系,但二元对立的思想把人与自然相分离,将自然看作是可以被掠夺、被支配的对象。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导致了生态危机的频繁发生,人类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出走。
二、人际关系冲突所展现的社会生态危机
公路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一种,它承担着“富有意味的叙事系统的文化意义”[1]。作为公路电影的“囧”系列,其文化意义就体现在旅途过程中所建立的伙伴型人物关系。这种人物关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旅途的搭档在现实生活中南辕北辙,没有任何交集,但封闭的旅途环境却为他们创造了沟通的契机。经过一系列的误会巧合,他们被迫相互磨合,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反思自我,最终找到人生的价值。较之以往,《囧妈》中的伙伴型关系不再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而是真正的母子。展现母子冲突对于现实社会来说,更加具有关照性。面对母子冲突,在开放式的环境中儿子以回避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在旅途当中,尤其是身处卧铺包厢这个局促的环境当中,所有的矛盾都被凸显、激化,无休止的争论最终导致母子相继出走。
人与自然对立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对立,自然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性的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始终贯穿着二元论的思想,当人类位于世界中心,他们开始制定规则,确定自身的权威性,明确他者的从属地位,将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划分成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每个人都争相成为规则的制造者,建立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社交圈。当自身作为绝对唯一的存在时,他就成了“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2],他人只能服从和遵守。在拍摄《囧妈》包厢场景时,影片有意识地采用小全景镜头,让主人公始终处于“顶天立地”的位置,其寓意是在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人都显得多余。
西方启蒙运动重构了人类的社会价值理念,人类凭借理性之光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建构起一个现代化社会。然而,伴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启蒙理性在瓦解宗教秩序的同时又不断神圣化、绝对化,最终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我们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3]人们制定规则的实质是为了设置作为对象的他者,将他者看作是自我意识的外在呈现,对统一化标准的强调就是为了把所有的差异性转化为同一性,在统一的标准之下,人类的差异性逐渐被抹杀,主体性的外化将最终消除他者的客观存在。在《囧妈》中,卢小花的标准是“你是我儿子,必须听我的”,妻子的道理是“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置身其中的当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干涉他人的生活,每个人对于“我”这一主体而言,都成了他者,成了实现“我”的目的或欲望的工具。以徐伊万母子为例,儿子对于母亲的意义,就是帮助其实现生育意志,从而成为母亲在的证据。因此,只有儿子的存在,卢小花才能确定自己的母亲身份,所以在她看来,儿子是从属于自己的。徐伊万的夫妻关系亦然,对于自身而言,对方也只是达成欲望或实现目的的工具罢了。这就形成了人与他人间的悖论,他人既是“我”存在的前提和确证,也是“我”生存的最大障碍,即他者既是自身实现自我意志的场域,但也是展开自我意志的障碍,这必然会导致冲突,进而形成对立,至亲关系因此形同陌路。徐伊万在与母亲、妻子的较量中情绪崩溃大量饮酒,在聚会中行为出格,成了众人眼中的小丑。酒精的麻痹作用终于让他彻底放弃了理性,尽情高歌不再压抑,但因此却成了他人的笑柄。这个看似可笑实则惨烈的场景恰恰展现了现代人的病态,这是社会生态危机直接导致的后果。
三、与自我和解,回归家园
在现代社会,科技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念瓦解了人类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意义,人类的肉体被安放在由钢筋混凝土筑成的稳定建筑物之中,但精神却流离失所。精神的“离乡”成为了现代人的真实写照。面对精神世界的迷失,生态批评给予了人类重新回归的契机。这里的“回归”不仅仅是返回某一个地点或某一个时间点,它更是精神上的皈依,其实质是要解决生态危机,重构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的关系。电影“囧”系列探讨的是人们为什么回归以及如何回归的深远问题,主人公在旅途中历经波折,他想要寻找一条能够通往家园的道路。这个“家园”不局限于故乡,更指涉了能够给人们带来安静踏实的感受,能让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一切介质。家园与记忆相连接,人们走进怀旧的空间,通过追寻生命的本真,打破目前的游离状态,找到意识深处的情感依托,以此弥补现实中的失落。在《囧妈》中,镜头缓推至卢小花家中的照片墙并在此定格,缓推镜头铺垫的压抑情绪与那些黑白老照片交相呼应,强化了时光不再的无力感。那些照片记录的是卢小花在伊宁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那段岁月。在那期间,她作为合唱队的骨干,演出不断,同时又收获了爱情,拥有了儿子,在她看来,那是最值得纪念的岁月,是最为完美的生活状态,但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回归家园对于卢小花而言,是要重温那段充满了生命力的美好时光。记忆中的这段时光自始至终由苏联歌曲串联,因此只有来到俄罗斯,重唱苏联经典,才能找回年轻时的状态,重拾曾经的美好。卢小花执意要去俄罗斯演出,就是为了自我修复,她想以此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紧张焦虑,恢复心态的平和。从俄罗斯返回家中,面对镜子她从容地摘下了之前从未取下过的假发。假发曾让她看起来精神百倍,那是她最后的伪装。影片在此刻有意识地使用了平视镜头,它象征了卢小花最终放下了执念,选择与自我和解。
工业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科技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给人们带来相应的幸福感。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的单向度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世界被割裂为主客体,人类作为主体任意安排、随意宰割,客体只能听从安排,成为被规划的存在。这种以牺牲他人为前提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出现伦理危机。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占使得人际交往变成了利益交换,在由金钱和权力构成的世界里,他者的存在都是对自我的威胁,人们互相疏远、彼此猜疑和敌对,不再互相关心,也无法共享生活的乐趣。“与一种很少区别的社会体系最初共处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多地下降为一种与其他下属体系并行的一种下属体系,在这里,体系机制越来越脱离社会结构,即脱离社会统一借以进行的社会结构。”[4]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也被用于对人自身的奴役。人们试图通过自身的优势实现对他人的全面控制,这就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异化。徐伊万把自己看作是可以改造对方的救世主,想要对妻子全面控制和占有,相濡以沫变成了相互较量,曾经的美好消失殆尽,婚姻走向了解体。所以对于徐伊万而言,回归家园就是要回归自我,要回归到不被欲望奴役的本真状态,在此状态之下人与人之间可以坦诚相见,和谐共处。
生态主义的核心是整体主义。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大自然是由人和自然万物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各成员之间是共生互动的关系,每一个物种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他们都不可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对于《囧妈》而言,无论是怀旧背景下的自我吟唱,还是与他者进行的对话治疗,他们在旅途过程中都逐渐发现了自身的缺陷,觉察了他者的价值,学会了接纳和释怀,达成了与他人、与自我的和解。
四、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最早的公路电影,此类电影以打破旧传统,建立新秩序为主题。随着“婴儿潮”这一代人的成长,此类公路片的主题由反叛转向了治愈,它试图通过诗意的想象来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旅行作为一种人口流动的方式,它对于以海洋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来说意味着出走,代表着希望,但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5]。因此,中国电影在对西方公路片的借鉴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中国公路片中,出走不会带来幸福,归家才能带来完满。
面对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人们努力压抑自己的天性,行为与内心的需求相背离,造成了自身与周遭世界的疏离,进而导致人格的分裂,这种人格分裂主要表现在信仰的缺失、反省能力的弱化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面对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人类的无力感不断增强,自我认同感不断降低,焦虑和紧张成为人们常态化的情绪。这一系列的病症最终导致了人类的精神失衡,引发了生态危机。公路电影借用旅途形式集中呈现了现代人的生活窘境以及因此造成的精神病态。但无论是徐伊万还是卢小花,他们人性的扭曲也恰恰反映了自身对于自我救赎的强烈渴望。为了实现自我救赎,在旅途过程中一方面他们逐渐建立了平等意识。他们学会了尊重他者,不再对他者进行同化和利用,包容了差异性,使其恢复了自主性面貌。影片中徐伊万母子关系的和解,正是从卢小花对儿子所说的那句“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也有自己的人生”开始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逐渐敞开心扉,尝试沟通。在去往俄罗斯之前,主人公固执己见,故步自封,但踏上旅途之后,他们逐渐学会了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通过沟通反思自我,从而打破了边界,修复了隔阂和疏离。这就是徐伊万夫妻怨恨消除的原因,妻子因为丈夫的坦白开始反思自己在婚姻中的过失,最终两人好聚好散。
生态整体主义就是重构人类的主体性,让其从征服者的角色回归至普通人,它承认自然万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倡导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平等互生关系。在《囧妈》中,主人公们在遭遇种种挫折之后,最终学会了尊重与接纳,他们重建了整体主义的生态观念,回归了理想中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