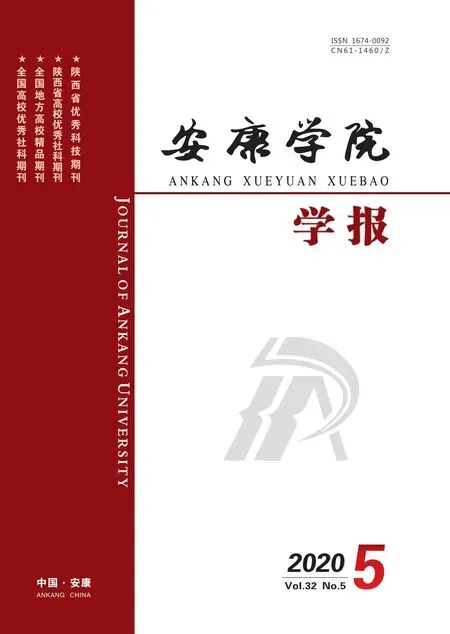路翎前期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2020-12-26熊文
熊 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路翎传》的作者朱珩青曾将路翎的创作来源归纳为民族生命力的启发与人类其他文明的养育,其中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学精神都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胡风的文学思想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指导,多种思想文化交织成一曲和谐的奏鸣曲。朱珩青也指出路翎作品中最为突出的“灵魂搏斗”与基督教“罪—赎罪”教义的相通之处,人物在精神的搏击中成长,在灵魂的抗争中重生,这样的书写在其作品中层出不穷。《财主底儿女们》中基督教教义和用语比比皆是,却鲜有研究者对基督教与路翎的关系做深入探究。本文拟从以《财主底儿女们》为代表的路翎早期创作出发,探讨路翎和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分析其思想的来源,梳理其作品中基督教文化的体现,并从作品透视路翎对基督教态度之转变。
一、路翎基督教文化的来源
1939年发表在《大声日报》的《朦胧的期待》是现今发现的路翎最早的小说,这篇以“流烽”为笔名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具有反战思想的日本飞行员的故事,怀着对家人团聚的“朦胧的期待”,他时常虔诚祈愿,“用一些血抹在照片上,然后开始忍者痛祷告,然而他并不祷告他这无保障底生命,他祷告:一家老小不要饿肚子”[1]。这一将血抹在照片上的动作并非随意的书写,而是基督徒“保护祷告”的一种,十七岁的路翎能够如此详尽地写出基督徒特有的祷告仪式,足见其在少年时代便已然接受过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与影响。现存书信、传记、回忆录能零星散见路翎与基督教的交集:路翎两岁时曾因军阀攻入南京而随家人在明瓦廊基督教城中的会堂里避难,这段经历“多年之后在路翎的头脑中依然留下淡淡的印象”[2],1944年路翎在黄桷镇作办事员时,“房东是木船业主,信奉天主教,每餐饭都要祷告,唱圣歌”[3]。而化铁也在其对路翎的纪念文章《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中回忆了他与路翎在40年代的一整个夏天每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古典音乐晚会的经历,这些生活片段表明路翎和基督教文化之间有着直接的交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路翎的基督教思想还存在以下两个来源。
(一)外国文学的阅读
近代以来大量的西方作品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作品大都有着相似的文化渊源,即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基督教文化植根于欧美作家的血肉之中,并从笔尖流泻而出,亦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生活。
鲁迅、周作人、巴金、曹禺等作家都曾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并主动阅读《圣经》,不少作家甚至有教会学校求学的经历,正如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写到的那样,“这个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人们,是非常的崇拜《圣经》”[4],文中无论是作为政治文化名流的蒋少祖,还是进步青年蒋纯祖,都对《圣经》语录信手拈来。路翎身处那样一个“新的就是好的”的时代,西方的一切都迅速地涌入和流行,阅读《圣经》成为知识分子深入触碰西方文化的极佳媒介。
路翎极爱读外国文学,他的阅读经历始于八岁,九岁时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的节译本,十二岁便开始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除却本国名家名作的阅读,他所阅读的外国文学数量亦极为丰硕。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雨果、普希金、显微克支、高尔基、卢梭、纪德等,这些作家极具宗教色彩的创作都曾被他反复阅读与咀嚼,他曾说过:“外国文学在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是影响和鼓舞着我的”[5]260。他指出托尔斯泰在《克罗采长曲》中显现了“蒙昧的人类,除了宗教,别无拯救”[6]7的思想,也极为看重罗曼·罗兰作品中灵与肉的冲突的书写。《财主底儿女们》初版本的封面便是选自《神曲》“地狱篇”的插图,路翎在创作之时也正读着胡风推荐的让他“觉得受了洗礼似的幸福”[6]61的具有极强的宗教性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与《战争与和平》,路翎后来喜爱的《罪与罚》,更是一部“灵魂拷问式”的“赎罪记”。路翎尤其爱读俄罗斯文学,他自言俄罗斯文学有助于他的美学观念的形成,而“在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中,宗教问题具有决定意义”[7]156,“俄罗斯宗教思想和宗教探索的重要人物主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7]177。通过阅读,路翎触碰和抚摸着基督教文化的纹理,并将其印刻在其创作之中。
(二)胡风及“七月派”的影响
如果说文学作品的阅读使路翎对知识文化和写作技巧有了认识和了解,那真正指导路翎创作实践的却是胡风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自两人1939年相识以来,路翎便“就找到了创作实践上的依据”[7]10,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等理论被路翎的创作所践行,而翻阅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通信书简就会发现,胡风不仅给路翎推荐书目、鼓励创作、帮他出版和发表作品,更批评和指正其创作中的缺憾和不足,而两人的书信中也是随处可见基督教用语:“我大概没有资格到伊甸园去当侍者”[7]43、“书通过,简直是上帝的恩赐”[7]50、“最初的理想者之一、单纯的加利利人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这种心情”[7]59。
纵观胡风的文学思想,其在《罗曼·罗兰断片》中将作家的角色功能譬喻为出现在耶稣之前的“施洗约翰”,即通向耶稣的桥梁,并通过对罗曼·罗兰的评价指出作家的责任是燃起民众力量的火种。在《论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文中,胡风又进一步阐释作家要有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要在人民的心灵中散布火种。可见胡风不仅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思想,并能够自如地转化运用基督教教义为自身的理论和创作服务。路翎延续了胡风的“施洗约翰”般将自己变为到达未来的桥梁与垫脚石的观念,声称“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到达未来的桥梁”[5]2。在此观念指导下的“七月派”创作,也受到了基督教精神的浸润。
胡风的理论来源除却西方文化影响外还可追溯到鲁迅的“为人生”和“国民性”批判等理论。而鲁迅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督教文化中的“爱”与“诚”、忏悔与赎罪、殉道与拯救、灵魂与精神开掘等观念在鲁迅的创作与思想中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胡风看到了鲁迅思想中的精神开掘和灵魂搏斗,并将鲁迅精神的核心概括为“心”与“力”的结合,以此为契机生发出“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理论,一方面强调作家深入到生活深处,与客观生活搏斗,重新铸造生活;另一方面也要求作品中的人物有强烈的主体力量,能够在与社会搏斗的同时进行灵魂的搏斗,修复精神创伤,获得新生和升华,对鲁迅创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汲取了其理论中隐现的基督教精神。“七月派”不少作家笔下都有基督教文化的影子,丘东平便自言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圣经》的宗教”[8],诗人绿原的诗作中更是充满了宗教体悟,虽然不是教徒却与基督教精神有着强烈的共鸣,在“文革”期间还在牛棚中写下长诗《重读〈圣经〉》,阿垅的诗作中也常用《圣经》中的典故讽喻现实。在继承鲁迅精神,践行胡风理论和与友人的密切交流沟通的过程中,路翎对基督教文化无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有了永远饥饿着并灵魂不灭的底层妇女郭素娥,有了矛盾分裂的搏斗英雄蒋纯祖,有了被噩梦缠绕直至疯狂的矿工许小东,路翎作品中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人物都在进行着灵魂的搏斗与精神上的较量。
二、基督教文化对路翎创作的影响
基督教思想在路翎持续十五年的前期创作中或直白或隐约地显现,就路翎而言,基督教文化仅是其作品中的元素,是他表达自己意图的工具,而并非核心。他在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同时将它为己所用,使它为作家的创作与表达服务,以《财主底儿女们》为例我们能看到基督教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 人物
基督教文化对路翎人物的塑造有深刻的影响,除去教徒蒋秀菊、王伦夫妇,作者赋予了《财主底儿女们》中大部分人物基督教文化的特质。王桂英被叫作“安琪儿”,金素痕被描述为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疯狂的蒋慰祖是“地狱的幽灵”,蒋淑媛和沈丽英少时都曾接近过这种她们口中“鬼知道是什么把戏的基督教”[5]454,现在却将宗教抛弃,以享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社会最高的善。资本家王定和也曾信奉过西欧与基督教,虽然他如今的教条变成了“永不接近官僚”。蒋少祖常呼唤上帝,历经了一次次的失望失败后,其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梦破灭,在绝望中领悟“耶稣是这样死去的——他们又看见天国,并且他知道了天国是不可能的”[5]469。迷惘的青年人也愿意亲近宗教,他们将《圣经》看作一种时尚,他们厌恶旧的家庭,甚至认为学校是可恶的,蒋纯祖们“在动乱中成长,早熟,有着毁灭的、孤独的、悲凉的思想”,他们渴望荣誉与爱情,苦闷于现实生活,找不到思想的出路。在战乱中他们狂热与兴奋,“怀着大的虔诚注视这一切”[5]497,认为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有了出路,将自己当作救世者与英雄。作者写道,这个时代的青年大多是在书店里获得人生的启示与天国的梦想的,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他们的理想是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的空中楼阁。蒋纯祖在无数次失败与爬起后一面绝望的指责中国是“官僚、名士、土匪——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一边乐观地安慰自己“这个时代自然有缺点,但是,除了天堂,没有没有缺点的”[5]1105。他怀着救世理想与爱的哲学,而心中高高在上的冰冷英雄主义却与他撕扯,在灵魂搏斗中为自己造了个类似上帝的寄托“克力”,并与他对话。蒋纯祖并非基督徒,但他却是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他害怕罪恶渴求新生,永远处于自我否定与自我搏斗之中,他不怕肉体的消亡,只在意精神的破灭,基督教思想是他分裂的依据,给他救世的理想,也给他灵魂的慰藉,他不信仰它,却从始至终需要它。路翎借助基督教精神赋予笔下的人物复杂的个性,人物与宗教间的遇合显现出性格的裂变,他们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与心灵,在动荡的现实中每个人都成了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
(二) 环境
路翎小说中也存在着一些极具基督教色彩的环境与场景,以此更加深刻地展现出动荡时世之中人的挣扎与强力,绝望与希望。首先便是蒋家儿女们共同的“天堂”:苏州老宅。他们曾拼命地逃离显赫却封建的家族,但在离开后充满了回忆与向往。他们在对故园的想象中重新确认自己的地位,自己仍然是庄严高贵的世家子弟,而不是叛逆的孩子,也不是尘世中沾满罪恶的大人。这种矛盾与挣扎在大哥蒋慰祖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他一次次离家出走,企图脱离父亲的掌控和旧家族的束缚,苏州却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一路乞讨,以一种朝圣般的姿态回去,快抵达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已近在地狱里无耻地活过,因此再也不能回到往昔的天堂”[5]267。在他眼里,苏州是“天堂”,而南京是“地狱”,他决定做一个痛苦的身处于人间的人,以疯癫的方式反抗地狱的吞噬,哀悼天堂的永诀。路翎赋予了文中两个主要场景“天堂”和“地狱”的对立指代,并让人物在此中抉择与徘徊,显现出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的对立。“天堂”是理想主义的幻想,蒋纯祖在演剧队时曾因恋爱受到猛烈的批评,他回击道:“我诚然是从黑暗的社会里面来,不像你们是从革命底天堂里面来!我诚然是个人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卖弄你们底小团体!”[4]782这些虚伪的青年利用革命为幌子肆意攻击,以别人的缺点为快乐,将自己看作无上权威的上帝,而蒋纯祖坚信最高的艺术该从群众的苦闷中诞生。这也是为什么路翎笔下的人物总是要一次次离开“天堂”而深入“地狱”,他们怀着向死而生的勇气,“较之带着理想,宁是带着毁灭。强烈的精神,在黑暗中生活,和周围一切搏斗,是较之理想更能认识现实经验的”[5]531。天堂是不存在的,和地狱相似的旷野,却也是路翎笔下反复提及与召唤的。
“旷野”在基督教的文化中极为重要,《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就是在旷野中漂泊了40年之久后蒙恩的,《马太福音》中亦有关于耶稣在旷野中经受住魔鬼试探与利诱的记载,俄罗斯文学中亦是常见旷野,在广袤无垠的孤寂里,更能试炼出人的精神力度。“旷野”这一场景被作为一种精神的呈现大量的出在新文学之中。《财主底儿女们》中使用“旷野”一词多达111次,路翎让蒋纯祖来到了旷野,并用了大段的笔墨描绘人在旷野之中渺小、虚无的状态,而“产生冷酷的人生哲学同时,这一片旷野便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使徒”[5]547,蒋纯祖在目睹旷野中的残杀和毁灭之后,获得主体意识的成长,从旷野中疯狂又冷酷的人们身上汲取精神的强力。当他被黑暗社会打击后,“他想在江南的旷野里他就应该死去,他想唯有宗教能够安慰他底堕落的、创痛的心灵”[5]814,旷野与宗教都是此时的蒋纯祖所向往的,甚至有了相似的意义,并非只是因为“旷野”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意味,更是由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5]563的状态如宗教一般关涉人的心灵与精神,给人炼狱的洗礼,使人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三) 情节
流浪与复仇是《圣经》中的重要情节,在西方文化中,人类自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开始便被流放,他们带着原罪而生,在罪与罚之间爆发出惊人的个人意志和英雄情结,对不公的一切进行控诉与复仇。流浪与复仇由此成了西方文学中的常见情节,主人公总要经历此般锻造与考验才能获得灵魂的升华。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有着流浪与复仇的经历,这样的写法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就是在流浪中成长的,他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因一句“我信仰人民”而踏上了漂泊的路途,在旷野中因朱谷良的死对石华贵进行精心设计的报仇,而后的一生都处于流浪之中,辗转于南京上海重庆,城市与乡村。蒋慰祖也曾在疯狂中投身难民的行列,在被找回后,面对再婚的妻子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最终成为乞丐在流浪中忏悔。正如钱理群所言:“永不停息地不断向前跋涉‘漂泊者’的形象,这类形象寄寓着人类不满足现状的变革冲动和探索精神。”[9]作品中的人物不满生存状态,通过流浪找寻精神的出路,在流浪的路途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欲望,在苦难中激发自身的“原始强力”与“主观战斗精神”,以缓解被奴役的身心所经历的痛苦创伤,流浪也就成了觉醒的必经过程。而流浪的背后是人物的精神苦旅,这种精神创伤被流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生存挣扎压抑着,越是压抑就越是易燃起因不解命运不公带来的仇恨之感,当遇上变故与刺激,复仇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
朱谷良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有三次复仇,都与流浪后精神力量的激化、主体意识的增强相关联。第一次复仇的起因是石华贵强奸妇女,出于“那种优于全人类”“要站出来执行人类底法律”[5]563的意识,虽燃起了复仇意识却并未行动,当他又一次目睹士兵强奸妇女时,他的仇敌石华贵却站了出来,与士兵搏斗,在手枪对准石华贵胸口之时,朱谷良杀了军官救了自己的仇敌石华贵。这个行为是之前仇恨之火的延续,而他放过有着同样强奸行为的石华贵的行为是一次精神上的复仇,成为一种彰显权威的手段。第二次复仇的对象是杀死同伴丁兴旺的团长,而这一次复仇实际上也是出于在石华贵面前彰显自身权威的需要。第三次则是与自己的仇敌石华贵的对决,他顿悟了自己不该“为内心的羞辱向石华贵复仇,正如他不会向小孩或野兽复仇”,他叫喊着“没有谁能征服我”[5]620,终被石华贵所杀。他的每一次复仇都是错位的,流浪过程中“原始强力”与“精神创伤”的残酷较量使得他迫不及待要凸显自身的主体性,从而使得“正义的审判”带有了主观的扭曲,当他一步步地成为了自我的上帝获得了自我的最大满足,他的复仇意志也就消解了,此时的他失去了“战斗精神”与“原始强力”,也就不堪一击了。而之后所导致的蒋纯祖的复仇,却成为了塑造蒋纯祖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关键。
流浪与复仇交织成沉重的交响,与基督教文化中流浪的意义相契合。流浪者地复仇进一步深化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观念,展现出人物在困境流途中的精神搏斗与顽强意志,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一次次的灵魂拷问带来的心灵冲突中,都体现出来个体的强韧力度。
三、路翎对基督教文化态度的转变
基督教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现代作家却大多不是真正的教徒,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也似乎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一方面作家吸取《圣经》的语言和精神,大量的基督教元素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另一方面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并非一味地肯定与褒扬,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趋冷静中立,甚至批判。路翎本人的精神理想和价值目标是非宗教的,但其作品中却能窥见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的笔下也出现了不少基督徒形象,透过这些寄寓了作者不同态度与情感的人物,路翎对基督教文化态度的转变也得以明晰。
1939年发表的《朦胧的期待》是路翎已发现的最早的基督徒书写,他借一位日本飞行员的反战心理表现了战争之残酷无情,全文并未提及基督徒,但读者能从主人公的行动中确认其基督徒身份,其反战的思想无疑与基督教义有所关联。在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青春的祝福》中,路翎则以教会医院女学生章华云的眼光反映了教会的腐败,内部人员的堕落荒淫,牧师公然出轨、弃病床上的发妻不管不顾,医院副院长为了牟利不顾良心和医德,一心想着榨取患者的钱财。借用教会医院透视当时社会之黑暗,而作为基督教徒的章华云最终觉醒。结尾写到她内心充满着阳光与诗,充满了新生的祈祷:“祝福一切受难的人们,光荣的奋斗……还有这县城,一切人们!你们站起来,走向新生,不饥寒,没有我们那么多弱点”[10]。这样的“青春的祝福”显然也是基督教“救世爱人”思想的体现。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四姐蒋秀菊是一位典型的基督教徒,她只关心自己,对国难冷漠而无动于衷,与积极投身社会的蒋少祖,满怀一腔热血的蒋纯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对比,这反映了基督教徒的麻木自私。而我们再看其丈夫,神学院学生王伦,他认为自己婚姻的最大收获是有名望的亲戚,并将妻子视作美丽的奴隶。他无视国难,渴望进入外交生涯只是为了获得出国研究神学的机会。他在学成之后回国传教,这仿佛也是一条拯救中国的路径,小说虽以蒋少祖的眼光对这条救亡之路进行质疑:“王伦和他底那年青而富有的一群底现代化的国家,将是完全奴化的国家”[5]746,却也可见路翎对基督教思想能否有利于社会的思考。而他在批判基督徒虚伪无能的同时也将基督教作为蒋纯祖们困境中的慰藉,精神的养料。
而路翎1949年发表在《新中华》第12卷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祷告》①《祷告》系笔者发现的集外文,路翎与《新中华》杂志早有渊源,著作年表中提到的收入小说集《平原》中的短篇小说《在一个冬天的早餐》实际上最早发表于《新中华》1948年复刊第6卷第10期上。而《祷告》一文却没被任何年表、目录、书信提及。也是以基督徒作为主角的。文中直接塑造了一位在贫穷困苦中不停祷告唱赞美诗的小学教员,当他的基督徒女儿萌生了逃离家庭的愿望时,他便迫使她祷告忏悔,最终使她软弱屈服,呼喊着自己有罪。他“不是因为信耶稣,而是因为孤独和贫贱”,宗教不过是他们逃离残酷社会的工具。“而邻居里面却有着阔气的少年,酗酒的军官,和新近从战线上逃难来的哀号呻吟的人们,他们都刺激了他。他对着他周围的享乐和炎害愤怒地、憎恶地唱着他的赞美诗。可是这种反抗是徒然的。小学校最近因为时局不好要解散了,他又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可以寄托,因此内心充满了恐惧。”[11]这样短短的几句话,不仅写出了基督教徒信教的虚伪,也写出了他们内心的惶恐无助麻木空虚,还侧面反映了战时社会的两极分化,黑暗腐朽。
这篇文章通过对一个家庭的一场冲突的讲述透视出战争末期人民的精神和生活状态——萧条之气笼罩城市上方,普通市民的惶恐、空虚,军官的堕落失意,难民的痛苦,富人的享乐放纵,虽一笔带过,却也勾勒出了众生百态,极具社会的批判力度。路翎曾在日记体散文《危楼日记》中提及,在1948年12月15日偶见基督教徒的游行宣讲的经历,笔调之间充满了鄙夷:“穿西装的男女基督们,身上每人套着一个白背心,上面写着‘罪’、‘快信耶稣’之类的红色的大字,敲着鼓,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喊着:‘金条靠不住,房产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那一幅虔敬的奴才相突然使我愤怒,就大叫着:不要脸!”路翎也尖锐地指出那些喊着:“换了朝代还是有罪”,“耶稣大头鬼,耶稣大洋钱”的基督徒,不过是“替中国底最后的专制暴君做掩护的”[6]188。路翎目睹了解放前夕社会的民生百态,“敲鼓的,宣讲的,逃亡的,痛哭流涕的,捶胸顿足的,然而,可有谁能够掀动那压在这都城底上面的巨大的,坚不可拔的东西?”[6]189在当时的路翎眼中,基督教与基督教徒成为了黑暗社会与愚昧人心的一个侧面,是推翻旧的世界迎来黎明曙光的绊脚石。
他在1949年给胡风的书信中写道:“南京解放,新天地于数日炮灰后突然出现,感觉上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瞎子突然睁了眼,大约就是如此吧。”[7]146并认为,“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12]。路翎对人与社会的关注,在其创作中也有体现,《祷告》一文便描绘了“瞎子睁眼”前的暗无天日,体现了对人的精神空虚、社会的黑暗腐朽之批判。文章从始至终围绕着这对基督徒父女展开,路翎在此文之前尚未见如此直接显白的以基督徒为主角,基督徒的生活心灵为全文描写重心的作品,这也使得该佚文成为路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有力例证,能为研究路翎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提供材料。
结合这篇作品,我们能进一步理清路翎对基督教徒态度的转变。1939年路翎尚且是个理想而浪漫的青年,在《朦胧的期待》中借基督教徒的反战心理表现战争的残酷与对和平之向往,基督教文化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对战争的长期化,路翎对于现实有了更为冷静的思考,对基督教文化呈现出褒贬混杂的含混态度:《青春的祝福》里一边批判教会的腐朽一边体现救世爱人教义,女主人公结局仍是以“爱”给予“青春的祝福”。《财主家底儿女们》指出了当时人们对于教会学校的驳杂态度:“南京的人们,由于惶惑和嫉恨异端,是憎恨着把几百个少女聚在一起的这种宗教的、学术的企业的……年轻的男子们把它看成迷惑的泉源和温柔犯罪的处所,另一些人把它看成妖精的巢穴。第三部分人则在自身的惶惑里歌颂它,显示出爱好自由的高尚风貌来”[5]420,并通过王伦这个人物对基督教救世之路进行了探讨,但路翎此时对基督教的态度显然已转向否定。而《祷告》中则将基督教视作蒙蔽人心的工具,对其作了坚决批判。可以发现,路翎对基督教徒的书写走向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基督教文化成为现实社会的“绊脚石”,浪漫主义的色彩被削弱,作品中的现实意味也愈加浓烈。他在1944年书信中便已表示:“对于小说及小说的做法,我实在觉得腻了……我认为只要不是混蛋和可怜虫,都应该直写人生,花巧越少越好”[6]113的写作态度,这样的转变实际上是路翎的创作减少“理想主义”的色彩,越来越走向“直写人生”的现实书写的体现。《祷告》写出了“黎明前”人民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普通市民的惶恐、空虚,军官的堕落失意,难民的痛苦,富人的享乐放纵,虽一笔带过,却也勾勒出了众生百态,对社会的批判极具力度。对基督教徒与基督教文化态度的转变之后显现出的是路翎用文字为武器去“掀动那压在这都城底上面的巨大的,坚不可拔的东西”的文学理想。
四、结语
路翎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梳理其与基督教的关系能为更好地理解路翎提供新的视角,现存传记与年谱中虽未见路翎与基督教的深入接触,我们却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发现鲜明而强烈的基督教元素。路翎在其并不长久的创作生涯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以基督教文化为切入点对路翎创作进行解读,有助于路翎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