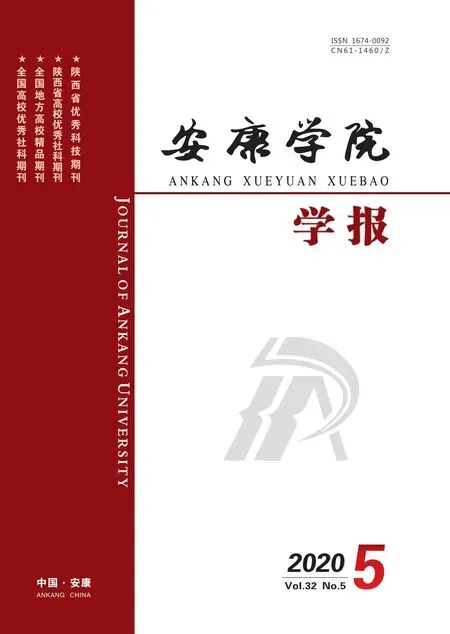论苏辙《古史》对司马迁《史记》的重新书写
——以尧舜故事为例
2020-12-26王兴武
王兴武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两宋是我国史学发展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兴起了著史的热潮,著名的史书如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薛居正编修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 《新五代史》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以至于陈寅恪先生曾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272,认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在赵宋一代达到了极点[1]277。苏辙的《古史》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苏辙在自传中这样阐述其作《古史》的缘由:“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 《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2]1017在《古史自叙》中,苏辙详细叙说了其作《古史》的目的:“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来,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 《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故其记尧舜三代之事,皆不得圣人之意……余窃悲之,故因迁之书,上观《诗》 《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记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呜呼,由数千岁之后,言数千岁之前,其详不可得矣。幸其犹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为作也”[2]3。可见,苏辙为了弥补《史记》“不得圣人之意”的缺憾,故在《史记》的基础上参考它书,对上古三代以至秦始皇的这段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名之曰《古史》,以使历史更加符合其心中的“圣人之意”。本文在对《史记》与《古史》作宏观比较的基础上,以尧、舜故事为例来分析两书的异同,旨在探讨苏辙作《古史》的得与失。
一、苏辙《古史》对司马迁《史记》篇目的增删调整
苏辙《古史》六十卷,本是依司马迁《史记》而作,但苏辙在《史记》的基础上,对相关篇目做了调整与增删,以补司马迁作史的缺失。篇目调整主要有三类:
(一)增加篇目
司马迁《史记》第一篇为《五帝本纪》,苏辙《古史》在《五帝本纪》前增设《三皇本纪》记伏羲、神农、黄帝三人事迹,“复记少昊于五帝首”[2]6将司马迁阙而不记的历史延伸至更为渺远的三皇时代。在列传部分,增加了《柳下惠列传》 《曹子臧吴季札列传》 《晋范文子列传》 《晋叔向列传》《郑子产列传》 《叶公列传》等人物传记。苏辙根据《左传》补入这些人物传记,丰富了春秋时期人物群像。
(二) 删减篇目
苏辙《古史》删去了《史记》中的《司马穰苴列传》。苏辙认为《史记》所载的司马穰苴事迹取材于《战国策》,而《左传》中并没有相关记载,因而不可信,正如苏辙在《古史自叙》中所说:“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 《诗毛氏》 《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战国之际,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一时之说,迁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传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己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着,迁亦未暇详也”[2]3。叶适曾曰:“《左氏》前后载齐事甚详,使有穰苴暴起之功,不应遗落也。况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时所无。大司马亦非齐官,迁故称‘田乞豹由此怨高国’,若不考信于《左氏》著,盖作书之人夸大其词,而迁信之尔。”[3]钱穆也称《史记》所载司马穰苴事迹是“史公特误其时,又误其事耳。”[4]可见,苏辙在《古史》中将司马穰苴列传删去是正确的。
(三) 调整篇目
苏辙作《古史》时对《史记》部分篇目做了调整,如改《管蔡世家》为《蔡叔曹叔世家》,改《越王勾践世家》为《越世家》,改《晋世家》为《晋唐叔世家》,改《平原君虞卿列传》为《平原君列传》,改《鲁仲连邹阳列传》为《虞卿鲁仲连列传》,最能体现苏辙思想倾向的是他将孔子从《孔子世家》降为《孔子列传》,并将《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更名为《老子列传》,置于《孔子列传》与《孔子弟子列传》之后,《孟子孙卿列传》之前。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之中,体现了其尊慕孔子之意,苏辙的调整虽然更符合史实,但也显示了其尊崇佛老的思想。
二、《古史》中尧舜故事的重新书写
尧舜作为古代帝王的典范,代表着古代社会最崇高的美政理想。尤其是舜,其生活在“父顽,母嚣,弟傲”[5]26家庭环境之中,却能恪守孝道,不至奸邪,最终受到尧的禅让而得以摄行天子之政。尧舜生平事迹,在《尚书》和《孟子》中有相关记载,并成为《史记·五帝本纪》取材的重要来源。由于《史记》的巨大影响,《五帝本纪》中所载的尧舜故事逐渐成为后世的权威版本。但随着北宋中后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勃兴以及当时士人对三代之治的倾力求索,《孟子》所载虞舜事迹引发了两宋学者的诘难和论辩[6]。苏辙在《古史·五帝本纪》中对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尧舜故事的重新书写,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一)史料的去取:尧舜事迹的改写
苏辙在《古史自叙》中就称司马迁“记尧、舜三代事,皆不得圣人之意”[2]3。在《古史·五帝本纪》后的“苏子曰”中更是对司马迁进行发难:“学者言尧、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2]11“三妄”指的是“舜不告而娶”“舜之父瞽叟与弟象焚廪掩井”与“舜让辟尧子丹朱”之事。“舜不告而娶”事见于《孟子》:“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7]宋人对此事多有质疑,如《邵氏闻见后录》就记载苏轼曰:“自舜以来,如瞽叟者,盖亦有之,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缘礼而不得其妻者,天下无有也”[8]。司马迁《史记》未采《孟子》之说,这也是苏辙认为“太史公得其一”的原因。
《古史》对尧舜事迹的改写主要集中在苏辙所说的“太史公不得其二”的焚廪掩井与舜让辟尧子丹朱这两件事。首先来说焚廪掩井之事,司马迁《五帝本纪》载:
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5]40
对于此事的真实性,宋人多有质疑,以为此事悖于情理。如程颐就曾说:“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说,恐未必有此事,论其理而已矣。尧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亩之中,岂容象得以杀兄,而使二嫂治其栖乎?”[9]欧阳修也曾说:“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俚巷之语也。”[10]司马光在《史剡序》中的质疑更加详细:“顽嚣之人,不入仁义,则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叟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叟岂不欲利其子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人,亦不可得已,借使得杀之,瞽叟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此特闾父里妪之言,而孟子信之,过矣。后世又承以为实,岂不过甚矣哉?”[11]苏辙在其《孟子解》中也道:“吾以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论也。”[2]956并认为“孟子盖失之矣,世岂有不能顺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2]11因此在《古史》中将这件事删去。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评价曰:“《史记》载尧妻舜之后,瞽叟尚欲杀舜。《古史》本《尚书》‘瞽亦允若,尧闻其贤,然后妻之’于理为长,和从《古史》。”[12]347从事理的角度来看,《史记》中记载的瞽叟在舜被尧举荐之后还想杀舜的事情确实有乖谬之处,苏辙《古史》阙载此事,确实更加合乎情理。
关于舜让辟尧子丹朱之事,《史记》载: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5]36
司马迁对尧舜禅让的故事颇为称赞,《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的第一篇都与避位有关,可见司马迁心中,避让是其称慕的权位继承方式。《史记·五帝本纪》虽然着重写了舜天生具有的异乎常人的才能以及丹朱的不肖,突出舜即位是天命所为,不可改变,可还是写了舜避让丹朱之事,显示了司马迁对避位禅让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除了写舜避让尧子丹朱之事外,在舜死之后,还写了禹让舜子之事:“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5]52。让这种理想的权位继承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可见,舜避丹朱之事寄托着司马迁美好的政治理想。
舜让辟尧子事最早载于《孟子》,而《尚书》中却没有记载。随着孟子在宋代地位的提升,加之当时兴起了疑古思潮,宋人对这件事也多有怀疑。苏辙《古史》中弃此事不载,反映了其对此事的态度。正如朱熹所指出的:“如苏子之言,则是凡世之为辞让者,皆阴欲取之而阳为避逊。”[13]3499苏辙不仅对司马迁所记舜避让尧子之事产生怀疑,而且认为司马迁的记载有损于舜的形象,这也是苏辙批评司马迁所记尧舜事“皆不得圣人之意”[2]3的原因之一。
(二)由天命到仁义:尧舜禅让内涵的重构
对尧舜禅让之事,司马迁是极力称赞的。在司马迁看来,舜接受尧的禅让是天命所定,反映出司马迁崇尚天命的思想。在《史记》中,尧在将帝位传给舜之前,对舜进行了多方考察:
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5]26
舜生活在一个“父顽,母嚚,弟傲”的家庭环境中,并且父、母、弟还想杀舜,舜自小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养。而舜却能“烝烝治,不至奸”[5]26,并能在尧考察他时将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了不同常人的高尚品格与治理才能。并且进入山林草泽,遇上暴风骤雨也不会迷路,使尧认为他身上具有圣人的品质。舜的这种杰出的才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司马迁为了进一步突出舜与众不同的帝王气象,又从“舜目重瞳子”[5]428这一异于常人的特征;尧的嗣子丹朱顽凶不肖,不足以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5]36;与舜让丹朱,而“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5]36三个方面层层递进,突出舜继尧为帝是天命所定。
在《古史》中,苏辙认为舜可继尧的原因是舜的仁义,而不是天命。苏辙曰:“世岂有不能顺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则舜之为庶人,既已能顺其亲,使不至于奸矣。父母兄弟之际,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顽父、嚣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亲,惟至仁能之。此尧之所以用舜而不疑也。”[2]11因此,苏辙《古史》在写尧舜禅让时,舍弃了司马迁所记载的舜父、母、弟皆欲杀舜的记载,而这样记述:
父母爱象而恶舜,遇舜不以道。舜事父母抚弟,笃于敬爱,瞽犹不顺。舜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祇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亦允若,不至于奸。[2]9
面对父母的厌恶,舜仰天大哭,深切自责之后又恭敬恐惧地回来见瞽叟,最终感动了瞽叟,《古史》突出了舜至仁的品性。
《史记》中舜因为具有深入山林遇上烈风雷雨也不会迷路的能力,使尧认为他是圣人,进而更加坚定了尧要将帝位传给他的决心。而《古史》中则写道:
尧闻其贤,妻之二女,以观其内;事之九男,以观其外。二女不敢以其贵骄,而九男皆益笃,尧知其圣人也。[2]9
在《古史》中,尧以为舜是圣人的原因是尧之二女九男在舜的仁德的感召下养成了不以身份高贵而骄傲,并且日益笃诚忠厚的良好品性。苏辙舍弃了《史记》尧舜故事中带有尚奇色彩的天命观,而将舜继尧位的根本原因解释为舜具备圣人之德,在对史料的取舍中体现出宋代崇尚礼教的社会风气。
(三)由详到略:叙述语言的重组
苏辙《古史》不仅对司马迁《史记》中尧、舜故事进行了改写,使其更加符合圣人之意,而且在叙述语言上也更加简省洗练。例如在叙写尧时,司马迁《史记》载: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5]18
司马迁为了突出帝尧的崇高品德,在叙述时使用了带有夸张色彩的语言,而苏辙在写《古史》时全部删去。
又如舜在即位以后,制定历法,教民耕作,司马迁写道: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困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5]20
而苏辙在《古史》中则改为:
尧乃复育重、黎之后,曰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平秩四方,以正四时;允釐百工,庶绩咸熙。[2]8
《古史》对《史记》的叙述语言做了简化处理,使之更具概括性。这种详略繁省的差异在《史记》与《古史》中出现较多,不必一一胪列。但总的来看,《古史》在叙事上虽较《史记》洗练,但不如《史记》叙事清楚。司马迁《史记》中记述的一些事件,如瞽叟杀舜虽经不起推敲,但却使叙事更加生动,也有利于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苏辙删去的一些细节虽然体现出其对史料的甄别,但也使《古史》的语言较《史记》逊色不少。正如黄震在《黄氏日钞》中指出的,“是以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文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12]347。
三、苏辙作《古史》的得与失
通过与《史记》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辙作《古史》时,不仅在形式上对《史记》的篇目作了调整,更在内容上对《史记》中的史料作了甄别与增删,以求追录圣贤之遗意。《古史》成书后,后人对其褒贬不一。如南宋的朱熹就对此书颇为推崇,称其为“秦汉以来,史册之言近理而可观者,莫若此书”[13]3496。清人王王士禛也说:“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记》外则有苏氏《古史》……凡此诸书,皆当兼收并采,不可以其不列学官而偏废之。”[14]《四库全书总目》在提到《古史》时,也称其“去取之间,亦颇为不苟,存与迁书相参考,亦无不可矣”[15]。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就曾感叹:“《书》阙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5]54-55《古史》在《史记》的基础上,“上观《诗》 《书》,下考《春秋》,及秦汉间杂录”[2]3,并融入了苏辙对一些史料的思辨,对《史记》中的一些史实有所补正,其存史之功是毋庸置疑的。
但苏辙在作《古史》时自视甚高,其以“追录圣贤之遗意”为作史宗旨,以为“尧舜三代之遗意,太史公所不喻者于此而明;战国君臣成败得失之迹,太史公所脱遗者于此而足”[2]470,并批评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其记尧舜三代事,皆不得圣人之意”[2]3,这一点颇受后人指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指出:“然其称迁浅近而不学,疏略而多信,迁诚有可议者,而以为不学浅近,则过矣。”[16]黄震在其《黄氏日钞》中更对苏辙所说的“得圣人之意”的作史宗旨提出了质疑:“然则苏子正惟不以圣人之施于治者为道,而必欲他求其道于荒忽无形之中,不以太史公载圣人之治为足,而必自指其荒忽无形者,为得圣贤之遗意,此《古史》之所作欤?”[12]347黄氏接着进一步指出:“呜呼!以是为得圣人之意,《古史》不若不作之俞也”[12]362,从根本上对苏辙《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的宗旨作了否定。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不能说全都客观,但基本上切中《古史》得失之要害。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指出:“苏氏之学的特点是融合儒、释、道三教于一家之学。”[17]这在苏辙《古史》中有突出的体现。苏辙在《古史自叙》中说:“古之帝王皆圣人也,其道以无为为宗。”[2]3接着又引用孔氏之遗书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3,体现了其糅合儒、道的思想特点。加之苏辙在编《古史》时,将孔子的传记从世家降为列传,列于叔向、子产传记之后,又将老子独立成传,列于孔子弟子的传记之后,并在老子传记后的评价中说:“三代之后,释氏与孔、老并行于世,其所以异者,体道俞远而立于世之表”[2]316。不难看出,苏辙所追录的“圣人之意”实际是糅合儒、道、佛思想而构建的一种道体观[18]50。其所谓的“圣人之遗意”也仅是其一家之言。朱熹说其:“特以老子、浮屠之说论圣人,非能知圣人之所以为圣。”[13]3496-3497可谓一语中的。
四、结语
总而言之,苏辙由于不满司马迁的《史记》,故在《史记》的基础上作《古史》,想要补《史记》之阙,明圣人之意。但苏辙《古史》成书后,后人却对其颇多非议。客观地讲,苏辙对一些史料的甄别和取舍虽然有正《史记》之讹误、补《史记》之阙载之功,但《古史》并未真正达到苏辙所追求的阐明圣人之意的目的,苏辙也并未取得如司马迁那样的史学成就。即使从语言上看,《古史》的语言也没有《史记》那样富有表现力与文学性。但我们不能否认苏辙在《史记》的基础上编纂《古史》的意义。作为宋代史学繁荣背景下的产物,苏辙的《古史》体现了宋儒疑古辨伪的治史特点,苏辙仿效《史记》的“太史公曰”,在《古史》的每篇末尾也加入了“苏子曰”,这些“苏子曰”充分体现了苏辙的史学主张与两宋史学义理化的特征,这对南宋朱熹史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专门创作《古史余论》,推崇其为近世以来言史者中唯一近理之书。由此言之,无论是探索两宋义理化史学的发展,还是研究两宋史学思想的演变,《古史》均具有重要价值[1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