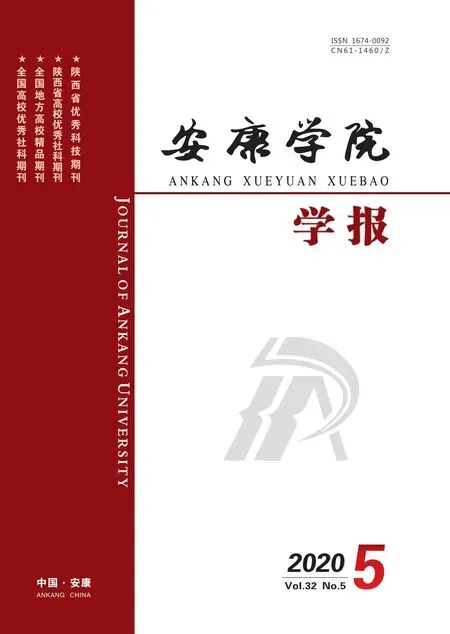温柔敦厚的美学质地
——论李春平的盐道题材小说
2020-12-26侯红艳
侯红艳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盐乃“食爻之将”“百味之首”,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苏联塔塔里诺夫说:“人类没有火箭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没有盐是不可思议的。”[1]盐之于人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更是一种精神财富,由此衍生出的制度、产品等共同构筑了内蕴丰厚的盐文化。弘扬中华盐文化必须扩宽研究涉猎范畴,特别是关注和探究关于盐物质的文学作品,通过文本的研究挖掘和推广盐文化。从张荣生编著的《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看,自汉代早期开始出现盐文学以来,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体裁的盐文学作品共计有1450篇,其中长篇小说仅《自流井》一部。在《〈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绪言》中,张荣生认为:“《自流井》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井盐文化的代表作品,它矗立起中国盐文学史的新峰巅”[2]。继《自流井》之后,先后出现了刘成的《盐女》、田永红的《盐号》和李春平的《盐道》《盐味》等长篇小说体裁的盐文学作品。
李春平的《盐道》和《盐味》以隐匿在秦巴崇山峻岭间的历史遗迹镇坪古盐道为依托,通过温情的叙事手法,为读者讲述了一段前所未闻的盐道传奇,再现了巴山盐背子们真实的生存图景和精神样态,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在整个文本创作中,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李春平既没有采用欲望化、审丑化的市场写作思路,也没有玩弄新奇的叙事技巧,而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通过温情的语言叙述了巴山盐背子家族的日常生活琐事,作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稳定、朴实、平和的审美追求,即温柔敦厚的美学质地。温柔敦厚是儒家审美思想的集中展现,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3]后来逐渐由诗教原则演变为审美趋向。李春平是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作家,戴承元曾经发表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李春平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渗透》一文,专门论证了此问题。作家本人也多次表示小时候在父亲耳濡目染下独爱儒学。受此影响,在盐道题材小说中,李春平除了在内容上表现出尊崇儒家思想的倾向外,在作品的审美格调上也彰显出温柔敦厚的美学质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发生新的变化:基于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茁壮成长,逐步占领了整个文学叙事场域,文学生产的商品性更加突出,从创作到出版,从出版到阅读,都充斥着对虐恋情节和惊悚场景的渴望,身体、暴力、血腥、时尚,乃至性成为消费社会的文化符号。受市场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指向的影响,许多作家不惜放弃自己崇高的文学理想,忽视文学的精神质地,而将其彻底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导致“三俗文化”一度泛滥。在当今消费至上的社会大语境下,能坚持忠实于自身的文学抱负,用文字铸造人类精神大厦的作家是值得钦敬的。李春平在《盐道·后记》中写道:“几十年来,我的创作走过了一条农村——城市——官场的路子,到了应该转型的时候了。于是,我的寻找便具有了求新求变的目的。寻求的目标就是,多一些文化内涵,多一些历史记忆,多一些艺术上的纯粹。而这类作品通常又是不受市场欢迎的。那么,我就得放弃市场的考虑,为纯粹的艺术创作而努力了。”[4]294
在“为艺术创作而努力”的文学信念指引下,李春平把小说题材转向了具有历史文化意蕴的镇坪古盐道。这是一条位于陕西省最南端镇坪县境内的古盐道,它起源于距县城南约45公里的重庆市巫溪县大宁河盐厂,全长共计153公里,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布满了栈道石孔,以山间石板路为主,异常艰险,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古盐道之一。据历史记载,镇坪古盐道大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从巫盐产生就有,“巫盐发现初期……时间在五千年前,约与中原的黄帝相当”[5]。2011年,镇坪古盐道作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的27个古遗址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录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2014年,镇坪古盐道被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烙下盐背子们层层叠叠脚印、浸满他们斑斑血泪的古盐道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一片废墟。李春平说:“古盐道留存的东西太少,而民间不系统的传说太多,甚至杂乱到无法整理的程度。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段历史可能是最佳的方式了。”[4]296
那么,到底以怎样的文学形式来表现这段历史,即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李春平思虑的又一个问题。每一位文学创造者都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文学与生活之间建构属于自我独特的艺术创作观。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派文学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坚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背离,他们主张反对传统,过分强调想象、虚构等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甚至肯定文学对现实生活的颠覆与消解,热衷于运用新奇、怪异的叙事手法来表现人性的异化和生活的荒诞。在盐道题材小说中,李春平把这种“先锋”不动声色地搁置起来,坚守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他始终以表现时代为己任,将普通人物(盐背子)的日常生活纳入文本叙事中,还原了一个时代的原貌。
正如迟子建所说:“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而是体现那些共性甚至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这里包含着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6]李春平的盐道题材小说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具有共性的盐背子家族的日常世俗生活上。《盐道》的核心人物崔无疾是盐背子,他的爷爷、爹爹以及三个儿子都背过盐。更有趣的是,他们家的三个女人(崔无疾的老婆及两个儿子的老婆)都是从盐道上得来的。正如小说中所写:“盐,构成了他(崔无疾)的家族史和个人史的各个章节。他身上的每一处都与盐有关,他家的每一件家具都与盐有关。”[4]82《盐味》中除了每天摆弄着盐罐罐的奶奶,还有主人公张迎风和林万春,他们都是盐背子,两家人也是因盐而结缘,由邻居发展为亲戚。
总之,在《盐道》和《盐味》中,所有人都与盐有关、与盐道有关,他们或是盐背子,或是盐背子的家属。在大巴山,盐背子曾经是最普通的生存群体,他们主要以背盐、运盐为生存手段。作家李春平小时候就见过许多盐背子,他本人也是盐背子的后代。现今,随着社会的进步,背盐逐渐退出时代舞台,盐背子也随之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勤劳、仁义、诚朴、善良和坚毅而乐观的品质,却最终成为这一区域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样态。评论家谢有顺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人转瞬间已成为过往,芸芸众生的身影在历史的困境中悄无声息地存在着,然后又被巨大的历史大潮裹挟而去,终而弥散。谁为他们的存在作证,去勾勒出他们那依稀的背影,去聆听他们在历史中心之外的边缘的声音?文学是人学,是个体心灵的历史,文学是对人的精神的关怀和烛照,是对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一种深切的关怀和体认。”[7]盐业研究员邓军认为:“(川盐古道研究) 注意对‘人’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对沿线的背夫、挑夫、船工、马帮、盐商等运盐群体及盐业家族、盐号、商号等盐运组织进行研究。”[8]李春平的盐道题材小说通过关注巴山盐背子这一普通的生存群体,展现巴山人民生活的苦难,诉说他们的心灵独语。在谈到《盐道》创作动机时,李春平说:“在《中国盐业史》 《巫溪盐业史》 《抗战中的中国盐业》等诸多的历史著作中,几乎都没有涉及盐背子的生活。也就是说,盐背子或运盐人是历史研究者所忽略的重要层面”[4]296。
李春平的盐道叙事主要聚焦于盐背子家族的生活日常。在《盐道》 《盐味》中,读者看不到轰轰烈烈、海誓山盟的爱情,也看不到感天动地、惊悚恐怖的场景,本文呈现出的主要是平凡庸常的人生。他们忙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等。《盐道》中的崔无疾,子承父业,为了养家糊口,他背着父亲死后留下的背篓,带着儿子去背盐;崔张氏每天养猪喂鸡,缝衣做饭,与老头斗嘴,等儿子背盐回来;儿媳们在婆婆的带领下,团结和睦,一起上山打猪草、相互开玩笑,唱山歌,说趣事,争抢着孝敬双亲,在家玩耍时还经常拿孝顺来打赌,赢者为父母洗脚;崔家三儿子崔小岭添女儿了,干伢王国江带着小老婆唐幺妹从四川巫溪到陕西镇坪,给干儿子添女儿“打三朝”,带来了贵重的八色礼。《盐味》中的日常生活更是丰富,年过百岁的张家奶奶,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空闲了就抱着家里的坛坛罐罐摇晃,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或有多少东西;盐背子林万春为了帮助发小张迎风解决生活困境,带着他去背盐,不幸却意外“失踪”,林万春为了弥补过失,表达歉意,缓解张妈失去独子的悲痛,他不惜将自己“赔”给张家,肩负起照料张家老小的重任,对张迎风的女儿臭臭,视如己出,疼爱有加……这些故事都饱含着丰沛的情感和朴素的思想,以及人文风情的元素,将仁爱、道义、伦理等传统文化蕴含其中,使生动的叙事和深厚的思想相得益彰,在盐背子的日常生活中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
二、对真善美的坚定信仰
李春平是一个善良而感性的作家,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有一个“道”,这个“道”就是对真善美的坚定信仰。正如评论家吴义勤所说:“在当今的中国,如果要评一个‘温暖’、阳光的文学‘形象大使’的话,迟子建当之无愧”[9],笔者认为,李春平亦然。熟悉李春平作品的读者,肯定都有一个共同的阅读印象:温暖。这大概源于作者对真善美的坚定信仰。这种坚守使李春平的盐道题材小说中盐背子们平凡庸常的生活透射出一种让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
在盐道小说中,李春平除了讲述一段精彩传奇的盐道故事外,还不遗余力地展现大巴山盐背子生存的自然环境。“整个大巴山就是这样一个折叠的奇妙产物,所有的神奇和深邃都呈现出明显的折叠之后又再度拉伸的自然效果。笼统看去开始漫无边际的绿色,是空旷幽远的苍茫,这些绿色和苍茫厚重而缠绵,舒展而蓬松。”[10]2“大巴山的秋天是分期分批进入的,通常是一半春色一半秋。在同一座山上,上半身还是碧绿,下半身就泛黄了。”[4]1磅礴雄浑、神奇险峻的大巴上,在作者饱含诗意的笔墨下可亲可爱,仿佛每一个细节都是灵动的、活跃的,我们能够看到巴山的绿、巴山的黄,听到巴山的空寂与苍茫。
除大巴山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从森林和河面上穿越而来的夏风,飘荡在山涧的鸟鸣声,以及大片的向日葵地,“向日葵……向天地绽放自己与生俱来的色相,然后以挺拔的身躯、舒展的姿态、微笑的面容,以自己高贵的黄色来诱人,它自始至终不媚不俗,不卑不亢”[10]90。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融洽,大巴山上的自然清丽而丰盈。其实了解大巴山的人都知道,对于盐背子来说,当时生存的自然环境是很恶劣的,盐道都是在悬崖绝壁上,且宽不盈尺,如果迎面走来一个人,得歪着身子给对方让路,屁股稍大点或者屁股稍撅高点,就会撞在路旁的岩石上,且高一脚低一脚,稍不留神,则命断黄泉。据说盐背子摔死的很多,路上还经常遇到野兽、土匪等。源于作者对真善美的信仰,他在自然描写中有意识地淡化了自然的艰险,而无限放大其优美的一面,将其置换成隽永的文化镜像和诗化的精神家园。作者这种“以轻击重”的叙事手法大大增加了文本的精神厚度,将巴山盐背子的生存之痛沉淀为一种沧桑的力量之美和生活之美。这既表达了作者对大巴山自然风物的赞美,也突出了盐背子们积极乐观、坚忍不拔的生活态度。
对真善美的坚定信仰,一方面表现在对大巴山自然美的描写,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大巴山盐背子光辉人性的颂扬。《盐味》中张黑娃家里被土匪抢光,两天没吃饭,跑到林万春家偷吃的,结果因为胆小没成功,张妈为他端出一大碗剩饭,离开的时候,还送了些吃的给其生病的母亲;《盐道》中正直、善良、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崔无疾,对土匪恨之入骨,但当看到倒毙山间的山大王时,却吆喝同伴为其收尸,努力把他埋成人的样子。“小时候,我听父母和其他乡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人要讲仁义’,颇像鲁迅先生挖苦的那样‘满口的仁义道德’。可是,乡亲们口中的仁义道德真不是虚假的,他们就以‘仁义’修身齐家,‘仁义’是他们骨子里的精神秉持,是崇高的日常行为操守。”[11]“确实,李春平笔下的山民颇为类似于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及‘湘西’人物,基本都以淳朴、善良、热情、勤劳的生命样态显现于山野之间,给人的印象是‘暖男’不少,‘暖女’亦多。”[12]
对李春平来说,人性应是善良的,生活应是饱含温暖的,面对生活,他从不苛刻,而是用理解、包容和宽宥去探寻生活,审视人性。尤其是对待男女感情,他更是完全站在超越道德的人性角度去表现。《盐道》中春儿与已婚崔小岭的私情;《盐味》中左木匠与陈氏的暧昧,被女儿鄂鄂知道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而被女婿林万春知道后,对陈氏更加敬重和关心。在作者笔下,这些男女爱情故事自然真实又合乎情理。这也许是李春平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生活和人性做出的善意诠释,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善意浓情的乌托邦世界,奠定了小说温暖柔和、中性自然的叙述基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善意的诠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理想主义倾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说的诗性和温度,却削弱了文学的批判性。
三、贴地而飞的文学姿态
“许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是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中国人的人生观。”[13]土地和历史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犹如儒道两种思想一样,伴随一生,受益一生。特别是前者的土地情结,它是一种深入到骨髓深处的精神遗传,一种集体无意识。李春平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我是一个有故乡情结的人,我在上海或外出旅游疗养,看见外面的山水就会想到家乡。……如果能为故土的建设出力,也是一种尽孝。”[14]在盐道系列小说创作中,作者取材于生养他的秦巴山区,通过讲述镇坪古盐道的故事,表现这一方水土独特的民俗风情。笔者将这种扎根故土的写作态度概括为一种贴地而飞的文学姿态,而这个“地”特指故土,无论作者的文学世界有多远、多大,但写作的根始终扎在秦巴乡野中。
具体到《盐道》和《盐味》中,首先表现为对大巴山巫文化的集中展现。李春平出生于陕西南部,从自然环境讲,这里北通秦岭、南依巴山、气候温润、植被繁盛,地处世界北纬30°神秘文化圈,适合巫文化滋生和传播。《华阳国志·汉中志》载有:“西城(今安康)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同。”《汉书·地理志》则记录:“汉中,楚分也,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伐山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信巫鬼,重祭祀,与巴蜀俗同。”[15]从《盐道》的第六章至第十五章,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民间巫术。盐道上的著名巫师崔小岭通过跳端公帮助干伢王国江成功收拾了给别人家竹笕里塞石块的郑拐子,三天后,他家的盐锅奇怪炸裂;崔小岭在家帮母亲给小猪做法,小猪们“一个个都长得油光水滑的”;百姓家在婚丧嫁娶、开工修屋时,要请崔小岭来挑个吉日;官府在修房建屋时,也要找崔小岭看个“好日子”……崔小岭成了当地的活神仙,成了民众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支柱。对具有神秘性甚至伪科学性的巫术,李春平没有过分渲染,而是把它融入日常生活琐事中徐徐道来。在整个文本的阅读接受中,读者感受不到巫术的荒诞与怪异,更不会将其斥之为愚昧和无知。淳朴善良的盐背子们在艰险困苦的自然生态面前,他们无奈地将生活的憧憬与希望寄托在神秘的巫术中,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真实还原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貌和文化心理。
贴地而飞的文学姿态,还体现在对巴山民歌文化的反映上。在《盐道》和《盐味》中,民歌共出现10余处,内容丰富绚丽,语言大胆质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6]7民感于“物”而成于“歌”,民歌产生于老百姓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感悟。民歌是地域文化中最通俗、最真实的记录方式和情感载体。从先秦《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再到宋词、清代竹枝词等,中国民歌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老百姓的生产劳动、节庆习俗及日常生活。《文心雕龙·乐府》在提及民歌功能时,曰:“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16]7。由民歌可感知一地之风物人情,“在大巴山,人人都会唱歌,不用教,也不用学,天生就会唱”,“在陕川鄂交界处的巴山一带,只要会说话的人都会唱歌,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歌”[4]82。爱唱民歌是大巴山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和爱好,他们在劳动时唱,休闲时也唱,开心了唱,悲伤了也唱,唱歌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盐道》和《盐味》中,出现内容最多的,一类是描述盐道生活的民歌:“四脚爬坡梯百步,打杵磨烂篾背篓。爹把儿子背成人,儿子把爹背进土”“住的是山沟沟呦,吃的是洋芋坨呦,烤的转转火呦,睡的包谷壳呦”[4]11-12。此类民歌真实记录了贫苦、艰难、恶劣的盐背子生存境况。另一类就是打情骂俏的情歌:“送郎送到大路边,巫咸国里去背盐,奴知路上多艰险,不知何时把家还,晚上搂着空枕头,想到小郎心里酸”,“弯弯背架像只梭,我是巴山背二哥。太阳送我上巴山,月亮陪我过巴河。晚上歇在幺店子,还有贤妹来煨脚,打一杵来唱支歌,人家说我穷快活”[4]84-85。语言直白,用词大胆、泼辣,盐背子们及巴山人爽朗、率真、奔放、乐观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对两类民歌内容作对比后,我们发现,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盐背子们把民歌既作为他们生活的调味品,又作为他们与贫困作斗争的精神武器,这真实地再现了巴山盐背子“坚忍不拔”精神品质和“苦而不怨”的生存智慧。李春平是土生土长的巴山人,对巴蜀生活非常熟悉。他曾说过,“我看到,再苦再累,再恶劣的环境,我周围的父老乡亲也从来没对这片土地失望过,没有谁能够打垮他们的生存意志。他们每天都在顽强地挣扎和奋斗着。古盐道上,不知道摔死了多少,病死了多少,打死了多少,但盐背子这个职业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宁厂的盐照样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10]356。这不仅是李春平对生活在秦巴山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盐背子们的讴歌和赞美,也是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精神的坚守与传承,从整体上增强了小说厚重博大的文化内蕴和温柔敦厚的审美质地。
李春平是一个对生活和文学具有高度热情的人,他以古盐道为题材的小说创作,通过对已消失的盐背子群体的书写,再现了民国时期大巴山人的生活况貌,让读者在阅读中体悟盐背子生活的艰辛,感受盐道精神的伟大。盐背子们在恶劣的生存境遇中表现出的豁达乐观、负重前行的精神品格,正是中华民族在苦难深渊中奋力崛起的历史写照。李春平盐道系列小说创作,不仅丰富了盐文学创作,也将盐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坚持用文学创作给人以温暖和阳光,传递社会正能量。这样的文学创作观,既维护了文学的人文维度和历史厚度,也突出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创作个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春平是一个具有超强艺术感悟力和文学表现力的作家。我们期待他在“盐道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有更出色的表现,为中国盐文学再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