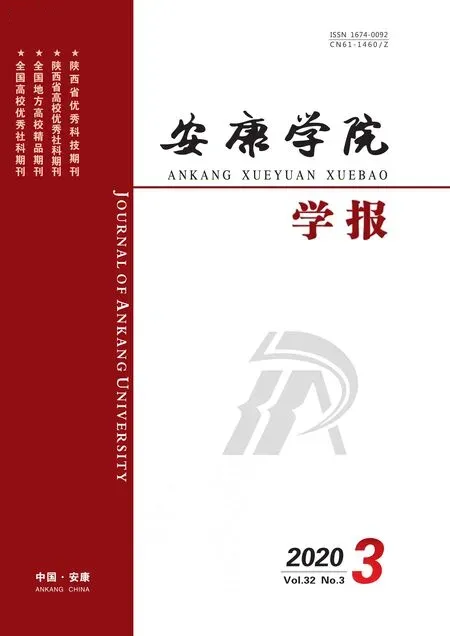论陈维崧《箧衍集》的选诗倾向
2020-12-26汤洁
汤 洁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箧衍集》作为陈维崧生前的未刊之作,“辑以国朝诸家之诗,分体编次,所选颇为精华”[1]。作品中辑录了清代康熙中叶前的重要诗人157位,诗作849首,同时,将各人诗作按“五言古诗”“五古长篇”“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及“五言联句”分体编排,其中更不乏清初名公佚作,实担得“希珍”二字。目前,学界关于陈维崧的研究不知凡几,但对其《箧衍集》的关注则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以刘和文先生点校的《箧衍集》为参考,拟从《箧衍集》的选诗角度对文本进行初步探析。
一、地域:以江南为主
《箧衍集》中包含清初众多诗文作者,尽管名气有别,但在地域分布上,存在一定共通之处。诗集作者中,江南文人有69位,占总量的近半数。这里的江南便是我们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吴文化地区。此外,诗集中还收录浙鲁文人作品,但均未超过20位。由此可知,陈维崧在辑录诗集时,对江南地区文人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倾向,可从三方面进行解读。
天启五年,陈维崧生于江苏宜兴文学世家,才气笼罩的江南为“江左凤凰”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土壤。因此,陈维崧对江南的感情是十分浓厚的。正如凌扬藻所言:“粤中风雅,自唐曲江公,宋余襄公、崔清献公、李忠简公外,莫盛于前明,《诗海》收至四百七十余家,亦云多矣。我朝文治诞敷百八十年,薄海遐取,贤才辈出,使不为之荟萃,以跻其于唐宋元明之上,而昭见培植之深乎?”[2]在盛行乡邦文献整理与收录的清代,陈其年将《箧衍集》作为倾诉桑梓之情的载体。
与此同时,明末清初之际,江南的文人社群数量十分可观,学术团体与江南优秀文人的大量出现,为陈维崧的诗歌辑录提供了充分的信心,如《箧衍集》开篇即收录了江南文人钱谦益的《田园杂诗二首》及邢昉的《忆幼子》 《过黄州宿园居》等诗。这种江南地区与江南文人的双重组合,自然而然地影响了陈维崧诗歌选择的方向。陈维崧作为诗集收录者,对家乡优秀的文化成果感到自豪,与殷璠、阮元等人一样,陈其年在辑录诗作时,将地域作为其作品亮眼的显性特征。
陈维崧作为阳羡词派的领袖人物,他以江南地区为主的交友圈必然会对其诗歌选择形成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他倾向于收录阳羡词派词人之诗。其中较为著名的当属蒋景祁,蒋景祁身为江南文人,更是“阳羡后学”,创作风格颇肖陈维崧。他的创作以词为主,但《箧衍集》中却收录其诗五首,除常见的《伏波庙》外,还包括《观趵突泉歌》与《再观趵突泉歌》等游历纪行之诗。其次,陈其年偏爱收录友人之作。与其有交游经历的朱彝尊、宋荦、汪琬及龚鼎慈等人的诗作皆赫然在列且数量可观、类型丰富。赠诗、家书、纪行等俱有涵盖。陈、朱之谊自不必多言,《朱陈村词》便得窥见。最后,诗集中还收录王士禛诗歌35首,对《箧衍集》的考据有极大帮助的序,也有王士禛、蒋景祁、宋荦等人的参与,足以见得陈其年交游范围之广,与友人情感之笃。这种以阳羡词派为中心蔓延而外的交友圈,也为陈维崧的诗集收录提供了优质的素材与巨大的便利。
桑梓之情与交游之谊是陈维崧诗集收录的一大考量,除此之外,江南地区浓烈的反清行动与思想也影响着其人其诗。清代的高压政策,使文人饱受其害,更遑论作为文学中心的江南地区。因此,反清复明的思想几乎贯穿清廷统治的始终。
而江南地区文人荟集,党社众多,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以复社为代表,党社的领袖人物几乎被摧残殆尽,文人集会一度停止,文人的反抗情绪愈演愈烈。江南著名诗人邢昉在清军入关后数度拒征不仕,穷困潦倒,以布衣之身发“十年垂白发,流浪逐人间”[3]146之慨叹。其好友杨文骢因不屈清人被杀害,其同乡赵士林也惨死于清军刀下。邢昉哀其友,作诗道:“颈血鲜鲜百日中,握拳透爪气如虹。平生陋巷谁知者?死后方同颜鲁公”[4]。清朝的统治使江南文人感到压抑与痛苦,这种反清思想甚至由个人蔓延至家族。近代最大的文人社团——南社,其中便有许多江南家族的影子,他们反清复明的政治意志亦十分浓烈。如以家塾教育闻名的金山高氏,他们的家族成员通过诗歌创作来彰显反清意志。高燮以“托报亡国向谁语,长抱芳心追上古”[5]表达鲜明的反清态度。其侄高旭紧随其后,高呼:“劲枝铁干横高崖,凛然饶有杀胡气”[6]。除高氏外,吴江柳氏家族、杭郡丁氏家族等也都表现出鲜明的反清意志。这种作为群体意识出现的反清思潮为底蕴深厚的江南文学又添了一抹文人傲然之气。
不仅如此,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拒仕清廷,隐居乡间,逾十年未入城市。生于讲求气节的文学世家,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又都是江南文士们的铮然傲骨,再结合他自身的仕途经历,我们可以推测,陈维崧秘不示人的《箧衍集》中必然反映了对江南抗清思想的赞同。因此,江南诗人作品必然成为迦陵《箧衍集》中重要的文化符号。
二、群体:遗民与贰臣
明清易代造成了士人们政治选择上的分野,大量的遗民与贰臣随之出现。“遗民者,则处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也。”[7]6与之相对的是在《桃花扇》中被孔尚任无情批判的“蒙面灌浆人”,孔氏认为贰臣们道德沦丧,不配入朝。而这两属性相对的人物同时出现在《箧衍集》中。
《箧衍集》中辑录了大量遗民诗人的作品。以顾炎武、屈大均、姜垓、钱澄之等人为代表①需要说明的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的余姚黄氏刻本中,还收录遗民诗人黄宗羲诗六首,而点校本《箧衍集》以乾隆二十六年华绮刻本为底本,未列此人,故本文对黄宗羲暂不作讨论。。遗民诗人群是气节与风骨的代名词,被称为“清学开山始祖”的顾炎武,《箧衍集》收其诗17首,除著名的《登岱》外,还有《大同杂诗四首》 《赠友人二首》 《无题三首》及《姬人怨二首》。他的诗中写道:
旧府荒城内,颓垣只四门。先朝曾驻跸,当日是雄藩。
采帛连楼满,笙歌接巷繁。一逢三月火,惟吊国殇魂。[3]73
明确表达出自己对明朝覆灭,旧土支离破碎的感伤。遗民诗人们不仅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坚定的态度,在行为上更值得后人赞颂。顾炎武不仅数次拒绝仕清,还不断奔走于各股抗清势力之间,率众结社,锒铛下狱,颠沛流离,但他仍以精卫填海的精神为抗清事业不断努力。姜垓也是遗民诗人的主要代表,他借“楚亡白壁疑门下,汉起黄巾赦党人。投匿容留方恨晚,无家更苦玉关尘”[3]168来表达对清朝的不满,他本人也因持节不降而被世人称赞。还有揭竿反清的屈大均,因其《皇明四朝成仁录》中夹杂反清情绪,而被清廷下令焚毁,其著作更在雍正、乾隆时期遭到三次禁毁,足见清代对于遗民文人群体的打击之剧烈、彻底。在这种高压氛围下,勇敢的遗民诗人们通过坚守气节澄澈内心,通过诗文作品缅怀明朝,他们是战火与硝烟中不曾蒙尘的风景。
遗民文人看中气节风骨,也因这种坚忍而留名后世,这就使得众多仕清贰臣被时人及后人无限诟病。“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8]的龚鼎慈就是千夫所指的一位,丧失节操至极点,被明人鄙夷,更为清人所不齿。“江左三大家”的文人成就与刑部尚书的政治家身份却仍无法抹去清人对其“哄笑长安”的贬斥评价。但就是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贰臣,《箧衍集》中却收录其诗10首。
与失节的龚鼎慈不同,还有一批诗人,他们虽然也带着贰臣的帽子,但却始终难逃强烈的自我谴责,最终走上不仕清廷的道路。顺治二年迎降官员钱谦益向清军大开洪武门,并行四拜礼,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贰臣了。但清顺治六年归家后却暗中与反清复明势力联系,并于其后的十一年间数次参与反清起事,不顾老迈,奔波呼号。对于钱谦益此种仕清又反清的变化,从《箧衍集》所收其《渡淮闻何三季穆之讣》中可窥见缘由。“世事供涕唾,流俗丧械杻。求志良已奢,用我挟以走。”[3]42这种悲哀的内心忏悔还反映在同是贰臣文人的吴伟业身上,其《送何第五》云:“激昂承明廷,面折公卿议……逊子十倍才,焉能一官弃?早贵生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子所愧……”[3]45与钱牧斋的主动仕清相比,吴伟业是在清廷威逼与老母敦促下被迫出仕,因此,出于内心对气节的坚守,屈节的哀痛笼罩着他整个晚年生活,引起他不断地自省与忏悔。这也是为何龚鼎慈声名狼藉而吴伟业却被客观评价的重要原因吧。除牧斋与梅村,还有以疾辞官的贰臣曹溶、焚稿绝念的周亮工等人,在贰臣的身份下,也都隐藏着这些文人不为人知的哀痛。
三、情感:感念故国
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在政治身份上水火不容,在文学交流上,却能共谱“高山流水”。谢正光先生的《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中探析了顾炎武与曹溶的交往始末,作为“蒙面灌浆人”的曹秋岳也积极招揽遗民作为门客。顾炎武还先后与降臣程先贞和史可程结下了深厚情谊。作为忠节的践行者,顾炎武甚至对降臣发表过“不齿于人类”之论,那他为何会漠视政治操守,结交这些名节已污、广受非议的失节之人呢?正光先生如是解答:“亭林晚年择友,既未以个人的政治操守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他所考虑到的,至少也包括了学术文化活动的参与和认同,以及个人习性的相近等因素。”[7]329所以,撇开政治选择不论,遗民与贰臣之间是存在一定契合之处的。
遗民之诗与贰臣之诗在情感的表达上是具有共通性的。如此一来,关于《箧衍集》中遗民与贰臣之诗兼而有之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首先,他们面对国难都是伤感的。遗民诗人群将故国逝去之殇直接地倾诉在诗歌中。如邢昉的“流泣但徘徊,空惭子桑扈”[3]2;“解缆一挥手,惆怅月明下”[3]2;“惆怅故情歇,难为永日留”[3]2。诗歌中随处可见“泣”“惆怅”等字眼,哀痛之情展于话中,延至话外。贰臣群体同样面临巨大的伤痛,“座中谁无忆旧情,饮罢微闻声唧唧”[3]107是曹溶的伤痛;“丈夫行年已七十,天涯戎马知何日?”[3]113是梅村的哀愤;“酣放动经六十日,千载惟公知此心”[3]139是翁山的无奈。就连丧节至极的龚鼎慈,都发出了“何来双杜宇,叫出断肠诗”[3]98的慨叹。在覆灭的国家面前,尽管选择的道路有别,但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的伤感是难分伯仲的。此外,诗人们的这种感情又是积极的。张之洞有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9]对故国情感的坚守催生了文人们的反清观念,上文的江南文人便是极好的例证,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拒不仕清,他们表现出的这种或“惆怅”或“恨”的情绪成为他们组织或参与抗清活动的重要动力。
明末清初的诗人们将他们对于国家的复杂感情倾入诗作中。一方面,陈维崧作为别集的编纂者,他游食四方,羁旅漂泊的经历,强化了他对故土的归属感,正如他词中所诉,“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这里的“寒”既是环境的写实,也是陈其年“慷慨”之情的流露。这种不甘沉寂,感慨激励的态度引导着他的选诗方向。另一方面,诗歌作者的情感表达也是他们得以入选诗集的重要考量。除卷十二的七首五言联句外,前十一卷中,无论是纪行诗,交游诗或咏物诗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作诗者的怆然之感。这批作者或是官衔在身,宦海浮沉;或是辞官归隐,壮志难酬。他们的经历一般都坎坷而丰富。因此他们这种自觉性的感情抒发也常与自身经历密切相关,但诗集中却难见谄媚之语,多的是如“十年不向姑山去,别恨羁愁乱如雾”[3]124这般对故乡故土的眷恋以及物是人非的慨叹。
不难发现,陈维崧的《箧衍集》摒弃了各种诗作者的政治身份之别,而着力以情感为依托,辑录众人之诗。先仕清后反清与始终拒不仕清的文人们,诗歌中都蕴藉着浓烈的感伤与抗争情绪,情感因素成为连接两者的纽带。同时,需要肯定的是,他们的这种情感又是积极而主动的。国家易代之际,爱国的文人内心总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如蒙古铁蹄践踏下的元代文人,他们的情感更为消极和低沉。他们的作品是他们自己错乱与麻木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清代雄实的学术氛围造就了文人们不吐不快的刚健性格,所以《箧衍集》中的反抗情绪也是鲜明而深刻的。
四、意识:真情、诗史与关怀
《箧衍集》作为清初诗集精品,蒋景祁序有云:“其选主于自怡,故不谋于人;艰于借抄,故篇弗求备,使迟以岁月,博以摭采,岂不伟然一代之全书哉!”[10]该书在诗歌的选择上,除上文提及的地域、群体与情感因素外,还体现了一定的意识性。
《箧衍集》选诗“主于自怡”,“自怡”即“自乐”“自娱”之意。说明陈维崧在选诗时讲求顺遂心意,那么陈维崧心意为何呢?《迦陵文集》中有云,“歌”即“诗”,陈维崧认为诗歌中应该表达嬉笑怒骂、悲喜欢愉之情,即诗应言心声,应言真情。迦陵诗在内容上较为丰富,或感慨兴亡、关心民生;或忧怀身世、羁旅漂泊;抑或游览山水、道尽伤逝。需要指出的是,陈维崧用悲怆刚健之情贯穿诗歌描写前后,尽管所写对象各有不同,但他的情感表达却始终真挚而热切。
陈其年的真情意识还体现于《箧衍集》卷八所收录的无名氏之诗以及卷十二收录的七首五言联句上。汪淇曾言,清代见不作诗者,实为奇事矣。在清诗数量如此繁盛之际,陈维崧却择一无名氏之诗于诸大家之诗中,究其原因,惟性情相符之由最为可靠。
十二尧官隐宫绿,兽猊喷酒椒壁馥。渴乌涓涓不相续,辘轳欲转霏红玉。
百刻香残陨莲烛,五龙吐水漫寒浆。红绡佩鱼无左珰,两两悬足瞻扶桑。
红苹半瓣出波面,回首觚稜九霞绚。鸣鞘远从天上来,大剑高冠满前殿。[3]165
本诗以“兽猊”“五龙”“觚稜”“大剑”等厚重意象传达作者沉郁悲怆之情,引发陈维崧内心共鸣。而卷末的七首五言联句,同样句句真情,如《八月十二夜天延阁联句》记载了秋日里好友相会,举杯话孤愁的怅惘之情,彰显着陈维崧的“诗言真情”意识。
《箧衍集》中7次出现吴伟业,收其诗多达51首,其中又以五律与七古的数量最为可观。除吴伟业自身诗力雄厚,成就突出外,还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
其一是吴伟业与陈维崧存在师承关系。陈维崧的《酬许元锡》中明确提出他于弱冠之年师从梅村。同时,吴伟业对陈维崧也尤为赞赏。陈维崧对吴伟业的“梅村体”推崇备至,他在继承吴伟业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将七言歌行的风格朝雄浑方向进一步发展。然,师承关系仅是收诗考量的一个方面。
其二是吴梅村诗歌中的诗史意识是收诗之多的关键。首先,他的诗歌“载真事”。吴伟业在七古的创作上自觉地借鉴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杜诗以“诗史”著称,这也影响了梅村对于诗歌真实性的追求。他的七言古诗《三松老人歌》,写老人“箬帽棕鞋神奕奕”[3]112,近乎白描,写事件“醉值金吾争道过,将军司隶与钱通”[3]112,反映的是无奈可悲的社会现实。其次,吴伟业的诗歌同样“诉真情”。仕清经历造成了吴梅村内心的巨大痛苦,他的感伤情绪在诗中显露无遗,“而今零落无收处,故国兴亡已十年”[3]218一句道出其以国为家,内心无依的孤苦。吴伟业的诗歌习惯于将社会历史事件与真情实感相结合,他的《悲歌赠吴季子》以季札为赠诗对象,发历史兴亡之泣诉,“受患袛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3]114又何尝不是在自我诘问呢?
吴伟业这种“记史”与“传情”并重的诗史意识对注重“真情”的陈维崧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便体现在《箧衍集》对梅村诗的大量收录上。
明末清初,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诗派以及以陈子龙为先驱的云间派活跃在江南地区,在诗坛地位上,三诗派竞争不断,云间派与娄东派不愿放任虞山诗派一家独大,这一竞争也促使三派文学作品迭出。在宗法前代的问题上,钱牧斋同样有别于另二人的宗法唐诗而主张唐宋兼宗。尽管三诗派发展迥异,所尊有别,但从政治维度来看,江南三诗派都有着极强的社会关怀意识。
一方面,三诗派领袖及其成员表现出对社会民生的极大关注。钱谦益与吴伟业对于社会事件的参与前已有论,在此不做赘述。而云间派领袖陈子龙被公认为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倾向于直面现实,表现出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兴亡的殷切关注。而三诗派的成员们同样践行着领袖们的关怀意识。如娄东派的太仓十子,他们以梅村为师,以创作现实主义诗歌为旨归,发社会兴亡之叹。十子成员黄与坚诗中写道:“同话寂寥皆逆旅,两经离乱即余生”[11],流露世事沧桑与人生苦难之感。
另一方面,在清廷的压迫下,三诗派表现反清复明的心灵默契,这种反清复明思想着重体现于三诗派领袖的行为上。陈子龙的反清情绪始终浓烈,而牧斋与梅村虽有仕清经历,但其后二人都为反清复明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吴伟业的《观棋六首》就是以“观棋”来隐晦地评论时局,传达反清复明思想。而钱谦益更先后参与黄毓祺起义、联络东西两地抗清势力等活动,乾隆谕中称他与屈大均为“匪人”,更责令各家诗文中削去二人作品。
江南三诗派的诗人们在时代变革之际,体现出文人特有的风骨气节与社会关怀意识,他们的诗歌创作是特殊时代的历史纪实。
五、结语
钱仲联先生说:“清诗作家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上,开出来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12]《箧衍集》作为一部辑录清诗的优秀诗选,为后人更全面地认识清初社会提供了重要借鉴。除选诗倾向外,《箧衍集》反映了陈维崧何种诗学观、《箧衍集》中佚作及其价值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