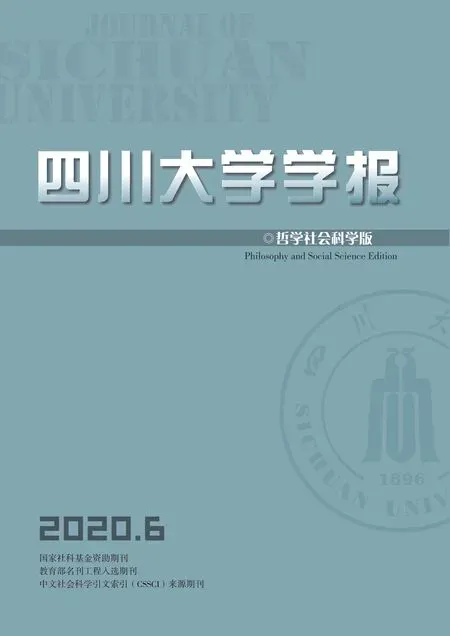体系中的人
——罗森克朗茨与黑格尔《伦理体系》中的整体主义
2020-12-26翁少龙
翁少龙
黑格尔《伦理体系》(SystemderSittlichkeit)作为首次以“体系”命名的著作,在德国文献学家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那里被视为黑格尔对其法兰克福时期思想的总结,它的地位如同耶拿时期著作群的最后作品《精神现象学》那样崇高。罗森克朗茨的观点后来遭到基默(Heinz Kimmerle)的否定,因为他根据黑格尔在不同时期的笔迹特征认定《伦理体系》就是耶拿时期的作品。(1)参看Heinz Kimmerle, “Zur Entwicklung des Hegelschen Denkens in Jena,” in: Hegel-Studien, Beiheft 4. Bonn 1969, S.33-47.此外,基默也在《黑格尔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对罗森克朗茨所编辑的《伦理体系》的批评文章,参看Heinz Kimmerle, “Die von Rosenkranz überlieferten Texte aus der Jenaer Zeit. Eine Untersuchung ihres Quellenwerts,” in: Hegel-Studien 5, Bonn 1969, S.83-94. 然而,与基默正好相反,对于用“体系”来命名的这部作品,此后却获得了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支持,并认为这是黑格尔在最困难的时期所完成的最为艰难的作品,马尔库塞因此给予了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因其是未完成之作而变成了德国哲学中最难读懂的作品之一。参看Herbert Marcuse,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Hegel und die Entstehung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Neuwied am Rhein und Berlin:Luchterhand Verlag,1962,S.60.这样一来,罗森克朗茨关于《伦理体系》的定位就变得很成问题。此外,《伦理体系》这个书名也是罗森克朗茨取的,然而,德国文献学家麦斯特(Kurt Rainer Meist)在对黑格尔耶拿著作群进行仔细梳理之后,认为这部誊清稿其实就是黑格尔在耶拿开设的自然法课程的授课纲要,因而,准确的标题应该是《费希特自然法批判》(CritikdesFichteschenNaturrechts)。但是,《伦理体系》这个名称显然远比《费希特自然法批判》更为流行,麦斯特的重新命名仅作为该书的副标题供读者参考,尽管麦斯特的结论可能更接近历史事实。
罗森克朗茨尽管遭遇德国文献学家的诸多批评,尤其是在对黑格尔早期文献编辑的不严谨方面,(2)当然,这种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将《伦理体系》视为法兰克福时期的作品,那就意味着黑格尔至少提前4年就开始进行哲学的体系化建构,并且足以贬低他在耶拿大学时期那些未发表的手稿的价值;但如果将它视为耶拿时期的作品,那么在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又好像缺失了总结性的作品,使得他的这个时期变得非常平淡,完全无法与接下来的耶拿时期相提并论。当然,《伦理体系》的命名已经流传甚广,几乎无法再用其他名称来加以定义,因而作为历史的事实,学界也是公认了罗森克朗茨的命名,尽管我们现在已无从考证他当时的设想,或许他就是为了在法兰克福和耶拿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间做出权衡。但作为最早接手黑格尔遗稿的文献学家,同时也是最早的黑格尔传记的作者,罗森克朗茨对《伦理体系》的挖掘和整理毕竟功不可没。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繁琐的文献考证,单就《伦理体系》的内容来看,罗森克朗茨的编辑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他从这部誊清稿的内容中提取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伦理性”(Sittlichkeit)概念,区分了“自然伦理性”(Die natürliche Sittlichkeit)、“否定伦理性”(Die negative Sittlichkeit)和“绝对伦理性”(Die absolute Sittlichkeit)的子概念,并据此编辑为一部完整的著作。以下,本文拟就《伦理体系》的这个三分法为罗森克朗茨作些辩护,以说明流传至今的《伦理体系》书名不仅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更在于内容上的自恰性。对于麦斯特的批评,本文认为,罗森克朗茨显然并没有忽视费希特的自然法理论在黑格尔时代所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毕竟也是由黑格尔接替了费希特在柏林大学的哲学教席,两人共同将自然法的探讨与国家制度的建构关联起来,使得哲学真正履行了为国家服务的目的。不仅如此,本文还认为,罗森克朗茨比麦斯特更好地把握了《伦理体系》这个耶拿讲课纲要的精神主旨,即从哲学上思考何以个体会成为“体系中的人”。
一、自然伦理性
罗森克朗茨可以说是黑格尔最早的诠释者之一,他的两部重要著作《黑格尔传》(G.W.F.HegelsLeben, Berlin, 1844)与《作为德国官方哲学家的黑格尔》(HegelalsdeutscherNationalphilosoph, Leipzig, 1870)为此后学界对黑格尔的形象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伦理体系》的主题把握也同样如此。当然,罗森克朗茨对黑格尔著作也并非只是单纯的辩护,而是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考证基础之上的编撰阐释。罗森克朗茨使用“体系”这个概念来命名黑格尔的这部手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看到了黑格尔伦理性概念的辩证性,就如同我们所熟知的黑格尔逻辑学,其中的概念体系不是僵死的,而是由低到高,不断扬弃自身并发展自身的螺旋式上升的。黑格尔“体系中的人”就是不断递进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人。(3)黑格尔在《伦理体系》中惯用的“级次”(Potenz,或译为“因次”)概念其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递进性,它既表示个体趋向整体的目标,也表示个体自身所具有的趋向整体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并不从原子个体出发来探讨伦理性的概念,而是一开始就将整体作为基础,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是“关系”(Verhältniß)这个概念,因而个体“必定要被视为关系之后的绝对伦理,或自然伦理”。(4)G.W.F.Hegel,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2, S.4.以下在引文后直接标注简写德文版页码。
这是黑格尔从经验意识出发对个体关系的认定。因为很显然,无论是经验的还是形式的自然法,若将“关系”概念首先排除在外都是不可能建构起伦理性这个概念的,因为伦理性就是关于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体系,必定要以主体间性作为理论的前提,也就是首先必须要把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他者当作一个整体。在黑格尔看来,“第一级次就是直观的自然伦理”(S.5),这显然是建立在生活常识之上的判断,因为经验的直观告诉人们,必定会有他者的存在才能形成互动关系,原子式的个体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是健康的理智所能理解的。在此意义上,作为整个“伦理性”体系的起点,自然伦理性最好地说明了黑格尔对人的感性欲望的承认,而此后所有关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信念均需以人的自然存在及其属性为基础。
在黑格尔那里,人们关于伦理性的概念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对日常生活“习俗”(Sitte)的深切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就是对这个经验意义上的习俗的绝对化。依此,黑格尔便将两者的关系用“直观”和“概念”加以区分。这样一来,黑格尔就点明了自然伦理性的基础作用,换言之,从形式主义中只能产生无差别(Indifferenz),但是这并非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因为人作为经验的存在,他的特征就是差别化,这种差别也体现在需求和满足的差别上,也体现在由这种差别而形成的后果上,即在现实之中所出现的阶层的差异化,对于这种差异化,根据罗森克朗茨的分析,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其实包含着宗教的因素。(5)Karl 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 Berlin: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844, S.132-141.但在黑格尔那里,人们就是出于实践的需要,因而并不只是出于宗教的同一性的因素,同一性在此毋宁就是个实践哲学的概念,罗森克朗茨从宗教哲学出发试图给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做出诠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就写过《论信仰与宗教》(Zum Glauben und zur Religion)。(6)G. W. F. 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2,Hamburg:Meiner Verlag, 2014, S.3-14.在罗森克朗茨那里,启蒙精神所能给予黑格尔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黑格尔对宗教进行的实在性论证,但就劳动生产的实在性而言却并不就是宗教层面上,因为在劳动的对象化中,人们才发展出了自身的理智,并且为了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不断地发明创造,黑格尔在耶拿所做的实在性研究,更多地是在说明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去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伦理性是黑格尔建构起体系化的伦理思想的基础,这是他区别于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地方。在黑格尔看来,“超越这个形式概念也就变成了生命的自然关系”(S.19),也就是说,在自然伦理性中,黑格尔所面对的是具体的生命对象。在此意义上,首先是经验的外在对象的存在,而且是作为整体的对象的出现才能形成具有体系化的伦理概念,进而可从总体上把握人与共同体所处的位置。就此而言,人所具有的属性并非被形式化地规定,因为形式主义完全忽略了人所处的环境及其关系的复杂因素。黑格尔所说的实践是以劳动生产的方式不断地实现着为了生命自身的持存而做出的努力,与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法则相比,实践代表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它能够以此来实现对其自身的主宰,并运用理智去支配外在的力量。据罗森克朗茨的考察,黑格尔的实践概念大都出自他对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政治经济学原理》(InquiryintothePrinziplesofPoliticalEconomy)的解读,这其中包括需求与劳动,以及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黑格尔在1799年2月至5月期间曾经对这部著作做过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评论,可惜后来都遗失了。(7)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 S.86.
就实践而言,黑格尔指出,它的主体和对象就是作为感觉的主体和可被感觉的对象物,因而凡是超出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都是在实践之外的,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试图打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凡是实践的对象,必定具有符合主体的属性。很显然,人的劳动对象是符合其主体需求的,而劳动产物也只能是有利于其生命的持存才是有价值的,从对象物再返回人自身,人会认识到自身的实践主体性其实就是由外物所塑造的,在这个互动关系中,主体才将自然置于自身的支配之下。黑格尔对伦理性的生成转换的论述,事实上已经包含着他后来构建的逻辑体系的萌芽。很显然,这个“关系”就是个矛盾的辩证运动,黑格尔反对康德试图消除矛盾和对立的观点,而是强调在现实中包含着矛盾和对立。但是,黑格尔在自然伦理性中对“关系”的揭示还不充分且相当晦涩,后来经过卢卡奇(Georg Lukacs)的总结和阐发,其自然伦理性的概念才更加切合劳动生产的维度。(8)Georg Lukacs, Der junge Hegel, Zürich:Europa-Verlag AG, 1948. 此外,还可以参考瓦切克(Nobert Waszek)的研究,他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黑格尔的伦理性概念,并从苏格兰启蒙学派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做了全面的梳理,参看Nobert Waszek,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 London:Kluwer, 1988.
在自然伦理性中,黑格尔既探讨了劳动生产,也探讨了在此基础上所结成的家庭关系,这是人所能形成的最早的共同体。其实,黑格尔已经注意到,人的个体性首先被消除的动因就是来自家庭的“爱”(Liebe)。关于爱的研究,黑格尔早在1795年关于耶稣生平的论文中已有阐述,文中黑格尔以凡人的眼光平视神圣的耶稣,以说明即使在人间的平凡之爱也具有超越凡间的力量。(9)G. W. F. 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1, Hamburg:Meiner Verlag, 1989, S.245-249.而在家庭这个最初的共同体中,人的个体性很快就在爱的氛围之中被融化,“也就是在特殊性的直观之下,个体性作为如此而被涵摄,因而作为自然显现”(S.30)。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够感受到来自整体的力量的牵引,进而将其自身升华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其作为自然的本质,而且在家庭成员之间,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并由此而产生了最初的在道德情感上的升华。这种趋向整体的力量,黑格尔称其为“特殊性的直观”,因为在他看来,人在自然伦理性中所建构起来的情感依托本身就具有某种神秘的属性,它对人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以自然的方式将所有个体融合为一个整体。
二、否定伦理性
在罗森克朗茨那里,黑格尔的作为整体主义的伦理性也是辩证的伦理性。诚然,最高的伦理性是“体系中的人”所应该达到的目标,也是绝对精神的最终实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形式的伦理性也会产生否定性,“否定要么就是纯粹消极的,这样一来,它也就会是辩证的”(S.33)。在罗森克朗茨看来,黑格尔所论述的这个辩证过程就体现在个体从自然存在上升为整体的伦理存在的过程,而伦理性其实也就是在自身内部由诸多环节的运动所构成的整体。黑格尔试图以否定性的形式给予他的伦理体系以内在的辩证运动,同时也为自然伦理性和绝对伦理性之间提供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以实现从“自然性”向“伦理性”的合理过渡,而在其中,个体经由否定性这个环节也就从消极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了积极的伦理建构。罗森克朗茨显然是看到了黑格尔对于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应该具有的特征在总体上的把握,因为黑格尔通过对英国的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认识到需要有个伦理性的方案来维护每个劳动者的尊严。(10)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S.177,85.很显然,这个过渡是极其必要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法哲学如同他在柏林时期的法哲学那样,都是探讨法的观念的现实化问题,(11)当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会认为,黑格尔早期的理论体系与其后期的理论体系存在明显差别,因而,他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作品作为单独的而且是自成体系的理论来看待。参看Wilhelm Dilthey, 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 Berlin:Verlag von B.G.Teubner, 1905.就此而言,人们在观念中所具有的法就按照否定的辩证运动而成为现实。具体说来,作为法的实在对象,它在人的观念之中是以抽象的形式而存在,因而,这是个双重的否定性:首先,在对象物那里,个体的观念变成了确实的外在之物,但与此同时,现实的观念物在经过抽象化之后也不再是它此前的形态,而是成为能够被思考的对象物。
这是黑格尔对劳动对象化的哲学分析,在这里,主体自我试图实现对外物的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形成了某种辩证的关系,“否定这个实践规定,就是与矛盾的最初特殊性相对立”(S.35),黑格尔在此是要将此前在自然伦理性中的规定性以另外一种方式予以整合,“否定性”在此包含着打破主客二分的对立性的涵义。(12)黑格尔在耶拿大学所举办的系列讲座非常类似于他此后对哲学体系的划分,也就是“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但是《伦理体系》却把这三者包含于自身,因而“否定性”概念其实已经包含着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思维。参看Wolfgang Bonsiepen, “Der Begriff der Negativität in den Jenaer Schriften Hegels,” in: Hegel-Studien, Beiheft 16, Bonn, 1977,S.78.而事实上,在自然中的各种规定性就是需要被扬弃的个别性,这对于劳动主体和劳动对象都是如此,没有经过否定性这个环节的对象物都是彼此孤立和抽象的无差别,“否定使得自身成为根源,并规定自身为否定的无差别”(S.35)。而这个在劳动中所实现的否定性,首先要实现的就是对实践主体的改造,它表明主体在劳动中所具有的自主性,而且这种自主性在超越了自然伦理性之外而能被扬弃为具有整体主义的自主性。而正是在这样的否定性之中,个体作为实现理性和自由的主体也呈现出某种先天的不足,同时也更为具体地表明,个体必须要有作为必然的整体意识才能完成伦理性在其否定意义上的重构。
黑格尔在否定的伦理性中列举了许多与善相对的行为方式,即作为犯罪的否定伦理性,而正是这些犯罪现象呈现为不同个体之间的消极的互动关系,并在斗争中达到相互妥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契约精神也就产生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市民社会的生存状态就如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那样,它需要从无序中找到某种均衡。但对于黑格尔而言,他不能在否定性上形成这个秩序的观念,而必定要超越否定的伦理性,也就是说在扬弃市民社会之后才会有作为整体的制度和精神的出现。而这都是从否定性进入绝对性的必然过程,它所显现的是对日常经验生活状态的扬弃和超越,也是黑格尔从绝对性的视角对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重构的手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概念“是在它的矛盾否定中,通过自身相互的否定而达到的绝对主体性的现实存在”(S.38)。
因而,在否定伦理性中存在着这样的辩证性:对个体自身的局限性的扬弃,同时就是对整体性的接纳,而否定性在整体之中也就变成了积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个体性就是否定性,是需要被更高的契机所否定的“环节”(Moment),而黑格尔显然不是要将个别的局限性加以否定,而是将所有个体作为一个类别,在完成了对个别性的否定之后也就形成了作为“体系中的人”。从否定性这个概念中可以看出,黑格尔一开始就不是要把人限定在“个别性”(Einzelnheit)之内,而是从辩证的角度出发论证人所具有的趋向于整体的特性。罗森克朗茨正是借助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来论述个体的抽象化,因为与单独的个别性相比,个体只有被抽象为普遍化的存在才能更接近绝对精神的本质。(13)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 S.136.从实践的目的来看,个体有追求善的完美存在的整体动因,而这个动因的实现依赖于个体对其自身的限定性的把握,并在绝对精神的指引下将这美好的生活的实现放在整体之中。
在黑格尔看来,经过了否定的伦理性,个体也就变成了完美的无差别,表现为对其自身的个别性的扬弃之后所具有的现实同一性,它均衡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在此意义上,个体与整体实现了同一,这是最高层面上的自我实现。就此而言,在否定的伦理性中,个体对消极的原子自我的扬弃,进而在作为总体的体系之中实现了黑格尔所称的绝对性,因而,个体就从其作为个体的固化之中进入了现实的整体层面。而能够连接个体与整体的环节就是“荣誉”(Ehre),在黑格尔那里,荣誉是整体赋予个体的人格性,如果人从整体之中脱离出去,那么就必定会丧失其获得认同的基础,“通过荣誉,个体成了整体和人格”(S.42)。因而,“荣誉”正是作为共同体给予个体作为“体系中的人”的身份符号,在此,黑格尔以近乎图腾的方式褒扬了“荣誉”在个体之中所具有的感召作用,这说明在经过了否定的伦理性之后,个体从分裂的世界已经进入更高层次的有机整体之中,而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由否定伦理性向绝对伦理性的跨越。
三、绝对伦理性
绝对伦理性在《伦理体系》中就是个体潜在的整体主义的实现。罗森克朗茨认为,黑格尔对此的界定是居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14)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 S.129.在黑格尔的这部著作中,显然他所面对的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但令当代学者诧异的是,黑格尔使用的却是古典的整体主义方法。当然,罗森克朗茨将这部手稿命名为《伦理体系》,也是因为只有体系这个概念才能完整地表述整体主义从潜在到实现的完整过程,并且用体系去塑造个体为“体系中的人”,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伦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自身的实现。在最初的自然伦理性阶段,个体从劳动生产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中形成了最早的自然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在否定伦理性中扬弃了自身,导致了家庭的解体,并由此进入市民社会的更高层面。而市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众多家庭的联合体,因此,它所实现的就是个体在更高层面上的跨越,是整体主义在更高层面上的自我实现,但是,那些先前的整体主义观念在伦理的绝对性中却又在更高的整体之中保存了自身,“伦理性必定就是对特殊性及其同一性的完全否定”(S.47)。作为“体系中的人”在此才真正地将其内在的作为整体的观念变成了现实的制度和精神,而这个同一性也不再是停留在自然伦理性中的道德意识,也不再是否定伦理性中的那个狭隘的自我意识,而是在最高的绝对伦理性中将其自身完美地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个体的行为方能够与外在的制度和规范相符合,从而 “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个体作为“体系中的人”所需要的自由和正义的信念,同时也能够满足作为民族的整体对个体的要求。
但黑格尔同时强调,在整体之中的个体不是形式上抽象化的存在,而是为了让他作为本真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体现,在绝对伦理性中依然保存着个体在经验意识上的特征,“伦理性据此也就被规定,就是有生命的个体,作为生命等同于绝对概念”(S.48)。就此而言,伦理性就是经验意识与绝对性的同一,作为有生命的个体所组成的整体也因此成为生命的有机体。因而,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伦理性是有现实的生命力的,它就体现在所有个体的生命持存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生命的总和的国家制度和民族精神就是自然伦理性的总和,黑格尔非常看重自然哲学的思想在法哲学中的运用,在绝对伦理性中虽然已经扬弃了自然伦理性和否定伦理性,但是却把二者以更高的方式予以了综合,而这也很好地体现在绝对伦理性的“平等性”之中,也就是说,所有个体在伦理的绝对性中所保存着的就是其作为伦理精神的平等与正义。
就此而言,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伦理性就是个有机的生命体,这个伦理“在每个人那里就是绝对的个体,就是个绝对普遍,并且与个体相关,显现在每个部分就是这个普遍性”(S.51)。在罗森克朗茨看来,这种有机性就体现在作为正义的体系之中,它对内与对外都表现出了它的公正本质。(15)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S.131.因而,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一样,黑格尔的绝对伦理性就变身为一个“百手巨人”(Bryareus),个体就如同这个巨人身上的一只手,当所有人都变成了这个巨人身上的手的时候,这个巨人就会发挥出它的最大的优势——作为整体的优势,具有了作为个体所没有的功能和作用。(16)从整体主义的视角来看,霍布斯对黑格尔自然法的影响还可以参看Ludwig Siep, “Der Kampf um Anerkennung. Zu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bbes in den Jenaer Schriften,” in: Friedhelm Nicolin und Otto Pöggeler (hrsg.): Hegel-Studien. Band 9, Bonn: Bouvier Verlag 1974,S.201.当然,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使用了“百手巨人”这个比喻也可能来自霍布斯“利维坦”的启发,因为这两者都表示的是某种巨大无比的神兽,它们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但共同点都是由人所构造起来的,都是人的整体观念作为制度而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而对于个体而言,也借助于成为这绝对的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壮大了他自身的力量,这个整体看似由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但是在其中,所有个体都秉承着他的使命,并依据自身的功能而实现着这个有机体的运作。在此意义上,那个具有简单功能的个体就不是被分割开来的存在形式,而是每个个体都附属于整体之中,因为个体脱离了整体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就如同手脱离身体便失去了手的功能且不成其为真正意义的手一样。就个体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而言,个体也在其中被培养起某种秉性,也就是他在其内在性上具有了趋向整体的目的,个体的所有活动的环节都体现在为了维持这绝对的伦理性上,并使这个整体成为维护个体自身的重要保障。
至于作为整体的意识如何作用于个体,在黑格尔看来这需要有个普遍的伦理观念,“普遍,伦理的绝对,并且如同就在它的现实性之中”(S.55)。就此而言,康德的“人为自身立法”在黑格尔这里做了必要的转换,这里的“人”显然已经是作为“体系中的人”,是作为共同体的“人”,而非康德意义上的作为个体的人,因而能够起到在思想上立法的必定是这个整体主义所给予个体的普遍意识。但是,黑格尔关于普遍的绝对意识对于个体的作用的论述并非停留在理性层面上的,而更多地是在现实的效用上,因为在他看来,个体在作为伦理性的体系中的生存显然要比在孤立的自然状态中更好。而对此的分析,罗森克朗茨把政治经济学的观念与黑格尔的伦理性体系作了综合。在他看来,黑格尔之所以没有完全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念以及对国家职能的区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他的深刻影响;因而黑格尔的这个伦理性概念虽然包含着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的因素,但它所面向的恰恰是现代性的社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贯穿着黑格尔在耶拿大学的课程讲座始终,包括《论自然法》和《耶拿实在哲学》,尤其是其中的精神哲学部分。罗森克朗茨的上述分析是科学合理的,即使是当代的学界也很难与之相媲美,因为他掌握了黑格尔大量的史料,足以证明黑格尔提出体系性的整体观念是有很强的时代背景的。其实,罗森克朗茨早就认识到,在黑格尔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已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世界不再是按照牛顿力学的机械观所理解的世界,而是有机联系的生命体,应辩证地把握黑格尔的这部手稿,而对伦理性的跨越式理解也只能在作为有机的世界整体之中才是正确的。(17)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 S.19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法哲学中,甚至以带有功利主义的方式去叙述人们愿意接纳自身为整体的成员,因为人们只有在整体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幸福。事实上,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劳动分工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黑格尔的论述。
除了个体具有内在的趋向整体的主动性之外,黑格尔还以体系的“包含”(Subsumtion)力量而将所有个体纳入其中,也就是说,在绝对伦理性中,个体是有被吸收进整体的被动性的,当然这是一种体系化的功能,因为体系一旦达到绝对完善的时候,它对于所有个体都会有这样的作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说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法哲学就是作为现实的实践哲学,因为作为普遍的伦理性所具有的绝对性并不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而更为重要的就在于,它已经融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转化为人们的习俗(Sitte),进而在更为普遍的绝对性上成为每个个体的生存方式,因而也就具有了其作为普遍认同形态的“伦理性”(Sittlichkeit)。当然,这是个稳定的心理认同关系,它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作为伦理体系所具有的在整体上对个体的驾驭作用,与此同时,也从个体对整体的评价之中产生了个体对作为“体系中的人”的向往。
很显然,这个向往是个理想型的目标,黑格尔在此所要构建的就是这样的理想型社会,而在此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国家制度便具有变革社会现实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也能保持着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因为正是在黑格尔那个时代,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共同体的德国都处于分裂状态,黑格尔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但他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作出构想。罗森克朗茨对黑格尔《伦理体系》及其耶拿时期的手稿的定位颇高,在他看来,它们构成了《哲学全书》的胚胎,而此后关于伦理共同体的观念基本源自于此。(18)Karl Rosenkranz, Hegel als deutscher Nationalphilosoph, Leipzig:R.E.Prutz, 1870, S.43.黑格尔亟需从个体层面上恢复人作为劳动主体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的具有主体性的道德意识,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对于当时的普鲁士王国,黑格尔寄予了厚望,他希望建构起强大的国家制度,从上而下地对整个国民的性格进行改造。罗森克朗茨认为,黑格尔的这个设想就是来自于柏拉图的国家理念,因为黑格尔显然不同于德国的自然法的历史学派,因为他所秉承的是从古希腊政治学到康德和费希特这一系的国家学说。(19)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 S.159.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反复提到“教化”(Bildung),他显然是看到在当时的德国要实现整个国家的统一,就必须要有作为整体的公民的出现,也就是要从政治意识上团结每个人。换言之,在黑格尔那里,公民亟需教化的原因是启蒙精神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呼应,而市民社会的发达也将个体的生活完全置身于日常的私利之中,进而忘记了作为共同体的团结因素。因而,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必须要建构起作为超越私人生活的国家意识,也就是亟需要培育“体系中的人”以顺应国家统一的潮流,进而把这个整体主义的方案在实践中变成现实。
结 语
从以上三个“伦理性”的评述中可以看出,罗森克朗茨将黑格尔在耶拿的这部手稿命名为《伦理体系》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在整部手稿中,黑格尔都在论述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而这个进程就表现在他作为“体系中的人”所具有的整体意识。当然,罗森克朗茨对手稿精神的直觉把握也会存在些许的争议,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在于,他可能有意要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法哲学作为整体主义的实现方案,而这个方案也与作为个体的自由主义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冲突。因而,在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中也就有对黑格尔的批评,认为他是以牺牲了个体的自由为代价,而将国家整体作为首要的因素,就此而言,很有必要从根本上对其整体主义做些现代性的重构,以便赋予社会可供分析的内容。对此的批判当然有其现代的背景,尤其是在西方个体主义盛行的年代,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方案很难获得认同,这也是长期以来,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对黑格尔思想的当代复兴往往会遭遇挫折的原因,而提倡个体主义的康德方案尽管有诸多的问题,反而成为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想。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做出两个层面的分析:首先,就黑格尔而言,选择以体系化的方式去整合他此前的思想,是因为他认为他那个时代尤其需要从总体上实现对个体和共同体的同一,黑格尔更看重的是其理论的历史价值;其次,就后黑格尔时代而言,很显然的是,黑格尔的古典精神已经成为过去,后来者已不可能像黑格尔那样在一个庞大的理性体系中去建构世界,就此而言,在后黑格尔时代,人们往往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方式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改造,用以回答各自时代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