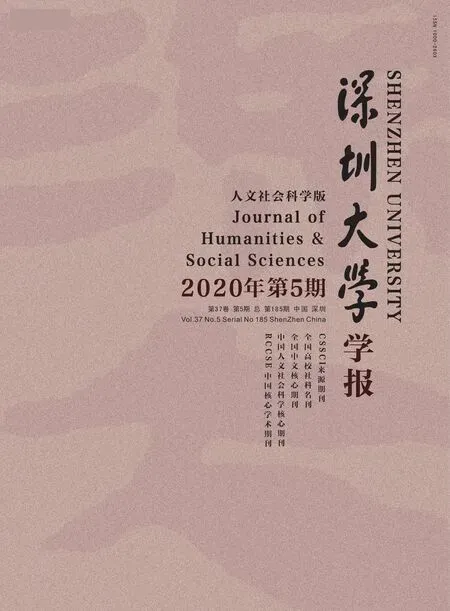网络女性主义“女性向”叙事新变及方向
2020-12-25江涛
江 涛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21)
被誉为“先知”的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媒介自身所取得的任何发展都会引发人类社会的巨变。 而第五次媒介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互联网时代,它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工作、交往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在文化领域也催生出了新的业态:网络空间中各种新的文化现象如雨后春笋,而传统文化也在“网络移民”后获得了新的生机。 本文重点关注的便是在媒介革命的语境下,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在互联网时代中所呈现出的新变。
由于网络与现实之间横亘着 “次元之壁”——“二次元”(虚拟世界)中的“女性向”空间不受“三次元”(现实世界)的束缚,这便为女性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从文本生产、传播到阅读、交流和评论的新平台。 更重要的是, 在整个线上的文学活动链条中,由于在理论上屏蔽了男性的介入,是“女性在逃离了男性目光的独立空间里,以满足女性的欲望和意志为目的, 以女性自身话语进行创作的一种趋向,是网络空间的产物”[1],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比伍尔夫所期待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更为自由。 那么,在这样一个既特别又特殊的空间内衍生的文学创作,也必然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与价值意义。
一、从“精英女性主义”到“网络女性主义”
众所周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虽在20 世纪初就进入了中国,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它最初只是启蒙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附属品,与其他男性精英话语一同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尽管当时产生了一批如冰心、丁玲、冯沅君、萧红、卢隐等知名女作家,她们的作品也有着较强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但总体而言仍是一种“花木兰境遇”(克里斯蒂娃语)式的写作,她们作为现代第一批“逆女”,发起了对封建宗法制度下孕育的父权制社会的反抗,诉诸的是生而为人的平等权利,而对“做女人”的权利,即两性差异造就不同人生境遇的追问几乎浅尝辄止,更难以在文本中建构一种属于女性的审美意识形态,所以通常不认为这是女性主义写作。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写作是在20 世纪90年代左右才从新启蒙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旁逸斜出,极力彰显了一种属于女性的审美形态。 “90年代的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女性写作显露出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 ”[2]所以,女性主义写作更强调一种迥异于男性以及与男性共享的公共意识与文化趣味的、凸显女性特质的创作倾向,尤其是对女性私人化的生存经验、生命感受、欲望需求的表达,以及由此生成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去对抗、颠覆传统化、历史化、男性化的宏大叙事和美学观念。
然而,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女性主义写作为什么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才真正产生?其中的原因自然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 城市之所以作为现代性的空间载体,是因为它提供了人们依靠智力与知识来代替体力去获得生存和竞争的可能性,这也就等同于“提供了一个将没有生产资料、体力先天赢弱,只能在闺阁中依靠性别的附属功能去依附和满足男性的‘女、妻、媳、母’们解放出来的契机,带给了她们一个依靠着自身智慧去同男性在同一层面中竞争的机会”[3],因此,在20 世纪90 年代横空出世的陈染、林白、海男、卫慧、绵绵、安妮宝贝等女性作家笔下,所有的故事几乎都与城市有着不解之缘, 她们在城市中寻觅 “自己的房间”,大胆暴露着女性幽闭、敏感乃至惊世骇俗的私人生活,甚至不惜以“身体”为准绳去渲染一种顾影自怜的迷狂和离经叛道,以求凸显出一种被男性中心神话所遮蔽的女性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观念。
可以说,20 世纪90 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绝对权威,它不仅强调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更彰显了女性语言和女性美学,这是“精英女性主义”写作所取得的重大突围。 然而不幸的是,随即而来的商业大潮很快便裹挟了它的正向价值,一些女性主义写作(卫慧、绵绵等)跌入到了另一个泛娱乐化的陷阱里:曾经对抗男权文化的身体利器、私人生活和个人战争,被“俘获”进了男性窥视的欲望之眼里,变成了情色意味的高床软枕和纸醉金迷。 另一方面,城市中那个“自己的房间”虽是女性的“根据地”,但当你在“房间”中完成带有女性革命意味的作品后,依然还需走出“房间”,进入公共领域去接受大众的审阅,你仍然需要面对那套来自男性建构的 “文学经典”体系的挑剔和规训。 可以说,城市为女性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温床, 但绝不等同于贴上了女性的标签,优越的男权文化和男性标准犹如幽灵般时刻监控着企图反叛的新一代“逆女”。 于是,女性主义写作的意义也便渐次消解,变成了一场虚张声势的独角戏。
事实上,精英女性主义们从一开始以剑拔弩张的姿态对男性神话的宣战就注定了它的偃旗息鼓。因为在这个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现实空间里,男性的意识形态早已如一套金科玉律植入了女性的潜意识里,即便女性在自我觉醒与启蒙中衍生了对抗性的异质力量,也不足以撼动它的根深蒂固,所以进入新世纪以后,传统的写作领域中女性创作与女性文学依旧长盛不衰,但几乎仍然只停留在了对女性的个体命运、情感、权利的关注上,缺乏更进一步的言说空间。
直到第五次媒介革命的发生。 被誉为“先知”的麦克卢汉认为,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基本构型产生重大影响,而网络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人、计算机和信息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不仅能模拟现实更能超越现实的“赛博空间”,它是信息传播的平台,更生产着信息,它的无边界性与虚拟性或许可以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温床。 英国沃里克大学的塞迪·普朗特(Sadie Plant)认为,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能够赋予女性新的权力,女性在现实空间中难以获得的平权与自由,可以在网络中得到某种想像性的补偿。 事实上,早在1996 年,霍尔就提出了“自由的赛博女性主义”( Liberal Cyberfeminism)的概念,“强调网络能给女性和女性主义带来一种解放的效应”,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学术界并没有达成统一共识,主要研究的重心只是将女性主义作为基点,结合当代先进的网络科学技术,考察性别与科技之间的关系。
国内对于“网络女性主义”的定义和研究与西方学者们的研究路径截然不同。 它不是20 世纪90年代“精英女性主义”在网络中的延伸,而是“在网络天然形成的欲望空间和充沛的情感状态中生长出来的,它是未经训练的、民间的、草根的、自发的‘女性向’”[4],主要通过小说、漫画、剧本等亚文化创作传递一种进步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其本身虽缺乏具体的理论建构,但又天然地与“精英女性主义”有着近似的功能和目的——反抗男性霸权与追求女性平权。 所谓“女性向”,原是指日本社会在二战后推行的一套刻板的性别分工秩序 (男性从小读男校,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女性从小上女校,毕业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由于绝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中男性是不在场的,于是便渐渐在这一群体内部形成了一个“男性世界的死角”[5],并衍生出专属于女性的娱乐文化空间,如女校文化、女性ACG 文化、女性俱乐部等。“男/女性向”空间的出现直接造就了日本流行文化在性别上的分野①,并在20 世纪90 年代末引渡中国,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无边界性寄生于其中,最终发展出了与日本现实社会类似的网络“女性向”空间。
在过往的研究中,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对于新媒介文化多抱有偏见,即便是在性别研究领域,同样认为受商业消费主义主导下的流行文化是男性的欲望投射。 不可否认,这一逻辑直到当下依旧成立。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对流行文化盖棺定论,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女性向”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几乎都是当下的“独生女一代”,因代沟问题,亲子间共同语言不多,难以有效沟通,因此互联网便成为了她们彼此慰藉情感、宣泄不快的载体,并迅速发展成专属于她们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社区、女性频道等),她们在这个远比伍尔夫式的房间更为开阔的“女性向”空间内行使自身的权力,而自给自足的“女性向”空间,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在逃离了男性审阅的目光之下,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生养、放纵自身欲望的想像空间,从而使女性逐渐意识到自身被压抑已久的女性经验与女性价值。所以在其内,不仅产生了全权由女性自发“册封”、“供奉”的文坛大神及经典作品,还推出了相关的诸如音乐、动画、广播剧、舞台剧等周边产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她”的产业链,继而也就摆脱了“精英女性主义”创作无法突围的桎梏,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也更为本质的力量。
二、从言情到反言情:主体性的“失而复得”
与“男性向”创作更多地关注家国天下和功业千秋等宏大主题不同的是,“女性向”小说多以情义千秋为焦点,这自然是纸媒时代的大众通俗文学所遗传下来的血脉。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造就了男性有多种人生选择的机会:进,可入驻庙堂,获得功成名就;退,可抽身离去,相忘于江湖,而女性却受制于“三从四德”的金科玉律,人生一世仅限于家庭内围,所以相较男性热衷追逐权力与功业,女性则更多地考虑家宅内部的情感维系,于是,爱情这种两性情感关系便成为了女性最理想的渴望。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 年代,以琼瑶、亦舒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风靡一时,奠定了“女性/言情”的基调,进入网络时代后,从安妮宝贝擅写年轻女性在都市中的情爱遭遇,到穿越、耽美、宫/宅斗、种田、校园等更为精细化的“女性向”类型文,几乎都与“情”息息相关,言情,早已被默认为是女性创作的普遍主题。
但对爱情立场的转变却值得细细咀嚼。 首先,网络“女性向”叙事中存在着大量延续传统言情小说的固定模式,如流行一时的“总裁文”、“甜宠文”、“高干文”等,这些言情文中的女主被网友们戏称为“玛丽苏”,她们往往容颜姣好、才貌双全,深受高富帅男主最专一的宠爱。 人类心理学认为,追求完美是人性本能,但普罗大众却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收获最完美的体验,所以依靠文学寄托白日梦就成了重要手段,即“爱情乌托邦”的建构与“代入感”②的养成。 长盛不衰的言情文恰恰满足了青少年女性对理想爱情和理想生活的幻想与憧憬,这背后,除了欲望的驱动和极度自恋之外,依然可察觉到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对女性意识的潜移默化,即完美女性总是渴望更完美的男性对其的征服或专宠。
可以说, 网络言情小说是男权主导意识下的“超生儿”,在传统的言情文里,主CP 多为“男强女弱”的固定搭配:灾难不断的“白莲花”女主必须搭配一个强大英俊的男主将其从水生火热中救出。而当代网络言情小说中,“玛丽苏”相较于“白莲花”而言大多能力较强,有着职业女性的独立和生存技能,也有着不弱于男性的处事能力,她们原可凭借自身能力改变其从属的社会地位,甚至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建构,但让人惋惜的是,她们在遇到完美男主后更愿意做其事业或家庭的幕后英雄,而不是去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 特别是一些穿越小说,如《步步惊心》中的若曦、《醉玲珑》中的凤卿尘、《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盛明兰等,这些“玛丽苏”女主在穿越回古代后,从未想过利用自己的现代学识给古代社会带来文明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反而无比尊崇古人的生存伦理,她们默认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甚至在风云变化的历史深渊中丧失了自身的存在感,沦为男性(权力)或宠或虐的被动客体。
总之,玛丽苏文虽是“女性向”叙事中最常规的文类, 但它对女性主体性的重塑却是喜忧参半的:她们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一切能力,但却仍以男主意志为中心;她们原可活得独立自主,但却仍旧落入了“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的男性逻辑里。 因此,玛丽苏文是血脉不纯的“女性向”叙事,它所迎合的女性欲望不过是被男权文化所异化的女性们关于“男神”的白日梦,叙事模式中大量存在的上帝视角、 主角光环和作者投射的自恋心态,皆昭示着男权社会下女性普遍痴迷的恋爱欲、 财富欲、 权利欲与虚荣心。
然而,让人倍感兴奋的是,类型化的言情文脉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创新性的“反类型”写作——徜徉在“爱情神话”的中现代女性,总有一天会大梦初醒,开始用心谋划个人的发展,于是,真正意义上重塑女性价值、建构女性成长话语的“反言情”小说便应运而生。 这类叙事虽涉及爱情,但重心已不再是编织一段浪漫的纯爱故事以满足女性对完美男性的渴望,而是将女主置于一段爱情之殇后,主动断念,开始谋求个人的发展,也就是说,男性只是充当了女性苏醒与成长的“催化剂”。 比如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中,陈孝正是作为郑微终将腐朽的青春证词;鲍鲸鲸的《失恋33 天》里陆然对黄小仙的背叛,让她开始反思自我;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 中甄嬛对渣男皇帝的复仇……这些女主都相继领悟到了依靠委曲求全所维系的爱情果实终究是海市蜃楼,远不如自身利益的得失来的重要。
于是我们发现,这类“女性向”叙事便从传统言情文中“有一个男人值得等待”,转向了“有一段情需要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完美的“男神”相继原形毕露,被丑化为各种“渣男”,他们的自私和胆怯让原本有所期待的女性们彻底寒心,所以,她们从“愿得一心人”的梦幻爱情中猛然醒悟,言情最终转向了它的反面。 其中,女性主动为自我抗争的现代价值观得以彰显。 如《后宫·甄嬛传》的作者流潋紫就曾说过:“中国的史书是属于男人的历史,作为女性,能在历史中留下寥寥数笔的只是一些极善或极恶的人物, 像丰碑或是警戒一般存在, 完全失去个性。 ”后宫女子作为服侍君主、繁衍子嗣的工具,本就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为得帝王恩宠,互相倾轧,只有甄嬛敢于向最高男权发起挑战。 她对皇帝的复仇,与1968 年“女性攻占话语权”和1789 年“攻占巴士底狱”的女权运动有着隔空呼应的意味,后者标志着女性逃离了囚禁她们的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与男性争夺地盘与话语权,正如甄嬛最后的大权在握;前者则是女性针对支配、压迫和荼毒她们的父权制社会的最高权力发起的绝地反击,正如甄嬛对皇帝的谋杀,均带有革命性意味。
三、“女尊”与“女性向”历史叙事:女性的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
当女性历经了一段注定失败的爱情之殇并逐渐意识到了“我在故我思”的主体价值后,便不再满足以个体的独立自主而获得与男性的平分秋色,而是渴望跳出传统的性别藩篱去重构一种新的性别秩序,于是,绝对主导权力的拥有便至关重要,而女尊文满足的正是这一诉求的“女性向”叙事。
女尊文是“网络女性主义”创作中的激进化产物,它往往“借助架空历史或创世的设定,作者有权力自行设计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包括性别秩序、婚姻制度等,能借助各种颠覆性的想像,构架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时空”[6]。 在这个“我的地盘听我的”世界里,传统的“男尊女卑”被强行反转为“女尊男卑”,女性不仅社会地位优于男性,甚至在大量“逆后宫文”③里,还可以享受“一妻多夫”的权利。 比如祈容的《重生宠夫之路》是女尊文中较为普遍的“女强男弱”的设定,丈夫总是被妻子宠溺;竹露清响的《穿越女尊之纯情天下》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女性水纯然穿越到了一个女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充斥着各色花样美男,却都倾心于她,最后她娶了10 位夫君,享受着“齐人之福”。类似的还有风间名香的《舞娘十夫》、北藤的《女皇选夫》、无心娇娃的《无盐女美男多多》 等几乎全是一妻多夫的设定。这类女尊文普遍在开篇便会花大量笔墨向读者交代架空世界的具体法则和伦理,以设定的方式强行反转既有的性别秩序,将男权一统天下的父权制社会硬性修改为由女性全权主导的“母系社会”,而养成了代入感的女性读者们便可在女尊的世界里享受一把前所未有的女权至上。
女尊文在颠覆男权文化上的激进,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对以杰梅茵·格里尔和凯特·米勒特等人为首的西方激进女性主义流派的跨时空回应。 激进女性主义者们发现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它夸大了男女的生理差异以确保男性拥有支配角色,女性拥有附属角色,而格里尔在《女太监》一书中认为,女人是被动的性存在,因为她被男人阉割了,所以她主张解放妇女的性,并将它表现在人格里。 总之,她们企图用各种激烈的方式为妇女寻求摆脱压迫的路径,但无奈的是,这些方式因过于激进而在现实社会中阻力重重,甚至受到了女性内部的激烈反击。 而网络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游戏性虚构”④,即不以现实世界为依据,只以欲望满足为目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我时代”的虚拟游戏。 因此,当女性意识到自身受压迫的根源却又无力救赎后,索性逃往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去建构一个随心所欲的女权世界,以幻想的方式短暂地为西方激进女性主义流派找到一条摆脱男性压迫的新路径。
但问题在于,这类女尊文所架空的世界太过天马行空,而呈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荒谬感,人为设定的方式虽强行赋予了女性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却无力填补这一结果与现实的万丈鸿沟,更无法回答女性经验应该如何介入历史,如何在历史中重建主体性和自身价值等实际问题,因此它只提供现实的释放,而非现实的解放,用犬儒主义的鸵鸟心态满足了女性读者一时的意气用事。 但不可否认,女尊文在处理两性关系上虽过于激进,但对男权的反击却是伤筋动骨的,而与其并驾齐驱、同样需借助架空历史或创世设定的“女性向”历史叙事却另辟蹊径,将女性经验融入到了家国天下与苍生之念中,继而赋予了女性可与男性平分秋色的政治权力,最终将“herstory”潜移默化进了history 的故事中。
古人有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言下之意便是男女分工各有不同,越俎代庖被视为不伦,它讽刺的是女性的篡权乱世。 在2004 年晋江原创网连载的《且试天下》却有意颠覆了这一性别分工。 作者以架空的方式虚构了一个风、丰、皇三国从分裂到统一的一段风云变化的历史时代。 女主风惜云原是风国的惜云公主,后即位为国王,她稳重大气、睿智无双,乃巾帼枭雄。 她以女性身份与丰、皇二国竞逐天下,实力与权谋不逊于男性。 不仅如此,她还不是那种“去女性化”的铁娘子形象,有着头号女主该有的风华绝世,在感情方面也呈现出了女性一以贯之的细腻、专情,最终与夫君丰兰息归隐,不问世事。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只作为男性欲望之眼里的美色,比如历史言情小说的男性往往“不爱江山爱美人”,女性是男性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在野史秘闻里,女性又成为了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如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与周幽王为褒姒一笑的“烽火戏诸侯”。 总之,女性只是一个拥有了美艳外表的躯壳,除了以色示人,她的内在是靠男性给予具体的意义。 而风惜云的形象却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男性霸权模式,她不仅拥有美艳外表,也有着独立的内在意义,她将自己的女性经验注入到了整个国家和历史的建设中。
乘着《且试天下》这一首开先河的设定,之后的“女性向”历史叙事一方面与男性叙事一样敢于触及宏大驳杂的历史,另一方面却也在暗地里实施着偷梁换柱的性别革命,即女性以本色示人的同时,却依旧同男人一样出将入相、参与家国大业。 如海晏的《琅琊榜》中霓凰和夏冬,她们身为女性,却可上阵杀敌、参与朝政,以女儿身行男儿事,这种设定也就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男性所指权力、女性所指欲望的刻板结构。 特别是随着《琅琊榜》的同名电视剧大获成功,这种违反传统性别结构的范式逐渐走出了网络“女性向”空间,进入了更为主流的大众视野。
所以,女尊文和“女性向”历史叙事作为“网络女性主义”创作的一体两面,前者的意义在于反转了女性在情感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化被动为主动,完成了女性的修身与齐家,后者则颠覆了女性与政治历史的无缘,以强势的女性主体进入庙堂,获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力,从而完成了独属于女性的治国、平天下。
四、耽美:“性别革命”与“破壁逆袭”
如果说女尊文和网络“女性向”历史叙事只是停留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中的“小打小闹”,那么耽美文则完全破坏了这一结构,完成了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全面颠覆。 耽美文是“女性向”叙事中极具先锋性的文类, 其作者与读者皆是青少年女性,而文本所描写的主题却以“美少年之恋”为情节,主人公几乎是清一色颜值较高、个性鲜明的美少年,在文学理念上追求一种氤氲之美。 耽美小说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最早深受日本漫画的影响,原本只是网络中的小众文化,甚至被毛尖教授一度定性为“资产阶级二代的美学语法”[7],但正是由于这是由女性编织的男性故事,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也就天生具备了某种异质性。
众所周知,女性在传统叙事中一直被视作男性欲望的客体投射,是被“凝视”(劳拉·穆尔维语)的对象,而耽美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女性拥有了幻想男人恋爱的权力,当女性行使这一权力时,无形当中她就从一个被动的客体投射转向了作为权力实施者的主体,男性反而沦为了被女性凝视与想像的客体。 同时, 这种颠倒的模式也促使女性读者“以‘窥视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在幻想中体验到男性气质所带来的权利和地位,从而获得身份置换的愉悦,实现长久以来被男权制社会所压制的女性欲望的表达,使女性获得审美的主体性身份”[8]。
首先,从耽美文的发展模式来看,早期耽美小说其实是传统言情文的变体,基本沿袭了言情小说中“男强女弱”的设定,只是把女方置换成了弱小的男性,但有趣的是,这种设定很快就遭到了读者的厌弃,并催生出了各种不同的组合设定,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欧美同人圈兴起的ABO 文,更是展现了极强的性别实验色彩。 ABO 指的是一种世界观的设定,它将人的属性分为3 类,并通过两两交叉组合的实验,实现了6 种性别的可能性,这些灵活多变的组合模式彰显了耽美创作对于亲密关系和性别角色的多元化尝试。 于是,在这些看似游戏的文学实验中,也在无形当中拆解了人们对于“男性/女性”, 以及性别背后所对应的那套刻板的审美文化的固有认知。 正因如此,笔者以为,“女性向”创作中的耽美一脉,已触及了“精英女性主义”创作未曾抵达的领域,即对性别本质主义的破除,这对于男权文化的颠覆和嘲弄是伤筋动骨的。
正如前文论述,“女性向”创作是部分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女性在网络时代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集体臆想,由于它隐藏在“二次元”世界里,便短暂形成了一个隔绝男性目光的“母系社会”,成为与“精英女性主义”遥相呼应的“网络女性主义”的绝佳实验场域。 由于互联网本身的社群属性(兴趣相投的网民汇成的部落格),“男/女性向”各自恪守一方天地,彼此相安无事。但当这种“女性向”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蕴含的反叛性因子便极有可能冲破空间的壁垒,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抗性力量,特别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解构,以及对男性美学和气质的颠覆颇为独到。 约翰·麦克因斯认为“男性气质不是个人身份的特征,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下形成的意识形态机制”[9],这一见解与199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酷儿理论十分吻合。 巴特勒就认为,人没有固定的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其实是对 “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 的一种表演, 同时, 酷儿理论还反对“男/女”的二分结构,提出了超性别(transgender)概念。 “所谓超性别包括异装和易性,还包括既不异装也不易性但是喜欢像另一个性别的人那样生活的人”[10]。 由此可见,酷儿理论提倡超越各种性别类型的划分,并发现了性别身份其实是一个“被建构”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两性差异被建构成一种尊卑秩序连同所对应的审美特征也被相应地固定排序。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些言传身教的背后,是对刚毅、坚强的男性审美气质的维护和稳固,而这种气质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是优于女性审美气质的,所以日常生活中,雄性化的“女汉子”往往能够被人们所接受,而女性化的“娘娘腔”则极容易被厌弃,这背后自然有着上野千鹤子所提及的“厌女症”在作祟。 但耽美小说对于男性形象的多重性的实验在某种程度上便破解了单一刻板的男性气质,比如小说《凤于九天》中的鹿丹、《魔道祖师》中的蓝忘机等形象,他们身为男性,却有着女性的绝世容颜,喜欢着女装,有女性温柔、细腻和敏感的一面,同时又保留了坚毅、果敢的男性气质。 当这些拥有多重性别气质的男性形象受到越来越多女性读者的喜爱和追捧时,就在青少年女性群体的内部自发地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主流性别文化的美学力量,甚至逆向影响了大众的审美倾向。据笔者调查,20 世纪80~90 年代受到追捧的男性明星如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等,几乎都是“孟加拉虎”(张辛欣语)般的硬汉形象,但当下的审美风向正在悄然改变,一些妆容精致、长身玉立却如弱柳扶风的“小鲜肉”们深得饭圈女孩的钟爱。这种审美文化的流变,或多或少都与耽美的性别实验有一定的关系,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与主流审美文化(也是男性审美文化)所匹敌的新的美学原则与美学权力。 总之,去性别本质主义从耽美小说中孵化而出,已渐渐打破了“女性向”的壁垒,从“圈地自萌”开始走向了“对外输出”。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耽美对于性别本质主义的革故立新,是在女性们猎奇的欲望目光之下完成的,虽然影响力仍在扩大,但与学院派“精英女性主义者”们所主导的在现实层面中对男权的反抗与女权的诉诸等具有政治意味的行为相较,其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五、众矢之的,还是新的机遇
我们知道,相较于更为专业化、权威化,也更为高门槛的传统出版业而言,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互联网1.0 时代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怀才不遇”的文学草根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和表达思想的平台,呈现出了无穷的生命力。 但是,这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却并没有持续多久,早期“我手写我心,我文抒我情”的网络文学生态机制在2003 年VIP 阅读制度的建立与商业资本对文学网站的把控之后,便在悄无声息中向市场“缴械投降”。
起点中文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文学网站,红袖添香、晋江文学城等紧随其后。 VIP 阅读制度指的是一种付费的在线阅读,也就是说,网民必须注册并充值账号成为VIP 会员才能阅读连载的作品,而付费阅读所得到的收益一方面用于网站自身的维护,另一方面也用于支付作者的稿酬。 于是,以写文为生的网络职业作家开始与日俱增。VIP 阅读制度的建立, 表面上看促成了网络类型小说的蓬勃发展,但其背后却是商业资本对其的强势操控。 虽说网络文学的商业性与文学性并非绝对二元对立,但面临生存压力的网络作家们在写作之前务必会优先考虑粉丝的口味,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取悦读者,才有可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从而在竞争残酷的网文市场中存活下来,如果只是一味地“我手写我心”,恐有失去衣食父母的危机。 所以不得不让人担忧的是,网络文学在遭遇商业帝国的入侵与征用后,原本的创造性与反叛性等正向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更多地被程式化与娱乐化所取代,最终沦为法兰克福学派极力批判的文化工业的生产与消费。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网络文学成为了学院派攻击的众矢之的:“消费时代网络文学女性写作不断在揣摩和迎合读者的需求和审美取向……文学本该具有的艺术担当被世俗的感性愉悦所遮蔽……”[11]。
另一方面,如果说市场的入侵与网文的日趋商业化之间仍有回旋的余地,那么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则彻底为网络空间重新立法。 2014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刊发了《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一文,指出网络文学存在着数量大质量低、抄袭、盗版、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监管不善等问题[12],2015 年 1 月 31 日的《法制日报》刊登的评论文章《规范网络文学是净网重要步骤》更是直指网络文学在创作上的弊端:
考虑到网络文学的阅读群体包含着为数众多的青少年, 人们对于网络文学所谓的YY等不良倾向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如果仅仅是谈论宫廷里的风花雪月,或是在某个子虚乌有的大路上称王称霸,又或是历经磨难修炼到长生不老天下无敌,给人感觉尽管失之荒谬,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 最多将其斥之为精神麻药。 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在网络文学中不乏诲淫诲盗之作,比如色情、凶案、黑道等题材,关于一些细节的展开极尽想入非非之能事,传递的负面信息和导向是十分明显的,对于一些价值观、人生观尚未完全成型的青少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言而喻。[13]
一场轰轰烈烈的净网运动就此打响。 不仅起点、晋江等主流文学网站中大量网文被锁,更是下架了部分网剧、动漫,如2016 年年初在全网播出的耽美剧《上瘾》在尚未播完就被责令禁播,引发了网民的讨论。 这场净网运动的突如其来,一方面说明网络文学确实存在种种问题,需要监管和引导,同时也预示着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重点治理这块曾经充斥着低俗、暴力的泥沙俱下之地。 从网络文学特别是“女性向”叙事来看,无论是穿越、宫斗、女尊还是耽美,这些文类所推崇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都与主流价值观存在着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被重点整改也就顺理成章。 笔者认为,整改并不意味着网络女性主义“女性向”叙事永远都会是为人诟病的众矢之的,反而会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发现,规范后的许多“女性向”创作逐渐突破了网络类型小说的局限,在涉及一些严肃问题的思考的同时,又具备了一定的人文主义价值关怀,比如priest 的很多小说虽属耽美类型,但“美少年之恋”已不再是小说的主旨,只是一个附属的背景板,作者对社会生存境遇的透示,对个体价值的探索,对人类文明未知命运的担忧,甚至是对严肃文学“数据库”式的引用,都彰显了作品已具有了严肃文学的“经典性指向”。
总而言之,在网络中生成的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女性向”叙事,原本属于一种脱离于主流与精英文化的亚文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颠覆了既有的性别文化与性别秩序。 但是,它对性伦理(女尊文“一女多男”的设定)的直白讨论与性禁忌(耽美“美少年之恋”的设定)的实验性探索,也的确触及了主流价值观的红线,成为了重点规范的对象。同时,由于网络类型文与生俱来的商业与娱乐属性,又导致了大量程式化、低俗化、感官化的创作层出不穷,以及抄袭、版权等纠纷屡见不鲜,最终直接引发了精英话语对其的大肆批判。 而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规范与引导,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给予网络文学一次“正名”的机会。 因为无论何种文学,何种类型、何种套路、何种人物形象,使用何种技能、实现何种目的,都需在悦心快意的阅读快感之后彰显人文主义的精神取向,在天马行空的想像象中坚守最朴素的道德情操,这不仅是网络文学理应保证的精神品格,亦是其称之为“文学”所本该具备的价值底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作为下里巴人的网络文学“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14]。
注:
① 在日本,“男/女性向”的消费概念已成为普遍现象,不仅有专门提供给女性阅读的书籍、漫画、剧场、日用产品,就连公共空间中也有专门的“女性向”场所,比如女校、电车上的专用女性车厢等。
②所谓“代入感“即读者将自己想像成作品中的角色。
③ 逆后宫文:指女性作品的一种,一般的后宫文指的是一男配N 女的模式,而逆后宫文强调的是一女配N 男的模式。
④传统的文学创作中所塑造的世界必须是以现实世界为模板,从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即便是现代主义的超现实写作,它的文学功能也在于借助一个变形的世界去帮助读者认识现实背后的本质和真相,所以传统的文学创作都必须符合一种公认的现实逻辑。 而网络文学的“游戏性虚构”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真实感,是对现实的模拟而非模仿。 它的“叙事”是建立在“叙世”基础上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设定”基础上的。 (详见邵艳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