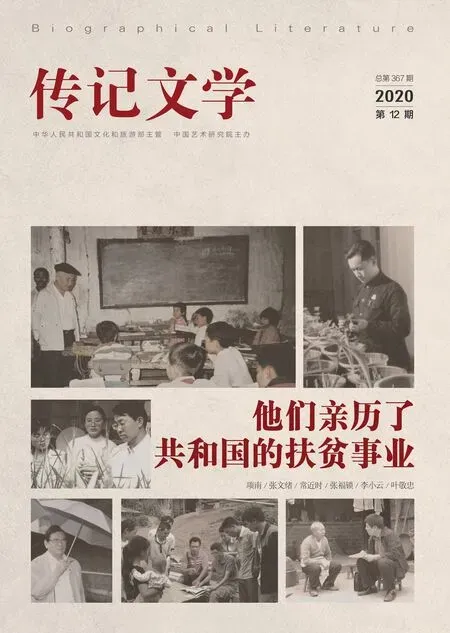从师记(下)
2020-12-25刘跃进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三
工作两年以后,我终于获得报考研究生的资格,正逢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托招收第一届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班,学制两年,毕业后写论文,再回来答辩,在高校工作的老师可以不变动人事关系。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起码可以留住北京户口。读大学伊始,我在图书馆书架上瞥见过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赋校注》,纸张发黄,落满尘土,我还以为作者是清朝人呢。后来知道姜亮夫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居然还在招生,怎能不欣喜若狂。
开学典礼上,姜亮夫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梁启超先生赠送的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姜先生是梁启超的学生,梁启超又是康有为的弟子,故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系宣统朝南书房行走,是溥仪的老师,故曰“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我们是姜先生的弟子,按辈分,应当是清华学堂诸导师的三传弟子。姜先生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准备吃苦,实事求是地治学;二是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学习。姜老拟定的教学大纲:
一、必修课:文字学(以《说文》为基础)、音韵学(以《广韵》为基础)、训诂学(以《尔雅义疏》为基础)、文献学(以《文献通考叙》为基础)、目录学(以《汉书·艺文志》为基础)、版本学、校雠学(以《通志·校雠略》《校雠通义》为基础)。
二、选修课:《史通》《文史通义》《通考总叙》《文心雕龙》《国故论衡》《国史要义》《因明入正理论》《墨子》《史记》《资治通鉴》《中国书制史》。
三、专题报告:

本文作者1984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准考证

本文作者研究生入学通知书
1.中国地理:从《汉书·地理志》到《天下郡国利病书》,请陈桥驿主讲。
2.中国工艺:从《考工记》到《天工开物》。
3.中国农业:《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请胡道静主讲。
4.中国居室建筑史:古代宫室制度和《营造法式》。
5.天文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6.中国逻辑学,即先秦名辩学。
7.印度三宗论与佛教提纲。
8.中国艺术综览,请王伯敏主讲。
9.书画同源。
10.古文学概论。
11.历代职官变迁。
12.本草与医药。
13.体育训练。
14.音乐。
15.礼俗与民俗。
16.中国社会发展史。
17.中国古代社会。
四、十二种先秦古籍选读:《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周易》《老子》《论语》《大学》《礼记·曲礼》《屈原赋》。
每个学生毕业后,有“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低限是学术史)的能力,就各种学术(分类)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
在我的求学过程中,在杭州大学古籍所读研的两年至关重要,完全改变了我的读书观念。大千世界,图书无限。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关键是如何读。这就需要掌握读书方法。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倡导一种“读书有限偷懒法”,就是要充分掌握目录学知识,在书海中自由航行。我在《予望之》小引中说,在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讲治学体会,讲清华学校往事;沈文倬先生讲校勘学;刘操南先生讲《诗经》与天文历算;雪克先生讲《汉书·艺文志》与目录学;郭在贻先生讲《说文解字》与训诂学;张金泉先生讲《广韵》与音韵学;平慧善先生负责协调安排……在人情浮竞中,我感受到一种超脱的宁静与学术的坚守。庄子说:“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大约就是这种境界。这种境界的核心就是放弃功利目的,通过有计划的阅读,掌握相关领域知识。即便是做文学研究,也要明白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姜老在培养方案中说得很清楚,举办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班,不是要培养电线杆子式的专家,而是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听蒋礼鸿、郭在贻先生讲训诂学感受很深。我们看相关著作,动辄段玉裁如何说,王念孙如何说,就是没有自己的说法。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多是自己如何说。郭在贻先生的《唐诗异文释例》针对中华书局校点本《全唐诗》的异文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明近代汉语知识对古籍整理的重要性。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这才是硬核学问,不服不行。
选择硕士论文题目,颇费周折。最初,通过复旦大学王继权老师的介绍,我与黄山书社胡士萼先生联系,想整理一部皖人集子。虽然没有做成,也借机了解了古代安徽作家的情况。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看到一部戴名世的《忧庵集》抄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戴名世集》里没有收录。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有戴名世《忧患集偶钞》不分卷,与《孑遗录》一卷合刻,康熙宝翰楼刻本。又查蒋元卿《皖人书录》,安徽省图书馆亦有收藏,我给蒋先生写信求教,蒋先生给我回信介绍此书情况。《皖人书录》著录的是手稿,我觉得未必是定论,于是撰写了《极摹世事炎凉 曲尽人情变态——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发表在《江淮论坛》1994年第1期上。

杭州大学古籍所1984级研究生和老师们合影。前排左起:张金泉、郭在贻、平慧善、姜亮夫、徐规、刘操南、王荣初,后排左起第八位为本文作者
在清华大学翻阅资料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吕天成的《曲品》,那个本子是乾隆年间杨志鸿的抄本,与《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的《曲品》差异很多。我把全文抄录下来,根据不同的本子进行比对,草拟了《通行本〈曲品〉校补》,得到沈文倬先生的首肯,发表在古籍所论文集《文史新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中。我准备以清华大学藏钞本《曲品》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后来了解到吴新雷、吴书荫等前辈都曾有过专题论文,吴书荫先生还有《曲品校注》。我学养不够,知难而退。

前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后排左起第三位为本文作者
浙江古籍出版社计划整理朱骏声及其后人遗著,郭在贻先生认为可以选取一本整理出来。此后一段时间,我泡在浙江省图书馆,除查阅《吴县志》外,还读到朱师辙编《吴郡朱氏两代遗著书目》,并附有自己的著述目录。由此确知三代人分别号石隐、半隐、充隐。故此,王季思先生给他们的文集取名《三隐堂文集》。我初步拟作《三隐堂著述汇考》,争取将朱氏三代著述全部浏览一遍。我先撰写了《朱骏声著目述略》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上。经郭在贻先生介绍,我拜访了许嘉璐教授,他告诉我他的学生也在做这个选题,劝我放弃。
在杭州大学,陈桥驿先生给我们开《水经注》专题课,介绍《水经注》的版本和研究现状,涉及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知识,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由袁英光、刘寅生整理的王国维《水经注校》,我在校读过程中发现整理本问题较多,觉得是个可以着力探讨的问题,就向指导教师郭在贻先生求教。郭先生建议我从校勘学入手,作客观比对,并由此生发开去,讨论一下整理古籍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在郭先生的指导下,我撰写了《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一文,并以此申请文学硕士学位。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由祝鸿熹老师任主席,郭在贻先生和张金泉、雪克、崔富章等老师为答辩委员会委员。
硕士毕业后,我向罗宗强老师汇报学习情况,说自己如果不到杭州读书,就不知世间学问之大。王国维说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个学者能有望尽天涯路的眼界,并非易事。罗老师说,现在很多教授还不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以为自己写了几本书就是专家。他看了我的论文,说我在杭州大学确实学到了治学的本领,亲自推荐发表在《南开文学研究(1987)》(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罗老师还进一步为我规划治学方向,他说:“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项工作。从你的性格特点、才思特点看,都不宜终身干这一行。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祈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
1986年,清华大学恢复文科建制,成立了中文系,聘请傅璇琮先生任兼职教授。我有机会多向傅先生求教。傅璇琮、蔡义江先生在中文系听取年轻人汇报工作。我提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张潮《友声新集》,收录很多清人书信,包括孔尚任的8封信。忽忆《文史》曾发表刘辉先生论张潮《友声初集》及《尺牍偶存》的文章,似未涉及《新集》,就说自己很想做清华大学馆藏古籍善本提要,傅先生深表赞同。我用了两周时间,把清华大学善本书目油印本全部抄录下来,又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线索,将清华大学所藏孤本、稀见本书目摘录出来,约有400多种,利用一切机会逐一翻阅,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后来还雄心勃勃地计划编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未刊序跋辑要》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叙略》。
傅先生知道我研究沈约,又热情地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与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建立联系,方便求教。1986年秋天,我第一次到文学所拜见曹、沈二位先生,汇报自己研读南朝五史时发现的一些问题,沈先生特别兴奋,说听了我的话,犹如空谷足音,好多年没有听到年轻人关注这些问题了,大有“吾道不孤”之感。我后来知道,曹、沈二位先生整理编辑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家大辞典》,并继续着手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正在一一比对史料,撰写札记,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沈先生听说我拟做沈约研究,非常赞赏,说:“你研究我的本家,太好了!”他还建议我报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本文作者1988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准考证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第一批博士授予权资格,曹道衡先生被评为博导,可以招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1987年年初,沈先生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曹先生指导博士生的名额被挤占了。那一年,我的希望落空,但是有曹、沈二位先生的鼓励,我终于把沈约年谱编完。1988年继续报考,如愿考入曹道衡先生门下。讨论选题时,我这个北方人作南朝文学研究,南方同学吴先宁做北朝文学研究。最初的题目是《沈约与永明文学研究》,沈先生认为这题目过长,不如《永明文学研究》明了,可以把沈约研究成果作为附录。论文写作很顺利,每完成一章,就先请曹先生看,曹先生非常认真,在文稿旁增添很多史料,指出不妥的地方。我修改誊抄后,再给沈先生看,沈先生是老编辑,特别注意行文的明快流畅,经过他的修改,文字顺畅多了。论文写作就像流水作业,一气呵成。博士论文答辩也很顺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程毅中先生,委员有曹道衡、沈玉成二位先生以及邓绍基、袁行霈、陈铁民、葛晓音等老师。后经刘世德先生推荐,以这部博士论文为雏形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6年出版。我在后记中写道:“这部小书,写作时间前后加起来,不过两年,但是基础工作却准备了十余年的时间。幸运的是,我游学南北,数从名师。他们从材料的甄别、论点的推敲、行文的斟酌、书写的格式,甚至标点符号的运用等,给予我许多具体的指导,披隙导窍,发蒙解惑,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并初步摸索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这部小书实际凝聚了许多学者的心血,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在商品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实用哲学成为当今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学者梦之所以还在支撑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底破灭,导师们的谆谆教诲和甘于寂寞的敬业精神,是我至今得以恪守信念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的作家梦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贫瘠的山乡,但愿我的学者梦能在清贫的学苑里继续做下去。”
我很感谢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做过游国恩先生的助手。曹先生曾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童书业先生,对《左传》等经书下过苦功。1950年考上北京大学又跳了一级,1953年毕业,先被分配到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就是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曹先生觉得那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他想做学问,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的时候,他就申请调过来,成为文学所的元老。沈玉成和傅璇琮先生一起做游国恩先生的助手,熟悉先秦两汉文献。他们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北京大学,傅先生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沈先生一路颠簸,辗转多处。1985年,文学所编撰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余冠英先生把他调到文学所参与编写工作。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曹、沈二位先生最初都研究先秦文学,由于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被安排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开辟一片天地。沈先生极富才情,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曹先生看似话不多,逻辑思辨能力极强。曹、沈二位先生走到一起,可谓因缘际遇,珠联璧合,成就了一段学术合作的佳话。
四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在学校有老师面授知识,离开学校有目录学作引导。更何况,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老师无处不在,老师永远相伴。
1982年年初,我也忝为专职教师,教过本科生,带过硕士生,至今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慢慢理解了教师工作的意义。
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的老师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文、史、哲、政、经等都有。作为应届毕业生,我最早到清华大学报到,随后又有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宿志丕老师。她是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的女公子,有家学渊源。她讲历史,我讲文学。我心里没底儿,第一次讲课很紧张,准备了两节课的内容,一节课多一点的时间就讲完了。我语速快,又紧张,在讲台上来回走。学生们说,我的讲课就像打机关枪,太快了;在台上走来走去,像笼子里的狼一样。好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是全校本科生的选修课,对于讲课内容,没有硬性要求,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留下了发挥的空间。
讲课是一门艺术。我没有经过教育学、心理学的训练,只能在教学实践中摸索。以后讲座,听众的层次、需求多有不同,我特别注意与听众的互动,关注他们的每一点变化,譬如听众的眼神、无意的哈欠、轻微的动作,可能都与你的讲授有关,如果必要,就需及时调整思路,否则很可能失控。讲课有点像说相声,什么地方该丢“包袱”,自己心里要有数。这就要求每节课都要有别具会心的东西,让听众眼前一亮。我在清华大学讲授10年,每学期末,都会有问卷调查,总结经验教训。
在南开大学受到叶嘉莹先生、王双启先生、郝世峰先生的熏陶,我略知如何欣赏美文,讲授诗歌时,尽量做比较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努力找到诗歌的妙处,要比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的讲授,效果好很多。我特别感谢赵立生老师。最初他让我在他的课程中穿插着试讲几次,后来,我们还分别开设古典诗歌欣赏课。当时规定,选修课两周之后可以调换。开始,选修赵老师课的人多,可惜他的河南口音太重,两周后,很多同学转到我这里。赵老师不无幽默地说,带出徒弟饿死师傅。据各方面反映,我在清华大学讲课效果还不错,每次课都有上百人,最多的时候达到800人,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最后一排学生拿着望远镜来上我的课。渐渐地,我在清华大学讲台上逐渐站稳了脚跟。1998年,我的讲义以《赋到沧桑》为书名,交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后记中写道:
198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上文学课,当时抱着两个现实目的,一是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二是增强同学们的爱国感。其实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传统文化的根留在同学们的心中。这愿望当然是美好的,但是后来发现,倘若过分拘于这两个现实目的,同学们会很反感,以为你又在搞老一套,传经布道。
经过十几年的教学探索,我渐渐感到,要抓住清华大学文学课的特色,必须首先明确两个前提:
第一,文学与其他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首要作用是给人带来美感,而不是教育。萨特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同时,还随时关注着理论界的思考。我注意到了汤因比与池田大作之间关于科学研究目的问题的对话。汤因比说:如果把科学研究的目的看作是使饥饿的人果腹,或将其研究活动仅局限在完成这一值得称道的现实目的,结果科学被固定在这样的小圈子里,就会成为无用的东西,对饥饿的人反而或许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束缚在这样有限的目的中,科学在完成重要的新发现方面——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发现——都会碰到障碍。科学研究在将其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时,也就是不带任何功利的意图,只是为了满足求知的好奇心的时候,才会有种种新的发现。这种不带某种社会性动机和其他意图的研究,在其所获得的各种发现中有许多本来是没有计划和指望的,但到后来却令人吃惊地发现,可以对社会发挥有益的效用。而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正是在追求这种效果吗?
第二,清华大学文学课与其他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课很不相同。我们面对的同学,一方面文学知识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又都自视甚高。如果按照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要求安排课程,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你就会感到曲高和寡,同学们毫无兴趣;如果仅仅为了迎和同学们的趣味要求,在文学课中加进大量的水分,甚至“插科打诨”,用“下里巴人”来逗乐取笑,同学们一定会感到你在愚弄他们。既能叫同学们欣赏你的课,从中得到教益,又不至于降低水准,这就需要精心安排。
清华大学文学课的特色,就在这种精心安排之中。
首先它是文学课,以传授文学知识为主;其次它又不仅仅是文学课,要让同学们在欣赏文学的同时,从历史走到现实,又要用现实来反观历史。历史往往就是一面镜子,众镜相照,才能真正看出社会的真实面貌与个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欣赏吴宓教授《文学与人生》这门课的讲义。我觉得,这才是清华大学文学课的特色,也应当作为清华大学文学课的传统继承下去。
就是这句话,让后世记住了一个自恋的娘炮。人们在反思黑暗幽深的历史时,一不能怨皇帝,二不敢怼权臣,总要找一个“背锅侠”,气质妖艳的何晏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就这样成为中世纪最为惹眼的恶之花。
要保持清华大学文学课的特色,对教师必然要有较高的要求。
很多人以为在清华大学这样的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讲文学课非常容易,其实哪里是这回事。满腹学问的人未必就能讲得好;没有学问的人可以蒙混一时,但是到头来,同学们还是不买你的账。选修课,同学们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我认为,以某种强迫的方式,比如点名、考试,来让同学们听你的课,这不仅是对同学的侮辱,教师自己的脸上也无光。同学们不爱听你的课,教师首先应当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能怪罪同学。你的课讲好了,自然有人来听;你的课没有意思,反而强迫人家来听,作为教师,应当感到丢脸,而不应理直气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学们是最公正的裁判。要对得起学生,同时也要对得起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讲出一分,起码得有十分的准备。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的课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渗透力,同学们可以举一反三,这对他将来的自学将会受用无穷。
其次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教书育人,应当现身说法。中国人重视诗品,更重视人品。人品不好,诗文写得再好,终究要受到唾弃。这本身就很值得后人玩味。从诗品、人品讲到人生境界,讲到处世原则,不能摆出一副经师的样子,居高临下,发蒙解惑,而是要把自己与学生们摆在平等位置上,不回避自己的观点,不忌讳自身的弱点。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讲课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同学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从听课当中、从前人的境遇之中学会怎样处世,怎样处人,怎样处己。比如在考试题中,我经常出一些类似“我心目中的杜甫”“我心目中的陶渊明”这样的试题,提示同学们:我们不仅仅是在考文学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人生课题。对此,同学们大都有较深的体会。
在清华大学讲授文学课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保守一点估计,听众已达数千人。同学们对于此课始终抱有热情,给予积极的评价,作为教师,当然是感到由衷的欣慰。从同学们热情期待的目光中,从同学们会心的微笑中,我越发意识到肩上的重任。
几千年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根。
要把根留住,根深才能叶茂。
2000年,清华大学音像出版社给我做了32讲的录像,公开出版。
博士研究生教育有两种,批量培养方式比较常见。一个老师带好几个学生,大陆的、台港澳的,还有国外的,老师甚至叫不上学生的名字。另外一种方式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办法,熏陶感染。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就是这样指导的,文学所老师指导博士生,大都采用这种办法。那时,研究生名额少,一届毕业后才能继续招收,老师也认真。我更喜欢师傅带徒弟的方式。1995年冬,沈玉成先生突然去世,先唐文学研究的指导老师失去一员大将。文学所考虑将先唐文学分为两个阶段招生,一是先秦两汉文学,二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两个方向均由曹道衡先生负责。曹先生非常认真,起草了《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
一、必修课:
1.中国上古史 一年级上下二学期 共6学分
2.《诗经》 一年级上学期 3学分
3.《楚辞》 一年级下学期 3学分
4.历史散文 二年级上学期 3学分
5.诸子散文 二年级下学期 3学分
6.《史记》 二年级上下学期 共6学分
7.中国经学概论 二年级上学期 3学分
8.古文字概论(请语言所开设) 二年级下学期 3学分
二、选修课
以下课目视毕业论文决定,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每人可选修2至3门
1.乐府诗研究 2学分
2.魏晋南北朝诗歌 2学分
3.《文选》研究 2学分
4.《春秋》三传研究 2学分
5.《战国策》研究 2学分
6.汉赋研究 2学分
7.《汉书》研究 2学分
8.《尚书》研究 2学分
以上课目由曹道衡开设,刘跃进协助讲授。
三、必读书
《通鉴》卷1至卷184
《史记》(参考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战后版)
《汉书》(参考王先谦《补注》、杨树达《窥管》)
《后汉书》(参考王先谦《集解》)
《周易》(王弼或朱熹注)
《尚书》(伪孔传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诗经正义》(毛亨、郑玄、孔颖达)
《诗集传》(朱熹)
《毛诗传笺通释》(马瑞辰)
《诗毛氏传疏》(陈奂)
《诗三家义集疏》(王先谦)
《楚辞章句》及《楚辞补注》(王逸、洪兴祖)
《楚辞集注》(朱熹)
《山带阁注楚辞》(蒋骥)
《离骚纂义》(先师 游先生)
《天问纂义》(先师 游先生)
《左传》(杜预注、杨伯峻注)
《国语》(韦昭注)
《战国策》(诸祖耿汇注)
《论语》(朱熹、刘宝楠)
《孟子》(朱熹、焦循)
《庄子集释》(郭庆藩)

曹道衡先生《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手稿
《荀子集解》(王先谦)
《韩非子集释》(陈奇猷初版本)
《墨子》(选读)
《老子》(王弼注)
《乐府诗集》(郭茂倩)
《文选》(李善注)
《全汉赋》(费振刚)
《说文解字》
《尔雅》(郭璞)
《经学历史》(皮锡瑞)
四、参考书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
《说文释例》(王筠)
《尔雅义疏》(郝懿行)
《汉语音韵学》(王力)
《观堂集林》(王国维)
《读书杂志》(王念孙)
《潜研堂集》(钱大昕)
五、毕业论文
应在二年级上学期前确定题目,再按内容安排二年级下学期以后选修课及重点阅读书目,二年级下学期,至晚三年级上学期交出论文提纲,由导师、副导师审阅,写论文时,定期进行辅导。
六、具体要求
总的要求是在三年之内对先秦两汉文学有通盘了解,并对其中若干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必建立在掌握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特别这一专业,对经学和文字学必须有较深修养。应强调史料和作品本身,坚决反对空谈、人云亦云及发奇谈怪论。
第一年:先秦至少读完《诗经》《楚辞》《左传》《国策》《孟子》《庄子》《论语》诸书(《诗经》至少阅读《正义》《集传》及马、陈四书。《楚辞》至少读完王逸、朱熹及游师二书),两汉至少读完《史记》及汉代乐府,又《通鉴》卷1-卷184,以期有通盘了解。
第二年:至少把规定必读书读完;把所学课程每课写论文一篇(6000至10000字),要有自己意见。对所选论文题目有较深的理解,并形成初步的看法。要求在这一年终了前,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至二篇(外籍学生不强求)。
第三年:要求除必读书目外,对《诗经》《楚辞》注本再能多读几本(从正续《清经解》中选读)。对自己选择的研究题目有一定创见,并立论允当。要求史料丰富、扎实,经导师、副导师一致同意,方可打印,参加答辩。凡经过答辩者,均应在本学科内有坚实基础,而对所研究的问题,更能达到有创造性见解的程度。但凡先秦文学研究中主观臆测、硬套国外理论框架的做法,均应坚决反对。
这份培养方案,与姜亮夫先生拟定的方案相比较,有不少相通的地方,都强调通识的重要性,又注重基本典籍的细读。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指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史网”来概括。我们常说,古典连接现实,文学就是人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有多复杂,文学就有多复杂。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人学;关注人,就必须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等。读懂文学,首先要读懂作者的人生,还要进入历史现场,深入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由此看来,文学研究,广大无边。

本文作者与曹道衡(中)、沈玉成(左)二位先生合影
现在博士研究生名额比过去多了不少,我觉得没有必要人人都要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所益处。开卷有益,没有白费的工夫。重要的是要阅读,要有积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当然,如果立志问学,那就要选择正确的方法。黄侃说:“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为避免走错路,就必须放弃狭隘的专业束缚,从传统文献学入手,强调问题意识,避免任何花里胡哨的选题。
这里,我还想重申一下资料编纂工作的重要性。
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概论》中说:“编工具书这件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学人不大看得起工具书和编工具书的工作。回忆我的老师王国维先生,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编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讲金文的书全部著录。他研究宋元戏曲,先做《曲录》,把宋元所有的戏曲抄录下来,编成一书。所以,他研究起来,就晓得宋元戏曲有些什么东西。……他的《宋元戏曲史》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至今已成为不可磨灭的著作。因为他的东西点点滴滴都是有详细根据的。”事实上,姜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研究《楚辞》,而有《楚辞书目五种》;研究敦煌学,而有《瀛涯敦煌韵辑》《莫高窟年表》;研究历史,而有《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这样做,能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础上而能有所发展。
事实上,好的工具书或资料长编,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严耕望先生的学术论著,多是有深度的资料长编。我曾拜访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芮效卫教授,他把《金瓶梅》视为明代百科全书,举凡相关资料,分门别类,分装在不同的卡片柜中。他的资料柜就像中药铺子的药匣子,与《金瓶梅》相关的衣食住行、市井风情、文化掌故、历史事件等海量资料,无所不包。根据选题需要,随时调阅不同的资料。无论什么样的资料长编,都要尽量做到竭泽而渔。表面看,这是一个慢功夫,但这项工作又必不可少。
总之,研究一本书,就要从这部书的流传版本做起,继而掌握作者的全部资料,最终要关注到作者的时代。同样,研究一位作家,要从他的年谱、交游考证做起,熟读他的全部著作,最终还是要关注他所处的时代。研究一个命题、一个专题,也是如此,都要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入手。系统整理资料,可以有助于我们走进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也有助于我们从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面相。有的时候,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历史细节里。我在《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贾谊的时代与贾谊的文学》(《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等文中,通过资料的系统梳理,分析了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的“大义”与贾谊撰写《新书》所蕴含的远大抱负,都是从历史细节中找到进一步研讨的线索。
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支撑,只是汇总各类知识,四平八稳,充其量是平庸的教材。真正有价值的教材,作者一定是学有专攻的学者,其内容能反映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现在有些专著,往往连概论都不如,只是依据既有的知识,预想一个题目,然后利用现代手段收集相关资料,拼凑成书。这样的成果,或许能给作者带来一定好处,对学术界来讲,几乎没有借鉴意义。
当然,做地毯式的资料收集,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或许可以做到,研究明清文学,就比较困难了。因此,如何收集整理资料,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时段,自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能一概而论。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整理资料的方法。这是我在南开大学、杭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时,老师们传授给我的最重要的学术方法。
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杜甫《戏为六绝句》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我过去40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那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