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地“依法交回”条款的司法适用:规范表达与逻辑展开
2020-12-23江保国
江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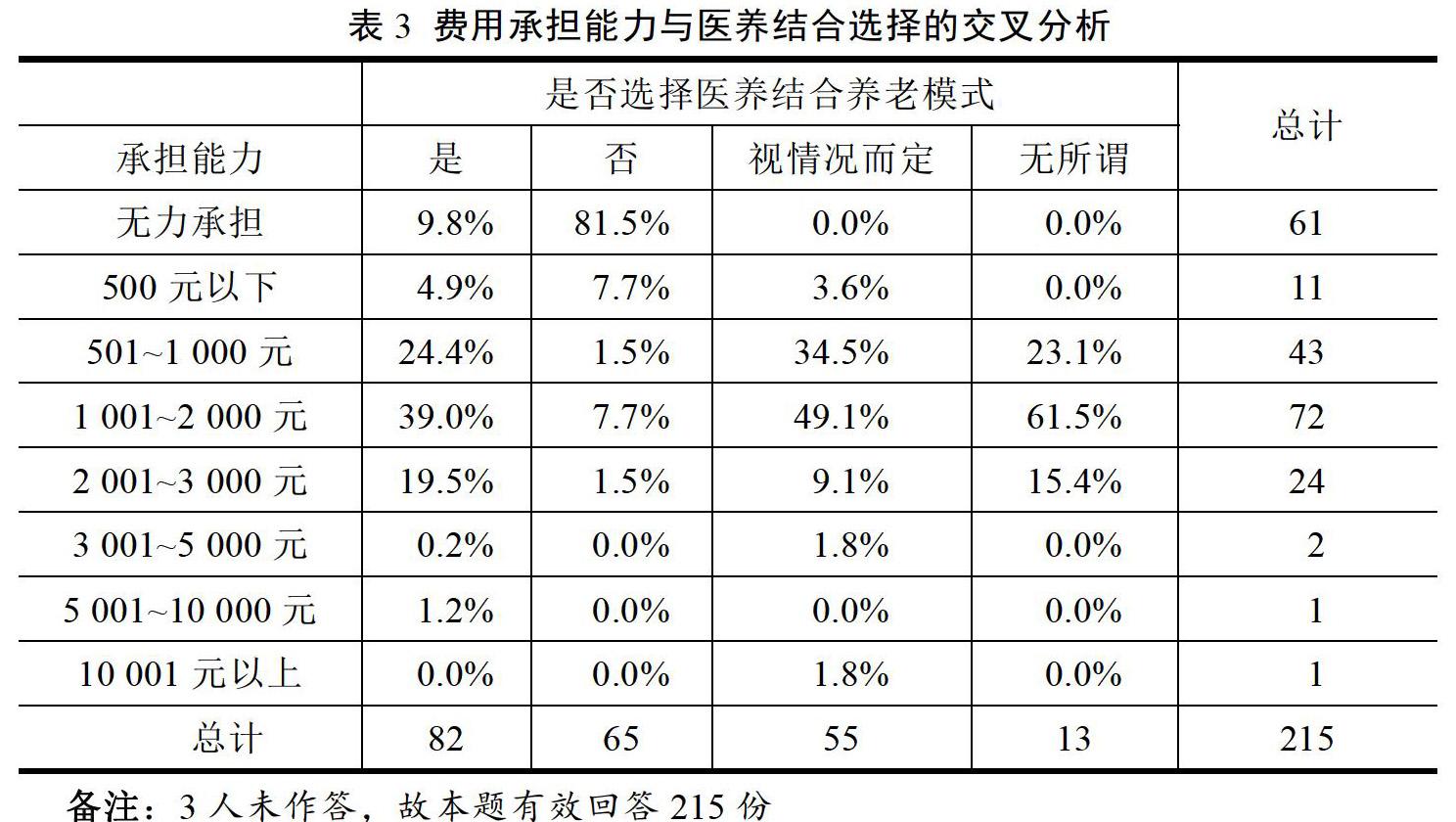
摘 要:承包地“依法交回”条款16年的司法适用对当下建立承包权退出法律制度仍有諸多启示,其在规范表达和逻辑展开两个方面存在的诸多内在矛盾,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诸多困惑,彰显了各方主体在其中的不同立场和利益关切点,体现了政策与法律、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双重张力关系。当下我国承包权退出机制的建构完善需要因应强制退出到自愿退出的转变,将自愿退出权利化、程序化。
关键词:承包地;依法交回;司法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6-0025-09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居城镇。为了适应情况变化,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3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以下简称“依法交回”条款)。此即该法第28条所称的承包方“依法交回”承包地,以区别于第29条规定的“自愿交回”承包地。由于“依法交回”基于法定事由而产生,并不取决于承包方主观上的意志,实质上是“强制退出”。无论是“自愿交回”还是“依法交回”,实际上都是土地承包权的退出,“其背后指向的是土地承包资格的让渡与放弃”[1]。本文论域中的承包地“依法交回”或土地承包权“强制退出”与该条款在同一意义使用,既不包含有学者所称的通过流转方式进行的经营权退出[2],也不包含因承包方死亡(主体消灭)、承包地被征收(客体消灭)等情形导致的土地承包权消灭。
虽然《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实施后,引导支持农民自愿退出土地承包权成为主要原则,但该法2002年设置这一制度时所面临的矛盾基本未有大的改变,甚至更加突出。因此,修法过程中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土地承包权退出制度的价值和必要性依然十分肯定[3]。事实上,新法也仅仅是对承包权退出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而非废除[4]。因此,“依法交回”条款体现了立法和政策的变迁历程,凝聚了特定时期的时代特征,其16年的阶段性司法适用提供了一个总结研究的契机和标本,其中昭示的政策与法律、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张力关系对我国农业立法依然具有现实针对性[5]。在此背景下,对承包地“依法交回”条款的司法适用进行系统检视,无疑有助于把握我国土地承包制度变迁的内在理路,分析各方主体在其中的立场和利益关切点,为未来的制度更新做铺垫。
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6]司法适用的过程实际是法官对立法规则进行解释的过程,其基本方法不外乎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两类 ,前者侧重于立法规则的用语和语法等外在表达,后者则侧重于立法规则的制定目的、背景和体系等内在逻辑。下文分别从这两个维度对“依法交回”条款16年的司法适用情况进行研究。
二、规范表达
为了使法律规则具备一定弹性,立法者经常故意使用一些具体细节不确定的表达,以给法官个案自由裁量预留空间。然而,“应当区别对待法律词项的含混性和模糊性”,前者系指立法中应当尽力避免的可以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选择的模棱两可的语病[7]。“依法交回”条款的若干用词具有一定的含混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不少困惑。
(一)“农户”与“承包方全家”
根据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15条之规定,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由于《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使用的概念都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因而学界素有两者能否等同的争议[8]。作为承包方,农户是集合民事主体应无疑义[9],由此就产生了如何区别农民个人与农户整体的主体资格以及与之相伴的权益分割问题。在“邹敏山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中,承包方农户5口人中有3人将户口迁入设区的市,发包方以此为由收回了部分承包地,法院认为这“不符合法律规定” 。为了强调农户的集合性和整体性,“依法交回”条款采用了“承包方全家”的表述[10],因此在诸多类似案件中,法院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农户部分成员迁居对农户整体作为承包方的主体地位无实质影响,对承包合同的效力也无实质影响。
然而,问题在于农户内部成员之间就承包权退出产生纠纷时如何处理。在“何福云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农户成员之一进城落户后,还能否和其他成员一样享有第二轮延包土地的承包权?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该案后判决应当类推适用“依法交回”条款,认定该成员符合强制退出的条件 。这种类推与前述部分不影响整体的分析框架之间显然存有矛盾,如果扩展适用于外部纠纷可能就与立法目的相悖。
(二)“设区的市”与“小城镇”
“依法交回”条款将迁居“设区的市”作为退出土地承包权的必要条件,而同条第2款则将迁居“小城镇”作为退出的排除条件,即“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由此引出设区的市与小城镇的界分问题。
虽然《宪法》《立法法》都提及“设区的市”,但其外延却颇为多样化:有的设区的市只有市辖区,而有的还代管县、县级市等,有的区下还设有镇。而对“小城镇”进行界定则更加困难,有代表性的观点至少有六种之多[11]。虽然由立法工作者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以下简称《释义》)认为,“本法所称的‘小城镇,包括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12],但它与设区的市在外延上仍有一定交叉。
在“周利华等承包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周利华案)中,承包方农户全家迁入常州市武进区所辖的洛阳镇并转为非农户口。一审法院认为“依法交回”条款“没有将市设区所辖的建制镇排除在设区的市非农业户口的范畴之外”,因而区辖镇应当属于设区的市,二审法院对此表示赞同 。但在另一个与之类似的“陈清棕等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以下简称陈清棕案)中,承包方农户全家迁居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并转为非农户口,一审法院认为该镇属于设区的市,但二审法院却结合立法目的认为该镇只是小城镇 。
(三)“应当”与“可以”
在权利义务的设置上,“依法交回”条款对承包方使用的措辞是“应当”交回,而对发包方使用的则是“可以”收回。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法律在表述义务性规范时一般用“应当”,而设定权利时一般用“可以”等表述。也即对于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是义务;而对于发包方,收回则是权利。两者原本相互对应,组成一个闭锁的通路:规定了承包方的交回义务,就意味着明确了发包方的收回权利。如果承包方违反其依法交回的第一性义务,就会产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第二性义务[13]。然而,“依法交回”条款在表达上不仅未明确承包方不履行交回义务应予承担的法律责任,反而将发包方行使收回权作为对应的法律后果,使两者关系产生错位,而权利行使的可选择性又使这一法律后果的发生处于不确定状态 。在“张秋生等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即认为本条“规定的是‘可以收回,而不是‘必须收回”,发包方因此也可以不收回承包地 。
(四)“交回”与“收回”
从“依法交回”条款的文义来看,无论是承包方的“交回”行为,还是发包方的“收回”行为,都是以终止土地承包关系作为积极追求的法律后果,其作为表意行为的性质甚为明显。然而,“其权利基础、发生要件及实现程序在法律上欠缺明确的规定,学理上也未展开充分的讨论”[14],导致其行使及效力认定等问题基本无法可依。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情况,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29条规定是“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但对于依法交回的方式和程序却未置一辞。在“孟照霞等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中,承包方农户代表人与发包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同意将该户部分迁居成员的承包地份额交回。二审法院认为农户代表人的意思表示可以代表农户整体 。在“王永倩等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中,农户代表人的家人(与其不属同一户口关系)代为同意交回承包地的行为也得到了认可,虽然法院承认存在“收回程序不规范”的事实 。
三、逻辑展开
根据《释义》,“依法交回”条款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承包方全家进城落户后丧失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二是基于社会公平考虑;三是为了缓解农村人地矛盾[12]。这三个理由分别从成员权、社会保障需要和分配正义角度论证了承包权强制退出的必要性,然而仔细分析却发现其遵循了不同的逻辑理路,相互之间也存有龃龉。
(一)成员权
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该条体现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成员权间的密切关联,即具有成员身份是享有成员权的前提,享有成员权则是具有成员身份的逻辑结果。虽然“依法交回”条款没有直接点出成员身份问题,但其文义已呼之欲出。正如《释义》所申明的:承包方全家迁居转户后丧失了成员身份,自然也丧失了附着在身份上的成员权,因而应当退出承包权。这一简明扼要的推理蕴藏着强大的逻辑力量,得到不少法院的认同。在“雷东红农户等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中,法院即认为鉴于承包方已进城落户,因而“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不具备享有案涉土地承包权应具备的身份条件” 。
在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下,户籍地和户口性质是识别人口身份的简易两维坐标。户籍登记于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区域并且是农业户口,就会同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村民身份。然而随着这一体制的松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村民身份的同构性日渐瓦解。原本作为识别村民身份的户籍地等标准,在识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越来越捉襟见肘,使从身份丧失到权利丧失的推理存在部分失效的可能。
此外,这一推理的弱点还在于,要回答户口迁入设区的市在实质意义上与丧失成员身份有何内在关联的问题。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规定,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范围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同居直系亲属,可办理城鎮常住户口。据此,不少迁居小城镇的原农村居民将户口转为非农。按照“户籍地+户口性质”的识别标准,他们因此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同条第2款保留承包地的规定相矛盾。在“翟永军等承包经营权纠纷”再审案中,法院试图调和这一矛盾,将成员身份与承包权脱钩,提出“承包期内,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唯一依据是承包人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并取得城市户口,承包人全家迁入小城镇不再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发包人也不能收回其对原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然而,这种脱钩必然会导致从身份丧失到权利丧失的推理完全失效。
(二)社会保障需要
在农村社会保障几近于无的年代,源于土地的生产性收入起到替代性社会保障供给的功能。不少农民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或遭遇风险时又回乡务农,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城镇化”路径[15]。这一模式不仅增强了农民抗御风险的能力,还在整体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的设计必须因应这一渐进式城镇化的大背景,采取同样渐进而柔和的策略。
事实上,我国承包权的迁户退出标准经历了从“城市”到“设区的市”发展演变的历程[16]。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将退出地权作为农村居民落户小城镇的先决条件。2002年《土地承包法》的草案也一度规定承包方全家进城转户的应当交回承包地,但鉴于当时的政策是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且不少小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最终在通过时将其提高为“设区的市”标准[17]。其预设前提是:设区的市有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户迁居设区的市并转户后可享有城市居民身份所附载的福利待遇。在此情形下,如允许其保留承包地,就会导致城市与农村社会保障权益的叠加,形成享受双重福利的“超市民”或“第三种人”[15]。由于“许多小城镇还没有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一旦失去非农职业或者生活来源,那么他在农村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将是其基本的生活保障”[12]。
在司法实践中,社会保障需要常常成为法院对第26条进行目的解释的依据。然而,将“设区的市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或“小城镇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两个全称判断作为司法推理的预设前提,显然有不少风险。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与当地是小城镇还是设区的市并无必然联系。在市设区所辖的建制镇到底是小城镇还是设区的市问题上,前文述及的周利华案和陈清棕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此外,这种目的解释方法在涉及迁居小城镇、转为非农并且参加了社会保障的农户时,就难以自圆其说。在“崔春山等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中,承包方农户迁居小城镇后参加了当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在实质意义上已符合获得城市社会保障的条件,但形式意义上却不在第26条规定的“设区的市”范畴。为了弥合这一逻辑断裂,法院在判决中只好采用更加严格的保障程度标准,即“不能仅凭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确定其在进入小城镇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已经完全得到落实” 。然而,如何认定“完全得到落实”又是另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
(三)分配正义
人多地少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据统计,我国人均耕地仅1.3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18]。鉴于此,原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37条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然而这一度引发了与《土地承包法》在法律适用关系上的疑问,因为全家迁入城镇的承包方,通常也难以继续耕种原有承包地。在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此作出两种相反的解释:一是两法可并行适用,弃耕抛荒和进城落户行为都构成收回承包地的法定事由 ,甚至直接认定承包方迁入城镇即构成或者必然导致弃耕抛荒行为 ;二是两法只能择一适用,具体是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对于2002年后的案件适用《土地承包法》,对于之前的案件则按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适用《土地管理法》 。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支持第二种解释。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款否定了将抛耕弃荒作为承包地强制收回的法定理由,而只保留了进城落户。然而,两者的立足点均系缓解人地矛盾的分配正义,且在实践中其发生情由也多有交叉。中国传统思想中原本就有的“朴素的平均主义心态经由集体化的浪潮而不断被塑造,逐渐成为农民支配性的土地观念”[19],使得强制收回进城落户农户的承包地并重新分配在乡土社会中有较强大的文化基础和习俗支撑,由此也成为“依法交回”条款立法的一个加强性理由。
四、“依法交回”条款中的双重张力关系
承包地“依法交回”条款无论是立法表达还是逻辑展开,均对司法适用形成一定的挑战,体现了政策与法律、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双重张力关系。
(一)农业政策与法律
我国承包地强制退出政策的演进历程,体现出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适的高度弹性。例如,由于强制收回承包地引发了不少影响农村稳定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格适用《土地承包法》,叫停以土地撂荒为由收回承包地的做法。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此后,《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等中央政策文件反复重申这一规定,但在该政策未能及时法律化的情况下,也使法院是否继续适用“依法交回”条款面临着困惑。有的法院在判决时回避这一问题 ,有的则根据“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强调相关政策不适用于其发布之前的案件 ,还有的根据效力层级认为应优先适用《土地承包法》 。
农业领域常常存在着法律落后于政策、政策落后于实践的现象,而立法过程中法学的学科贡献和参与也常低于其他相关学科。“我国一般都是先由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探索,政府主管部门以此为基础展开试点并逐步形成党的文件,之后便以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为主导启动法律的制定与修改。”[20]在农业政策法律化过程中,法律往往来不及消化和沉淀政策的内容,在追随政策的路途上一直处于“逆风吃土”的尴尬境地。“依法交回”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即为典型。
与其他立法一样,农业类法律的基本功能是作為指示行为的准则,以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等形式理性价值作为圭臬。因此,农业类法律的制定要遵守较严格的程序,条文的表达要符合一定的逻辑规则和修辞规范。而农业政策则主要由一系列的原则或宣示构成,内容往往较为宏观,其主要功能在于引领一段时期内党和政府涉农工作的方向,并通过宣传实现社会动员。它们的制定过程虽然也常需征求各方意见甚至经历长期酝酿,但程序性并不突出。不过,农业政策具有灵活而柔软的身段,适于处理涉农改革中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满足一时一事之需。待相关政策定型成熟下来,则需要转化为法律使其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在此,政策被翻译为法律概念,并以立法文本的形式呈现。”[21]其间,立法需要对政策进行充分沉淀和过滤,用权利、义务等法律的构成性要素去表达和重塑政策。我国农地政策经过不断探索完善已大部分转化为法律,《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对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厥功至伟。但由于政策入法时的淬炼不够,不少农业立法在表达上常常显得较为生硬。这导致法律的政策化现象,使得相关法律“不仅严重落伍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长久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新政策,而且受时势局限在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存在诸多缺陷”[22]。
(二)法律逻辑与生活经验
1978年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一种新的产权结构,农民的土地生产性收益获得部分保证。但这一时期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大体上还是通过合同获得的一种债权,容易受制于政策的变化。为了稳定农民的权利预期,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希望在承包期内尽量不调整土地;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中,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到期后再延长30年,并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2009年开始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试点工作。可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一直沿着稳定地权、市场取向的改革路径前进”[23]。上述“长久不变”的政策,已落地转化为法律规定。从《土地管理法》到《土地承包法》,再到《物权法》,都将稳定承包权作为基本立法原则,对调整和收回承包地作了严格限制。特别是《物权法》将承包权定性为用益物权,明确了制度完善的方向。
与债权不同的是,物权是一种对世权,其存在不以现实地占有特定物为条件。承包权虽然由土地所有权派生而来,但其存在和行使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完全依附于所有权,也不受所有权人的任意干预。就法律属性而言,作为物权的土地承包权经登记确权后就具有公示公信力,不应因权利人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消灭。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早就呼吁“依法交回”条款“严重背离物权的本性(绝对性、排他性),应当予以废止”[22]。
然而,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24]土地制度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其蕴含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丝毫不亚于法律意义。土地能否成为财产性权利以及成为什么样的财产性权利,“并不决定于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决定于社会经济生活存在的基本状况”[25]。
土地承包制度是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实现形式,它脱胎于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本源上说就是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捆绑的。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不能全面深入覆盖广大农村而惠及全体农民,需要利用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特色,为农民构建一种带有浓厚福利色彩的基本保障制度[26]。而我国立法中的土地承包权仅具“较弱的物权性”:其主体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大体上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其客体限于“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且用途受到严格管制;其权能则要在特定条件下受发包方和法律的限制;其变动则需要登记才能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27]。此外,进城落户农民退出承包地,在实践中也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因此,“依法交回”条款的立法初衷虽然有乖于法律的逻辑推演,却有着坚硬的现实基础,故相关司法踯躅于法律逻辑与经验事实两端,几乎是必然结果。
五、余 论
2018年《土地承包法》將原26条第2、3两款分别修改为:“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与之前相比,新法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切断承包权退出与进城落户之间的法定因果关系,取消强制性的“依法交回”承包地要求,而代之以“引导支持”和“鼓励”其转让土地承包权益;二是不再区别“设区的市”和“小城镇”。
上述变化反映了2002年《土地承包法》施行以来我国城镇化实践和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但是,“进城落户”“引导支持”“鼓励”等表述仍是基本照搬了政策性语言,具体如何识别、有哪些方式和措施、各方主体在此过程中负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需要经过哪些程序等都尚不明确。因此,该条款与其说是一个法律规范,不如说是一个立法政策,是立法者在相关具体政策措施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个刻意(很可能也是无奈)的模糊。正如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所言,该规定“为政策适时调整留出了空间”[4],“建议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作出原则规定并规范必要的程序,把选择权交给进城落户农民和其原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不要代替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作出选择”[28]。这意味着短期内农户自愿退出承包权,仍然会以地方政府探索型的因地施策为主。鉴于前述对承包地“依法交回”条款司法适用的研究,当下相关制度的建构一方面应落实立法中从强制交回到自愿交回的转变,尊重承包方农户的意思自治,通过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来突出其主体性,使退出真正权利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完善进城农户行使退出权的书面通知、社区公示和变更登记等程序性规定,特别是通过程序来突显和充实作为承包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的存在,减少不必要的纠纷。此外,删除“依法交回”条款后,由此导致的诉讼案件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但对新法实施前的此类纠纷是溯及适用新法还是适用旧法,可能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困扰各地法院,需要通过适当方式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1] 高强,宋洪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74-84+158.
[2] 罗必良,何应龙,汪沙,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农户问
卷[J].中国农村经济,2012(6):4-19.
[3] 石亚楠.落实“三权分置”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N].农民日报,2018-10-26(2).
[4] 刘振伟.进一步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J].农村经营管理,2017(11):14-16.
[5] 高飞.进城落户农户承包地处理之困境与出路[J].法学论坛,2019(5):15-22.
[6]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2,
[7] 熊明辉,杜文静.科学立法的逻辑[J].法学论坛,2017(1):80-89.
[8] 崔建远.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建议[J].财经法学,2015(4):5-25.
[9] 朱庆育.民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67-468.
[10] 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J].中国社会科学,2016(4):91-110.
[11] 蔡秀玲.论小城镇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7.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EB/OL].(2003-10-28)[2019-11-16].http://www.npc.gov.cn/zgrdw/npc/flsyywd/jingji/2003-10/28/content_323090.htm.
[13]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19.
[14] 蔡立东.论承包地收回的权利构造[J].法商研究,2012(3):67-75.
[15] 张力,杨绎.人口城镇化背景下农民自愿退出农村地权的法律规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3):113-123.
[16] 金枫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法律漏洞之补充——小城镇与设区的市界定标准的检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2):99-105.
[17] 顾昂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02
年6月24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5):357-359.
[18] 徐绍史.国务院关于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2012年12月2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3(1): 89-93.
[19] 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M].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
[20] 高圣平.论承包地流转的法律表达——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18(8):13-28.
[21] XANTHAKI H. Drafting Legislation: Art and Technology of Rules for Regulation[M].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4: 3.
[22] 朱广新.土地承包关系长久稳定的制度建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4):118-125.
[23] 丰雷,蒋妍,叶剑平,等.中国农村土地调整制度变迁中的农户态度——基于1999~2010年17省份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3(7):44-58.
[24] 小奧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25] 郑尚元.土地上生存权之解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权利性质分析[J].清华法学,2012(3):80-95.
[26] 周清林.“带地入城”与农村地权:理念冲击、现实表达与制度应对[J].现代法治研究,2017(1):18-31.
[27] 张国敏,张合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较弱物权性评析[J].河北法学,2013(12):70-77.
[28] 刘振伟.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的认识(上)[J].农村工作通讯,2017(22):8-13.
(责任编辑:李 虎)
Abstra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ixteen year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ontracted land “retu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law” clause of the 2002 PRC Rural Contracted Land Act is still very rewarding,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is clause have resulted in many confus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reveals the divergent concern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the tensions between policy and law, logic and exper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oluntary contracted land returning mechanism in China will depend on the adoption of a new approach toward rights and procedures.
Keywords: contracted land; retu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law; judicial 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