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敏敏:研究神经学的“神人”
2020-12-23赵永新
赵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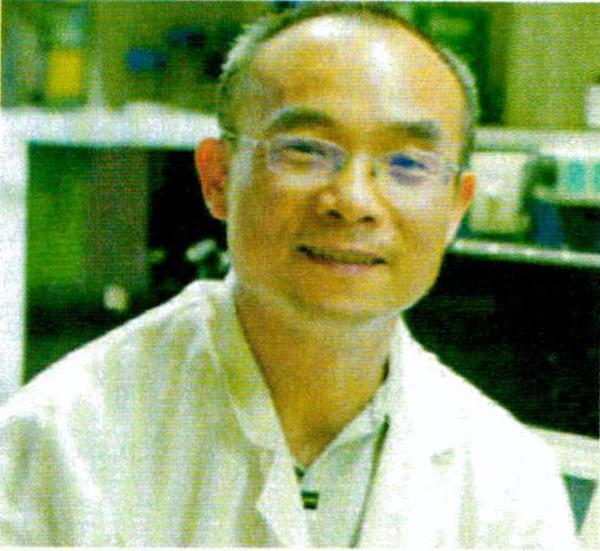
个头中等、皮肤黝黑、头发稀短的罗敏敏喜欢穿牛仔裤,说起话来语速很快,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尽管公众对他比较陌生,但他在业内影响力却挺大:在顶级神经科学期刊《神经元》的编委会中,罗敏敏是唯一在中国成长的神经科学家。同时,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被邀请在美国神经科学年会做大会报告的中国科学家。
除了科研做得好,他还擅长摆弄计算机、研发科研仪器——帮助他实验成功的好几种精巧灵敏的“神器”,就是他带着学生设计、研制的。
难怪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开玩笑:罗敏敏是所里的“神人”。
科研的每一天都很快乐
1991年,罗敏敏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他却有些发懵:“我本想报考理论物理专业,怎么被调剂到心理学了呢?”
罗敏敏生于江西省上高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中学时代是年级的尖子生,每次县里有理科竞赛都会让他去,而每次他都会拿奖。所以,高考的时候选了物理专业。专业调剂令他一时感到失落,但他很快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得益于北大自由的选课制度,他还选修了生物系、计算机系、电子系和物理系的课程。这种跨学科式的探索,延续到了他未来的专业选择上。从北大毕业后,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先后攻读了计算机科学硕士和神经学博士学位。
“罗老师是跨学科型的人才,这一点很少见。”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如此评价。但在罗敏敏看来,一切不过是兴趣使然。对未知科学领域的好奇心,是他广泛学习的最大动力。
博士毕业后,罗敏敏在杜克大学做了四年博士后,导师LarryKatz带给他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对科学有狂热的兴趣,不受世俗约束。”罗敏敏说:“他让我看到,对科学的热爱能够支撑一个科研工作者过上非常快乐的生活。”
令罗敏敏印象颇深的是,导师常常自称在科研工作中,预判的正确率只有百分之十。
“正视探索过程的艰难,坦然接受失败,是一个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所以我现在试图让自己每天都保持快乐的状态。我有个课题做了十年,猜了一百多次结果,最后都被证明猜错了。”罗敏敏哈哈一笑:“但这也大概是做科学最美妙的地方: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年之中总会有些天,你看到了你没有预期到的结果,就会感觉非常嗨。”
在罗敏敏看来,保持乐观也有实际的意义在里头。“我自己意识到的一点事,学生可以从老师的表现上得到很多。如果你因为实验的结果和你的猜想不一样而大发脾气,学生就会想:我如果做出来不是这样,老师生气了怎么办?这样会造成风险——学生们会迎合你,有意地去做一些结果。”
我只尊重科学事实
迄今为止,罗敏敏已在《科学》《细胞》《神经元》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取得多项重要突破:首次发现了哺乳动物嗅觉系统专门检测二氧化碳的细胞;阐释了中脑多巴胺神经元上的C型鸟苷酸环化酶受体在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综合征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他自己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是提出了5-羟色胺为编码奖赏这一革命性的结论。
在过去的近30年中,整个神经科学领域都把多巴胺和奖励当作同义词。在罗敏敏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全面。通过实验,他发现大脑内有个平行的奖励系统是5-羟色胺系统。多巴胺主要和动机有关,而5-羟色胺主要和奖励的评估有关。一个完全被预期的奖励可以激活5-羟色胺,使人产生快感。因此,对5-羟色胺系统的补充认识,可以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诸多行为。
但这一课题也面临一个问题:在神经科学领域,过去大家一致认为5-羟色胺是编码惩罚的。“我们是在冲击一个主流观点,已经争论了五六年。”罗敏敏说,他们重复了主流观点所依据的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有些人问我,你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追求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只是在诚实地对待数据。数据是这样,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如果和主流不一样,我们也要坚持不一样。我不会为了迎合领域内权威去改变我的说法,也不会为了博眼球而标新立异。”罗敏敏说。
尊重科学事实,是罗敏敏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竭力在自己的实验室营造的一种氛围。当学生的实验结论不符合他的预期,他绝不会表现出一丁点儿负面情绪,而是鼓励他们实事求是。他担心学生们会为了迎合他而刻意得出一些特定的结果,反而违背了科学原则。
“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有错误的成分,只存在相对的正确。”罗敏敏说:“所以,一定要能够承认自己是错的,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是错的,找出这个边界来,这是对科学的尊重。”
超级喜欢讲课
北生所在昌平,罗敏敏每次去清华大学上课,都要开车一个多小时。但他自称“超级喜欢讲课,喜欢和学生交流的感觉。”在清华,罗敏敏给本科生上大课,一对一交流的机会不多。但他希望传授前沿知识,用自己的讲课风格影响学生。
“我的风格就是讲一些最新的东西、批判性的东西。有些本科生可能不太适应,他们希望我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但我会告诉他们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不清楚的。”罗敏敏说,他想让学生们知道,教科书是用来改变的。认清现有的限制,才有可能去突破它们。他希望听过他讲课的众多学生之中,能有人在未来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而当他回到北生所、推开实验室的门,常常会感受到一股活泼、跃动的空气。他笑着问学生们:“你们真的在干活吗?怎么一个个看上去这么开心?”
学生们也笑着回答:“因为做实验确实太愉快了。”
正在读博的林睿在2012年来到罗敏敏的实验室,他认为学生们的“开心”源于极高的自由度。国内大多数实验室都是导师安排任务,学生们执行。但在这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问题,通常都会得到罗老师的认可。
当然,自由不代表放任。在林睿眼中,罗老师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他长年站在实验一线。“他特别喜欢自己动手作实验,甚至自己发明实验仪器。”林睿说,实验室里有一个可以戴在老鼠头上的显微镜,重量仅2.8g,就是罗老师带着大家自主发明的成果。“其他老师只听学生汇报成果,但他会跟着我们,关注实验的过程。”
2009年来到实验室的张举恩正在做博后,罗敏敏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可亲、随和。“他一日三餐几乎都和学生一起吃,在饭桌上就能和他交流各种问题。”张举恩说,很少有老师能做到这一点。找其他老师一般都需要提前预约时间,在办公室里正式讨论。罗老师给学生们的感觉更像是朋友。
可是在罗敏敏眼中,自己做得总还不够好。“我总觉得自己花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时间还不够。有时候忙起来,就不能静下心来,跟着他们把整个过程都看一遍。”他说。
努力做一个好老师,是为了整个团队能把科研做好,也是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身科研。罗敏敏认为,科研永远需要最聪明的人来做,但现在最优秀的学生往往选择去读商科,这是国内科研的遗憾。
“我们作为老师,应该为学生创设更好的环境,找出更多的工作出路,从而吸引更多好学生加入科研队伍。”罗敏敏说:“也希望学生们能看到,科研是快乐的,科学会为一个人带来美好人生。”
转换方向
2018年夏末秋初,记者去北生所采访,在大门口外瞥见一个穿短裤的人,侧影看上去很像罗敏敏。
我走上前一看,果然是他。小半年没见,罗敏敏的脸色似乎白了许多。
“你们的脑科学中心运行得怎样?”
“还可以。”他告诉我,北京脑科学中心购买了一批实验设备,建起4个实验室,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面向全球招聘实验室主任。
“您自己的研究进展如何?”“我转向了。”他笑哈哈地告诉我。
“转向?往哪个方面转?”
“转化医学啊!”他说,基于这些年的基础研究成果,他们准备重点开发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新药。“比如抑郁、精神分裂、药物成瘾等,目前这些疾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
近些年来,随着世界快速进入老龄社会,全球范围内的神经系统疾病呈高发趋势,无论是抑郁、失眠,还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等。但是,在新药开发中,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大制药公司都对这类疾病敬而远之,因为相关的科学机理很不清楚,开发新药的风险非常高,真正是“九死一生”。
“您对转向的成功率把握大嗎?”“当然不能说大,因为开发这类药物的确是太难了。”罗敏敏笑着说,“但总得有人去尝试吧,不试怎么能知道成不成呢?”
摘自《三代科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