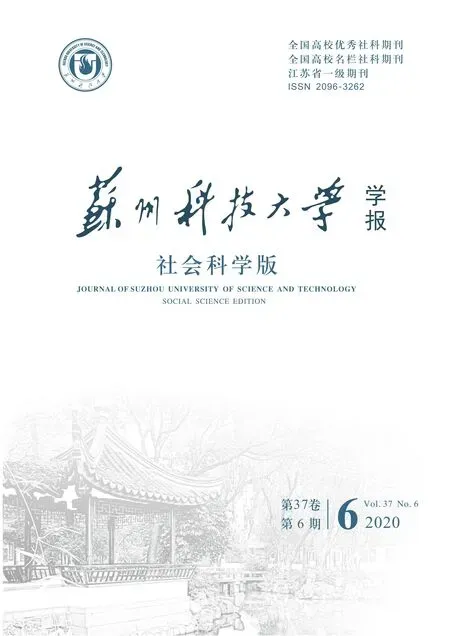解析比尔·奥斯戈比的青年媒介理论*
2020-12-23陈小燕
陈小燕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比尔·奥斯戈比(Bill Osgerby)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伦敦都市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专业教授,在青年文化、性别和英美文化史方面著述颇多,如《1945年以来的英国青年》(1998年)、《天堂里的花花公子:现代美国的阳刚、青春与休闲风格》(2001年)、《动作电视:硬汉,滑头和狡猾的小妞》(2001年与Anna Gough-Yates合著)、《摩托车手:真相与神话:最初的公路牛仔如何成为银幕上的轻松骑手》(2005年)等。奥斯戈比的重要著作《青年媒介》(YouthMedia)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阐述了青年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媒介的关系。此书在2004年由英国劳特莱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好评如潮。奥斯戈比从青年文化消费实践的历史出发,指出青年文化的场景经历了从餐车、汽车餐厅、自动点唱机、iPod到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变迁,青年文化与媒介发展及商业市场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复杂的互构互栖的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笔者拟从奥斯戈比的著作、研究背景、学术思想等角度探析青年媒介理论的思想逻辑,分析其中的独到见解与内在关联性。
一、跨学科、多视角的青年媒介史观
“青年”是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某种过渡阶段,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和监督的生活阶段。奥斯戈比在梳理青年文化与媒介的学术脉络时发现,学者们对青年媒介的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例如: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视角对青春期的性、犯罪与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青春期是身份形成的不稳定的时期;美国学者托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创造了“青年文化”一词,从社会学角度将青年视为受社会化共同过程支配的独特世代群体,他认为青年是一个缓解从儿童情感依赖到完全成熟的艰难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对整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青春期描述为一个尽管不是特别离经叛道但令人困惑的身份形成阶段;大卫·西伯利(David Sibley)认为区分儿童和成年的界限并不精确,在构建离散的“年龄”类别时划清界限的这种行为会打断青春期的自然连续性;克莱尔·华莱士(Claire Wallace)和科瓦切娃(Kovatcheva)认为,青年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职业官僚权力、工业社会和启蒙理性的现代世界是青年出现的关键因素。[1]5-9
总的来说,关于青年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前者强调维度内的权力和消费者实践,后者强调受众对文化的自我构建能力。奥斯戈比认为这两种范式并不冲突,政治经济学、文本性和青年接受问题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在对青年及其与媒介关系的“跨学科”和“多视角”分析中建设性地结合起来。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强调,为了充分把握媒介文化的性质和影响,人们需要发展方法来全面分析其含义和影响。因此,奥斯戈比一方面梳理了青年研究不同理论范式的发展;另一方面结合商业青年市场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形态,指出青年通过消费实践创造自己的身份,进一步分析了“青年媒介”在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强调它与现代社会商业市场和政治议程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全球青年文化中的不平等问题。
二、青年媒介崛起的动力因素
青年市场在消费产业全球化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在英国和美国,“青少年”文化被认为是现代消费文化的先兆,阶级和经济不平等的旧界限正在稳步消失。媒介中新富起来的“镀金青年”被描绘成一个激动人心且没有阶级的现代社会先锋。然而现实中,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仍然是年轻人社会生存的关键阻力。奥斯戈比认为,“青年”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产物,年轻人成为活跃的消费者,为媒体行业的发展注入了关键的生命力。因此,青年媒介的崛起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一)商业市场的需要
二十世纪中期,青年市场首次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支柱。尽管九十年代经济出现了衰退,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化,但青年的消费能力仍然是商业和媒体业的基石。“青年媒介”一直是商业生产者传递年轻受众和市场的重要手段,是了解现代青年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随着青年市场的经济和文化影响显著扩大,生产者和广告商越来越多地将“青年”的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与商品、媒介联系起来。一些品牌将自己定位为“年轻”和“酷”。“青年市场”和“青年媒介”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领域,而是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消费者身份,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以赢得广泛的文化吸引力。[1]4奥斯戈比指出,英国长期的经济衰退和投资不足侵蚀了该国的制造业基础,文化生产不再是重工业和制造业的次要部分,而是成为经济支柱。在打造英国文化经济的努力中,青年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1]44在青年市场,为了避免硬推销,营销人员开始将产品与“反叛的”个人主义品质联系起来,他们使用好玩的反讽和“颠覆性的”促销形式以及设计令人发指的公关噱头,试图营造一种与众不同的氛围,以吸引年轻消费者。例如,在方便面的电视广告中吹嘘自己是“所有零食中的渣”[1]43,这些带有颠覆讽刺意味的广告反而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消费者。
(二)政治议程的需要
媒体机构是一个争议性地带,提供了不同群体及其生活方式的象征性环境。媒介政治言论经常构建青春话语来积极动员青少年,为威权政治计划赢得支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英国工党为了将自己塑造成现代化的代言人,在其关于充满活力的新英国愿景中努力调动“年轻”概念。例如,用“酷不列颠”代替“大不列颠”,突出青年文化中“酷”的元素。又如,1996年托尼·布莱尔在工党大会上承诺,他的政府将“使这个年轻的国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和蔼可亲、精明能干、熟悉流行文化、与孩子们相处自如的人,并着重突出其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曾领导一支名为“丑陋谣言”的进步摇滚乐队的履历。[1]75政治话语不仅积极地调用年轻人的文化精髓,而且在动员青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戈比的研究肯定了年轻人在媒介实践和政治话语中的这种特征。
三、青年媒介互构关系的发展
究竟是媒介对青年的暴力报道催生了青年的暴力行为,还是青年的暴力行为导致了媒介中暴力内容的增多?关于“暴力媒体”与“暴力青年”的缠绕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奥斯戈比对英美两国的出版历史进行了梳理,他发现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十字军们将青少年犯罪的明显上升与“低俗小说”“低俗闹剧”剧院的风靡联系起来。在美国,这种勾连情况更甚:1873年,联邦政府实施《反淫秽法》,逮捕了“有害文学”的出版商,并禁止流通“一美分小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黑帮电影成为争议焦点,好莱坞被指责为将易受影响的青年带入可怕的职业生涯;五十年代,流行的“恐怖”和“犯罪”漫画是青少年堕落的源泉;二十一世纪,“视频垃圾”和电脑游戏被认为对年轻人构成威胁。这表明媒介对年轻人的描述不是直接的“反映”,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解释,构建了年轻人的形象,这些有争议的形象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一)媒介与青年的相互建构
媒介往往通过特定的代码和称呼来构建“青年意识形态”的各种方式,既把年轻人视为繁荣未来的令人兴奋的先驱,又把他们贬为文化衰落最可悲的标杆。不管是“青春即烦恼”(Youth as Trouble)还是“青春即乐趣”(Youth an Fun),都不过是媒介和政治家们利用“青年”主题进行社会变革评论的工具。[1]6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对青年的表征都不一样。1945年以后,福利机构和教育机构激增,“青年”开始成为一个独特的年龄类别。战后的“婴儿潮”确保了五十年代青年人口的迅速增长,而消费行业的扩张和传统劳动力市场的重新配置带来了青年就业率的上升,提高了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五十年代,青年被描述为“新的消费文化急先锋”;六十年代,青年被描述为可以促进“无阶级”的消费主义和国家活力的代表;七八十年代,青年则被描述为“邪恶的妖魔群”;九十年代,青年更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威胁力的社会存在;二十一世纪,青年被描述为商业大众化的糟糕例子。这表明,青年形象的角色多样性完全是媒介建构的结果,标签化成为媒介对青年形象建构的一种化约式表达。
同时,青年通过媒介消费实践创造自己的身份。年轻人在日常文化活动中有着能动的因素,他们通过媒介消费形成自己的身份,并与其他人相区隔。他们并不是不加批判地消费商品和媒介内容,而是积极地挪用市场上的产品,重新语境化并转换它们的意义——通常是以挑战或颠覆主导的权力关系体系的方式。在年轻人看来,意义并不是文化产品所固有的,而是通过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的。亚文化资本不仅在亚文化内部的地位等级中被调用,而且作为成员集体地将自己与外界区分开来的一种手段。[1]109青年的商品消费行为和媒介使用行为并不是被动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而是一种积极的实践,在各种媒体包括杂志、时尚和音乐中参与着文化。一方面,媒体行业邀请年轻观众理解他们的产品,但他们无法控制年轻人挪用、重新解释甚至颠覆文本含义;另一方面,年轻人“对商业产品有自己的理解,做出自己的审美判断,有时会拒绝服装行业对时尚的规范定义”[1]110。二十世纪后期,媒体和消费文化的扩散带来了更加流动的亚文化风格形式,青年更加多元化的身份凸显出来。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不再遵从刻板的亚文化流派,而是由个人的品位来决定。
(二)媒介对青年的过度“妖魔化”
传媒业一方面对越轨青年文化的风格兴趣盎然,将其当作消费社会中吸引眼球的工具和可以转化的商品进行批量销售;另一方面对荒废青年(Wasted Youth)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与抨击,引发公众恐慌,青年成为“民间恶魔”。[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戈比对这种由传媒过度报道引发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框架提出质疑,认为它是在对社会和大众媒介过于单一的视角下运作的,但他忽略了社会中诸种力量的反应。“道德恐慌”最早是科恩(Cohn)于1972年提出,“某个情景、事件、个人或人群显现出来,并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与社会利益的一种威胁”(1)转引自约翰·菲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171页。。当传媒业对青年的异端行为进行凸显式报道,公众对这一行为会产生恐惧。比如朋克摇滚,媒体的狂热报道一方面迅速地将新兴的朋克亚文化推向排行榜的顶端;另一方面将社会问题的包袱扔给朋克摇滚群体,认为他们是城市混乱和青年失业率上升的根源。这种粗暴的政治逻辑使得社会对朋克摇滚青年亚文化的负面反应越来越强烈。奥斯戈比在论述劫掠摩托车团伙这个群体时提出,尽管他们被认为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群体,但这类摩托电影掀起了人们反英雄的狂欢,成为蔑视主流价值观以及强调差异性的一种潮流。[3]这种潮流影响深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反英雄的运动,对抗传统道德斗士的声音日益增多。大众媒介对年轻人的“妖魔化”进程备受阻力,其“妖魔化”青年的做法变得摇摇欲坠。
(三)媒介与青年关系的修正
作为回应,青年对媒介中的话语讽刺表现出超然物外的冷漠。媒体塑造了一系列荒废青年的影视作品,对他们肤浅的行为进行浓墨重彩的讽刺。比如《瘪四与大头蛋》描述了瘪四和大头蛋这两个青年比赛蒙着眼睛玩滑板、高速购物车和吃到吐等令人作呕的恶作剧,展现了年轻的蛮子们(Young Daredevils)那种愚蠢的“美德”。[1]81这部动画片被评价为一部具有启发性的文化文本,是迷失在媒体世界并生活在超现实世界中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他们除了破坏事物,无事可做。然而,奥斯戈比认为这种媒介再现把年轻人塑造成虚无主义的一代,这种符号的建构不仅仅是对荒废青年的一种调侃,更会引发广泛的社会道德恐慌效应。与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越轨青年群体的积极抵抗不同的是,奥斯戈比认为讽刺对青年并没有太多的形塑作用,青年会选择超然地妥协来消解这种建构作用。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体、小众媒体和“利基”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青年的声音可以被充分地展现,“民间恶魔”们能够更自主地参与并反驳传统媒体的歪曲表述。“利基”媒体,比如音乐和时尚杂志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又一个连贯的亚文化。另外,更多的小规模和专业“微”媒体,比如传单和扇子,则传播了与亚文化发展相关的实用信息。尽管“利基”媒体的力量相对有限,但把年轻人描绘成一个社会威胁的做法,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自此,在多种媒体竞争态势下,媒介与青年的关系得以重新修正。
四、青年媒介的未来:多边关系的“共生”
青年、媒介和其他商业利益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在对青年意识形态收编过程中,媒介起到微妙而关键的作用。媒介运用视觉代码和文本技术积极地解释“年轻的”而非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在塑造亚文化的身份及其成员的自我意识方面至关重要。媒介内容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年轻人的“需求”与一个意图延续这些“需求”的媒体驱动的市场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共栖。
第一,媒介与青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媒介和青年的关系尽管互构,但也并非因果论的产物。以往人们认为说唱音乐和暴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种粗糙模型并没有捕捉到媒体和年轻人之间发生的复杂对话。媒介成为年轻人在寻求建立自主身份时的关键资源,比如通过观看最新的耐克广告宣传活动或浏览詹妮弗·阿倪妮斯顿的最新发型,年轻人可以在媒介上轻而易举地找到塑造自我身份的流行样板。年轻人可以在这个模版上围绕“什么是什么”来构建意义,如“酷”和“不酷”。奥斯戈比说,青年亚文化不是有机的、非中介的社会形态,也不是自发的草根文化,而是源自媒介呈现的文化。虽然“真实的”亚文化在本质上是媒介建构的,但它们仍然是参与者意义和自我认同的强大来源。[1]108青年的商品消费行为和媒介使用行为是一种“符号创意”实践,青年积极地通过媒介消费实践来创造自己的身份,并以此与其他代际人群相区隔。尽管大众媒介(如电视新闻报道)在道德恐慌、标签和放大过程中有着强大的作用,但奥斯戈比强调媒介对青年的讽刺是好玩的,而不是颠覆性的。[1]81
第二,媒介文本不是直接传递“信息”的简单工具,而是充满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话语。围绕着“年轻态”,市场创造了很多界限模糊的新词,如“中年青年”(Middle Youth)、“老龄化青年”(Greying Youth)。在消费市场,“青年”的概念已经脱离了特定的世代群体,并与特定的心态和审美趣味联系在一起。随着消费产品越来越“唯美化”,年轻人市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世代基础”(Generation Base)。[1]175媒体行业也开始瞄准“老龄化”(Greying)的年轻人市场,比如那些在年轻时就开始购买黑胶唱片的年长的购买者,老年消费者也日渐接受以年轻人为导向的媒体和产品。然而,“老龄化青年”市场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种怀旧行为,老年消费者们似乎保留了他们的“年轻”态度和消费模式。例如,在英国,市场营销人员创造了“中年青年”一词,用来指年龄在25岁到40岁的消费者,他们抵制中年的诱惑,喜欢曾经属于年轻人的品位和生活方式。
第三,粉丝群体通过盗猎文本的方式进行媒介内容的再创造。关注媒介受众的“创造力”成为研究粉丝及其文化实践的一个特别强烈的主题。作为青年群体的主要存在,球迷群体被普遍认为是相当可悲的生物,是社会功能失调的局外人,是非理性的痴迷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驳斥了粉丝是没有头脑的消费者和社会格格不入者的刻板印象,他认为粉丝实际上是媒介文本的熟练操纵者,粉丝们利用商业市场提供的材料来构建自己的文化,他们是“文本盗猎者”(Textual Poachers)。“文本盗猎”指的是从属群体颠覆主流文化形态意义的方式,次等和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利用文化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导形式所提供的资源,为自己形成一个适宜居住的文化环境。詹金斯对粉丝们的文化进行人种志描述,展示了粉丝们如何在一个丰富而有创意的文化中将这些节目作为他们自己的故事、歌曲、视频和社交活动的基础。[1]111由此表明,受众在积极地与文化形态和媒介文本进行协商时,偶尔会盗用甚至颠覆它们的意义。[1]85年轻人无疑是创造自己生活方式的积极力量,但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维护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试图进行任何象征性反对。
第四,对荒废青年的成见不仅是媒体偏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战略的一部分。[1]68人们认为漫画、摇滚音乐、垃圾视频和电脑游戏等对年轻人的思想构成威胁。社会主导群体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恐惧日渐上升,反对大众媒介过度娱乐化的运动不断增多,社会稳定问题岌岌可危。此刻,大众媒介成了一个有用的“代罪羔羊”(Scapegoat),政治家和道德斗士们很方便地将社会和经济问题怪罪到“代罪羔羊”身上。[1]53因为把责任推给媒体是一种方便的方法,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更难审查的问题上转移开。奥斯戈比进一步批评了美国媒体将黑人青年作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媒体机构把他们描述成“福利骗子和荒废青年”。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夸大了非洲裔美国青年的掠夺性和暴力性,并使得公众极易生成种族刻板印象,进而助推了鼓励公众通过立法对少数种族和阶级实施更为严厉的政策。这反映了主流政治在进行品位监督并划分等级,中产阶级的文化偏好得到积极的传播,而那些实力较弱的群体则遭到诋毁和压制。
第五,青年市场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全球商业领域,但其中媒介和娱乐消费并不平等。青年的商业市场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叶是年轻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消费群体的重要阶段,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推动了青年消费的热潮。二十一世纪,尽管“利基”市场更加细分了媒体的受众领域,青年市场转向商业聚集,更加协同化和国际化;但青年市场仍然是一个利润丰厚和有影响力的商业领域。商业媒体促进了全球青年群体的出现,他们不受任何社会和地理位置的价值观的影响,在消费主义的伦理中一起分享媒体和娱乐的共同菜单(Common Menu)。[1]121尽管年轻人作为无国界商业市场的潜力巨大,但其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和差异,比如社会阶层、性别、性取向和种族等等。因此,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财富、权力和生活机会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不是平等地参与任何“全球”青年文化。
五、结 语
在笔者看来,奥斯戈比“青年媒介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青年”与“媒介”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使得青年的文化实践特别是亚文化实践更富活力。青年通过符号消费建构自己的身份,并与其他世代相区隔。媒介对青年形象的构建,无论是“青春即乐趣”还是“青春即烦恼”,都不过是媒介进行话语调用的一种工具。奥斯戈比是一位建构论者,也是忠实的“相互依存”论者,他反对青年与媒体的“因果关系”,认为这种粗糙模型并没有捕捉到媒体和年轻人之间发生的复杂对话,媒介文本不是直接传递预先确定“信息”的简单工具,它充满了模棱两可和前后矛盾的话语。同时,青年受众也在积极地与文化形态和媒介文本进行协商,甚至盗用它们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媒介、青年、受众、市场与政治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构共生关系的认知,对于理解当下网络社会中国青年文化形态亦有积极意义。无论是网络媒体创造出的“后浪”或“乘风破浪”等话语,还是父辈话语中“前浪”自许的姿态,都是社会主流力量对“青年”意涵的一种积极征用。他们试图通过沟通交流来化解两代人的代沟差异。尽管年轻人并不买账,或调侃或拒绝,但这一场演讲已然撬动了固有的文化圈层,圈层破壁未来可期,青年在现代社会中将继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因此,对青年媒介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在当代依然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