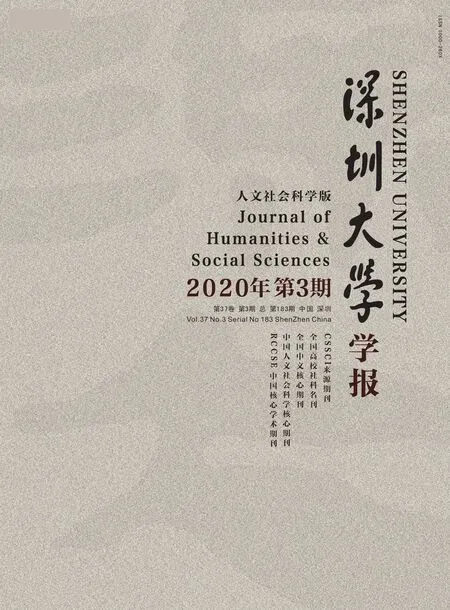关学的原型、流变及其研究空间
2020-12-22常新
常 新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是唐以来三教融合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宋儒维系儒家道统的一种理论自觉,其构建过程“采佛理之精粹以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1]。 理学道统的建构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标志,《宋史·道学》 的序言大致勾勒了这一过程[2](P12710)。 儒学在向理学过渡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汉儒天人之学与魏晋自然之学的转型,通过批判的形式吸收与消化了佛老思想,形成了一种儒学理论的新形态——理学。 张载作为“北宋五子”之一,对理学理论的构建厥功甚伟,在南宋时就以关、洛、濂、闽之“关学”称之。 自张载去世至明中前期,张载所开创的“关学”同中晚明以来所言地域性的“关中理学”有一定的概念差异性,它不强调地域意识,强调的是张载为开宗者,以蓝田三吕、苏昞等为主要门人的师承与学承关系,是同濂学、洛学、闽学并存的“全国性”的儒学派别。 由于“完颜之乱”和“宋室南渡”,张载之学在北方的影响与传播极为有限。 明初关中由于“河东学派”与“三原学派”的阐扬,张载之学逐渐恢复了与洛学、闽学相等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肇始于南宋文学地域性意识,催发了关中士人的文化地域意识,在“文学复古”运动中,“七子”中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为关中人,更是强化了关中士人的地域意识,晚明冯从吾编撰《关学编》,构建了以张载为宗师的“关学理学”学术史。 清代的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相继对《关学编》进行了增补,形成了脉络清晰的关中理学学术史。 翻检《关学编》可以看出,明清关学学术演变,其主线是关中学者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批判与融摄,并继承张载以来关学“躬行礼教”、“尊古尚经”、“经世致用”的精神遗产而展开,这一过程也使关学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理学学派。
一、张载开创的儒学新形态
北宋作为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后世重视。 清人章学诚尽管对清代理学评价甚低,但对宋代儒学发展给予肯定,认为“儒术至宋而盛,儒学亦至宋而歧”[3]。 “盛”者言宋儒对儒学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歧”者,言儒学在宋代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
宋代是在收拾五代十国残局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立国之初为缓和社会矛盾,与民生息,采取黄老之道,宋太宗曾言“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4]。到北宋末年,宋徽宗继续沿袭崇道的政策并提倡儒释道三教并用, 其间士大夫出入佛老成为普遍现象,如理学的开创者张载“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2](P12723),程颢“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2](P12716)。 考察张载和程颢二人为学的经历,其二人都是“有志于道”。“道”即是《宋史·道学》前沿所言“政教”的依据[2](P12709)。 在一个世俗的国家,从宗教层面寻求“政教”的依据存在诸多困难,因此二人最终皆“返诸《六经》”,对先秦儒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 北宋的经学在汉唐经学章句与注疏的基础上深化了义理与经济两个层面,这种深化基于北宋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文化领域释、道对儒学的挑战,社会治理方面需要解决民生,对外关系方面需要解决辽、金、西夏对北宋的军事压力,这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5],其核心的精神在于“本经义”以至于“圣人之道”,讲求“明体达用”、“内圣外王”,这也是北宋儒学转型的根本动力。
北宋诸儒以道统自任,有直追汉唐、兴复三代之志,以阐释经义为起点,致力于圣人之道的探究和践行,于是出现了“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局面,“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6](P251)。 张载对理学开创之功在《宋史·道学传序》中有载:“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2](P12710)。 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2](P12724)。 张载哲学体系总纲蕴藏在《正蒙》首篇《太和篇》及《西铭》中,在《太和篇》中“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7](P9),此即体现出《宋史》所言张载为学的理路。 《西铭》是张载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二程予以其极高的评价,“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7](P336),其“扩前圣之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8](P609)。 由于张载在理学方面开创性的贡献,受到宋、元、明官方的褒奖,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从祀孔庙;元泰定三年(1326)建横渠书院;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称“先儒张子”。
张载的理学思想无论从学术源头还是核心思想都与周敦颐的“太极”、邵雍的“象数”、二程的“天理”存在差异性。 张载的“太虚”尽管与这些范畴存在一定差异,但其理论的旨归一致:落实于本体论层面的“天理”、“命”、“性”等方面,汇通北宋诸儒,完成了对儒学的改造,形成儒学新形态:理学。
张载在思想形成过程中并未有意识地构造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形态,而是整个北宋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其学术思想被其门人所继承甚至固守,“《正蒙》之书,关中学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其徒未尝轻以示人”[9],吕大临“守横渠说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有说了更不肯回”[1O](P12)。这一时期的张载之学存在业师陈俊民先生所言的“师承”与“学承”[11]。 北宋灭亡之后,张载之学在北方的传播几近衰息,南宋程朱理学在王权的支持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直至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12]。 这一时期张载虽然被宋、元、明官方所认可,确立张载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但其学术思想独特性不似北宋那样与二程并称,而是被官方弱化。在南宋开始出现“关学”的称谓。根据全祖望的记载, 这一名称的提出者是南宋的吕本中。《宋元学案》卷六是全祖望所补《士刘诸儒学案》,他在“关学之先”《殿丞侯华阴先生可、申先生颜合传》下有一段按语说:“祖望谨按:吕舍人本中曰:‘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泰山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大之。 ’然则申颜先生之有功关中,亦已多矣。 ”[6](P261)同为南宋的刘荀在其《明释本》也言“(张载)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 此书所记吕大临、苏昞、范育,皆其门人也”[13],因此宋元的关学仅指张载理学思想,有别于明清在继承张载学统基础之上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进行了融汇的关学。 在关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中,后者是前者在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基础之上的理性发展,它保持了关学学理发展的连续性。
张载在宋至清理学史的地位不及程朱稳固,其学术影响力也经历了由显而隐的过程。 在北宋末年由于完颜之乱,张载之学随着宋室南渡,其学术传播不及北宋兴盛。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正月,张载与二程、朱子从祀孔庙[2](2554),在诏书中说“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2](P821)。 张载在理学内部获得了同二程、朱熹相等的地位。 明清由于科举考试对程朱理学的重视,张载与二程、朱熹相等的学术地位出现差异,个中原因除科举考试因素之外,张载地位的寒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清初的王夫之在其《张子正蒙注》进行了说明:“张子教学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 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未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 ”[14]除此之外,张载思想表述的艰涩性也影响其思想的普及,其学“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8](P59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元代以来理学内部忽视张载的造道之功而专注于程朱理学的学习与体悟。
二、明清关学的构建
完颜之乱后,北方相继为金人与蒙古人所控制,造成文化的巨大破环,“儒术并为之中绝”[6](P1094),“百年不闻学统”[6](P18),黄宗羲这一结语是基于金代程朱理学而言,而张载之学在宋室南渡之后“关陕沦亡后,横渠学统灭”[15]。 此时北方传播有苏东坡的“蜀学”[16],在《金史》中记有金人对孔子的尊崇[17],金朝的科举承袭辽、宋,强化了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重视,金世宗二十三年,下诏书翻译五经,有“朕所以令译五经者, 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7](P185)的记载,只不过金代的儒学“虽以科举取士,名尚儒治,不过场屋文字,而道之大者盖莫如”,程朱理学此时也有零星传播,“宋行人有箧至燕者,时有馆伴使之,乃不以公于世”[18],“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19]。 在冯从吾《关学编》记有金代杨天德晚年读到朱子《大学解》,沿及伊洛诸书[10](P16)。到了元代,程朱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开始普遍,且被蒙元统治者所接受,在冯从吾《关学编》所记杨奂、杨恭懿、萧 、同恕等大儒皆以程朱理学为旨归,在他们的著作中罕见关于张载的记录,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明初。 明初朱棣于永乐十二年下诏,增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性理之言于《四书》《五经》之下,尤其提到“《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20],恢复了张载在儒学道统中应有的位置,在关中地区出现了建造张载祠的一个高潮,仅正德至万历间共建了 8 所,远超宋元[21](P28)。 明清理学内部基于对程朱理气论的修正, 张载思想再现明清思想论域,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王夫之、戴震等人回溯了张载“气本论”思想,从中汲取思想资源。 关中三原学派的王承裕、吕柟、韩邦奇等或对张载的《西铭》《正蒙》进行注解,或对张载文献资料进行搜集与刊刻,接续了张载开创的关学在关中的学统。 张载在儒家道统地位在明代的重新确立对吕柟、冯从吾重构关学学派至关重要,关中学者需要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构建张载关学在关中的学统。 明代地域文化蓬勃发展导致士人地域意识的萌发,这一文化现象为张载学统的构建提供了契机。
吕柟的地域认同在其所撰《陕西乡试录前序》与《武功县志序》中有所体现,在前者中言道“夫陕西,山川之初,而天地之首也,故群圣多自此产”[22](P73),后者是吕柟为康海《武功县志》所作的《序》,在《序》中同样追述了关中圣人,“后稷,政之祖,横渠,教之宗”[22](P76)。吕柟对张载的重视从对张载遗著的搜集与刊刻开始,在其《刻横渠先生易说序》,中表露了这一心迹[22](P416),而此时作为张载之学地域性意识在吕柟观念中逐渐形成。 在整理张载文献过程中,吕柟重新审视了朱子“理在气先”的观点,用张载“太虚即气”修正了朱子“析理气为二”的观点,认为“太虚、人物,实为一体”[22](P573),“天命只是个气,非气则理无所寻,言气则理自在其中”[23]。同为关中士人的胡缵宗在为吕柟《泾野先生别集序》中有“在知关中横渠、蓝田之学之有传也”[24]。 与吕柟同时的韩邦奇认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25](P144-145),其对张载思想的继承体现在《正蒙拾遗》之中,在《正蒙拾遗》的序言中开篇即言“学不足一天人、合万物,不足以言学。吾读《正蒙》,知天人万物一体也”[25](P1358)。 《正蒙》成为韩邦奇构建其学术体系的活水源头。 到了晚明的冯从吾通过《关学编》的撰写,构建了以张载为宗师的关学道统与学统,构建了自张载以来所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一个理学派别:关学。
冯从吾对关学的重构同样基于其关中地域意识的萌发,在《关学编》的序言中冯从吾言“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撰写此书的动机与目的:“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10](P1-2)然后回溯了自张载至晚明的关学发展,视张载“横渠四句”为自孟子后的“道脉”之所系。
由于处于晚明,冯从吾凭藉的关学资源较吕柟为多,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四人作为关学中兴人物为冯从吾所倚重,为此编撰了《关中四先生要语》, 在该书序言中表达了对上述四人德业节义的追慕之情, 并矢志于四先生言行的领悟与践行[26](P580)。 冯从吾还著有《元儒考略》,该书所载诸儒虽然超出关中地区, 但通过对这些北方儒者的记录,留下了理学在关中传播的大致情况,以示儒家的道统在关中不曾中断,为冯从吾构建关学的学统奠定了基础。 冯少墟的理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辨学录》与《疑思录》之中,前者是为“崇正僻邪”而进行的儒、释之辨;后者是冯从吾对《四书》所作的剳记,二书“要之一子厚(张载)为正”,如在与他人论学的过程中,冯从吾以张载的《西铭》回答士子对程子“万物一体”的质疑[26](P219)。 基于儒家道统在关中的延续、关学学者继承张载的学统,冯从吾通过《关学编》的撰写,完成了张载以来“关中理学”的构建。
冯从吾构建的关学道统在清代得以延续。 清初李二曲早岁丧怙,为学孤苦自奋,泛滥于群籍。顺治二年(时年二曲 19 岁)借读《公》《谷》《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步趋遂定,以周、程、张、朱言行为儒宗正学,而儒学“以经世为宗”[27](P122)。此时关学在冯从吾离世之后成萎靡之势,“不振久矣”,关中“留意理学。 稍知敛华就实,心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者,犹龟毛兔角,不但目未之见,耳亦绝不之闻”[27](P177)。 李二曲以“悔过自新”与“体用全学”接续“张载横渠四句”之旨,提出“吾辈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达则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27](P368),使关学在清初得以复盛。 其后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遵循冯从吾《关学编》的体例与关学学者选取标准,对《关学编》进行了增补,使关学成为关中理学的地位逐渐巩固且为关外学者所认同与接受。 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中,都视关学为一相对独立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理学学派[28](P11)。 清国史馆臣撰《清史列传》同样视关学为关中理学,清初关中学人马嗣煜、李二曲为冯从吾之后的关学后劲[29]。
张载开创理学与“北宋五子”其他人有别,形成自身的一些特质。 张载在同二程的一次论学中谈到自身为学的旨趣,成为后世所公认的关学精神和致思路向:“子(二程)谓子厚曰:‘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 ’子厚曰:‘如其诚然’, 则知大不为名, 亦知学贵于有用也”[8](P1196)。这些特点被陈俊民先生大致归纳为学政不二的政治倾向;“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德实践;“躬行礼教”的社会实践;“学贵有用”、“精思力践”的“实学作风”[30](P29)。 关学学派这一学风与传统在张载以后关学后劲得以继承,塑造了关中士人的精神与风骨。
三、对关学学理“合法性”质疑的辩护
关学发展演化主要围绕关中学者对关学学统与道统的重视与继承、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融摄、对作为异端思想的批判、对新思想的接受与改造等问题展开。 宋代的关学在学承和师承方面都比较简单,张载及其弟子学术传承脉络清晰;金元时期关中学术以朱子学为主,张载之学在关中的传播有限;明清关学的发展主要是关中学者在接续张载之学的基础上融会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使明清关学在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互相批评与融通中稳步前行。 当代关学研究就此问题的梳理首先面临关学在张载去世之后是否存续的问题。
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所言“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31]。 在侯先生看来,关学既是张载及其关中弟子之学,也是同濂、洛并行的一个学派。 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衰熄”,而濂、洛之学随着宋室南渡而得以流布。 这一观点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先生所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有着同样的表述,该书甚至认为《关学编》是由冯从吾等人强行拼凑的结果,与《金华丛书》《江西丛书》《岳麓丛书》之类相仿,是地志类的资料,是“好事者为之,殆无意义”[32]。 这一观点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定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对关学演化与发展的轨迹缺乏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未能对关学发展以辩证思维进行考察。
中国儒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先秦儒学的出现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士基于春秋以来“礼坏乐崩”的窘境所作的反应;汉代经学作为儒学的新形态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魏晋玄学是经学道家化的新形态[33];北宋初期诸儒在扬弃经学、玄学、佛教及道教的基础上创立了道学,其后又谓之理学;清代出现的考据学又是儒学内部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所进行的一种自觉调试,尽管有汉学与宋学之争,但都未出儒学之规范。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考察儒学发展演化轨迹,可以看出,儒学的发展不是以线性形态行进,而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致使儒家学说不断推陈出新。 这些学说是人类逻辑思维能力在观念领域的表现,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产物,体现出辩证思维在观念领域的应用。
《中国思想史》与《宋明理学》的编著者视关学仅为张载之学是基于学统与师承完全一致基础之上,但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学统与师承存在割裂是常态,儒家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以心传心”的范式证明儒家学统的连续性。 孔子之世“礼坏乐崩”,孔子对周礼的传承不是通过师承来完成,而是“遥接”文王、周公,通过对时有文献的整理来获取周礼,并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能征之矣”[34]作为文献对思想传承重要性的依据。 先秦孔孟创立儒学至隋唐经历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隋唐的王通、柳宗元、韩愈以儒家固有伦理立场批判魏晋玄学对儒范的鄙薄,尤其是韩愈首次提出以儒家的“道统”抗衡佛教与道教的“法统”,以卫道者的姿态构建了儒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谱系,并认为孟子去世后,儒家学说“不得其传”[35]。 李翱更是提出其思想源泉遥接子思与孟子[36]。 清代理学家费密对儒家这种接续范式做了总结:“后世去圣人日远,欲闻圣人之道,必以经文为准。 不和于经,虚僻哓哗,自鸣有得,其谁信之,经传则道传也。 ”[37]因此以学统与师承的统一性作为某个学派是否成立的依据不具有学术的自洽性,就此而言,《中国思想史》与《宋明理学》以张载去世关学学无师承而衰息的结论并不符合关学发展的史实。
派别性是儒学一大特征,早在“子学时期”就有“儒分为八”之说[38]。 宋儒标举关、洛、濂、闽诸派,一方面基于张载、二程、周敦颐、朱熹等道学(理学)开创者的地望,另一方面是哲学道学(理学)家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概念与范畴,使儒学的发展在两宋进入了新天地。 在关、洛、濂、闽四派中,濂溪之学、洛学、闽学有着较为清晰的学统谱系与师承谱系,而关学相较而言是一独立学派,但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据,将四个学派完全割裂而视为相互独立的学术派别。 学术史的史实表明,二程与张载互相以欣赏的眼光汲取学术营养,张载思想是朱熹与吕祖谦撰写《近思录》的主要思想资源。 两宋道学(理学)就是在这些道学家(理学家)所持有的学术宽容与汲取的过程相向而行,衍生出明清理学的规模。
另外还有一个往往被学术界所忽视的问题:张载去世后其门人吕氏兄弟南传关学的史实。 吕氏兄弟的门人周浮沚、沈彬老等永嘉学派诸子在浙江传播张载之学,将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与张载关学学贵有用的学风相融合;南宋嘉定期间,有魏了翁私淑关学,这些学术信息散布在《宋元学案》中。 明代王廷相、清代王夫之等人继承张载之学,延续了关学的学脉。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宋亡以后,关学逐渐衰熄”的反证,对这些问题的发掘对于了解关学在关中之外的空间传播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限于篇幅,此处对此问题不再赘述。
明代关学是两宋道学(理学)在关中的延续,当王承裕、吕柟、冯从吾等关中学者融汇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过程中,遥接了张载的学术资源,对张载《正蒙》皆有发挥或注解。 冯从吾以关中理学思想继承者的身份撰写了《关学编》,并在《关学编自序》中简单钩沉了关学学者的谱系[10](P1-2),与冯从吾同时的关中学人张舜典在 《关学编·后序》 中给出《关学编》学人选取的标准:“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10](P62),这是后来关中学人补编《关学编》的圭臬。 民国川籍学者张骥在编纂《关学宗传》时“爰仿周海门《圣学宗传》、孙夏峰《理学宗传》之例,辑横渠以来至沣西(贺瑞麟)、古愚(刘古愚),计如千人”[39]。 据此看出理学史视域下的关学绝非关中学术, 而是关中理学。 学术与理学之概念内涵与外延明显不同,学术的内涵与外延远较理学为大,包含了除哲学之外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而这些领域被《关学编》诸多的编撰者排除在外,因此视关学为关中学术是与冯从吾及关学后劲对关学界定相悖,是对关学概念的误判与误读。
关学作为理学的一个地域性派别,自晚明至民国在理学内部得到普遍认同。 晚明和冯从吾大致同时的余懋衡与李维桢在为冯从吾的《关学编》刻本所撰的序言里都认同冯从吾构建的关中理学谱系[10](P121-123)。 清初黄宗羲与全祖望撰写的《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中同样认同张载以来的道学(理学)在明代得以传承,在《师说》中为吕柟撰写的按语中明言“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28](P11)。 民国的学术对关学的认知延续了关学为“关中理学”的传统,在诸位大家学术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兹以钱穆先生为例,以示民国学人对关学之理解。
钱穆先生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学案体清代学术史,撰写此书是从宋学的视角为清代学术把脉问诊,因病立方[40]。 该著所述清代思想以江南学人为主,北方学人仅有颜元与李塨二人,对清儒北方硕儒孙夏峰与李二曲在《引论》中一笔带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二人作为清初 “海内三大儒”①在清初的学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学对清代北方学术的关注。 幸好钱穆先生在其所撰《清儒学案序目》②中对以李二曲为代表的关学着墨较多,让后世学人得以重新认识钱穆先生对关学学理之认知,惜乎这一文献未曾受到当代学人的广泛关注,鉴于这一文献可能有助于当代部分学人对关学的认知,兹录全文如下:
昔北宋横渠张子,崛起关中,开门授徒,与洛学分庭抗礼,冯少墟《关学编》遂以讬始。 有明一代关中大儒,若王恕石渠、吕柟泾野、冯从吾少墟,皆恪守程朱;而渭南南大吉、瑞泉兄弟则纯主姚江;师说各不相同。 二曲论学虽主陆王,然亦兼取程朱。遂为清初关学大师。门下执贽著籍号以千计。弟子最著者曰鄠县王心敬尔缉,号丰川。 其它如李天生因笃、王山史宏撰,皆为交游,足徵一时关学之盛。[41](P554)
在钱穆先生所著《清儒学案》中《二曲学案》列于卷九, 并在同著中以乾隆年间关中学人张秉直为传主述为《萝谷学案》列于卷三十一。 该学案附晚清贺瑞麟,并称贺瑞麟为“关学之中权”[41](P560-561),张秉直在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中有传。同在该《序目》的《后跋》中钱穆先生记述了编《清儒学案》之前托友人在西安搜购关学诸集,获几近20余种的史实,这些关学书籍多为“关外人少见”。 钱穆先生对《清儒学案》沉江导致学界不能窥关学堂奥甚为惋惜:“昔为关学诸集网罗抉剔之一番苦心,亦付之东流,不知何日仍有人再理此业,尤深自惋惜”[41](P569-570)。 这里不惮烦扰引用钱穆先生为关学张目之史实,意欲说明在民国国故派人物中关学作为关中理学具有广泛的共识。 惜乎学人在国难不已、颠沛流离之际,学术交流与思想的流布大为受阻,让学人扼腕叹息。 梁启超认同关学为关中理学,视刘古愚为关学在晚清复苏的关键人物,称“清季乃有咸阳刘古愚以宋明理学自律,治经通大义,明天算,以当时所谓新学者倡于其乡。 关学稍稍复苏矣”[42]。
鉴于晚清时局,学人苦苦探寻救国之道,在与西学的比较中,儒学(理学)往往成为激进的革命派批判与反思之对象,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章太炎与刘师培所撰清代学术史皆对清代理学家没有留太多的空间,遑论李二曲、王心敬之后衰落的关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关学研究的沉寂。 其间尽管有除了上面提到的四川双流籍人张骥于1921 完成的 《关学宗传》,还有一部几乎为学人所忽视遗忘的、由安徽籍学人曹冷泉先生于1941 年完成的《关学概论》。在《关学概论》中曹冷全先生对学人质疑关学学派学理“合法性”进行了辩护,认为关学“注重伦常日用、躬行实践、与夫尊古尚礼”、“朴茂醇厚之色采”,“不同于程朱,不同于陆王”,“固可称为独立学派”,“惜乎关学未能蔚为全国学术主潮,不为学者之注视”[43]。 曹冷泉先生的《关学概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理学形态关学研究的一个学术总结,他以理性的批判精神为关学的学理“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同时也说明了民国关学研究之窘境。
四、关学研究的新天地
建国以后,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引进了苏联的研究范式,问题意识与话语体系和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大异其趣。 若以理性的态度考察这种范式转换可以看出利弊参半:一方面使封闭的中国人文学科在范式上走出了子学与经学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化的苏联式学术范式出现了“南橘北枳”与“水土不服”:研究方法单一僵化,意识形态统摄了学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初,中国的学术界对建国以来学术研究的范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探索中国学术研究的出路, 出现了学术争鸣与繁荣的新局面。 在哲学研究领域,哲学研究逐渐走出唯物与唯心二元论模式,从中国哲学原生的概念和范畴出发构建中国哲学新的理论和框架,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天地。
在关学研究方面,陈俊民先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关学研究已有成果,对关学进行了文献整理与开创性研究,于1986 年出版了《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该著沿袭了冯从吾《关学编》将关学作为关中理学的界定, 提出了系列的新观点。 杜维明先生承担了该著的摘要英文翻译工作,张岱年先生为该著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将关学进行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分,尽管定义广义的关学为“关中学术”,张先生非常清晰地表明广义的“关中学术”就是指张载之后的关中理学[30](P5)。 该著中尽管存在一些争议性的观点,如“二曲之后的关学回归至传统儒学,回归张载,不再是宋明理学”[30](P48)、明代关学“形成了一条折衷朱王,反归张载,还原‘儒学’的曲折路径”[30](P17)等问题,但该著毫无争议地成为研究关学的必备资料。 在这前后,陈俊民先生在海内外出版了由其精心点校与辑校的关学文献:《李二曲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关学编》《关中三李年谱》。 2019 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关学经典集成》及《导读》,共计 12 巨册,该《集成》是国家古籍出版重点资助项目,是陈先生积数十年之功精心点校而成,将为关学研究提供真实可信的史料。 在20 世纪90 年代,在陕西出现了诸如林乐昌、刘学智、丁为祥等一批在全国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关学研究者,这些关学研究者都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产生了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015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光华、刘学智二位先生主编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关学文库”。 张岂之先生作为“侯派学术”的嫡传,为“文库”撰写了《总序》,在《总序》中张先生修正了侯外庐先生等在《中国思想史》及《宋明理学》将关学定义为张载之学的观点,而将关学界定为“张载创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的地域性理学学派”[44]。 “关学文库”共 40 种、47 册、2 300 万字,2016 年获中国出版协会颁发的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有力推动了当代关学的研究。
由于学术研究范式转型及文献资料获取逐渐便捷,国内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研究的学者以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理性的学术态度重构中国哲学,出版的一些理学与明清学术史经典著作,为关学保留了“学术空间”。 如1985 年张立文先生所著《宋明理学研究》 中有关学及张载的道学思想专题,在该著中张立文先生完全接受了冯从吾《关学编》中对关学的界定[45]。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龚书铎先生主编、史革新先生著的《清代理学史》之“理学的流布”章有“陕西地区”,该著同样引用了冯从吾《关学编》中“关学”的定义[46]。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陈祖武先生所著的《清代学术源流》有“李二曲思想研究”章,该章有“李二曲与清初关学”的议题,在议题中陈祖武先生追溯了关学自张载开宗立派,至李二曲重振关学宗风的发展轨迹,视李二曲为关学在清代的代表[47]。 陈来先生视关学为“宋明儒学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发展”[48]。 杨国荣先生关注关学哲学意蕴,并基于对张载思想的考察认为关学发展思想脉络复杂,认同关学是“关中理学”的学理结论[49]。
最近几年关学研究在大陆之外的地区和国家逐渐兴起。 2001 年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举办“宋明理学中的关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张载至李二曲以来的关学进行了研讨。 此后在台湾出版了由许鹤龄先生所撰的《李二曲“体用全学”之研究》,该著沿用了冯从吾《关学编》对关学的定义[50]。台湾吕妙芬教授作为著名明清思想史专家梳理了关学发展过程中思想变迁的内在逻辑,认为明清之际的关学是对张载开启关学的复兴[21](P25)。 2017 年新加坡学者王昌伟先生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 这是海外学者所撰写的第一部具有关学通史性质的学术著作,该著基于关中地区自周秦至明清政治中心逐渐衰落的史实,考察了自北宋以来关中的学术变迁,其核心议题围绕张载开启的关学展开,考察了关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家族之间的内在联系。 该著以“新的起点”、“黑暗时代”、“文艺复兴”三个标题分别指示五代至北宋时期、金元时期、明清时期的关学,钩沉了关学发展的脉络,这一划分明显具有西方文化与哲学断代的痕迹,但与关学发展脉络大致相合,颇有新意[51]。 美国学者韩德林在探讨冯从吾讲学避开政治讨论[52]问题,罗威廉讨论关学与实学关系问题[53]时都以明代关学为考察对象。
比较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大陆和大陆之外关学研究,可以发现其间的差异性:大陆关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关学文献的整理、关学思想史、关学学人个案研究方面,大部分属于基础性的研究,这一情况同大陆关学研究起步较晚,深受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相关,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创新;大陆之外关学研究者大部分受到西方学术方法的熏陶与训练,对跨学科研究方法应用比较娴熟,从政治、经济、文化与关学互动关系方面研究关学思想的变迁。大陆和大陆之外关学研究就方法与成果而言,各有千秋:大陆的基础性研究可以为大陆之外关学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大陆之外关学研究可以启发大陆关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寻求突破,二者可以取长补短,使关学研究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学术接轨。
结合论文第三部分“对关学学理‘合法性’质疑的辩护”,再通过上述经典学术著作和文章可以看出,关学为“关中理学”在当代理学研究中是一个共识性概念,关学仅指张载之学作为一个争议性学术问题尚可,但断言关学仅指张载之学是学界共识则是一个伪命题。
总 结
关学是宋明理学在关中的存在形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 张载既是北宋道学(理学)的开创者,也是关学学派的开创者,两宋关学是与濂、洛、闽诸学派并举的道学(理学)学派,此时张载及门人所重者为学术思想自身,并未有明显的地域意识。张载去世之后,其开创的关学相较其他道学(理学)学派影响逐渐式微,到金元之时“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6](P18)。 明代关中士人着意张载之学,对张载的文献进行搜集与刊刻,追寻张载之学的原型。 吕柟之学“非程朱不以传,非张(载)、吕(祖谦)不以授”,“雍之西士子彬彬然知学有源委”,“横渠、蓝田之学之有传也”[24]。 冯从吾讲学“崇正辟邪”,使关中学子“上知有横渠与二程之学[54]”。 冯从吾通过《原儒考略》《关中四象生要语》,钩沉了儒家道统与关学学统在关中延续的脉络,以编撰《关学编》的形式完成了张载以来的关学谱系。 晚清的贺瑞麟在其主持刻印的《张子全书》的序言中总结了明清关学对张载思想资源的继承,言曰“关中论先生而后,理学溢昌,笃信先生之书如吕泾野之《张子钞释》、韩苑洛之《正蒙解》、刘近山之《正蒙会稿》、李桐阁之《张子释要》,安在兴起无人”[55]。 清初李二曲“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自任”[56],承袭吕柟之《四书因问》、冯从吾之《疑思录》的治学思路,成为清代关学的殿军。
关学为“关中理学”的界定在当代学界存在争议,关学研究者爬梳文献,对关学为“关中理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曾经否认关学在明清存续的一些学者也修正了原有观点,作为“关中理学”的关学被学界普遍接受。 大陆之外关学研究逐渐兴起,在研究方法上为大陆关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将关学研究与国际接轨, 推动了关学研究的发展。
注:
①关于明清之际海内三大儒所指何人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指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如全祖望之《二曲先生窆石文》曰:“当时是,北方当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 ”其二为20 世纪20 年代章炳麟在《重刊船山先生》中提出:“明末三大儒,曰顾宁人、黄太冲、王而农,皆以遗献自树其学。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
②钱穆先生曾撰《清儒学案》,惜乎在颠沛流离之际沉入长江,但先生为该著所撰的《序目》有幸被保存下来,这一珍贵资料可以视为《清儒学案》之提要,据此可以看出《清儒学案》之概貌。 从《序目》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完全接受关学为关中理学的学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