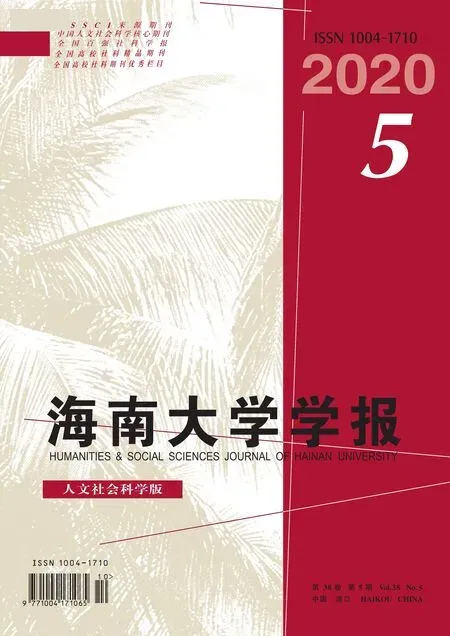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文学意义及特征演变
2020-12-20李轶婷
李轶婷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作为早期与诗、赋相关的群体性活动,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极具代表性,虽然与后世文人群体性活动有所区别,但在此类活动中,由于有诗、赋、赋诗者、赋家的参与,其性质也具有文学性的一面。尽管前者以用诗为主,后者以作赋为主,活动中采用了不同的文体及对文体运用的方式不同,但在用诗、作赋的过程中都展现了独有的文学意义,以及从用诗向作赋活动的转变中特征演变鲜明。本文拟在群体性视阈下,抉发春秋赋诗活动的诗学意义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以及对比两类活动所呈现的不同特征,从而对早期诗学活动与赋学活动的意义与特质作更深入的阐释,旨在从另外的向度对这两类活动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春秋赋诗活动的诗学意义
杨树达指出:“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①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春秋赋诗与“可以群”观念相联系,正是由于聘问歌咏、交接邻国是群体性活动,而其目的也主要是为实现诸侯国之间的友好与和睦。事实上,“可以群”的意涵不仅仅限于此,还包括赋诗活动中表现出的诗学意义,无论是赋诗与燕礼的关系,还是赋诗活动的特征,总体上都呈现了相互协调、统一与和谐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赋诗统一于燕礼。《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孟要求七子赋诗“以卒君贶”,即要完整呈现郑国国君的恩惠,赋诗是燕礼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在于:一是春秋以前,关于礼与仪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春秋时随着社会政局的变动,人们的礼、仪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如昭公二十五年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与周旋礼,子大叔认为属于“仪”而不是“礼”,因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足见,与揖让、周旋注重形式化的“仪”相比,人们更为看重具有实用性的“礼”。重礼轻仪使人们对燕礼用乐淡化,而显现出了被乐所遮蔽的诗,由此用诗也从重乐章义发展为重词章义。二是西周时,最早以“言”记燕礼,之后以“宴”“匽”作记,“以音近假借来记‘言礼’”,由此“‘燕礼’本应作‘言礼’”,源于“外交活动欲有所言”①刘雨:《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故燕礼最初就是与参与者带有外交性礼仪性的言语表达密切相联。可见,用诗来代替言语以实现外交事宜中的交流与切磋,是适应燕礼的现实需要与自身特征的结果。不仅如此,如何定生云:“《左传》、《国语》二书的记录,可说是《诗经》在礼乐用途中的转形期。故其所记之礼,皆属‘享’后的‘宴’;而其乐次也即相当于‘无算乐’。故春秋时代的‘赋诗’风气,也可视为‘无算乐’的一种转形活动,或与乐歌兼行,有时也代替了‘无算乐’的节次。”②何定生:《定生论学集——诗经与孔学研究》,北京: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91页。这里的“无算乐”正与燕礼中的“无算乐”相关③曹建国:《春秋燕飨赋诗的成因及其传播功能》,《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第7-14页。,可以说春秋赋诗也充当了燕礼“无算乐”的职能。综上,赋诗是统一于燕礼的重要活动。
其二,“歌诗必类”具有双重内涵。《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让诸大夫起舞,并对其提出“歌诗必类”的要求。其中,“类”有双重意涵。一是取诗之义与赋诗者之义同类。即采用引诗譬喻所达之义与赋诗者真实内心意旨要一致,如襄公八年载晋范宣子来聘,报告准备向郑国用兵,并赋《摽有梅》言成熟的梅子纷纷落地,以比喻女子青春易逝,男子求女应及时。范宣子赋此诗取其尽快、赶快之义,意与鲁国共同讨伐郑国。季武子明白宣子“譬于草木”之思,故云“欢以承命,何时之有”而接受了晋国邀请。在考虑取诗赋诗具有“类”的一致性的同时,也应兼顾“类”的宗法礼仪性,遵从传统社会的伦理纲常,而不能超越道德规范,如文公四年载文公设宴招待宁武子,并为其赋《湛露》《彤弓》,而宁武子却“不辞,又不答赋”,正是基于对古礼的遵守而不敢“干大礼”。二是赋诗与舞相合。杨伯峻引王绍兰语云:“古人舞必歌诗,故《墨子》(《公子篇》)曰‘舞诗三百’。”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26-1027页。又舞与诗皆属古代诗乐教化的范畴,如《郑风·子衿》之《毛诗序》云:“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⑤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故春秋赋诗旨在将大夫经过诗乐教化后的良好修为与品格融入到这个群体性活动中,从而使他们“歌之”“舞之”的技能得到锻炼,“舞诗三百”相得益彰的技巧得以提高,在展现自我掌握歌舞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能够受到检阅。如竹添光鸿亦指出:“盖古者舞与歌必相类,自有一定义例,故名大夫以必类。”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312页。可见,歌诗与舞配合具有一贯的规则,大夫都应掌握与遵循,而此过程也是对诗乐教化成果的展现。
其三,己志与国志合一。《左传》襄公十六年载荀偃从高厚“诗不类”中判断“诸侯有异志”,使高厚险些遭受“同讨不庭”,又襄公二十七年赵孟认为伯有赋《鹑之贲贲》“志诬其上”⑦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5页。,与其余六人赋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不同而视为“有异志”,并指出“幸而后亡”。可见,赋诗要求己志与国志合一,个体情志的表达要与国家志向的抒发相统一,而不能自我标榜、独树一帜,否则便会遭致不幸。抒发己志之赋诗相当于“为情造文”,为表达一己之情而用诗,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情感是自然生发出来的。抒发国志之赋诗则相当于“为文造情”,为实现某一政治目的而用诗,受到政治意旨的支配,故此时的情感是被创造出来的。然而,正是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赋诗者的用诗技法与能力获得多方面的训练,进而掌握了更多的用诗经验。尤其是,由于受到国家意志的规约,春秋赋诗与个体单独作诗言志不受任何思想观念束缚不同,那些平日所表达的带有个性化色彩的情感,在这个群体性活动中被熔炼和整合,强化赋诗者个体抒怀能够与群体性认同融为一体,赋诗者可能会因此失去自我情感,但其获得的却是高于原有情感的更深广的情感。所以,在“为文造情”的创作实践中,不仅使赋诗者用诗技艺得到培训,而且个体胸怀与人格思想也得以提升。
其四,观志与言志相符。由观诗而观志是春秋赋诗的典型特征,如垂陇会七子赋诗而观七子之志,由郑六卿对韩起的饯行赋诗而观郑国之志。与“诗言志”单向性表达作诗者之志不同,“赋诗言志”具有双向性,不仅要求赋诗者言“志”,而且观诗者还要能明白对方赋诗所言之“志”。所以,准确选择和运用诗以言志以及判断赋诗中所达之志,便成为言志者与观志者需要熟练掌握的技能,而不仅仅是将诗作为传统学习的课目。尤其是,还要充分发挥“类”的联想特性,言志者依据现实政治需要表达意志时,是从诗中选取与之相关或相似的篇章,而观志者则通过言志者所传达的诗的信号,同样根据特定情境来揣测言志者之用意,“所赋之诗实际上成了表达思想的一种信息符号,思想的交流是通过将某一思想转换成信息,再将信息还原成思想而完成的”①水渭松:《对于“赋诗言志”现象的考察——兼论〈诗经〉的编律和演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即诗在赋诗活动中实现了从思想-符号-思想的转换。可以说,言志蕴含着特定的动机与目的,所用诗充当了交流符号的作用,观志则是对此交流符号的解读与品评,也是对言志的回应。在如此复杂而微妙的用诗活动中诗的价值得以彰显,也使得言志者与观志者在充分掌握诗本义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政治环境对其进行合理转化和应用,从而使用诗的技能更为圆熟与灵活,进而促进诗学技能的进步。
其五,风雅氛围的营造。劳孝舆云:“垂陇一享,七子赋诗,春秋一大风雅场也。”②劳孝舆:《春秋诗话》,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又云:“自垂陇七子赋诗后,至此二十有一年,复有六卿之赋。郑以孱国处必争之地,诸君子以风雅之气扶持勿衰,孰谓诗人无益人家国哉?”③劳孝舆:《春秋诗话》,第9页。可见,七子赋诗与六卿赋诗在活动中均体现了风雅风貌。七子所赋诗出自《召南》《鄘风》《郑风》《唐风》《小雅》等,选诗范围广泛且风格多样。七次赋诗中,有六次都是对赵孟的赞扬,在使赋诗活动沉浸在和睦氛围的同时,双方良好的礼仪修养、诗学品质、人格气度等也在言志与观志中得以展现,从而形成了一个“风雅场”。赋诗活动不仅使赋诗者用诗的技巧技能得到锻炼,还将其赋诗时由内而外的风貌与风采得以展现,可以说是一次较为全面的用诗训练。郑国以孱弱的区区之地却得以在春秋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纷争中幸存,正是由于六卿赋诗时展现了难得的具有“风雅之气”的外交方式,即借抒发男女之情的《郑》诗以示对观诗者的欣赏,饶有趣味的比附使赋诗变得既风韵又雅致,在呈现郑人带有风雅特质的诗学品格的同时,也拉近了双方友好相处的距离。可见,七子赋诗与六卿赋诗都从整体上营造了风雅氛围,从而使其成为实现政治外交的有力工具。
综上,在春秋赋诗微言相感的群体性活动中,表现出了不同于诗人日常用诗的特有的诗学意义。“诗可以群”孔安国注云“群居相切磋”④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通过关于诗的活动不仅可以将人们聚集起来,还能围绕诗展开相互交流与切磋、协恰人我,而春秋赋诗正体现了这种用诗的本义。事实上,不仅“诗可以群”,赋也有“可以群”的特质,在西汉赋家活动中即有所体现。无论是汉初还是武、宣时赋家们的群体活动,尽管有从用诗到作赋的转变,但由于作赋活动也是在群体中展开,同样呈现了不同于个体单独作赋时独有的赋学意义,拟从以下内容展开具体研究。
二、汉初藩国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
文景时期,虽然帝王“不好辞赋”,但藩国君王却广纳贤才,其中,以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以及长沙王等对辞赋家的吸纳最为显著,文献记载如下:
其一,以吴王为核心的赋家群体。《汉书·邹阳传》云: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⑤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338页。
其二,以梁孝王为核心的赋家群体。《汉书》之《邹阳传》《司马相如传》云:
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⑥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343页。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⑦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529页。
其三,以淮南王为核心的赋家群体。《汉书·淮南王传》云: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宴见,谈及得失及方术、赋、颂,昏莫乃后罢。①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145页。
其四,以长沙王为核心的赋家群体。《汉志》“孙卿赋”录《长沙王群臣赋》三篇②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750页。。又《汉志》“屈原赋”录《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传世文献中唯《哀时命》《七发》《屏风赋》《招隐士》可信。从上述材料看,汉初藩国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主要体现在:
激发赋家创作的群体热情。在藩国赋家群体活动中,赋家创作的积极性被激发,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赋家之间的相互激赏。相如见到随梁孝王入朝的邹阳、枚乘、严忌时“说之”,于是借生病之由辞去官职追随梁孝王。其原因在于景帝不好辞赋,才华与才能得不到施展,而邹、枚、严却以辞赋显达,共同的兴趣爱好使相如更愿意与其一同入梁。由此获得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机会,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创作了《子虚赋》。可以想象,在相如与他们日月相处中,相互间辞赋交流与切磋是常有之事,从而使其辞赋鉴赏力与创作力得以提升。相如入梁前没有高质量的赋作,周围缺乏志同道合之人可能是重要原因,缺乏赋家间的相互激荡与欣赏,从而削弱了创作的积极性而难以呈现出好作品。二是藩王与群臣共作赋论赋。淮南王不仅自己作赋,还与群臣一起积极从事辞赋创作。《汉志》载刘安本人就有赋作八十二篇,而组织群臣所作赋也有四十四篇,不仅如此,《楚辞》中还有淮南王宾客创作的多篇作品,创作之繁盛是其他任何赋家群体难以企及的。尽管作品多已散佚,但还是能够想象当时辞赋创作活动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王“辩博善为文辞”,每次宴会后都要与君王谈论古今得失、方技、赋颂等方面之事,直到“昏莫然后罢”。可见,淮南王热衷于交流与切磋,与君王尚且如此,何况对于群臣,很大程度上会倡导此行为。由此在淮南王集团中,藩王与群臣通过组织探讨辞赋创作的活动,在相互砥砺中迸发创作热情而产生大量赋作。
形成赋作的统一风貌。由于材料多已散佚,藩国君臣的辞赋创作所涉内容难以全面考索,但从现存的材料看亦能有所推测。《汉志·诗赋略》将庄忌、枚乘、淮南王及淮南王群臣赋归入“屈原赋”,可知赋作多以“写怀”③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5页。“抒情”④班固:《汉书艺文志讲疏》,顾实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为主。如王逸为《哀时命》作序云:“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裴然作辞,叹而述之。”⑤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为《招隐士》作序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⑥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32页。此外,《汉志》所载藩国君臣赋中还有枚乘《七发》和淮南王《屏风赋》。《七发》通过对音乐、饮食、骑射、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事的书写,以此讽谕太子享乐奢靡的生活,并借此劝其归于正道。尤其是,凸出了对物的描写和铺陈,具有了体物写志之义。又淮南王《屏风赋》写幽谷之木而幸遇名匠制成屏风,旨在以物寓意表达士人渴求遇明君之志,包括刘向《别录》载“淮南王有《熏笼赋》”⑦刘向,刘歆:《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由此体物言志赋也是当时汉赋创作的方向。不仅如此,《诗赋略》将“《长沙王群臣赋》三篇”列入“孙卿赋”⑧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750页。,属于“骋辞之赋”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5页。,这可能是汉赋主流创作外的另一创作趋势。
三、武、宣时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
迨至武帝时,一改文、景帝“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的局面,“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⑩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72页。,积极主动参与文学、文化建设活动。尤其是,武帝广揽人才,不拘一格任用贤士,“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⑪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第672页。,以及吾丘寿王、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①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863页。,其“遗风余采,莫与比盛”②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第672页。。这个“言语侍从之臣”的队伍数量庞大,以至形成了一个“内朝”统治,如钱穆云:“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朝所贵侍从,则尽贵辞赋。”③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8页。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机会参政议政,从而走进政治权利中心,《汉书·严助传》云:
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④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775页。
此外,这些言语侍从之臣还常随武帝出行,《汉书》之《枚皋传》《司马相如传》云:
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⑤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367页。
尝从上至长杨猎……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⑥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589-2591页。
由此可见,武帝时赋家群体活动对赋家与赋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包括:
其一,赋家才能与技能得到施展。武帝组织的内外朝群体性辩论,使赋家良好的知识储备和辩论技巧得以充分施展,如东方朔“十六学《诗》《书》……十九学孙吴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⑦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841页。,严助“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⑧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775页。,朱买臣“好读书……担束薪,行且诵书”⑨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791页。,吾丘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⑩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794页。,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⑪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798页。及徐乐、庄安也都属于纵横家⑫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739页。,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⑬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529页。“东受七经,还教吏民”⑭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73页。,作《凡将篇》“无复字”⑮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721页。等。可见,赋家深厚的经学、诸子学、小学等学养均可以借此机会得以施展。除此之外,武帝时组织大规模的群体性活动不计其数,而作为内朝的赋家常“并在左右”,“上有所感”便命其作赋,由此使赋家快速揣摩君王心思与迅速构思辞赋的能力得到训练,如枚皋就练就了“受诏辄成”的作赋本领。
其二,赋作质量与数量得以提升。通过参与政治论辩,赋家可以从中取材以充实赋作,如相如《难蜀父老》“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以实现“遐迩一体,中外提福”⑯费振刚等校释:《全汉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如此成熟周全的长远之计,视野宽广的战略构想,无论从政治气概还是从国家气魄来讲,与汉初赋作重视个人情志的抒发完全不同。虽然此创作观的转变有相如的一己之思,但朝中上下群体性论辩给汉赋创作带来的启发或许也是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其它活动也有赋家参与,如在甘泉、雍、河东等举行祭祀而作祭祀赋;在泰山举行封禅而作封禅赋;过宜春宫时作哀二世行失赋;君王得子及河口堵塞而作赋以贺,以及对宫馆、山川的巡游和一些娱乐活动,都会有汉赋创作。《汉志》录《枚皋赋》百二十篇,在数量如此庞大的赋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应诏之作。随从武帝的赋家应不限于枚皋、司马相如与东方朔三人,或许还有其他赋家参与创作不得而知,但以此为例亦能窥探当时汉赋创作的情形。
总之,无论在“朝夕论思”的辩论中,还是随同武帝参与的各种群体性活动中,赋家与赋作都从中受益。迨到宣帝时,由于“修武帝故事”,同样召集了如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王褒等深受青睐的赋家⑰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821页。。《汉书》之《王褒传》《刘向传》云: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①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829页。
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②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928页。
从材料看,宣帝时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主要表现在:
其一,赋作评选标准的讨论。汉宣帝多次命王褒等以待诏的身份陪同巡猎,每到一处宫馆,便命他们创作辞赋,并依照评选等级以赐帛。在这个群体活动中,王褒等赋家均是即兴创作,其宗旨为润色鸿业、藻饰上德。赋作完成后,宣帝还组织评比以分出高下。就评选标准而言,赋作需以“歌颂”为宗旨,这是无可争辩的。除此之外,对辞藻华美的限度则存在异议。“议者”认为“淫靡不急”,一定的藻饰是需要的,但奢靡过度就没有必要了,如王褒《九怀》“以裨其词”③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69页。。然而,宣帝并不以为然,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娱乐对象,如同“绮縠”“郑卫”终是愉悦君王之耳目,不限于对丽辞的过分追求,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这种群体性评骘品评汉赋的活动,对后世将文学交流活动作为文人生活一部分的群体而言,无疑是有影响的。
其二,汉赋理论的提出。宣帝针对“议者”的指责,提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并认为汉赋“贤于”绮縠之工、郑卫之音、倡优、博弈等,正在于它具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丽”的价值。就“仁义”言,相如《上林赋》载帝王通过“驰骛乎仁义之途”“游于六艺之囿”④费振刚等校释:《全汉赋》,第70页。以匡正自身;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指出“引义以正其身”“本仁祖义”是“帝王所由昌”⑤费振刚等校释:《全汉赋》,第133页。的关键。就“风谕”言,枚乘《七发》、相如《子虚上林赋》《大人赋》等讽谏方式各不相同。由观鸟兽草木之名而实现:一是“观风”,从《天子游猎赋》记载的多种珍稀名物,便可知汉朝东西南北、域内域外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又通过对博物的识记,便可以达到人与物的和谐共处,从而培养仁义之心以实现教化作用;二是“观美”,一方面驰骋于辞藻堆叠的审美快感中,另一方面鸟兽比兴带来的艺术想象使身心获得审美愉悦。此外,还有对侈丽闳衍之辞的追求,丽淫、丽靡、侈丽、弘丽、淫丽、靡丽等一系列“丽”范畴的出现,表明它已成为汉赋创作的趋势,以至“没其风谕之义”⑥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756页。。可见,正是通过群体性品评赋作的活动,才促使宣帝对汉赋价值的深入思考,从而提出具有开创性的汉赋理论。
其三,汉赋政治职能的强化。颜师古注云:“进对,谓进见而对诏命也。”⑦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929页。刘向、王褒、张子侨等就是通过献赋的方式答复君王之诏,以实现或讽诵、或颂赞的目的。可见,宣帝时赋家群体性活动不仅发生在巡猎之际,也发生在朝堂之上,与前者即兴作赋有别,后者是应对诏命的创作,受制于皇权与政治的要求,类似于奏议文。献赋活动表明赋家对朝政朝纲给予了积极关注,为其入仕参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与此同时,朝廷也能够通过所献之赋了解下情,适时调整朝政国策,以及借颂赞大赋彪炳帝王的千秋鸿业,从而实现“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西汉献赋活动繁盛,不仅有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还有公卿大臣“时时间作”,可以说献赋“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⑧刘青海:《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0-19页。,尤其是强化了汉赋的政治职能。
四、从春秋赋诗到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特征演变
春秋赋诗活动向西汉赋家群体活动转变中,其特征演变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政治性向娱乐性的演变。先看主体地位。《左传》赋诗者身份大致分为三类:诸侯;王侯夫人、子女;卿大夫①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28页。。诸侯的政治地位不必多言,卿大夫则位于诸侯之下士人之上,且在“国人”中担任领导者。迨到汉初,中央朝廷被武将把持,由于自身“质木而少文”,也使他们对士人进行排挤。与之相反,藩国则广泛招客养士,为寻找新出路的士人便很快与治民聘贤的藩王相结合。他们在帮助藩王巩固藩国地位的同时,还具有粉饰清平、消遣娱乐的作用②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西汉中期,群体活动中的赋家则多取悦、讨好君王。如枚皋赋“恢笑”“嫚戏”,侍从武帝巡行途中所作赋,就有关于“狗马”“蹴鞠”等游戏之作。又东方朔“口谐倡辩”“诙达”“滑稽”,虽然从现存《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政论性作品中无法窥探到,但可以推测在《责和氏璧》《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等娱乐赋中不免有所流露。由此,赋家被视为文学“弄臣”,赋作也成了“帮闲”之物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可见,从诸侯卿大夫—游士—弄臣,主体地位的政治性逐渐减弱,而愉悦君王的一面却得以凸显。
再看用诗作赋的目的。春秋赋诗的目的,如《论语·子路》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邢昺疏云:“古者使适四方,有会同之事,皆赋《诗》以见意。今有人能讽诵《诗》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达;使于四方,不能独对,讽诵虽多,亦何以为。言无所益也。”④何晏,邢昺:《论语注疏》,第196页。可见,通过“专对”以实现“达政”是春秋赋诗之本。这也就意味着,赋诗所言之志不是一己之志而是一国之志,充分表达国家的政治理想与诉求是赋诗者的外交职责。汉代以降,枚乘《七发》旨在讽谏太子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中而劝其归之于正,甚至有学者认为《七发》就是谏阻吴王刘濞之谋逆。又司马相如各赋“无不有深刻的讽谏意味”⑤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如《子虚赋》借批判楚王“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以实现对藩王的警戒。《哀二世赋》虽然没有涉及“讽谏”,但哀叹之感本身就具有以古鉴今的讽谏之意。尽管汉赋“讽谏”最终演变为“劝百讽一”,但“讽谏”仍是相如作赋的初衷,亦如司马迁指出相如赋“然要其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⑥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3页。。汉赋创作的结果与设想相违背,欲讽而反劝,以至“劝而不止”⑦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3575页。。然而,正因此使君王“大说”“善之”,对侈艳华丽之辞的追求愈加狂热,不惜掩盖“讽谕”,从而形成了“赋颂”⑧王充,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2页。之作。由此,汉赋匡正时弊、指摘君王的功能消失了,而沦为粉饰朝政、阿谀君王的消遣之作,如王褒多次侍从宣帝巡行,“所幸宫馆,辄为歌颂”,其《甘泉颂》《洞箫颂》还具有使太子身体安康、心情欢悦的作用。综上,由“达政”—讽谏—“劝百讽一”—“歌颂”—愉悦身心,政治功利性减弱,游戏娱乐性增强。臣子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为国为君的担当意识,也随着这一变化而削减。
其次,礼仪化向日常化的演变。从合礼化、仪式化两个角度看群体活动如何向日常化转变,分析如下:
其一,合礼化向日常化演变。诗乐舞合一较早存在于上古祭祀仪式中,如《尚书·尧典》云:“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⑨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直到周代,这种诗乐舞一体的仪式活动才被典章化固定下来,所谓“制礼作乐”。初期表现以乐舞为主诗为辅,《雅》《颂》产生后,诗逐渐受到重视,从而用于合乐行礼,如《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⑩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5页。可见,从上古祭祀仪式到周代制礼作乐,诗乐舞一体的合礼化得到延续的同时,诗的地位逐渐凸显。直到春秋赋诗,虽然弱化了乐性,但通过“歌诗必类”的合礼规则,诗舞合一的形式在赋诗活动中还可以看到。迨至汉代,赋与乐、舞分离,汉赋又如何表达?《史记·乐书》云: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⑪司马迁:《史记》,第1177页。
《汉书》之《礼乐志》《佞幸传》云: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①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045页。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②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3725页。
以上,记载了武帝时作《郊祀歌》十九章的背景。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语云:“(相如)死后七年,延年始得见上定规之乐……是相如前造诗,延年后为新声。‘。‘多举者’,言举相如等数十人之诗赋,非举其人也。”③班固:《汉书补注》,王先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在王氏看来,相如等所造“诗赋”,事实上就是“诗”,又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故这里所说的“诗”,指将用于“合八音之调”的歌辞。由于歌辞属于诗,故王氏有“是相如前造诗”之言。也就是说,材料中的“诗颂”也指的是诗。又“不歌而诵谓之赋”“颂之言诵也”,赋与颂都可以通过“诵”来表达,这也是“诗赋”与“诗颂”可以替换的原因所在。以此可知,作为歌辞表达方式的“赋”与“诵”相通,而“赋”在汉代又是文体名,由此对赋作的展现自然也会采用“诵”的方式。这样看来,周代至春秋“诵诗”的传统被汉代所承接而为“诵赋”。没有了乐舞的限制,诵赋变得灵活自由,无论在朝堂之上,还是在巡游的各地,西汉文人群体皆可为帝王诵赋,合乎礼仪规范的一面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符合现实境遇、顺应现实需求日常化的一面加强。
其二,仪式化向日常化演变。如“登高能赋”可视为赋诗活动的重要仪式,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④章太炎:《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5页。故赋诗活动发生在堂上或坛上。《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坛宇……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廷也。”杨倞注“坛宇”云:“谓有所尊高也。”而王念孙则认为:“言有坛宇,犹曰‘言有界域’。”⑤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6页。事实上,无论从“尊高”还是“界域”来讲,都说明赋诗具有特定的仪式,不仅需要登临高处用诗言说,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范围,适合一定的场合。赋诗遵循的基本程式是:一方先赋诗,另一方由观诗而观志并作出回应,然后再赋诗再回应,以此循环往复。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鲁国为华定赋《寥萧》,《诗集传》序云:“……天子与之燕以示慈惠……。”⑥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旨在使华定明白鲁国对他的“慈惠”。然而,华定并没有观出其志,故昭子认为其“必亡”。可见,遵照程式赋诗的重要性。与之相比,西汉赋家的群体活动则没有了特定地点与方式的限制而显得平常化,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活中君臣共作赋论赋。如《汉志》记载淮南王刘安一人就作赋八十二篇,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⑦赵歧,孙奭:《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在君王的积极倡导和带动下,淮南王群臣共作赋四十四篇,活动期间不乏有对汉赋创作的相关讨论。二是朝堂上辩论、献赋。武帝在朝中组织的多次内外朝辩论,虽然不是专为赋家组织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但内朝中绝大多数为“言语侍从之臣”,由此与外朝大臣展开辩论时不免涉及关于学术、文化的相关话题。另外,如刘向、王褒、张子侨等进见君王回答诏命时就采用赋作的形式,汉赋便成为君臣日常交流的载体。三是巡行中作赋评赋。赋家参与君王组织的活动,还包括巡行中的祭祀、封禅、巡猎、游观,以及一些游戏活动,甚至临时性庆典,赋家均应命制赋。而且,赋作完成后还常品评高下,尤其是君王也参与其中与“议者”展开讨论。由于程式化的仪节被舍弃,赋家辩论、作赋、献赋、论赋、评赋,都较为常态化。
最后,主体参与性增强。春秋赋诗主要以用诗为主,采用“断章取义”法。《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云:“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佘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⑧左丘明:《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8-1239页。杜预注云:“言己苟欲有求于庆氏,不能复顾礼,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⑨左丘明:《春秋左传正义》,第1239页。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穆公设宴招待重耳时“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杜预注云:“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他皆放此。”①左丘明:《春秋左传正义》,第474页。可知,“断章”或取一章(多取首章)、或取全篇两种形式,借此以获得诗义。又由于春秋赋诗是燕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所言“余取所求”,但事实上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选诗,还是要依据一定的等级制度和礼制规范。因而不可能完全脱离诗本义,是在有所顾及与依托的基础上,结合赋诗情境与国志所需而选诗用诗。这也使得主体发挥受到局限,而难以摆脱诗义框架的束缚。在西汉,现存庄忌、枚乘、淮南王及淮南王群臣赋都被《汉志》归入“屈原赋”,可知抒情写怀赋已在汉初出现。如庄忌《哀时命》强烈地表达了生不逢时的内心苦闷以及对人生道路的迷茫。《招隐士》则抒发了“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之志。之后,司马相如随行武帝过宜春宫时创作的《哀二世赋》,除感叹历史以激励后人外,还表现了一定的使命感。站在曲江岸头的沙洲上,遥望峰峦起伏的终南山,在如此宽广的视野下,古今交织而畅问历史,使自信与自豪的风范与气度尽显。宣帝时,王褒《甘泉宫颂》通过对甘泉宫盛景的称赞,以示对君王“中和”“太平”统治的颂扬。当用诗发展到作赋时,由于不再采用旧作,便可以自由表情抒怀。从汉初围绕个人苦闷惆怅之思的情感表达,到叹古论今强烈责任感的抒发,再到对君王与盛世的歌颂,在西汉赋家群体活动中的汉赋创作,主体从抒发一己之思,到为国而思,再到为汉而颂,情感的表达逐渐升华,也说明主体参与性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