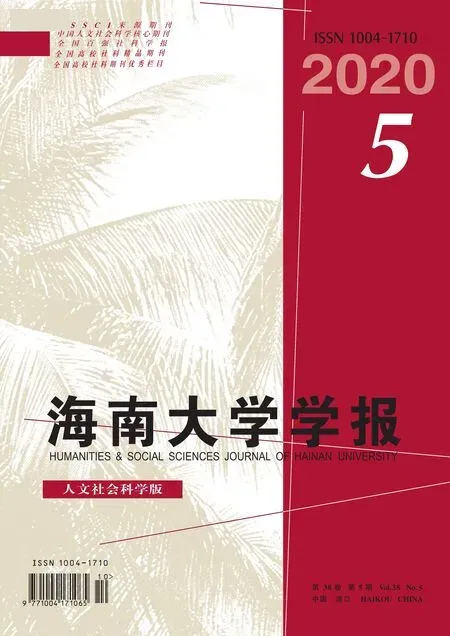《文选》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2020-12-20赵季玉
赵季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
汉藉对古代日本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奈良、平安两个时代,盛行尊崇中华文化的潮流。当时的执政者兼知识阶层,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文学,使得汉学在古代日本地位特别高。比如,日语中的“才(「ざえ」zae)”专指汉学之才,“文(「ふみ」humi)”专指汉诗文。深厚的汉诗文造诣是当时知识阶层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古代文人非常热衷于学习汉诗文。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526—531年)便是其中之一。该书由南朝梁武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共计三十卷,收集了从周代至梁代130余名诗人的约800篇作品,对中国古代文人写作和科举考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唐以前的诗文集中唯一留存基本原貌的作品,文献价值巨大。该书成书以后,《文选音义》《文选钞》《文选音决》等注释书相继问世,其中尤以李善注、五臣注盛行。至唐朝时期,形成专门讲授与研究《文选》的“文选学”,盛极一时。在此影响之下,《文选》白本、以李善注为代表的诸注本也相继东传,与《白氏文集》一起构成了影响日本古代文学的中国典籍之“双壁”。
一、《文选》白本
《文选》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不详,一般认为,早在飞鸟时代(592—710年)就已经传到日本。其影响日本文学的最早踪迹可追溯到《伊予汤冈碑文》①山田胜久:《奈良平安时代的汉藉受容:以文选与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传为例》,《语学文学》1979年第17期,第33页。。推古天皇四年(596),圣德太子行幸道后温泉时在汤冈立碑,并于碑上刻诗,诗文见于《伊予国风土记》。其中的“意与才拙,实渐七步”运用了《文选·卷六十·曹植〈七步诗〉》典故。其后,圣德太子颁布的《宪法十七条》(604年)引用了《文选》。条文第五条规定诉讼裁判应公正,“……便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是以贫民则不知所由,臣道亦于焉阙”②小岛宪之:《日本书纪》二,东京:小学馆1994年版,第545页。,划线部分出自《文选·卷五十三·李康〈运命论〉》。从现实角度讲,一部典籍从传入到被阅读再到被运用于文学创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之,五世纪时史书中便已有王仁向日本献《千字文》《论语》等汉藉之记载,日本与朝鲜半岛交流非常频繁。所以,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元六世纪末期之前,《文选》已经传入日本。
《文选》传入日本之初,主要在政治及文学两个层面发挥了作用。七世纪初期,出于建设律令制国家的需要,日本仿照唐朝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教育制度方面,朝廷于670年根据“唐学令”设置“学令”,置大学寮作律令制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负责学生的教育与考试,为选拔官员服务。在此契机之下,《文选》成为了考试的指南书、纪传道中最重要的教科书以及官吏选拔的重要指标。《养老令》(718年)“考课令”规定:“凡进士,试时务策二条;帖所读,文选上秩七帖尔雅三帖。”①惟宗直本:《令集解》,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第166页。“帖读”即背诵,“上秩”即前十卷,从《文选》前十卷中选七帖。“进士”为次于秀才与明经的第三级别的官员录用考试。“选拔令”中的规定基本相同,“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以上者,进士,取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延喜式》(927年)卷二十“大学寮”条规定:“凡应讲说者,礼记左传各限七百七十日,……三史文选各准大经”②虎尾俊哉:《延喜式》,东京: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523页。,《文选》被抬升至准经学的地位。
在上层建筑的作用之下,《文选》成为了知识阶层的必读书目,能够诵读该书是文人的汉文基本素养之一。《续日本后纪》“藤原常嗣薨传”承和七年(840)四月二十三日条记载:“常嗣……涉猎史汉,暗诵文选”,《文德实录》“藤原诸成卒传”齐衡三年(856)四月十八日条记载:“暗诵文选上秩”。此外,《九历》天历二年(948)八月十九日条记载了村上天皇赞叹藤原高光能背诵《文选·卷四·左思〈三都赋〉》之事。《古今著闻集》“卷四文学第五”第123篇,劝学院③藤原冬嗣创建的供藤原氏族接受教育的地方。的学生在酒宴上决定不按年龄而按照才能排座,其时,惟宗隆赖径自坐上首席,遭到其他学生质疑,其表示若有人能像自己一样诵读《文选》三十卷、“四声切韵”便让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一方面显示出古代文人对《文选》的重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他们并没有掌握《文选》的所有卷篇,藤原高光能够背诵的内容为左思《三都赋》、藤原诸成诵读的是《文选》前十卷、像惟宗隆赖一样能背诵三十卷的人少之又少。
古代日本文人学习《文选》的方式,据《令集解》“学令”记载,“凡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讲义”④惟宗直本:《令集解》,第449页。。这条规定显然仿照了《唐学令》中的“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根据此条可知,学习汉藉,第一步是“读”,即无需理解文意,大声朗读,然后由博士讲解文义。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汉语对于日本人而言相当于“外语”,在朗读方面要比中土多一道程序,即所谓的“白读(音读)”,跟随音博士学习汉音。《文选》的读音方式为先读汉字音接着训读,如“细细腰支”读作「細細(さいさい)と細やかなる腰支(ようし)の腰(こし)」,再如“关关雎鸠”读作「関関(かんかん)と和(やわ)らぎ鳴ける雎鳩(しょきゅう)の雎鳩(みさご)」,前一个词语的音读构成下一个训读的定语或状语。训读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准确的翻译方法,它不仅实现了汉藉的“日本化”“外语”的本土化,而且,保证了日本文人对汉藉的理解,是中国古代典籍在日本源远流长的语言基础。九条家旧藏《文选》是现存最古的传本,其书写方式为上代假名⑤中村宗彦:《九条本文选古训集》,东京:风间书房1983年版,第28页。,为日本人对《文选》进行了训读之佐证。据《续日本纪》宝龟九年(778)十二月十八日条记载,“玄蕃头从五位上袁晋卿被赐姓宿弥,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于后历大学头安房守”⑥藤原继绳:《续日本纪》,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第445页。,唐人袁晋卿于天平七年(735)随遣唐使到达日本,由于通《文选》音,被任命为“大学音博士”。“文选音”即《文选》汉字音,袁晋卿担任的是教授《文选》汉音之职。由于上述读音方式主要用于《文选》,因此,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文选读(「文選読み」monzenyomi)”,这从侧面反映出《文选》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古代文人接受《文选》的样式多种多样。据《菅家文草》(900年)卷六“北堂文选竟宴”记载,宽平八年(896)秋冬之交,文章博士纪长谷雄于纪传道校舍文章院(北堂)讲读完《文选》之后,举行了“竟宴”。“竟宴”中的“竟”为结束之意。平安时代,宫中进讲完一部典籍或者敕撰完毕一部和歌集之后,作为结束仪式会摆设宴席,是为“竟宴”。席间一般会以讲读内容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天皇若在场还会赏赐大臣物品。此次“文选竟宴”上,每人被要求以《文选》中的语句为诗题作诗,其中,菅原道真被分配到的诗题为谢灵运《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中的“乘月弄潺湲”,其所咏诗为:“文选三十卷,古诗一五言。五言何秀句,乘月弄潺湲(后略)”①菅原道真:《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川口久雄校注,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353页。。除了“竟宴”方式之外,《文选》诗意还被绘制于屏风之上,诗文的意境被具体化、视觉化的同时降低了阅读门槛,成为汉文能力较低的女性受容该书的重要方式之一。据《荣华物语》卷十六记载,藤原齐信由大纳言升职为中宫大夫以后,专心为独生女物色结婚对象。当时日本处于摄关政治之下,将女儿进献给天皇成为外戚进而掌控政治是当时贵族在政治方面的最高追求。为了将独女献给更高级别的贵族,藤原齐信悉心培养其修养,“近年来,(齐信)一心专注于养育女儿,其它事皆不关心,制作了《后汉书》御屏风、《文选》《文集》屏风,放在帐台(坐卧之处)、幔帐等地方,……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女儿送给天皇或者中宫都配得上。”②山中裕:《荣华物语》,东京:小学馆1995年版,第245页。至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日本开始流行刻本《文选》。据源经赖《左经记》万寿二年(1025)七月三日条记载,“及午御参堂。东宫以子克御迁大内。仍有御送物用意〈摺本文集一部、同文选一部。……〉”。“摺本”即刻本。当日,东宫敦良亲王即后来的后朱雀天皇从上东门第回到宫内,经赖祖父藤原道长赠送刻本《文选》以示祝贺。
《文选》对文学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成为文学特别是汉诗文创作的范本,其影响范围跨越整个日本古代文学,即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在长达18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的接受阶层虽然经历了从贵族到武士最终庶民化的过程,但其作为汉藉经典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
奈良(710—794年)、平安时代(794—1192年),接受教育是皇家贵族的特权,如《养老令》规定只有官位在五位以上氏族的子孙才有资格进入大学寮学习。众所周知,在日本律令制度中,五位为位阶分界线,以上者为贵族阶级,以下者为非贵族。《文选》的接受阶层自然也被局限在了贵族文人阶层。据《日本后记》弘仁十年(819)正月条记载,文章博士菅原清公侍读嵯峨天皇《文选》,据《日本三代实录》仁寿元年(851)四月二十五日条记载,春澄善绳为文德天皇讲读《文选》,可见《文选》在皇族的受欢迎程度。随笔《枕草子》第121段曰:“文章最好的当属文集、文选……”③清少纳言:《枕草子》,松尾聪,永井和子校注,东京:小学馆1997年版,第336页。,反映了贵族文人对《文选》的热爱。对当时的作品的影响方面,《日本书纪》为日本现存最古的正史书,该书“雄略纪卷十四”中的“命虞人纵猎,陵重巘赴长莽,未及移影,狝什七、八,每猎大获,鸟兽将尽,遂旋憩乎林泉,相羊乎薮泽,息行夫,展车马”语出《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④小岛宪之:《书纪的素材——与文选、史记、汉书、后汉书之间的关系》,《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1951年第2期,第67页。。平安中期的《本朝文粹》卷十“暮春、陪上州大王于池亭,同赋‘渡水来落花’”中的“古人有言曰:天下良辰美景赏心悦事,此四者难并”出自《文选·卷三十一·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汉诗文集《性灵集》中的“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者一首”中的“伏惟大唐圣朝,霜露攸均,皇王宜宅。明王继武圣帝重兴。掩顿九野牢笼八纮”,分别出自《文选·卷四十三·丘迟〈与陈伯之书〉》“霜露所均,不育异类”与卷四十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直接引用,而是对词语进行了巧妙组合,且重组的词语意思无误。如果不是已将《文选》烂熟于心,是不可能如此运用自如的。此外,平安中期源为宪撰《世俗谚文》共收录631条谚语,语出《文选》者有20条。
镰仓、室町时代(1192—1603年),日本政权由公家天皇转至武家幕府。由于幕府及地方诸侯并未设立学校,因此,这个时期文学及文化的担当者为僧侣,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文人对《文选》的喜爱与引用。吉田兼好在日本古代三大随笔之一的《徒然草》(1317—1331年)第13段列举了自己的爱读书目,“独坐灯下,披卷诵读,与古为友,是最上的慰安。其书则《文选》之妙文……”⑤鸭长明:《徒然草》,神田秀夫校注,东京:小学馆1995年版,第91页。,并在第21、30、38、93、129段等部分大量引用了《文选》诗句。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曾我物语》引用了12条《文选》中的格言。说话集《十训抄》中有8处引用《文选》,分别为卷一第22篇、卷二第2篇、卷五序文、卷六第17篇、第34篇、卷九第5篇、第7篇、卷十第66篇。
江户时代(1603—1868年),德川幕府大力倡导文教,兴办了包括“寺子屋”在内的学校教育机构。随着教育的普及,虽然《文选》的接受阶层庶民化,但评价仍然颇高。服部南郭在《南郭先生文集》四编卷六所载“文选读例三则”中高度称赞《文选》,“昭明选,今犹击节其清英,通观古今后,知其无比。且古人之绝作,独存此书,因以不朽者,间有之。伟哉。”①服部南郭:《南郭先生文集》,东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版,第59页。《文选》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从印刷、发行情况可知。据芳村弘道统计,江户时代出版的《文选》版本有12种之多,有白本、注释本、删减本等,而且每种版本被不断重版、再刊②芳村弘道:《和刻本〈文选〉——从版本看江户与明治期的〈文选〉受容》,《学林》2002年第34期,第38-91页。。
二、李善注、五臣注等注本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藉目录学著作,此书收录了在日本历代皇室藏书地冷泉院火灾(875年)中幸免于难的汉藉、火灾前被借出尚未归还的汉藉、藏于皇家贵族以及寺院中的汉藉,是九世纪之前中日书籍交流之重要文献佐证。该书“总家集”条目下共著录85种书籍,其中与《文选》有关的有十种,“文选卅昭明太子撰”“文选六十卷李善注”“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抄卅”“文选音义十李善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文选音义十释道淹撰”“文选音义十三曹宪撰”“文选抄韵一”“小文选九”③藤原佐世,空格矢岛玄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4年版,第224-225页。。
从书名来看,九世纪之前在日本流传的《文选》诸本,除了白本之外,李善注本、各家注《文选音义》等琳琅满目的注释本也传到了日本。这是因为虽然日本文人积极学习汉藉,但其汉文能力仍然有限,需要借助注释本才能更好地理解。据《新唐书·李善传》记载,《文选》在李善加注、其子李邑补订以后才变得方便易读。可想而知日本的情况。那么,这些注释书是何时传到日本的?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怎么的影响呢?
日本文学中使用李善注本的踪迹可追溯到《日本书纪》(720年)。据小岛宪之考察,该书《天智纪》中的“西北带以古连旦径之水,东南据深泥亘堰之防,缭以周围,决渠隆雨,华实之毛则三韩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则二仪之隩区矣……州柔设置山险,尽为防御”出自《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④小岛宪之:《书纪的素材——与文选、史记、汉书、后汉书之间的关系》,第62页。。其中,划线部分不见于《文选》正文,出自李善注。并且,此时,成书于开元六年(718)的五臣注本尚未传到日本,因为遣唐使宇治比县守刚刚回国,下一批的遣唐使还未出发。也就是说,李善注本在八世纪初以前已经传至日本。
由于注释本更加方便理解阅读,李善注本很快在日本得到传播。比如,正仓院古文书主要收集了圣武天皇(701—756年)与光明皇后(701—760年)的遗物,其中有写经生抄写的《李善注文选拔萃》⑤东野治之:《正仓院文书与木简研究》,东京:塙书房1977年版,第194页。。所谓写经生,即在朝廷设立的专门抄写汉藉的机构“写经所”中负责抄录、誊写工作的人群。他们一般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选出,需要认真摹习,以求最大程度地接近唐本。《李善注文选拔萃》中所抄写的基本上是《文选》中的难解诗词,这从反面证明了注释本对于日本人的重要性。此外,如前所述,古代日本人阅读《文选》时,有音读与训读两种方式。据中村宗彦考察,古代日本人训读《文选》时,依照的是李善注与五臣注,很少使用钞、音决、陆善经等其它注释本⑥中村宗彦:《九条本文选古训集》,第28页。。至十二世纪时,李善注本仍然是贵族的收藏书目之一。据《台记》康治二年(1143)九月二十九日条:“今日所见及一千三十卷,因所见之书目六载左……李氏注文选六十卷自笔抄保延六年”⑦藤原赖长:《增补史料大成第23卷台记一》,京都:临川书店1965年版,第99页。。
随着李善注本的传播,李善之注释也被运用于了诗文创作中。平安前期的贵族、文人都良香(834—879年)的家集《都氏文集》卷三“辨薰莸论”中的“不同器而藏,当异处而种”出自《文选·卷五十四·刘峻〈辨命论〉》李善注“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同国而治,以其类异也。”《本朝文粹》卷八“七月三日,陪第七亲王于读书阁同赋‘弓势月初三’”中的“频献燕弗,欲继陈篇……初三夜月,似一张弓。望兔影细悬……”中的“陈篇”“兔影”等词语出自《文选·卷十三·谢庄〈月赋〉》及李善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不见五臣注。其出现在文献中可追溯到《御堂关白记》宽弘三年(1006)十月二十日条,“唐人令文所及苏木、茶碗等持来,五臣注文选、文集等持来”⑧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上卷),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6年版,第124页。。“令文”即宋朝商人曾令文。其将带至日本的“唐物”送给道长,其中便包括《五臣注文选》。
但是,五臣注被应用于文学,至少可追溯到奈良时代。小岛宪之曾经提到,成书于平安时代的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文总集《经国集》(827年)有使用五臣注的痕迹①小岛宪之:《国风暗黑时代的文学 中下1》,东京:塙书房1985年版,第1959页。。笔者在小岛宪之的基础上发现,《经国集·卷一》所收贺阳丰年(751—815年)《和石上卿小山赋》为奈良时代之作,文中有用词语出自五臣注。该诗“公既自畅俗,亦退私寻真。……嗤东海肥遁,恨北山隐沦”中的“北山隐沦”指周颙隐居北山,出自《文选·卷四十三·孔稚珪〈北山移文〉》:“孔德璋善曰……向曰,……其先,周颙伦隐于此山。后应诏出为海盐县令,欲却过北山”②萧统编:《六臣注文选》,李善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17页。。而“隐沦”对应五臣注中的“伦隐”,不见于白文及李善注。该诗创作年代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于“石上卿”即石上宅嗣(729—781年)存世年间,因此,确定为奈良时代的作品。如此,五臣注的使用年限可推至奈良时代。
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使用五臣注的痕迹。《都氏文集》卷五“辨论文章”(877年)写道:“虽云经籍满腹之儒,难逐文章随手之变”。这部分依据的是《文选·卷十七·陆机〈文赋〉》:“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诗文中的“逐”,李善注为“逮”,五臣注为“逐”,可见,该诗依据的是五臣注本。
至于奈良时代便已传入日本的五臣注本却不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原因,笔者猜测可能是因为在冷泉院火灾中被烧所致。
此外,文献中也可零星见到公孙罗的《文选抄》《文选音决》、六臣注本。据《江吏部集·卷中·述怀古调诗一百韵》记载,长德四年(998)九月某日,大江匡衡被召入宫中,担任天皇的侍读。当时所读内容为:“……文选六十卷 毛诗三百篇 加以孙罗注 加以郑子笺……”③大江匡衡,柳泽良一:《江吏部集》,东京:勉诚出版2010年版,第179页。。“孙罗注”,点明匡衡讲解《文选》使用的文本为公孙罗注本。依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知,为《文选抄》《文选音决》二书。
六臣注本,笔者检索了以《御堂关白记》《权记》为首的19部史料④分别为:《八条式部卿私记》《太后御记》《沙门仲增记》《元方卿记》《济时记》《藤原宣孝记》《小右记》《御堂关白记》《一条天皇御记》《左京记》《春记》《二东记》《后朱雀天皇御记》《师实公记》《后三条天皇御记》《宽治二年记》《季仲卿记》《高阶仲章记》《清原重宪记》。,皆未记录。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所收88部文学作品中唯一提到六臣注的作品为江户时代江岛其磧的《浮世亲仁形气》(1720年),“今后若是想读《文选》……肯定会缠着让我给他买《六臣注》”⑤长谷川强:《浮世草子集·浮世亲仁形气》,东京:小学馆2000年版,第493页。。这个现象与前文提到的芳村弘道的考察结果相吻合。芳村所统计的江户时代《文选》版本中,绝大多数为六臣注本,仅元禄十二年(1699)、天明四年(1784)、明治十五年(1882)年出版过白本《文选》。可见,六臣注本盛行于江户时代。
三、《文选集注》
十九世纪初,日本发现了《文选集注》抄本残卷。该书以李善注本为底本,集合了《钞》(《文选钞》)、《音决》(文选音决)、五臣注本、陆善经注本等诸多版本,共计120卷,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由于《钞》《音决》、陆善经注本原书已散逸,且该书保留了李善注原貌,故文献价值甚高。1955年,被日本指定为国宝、重点文物。如今,遗留在日本的抄本残卷有二十五卷,分别藏于东山御文库藏、金沢文库。关于该书以及古抄本的编者、成书时间、地点等是目前国内研究的焦点,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中国唐代学者所编⑥傅刚:《〈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第8页。。由于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关注点,此处不再详述。
一般认为,日本文人使用《文选集注》的时限横跨整个平安时代。因为现存《文选集注》两种传本中,东山御文库藏本(卷八、九)最初被认为是平安后期的抄本,因为两卷卷末写着“校了。源有宗”,而源有宗生活在白河天皇与堀河天皇时代,为平安后期人物。但是,近年来,发现了卷七断简,学界从字体判断,认为是平安前期的抄本。金沢文库本,一般认为晚于东山御文库藏本,为平安中期的抄本⑦川濑一马:《日本书籍蒐藏历史》,东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版,第27页。。从两部抄本可知,《文选集注》在平安时代已经流传。
《文选集注》出现在日本文献中的时间,学界追溯到了一〇〇四年。《御堂关白记》长保六年(1004)十月三日条记载:
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持来。感悦无极。是有闻书等也。①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上卷,第59页。
小尾郊一、陈翀等一致认为,引文中的“集注文选”即为《文选集注》一书②参考小尾郊一、花房英树《:全释汉文大系第26-32巻 文选(文章篇)一》解说,东京:集英社1974年版。陳翀:《集注文选》成立过程:以平安史料为线索》》《,中国文学论集》,2009年第38期,第55页。。对此,笔者没有异议。但是,《文选集注》在文献中的出现时间问题似乎有待商榷。因为早在《御堂关白记》之前,已有相关记载。藤原行成《权记》长保二年(1000)九月六日条曰:“左府于中宫有召,即参向……亦先日匡衡朝臣所传仰注文选、才所求得四十余卷。非一同。随仰可令进上。”③藤原行成:《权记》,京都:临川书店1965年版,第218页。六日当日,左大臣藤原道长召见藤原行成(972年—1028年),行成向道长汇报了各种事情。引文为其中诸事之一。之前,道长已向大江匡衡(952—1012年)传达了天皇令其进奉“注文选”的命令。行成报告道长,截至当日,匡衡已求得40余卷,还没有收集齐全。对此,道长令行成督促匡衡,按照天皇之命奉上“注文选”。至七日,行成将道长的意思禀告天皇,天皇曰:“文选虽不具,可进”,表示即便没有收集也可奉上。
这条文献已有日本学者注意到,但均围绕编者问题展开④陈翀以该条记载为依据,指出《仰注文选》即《文选集注》,故《文选集注》的编者为大江匡衡(陈翀:《〈集注文选〉成立过程:以平安史料为线索》,《中国文学论集》,2009年第38期,第51页。)对此,佐藤道生提出异议,指出“仰”为命令之意,大江匡衡编者说不成立(佐藤道生編:《注释书的古今东西》,东京:庆应义塾大学,2011年版,第118页)。,没有考证其中的“注文选”一词。佐藤道生只提到一句,“《注文选》指谁人之注,不得而知,将其看作是来自中国的注释书比较稳妥。……天皇希望得到的书为《文选》”⑤佐藤道生編:《注释书的古今东西》,东京:庆应义塾大学2011年版,第118页。。后藤昭雄表示:“天皇寻求的书籍为《注文选》,令大江匡衡搜集,该书为何物,仅凭这条记录,不得而知”⑥后藤昭雄:《大江匡衡与文选》,《语文(大阪大学)》2013年第100期,第16页。。
以下两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第一,“注文选”究竟为何书,第二,六日条中的“注文选”为何在七日条中变为了“文选”。第二个问题的不明确,导致一者曰天皇希求书籍为《文选》,一者曰为《注文选》。对此,笔者认为七日条中的“文选”与“注文选”为同一书,天皇命令大江匡衡搜集的并不是《文选》,而是《文选》注释书,更准确地说是《文选集注》,理由如下。
第一,《文选》白本共计30卷,而六日条中大江匡衡收集到的卷数为40余卷。可以肯定,该书为注释书。从“才”字可知,所搜集到的卷数与书籍原卷数之间差距甚大。若搜集目标为60卷本李善注或五臣注,则40余卷已经非常接近总数,应该不会使用“才”字。从这两点可以猜想,“注文选”为《文选集注》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日本当时有将《文选集注》称为《文选》或《文选注》(《注文选》)的现象。比如,《三教指归集注》卷上:“文选云,古包羲氏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句不见于《文选》白文,李善注、五臣注虽有类似语句,但并不相同。相同语句仅见于《文选集注·卷四十七·潘安仁为贾谧作赠陆机》⑦周勋初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又,该书中卷:“文选注云,苏非……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乃与登山,即日升天,八公安所践石上,人马之迹,于今存也”,此句也仅与《文选集注·卷五十九·谢玄晖和王著作八公山诗》重合。由此可见,该书施注者成安在引用《文选集注》时,并没有写“集注曰”,而仅以“文选曰”或“文选注曰”道出。这说明在当时的日本文人看来,“文选”“文选注”可以代称“文选集注”。
第三,其它史料中也有将“注文选”与“文选”混称的情况。宽弘七年(1010)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条天皇从枇杷殿还幸固定住所一条院。道长为表示庆祝,将汉藉作为礼物献给天皇。此事被同时记录在了《小右记》《权记》《御堂关白记》,但汉藉名称有异,分别为“模本注文选”“摺本文选”“摺本注文选”。“模本”“摺本”即刻本,是印刷术兴起的产物。道长所献的同一部汉藉分别被记为了“文选”“注文选”,显然是因为“注文选”可被简称为“文选”。
第四,据《御堂关白记》宽弘元年(1004)十一月三日条记载:“事了间,集注文选,内大臣取之。右大臣问,内大臣申云、宫被奉集注文选云云。”“宫”指中宫彰子,道长之女。当日,一条天皇到彰子宫中游玩赏乐,结束后,彰子进奉《文选集注》。将这条文献与开头提到的两条结合来看,天皇在四年之间分别于一〇〇〇年九月七日左右得到“注文选”、一〇〇四年十一月三日获得《文选集注》。可以猜想,天皇第一次仅得到40余卷,并不满足,事后很可能会继续令人收集,这两次献书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或许十一月三日的《文选集注》为“注文选”之后续。十月三日条中,道长得到《文选集注》之后“感悦无极”,称其为“有闻书”的原因或许也在这里。由于知道该书为天皇希求之物,道长于十一月三日将乘方所献《文选集注》通过彰子之手献给了天皇。
上述种种迹象均表明天皇命大江匡衡所收集的“注文选”即为《文选集注》。如果上述推测正确的话,那么,史料中关于《文选集注》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一〇〇〇年。其后,《文选集注》开始频繁出现在文献中,如《江谈抄》卷六—“张车子富可见文选思玄赋事”曰:“予问云,丹波殿(大江匡衡)御作诗中,司马迁才虽渐进,张车子富未平均。张车子事见集注文选思玄赋之中。”①大江匡房,藤原实兼:《江谈抄》,山根对助,后藤昭雄校注,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25页。该书同卷“游子为黄帝子事”曰:“游子有二说,一者黄帝子也。……此事见集注文选祖席之所也,饯送之起此之缘也。”
此外,《文选集注》被日本文人使用的记录可追溯到十世纪中期。据中国台湾学者邱棨鐊考证,抄写于天历二年(948)五月二十一日的《汉书·杨雄传》古抄本旁注中有一条注释出自《文选集注》②邱棨鐊:《唐写本〈文选集注〉九十八卷跋:〈文选集注〉为唐写本再证》,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30页。。此外,《三教勘注抄》中的“目龙川以带垌,尔雅曰,林外谓之垌,音决,吉营反”引自《文选集注·卷九·吴都赋》:“音决,垌吉萤反”③周勋初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81页。,“左思吴都赋曰,双则比目,片则王余……钞曰,尔雅曰,东海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郭氏曰,状如牛脾细鳞,鳞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行”亦出自《文选集注》。凤来寺旧藏《和汉朗咏集》古抄本白文旁注也有引用《文选集注》的痕迹④佐藤道生編:《注释书的古今东西》,第109页。,该抄本“蒸栗”注曰:“集注文选八十三曰,美玉之黄侔蒸栗。注,刘良曰:栗,木实。蒸之妻色鲜黄。言美玉有如此色”,“春华”注曰:“集注文选八十九曰,擒春华。吕延济曰,发文如春物之华。”
四、结 语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文选》早在飞鸟时代便已传入日本,并很快在政治及文学层面发挥作用,成为了律令制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指标、纪传道中最重要的教科书以及文人诗文创作的范本。其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与影响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于古代日本文人而言,用汉字书写、以汉音朗读,是驾轻就熟之事。古谚语“劝学院的麻雀也会音读《蒙求》”便是音读盛况的真实写照。日人汉音读与训读的一般顺序为将一句话或大段文字音读完毕之后再进行训读。《文选》的特别之处在于,每读完一个词语便随即进行训读,前一个词语的音读构成下一个训读的定语或状语,极为特殊。第二,《文选》受容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文字方式之外,其语句经常作为诗题在“竟宴”上被赋诗吟诵,甚至被绘制于屏风之上,诗文意境实现了具体化、视觉化。第三,由于注释本有助于更好地进行理解,李善注、五臣注等注本很快相继东传,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学。本文在小岛宪之的研究基础上,推测五臣注本应该早在奈良时代便已传入日本,并且,通过文史互证指出《权记》长保二年九月六日条中的“注文选”为《文选集注》的可能性极大,由此将学界目前考证的《文选集注》在日本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由一〇〇四年提前至一〇〇〇年。值得注意的是,与白本、其他注本不同,《文选集注》的主要作用是被用于注释相关典籍,对平安中后期文人而言是一本相当于辞典性质的工具书。江户时代最盛行的是六臣注本。第四,从飞鸟时代至江户时代,随着印刷术的出现,日本文人使用的文本从抄本转换为刻本,随着政权更迭与知识阶层的改变,《文选》的接受阶层依次从贵族文人(奈良、平安时代)转变为武士僧侣(镰仓、室町时代)再到町人庶民(江户时代)。严格说来,这个特征并非《文选》所特有,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典籍在日本流传的普遍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选》的第四个特征可谓是整个中国文学在古代日本流布的一个缩影。不过,《文选》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在日本作为经典的时间且长广泛,很少有汉诗文能与其相比肩。
在东传日本的广袤汉藉中,相较于学界对《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之研究蔚为壮观的景象,《文选》显得颇为寂寥。实际上,《文选》传入日本的时间比《白氏文集》早将近300年,在后者东传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一枝独秀,是影响日本古代文学作品时间最长的汉诗集。其与诸注本一起为日本文学提供了华丽而丰富的辞藻,丰富了其内涵,浸润到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文选》中的诗文素养,一直流淌在日本文学中,构成闲雅幽静的诗文世界,成为了“花鸟风月”旋律之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