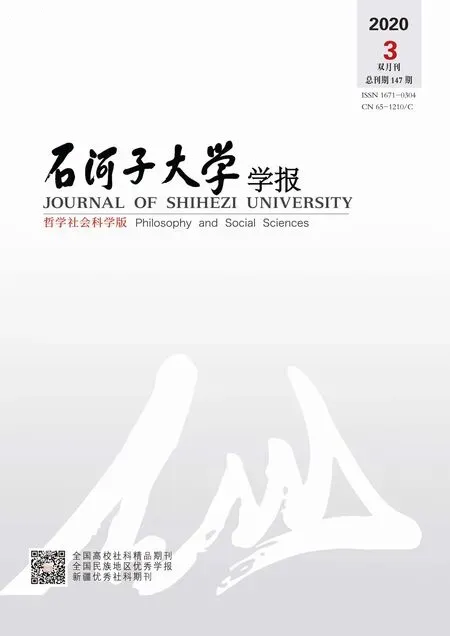从“资源宝库”到“战略要地”
——20 世纪初至30 年代前期国人新疆游记中的新疆形象
2020-12-20成湘丽
成湘丽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自古西域多被视为朔漠苗方,“不独是地理上的远方,也是文化的远方,是认同的远方,是交流的远方。”[1]146西行之路多被视为畏途,所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故中国传统士人阶层,若非遣戍、仕宦、奉使、流放、发配等非个人因素,少有主动行旅于西域者。然而从民间交往而言,由于屯边、行商、行伍、传教、逃荒、犯罪等情形,普通民众行旅往来于古丝路上的,一直都是络绎不绝。
自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收复西域后,西北史地学成为显学,对西北地区的建制沿革、风土地理等的考订盛极一时,其中不乏纪昀、洪亮吉、祁韵士、徐松、林则徐等赴新疆的内地一流文士,加之中国传统文人立言不朽之夙愿、明清时期游记文体之发达,造成后来大凡有机会足履西域的,莫不以撰写行旅日记并在其中旁搜博引前人著述为乐事,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加之其时中国正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赴新疆名士的文化身份更为复杂、国家立场更为坚定、忧患意识也更为强烈,这些都潜在地影响了20 世纪初国人新疆游记的整体性观念变革和风格转向。
一、20 世纪初至20 世纪20 年代中期:西北舆地学及余脉影响下的“新疆图志”
20 世纪初至民国元年,依次被遣戍、调任、贬谪到新疆的内地政府官员有方孟希、裴景福、宋伯鲁、温世霖、袁大化、单骑、刘雨沛等,清廷新政后聘到新疆者有李德怡、贾树模等。裴景福1905 年被谪戍新疆,旅程日记《河海昆仑录》分4 卷,记录沿途地理、气候、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民族、风俗、宗教,有大量即景诗词。宋伯鲁因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上海被捕,为伊犁将军长庚所救后于1906 年3 月离家赴疆,其《西辕琐记》记录沿途所见风土人情、地方物产。李德怡在《北草地旅行记》(1907)中,扼要记录了一路“水陆途程,山川形势、风俗人情、起居习惯、气候物产、经历沿革”[2]4。1910 年末,温世霖因以“全国学界同志会”会长名义遍电各省,要求罢学并速开国会,而被直隶总督下令拿办。温世霖于1911 年1 月10 日被押解上路,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五省,于1911年5 月31 日抵达戍所迪化,《昆仑旅行日记》记载了沿途所见社会面貌、地景风俗、教育人文等。
1910 年11 月13 月,清廷宣布调任袁大化为新疆巡抚,1911 年2 月6 日,袁大化从家乡安徽涡阳出发,一路日夜兼程,于1911 年6 月11 日抵达迪化巡抚衙署,著有《抚新纪程》和《壬子回程记》。在《抚新纪程》中他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人口、店铺、井渠、地势、矿藏、植被、驿站、兵邮、气候、民风、军政面貌、教育情况等。
这些清代末年游记中的新疆形象,基本还是接续清末西北舆地学的流脉,其基本体例是遵循晚清西北舆地学的传统,既重视乾嘉考据学的运用,更重视实地调查的经验,沿行经路线严格记录了每到一地的里数、路况、地貌、植被、水道、街市、遗址、物产等。同时,这些著述中莫不包含有大量历史地理之信息、地志通史之内容,不足在于有错引漏引、不加考证的地方。
1911 年5 月,清末陆军军官刘雨沛因部下倡举革命,被牵连发配到新疆,九月抵达迪化。民国元年因鄯善令裴逖亏空巨款后潜逃,刘雨沛奉袁大化之命前去镇抚,撰有《民国元年五月率师至吐鲁番哈密镇抚途中日记》,时间起于1912 年5 月5日,止于6 月1 日。因为身负军事重任,无暇顾及全面,书中更多是对所经之地战事讯息、民生概貌、地方势力、道路交通、地理沿革等的记录。
贾树模,河北保定人,1910 年“应新疆实业教员讲习所之聘,以赴新疆方期竭尽绵薄”[3]14-15,主讲地理、生物等课程,因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学堂被撤而东归,1911 年到迪化旅行,11 月返程经古牧地、阜康、三台、奇台、阿尔泰、鄂博金等地返回保定,著有《新疆杂记》①参见贾树模《新疆杂记》,原载于《地学杂志》,1917 年第1、2、4、6-12 期,1918 年第2、3《新疆归途记》。其《新疆杂记》采用的是专论文体,全文六章分别以新疆之地理、人文、天然物、生计界、新旧政界、结论为题,其中天然物分别从动物、植物、矿产,生计界分别从农业界、农作物、植物、交通及运输业,新旧政界分别从官界、审判界、警察界、军界、学界,学界又分别从教育界、报界、特别组织等方面入手,对新疆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予以细致梳理。
单骑的《新疆旅行记》记录了自1913 年3 月—8 月间,从北京出发赴新疆考察的往返行程,其中“上卷记述自京赴新疆路程详情,约占去全书三分之二篇幅;下卷叙述在新疆省城调查情形,涉及财政、军队、教育、商贸、官吏、民情、地形、物产、制造、政府文书、民族关系及外情等各方面,并包括一份新加整理、相对详尽的新疆全省道里纪录”[4],以及疆内40 条道路的具体情况。
谢彬,湖南衡阳人,字晓钟,作为北洋政府财政部特派员到新阿地区调查财政问题,一路经过数十省,1917 年2 月24 日至11 月18 日在新疆考察,足迹踏遍新疆38 个县辖行政区(共43 个县级单位),疆内行程16 675里。30 万言的日记体游记《新疆游记》经《时事新报》刊载,《地学杂志》《民心周报》等转载,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单行本《新疆游记》,1923 年4 月初版,1929 年3 月就已达7 版,被誉为“20 世纪初新疆的百科全书”。《新疆游记》就途经每一行政区记下其地理沿革,并详细记录了每到一地之地貌水道、物产奇闻、人口八栅、道路里数、文物古迹、历史沿革等。
与谢彬同行的助手林竞,浙江平阳县霞关人,字烈夫,1916 年冬赴疆考察9 个月,“以财政部特派员名义来新考察全省财政,兼以农商部特派员名义调查新疆实业状况”[5]23,出版的考察报告《新疆纪略》2 万余字,从吏治、军政、财政、外交、实业、教育、司法、民族、交通等方面分门别类地概述新疆整体状况,天山学会1918 年4 月出铅印本。1918 年11 月,林竞又奉北洋政府交通部命令,率测量队到新疆实地查勘铁路线,经北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于1919 年5 月5 日抵达迪化并短期停留。后林竞拟出《西北丛编》八卷,其中计划在上编第1、2 卷收入1916—1917 年的新疆游记,但正式出版时,只有上编的3、4 卷①《西北丛编》(3-4 卷)由上海神州国光社1920 年出版,1931 年再版,其中第3 卷为“民国七年由北京往新疆迪化”,第4 卷为“民国八年由新疆迪化至绥远归化城”。第3 卷记载了1918 年从北京出发经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到新疆迪化的经过,第4 卷记载了1919 年自新疆迪化经蒙古返京的经过。甘肃人民出版社将《西北丛编》校对后于2003 年以《蒙新甘宁考察记》题名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将《西北丛编》收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于2010 年、2013 年以《亲历西北》题名出版。,为其第二次西北日记。此书主旨是为改善西部的交通状况,勘测建设“西北国道”。在从迪化返回绥远归化的路上,每到一地林竞都按行进路线记录了各地之地理概况、山脉水道、道路地势、气候概述、里数疆域、险要杂记。
邓缵先,自号毳庐居士,广东紫金县蓝塘镇人,1883 年15 岁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14 年9月,应北洋政府内务部第三届县知事试验,取列乙等,分发新疆。1915 年邓缵先辗转数月于7 月抵达迪化。1917—1920 年,相继代理乌苏县知事,任叶城县知事。1921 年,历任新疆省总选举文牍员、新疆省公署文牍员、编辑员、新疆省公署政务厅内务科长总务科员、新疆覆选区选举调查会会长等职,为省主席杨增新撰写公文。1926 年至1933 年,历任疏附县知事、墨玉县知事、巴楚县县长,因南疆暴乱而举家殉职。他在乌苏、墨玉等地重视开渠引水,兴修水利,并促进了墨玉县农桑、丝绸、金玉业的发展,1920 年卸任叶城知事返迪任职时,“父老子弟壶浆饯送,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至玉河边,犹留恋涕泣。”[6]11其记录沿途见闻的《叶迪记程》(1921),“如山脉、水道、物产、民风、城市盛衰之迹,官治沿革之由,靡弗援古证今,举要陈述。”[7]199
钱桐,字孟材,江苏无锡人,杨增新时代曾任新疆驻京办事处处长,在《东三省西比利亚新疆观察记》(1918.9.1)中记录了他经满洲里至塔城的往返路线,多为中苏经济贸易、货币政策、新疆现状和苏日关系等的记录,后来他在《赴新考察记》(1928)中增加了关于新疆财政、军事、教育、物产、吏治、交通、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和开发新疆的建议。
二、20 世纪20 年代中期之前新疆游记的主要面向:初描资源宝库 擘画开发蓝图
这些政府官员大多肩负考察经济、镇压叛乱、政府委令等特殊任务,其游记整体风格并不是以表现行旅之凄苦艰辛为主调,而是延续了清代新疆游记经世致用、雄健明朗的写作传统,并竭力以客观全面的史家笔法审度新疆风物。清末名士王树枏在晚年自订的年谱中说:“窃谓新疆地方二万余里,农田、水利、桑棉、瓜果之盛,牧畜之繁,五金之矿,富甲海内。”[8]68-69曾做过金矿主办等实业的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详细考证了每到新疆一地的道路井渠、人口吏治、兵邮民店、田亩畜数、资源物产等,并擘画设计着执政后的垦殖移民、规划道路、兴修水利、开发矿藏等宏图伟业,他不无豪情地写道:“可招民实边,为国家尽一分心力,培一分元气,绵一分国祚也。然为民兴利,办一分即收一分之益。果能实心任事,勤加董劝,则民不招而自来,何患利之不兴?财之不阜?凡是皆然。”自星星峡至哈密一路,他最重视的是“凿井筑室,招民屯种”[9]208,“从招民垦荒入手,为根本之谋”[9]208的安排,因为“兴利实边之策无古今,一也”[9]211。东、西盐池“户少无可专卖,设局徒多扰累,尚不如按丁摊课为简便也。亦目前计,非经久策,将来盐场仍须收归官有耳。”[9]216看到迪化水西沟、阜康等地的煤矿,袁大化筹划“将来生齿繁衍,铁路开通,其利无穷也”,阅视水磨沟机器局,“俟物力殷裕,尚可扩充。”刚刚到任后的1911 年夏天,袁大化就上奏折吁请清廷修建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的铁路,以国防屯边之需,正如徐翔采在《抚新纪程》跋文中对袁大化的评价:“固其记载,不为高尚之论以惊世炫俗,据实直书,切近事功。”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之策也为时人频频阐发,钟广生述《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中说:“新疆幅员二万余里,荒矿工牧甲于环球。公初入境,凡遇草木丰茂,山川奇兀,水必穷其源,山必竟其委。见夫煤露于山,土弃于地,恻然念民生之不易,实边则有为也”①参见钟广生述《新疆伊犁乱事本末》,1912 年。。贾树模在《新疆杂记》的结论中,在分陈新疆乐观悲观之前途利弊后,特辟筹新疆一节,感叹“新疆之利若彼,新疆之危若此,然则筹新疆者将奈何?夫筹新疆者亦多矣,曰练兵也,曰移民也,曰兴实业也,办学校也,修铁路也”[10]43-44。单骑认为:“新疆虽取若何政略,接济巨款,训练重兵,振刷吏治,抚辑边民,而不办交通,皆成空言,无救存亡之局。”[11]668林竞在《新疆纪略》中指出:“欲图新疆者,必自铁道路”“交通一便,莫重于移民”,认为“执此二端,能举则存,不举则亡,其著效固不待五年也”②参见林竞《新疆纪略》,迪化:天山学会铅印本,1918 年版,第47 页。。一直到20 世纪30 年代,吴绍璘在《新疆概观》中同样认为:“总理所昭示吾人之修筑铁路、移民殖边二办法,既详且切,训政开始,当即奉行勿失。”[12]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国内舆论界已注意到新疆作为资源宝库之潜在价值,《申报》上甚至说:“新疆矿产,和阗之玉,于阗之金,人所共知”,而金矿“几至遍地皆是”[13],林竞称“西人谓中国矿产甲于全球,而新疆复甲于全国。”[15]13“将来畜牧繁兴,则新疆一省,可供世界之需求,固不仅称雄全国已也。”[14]19同时,林竞还在《新疆实业纪略》一文中说:“兴新疆语实业。各省殆无有能望其项背者。言矿产则昆仑天山千支万派,奇杰雄伟,五行百产之英,孕育繁富。言森林则枝梢参天,朽干满谷。言农牧,则塔里木河伊犁河孔雀河诸流域旷原无边,气候适宜。言工则土人智巧不逊汉人,鞍鞯革氍毹,霞夷之属,皆为中外所称道。言商,则地处欧亚之冲,四塞灵通,土人嗜利,远趋不亚粤鲁,诚神州天府之区,世界实业之大舞场也。”③参见林竞《新疆纪略》,原文裁《农商公报》,1920 年,第6 页。这段对新疆极尽溢美之词大致源自谢彬:“新疆轮廓二万余里,面积之广,伯仲关东。地味饶沃,矿藏繁富。物产之丰,甲于寰宇。以言农田,膏腴美地,遍天山朔南。以言畜牧,羊马牛驼,群翳原野。以言森林,树木参天,浓荫纷乘,朽枝老干,横满山谷。以言工艺,旃裘齿革霞夷氍毹,屯积都市,远销英俄……”[15]361
肯定新疆之为资源要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游记作者们已初具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疆域观和领土观,中国传统文人之“天下观”和“夷夏观”开始逐渐被“世界观”和“国家观”所取代,尤其是“晚清对外关系是整个传统的中国文明在全球化时代进行顽强抗争的历程的最尖锐体现。因此,晚清成为国人的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结:这种情结使我们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尤其重视民族的尊严,对于国际关系的平等问题尤其敏感。”[16]20一方面是晚清政府签署的一系列割地赔款条约,一方面民族解放浪潮已开始波及大批帝国主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都促进了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民族权益和国家安全意识之提升。这正如当时徐益棠所说,清末民初直到20 世纪20 年代末,大凡谈论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17]。这一趋势之加强,与现代学科体制和学术制度之建立关系甚密。
三、20 世纪20 年代后期至30 年代前期:现代考古学和边疆学发凡中的新疆考察热潮
不同于民国初年到访新疆并留诸文字于世的刘雨沛、谢彬、林竞、钱桐等人,时至20 世纪20 年代末,随着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之逐渐确立和海外留学活动的日益高涨,作为中西现代学术学科体制联手打造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新疆历史考古、地理地质、气象生物等诸多方面的第一次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勘查,西北舆地学的学问之道也逐渐被现代科学考察活动所取代。这些学者的行游日记不仅呈现出现代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知识背景,同时他们对当时中国时局政坛之变幻、新疆时政边防的针弊、历史文物古迹之价值、社会文化教育的现状、新疆经贸税赋之特征、交通通讯信息的落后、民族风俗艺术之特别等,都有不少醒人耳目的真知灼见和感同身受的体察。
比如西北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旭1928 年6 月在焉耆明屋遗迹,痛惜地感叹:“我等在此处发掘,专捡被火焚处工作,因未被焚之地悉被外人掘尽,被焚者外人所不顾也。火烧后犹有残余可寻,而外人发掘后片物无存,此余等来晚之苦衷也。”[18]205在如此逆境中,黄文弼的考古发掘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1928 年春,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在迪化只逗留月余(3 月8 日—4 月19 日),就孤身踏上了前往南疆的科学考古之旅,当时的新疆政府多次致电地方官员催其返回阻拦其行,黄文弼“思之甚久,决定前行,宁可被阻而返,不可示弱”,并坚持孤身在南疆继续考察文物遗迹,后又大致取原路返回,其日记中也保留了他对当时南疆地貌物产、山川河道、民族宗教、风俗文化等的总体印象。黄文弼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道听途说的古迹之所,他在民间广泛搜求各类与古代文物或有关联之物,因“盖人民生活状况,随时变迁,以古证今,求其变迁之迹亦最有兴味之研究也。”[18]279多沿之前外国探险考察人员所行进路线和雇佣向导,深入阅读各类与新疆有关的史书、图志以资勘查考辨,其日记中尤其重点介绍了南疆佛寺、墓室、城关中铜钱、经卷、佛像、碑铭、干尸、竹简、文书、衣物、器皿等的发掘情况。这些详实丰赡、细致清晰的记录为其后来关于西域考古文物文献研究的学术著作《高昌》《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黄文弼又三次赴新疆考察,每次都撰写有大量与新疆考古、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关的专业学术论文、普及介绍类文章以及行旅游记日记等,并因居延汉简等重大文物的发现而成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
相较而言,中法学术考察团的学术考察活动则乏善可陈,即使是在为出行正名的辩词中,中方团长褚民谊也说:“此次考察团名为学术考察团,实旅行团耳。所考察者,不过所遇城市乡村部落,而为走马看花之考察也。法方固不愿逗留我国甚久,如此则考察团仅观察西北边陲之政情、风俗、物产而已。”[12]325
20 世纪30 年代初,正如方秋苇所说:“要了解非常时期我国边疆的危机,必要了解世界危机的发生及对于我国的影响”[19]42。至于新疆则“已非中国的新疆,而是国际化的新疆了。它的前途和它的一切变化,都是在整个东亚形势演变之下而被推动着”[20]44。一方面,列强对外侵略促成了国人边疆危机意识的提升,边疆问题和地缘政治在日益复杂的国家关系中日趋敏感,另一方面,欧美列强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国家战略利益等刺激下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在边疆地区的势力博弈又加剧了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中国国内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蒙古难保、东北沦陷之背景下,国内要求开发西北的声浪盛极一时,正如马鹤天在《甘青宁边区考察记》中所说:“空前的觉悟却也由之而起,优秀分子都到西北和西南,开发的事业肴肴进行,每一个国民的心瓣上都展开了‘边疆’两字。”加之为鼓励国人赴西北考察,民国政府内政部于1931 年、1935 年两次颁布《提倡国人考察边境办法》①参见吴绍璘《新疆概观》,南京:仁声印书局,1933 版,第16-17 页。,除对国人赴西南、西北边境考察加以明确规范外,还要求沿途各地区行政机关予以保护和协助,并对考察者给予半价乘火车的优惠等便利②参见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之附录二《提倡国人考察边境办法》;又见王衍祜《西北游记》,广州:清华印务馆,1936 版,第64-66页。。与西北实地考察活动和相关游记出版相伴生的,是大量西北研究团体和研究报刊的创立。早有学者统计,近代中国期刊刊名中冠有“西北”出版的,在1930 年以前只有5 种,但在1931—1945 年间出版的,则多至70 种③参见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载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1 期,“根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贯有“西北”二字的杂志如西安《西北论衡》《西北史地》、北京《西北研究》《西北言论》等杂志目录统计:1930 年以前的5 种,1931—1945 年的70 种,1946—1949 年的13 种。”。
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边疆学迎来了第一个春天,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边疆研究也不再是仅隶属于史学研究的领域,而是出现了大量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等现代学科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著述。同时,一些之前未有机会出版发行的新疆或西北游记开始受到青睐,如《新疆游记》等早先的游记开始被反复重印,清末李德怡的游记《北草地旅行记》1936 年6 月由其次子季伟抄誊付梓(蓉城刊印本),王天元的《近西游记》1935 年由南京拔提书店印,已回内地多年的伊犁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杨缵绪的《现在的新疆》出版,该书序言说明写作动机“是为救国而作”,吁请国人“注意那快要被人攫去的宝藏边陲”。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刊载于报刊上的连载游记,也被出版社很快结集出版,同时还有很多报纸如《晨报》(北平)、《中央日报》(南京)、《时事新报》和《申报》(上海)、《大公报》(天津)等时有刊载开发西北的报道文章和旅人见闻。
四、20 世纪30 年代前期新疆游记的主导面向:战略要地和资源大省
此时的舆论报刊开始不断强化“到西北去”之主张,薛桂轮说:“抵沪之日,重见洋场崇楼大厦,车马行人憧憧往来,顿感觉大不自然。噫,若辈甘于局促一隅,饱尝拥挤风味者,殆不知另有世外桃源,其富无比,其大莫京,正待人之开发乎!彼饱食暖衣,徜徉娱乐作海上寓公者,盍亦思及无衣无盐,无枝无栖,致颌下生奇瘤,鬻子女而度活,乘牛羊皮筏以冒险,一切不得自由,更不知幸福为何物之同胞乎?茫茫神州,沉沉大陆,倘有实行救国救民,利己利人之主义者乎!窃愿以最简单之方式,进最诚恳之忠告曰:‘还是到西北去。’”[21]244实际上,在“到西北去”的声浪中,很多人的考察都是止于陕甘青宁诸省,如蒋介石、宋子文、顾颉刚、马鹤天、范长江等,薛桂轮、林鹏侠、陈赓雅等原定的新疆行程也只能止于哈密,这些游记作者所承担的大多是这一建构在国家立场和国族意识之上的大规模的知识与实践工程的中介角色[22]172。边疆学发凡中的新疆问题研究,还主要表现在对新疆史地沿革、国防战略、物产资源等的一般性介绍和通论式述评上,很多文章都存在着大而空疏、博而不专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新疆到甘肃一线已被不少爱国知识分子看成是关乎国家命运和抗战成败的生命线,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新疆也最易调动起国人“保我国土”的爱国热情和“五族共和”的民族情怀,新疆作为西北重地,开始受到民国政府要员和精英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关注。左宗棠的“保疆论”之鉴史名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23]702——开始被广泛引述,用以强调新疆作为中国西北要塞咽喉的重要性。如吴绍璘说“惟在今西北诸省,处地最要,出产最饶,有关中国前途至深且巨者,当首推新疆,新疆存则中国安,新疆失则中国危。盖新疆者,中国西北之屏藩也。屏藩若撤,西北即亡,秦、陇、青、宁,难图安枕。果尔,则沿海既不堪守, 边腹又不能保, 所谓泱泱大国, 尚有立足地耶?”[12]2陈赓雅说:“西北为我国堂奥府库, 新疆尤为中部屏藩,蒙藏依界……”[24]3褚民谊说:“在地势上,西北更形重要。新疆与蒙古唇齿相连为中原之屏障,为边陲之第一道防线。……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则华北各省皆呈动摇川。”[25]刘湛恩说:“诚以新疆失则秦陇危。秦陇危则燕冀震动,则中原将瓦解。”[26]7向波说:“新疆外接苏俄,内联蒙藏,实为我国西北边防上之第一屏障。”[27]易敌无也称“此可谓千古扼要之论”[28]264。
另一个对新疆之关注焦点是对新疆物产资源的肯定,这一经济学视角对西部风景的介入与1930 年代初国民政府在中国面临日本威胁时“开发西北”之舆论导向有关,“西部中国从‘自然风景’向‘物质资源’的转变,既是从古典‘游记’向现代‘新闻’的文体转换,更是一种对‘原始’的西部进行现代化开发的设想。”[29]。谨慎者如吴绍璘称:“新疆乃一未经开发之处女地,其土地之广大,山川之雄奇,位置之重要,固足令人叹为西北之豪富。”[12]223夸张者如美国人丹伯在1930 年从新疆返回上海后说:“新疆实为中亚西亚之天府,……诚遍地黄金之地也。”[30]40-41深情者如陈赓雅,他在未能继续成行而从哈密返回兰州归途中写道:“即窥其外表,举凡草瑞花琪,露润气爽,林木葱茂,沙石晶莹,石油涌现于沟壑,煤盐更缘山麓而暴露,已足令人低回流连,心旌摇曳不已矣!”[24]321深思者如冯有真,他对新疆农业、矿业、牧业、手工业等的发展都提出了具体建议,如对“弃而不知其用”的皮毛,应“运至工业区域,殆为毛织品最佳之原料矣!”[31]29“按南疆气候土壤,颇类江浙,故宜蚕桑,如能善授其法,努力提倡,则新疆蚕丝之利,亦为可计也。”[31]32“窃以新疆地广人稀,如移民屯垦,用科学方法,改良农业,则既可减内地拥挤之苦,又可收开发西北之效,一举数得,利莫大焉。”[31]31。更多论者称:“新疆乃我国富庶之区,西人有名之为中国未发之宝藏库者。新疆之富饶,可谓神州天府之区,世界实业之一大宝库也”[26]5,“中国矿产甲于世界,新疆又为中国各省之最,洵非虚言也”[32]664,“新疆轮廓二万余里,面积之广,伯仲关东。地味饶沃,矿产繁富,物产之丰,甲于寰宇。”[33]“夫新疆者地大物博, 早为中外人士所深悉, 如贵重之黄金、白玉,工业重要原料之煤、铁、石油,牧狩物如皮、毛、骨角,农作品如米、麦、葡萄、瓜果等,产生各种人生必需物品多至不能枚举,诚足为中华民族的西北经济乐土”[34]。在20 世纪30 年代前期的新疆著述中,我们所见如此大量的对新疆自然资源不无夸饰的溢美之词,或许更多体现的是当时国人普遍对国家领土安全和边疆地缘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些对曾经习而不察的风景的热情高涨和重新发现,更多是基于行旅者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升华出的“恋地情结”。
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提到的是,由于20 世纪30 年代前期,新疆不断陷于政治危局和兵燹之灾,并曾面临人口锐减、土地荒废、经济破产、生产瘫痪等严重问题,所以也有很多考察新疆的行旅作者,如实记下了当时的新疆社会面貌,如杨钟健的《西北的剖面》记载了自星星峡至哈密以及在哈密城内所亲历的马仲英叛乱;李天炽在《新疆旅行记》中提及由于财政亏空不得不印制省票,以致“支出额则以印刷额之多寡为断”[35]。吴蔼宸的《新疆纪游(附苏联游记)》主要记载了1933 年马仲英叛乱围攻迪化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冯有真所见当时哈密遭遇兵乱后的面貌是:“兵变之馀,生灵茶毒,房舍被毁,现在断垣残壁,十室九空,一片焦土,惨不忍视”[12]141。徐戈吾的《新疆印象记》和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都详述了战乱对哈密等天山北麓居民生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
1933 年6 月初,黄慕松赴新疆宣慰,7 月21日黄慕松及其随员高长柱、杨秉离、艾沙等回南京复命。虽然未竟事功,但随黄慕松赴新疆的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百余名宣慰使署人员,如王应榆、钱桐,自兰州随行的新疆代表宫碧澄等,后来多有关于新疆的专论发表。黄慕松回南京后即于8 月2 日召开记者招待会专谈赴疆宣慰经过,在简略介绍了此行经过和新疆局势后,他一面担忧于“经第二次政变后,各方疑惧益多,前途更为可虑,加之新省交通阻塞,商运停顿,纸币低落,物质缺失,留心新事与国防者,应有深之注意与研究”,一面期盼于“新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载之各游记各史册者,历历可考。固不待亲历其境而后知蕴藏之厚。且几千年前,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若国人举全力而开发,其利于国计民生,诚非浅鲜。”[36]这一态度较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时期专访过新疆的高层官员对于新疆的基本认识。
如果说,在自清中叶以来一代代被流放、贬谪、获罪至新疆的文人骚客那里,游记主体因不甘放逐而沉重摇摆之内心,与面对迥异于内地的边塞风光而生的沉浸忘忧形成的反向情感张力,使其笔下的新疆形象也总是处于荒僻奇险与开阔壮丽之反复摇摆之中;在20 世纪40 年代之前的外国作者游记那里,经过层层叙述累积,新疆形象往往被塑造成一个完全迥异于本国经验的充满异域情调和神秘魅力之所在。对照之下,20 世纪初至30 年代前期能有机会行旅新疆并付之于文者,大多政府特派官员或精英知识阶层,行旅者大多以民族国家立场和国家开发实业为大计,所以这些游记中呈现更多的是作为国防要塞、资源宝地、文物宝库和开发要地之新疆形象。这一时期新疆行旅记游书写的主体还是从内地赴疆考察的知识分子,由此生成的新疆形象也绝大多数孕育于北平、上海、南京等相对发达繁荣的中心城市。可以说,从20 世纪初内地行游者笔下的资源宝库,到20世纪30 年代关注西北学者眼中的战略要地,新疆形象的变化主要源自当时主流的知识生产模式、媒介传播方式、信息资讯手段、舆论价值标准、文化消费观念等对边疆知识生产和文化经验的影响渗透,加之20 世纪前期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兴起,都潜在影响了这一时期国人新疆游记的主流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