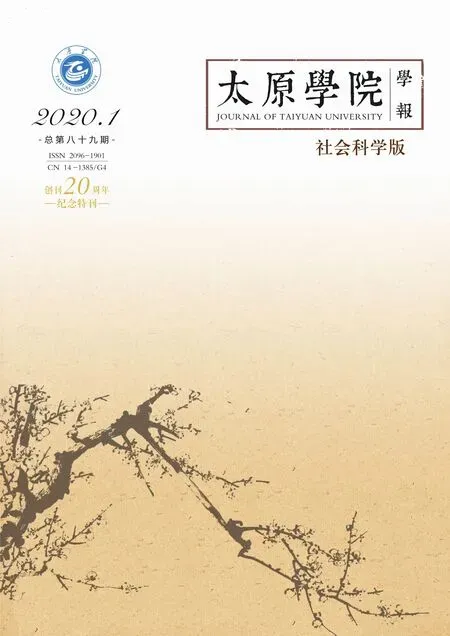文学地理景观的古今之别
2020-12-20费团结
费团结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文学中的地理景观描写,由于景观物质的稳固性、恒常性,因此在古今作家笔下似乎并无区别。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古代诗人吟咏过的山、水、花、木、月亮等自然景观,仍是现当代作家经常表现的审美对象。就像当代诗人流沙河笔下的那只蟋蟀,“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类似蟋蟀这样永恒的地理性文学意象何止千万!但是,仔细辨析,古今作家笔下的文学地理景观仍是有所区别的。
一
现代文学中的风景何以不同于古代作家笔下的风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所谓的风景与以往被视为名胜古迹的风景不同,毋宁说这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1]1他是以风景及其发现的视角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因此,他所谓的风景是指现代的风景,在他看来古今文学中的风景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这两种风景的不同与康德所论及的美与崇高的区别相联系,进而论述道:“被视为名胜的风景是一种美,而如原始森林、沙漠、冰河那样的风景为崇高。美是通过想像力在对象中发现合目的性而获得的一种快感,崇高则相反,是在怎么看都不愉快且超出了想像力之界限的对象中,通过主观能动性来发现其合目的性所获得的一种快感。”[1]1通过这样的区分,柄谷行人认为:“现代文学就是要在打破旧有思想的同时以新的观念来观察事物。”[1]2在柄谷行人的论述中,不管是“风景之发现”,还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发生,具有“新的观念”的人或对外界不抱关怀的“内面(内在)之人”是其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只有现代人的确立,才能发现现代之风景、创建现代之文学。在这里现代人的新视角、新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以柄谷行人的看法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无疑也是妥当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现代人逐步确立的过程中诞生的。仅就风景、景观描写来看,现代人的新视角、新观念带来了新的风景面貌。如鲁迅笔下 “故乡”的“苍黄”“萧索”,沈从文笔下“边城”的“青山绿水”“风俗淳朴”等。作家何以如此描写?这只能从作家主体所具有的启蒙思想或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理想等角度去分析。当代学者张夏放注意到了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月亮”形象的“象征性”,认为相比古典小说来说,这一点正是现代小说“现代性”的一个特征;他进一步比较了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在风景描写上的不同:“现代小说更注重小说整体的象征,写景状物会顾及到全篇的构思,而古典小说的写景文字却有局限性,只在情节转换的某一处渲染气氛,或营造意境,或烘托人物情怀,常常是寥寥数笔,点到为止,写意性较强,不像现代小说为了小说的整体目标而致力于对风景的刻画。”[2]33这里张夏放对现代小说“象征性”的强调,实际上强调的是现代作家在创作中注入的整体性的思想观念。现代小说之所以“致力于对风景的刻画”,正源于现代作家所具有的现代观念、现代视角。在此崭新观念、视角的观照之下,现代作家重新发现了风景,或者说重新发现了风景的新的意蕴、特质与价值。
吴晓东在论析郁达夫对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时,注意到了“郁达夫笔下的诸多风景在东方文化的底蕴外,其实也经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3]86。具体地说,就是在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他“喜欢把东方风景与西方景观进行类比”,他借助于西方书本和图片中的“拟象的风景”,如米勒的画、外国古宫旧堡的画、显克微支的小说、易卜生的话剧和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小说等,来对中国的风景加以观照并赋予意义。吴晓东指出:“郁达夫与西方图片的这种比照隐含着某种他自己或许也无法意识到的悖论:这种‘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正是借助于他者的眼光透视出来的。风景由此也成为西方的他者的眼睛所见的风景,而多少丧失了东方自己的自足性。”[3]88郁达夫没有意识到自己观看风景的眼睛并非全是自己的,而是背后还有一双“西方的他者的眼睛”。这是一种双重视角的观照,其中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也是现代的文化视角。正是在这一外来的异质文化视角的烛照下,郁达夫才发现了东方风景具有崭新的意义和面貌。其实鲁迅、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对乡土中国风景的描写,何尝不是西方现代文化视角观照的结果。
柄谷行人谈到风景的发现是通过对外界不抱关怀的“内面(内在)之人”。这里人的“内面(内在)”与外界的区别,实际上也是主客观世界的区别。这一世界的二元区分,不同于古代人与自然相联系、相混同的一体化的世界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正是这种古代世界观的典型体现。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罗宾·柯林武德论及古希腊的自然观,指出古代希腊人的自然观是建立在自然与人的类比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intelligent);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4]4。古代希腊人这种自然与人相类比的思路,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样,都认为世界是由人和自然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西方,大致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与自然逐渐分离从而诞生了现代的人,与此同时也发现了纯粹的自然和风景。荷兰学者梵·丹尼·伯杰指出,在西欧最初把风景作为风景来描写的是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他说:蒙娜丽莎属于被风景疏远化了的“最初的人物”,她背后的风景也正是风景作为风景而被描写的“最初的风景”,“这是纯粹的风景,而非仅仅是人的行为之单纯背景。这种风景是中世纪的人们不曾知道的自然,自给自足的外在自然,其中原则上消除了人的要素”[5]18。梵·丹尼·伯杰所谈的“最初的人物”就是现代的人,“最初的风景”就是现代的风景。也就是说,现代的风景与现代的人通过相互疏离而同时诞生。这里虽然谈论的是绘画,但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柄谷行人明确指出:“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的。因为写实主义所描写的虽然是风景以及作为风景的平凡的人,但这样的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须通过对‘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的发现才得以存在。”[5]19
二
对于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景描写及其与传统小说的区别,中国学者李扬有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说:“景物描写又称为环境描写,是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要区别……在黑格尔提出了历史逻辑中的个人主体性之后,作家才可能站在传统之外、历史之外、环境之外对‘客观世界’进行一种细致的描写,正因为这个原因,18世纪以后随着启蒙运动产生出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与传统传奇史诗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区别就是现实主义对环境的描写。这种描写在巴尔扎克那里达到了顶点,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常常出现有时长达数页的环境描写。”[6]98-99对于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作家来说,作为主体的人与环境是主客二分的,他们已经习惯于环境的客观性,可以随时从外面观察和描写环境,但对古代作家来说却并非如此,古代作家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独立于自身以外的风景可供他们描写。因此,不同于古代作品中很少有静态的客观环境描写,高扬主体性的现代作家突然发现了外在的风景,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了这些风景。李扬深刻地指出:“环境与景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某一套叙事话语中。只有人不在‘环境’与‘景物’之中的时候,人才可能去客观描述它,而认为人能够站在环境、历史之外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的现代叙事。”[6]99根据李扬的论述,大量的环境、景物描写的出现以现代作家主体性的产生为根本条件,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正是现代小说环境、景物描写的典型代表。李扬论述的要点,除了作家主体性的不同特点以外,主要着眼于环境、景物描写量的多寡。如果考虑到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实际,那么其环境、景物描写显然是以人文社会地理景观为主的。另外,也许考虑到了与自己论题的关联性,李扬在此并未提及同样因启蒙运动而生的浪漫主义文学对环境、景物的热衷描写。
勃兰兑斯在论及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思》(也译作《新爱洛漪丝》《新爱洛伊丝》《新爱洛依丝》等)时说它“第一次在英国以外的小说中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真正感情,以此取代谈情说爱的客厅和花园”[7]16。勃兰兑斯比较了新旧不同时代出现于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不同的景观:“在路易十五和摄政时期(在书中和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在闺阁绣房中度过他们的时间,这里是谈情说爱、干风流韵事的好地方。这些房间,就像伏尔泰在《即兴诗》中描绘的那样,点缀了大量的爱神和赐人美貌、欢乐和幸福的三女神像。在花园里,在人工喷泉边上,有羊脚畜牧神拥抱白色苗条女仙的浮雕。瓦多和才气稍差一些的布谢和朗克莱在他们描绘当时游园会的图画中,给我们留下了这种花园的情景:在林荫小道上,在寂静的角落里,高雅的绅士和轻薄的贵妇人,装扮成小丑和小丑的情妇,调情卖俏,低声耳语,为参加这纵情欢乐的化妆舞会露出得意的神色。”[7]16而卢梭的《新爱洛绮思》主要描写的是他的家乡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日内瓦湖的自然山水风景,当然不同于摄政时期的文学取景。如他对日内瓦湖旁边的瓦莱山区“一些出乎意料的风景”的描写,就写出了自然山水的诡谲、壮丽和经过人类开发的“人化自然”的精巧与伟大。卢梭作品对自然景观的艺术描写及其“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对他同时代的作家和后代作家都影响深远。勃兰兑斯曾说,卢梭在十九世纪初“对欧洲所有主要国家巨大文艺运动影响程度之深是惊人的”[7]5,像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乔治·桑,德国作家蒂克,英国诗人拜伦等,都受过他的影响。比如夏多布里昂,他的小说《阿达拉》对北美景物富有浓郁色彩的描绘,就脱胎于卢梭对瑞士风光的描绘。但夏多布里昂与卢梭在写景方面也有不同之处,“夏多布里昂写景时对男女主人公情绪的考虑要多得多。在内心感情的波涛汹涌时,外界也有猛烈的风暴;人物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人物的感情和情绪渗透到景物中去,这在十八世纪文学中是从来没有的”[7]18。显然,夏多布里昂在小说的自然风景描写上,既承续了卢梭,又发展了卢梭。岂止是夏多布里昂,上文提及的受卢梭影响的许多作家,在风景描写上也是各有发展,各有个性特点的。
需要注意的是,浪漫主义作家对类如夏多布里昂笔下北美丛林那种神奇、暴烈的自然景物特别感兴趣。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论及了这种独特的审美趣味:“……他们的审美感和前人的审美感不同。关于这方面,他们爱好哥特式建筑就是一个顶明显的实例。另外一个实例是他们对景色的趣味。……卢梭以前的人假使赞赏乡间的什么东西,那也是一派丰饶富庶的景象,有肥美的牧场和哞哞叫着的母牛。卢梭是瑞士人,当然赞美阿尔卑斯山。在他的门徒写的小说及故事里,见得到汹涌的激流、可怕的悬崖、无路的森林、大雷雨、海上风暴和一般讲无益的、破坏性的、凶猛暴烈的东西。这种趣味上的变化多少好像是永久性的:现在差不多人人对尼亚加拉瀑布和大峡谷比对碧草葱茏的牧原和麦浪起伏的农田更爱好。”[8]235-236卢梭前后作家审美趣味的不同,实际上正是柄谷行人提到的康德所区分的美与崇高的不同。因此,卢梭及其影响的作家的笔下风景,正是一种现代的风景。
三
不管是卢梭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风景,还是巴尔扎克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风景,都是一种不同于古人或传统的现代风景。这种不同,一方面在于产生崇高感的风景与产生美的风景不同,另一方面更在于观看风景的人的不同,人的观念、视角等的不同。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观看者,就有什么样的风景。古人看到的只能是古代的风景,现代人看到的也只能是现代的风景。这里,人、观看者,或者就文学创作来说就是作家主体,其所持有的现代观念(包括自然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代风景可以说是以主客分离的主体性哲学为基础,高扬作家主体性而生成的风景。
郁达夫曾经比较了现代作家创作的“农民文艺”与古代诗人创作的田园诗歌的不同:“古代中国的田园诗人的作品,大抵是赞叹田园风景的纯美,农民生活的安乐的。……这些作者,大抵是自身不到田里去,只立在高岸上作客观的人。由客观的地位看来,农夫周围的自然风景,的确是美得很,农夫的生活的态度,当然是高尚自由的。然而太阳火热的五月的日中,他们不得不去耘田,秋风凉爽的八月中间,他们不得不和自然争斗,趁天气晴快的时候,去割进稻来的那些苦楚,是客观的诗人怎么也梦想不到的。况且天旱了,有旱时的焦急,天雨了有水灾的危惧,这些情感,这些心事,是哪一个诗人,曾经道过?这中间更有催租的官吏,榨取的大农,和威吓欺诈的土豪劣绅,中国的诗人,何曾将这些农民的苦楚申诉出来?”[9]281-282不同于古代那些对农民真实生活作岸上观的“客观的”诗人,创作农民文艺的现代作家是积极主动的,是代民立言的,郁达夫对创作农民文艺的作家在主体性上提出了要求:“第一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要有正确的意识。不问你是否出身于泥土的中间,只教你下笔的时候自觉到自己是在为农民努力,自己是现代社会中一个被虐待的农民。你的脚下,有几千万里的大地在叫冤,你的左右,有数百兆绝食的饥民在待哺。见一点写一点,有一句说一句,把你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不平,完全倾吐出来,最好的农民文艺就马上可以成立了。”[10]285-286联系郁达夫提倡农民文艺的时代语境,他无疑强调作家要具有革命的阶级的感情和思想观念。鲁迅小说《风波》开头所描写的晚饭时候的乡土田园景观,坐船路过的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这真是农家乐,这文豪无疑属于郁达夫批评的古代田园诗人之列。关注农民真实生存状况的现代作家鲁迅显然与此不同。具有现代启蒙思想的鲁迅,其笔下的乡土景观只能是一幅“苍黄”“萧索”的图画。
由郁达夫和鲁迅推衍开来,其实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诞生,也正是乡土作家所具有的不同于乡土传统的现代都市文化观念和视角观照的结果。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论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乡土文学时,把乡土文学与侨寓文学相提并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乡土文学作家虽出生于乡村但当时却寄寓于大都市的生活状态。这一都市生活状态使得这些乡土作家和自己从小就特别熟悉的乡土世界分割开来,得到了从外反观的异质文化视角和观念。在这一都市的也是现代的新文化视角观照下,原来熟悉的乡土世界呈现出一片新“风景”——不仅包括大量的自然地理景观,也包括大量的人文地理景观。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风景画、风俗画描绘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中国现代乡土作家“风景之发现”的结果。
上文论及巴尔扎克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卢梭、夏多布里昂等作家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对风景的大量描写,这是西方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显著区别之一。仅从风景描写多寡的量的角度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似乎区别不大。根本的不同在于作家描写风景时所具有的不同的观念、态度和视角。仍从量的角度说,近年来丁帆、徐兆寿等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已开始大面积消失或者正在死去的看法,在缺乏科学、详尽的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谨慎下这一结论。我们倒是觉得,因为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凸显,以及环境美学和自然美学逐渐成为当代国际美学的主流之一,在此时代语境下,风景、尤其是自然风景,有可能会成为文学创作争相表现的内容。像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美国自然文学流派,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出现的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生态文学作品,都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