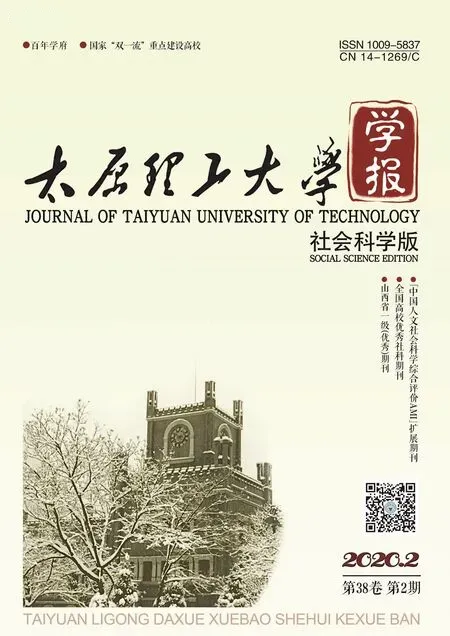“雅”在南宋词论中美学内涵的演变
2020-12-19谷青
谷 青
(西安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雅”是宋代词论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从北宋到南宋,这一美学范畴在继承“雅”已有美学内涵的同时,不断结合时代文化特征与词体自身美学特征对其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与发展,前期已撰有《浅析北宋词论中“雅”的美学内涵》[1]一文,阐释北宋词论中“雅”的美学内涵,本文则对南宋词论中“雅”的美学内涵进行解析。
一、南宋词学中的“复雅”思潮与词学中的“雅正”
南宋初期的词学笼罩在“复雅”思潮之中,论词则言“雅正”,以正统的儒家诗教思想来规范词的发展方向。
陈(上髟下犭異)与詹效之在曹冠的词集序言中以“雅正”论词,认为曹冠的词作是“纯乎雅正者也”,称其“造意正平,措辞典雅,格清而不俗,音乐而不淫,斯为上矣”[2],“感物兴怀,归于雅正,乃圣门之所取”[3]。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雅正”之“雅”包含“造意”“法度”“格”与“乐”四个方面,即词的情思内容、创作手法、美学风格及词乐。
(一)内容之“雅正”
“雅正”之词最重要的便是要有“雅正”的思想内容,那怎样的情思内容才能被称之为“雅正”呢?
南宋时期曾慥编选《乐府雅词》,鮦阳居士编选《复雅歌词》,两者皆以“雅正”为编选标准,在内容上确定“雅”词的范围,明确划定“雅词”的标准。
首先被曾慥排除在“雅”词之外的是“谐谑词”与“艳情词”,其编选词集不仅“涉谐谑则去之”[4],并且把矛头指向了“艳情词”,对艳情题材的否定涉及的词作数量和词人是非常多的。北宋时期词人继承五代花间词风,有着“词为艳科”的词学观,因此创作了大量的“艳情词”,其中不乏德高望重之人,如晏殊、欧阳修等。这正体现出北宋词人对词体本质美学特征的认知,“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如韩魏公、寇莱公、赵忠简,非不冰心铁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词,……皆极有情致,尽态穷妍”[5],有名望之人作极有情致的旖旎之词,在北宋时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南宋“复雅”词学思想的指导下,“艳词”成为与“雅正”绝对对立的题材内容,被认为是淫鄙的“郑声”。因此对于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曾慥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将其删除,言“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鮦阳居士的《复雅歌词》也有着严格的“雅正”标准,对北宋时期受花间词风影响的词作提出批评,“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其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己”[6]。其中“犹祖其遗风”指的便是对温庭筠“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的词风继承,在批判北宋时期以“娱宾遣兴”为创作目的的词作时,还从正面规定了“雅正”词应有的情思内容,那便是“骚雅”。
何为“骚雅”?“骚”本指《离骚》,“雅”指《诗经》中的《大雅》与《小雅》,这些作品被后世文人奉为诗歌中的经典,极受推崇,因此,“骚雅”便用来泛指由《诗经》和《离骚》所奠定的诗文优秀风格和传统。“骚雅”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所指,结合鮦阳居士鲜明的儒家诗教思想来看,其所言“骚雅”应该指的是词中的政治寄托内容,这也是《离骚》与《诗经》共有特征。因此他在解析词意之时便会紧紧围绕“政治寄托”来展开,如汉儒解经,颇多牵强附会。如其在解读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时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盘诗极相似。”[7]这便是他所说的“骚雅之趣”,体现出鮦阳居士“雅正”中的政治内涵。
(二)法度之“雅正”
与儒家的诗教思想相对应,“雅正”之词必然遵循儒家诗学的创作法则,被称为“雅正”的曹冠词在此词法上便体现出儒家诗学对情感委曲蕴藉的表现。詹效之评其词曰:“旨趣纯深,中含法度,使人一唱三叹。盖其得于六义之遗意,纯乎雅正者也。”“旨趣纯深”即言情思表达的深婉含蓄,而他所运用的创作手法便来自于《诗经》中的“六义”, 又言:“感物兴怀,归于雅正,乃圣门之所取”[3]。“六义”之法尤重“感物兴怀”,也就是“比兴”手法的运用,是将所要表达的情感意思通过比兴寄托艺术手法传达,将情感寓于感性的艺术形象之中。以其所作两首咏梅词为例,《汉宫春咏梅》(一品天香)与《水龙吟梅》(自古百卉千葩)这两首作品虽是咏物,却是“感物兴怀”,寄予着词人的政治理想。
词的上片均描写梅花“欺雪凌霜”和“孤标介洁”的“芳姿高洁”,由此起兴,在下片的末句运用“和羹”一典,“君看取,和羹事在,收功不负东皇”,“待芳心结实,和羹鼎鼐,收功须别”,寄托词人的政治理想。“和羹”一词源于《尚书商书说命下》“王曰:‘来!汝说……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8]。春秋时期的晏子对“和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生发,昭公二十年晏婴论“和”时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9]。将饮食中的“和羹”之道用于阐述君臣之道,君臣之间如“和羹”一般和谐相辅,才能成就政治升平,由此,“和羹”便用来指大臣辅佐国君治理国家,实现政治理想和功业。这种政治内涵寄寓在梅花的感性形象之中,深得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之旨。
(三)风格之“雅正”
“雅正”的词风主要表现在对“典雅”之美的追求。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释“典雅”曰:“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10],指的是文学应该符合儒家典籍的美学规范,包括语言风格的平实典重及作品整体风格的平和厚重。
詹效之在评曹冠词之“雅正”时,言其“措辞典雅”,即词作语言摒弃文辞的浮华不实,追求自然质实语言表达。汤衡在《张紫薇雅词序》中说道:“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虽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11]他反对唐末五代词作语言形式上的华丽,追求一种自然素朴的语言美,体现出“雅正”词论者对词作语言的美学规定。
“典雅”之美还体现在词作情感及行文的平和浑厚,这也是儒家经典著作共同的美学风格特征。言曹冠词“旨趣纯深”,言张孝祥词“无一毫浮靡之气”便是其词“典雅”风格的体现。
(四)词乐之“雅正”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从音乐的角度来论述宋词之“雅”。“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宋词之“雅”除了内容情感的雅正,词乐之雅也是宋词“雅”的重要组成部分。何谓乐之“中正”?“凡阴阳之气,有中有正,故音乐有正声,有中声”,“中正之声,正声得正气,中声得中气,则可用。中正用,则平气应,故曰,中正以平之”,“礼别异,乐和同”[12],这里所说的“中正”指的是儒家追求“和雅”的音乐美学观。
鮦阳居士在《复雅歌词序略》中也明确阐述了乐之古今雅郑的区别。“复雅”一词本身就蕴含着崇古非今的儒家思想特征,孟子有言“今之乐犹古之乐”,鮦阳居士对此加以否定,认为今之乐是郑卫之音,无法与古乐相比。“《诗》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词也,其言止乎礼义,圣人删取以为经”,随着古乐的衰微,夷音“天下薰然成俗”,“于是才士始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6]。由此可见,鮦阳居士所复之“雅”是从古之雅乐及《诗经》“止乎礼义”出发,带有儒家伦理教化的色彩。
推崇“复雅”思想的词论家,皆言“雅正”,对词体的内容、情感表达、艺术风格、词乐等各个方面做出了符合儒家诗教美学的规定性,将词体的功能与诗歌的教化功能相等同,强调其社会功能而忽视了词体自身的艺术美学特性,并不利于词体健康发展。但是南宋词学在推崇“复雅”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词体自身艺术特性的探讨,为词学中的“雅”注入了“词性化”的美学内涵。
二、南宋词人对词艺研究的深入与“雅”内涵的“词性”特征
随着对词体美学特征的认识及对词体艺术创作研究的深入,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风雅词派在词学上提出“骚雅”论,使“雅”的内涵呈现出鲜明的“词性”特征,“雅”自传统诗歌美学中引入,在宋代经过不断地丰富发展,最终真正成为具有词性美的词学范畴。
较早在“雅”论中融入词体自身美学特征的是张镃。他在《梅溪词序》中称赞史达祖词时说:“回鞭温韦之涂,掉鞅李杜之域;跻攀风雅,一归于正,不于是而止。”张鎡认为史达祖词的“雅”体现在情感风格与言辞两个方面,就情感风格表现而言,“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不流于訑荡污淫者”,所谓“乐而不淫”,正符合雅正之美。史达祖词作的语言“辞情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贴轻圆”[13],极具清新雅丽之美。张鎡所阐述的“雅”已经深入到词体本身,其美学内涵已经不再仅仅是对诗学中“雅”之美学内涵的继承与照搬,而是在“雅”的内涵中融入了词体自有的美学特征,如“清新闲婉”“妥贴清圆”,他所倡导的“雅”“既立足于‘词性’,又有借于诗,颇见丰富多样”[14]。
詹傅在《笑笑词序》中对“雅”的美学内涵注入了新的内容,他称赞郭应祥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并从“措辞命意”与“下语造句”两个方面具体阐明“典雅纯正”的内涵,“窃窥其措辞命意,若连冈平陇,忽断而后续;其下语造句,若奇葩丽草,自然而敷荣”[15],措辞命意含蓄蕴藉,曲折多变而又意脉不断,语言奇丽而自然,体现出词体婉美的美学特征。
南宋中期以后以姜夔为代表的风雅词派的兴起,“雅”的美学内涵在词学中的“词性”特征更加凸显,词论家往往结合词体自身的美学特征,将“雅”之内涵从音乐、情感内容、艺术表现等多个方面一步步具体化、深入化,终于在南宋末期成就了雅词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词源》。《词源》以“骚雅”“清空”论词,将词学中“雅”的美学内涵具体化、深入化、系统化,完成了一个精彩的总结。
(一)雅正——词乐之美
“雅正”的提出与音乐关系密切,张炎首先从音乐的角度确立了词体“雅”的美学特征,“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使宋词创作合乎音律。也就是说,雅词首先要审音定字,符合声律规范,才能称之为“雅”。张炎又进一步阐述了“雅正”的另一层含义,“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这是从情思抒发的角度来阐述“雅”的内涵。张炎认为诗歌与词在“陶写性情”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在情感表现上却存在不同,“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中情感的表达要含蓄委婉,以此为美学标准,辛派词人直抒胸臆的豪放词作自然排除在雅词之外,“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 因此词中的情感表现应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委婉而避免直露轻率,否则“失其雅正之音”,“淳厚日变成浇风也”[16]。张炎提出的“雅正”源于儒家诗学观,无论是对古音的推崇还是情志的表达,都体现出儒家诗学中“雅”的美学内涵。但是张炎所提到的“雅正”又处处结合着词体自身的美学特征,“雅正”之中包含着对词体音乐性及婉美风格的美学认知,使得“雅”之美学内涵完成了“诗化”与“词化”的结合,在继承中又有创新。
(二)和雅——词法之美
“和雅”是张炎评论清真词时提出的。“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词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16],这里的“和雅”主要是指清真词严密的法度,正如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所言:“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17]。清真词的法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音律谐美,另一个是词句运用均有来处。张炎尤为赞赏周邦彦对“古音”“古调”的再次审定,这当然也是清真词呈现“和雅”之美的重要原因,“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雅词的复兴与古音在词中的重新审定运用有直接的关联,这与王灼所言“中正则雅”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
(三)古雅——词风之美
“古雅”是张炎在阐述“清空”美学风格的时候提出的。“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这里的“雅”有着纯粹的美学意义,指的是清空词有清雅不俗的风格特征。“淡雅”是张炎对秦观词的评价,“体制淡雅,气骨不衰”[16]。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有言:“夫才童学文,宜正体製,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詹锳义证曰:“‘体製’也作‘体制’,包括体裁及其在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也包括风格。”[18]张炎所言“体制”主要指的是秦观词清淡高雅的词风。“古雅”与“淡雅”中的“雅”主要是美学风格层面的内涵,体现出作品超脱凡俗的美学风貌。
(四)骚雅——词体之美
“骚雅”是张炎词论中的核心范畴,是对南宋以来尚雅之风复炽现象最为直接的理论回应[19],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一范畴既体现出词论中“雅”范畴对诗学的继承,更结合了词体独特的美学特征,不仅代表着宋代词论的一个高峰,对后世词论也产生深远的影响。《词源》中有三处提及“骚雅”:
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20]。
陆雪溪瑞鹤仙云……辛稼轩祝英台近云……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20]。
美成词……惜乎意趣却不高远。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20]。
孙兢在《竹坡老人词叙》中有言:“竹坡先生少慕张右使而师之……由是尽得前辈作文关纽,其大者故已掀揭汉唐,凌厉骚雅,烨然名一世矣。”[21]他认为周紫芝的文章“凌厉骚雅”,到达了很高的文学境界。宋代词论中最早明确言及“骚雅”的是鮦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略》,虽然没有对“骚雅”的内涵做出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在宋人的词论中,尤其是南宋词论中,对“骚”的内涵多有论及。早在北宋元祐时期,张耒在《东山词序》中便赞扬贺铸词“幽洁如屈、宋”[22],“幽洁”是“骚”最具代表性的风格特征。南宋初黄大舆编录《梅苑》,其自序云:“于是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23]。“骚”蕴有芳草美人寄托比兴之意。南宋胡寅在《酒边集序》中对“骚辞”的情感表现特征有着较为祥切的论述,“词曲者,古乐曲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流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骚辞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24]。胡寅认为“骚辞”的情感表现以哀怨为基调,并且呈现出不受儒家礼义节制的激切风格。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词论家对“骚”的理解及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其背后蕴藏的自然是由于时代历史背景的转换而引起的文人心态变迁。张炎将“骚”与“雅”结合,又赋予“雅”怎样的具体内涵呢?
1.情感表达委婉蕴藉,别有寄托
从张炎对词作的评析来看,他认为具有骚雅之美的词主要以姜夔为代表,陆雪溪《瑞鹤仙》(脸霞红印枕)与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同样“存骚雅”,究竟这些作品具有怎样的品格使得张炎能够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
在评述陆、辛词“存骚雅”之后,张炎紧接着说,“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20]。这段文字对“骚雅”的内涵做出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其中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词作要有寄托,这与黄大舆在《梅苑》自序中所言“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含义相同;二是情感表达“乐而不淫”,含蓄委婉不激切。与诗歌相比,词更加强调婉美的艺术风格,“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这与胡寅所言“骚辞”怨迫激切的情感表现存在很大差异,究其原因正在于时代变迁对文人心态产生的影响。
被认为是“骚雅”词代表的姜夔的词作,同样符合这一美学特征。以《暗香》《疏影》为例,俞平伯评曰:“二首均咏梅花,蝉联而下,似画家的通景……上首多关个身世,故以何逊自比。下首写家国之恨居多,故引昭君、胡沙、深宫等等为喻”[25]。唐圭璋亦言《暗香》“无句非梅,无意不深,而托寓君国,感怀今昔,尤极婉转回环之妙”,又言《疏影》“寄托亦深……用王建咏梅诗意,抒寄怀二帝之情……用寿阳公主事,以喻昔时太平沉酣之状……皆能曲折传神”[26]。由此可见,就情感思想的表现而言,张炎所倡“雅”之美学内涵即是“在于作品立意不忘天下大事,但在艺术上要出以比兴寄托,继承《离骚》‘芳草美人’的传统,取曲而不取直,取温柔敦厚而不取强烈激切”[14]。张炎词学中的“雅”一方面继承了“诗言志”“乐而不淫”“含蓄蕴藉”的诗歌美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强调词比诗更加婉美的体制品格,强化了“雅”的“词性”特征。
2.章法、句法与字面的精美细密
张炎词学中所倡之“雅”,还强调词法的精密锻炼,章法、句法及字面只有经过反复锻炼修改,才能成就如“无瑕之玉”般的雅词,“倘急于脱稿,倦事修择,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作诗者且犹旬锻句炼,况于词乎”。
作慢词要先立意,而后“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需要承上接下”,“意脉不断”[20]。慢词篇幅较长,其层次转折较为复杂,起承转合的合理运用,才能让词作呈现出自然浑融的整体和谐之美,而无粗疏散乱之病。
句法也是构成雅词的一个重要方面。美成词“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张炎对词中句法提出了具体明确的美学要求,“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读之使人击节可也”[20]。这里的句法,主要指词篇中高妙精警的词句,这些句子似平易自然,却是词人精加锻炼的结果,如姜白石《扬州慢》(淮左名都)中的名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意趣高远,句法挺异,看似平淡的语句却蕴含着词人的笔力。
字面也是张炎极为重视的一点,“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的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20]。词中字面尤为重要,首先字要协律,“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其次字要自然雅致,避免粗疏,“词既成……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20]。与诗歌语言相比,词对语言的要求更加严格细致,语言较诗也更为精致,所以需要词人更多精思的投入。
和第一点相比,词学中“雅”的这一美学内涵所彰显的词体特征更为深入而明确,使“雅”真正成为具有鲜明词性特征的词学审美范畴。
3.清空之美的词风
张炎所倡雅词之“雅”,在风格上则是“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是“雅”在风格层面的又一层美学内涵。何为“清空”?张炎有言:“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这种“体悟”式的论词方式的确让人感受到一种美妙超然的意境,那么如何才能使词作呈现这一美学风格呢?就语言而言要疏不要密,“此词疏快,却不质实”,要合理运用虚字,“用虚字呼唤”,虚实结合,疏密相间,才能让清气流动其中,“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稍宽,庶不窒塞”;就用事而言,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用事“不为事所使”。如姜夔《疏影》词“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娥绿”,前者用杜甫诗意,蕴含的则是词人对二帝北去的痛惜与思念,后者用寿阳公主事,用以表现曾经的承平之世,两者都没有拘泥于典故本身,而是自然恰切地融入了词人自身的情思,别有深意。就咏物而言,同样不能过于拘泥所咏之物,“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总而言之,张炎的“清空”说主要涉及的是有关词作虚实疏密关系的重要美学问题,“清空”说的提出,同样丰富了“雅”的“词性”内涵。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炎的词学理论既立足于词之源(诗歌),同时凸显细化了词体自身的美学特征,既包含了作品的情思美,又包含了词的艺术美与风格美,使“雅”的美学内涵更加丰富、具体、深入,最终完成了词学中“雅”之美学内涵诗化与词化的结合,使词学中的“雅”拥有了与众不同的词性之美。
通过对宋代词学中“雅”范畴内涵的梳理,可以看到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过程。这一发展和变迁与时代审美及词体自身独有的美学特征相关,也是宋代词学中“雅”范畴美学内涵的新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