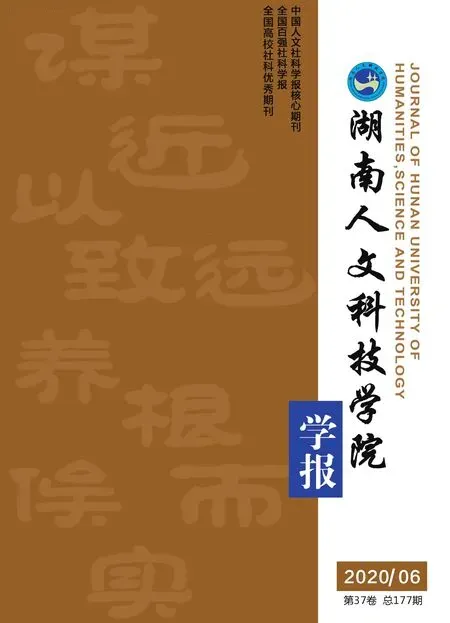由深闺走向社会
——清末民初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
2020-12-19王继平
苏 宇,王继平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19世纪末,内外动荡,民族危机空前,维新人士以强国保种为目的发起了女性“被解放”思潮,主张开民智,倡导男女平等。维新派批判女性缠足,认为缠足让女性失去了自卫和经济独立能力,不利于强国保种,并以此为理论指导发起不缠足运动,使女性迈出了“站起来”的第一步;揭露传统婚姻观中女性地位的不平等、不自由,主张一夫一妻制,鼓励婚恋自由、寡妇再婚,使传统的婚姻观产生动摇,为之后女性反抗家庭,走出家门起到了启蒙作用;深刻地批判把女性拒之门外的传统教育观,发起了创女学的热潮,极力宣扬女性应该同男性一样平等接受教育,女校、女报的普及成为女性“开智”的载体,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更多可能。时代对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男性在危机感下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女人。女性解放新思潮使传统社会思想受到挑战,新的实践活动改变了女性传统的思维模式,人格独立、平等自由等新观念随之到来,观念的改变又引起社会习俗的更新,这些都成为女性主体解放的突破口。传统女性逐渐摆脱自己的物化状态,开始审视自我、走出家门、关注社会,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人”。
一、私人领域从“废缠足”到女性主体审美观的建立
我国古代的女性缠足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审美取向密切相关,以“小”为美的畸形社会审美使男性把小脚视为美色必不可少的因素。小脚成了比脸蛋、身材更为重要的衡量美的标准,因此,缠足成风。对于古代女子来说,缠足就是用后天的人力手段去改变身体的天然状态,从而满足男性审美以获得宠爱,女性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传统陋习的受害者。
19世纪末,维新人士把不缠足作为强国保种的手段之一与国家危亡联系起来。在利国的前提下,他们宣传不缠足思想、积极组织不缠足团体,发起不缠足运动。康有为是维新派最早主张不缠足的人,1883年,他与区谔良在广东创立不缠足会,以不为女儿和侄女缠足标榜新思想,但最终因影响太小,被迫解散;1895年,他与弟康广仁再度成立“粤中不缠足会”,不缠足运动初见成效,使粤风大移[1]43;1897年广东成立不缠足会,入会者几百人,梁启超还作《戒缠足会叙》广为宣传。在不缠足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组织莫过于上海不缠足会,由梁启超、汪康年、谭嗣同发起,在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市成立分会。不缠足会在成立时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 “凡入会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2]。据统计,当时参加上海不缠足总会的会员约达30余万,可见其影响之大。维新派发起的废缠足运动,不仅作为一种改良手段在封建礼教上撕裂了一个突破口,促进社会开化,而且发起者、参与者中多数为男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影响并改变了男性审美。如果天足被接受成为美的标准,那么女性又何必残害自我呢?所以说这场由男性发起、男性参加的不缠足运动,对于女性“脚”命运的改变意义深远,而且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到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不缠足有了地方官员的支持,不少官吏直接出席不缠足会活动。1906年,山西创立山西天足会时,巡抚亲临会场参与;直隶地区官方制定了劝禁缠足章程,规定县城设立禁缠足总会,村设立禁缠足分会[1]45-46。可见,此时的禁缠足不再只是劝导,而是具有官方强制色彩,出现禁罚之势。朝廷的动向变化影响和鼓励着各个地方禁缠足活动的开展,逐渐形成了劝导加禁罚相结合的反缠足新形势。当然这一时期的禁缠足效果仍不是十分明显,不缠足作为新观念和旧习俗相违背,社会对于这一行为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分歧。官宦士绅家眷和女学生多能接受并积极响应,但在普通家庭中女子不缠足、放足仍比较少见。民国时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告各省禁缠足,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大规模的禁缠足运动,妇女放足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高涨起来[1]47。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多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公告,对妇女缠足做了从内容到形式上的详尽说明,各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废缠足工作。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旧传统受到根本性冲击,废缠足在城市里、知识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天足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但在偏远的广大农村,缠足风气到新中国成立才根除。
废缠足这一风潮逐渐构建了“以天足为美”的审美标准。从客观上来讲,这对于女性是莫大的福音,但对于缠足的女子来说,过去的“时尚”变为“落后”,被迫进行放足。而放足同缠足性质一样,都是女性受罪,放足的疼痛丝毫不亚于缠足,对于缠足年头久远者来说,取了裹脚布,脚趾不能伸展,无法走路;为了让四趾伸展,出现了醋泡、水泡等极端手段,严重影响着女性健康。
除此之外,受 “缠足是国耻”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在政府和社会强行要求放足的情况下,一些男子不愿意娶缠足女子为妻,甚至一些公共场所标明严禁缠足女子进入,缠足女子在承受放足的疼痛时,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指责,无疑是身心双重伤害。在广大农村,缠足习俗由来已久,已经完全成为一种乡土意识,是被普遍认可的审美标准,对于一些已经习惯缠足的女子来说,缠足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农村,大多女性自身仍坚决维护小脚。时下社会,新观念已树立,旧观念未清除,有媳妇放足被婆婆视为不详而毒死的,也有因是小脚而嫁不出去的。缠足与不缠足的鼓动者是男性,但承受伤害者均为女性,可见,女性在此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被迫的地位。
以废缠足为开端,标榜“健康美”的女性身体规训到五四前后进一步强化,进步人士多专注于女性健康美的客观宣传。一些女性刊物开始宣扬中国女子的弱不禁风是一种病态美,林黛玉式的女性美是国耻,“真正的‘女性美’是必须建立在健康上面,在一位病弱的女子身上,断不会找出什么美来……真正的健康虽然不是专注于外观之修饰,可是自然会给人一个美的印象”[1]53。对已经成为陋习牺牲品的缠足女子,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相应改善措施,大都市商场上专为隐藏小脚的“假纸套”应运而生[3]11。同时,社会开始把构建强健女性的途径指向女子体育,即女学堂的体操课。一些女学堂开始把体育课纳入学校课程范围,女子体育竞技也随之出现。此时注重运动、讲求卫生、革除束胸等社会行为树立起了健康、时尚、性感的新审美观。社会对于女性外在形态审美观念的变化引起女性自身审美的革新。传统服装为遮盖女性的形体而样式宽大,五四时期,女性服装开始向收身发展,旗袍也因此改良,衣袖变短,修身适体,使女性曲线之美得以展现,这些均反映出时代需要女性美发生改变。
男性把女性从家庭拉到民族的高度进行改造,意味着传统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从“男性需要”逐渐演变为“国家社会需要”。国家需要健康、自然、强健的女性,评判女性美丑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女性对于男性的奴性也在慢慢褪去。在新旧审美观念的碰撞下,女性作为传统的审美客体向审美主体转变,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二、家庭领域从婚恋自由到女性生活范围的扩展
“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夫妻关系伦理之本,体现在婚姻家庭里,便是“男尊女卑”“夫妇有别”的观念。传统婚姻观的“抑女性特征”,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地位卑下,深受压迫。如果丈夫对妻子不满意,还可以送回娘家,自古男子有休妻、再娶的道义,而女子则要终身忠贞于一个丈夫。由节妇、贞女、烈女等价值观发展成的贞节褒扬制度,使女性单方面的贞操观念定型化,它与妇女缠足要求相结合,完成了男权社会对婚姻家庭里女性精神和身体的控制。清末,随着社会的转型,妇女解放思潮逐渐兴起,思想家们开始批判旧式婚恋观,主张婚姻自由,发起“婚姻家庭变革”。
清末民初的婚姻家庭观念变迁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过程。首先,社会思想变革是女性婚恋观变迁的思想基础。从包办婚姻到婚姻自主最先是男性的主张,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把婚姻家庭革命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对包办婚姻作出了大胆的批判。康有为、谭嗣同都深刻地揭露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危害,提倡婚姻自由;严复认为妇女要走出家门、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改革婚姻制度。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人们对传统婚姻制度更加不满,主张“婚姻家庭革命”,传统婚姻观被当做旧风俗,遭到尖锐的批判。1900年,蔡元培的原配妻子逝世后,他提出“女方须天足、须识字;男方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男女意见不合可以离婚”[3]232等五个条件作为择偶标准。此时男性对婚姻的新要求使男女的婚姻家庭地位逐渐平等,婚姻当事人越来越在意对方的个人素质,不再只讲求财产多寡、门当户对。婚姻里夫妻身份逐渐平等,婚姻家庭中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思想也逐渐被夫妻平等思想代替。
其次,男性婚恋观的变迁引起了婚姻生活的改变,女性婚恋观也因此发生变化。在男子发起“婚姻家庭革命”时,一些女性知识分子开始将婚姻自由付诸实践,秋瑾与包办婚姻的丈夫离婚,走上革命;何香凝与革命中认识、相恋的廖仲恺结婚。女性知识分子也开始主动反对传统婚姻,冰心、张爱玲等女性作家,以婚姻、家庭、爱情等为题材,提倡男女平等,婚恋自由。可见,大量进步女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也成为呼吁女性婚恋自由的主力军。女学的兴起和女权运动的发展是女性婚恋观念变化的外在条件,女性在学习知识文化之余,逐渐增加了社会活动,接触到新思想,产生了新的观念,对于婚恋提出了新要求。五四运动后,未婚适龄的知识女青年对自己的婚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也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了理想的设计。在《女子世界》《妇女杂志》等刊物里已经出现了女性公开征婚的信息,虽然比较少见,但足以看出此时的婚姻媒介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初,出现了注重配偶才学品德、追求情投意合的爱情观。
秋瑾提倡与学堂的知己结婚,因为互相能够了解彼此的品性才识,且有共同的性情志趣。向警予在1918年被许配给湘西镇守司令,家人极力希望她做将军夫人,但她只身闯入周公馆表示毕生不嫁,以身许国,拒绝了这段姻缘,后在参与革命活动中,与蔡和森志趣相投,自由恋爱组成“向蔡同盟”,被传为佳话。从男性发起婚姻变革到女性主动提出恋爱自由、男女社交、离婚自由等新婚恋主张,反映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婚姻观念的改变使女性不再被束缚于家庭之内,“走出家门”成为女性的下一步追求。传统婚姻家庭里,男女各有自己扮演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内”观念把女性的活动范围缩小为家庭一隅。同时,“女正家正”思想,使婚后女性的行为举止成为衡量一个妻子是否合格的标尺,但对丈夫言行却没有任何要求。在传统婚姻家庭里,女性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传宗接代的机器,毫无社会价值可言。近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婚姻家庭观的变革,女性逐渐地走出家门,拥有了社会角色。
首先,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女性走出家门的先决条件。19世纪末,维新人士对女性就业提出了要求,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提倡女性就业、经济自立,以此减轻社会的负担[4];20世纪初,进步人士认为女性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和报效祖国的重要条件,金一在《女界钟》中把营业作为当时女性最应获得的权利;秋瑾指出女性经济自立可以补贴家用、兴隆家业,也可以提高在女性的社会家庭地位,她还提出女性要自立必须学习手艺,适应群体生活[1]149-150。
其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女性走出家门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使家庭手工业破产,城乡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市场。19世纪末,女工开始出现在缫丝厂、纺织厂,20世纪初,全国女工数量已达至工人总数的1/3,大多数都聚集于纺织、饮食、生活用品等轻工业产业[1]149-150。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当女佣,尤其在沪附近的乡间最为流行,因此出现了女佣介绍所等新兴中介机构。女工和女佣是当时贫苦农村女性所能接触到的职业,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知识分子从事教师、医护、编辑等工作。走出家门参加就业的女性扩大了社会生活空间,拥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支配力。
当然,女性进入社会生活之后,仍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走出家门之后,女性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增强,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现象逐渐增加,但社会还没有产生支持女性离婚的机制。法律制度在夫妻离异上依然偏向男性,如果男性不同意,女性单方面很难做到离婚;在子女的归属上,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仍依然更多偏向男方。同时,受社会观念影响,女子离异后,在社会上很难立足,有些无能力的女子只能寄居。走出家门之后,女性开始拥有了社会角色,参与就业的职业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丈夫和家庭的依赖。社会价值的提升使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也因此产生了家庭与职业的矛盾,在当今社会,这仍是多数女性不可避免的问题。
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拓展了自身的活动范围,在认识新天地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其他生存技能,不再寄生于家庭和男性。同时,女性逐渐站在社会的角度审视自我、发现自我,正视自身的价值,意识到“女人”不能仅仅只是美色和繁殖的代名词,不能只甘于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可以说,女性逐渐实现了“从自主经济向自主人格的转变”[5],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社会,组织妇女团体,出版刊物,争取更多的妇女权利,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更为深入和广泛。
三、公共领域从“女学生”到女性国民观的建立
随着女学的创办,女性获得了第一个被大众认可的社会角色——女学生。以学生的角色进行“被改造”的同时,女性开始通过参加社会生产甚至是政治活动,审视男性赋予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可以说,近代女性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女性从物化到主体化的解放,促使着女性意识的觉醒。
维新派女学理论的传播、西方教育思想及教会女校的影响,使中国人自创女校的出现成为必然。1898年,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学堂在上海成立,经元善为主事,刘坤一、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名士出面相助。办校初,招收女学生有20余人,第二年招收学生达70余人,后还设立了分校[1]64-65。女学堂虽由男性创办,但在其办学章程中明确表示,校内所有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均由女性承担。同时,经元善还邀请西方女性参与教学,这不仅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发展女学的捷径,而且中西女性有机会一起交流本身也有利于中国女性开阔眼界。学堂的教学内容分为中西文两种,并且在学习《唐诗》《古文》等文化知识的同时,杂以医学、女红等实践课程[1]64-65。经正女学堂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新教育性质,虽然因为政治缘故只开办了两年,但它创办女学之风对社会转型和女性觉醒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
到清末新政时,女学开始被正视,清廷确立了两性双规教育制度,1907年颁布的《学部奏定女学章程》使官办女学系统化,标志着我国女性第一次正式获得了享受学校教育的合法权益。此时的女学只有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虽不能在规模和水平上与传统学校相比,但开设的课程涵盖生活技能、科学技术、女性修养等各个方面,讲求德、智、体全面发展。民国初,临时政府进行了教育改革,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小男女合校、设立女子中学与职业学校等,是男女同校的开始,民国时期女校与女学生数量因此逐年增加。五四新文化时期女学得到新的发展,社会上关于男女教育平等的呼声愈来愈高。胡适等思想家、教育家在报刊上呼吁大学向女性开放,上海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开展了关于女性进高校的辩论。1920年春,北京大学收录了9名女性作为文科旁听生,首开解除大学女禁先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74。五四时期开展的“男女同校”讨论与实践,改变了传统的“男女有别”封建戒律,实现了一次男女人格平等的思想变革,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女性在传统礼教压制下的内心自卑感。
我国女性留学兴起于传教士携女童出国,后在国内推崇女学之时,自办女校女教员资源的缺乏使政府开始鼓励女子留学。1910年,清政府学部宣布女性自费留学生也可以享受官费补给,促进了女子留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国人出国经商游历携带其妻女产生的伴读留学与女子自费留学居多。日本是最早出现女子自费留学的国家,早期留日女学生大多生于名门并且有的在国内已经接受过教育;庚子赔款后,赴美留学形成高潮,其中女性最多时已达总人数的25.6%[3]52-55。之后兴起出国勤工俭学运动,留学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俄国等,造就了很多女性人才。这些女性回国后把女性解放深入到政治领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先进女性在学到知识之后,由深闺走向世界,不仅使自身文化素养提升,在社会上有一席立身之地,而且成为女性解放的先驱,带动群体女性意识的觉醒。女学生因此逐渐转变为肩负救国与要求参政的女“国民”。由于社会背景的特殊性,女性解放无法与民族解放分开,女学生了解了自身社会价值之后,毫不犹豫地以女国民身份肩负起了革命任务,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把女性解放与革命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女性的政治参与是妇女解放的高级形式。我国女性参加革命活动兴起于辛亥革命前后,何凝香早年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第一名女性成员;东渡留学的秋瑾在日本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回国后投身于革命并因此牺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去除了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革命胜利后,女性先驱对“共和”抱有极大希望,积极组织女性参政团体,宣传妇女参政思想。1911年,林宗素等女同盟会员成立的“女子参政同志会”是当时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女子参政团体,该会多次通过上书请愿的方式力争参政权[6]20。1912年,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并没有给女性参政以机会,引起女届动荡,各省女子参政团体纷纷成立,全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女子参政运动。1913年,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各省的女子参政团体被强制解散,第一次女性参政运动高潮随之消退。五四民主爱国运动时期,女性参政运动再次兴起,各地“女界联合会”、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等女性革命团体再次纷纷成立。其中各地“女界联合会”作为民间组织,抓住了1920年的“省自治”与“联省自治”契机,使部分地区女性在地方上取得了一定的参政权[7]。女性参加革命活动和女性争取参政议政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最高表现形式,从“女学生”到“女国民”,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结语
清末时局动荡,在内忧外患情况下,男性基于富国强民立场倡女权,女性作为社会的一大群体逐渐走上了“被解放”之路,开创了女性解放的历史新局面。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需求发生转变,引起女性在私密领域、家庭领域、公共领域的一系列社会生活逐渐发生变化。不缠足、禁缠足运动使女性从缠足的痛苦中解脱,迈出“站起来”的关键一步;家庭婚姻观的变革使女性走出家庭的禁锢,逐渐拥有社会价值;女学的兴起和发展使女性能够站在国民角度把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结合起来,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从这一解放历程来看,近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由被动转入主动、由外化于行转至内化于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