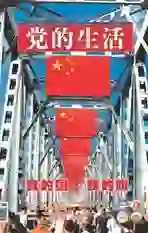雪冷血热·第23章 下江劲旅
2020-12-18张正隆
张正隆
第23章 下江劲旅
七军的三任军长
七军第一任军长是陈荣久。
陈荣久,曾化名王福东、刘长发,1904年生于宁安县东京城三家子村的一个雇农之家,念过两年书。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东北军二十一混成旅骑兵二营七连当兵。
日军侵入吉东地区后,连长要投降。这怎么行?陈荣久和几个弟兄一商量,去连部将连长缴了械,然后宣布抗日,他也随即被大家推举为连长。王德林举义后,陈荣久率连加入救国军,在穆棱、海林、宁安等地作战。救国军失败后,他又投奔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任军部副官,随军转战宁安、密山一带。
1934年春,李延禄进关期间,陈荣久负责四军的政治工作。同年7月,党组织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陈荣久回国,到饶河组建七军,任军长兼一师师长。
1937年3月6日,陈荣久率150多人到饶河西北部的天津班,准备召集几支山林队的首领开会。军部秘书罗英原是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被捕后叛变,又混入七军,“自告奋勇”去给山林队送信。伪县公署参事官大穗久雄接到密报后,即带300多名日伪军,乘马拉爬犁赶往天津班。
下午1点左右,战斗在屏岭山打响。
陈荣久将部队部署在三个山头上。山不高,也不陡,只是东荒3月的积雪依然很厚。伪军不肯玩命,稍有伤亡就趴下不动。鬼子抓着树枝子往上爬,雪没膝深,上面有一层冰样的雪壳子,踏碎了再拔脚就格外吃力。樹枝断了或是没抓住,那人就顺着冰壳子滑下去了,即便被树干拦住,也得哼唧一阵子才能爬起来。
陈荣久肩部负伤,仍继续指挥战斗,并亲自掌握机枪班,全力阻击威胁最大的敌人。
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鬼子的伤亡很大——在这种地势攻山头,是很难得手的,除非用炮弹把山头犁个遍。而在大穗久雄也成了枪下鬼之后,敌人的进攻就停止了。就在这时,伪警察大队大队长苑福堂带着200多名伪军,从屏岭山背后攻上来了。
苑福堂是饶河县出了名的铁杆汉奸。这个败类原来盘踞在暴马顶子,被游击队一顿胖揍之后,他的老巢也成了游击队、七军的根据地。为了讨日本主子的欢心,这小子在“讨伐”中更加卖力,也颇能收罗一些“有奶便是娘”的亡命徒。
眼见腹背受敌,陈荣久在指挥部队顽强阻击到天黑后,下令突围。他亲自带人断后,不幸中弹牺牲。
陈荣久牺牲后,由参谋长崔石泉代理军长。同年年底,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二师师长李学福被选举为军长。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朝鲜族,1901年生于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1915年迁居饶河县大佳河,后来又搬到三义屯,读过几年书后,辍学务农。
李学福性格豪爽、沉稳,乐于助人,处事公道,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被推选当了屯长。他曾从饶河电报局局长那里要来大别拉坑的一百多垧荒地,自己只留四垧,其余的都分给穷人,不收租税。
单立志老人说,李学福大高个,挺壮实,圆脸盘,和和气气的一个人。可见到朝鲜族人自顾自在一块唠得热闹,就黑下脸来批评,说中朝同志要团结一心打日本子,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扎堆儿,不是没隔阂也有隔阂了吗?越是唠不到一块去,越要往一块唠,这样才能相互信任。
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觉得没意思,有的就干脆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常把“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作“撤退”。如果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就完了,可要是打了败仗,就可能引起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一直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如果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还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四旅十二团将饶河县反日会会长李学福等十几名反日会成员逮捕。押往城外枪毙的途中,李学福瞅准机会,一头将一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见此情形,反日会成员有的钻进林子,有的跳到河里,有的被乱枪打死,有的负伤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一个池塘边跳了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总算躲过一劫得以脱身。
李学福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打了大大小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遗憾的是,他正值壮年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被送到苏联治疗,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在李学福因病半身不遂后,七军仍由崔石泉代理军长。后来经过选举,三师师长景乐亭担任七军第三任军长。
景乐亭,山东章丘人,1903年出生,何种家境,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信息均不详。在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后,为一旅一营营长。
入伍就在三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果敢、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三师、七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单立志老人说。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报刊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七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内部问题”
1936年春,崔石泉和四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也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但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就往腰包里揣。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后,他把三连连长邴升臣抓了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七军中高层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照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李杜的自卫军,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1936年任四军二师师长。二师改编为七军后,因陈荣久当了军长,郑鲁岩即消极怠工。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去海参崴交通局汇报工作时,指定郑鲁岩代理特委书记。于是,郑鲁岩派军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队做统战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头弟兄,只向他汇报工作。1937年2月,郑鲁岩到虎林收编山林队,临行前在军部讲话,说他要成立个十一军,跟七军竞赛。
原二师五团团长邹其昌到虎头另立山头,成立“暂编一师”,反对七军。原二师七团团长贾瑞福则发表声明当胡子,全团只剩下五个人。
内部问题如此复杂,外部环境自然恶化。原来团结在七军周围的一些山林队,有的不听调动,有的带队离去。叛徒罗英与混入七军的奸细,乘机大肆活动。天津班战斗后,罗英干脆准备夺权。
让陈荣久当军长,应该不无对这种内部纷争的考虑。陈荣久在苏联学习两年回来,跟这些人没什么瓜葛、矛盾,但与此同时,不利因素也相当明显——不熟悉情况,独木难支,也就困难多多。虽然枪毙了几个奸细,并不能挽回局面。
1937年2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给××同志的信》中说:“我们抗日联军处在极端孤立和危险的状态。我们认为:最近没得到我们上级机关的极力帮助的话,那么,下江一带的革命军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从游击队到抗联,各军无不受到“北方会议”“1·26”指示信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路线、方针、政策变化的影响,各自经历的坎坷、磨难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饶河游击队这样,开头几乎清一色朝鲜(族)人的队伍,由于地域、领导人的差异,也各不相同。而由四军二师改编的七军,与四军的差异就更大了,也同样到了不整顿不行的时候。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宝清县大叶子沟密营整顿完四军,月底又以吉东特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饶河县十八垧地,召开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着手整顿七军。
会议开了五天,通过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改选下江特委,改选了七军党委执委,并改选了七军领导。由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兼代理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调换了一批师团干部。
四军整顿相当成功,七军则不然。因为四军的问题比较单纯,七军这个偏居饶河一隅的“闺秀”,原本就鲜为人知,问题也就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帮派体系仍然存在,而这种体系原本就是难以消除的,除非在军与军之间进行干部调换。而且郑鲁岩当了政治部主任,会议决议又取消了军事干部的专权,无形中增大了他的权限,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东省委三人团对抗联七军党特委的工作检查》中说:“目前成为七军最大障碍者,厥为干部中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同志仍保存着个人之成见,骄纵、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发生联系,互相猜疑、嫉恨,以怨报怨,脱离组织原则,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应一律肃清之!”
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为七军经济部部长、二路军总部交通站虎饶站主任的徐凤山,在内部斗争中被抓起来,罪名是“民生团”。
单立志老人说,徐凤山是1939年6月被郑鲁岩下令杀害的。因不愿领命而被严厉批评的战士,是流着眼泪执行命令的,回来后大哭一场。
与东满、汤原不同的是,七军并未掀起大规模的反“民生团”运动,而且被杀害的还有汉族人,比如景乐亭、毕玉民、王贵祥等。这叫“内部处理”。
毕玉民,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中学毕业,1931年在虎林县吉祥镇入党,先后任虎林区委委员、县委委员、七军副官长、虎林办事处主任和补充团政委,1938年9月被郑鲁岩下令杀害,罪名是“与七军对立和不服从领导搞分裂”。
离休前为辽宁省盖州市农业机械厂党委副书记的王云庆老人,除了抗战时期打鬼子,这辈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机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拖拉机操作、维修人员,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头发斑白,满脸皱纹,朴实、文雅。我去采访他时,他用放大镜看完我的部队文职干部证,说:“你想了解抗联的事吧?找我采访的人,没别的事。”
王云庆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还不记事时一家人闯关东,来到虎林县义和乡同和村。1935年参加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8年初给毕玉民当警卫员。
老人说,毕玉民大高个,文化挺高,还会武术,一人来高的墙,他跑几步,一按墙头就过去了。这人性情爽快,有主意,还和气,能逗乐,我给他当半年警卫员,没有愁的时候。现在都叫“警卫员”,那时叫“传令兵”“勤务兵”,还有叫“护兵”的。他走到哪儿我跟着,倒是他经常护着我、伺候我。那年我还不到十五岁,长得也小,我俩在一起跟爷儿俩似的。
第一次跟敵人交手,是抓两个朝鲜族特务。那时朝鲜族人两极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当走狗。那时日本人对铁路看得紧,南满那边我不知道,北满这边的火车司机几乎都是朝鲜族,信得过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过来两个人,他一递眼色,我就知道有情况。我俩各有一支撸子,揣在兜里,他还有支左轮,因为撞针坏了,就背在屁股上拍打着。走到跟前,特务一下子掏出枪对准我们,然后伸手去摘那支左轮。我还没反应过来,“铛”的一枪,一个特务倒了,另一个特务的枪也到了毕玉民手里。特务拿支左轮扣不响,毕玉民说“那个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东腔不紧不慢,脸上还笑吟吟的。
他外出带我的时候不多,“过苏联”都是独往独来——那时管过界去苏联叫“过苏联”。他去一趟个把月,背个帆布兜子,通常背些药回来,伤员多呀。有一次不知去哪儿了,背回大半兜子钱,现在寻思怎么也有上万元。
那时我们管伪军叫“满军”。虎林县“满军”、警察、自卫团,少说有几千人,头头脑脑的,毕玉民少有不熟的。游击队、人民军时期和抗联初期,战场上能跟“满军”做生意,他们卖给你子弹。后来就不行了,作战消耗多少弹药,战后鬼子让上交弹壳。归大屯后,形势恶化,“满军”也随风倒。可毕玉民在虎林县的“满军”中照样吃得开。部队缺什么,他写个条,去人就取。听说他当过警察,是入了“在家礼”的,和一些人磕过头,神通广大。他被“内部处理”两三个月了,写个条、盖上他的戳,还好使。后来人家知道了,这些关系就断了。
后来,让我给团长×××(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当警卫员。给团长擦枪时,我觉得不对劲——这不是毕玉民的枪吗?再一想,一个多月没见到这人了。因为不敢问,就留心听。那时大伙儿都把我当小孩,有一些话也不背着我。毕玉民是在去军部的路上被打死的,从背后开的枪,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个王副官。听说本来没他什么事,可他在现场,怕传出去,就顺便“处理”了。
补充团有个“中央队”,头子姓刘,是×××(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打死的。还有个“得胜队”,头子姓李,四十多岁,杀毕玉民也有他的份。后来听说也被“处理”了。
“刘中央”等人都有股匪气,野蛮,骂人。毕玉民没一句粗话,遇事讲道理,那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这个人也有毛病,性子倔,有时抗上。听说“刘中央”等人打日本也挺厉害,但是到了困难时期,这种人就容易动摇、叛变。可毕玉民怎么可能呀?后来又听说是因为他搞分裂、闹独立。真要是这样,不说别的,他还能把那么多钱给抗联花吗?
八团团长王贵祥,也是山林队出身,报号“君子人”。这人困难时期也跟着咱们,也被“内部处理”了。他的女儿王铁环,和我同年参军,那年只有七岁。开头都在土顶子密营种地做饭做衣服,我寻思,她应该是抗联最小的女兵了。1954年我在沈阳当拖拉机站站长,见到她,问她知不知道父亲怎么死的,她说不知道。
1956年,在北京见到×××(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我說,我那时是个战士,不知道上边怎么弄的,你什么都清楚,毕玉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总得有个结论呀?咱们这茬人要是没了,就再也弄不明白了。需要我打证明,我现在就打。他叹口气,说:“过去了,拉倒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