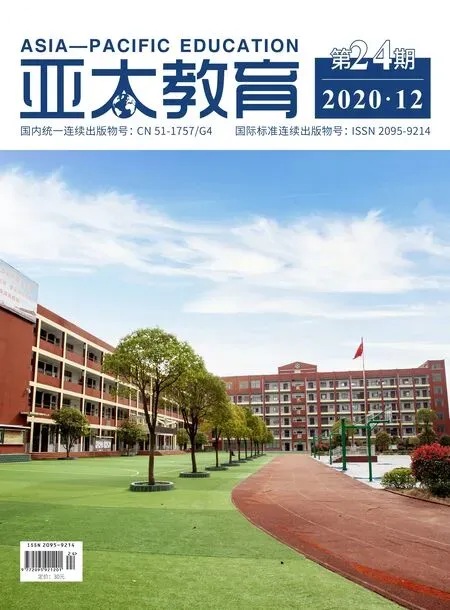认知—符号理论:引领第二语言教学界“认知革命”的先锋
2020-12-18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朱勘宇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朱勘宇
认知—符号理论(Cognitive code theory/Approach),我国也有著作翻译为认知—符号法或认知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卡鲁尔(J. B. Carroll)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提出的外语/第二语言教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包含了学习者的大量心理过程,其强调学习者在学习和运用语言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是,该理论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教学法体系,这与它的提出者是心理学家不无关系,也因此,它被一些介绍第二语言教学法的著作所忽视。但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第二语言教学界处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衰落、认知心理学兴起的历史转折期时,认知—符号理论率先将认知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第二语言教学,从而引领了第二语言教学界的“认知革命”,为第二代应用语言学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我们撰写此文,一是为当今第二语言教学的认知潮流溯源,二是以期引起学界对它的更大关注。此外,笔者还对以往文献中关于认知—符号理论的一些论述发表了不同看法。
一、认知—符号理论产生的背景
(一)心理学界
20 世纪50 年代的心理学界,已经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开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它基本不涉及人类的内部心理过程研究。这场批评的结果便是,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内部心理过程,即感觉、知觉、注意、意识、记忆、心理表象、思维、语言学习与使用等愈发关注,这一切心理活动被心理学家定义为“认知”。
(二)语言学界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大潮下,人类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获得被看作是受到外界刺激后所做出的反应。对此,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针锋相对地提出:人类使用语言是创造性地运用抽象规则产出新语句的行为;儿童对母语的获得是大脑中语言习得机制被激活的结果,而这套机制是人类通过遗传所获得的。受乔姆斯基语言使用观和语言获得观的影响,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开始关注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时的内部心理过程。
(三)第二语言教学界
20 世纪上半期,第二语言教学界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潮流下,盛行的教学法是“听说法”。到了20 世纪60 年代,随着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理论潮流的变化,听说法开始遭到批评。在理论层面,作为听说法之理论基石的行为主义语言学习观面临严重质疑;在实践层面,人们又发现,听说法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于是,此时的第二语言教学界陷入了危机,听说法遭到严重质疑,而与此同时能替代它,像听说法那样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完整教学程序的教学法却还未出现。
就在此时,对外语教学一直颇感兴趣的美国心理学家卡鲁尔指出:“听说法已经跟不上最近的发展,需要结合认知—符号理论的一些元素进行改进。”
二、认知—符号理论的理论基础
认知—符号理论具有强大的心理学基础,即认知心理学,以及教学论基础,即发现学习与教学理论。此外,它的语言学习观还受到乔姆斯基语言行为观的影响。
(一)心理学基础——认知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在获取、理解知识和信息的过程中是一个主动角色。基于此理论,认知—符号理论认为,成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是主动思考的,学习者会积极地运用概括、推理、总结等一系列方法主动地获取和理解知识。认知心理学关于人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人们学习新知识、获取新信息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以及该学科对人类思维所做的研究,对认知—符号理论教学原则的提出都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二)教学论基础——发现学习与教学理论
发现学习与教学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于1960 提出的,是以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学习与教学理论,它是认知—符号理论采用引导式发现教学法的直接指导思想。
认知主义教育观认为,教学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还在于使学生的思考能力等智能得到发展。依据布鲁纳提出的人类思维“假设—验证模型”,人们的思考过程是“假设—验证—改进”的过程。基于此,布鲁纳提出,教学要引导学生自己探求知识,而不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这样既顺应学生的学习认知过程,同时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发展,这便是发现学习与教学理论。
(三)乔姆斯基的语言行为观
受乔姆斯基“人类使用语言是创造性地运用抽象规则产出新语句的行为”这一观点的影响,认知—符号理论注重成人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的思考与创造能力,并主张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动角色。
“作文难,难文”这是小学语文教师的深切体会。老师教的筋疲力尽,学生写的痛不欲生,这是小学作文教学的常态。要想孩子们对作文产生浓厚的兴趣,消除畏难心理。新课标中所指出的“中年级学生要留心周围事物,乐于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三年级学生作文的起步阶段,教师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比对作文方法的教学更重要。如何培养学生对作文的热情,带领孩子们开启作文的兴趣之门呢?
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认知—符号理论的语言学基础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转换生成语法所基于的语言行为哲学观,即乔姆斯基的语言行为观对认知—符号理论的语言学习观有所影响,但是在操作层面,转换生成语法的具体规则并没有应用于认知—符号理论。转换生成语法是乔姆斯基为了解释儿童强大的语言获得能力而提出的假设,其并不是用来进行语言教学的,这一点乔姆斯基本人从一开始也旗帜鲜明地予以了表示。
三、认知—符号理论的教学原则
认知—符号理论从学习者认知角度出发所提出的教学原则,从日后的第二语言教学发展来看,在当时扮演了率先将认知心理学理论引入第二语言教学的“领头羊”角色。其中的一些教学原则,如引导式发现教学、宽容对待学生错误等,对后来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发展学生的认知— —引导式发现教学法
基于认知主义的学习观,认知—符号理论秉承的教学原则是:在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认知能力的存在,教学过程和方法符合学生的认知过程,积极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并以此达到发展学生认知能力的效果。
在布鲁纳“发现学习与教学理论”和人类思维“假设—验证模型论”的基础上,认知—符号理论采用引导式发现教学,由教师引导学生自行推导出语法规则。该理论特别指出,教师引导时要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出发,先复习学生已学的相关语法知识,然后通过展示一些句子,引导学生发现未学过的新语法规则。这个从已知到未知的引导过程,其理论基础来源于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是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学习新知识、处理新信息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把新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地建构其知识体系。
今天,从已知到未知的教学安排已普遍为第二语言教学界所接受,一个最常见的体现便是课堂教学的第一环节常常设置“热身”“导入”,其目的是激活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
(二)有意义的学习
由于认知—符号理论充分意识到并尊重学习者理解、推理、概括等思考能力的存在,并且旨在发展这些能力,所以它主张在理解基础上的学习,即有意义的学习。它摒弃听说法的机械性操练,主张对语言项目理解后进行练习,即有意义的练习。
章兼中认为,认知—符号理论的教学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教师通过引导式发现法教授并使学生理解语言规则。第二阶段,学生对语法规则和其他语言项目作理解性练习,练习形式有选择、判断正误、组句、扩展句子等。第三阶段,学生进行脱离课文的交际性练习,练习形式有对话、角色扮演、讨论、作文等。
(三)宽容对待学生的错误
认知—符号理论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错误属正常现象,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错误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即错误甚而可以看作是“学习”存在的标志。根据布鲁纳提出的人类思维“假设—验证模型”,人类的思考过程是“假设—验证—改进”,那么在此过程中,“错误”作为假设的结果,其出现不仅是合理现象,而且确实表明认识主体的思考正在进行中。
认知—符号理论视培养学生“假设—验证—改进”的思考方法为其教学目的之一。既然如此,那么当教师发现学生的错误后,如果立即纠正就等于中断了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学生无法继续后面的“验证”与“改进”了。这样既不符合学习的认知过程,又达不到培养目的,同时还会挫败学生的思考与学习积极性。因此,该理论主张教师对学生的错误进行启发式引导,为学生进入“验证—改进”步骤指引方向,而不是采取听说法的有错必纠。
认知—符号理论处理学生错误的方式在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来的教学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有错必纠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学生的错误予以有条件的宽容,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纠正已成为大多数第二语言教学法所采用的方式。
(四)适当使用学生的母语
认知—符号理论主张教学中适当使用学生母语,尤其是在解释语言现象时。提出这一主张的依据是: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学习新知识、理解新信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认知—符号理论由此认为,作为具有成熟思考能力的成年人,其关于母语的语言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对第二语言的理解,这一点对后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迁移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听说读写同步进行
认知—符号理论主张对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同步进行,反对听说法的听说领先,因为该理论认为:对成年人来说,学习外语最好的途径是多种感觉器官综合运用,单纯靠声音学习外语是不符合成年人学习外语的心理特点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该理论提出四种技能同时培养的出发点是成年人学习的认知特点,而不是今天我们通常会首先想到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第一语言等因素。这就再次证明了心理学理论在认知—符号理论中的强势地位。
四、认知—符号理论的历史意义与地位
(一)缓解20 世纪中期第二语言教学界危机
20 世纪中期,当听说法遭到严重质疑,同时像它一样系统的教学法还未出现时,认知—符号理论的提出暂时缓解了这场第二语言教学界的危机。该理论之所以能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是因为它摒弃了听说法最受批评的两大特点,即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和无意义的机械性操练,它所基于的心理学基础正是与行为主义心理学针锋相对的认知心理学。这番对危机的缓解之所以只是暂时的,是因为认知—符号理论最终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第二语言教学法。根据Richards and Rodgers,一个系统的第二语言教学法需要有理论基础(语言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教学设计(包括教学法目标、课程大纲模板、教学活动设计、学生角色说明、教师角色说明等)和教学程序(包括课堂教学步骤、技巧、策略等)三大块。而这些要素中,认知—符号理论只具备强大的心理学理论基础。20 世纪中期的这场第二语言教学界的危机,一直到70年代后期交际法兴起才算得到彻底解决。
(二)引领第二语言教学界的“认知革命”
虽然认知—符号理论没有在实践层面提出系统而具体的课堂教学设计和教学程序,但是它对第二语言教学所做出的理论层面的贡献与思想指导在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新时代的意义。
20 世纪中期以后,语言教学的研究关注点从教师转向学生,这是应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学者将转向之后的发展阶段称为“第二代应用语言学”。而在当时“转向”的当口,也就是第二语言教学界处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衰落、认知心理学兴起的历史转折期,是认知—符号理论率先将认知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第二语言教学。它引领了第二语言教学界的“认知革命”,其提出的引导性发现教学和处理学生错误的方式等教学原则,对日后的第二语言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促进认知科学的发展
认知—符号理论将认知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第二语言教学,也反过来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同时,第二语言教学所属的语言学又是认知科学中的核心学科,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认知—符号理论推动了人类认知科学的发展。
本文为当今第二语言教学研究与实践的认知潮流进行了溯源,阐述了率先以认知心理学作为理论基础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认知—符号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基础、教学原则及其在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等。基于本文所阐述的认知—符号理论的三大意义与贡献,我们期望引起学界对该理论的更大关注,虽然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第二语言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