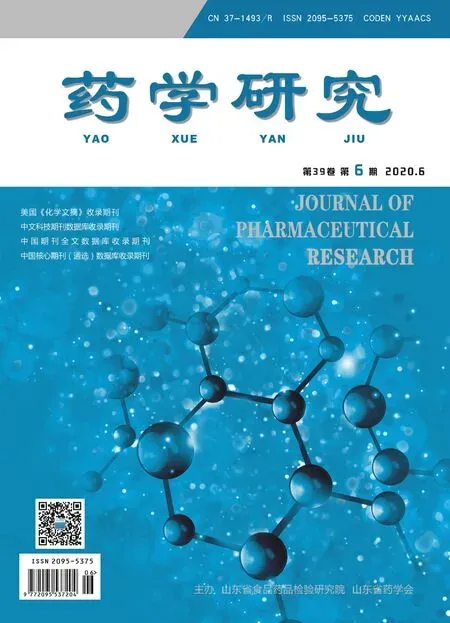藏药浴五味甘露的研究进展
2020-12-17王常悦卢燕
王常悦,卢燕
(复旦大学药学院,上海 201203)
藏医药是中国医药领域的一颗明珠,它是藏民族同胞在总结了三千多年来长期医药实践的基本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又将汉族的中医药学以及天竺、大食的医学药学理论加以吸收融合所形成的独特的医药体系[1]。青藏高原是传统藏药的主产地之一,其复杂的地理和生态环境造就了那里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也赋予了藏药独特的疗效和药用价值。
五味甘露是藏民族的医疗方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剂,也是藏药浴应用的基本处方,其对于配伍药物和疾病治疗的极大包容性奠定了其在藏药中无法撼动的地位,在藏民族甚至附近其他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的应用非常广泛。五味甘露的主方是“杜鹃、圆柏、水柏枝、藏麻黄、青蒿”,由于疾病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五味甘露药浴在使用时往往是根据病症增加一些配伍使用的药物。确定复方后按照一定的制作工艺进行配制后即可使用。
《四部医典》对五味甘露的评价极高,认为其可医所有在藏医理论中认为因“隆”失衡引起的疾病,而现代药理研究也证明五味甘露具有极为丰富的药理活性,也预示着针对五味甘露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 主方药材[2]
五味甘露方是由宇妥宁玛·允丹贡布于公元8 世纪最早记载于藏医经典《四部医典》中,但其具体成分并没有列于书中,《四部医典》初刻版中亦仅仅译出“五味甘露”和“五甘露”这个复方名。然而在马世林译本中,在初刻版中“五甘露”对应的位置则直接出现了“药用青蒿、杜鹃花、藏麻黄、圆柏枝、水柏枝”这样的译文。后来在《四部医典》的注释本《祖先言教》和《医学四续注释·蓝琉璃》中都分别给出了一样的五味甘露的组成成分:杜鹃、圆柏、藏麻黄、水柏枝和青蒿。
1.1 杜鹃 藏药名为“达里”,现知的藏医应用过的杜鹃超过20 种,在藏医理论中将杜鹃分为黑白两种,其中应当入药的为白杜鹃,常见的植物基源有杜鹃科(Ericaceae)杜鹃属(Rhododendron)植物烈香杜鹃(R.anthopogonoides)和樱草杜鹃(R.primuliflorum)的花和叶[3-5]。杜鹃属植物最有代表性的成分是黄酮类的成分,其他成分还包括挥发油、三萜类、二萜类、甾体类等[6-7]。根据目前的研究,烈香杜鹃中的槲皮素(quercetin)、槲皮苷(quercitrin)等黄酮类成分可以提供镇咳、平喘的功效,其挥发油成分在抗菌、抗炎、松弛平滑肌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活性[8]。对樱草杜鹃的研究相对更少,但可以明确的是樱草杜鹃中也含有大量的黄酮类成分,其在抗氧化方面显示出良好的活性[9]。
1.2 圆柏 藏药名为“徐巴”,柏科(Cupressaceae)刺柏属(Juniperus)的多种植物的枝叶都可以入药,包括大果圆柏(J.tibetica)、滇藏方枝柏(J.wallichiana)、叉子圆柏(J.vulgaris)、祁连圆柏等(J.przewalskii),且刺柏属植物的化学成分非常多元化,包括挥发油、萜类、黄酮类、木脂素类、香豆素类、甾体类等化合物[10-12]。以往的研究表明,刺柏属植物的挥发油成分显示出一定的抗菌、抗肿瘤和杀菌作用[13-14],而黄酮类成分,如柏木双黄酮(cupressuflavone)等,无论是在抗炎、抗氧化方面还是在解热镇痛方面,甚至在降压、降脂、降血栓、抗病毒和杀虫方面都呈现出了良好的活性[15-16]。
1.3 藏麻黄 藏药名为“策敦木”,本味药材的基源比较明确,入药植物为麻黄科(Ephedraceae)麻黄属(Ephedra)植物藏麻黄(E.saxatilis)的地上部分,也有地方以山岭麻黄(E.gerardiana)和西藏中麻黄(E.intermediavar.tibetica)等代替藏麻黄使用[17]。目前对于藏麻黄的研究较少,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方面主要是对麻黄属的其他植物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以草麻黄(E.sinica)为典型的麻黄属植物中分离鉴定出145 种化合物[18],最典型的化学成分是生物碱类,以麻黄碱类及其类似物为主,在体内具有较强的抗炎活性,咪唑类生物碱则显示出抗氧化和保肝活性,除此以外还包括黄酮类、鞣质类、多糖类、挥发油类等[19]。麻黄水提物显示出抗肿瘤活性[20],酚类和黄酮类成分具有抗氧化作用[21],麻黄提取物在镇痛方面有显著作用且在体外有抗HIV活性[22-23],而去除麻黄碱类成分的麻黄提取物则表现出抗流感病毒作用[22-23]。另外麻黄多糖具有抗炎镇痛的作用[25]。
1.4 水柏枝 藏药名为“翁布”,怪柳科(Tamaricaceae)水柏枝属(Myricaria)的多种植物都可以作为本味药材的植物基源,如三春水柏枝(M.paniculate)、宽苞水柏枝(M.bracteate)和小花水柏枝(M.wardii)等[26],主要入药部位为花、枝叶和嫩芽。至今对多种水柏枝的化学成分均有研究,主要成分包括黄酮类、鞣质类、三萜类、酚酸类、木脂素类和长链脂肪酸等[27]。水柏枝的水提物及醇提物均具有较为广谱的抑菌作用[28],其水提物在抗炎镇痛、提高细胞免疫、抗自由基、抗氧化等方面都显示出良好的活性,且证明其中黄酮成分对抗炎活性有较大贡献[27,29-31]。水柏枝中的鞣质类具有体内抗肿瘤作用和体外细胞毒活性[32-33],萜类则具有镇静和抗菌的作用[34-35]。对于藏药水柏枝的质量标准的建立现在也已经有比较全面地研究,《中国药典》对原植物性状鉴别和显微鉴别进行了规定[36],也有研究者补充了TLC鉴别、水分测定、灰分测定、浸出物测定、含量测定等方面[37]:TLC鉴定以没食子酸作为对照,以氯仿-乙酸乙酯-甲酸(5∶4∶1,V/V/V)为展开剂,并以0.5%三氯化铁乙醇溶液显色,于日光灯下进行检视;以烘干法测定其水分,拟定水柏枝药材水分不得超过10.0%;拟定水柏枝药材的总灰分不得超过6.0%,酸不溶性灰分则不得超过2.5%;拟定水柏枝药材的水浸出物不得低于15.0%,醇浸出物则不得低于10.0%;以C18柱为固定相、乙腈- 0.1%磷酸溶液(5∶95,V/V)为流动相测定没食子酸的含量要求不得少于4 mg·g-1。
1.5 青蒿 藏药名为“坎巴”,对于药用青蒿的基源,也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目前可查历史上多用的包括大籽蒿(Artemisiasieversiana)、黄花蒿(A.annua)、青蒿(A.carvifolia)等多种菊科(Compositae)蒿属(Artemisia)植物的地上部分,在现在的应用中基本确定本味药材的植物基源为大籽蒿。大籽蒿中主要含有倍半萜类、黄酮类、甾类、木脂素类及挥发油类等[38-39]。根据目前的报道,大籽蒿具有祛痰平喘的药效,醇提物具有抗人大肠癌细胞作用;倍半萜类成分,如苦艾素(bacosine)和蓍草苦素(achillin),显示出体外抗肿瘤作用和抗过敏作用;黄酮类化合物如芦丁(rutin)具有抗炎作用;甾类化合物则有强抗炎、强抗菌和抗病毒作用[40-41]。
2 常见配伍药物[4,42]
作为藏药浴的经典,五味甘露只是一个基础方,其组方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循证进行辅助药物的辩证加减,也常常与其他药物联用。用以与五味甘露配伍的药物很多,包括植物类药物、动物类药物和矿物类药物,且多以清热燥湿的药物为主。
2.1 植物类配伍药物 植物类配伍药物是五味甘露药浴应用时最常使用的配伍药物,常见的有文冠木、决明子、天门冬、红景天、藏红花等。
2.2 动物类配伍药物 动物类配伍药物比较少见,常用的有犀牛角、麝香以及动物的内脏、肉、骨及粪便等,如獐子粪和麝粪。
2.3 矿物类配伍药物 矿物类药物也常常作为配伍药物出现在藏药浴的复方中,如珍珠母、滑石、硼砂等。值得注意的是,藏药浴是源于对天然温泉的仿制,矿泉浴中富含矿物质,是藏族浴疗法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3 制作工艺
五味甘露药浴作为藏药经典方剂,其制作工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但可以知道的是,五味甘露绝不仅仅只是将五味药材简单地经过打粉后混合,而是利用藏药材常用的发酵法炮制而成。根据目前的研究,林扎西卓玛[42]认为五味甘露药浴液制作需要发酵、煎熬及辅助药物的配伍这3个步骤:首先将等比例五味药材或刺柏叶、杜鹃、水柏枝、藏麻黄、野蒿以1∶1∶2∶2∶3晾干切碎置于铜锅并加水没过药物,浸泡后加热煮沸直至锅内水蒸完,再冷却至温热后与酒曲混合密封于容器中,10~15 ℃发酵5~7 d,此时药物表面应当发白似霜状并伴有酸味和酒味;然后将辅助药物添加于发酵后药物中并置于铜锅加水淹没,浸泡30 min后煎煮至原水量一半时过滤收集滤液,再向滤渣中加水淹没煮至1/3时取汁并重复一遍;最后将3次滤液混合放冷至50~55 ℃,添加白酒和辅助方的药粉或药液,搅匀即成。而根据艾措千等[43]的专利,制作本药浴需要等比例的烈香杜鹃、圆柏、大籽蒿、水柏枝、麻黄,洗净干燥后用水煎煮,取出之后置于发酵装置中加入酒曲和粮食白酒(原料∶酒曲∶粮食白酒=100 kg∶2 kg∶2~3 kg)拌匀后于37~40 ℃发酵48 h,取出晒干并用水蒸气蒸馏法对挥发油成分进行富集,再用30%~70%的水或乙醇加热回流提取3 次,每次提取2 h将提取液合并后浓缩至体积等于原投料量后冷却沉淀48 h,过滤后再将滤液经2~4 万分子量的分子筛超滤柱后收集或收集滤液经大孔树脂的30%~90%乙醇洗脱液,浓缩至一定体积后加入之前富集的挥发油和0.1%~2%乙醇或者吐温增溶,搅匀即成。具体的标准化的五味甘露的制作工艺还有待进一步地考证和规范。
4 作用原理
在藏医理论中,认为人体健康的状态是由隆、赤巴、培根3种构造(又称“三因”)的平衡维持的,而这三者中任一或若干因素偏盛或偏衰则是疾病的根源[44]。根据《四部医典》的记载,凡是因为隆这个因素失衡导致的“隆类疾病”都可以用浸浴疗法治疗,书中有言 “可浴四肢僵蜷与腐跋,核与炭疽陈疮与新疮,险症驼背肌骨黄水浮肿,凡属风症无遗皆可除”,即可以治疗四肢僵硬蜷缩、腿脚瘸跛、疔疮、新旧疮、身体浮肿、驼背以及骨内黄水病等[44]。采用药浴的方法可以使得药物在较高温度下较长时间地通过皮肤、血管等吸收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再结合卧于热炕的物理作用调节机体寒热,调整三因使三者重新趋于平衡,从而治疗疾病[42]。高温药浴的形式使得五味甘露药浴中的药效成分透过皮肤吸收后经血液循环达到全身各处,尤其是患处,从而发挥药效;而药浴之后的卧炕发汗则利于祛风排毒[4]。
5 功效与临床应用
根据《四部医典》,浸浴法可驱除湿毒、黄水,能镇风消肿,使瘦者肌肉丰润[44]。从几百年的应用中,人们总结出一定的经验,认为五味甘露药浴对于多种疾病的治疗都能够显示非常好的功效。五味甘露药浴的功效包括:发汗利水,舒筋活络,散瘀消肿,祛风散寒,扶正壮阳,提高免疫[45]。药浴的高温能够激发机体汗水的产生并利于风寒的祛除,由此可见五味甘露药浴对于小便不利、浮肿等积水性病症以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寒痹性疾病都有一定缓解能力;而药物浸浴利于机体筋脉活络,从而散瘀消肿并达到止痛的效果,从而对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疾病所引起的强直痉挛和关节积液与肿胀产生很好的疗效;同时,五味甘露浴能帮助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各类疾病的治疗概率;另外,结合其他辅助药物的功能,以五味甘露为基础方的各种药浴可以用于治疗皮肤病、妇科病、尿路感染等各种各样的疾病[45]。
由于五味甘露悠久的使用历史,各大藏医院、蒙医院以及中医院都长期采用五味甘露药浴治疗多种属于隆病范围内的疾病并且也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应用最广泛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青海省藏医医院[46]在对223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进行添加文冠木和麝香、五根散及驱黄水散的五味甘露药浴和文冠丸等口服治疗后,成功治愈65 例,显著有效者89例,有一般效果者56 例,无效者13 例,总有效率达94.15%。天峻县藏医院对收治的6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给予每天两次的五味甘露药浴并辅以二十五味儿茶丸等藏药口服制剂, 最后有显著药效的17 例,有药效的34 例、无效9 例,总有效率达85%[47];而也有研究者发现五味甘露与小叶毛球莸药浴联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更好的疗效:青海省玉树州藏医院[47]将10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随机列分为两组,一组以单纯五味甘露药浴治疗,另一组以五味甘露药浴联合小叶毛球莸药浴治疗,得到了联合组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单用组的治疗总有效率的结论。
除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有其他研究者尝试以五味甘露治疗其他隆性疾病,如青海省藏医医院对48 例银屑病患者采用五味甘露连续治疗3 周后真菌镜检及培养均显阴性有43 例,治愈率高达89.6%[49];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藏医院在五味甘露主方基础上依症加减硫磺、白芸香、生黄等药物并配合十五味乳鹏丸等口服制剂对65例带状疱疹患者进行了治疗[50],均获得满意疗效。
综上所述,五味甘露药浴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其药效潜力还有待继续开发。
6 现代药理研究
五味甘露对于疾病治疗的作用机制是极其复杂的,但目前为止对其药理作用的研究非常欠缺。迄今对五味甘露的药理学实验主要是针对完全弗氏佐剂诱导造模的大鼠佐剂性关节炎,从组织器官层面来说,五味甘露药浴给药组的大鼠足趾肿胀程度、免疫器官(胸腺和肝脏)脏器系数、踝关节滑膜切片等[51-52]都表现出与模型组非常显著的差异并趋向于正常对照组的指标。踝关节的滑膜组织中JNK1蛋白的表达水平[53]在给予高剂量的五味甘露药浴后也出现了大幅降低,而JNK对于参与关节滑膜中的炎症反应的MAPK信号通路有明显活化作用,所以抑制JNK1蛋白的表达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具有一定意义。而同时五味甘露药浴给药组大鼠的血清中NF-κB、TNF-α、IL-4、EGF含量都非常接近于正常对照组的值,而TNF-α、IL-4是促进炎性细胞的浸润以及滑膜组织和血管增生的炎症因子,NF-κB则会促进这两种炎症因子的产生,TNF-α、IL-4又能够反馈激活NF-κB的产生,从而进入恶性循环;而EGF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关节炎滑膜细胞的过度增生,故这几个指标的正常化都表示出五味甘露对于炎症治疗的有效性[52]。研究者在研究了各组大鼠下丘脑中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54]后发现,五味甘露药浴的给药可以大大降低5-羟色胺的含量,而作为一种促炎致病因子,5-羟色胺水平的降低意味着本药浴具有能够抑制多种炎症的能力。另外在测定了各组大鼠的痛阈值后发现,经五味甘露药浴治疗的大鼠痛阈更高,对小鼠而言也是无论在醋酸扭体反应还是光热致痛甩尾反应中,五味甘露药浴的治疗可以使得小鼠对痛觉的灵敏度下降[55],也可以对大鼠的体温升高有一定降低作用,这也证明了五味甘露药浴具有的解热镇痛作用。
根据刘彦平等[56-57]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给予五味甘露药浴治疗前后的检测结果则可以得出五味甘露药浴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很明显的调节作用这一结论。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血清中常常会表现出抗变性IgG的自身抗体,又称类风湿因子;变性IgG与类风湿因子可以结合并形成大分子量的免疫复合物,这种复合物会沉积于关节滑膜处,从而导致关节炎,且类风湿因子和免疫复合物的产生可能与患者体内的IgM、IgA、IgG的增高密切相关;刘彦平等的研究表明五味甘露药浴可以减少类风湿因子的形成,从而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56]。而赵淑兰等[57]的研究则进一步对T细胞亚群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结果表明五味甘露药浴治疗可以使得患者体内CD8+细胞增多,CD4+/CD8+比值基本处于健康指标,这也证明了五味甘露药浴可以帮助恢复免疫系统的平衡,稳定机体免疫功能。
另一方面,微量元素,尤其是锌,同样也在人体各项功能的发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研究证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体液内的微量元素含量与健康人相比具有显著区别[58],尤其是锌和铁元素含量大大低于正常指标,而五味甘露药浴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认为可能是五味甘露药浴可以帮助补充患者体内的锌含量,从而增强免疫能力。
从药浴这个形式来看,作为五味甘露的五种植物中含有很多既有亲水性又有亲脂性的成分,而这些成分既易挥发又易溶于药液也易被人体从皮肤吸收,这些成分经过毛囊壁到汗腺到皮脂腺再到角质层细胞的过程被体表的毛细血管网吸收后进入全身血液循环从而达到全身各处,尤其是患处,发挥其中药效成分所具备的各种药理作用;而同时药浴一般要求患者将全身或局部浸于约40 ℃的药浴液中,高于体表温度的水温将使得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大大提高了药物吸收效率和药效作用程度[59-60];而血液循环的加速能促进新陈代谢,从而加速机体的组织再生和增强机体白细胞的吞噬能力,促使炎性致病因子(如5-羟色胺和氧自由基等)或异物的排除;另外高温也可以促使挥发性药效成分挥发于周围空气中,通过毛孔、口腔、鼻腔等进入体内,增强各组织器官的活动能力与循环能力;同时药浴所独有的温热作用能帮助机体进行高级神经中枢的调节,可以降低体内末梢神经的兴奋度并松弛患者的骨骼肌,从而达到镇痛的功效[59-60]。
另外,采用药浴的方法可以使得药物直接透过皮肤进入体内从而发挥作用,既能避免药物经过口服给药会对消化道产生的刺激又能减轻肝脏的代谢负担;同时还能避免消化酶对药物的分解,大大提高了该药物的稳定性和利用度[59]。
7 检测方法
根据国家药品标准卫生部颁标准藏药第一册(标准编号:WS3-BC-0266-95),五味甘露药浴汤散的处方为五种药材等比捣碎而得,对其鉴别主要是显微鉴定和TLC鉴定两种[62]。
显微鉴定:取本品置显微镜下观察:纤维状下皮细胞易见,木质化或硅质化,多成束,长480~960 μm,直径10~16 μm;叶表皮细胞多角形或类长圆形,胞壁微弯或平直,直径15~20 μm;不定式气孔类圆形或长圆形,直径17~20 μm,长约20~29 μm,副卫细胞3~5 个;木纤维淡黄色,细胞长条形,微木化。
TLC鉴定:称取本品约5 g,捣碎,加乙醚20 mL,与浓氨试液2 mL,密塞、放置2 h,时时振摇,滤过,残渣用15 mL乙醚分3 次洗涤,滤过、合并滤液,加稀盐酸试液2 滴,摇匀、蒸干、残渣加乙醇2 mL使溶解,滤过,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盐酸麻黄碱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1 mL含1 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附录57 页)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5 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G薄层板上,以氯仿-甲醇-浓氨试液(20∶5∶0.5)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茚三酮试液,在105 ℃烘约10 min。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颜色斑点。
由于目前鉴定方式的局限性,有研究者提出需要进行更全面的TLC和含量测定以提高鉴别方法的专属性。郝忻伟等[63]提出需要将五味甘露复方与各种单味药材进行TLC对照才能进行更完善地TLC鉴别,同时他们还建立了一种高效液相色谱的含量测定方法,即将五味甘露散剂用氯仿提取后以1.0 mL·min-1流速,以乙腈∶0.1 %磷酸=25∶75为流动相经C18色谱柱在室温下层析,在210 nm波长下检测,以麻黄碱作为对照,用外标一点法测定方剂内麻黄碱含量。库进良等[64]也是以麻黄碱为对照,区别在于其采用水作为提取液,且流动相采用的是水∶乙烷∶十二烷基硫酸钠∶磷酸=650∶350∶5∶1。但是仅测定麻黄碱含量过分片面[65],于是有研究者提出改进试验方法,同时测定五味甘露散剂中槲皮素、山奈酚和盐酸麻黄碱的含量[66]。在高益槐等[66]的专利中,将槲皮素、山奈素和盐酸麻黄碱作为五味甘露药浴成分检测分析的标准,以“Zorbax SB-C18色谱柱,流动相为乙腈-0.2%磷酸溶液,检测波长360 nm,体积流量1.0 mL·min-1,柱温30 ℃”的条件分析槲皮素和山奈素,以“Zorbax SB-C18色谱柱,以乙腈-0.092%磷酸溶液以流动相,检测波长210 nm,体积流量1.0 mL·min-1,柱温30 ℃” 的条件分析盐酸麻黄碱,并用外标法计算五味甘露复方中3种物质的含量,从而反应整个复方制剂的质量。刘鸿雁等[68]则对五味甘露复方各种制剂统一进行了检测方法的规范和总结,包括利用植物的粉末显微特征对复方制剂中的刺柏和水柏枝进行显微鉴别、将复方提取物与烈香杜鹃、刺柏及大籽蒿对照药材提取液通过薄层色谱对比进行鉴别、利用HPLC技术测定复方提取液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的含量(麻黄所含成分,每1 g制剂所含的盐酸麻黄碱与盐酸伪麻黄碱总量不少于3.82 mg)以及艾黄素的含量(大籽蒿所含成分,每1 g制剂中艾黄素含量不少于238 μg)。
8 讨论
综上所述,经典藏药浴五味甘露的组方复杂,各味药材的基源尚未明确。鉴于同属植物间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差异,确定各味药材的具体植物基源,尤其是优质基源,是五味甘露现代研发与质量控制的首要任务。虽然研究者对单独的各味药材进行了一定的化学成分的分离和分析,但是对于复方整体的成分并没有报道。作为经过发酵处理的复方制剂,诸药的成分之间极有可能发生一定的相互作用,从而发生巨大的改变,故全面地对本复方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与鉴定是未来对本复方进行系统研究和阐述的必经之路。
根据《四部医典》的记载,五味甘露药浴对于藏医所归属的“隆”病均可治疗,而目前对于本复方的药理研究,基本都是针对类风湿关节炎模型,这是极为不全面的。在未来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大范围地对五味甘露的药理活性进行筛选,再利用不同疾病模型,测试其在不同疾病领域的治疗潜力,同时密切关注五味甘露药浴的临床应用,综合评价本方剂的药理药效意义。另外,为了更好地临床应用,必须以更系统的检测和鉴定方法对五味甘露的方剂进行规范。目前已有研究者提出对于五味甘露这样一个复杂方剂的检测不能只设立一两项标准。五味药材在本方中均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且各自作用亦不可替代,以任何一种单独药物的标准来规范本方的检测都是以偏概全。同时,仅以各味药材作为对照标准也是不够的,需要在对复方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并阐明其主要成分及特征后,制定具有专属性和特异性的鉴定方法。
藏医理论与中医理论一样,都是长期的、全面的、自成体系的一套医药学系统。其对于人体疾病的认知和治疗都自有其道理。作为藏医药学的经典,只有系统地阐述五味甘露药浴的方方面面,才能让全世界的人民认识到藏医之瑰宝,让这样一个经历了时间长河的洗礼和无数病例的打磨的复方被更多人接受,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于治疗,造福更多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