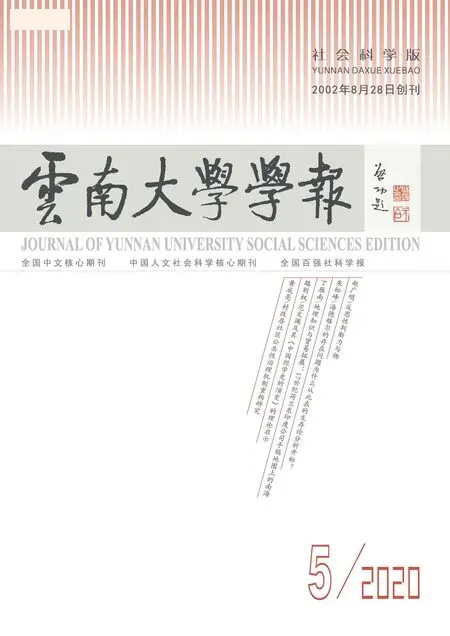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
2020-12-16郑佳佳马翀炜
郑佳佳,马翀炜
[1.昆明理工大学,昆明 650093;2.云南大学,昆明 650500]
理想的历史应该是多声部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道出了人们的愿望。然而,什么样的历史是理想的多声部,以及要如何避免各个声部“互相遮掩覆盖”却是使布氏困惑的。(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5-976页。口述史的出现及发展有可能打破呈现历史事实的这种困难。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材料来呈现历史的一种方法及结果。尽管“口述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源起都很早”,《荷马史诗》可以被视为西方最早的口述史,《史记》中的诸多部分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口述史的早期作品。(2)参见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在此意义上说,《格萨尔王》《哈尼阿培聪坡坡》等都属于口述史。但是,这些口述史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被当作口述史来关照。1938年,美国历史学者内文斯(Allen Nevins)出版口述史《通往历史之路》一书。现代口述史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兴起,其标志是 1948 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3)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在美国口述史不断得到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的口述史也逐渐发展起来。(4)参见王天红:《口述历史:国家图书馆关注的新领域》,《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5期。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文字社会有文献传播之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便成了最为重要的历史,口述材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就沦为了补充材料。但是,当这些口头叙事被命名为“口述史”之后,口述史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生命力是令人震撼的。内文斯是否算得口述史的老祖宗可以讨论,(5)参见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但他创造了这个概念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的提出绝非只是“给了一个名称”这么简单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中,口述史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于口述行为价值的重新认识。口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给予重视从根本上讲是对与言说相对的沉默的意涵的反思,对历史进行言说的言说者的身份多样性以及言说本身的多样性使得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单声部特性被显露出来,无论是历史的书写还是口述史的叙事都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也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口述史的出现使得关于历史事实的言说多了一些不同的方式和结果,多声部历史的愿望庶几可以实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对于历史的批判性反思都是有价值的。相比于正史写作的老到圆熟,口述史还显得稚嫩青涩,口述史的成长尚需汲取历史学及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经验。
一、不再“沉默的大多数”
口述史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论。譬如,何为口述史,口述史究竟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6)该观点作者为里奇。王铭铭、王尧等学者在介绍口述史时都提及了里奇所著的Doing Oral History(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于1994年、2003年以及2014年出版发行了该书的第一至第三版,可见该书在介绍口述史意涵之外,在口述史的研究设计、访谈的实施等系列实际操作指引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台湾历史学者王芝芝将该书译为汉语,台湾远流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分别于1997年、2006年翻译出版该译本。参见Donald A. 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Oxford Press, 2014.还是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7)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或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8)程中原:《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争论也包括口述史的技术方法路线,比如是否使用录音设备,是否将口述内容转换为文字档案进行保存。无疑,这些讨论都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讨论似乎还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思考应该从口述史何以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以及这种显然与“正史”存在差异的另一种对历史的言说到底是谁在发声是更为重要的。口述史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首先需要从其出现的时期进行考察。
口述史的提出绝非只是对早已存在的事项进行命名那么简单而已。18至19世纪的数次战争虽然帮助美国走向独立并不断赢得了信心,然而对母国(motherland)情怀的超越却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力的崛起。在经历了“光辉的20年代”和“萧条的30年代”之后,美国人也开始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了反思,试图保存更为全面的有关国家及社会的自己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录音设备等科技的发展,研究者邀请大量的普通民众(不同性别、族群、阶层)进行个人生活史的讲述,并将这些在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进行记录、保存。最为典型的是内文斯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上至老板、下至员工的历史访谈。美国“口述史”的提出以及此后广泛兴起的口述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保存其独具特色的特定时代社会万象的积极作用,也为后辈更为全面、细致地理解美国历史、美国精神提供了可行性。兴起于美国的口述史对于美国民众形成美国的历史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还在于,兴起于美国的现代口述史行动迅速在其他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并非缺乏历史书写的国度,甚至像中国这样拥有丰富的历史书写的国家也开始重视并实践口述史的行动。要而言之,人们何以开始对开口言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重视。
言说与沉默是相对的。可以说,沉默和言说就是生存的两种状态。虽然作为人而言,言说是一种常态。但是,在社会层面上,言说与沉默则往往表现为两种存在的状态。因此,言说和沉默从更深层次上看,都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少数有权者往往是言说者,多数的无权者虽然也可以用日常的言语表达,但这些表达是被权力所压制的,他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依然是沉默者。从社会意义上说,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言说,进行口头叙说并呈现给社会,这就表明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性的改变。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当越来越多的人可能通过口述史来表达对历史事实的理解的时候,就是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对历史与世界的理解的合理性获得了社会一定程度的承认。口述史的出现其实也是社会分层坚冰融化的表征。
言说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在对真实的世界进行理解时,往往要求诸语言。由于人的思维中存在普遍性的无意识思维结构,世界各地的神话成为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折射。(9)[法]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组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无文字民族向神话传说索求的东西,“就是为了阐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秩序和我们出生的社会的结构”。(10)[法]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栾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6页。与此同时,“当我们思索我们的社会秩序时,都会求助于历史,以便解释它、证明它或指责它”。(11)[法]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第86页。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地去思索社会秩序,不断地在各类史料中追寻秩序,原因在于秩序赋予了我们赖以生存其中的社会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德鲁克曾经指出,人们不可能将“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的、惊慌失措四处奔跑的人”称之为社会。(12)[美]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换言之,一个社会的成立及运作都离不开特定的秩序。若秩序无法顺畅发挥功能,则易于引起人们行动过程中的失范与无序。值得注意的是,口头形式存在的知识的重要性并不因书写形式存在的知识的出现而丧失或者降低。这就意味着,当大多数不再沉默,口头叙说所带来的意义,即口述史以记录口头言说行动的形式协助保存和传播社会秩序等知识,这直接为布罗代尔的历史呈现难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说话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人们说话“和走路一样”,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然而然”,以至于人们难以轻松地给它下定义。然而,如果说走路是本能性的行为,那么言语则是非本能性的行为了。(13)[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页。言语是获得的,因为言语行为能够表达与传递信息而具有社会文化功能。正是如此,哲学家们一直对人们的言语行为进行着思考。在追问“人之说话及其表达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时,海德格尔发现“任何表达,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都已经打破了寂静”。(14)[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页。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言说在言语表达之外的另一种形态,即沉默。申言之,说话以及不说话(沉默)两种状态的动态交替组成了人们整体上的言说行动。何时说、跟谁说、何地说、说什么、怎么说以及在社会的什么层面上说等等通常成为说话者从沉默状态滑向说话状态时需要考量的系列问题。这就意味着“开口说”即是为了表述特定内容,利用声音传输相关信息其实就是对意欲表达的事象进行标记。同样的道理,不开口说即保持沉默可能出于不必说、不用说甚至不能说等原因。
在口述史的视野中,由于开口讲述具有明确的时间起点,因此开口之前的沉默则是一个重要向度。在现代口述史出现之前,人们何以对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书写保持沉默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因而,“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并且“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也就成为史学家的任务。(15)[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页。史学家将各种历史之声编写为有规律的“曲调”,口述史赋予了大众类似的自由。这意味着,口述史开启的不再沉默的大多数的人们的言说是有其表达的目的的,也是人们希望听到不同声音的表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历史就是选取合适的声音的组合,使之有规律而成为音乐的结果。
二、历史叙事的多种可能
口头的叙事,或者说以口头言说存在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如也表达了一些不同于史官的另类的看法,无论这种史官是否代表权力掌握者的观点。这就是现在人们较多地肯定口述史发出了底层人们的声音的原因。尽管口述史并非就只是底层的声音。无论是否底层的声音或者边缘群体的声音,抑或是也包含了一些并非底层的声音,但口述史都是这原有的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之声之外的声音。哪怕存在着不真实的问题,口述史也会迫使人们去怀疑原有的单一的历史叙事的权威性,至少也会促使历史叙事要更加警惕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即使在不是直接讨论口述史的有关历史的思考中,已经书写成型的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是会受到不断的挑战的。阿多诺就认为在生存本能以及理性对自然的控制的推动下,“欧洲正史下掩藏着一部秘史”。(16)[加]黛博拉·库克:《阿多诺:关键概念》,唐文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这部秘史“包含着被文明压制和扭曲了的人类的本能与激情”。(17)[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本能与激情被压抑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对自然的异化很可能进一步导致人自身的异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口述史具有了协助人们宣泄本能与激情,调和人与自然关系进而调和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作用。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都同样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这些反映都可能存在缺陷,只不过口述史的问世使得历史这种观念的反映的缺陷更易于被人们所承认。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今的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的进步等都使得人群流动的幅度、频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传统的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记录与书写方式难以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多样性的理解以及对知识的多样性的求索。口述史有力地补充了传统史籍中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有所缺失的遗憾。更为重要的是补充了普通民众由于其身处地位的不同而具有的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的理解。事实上,人们在现实中记录历史知识的方法路径本身就是多样化的——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是一类,生活世界中的“日用而不知的”常识是一类,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也是一类。因此,不仅仅经典著作因承载着历史信息而成其为历史文献,家训、族规、蒙学读物也可以成为历史文献,甚至报摊上的通俗读物、人们的热点公共话题也都可以为人类思想发展史做出特定贡献。(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7页。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时期开封市民多场景、多主题、多面向的日常生活,这对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整体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所谓正史所不能赋予的。与此相仿,口述史的方法使普通民众能够自己亲口讲出对自我的生活、民族、文化、社会及国家的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不同言说者的不同声音,是对之前保持沉默的一种打破。不同的声音好似不同的声部,“言为心声”式反映历史事实的口述史在实质上是一曲多声部音乐的创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人们可以看到整合不同的人对生活、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从而形成历史发展的共同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但理想化的整合并非是同一乃至规训,而是允许不同的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形成复调的历史理解,使不同的认识可以因为对话的存在而最终消解其中的抵牾,使之共同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活水之源。
当世界诸多国家开始进行口述史的实践并开始有关口述史理论分析的时候,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展开了“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时间的‘实地调查’” ;(19)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这些调查成果也包含了大量的口述材料,而且口述者或多或少能够现身。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学中“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思潮引导下向外寻求方法也促进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理论探讨。(20)王尧:《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在这里,可以看到国内口述研究的学术建构源头。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口述史工作实践与20世纪70年代作为学科概念得以引介进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口述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口述史”这一概念得以引入前,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进行了先行的口述工作探索。这愈加表明了人类心智中普遍同一性的存在及其在言说活动中的共同表现。人们在言说活动中意识到打破沉默、发出声音的重要性。
五峰山长江大桥南主塔上横梁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单箱单室截面,总高度32.7米,共分四次浇筑混凝土。此次为上横梁第二次混凝土浇筑,浇筑高度6米。在完成上横梁主体第二次混凝土浇筑后,南岸墩身施工任务即进入扫尾阶段,很快进行最后的第三、第四次装饰段施工。届时,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将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江苏交通运输厅)
无论如何,过去那些被历史学家“疏远”的“在时间上与自己生活时代距离靠近的‘近历史’”(21)杨正文:《历史叙述与书写的“可表述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开始引起了学界内外的逐渐重视。人们对口述史的渴求甚至掀起了一场“当代中国的口述史运动”,而这场运动“缘起于破除政治迷信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当时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造成了反思历史的强烈苛求,但传统学术体制的知识供给机能严重不足”。(22)秦汉:《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这就不仅可以看到口述史对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具有共同探索多声部的复调历史之探索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具有比所谓正史的更早地表达对世界的理解的意义。
作为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方式的口述史,其存在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促使多种历史叙事的产生,并且为更多面向地理解世界产生动力。世界并不能理解为各种事物简单相加的总和,而必须被理解为任何事物可能存在的条件。(23)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3页。机械地将对不同事物的理解叠加后即认为获得了对世界的理解的做法,由于实践的创造性价值而不断调整,通过讨论各种事物,从而理解事物得以存在的条件,即对现实世界以及观念世界的理解、把握以及调和。这就意味着,口述史的意义还并不简单地在于在正史之外加上了另外一种历史。口述史通过激发不同声音的发出、不同声部的合作,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穷尽了对世界的理解,而是可能会使对世界的理解变得更为成熟和精深。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意欲对所有变化做横截面式的判定显然是不现实的,如何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恰恰需要汇聚各种个体、各种族群、各种文化的生活经历与生存智慧。这恰是口述史能够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理应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这种复调历史并非杜赞奇从基于话语的争夺、控制、实施和操纵等角度去理解社会和历史的过程这种话语分析方法并以解构民族国家单线叙事为目的的复线历史。(24)钟瑞华、赵旭峰:《民族国家叙事与复线历史之争》,《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2期;韦磊:《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复线历史范式的内涵》,《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葛兆光对杜赞奇基于复线历史观得出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之结论提出质疑,指出“‘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原本就是历史的延续体,这与西方不同,中国并不是后设概念,因此,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是更为合适的研究进路。(25)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页。依然基于文献而展开的历史,由于话语分析的使用,可以去挑战终极目的是为民族国家站台的历史,但同时,这样的历史也同样需要去面对到底应该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应该从历史去拯救民族国家的挑战。
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书写本来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观念的反映。但是,由于缺少其他的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声音,这种观念的存在的东西更容易被当成了事实的存在,从而遮蔽了其心声的实质。正是在社会不断发展,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观念的更新还是技术方面的进步都已经为不同声音的发出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之后,其他的心声也有了表达的需要及条件。并且,这样的表达可以使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观念存在的事实被确证。口述史存在的理由开始变得充分。哪怕口述史中存在的不够公正、不够全面、不够真实等等的问题被指出,尽管毫无疑义这些问题应该被克服,但都不会使口述史丧失生命力。因为,口述史就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而且在承认自己是心声的时候可以再次明确文献历史也只是一种观念的存在。
或许,文献历史更加容易获得更多的观念与事实相符性的实证。关于历史的无规则的声音就是指对那些实际发生的但未经整理的记忆的呈现。相对而言,文献记录的材料更能够便利地形成有规律性的书写的历史。口头言说因易变——造成易变的原因很多,如情景等影响——要在易变性的材料中建立逻辑关系就更加困难。但是,即使在比较中显示了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更具真实性,人们发现这种历史也面临着对文献材料本身的采用是否有所取舍,取舍是否得当,书写是否秉笔直书等问题。对历史进行言说的言说者的身份多样性以及言说本身的多样性都表达了对多声部历史的诉求。无论是口述史还是文献历史,都是观念的存在,都需要进一步地自证其与历史事实的相符性。口述史的出现使得历史事实的言说获得了更多的可能,结果就是促使多声部的复调历史之形成不断成为可能,这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三、书写事象的选择性及 切近事实的真实性
由于口述史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与自己生活时代距离靠近的“近历史”,对于这种近历史的言说应该与社会生活中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相关联,应该树立起人民史观,即并非所有的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值得书写的。此外,无论是口述史还是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切近历史的真实性都是其存在的重要理由。或者说,真实性是口述史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复调历史的可能性基础也还在于二者的互补性。
尽管口述史书写在近年来赢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口述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以口述史为名进行的口述记录行动有可能因为赢得市场的需要而放弃了对“口述史之‘人民史观’”的自觉,一味追求对“敏感话题”的聚焦而片面强调名人、伟人的生活秘史或回忆录,(26)秦汉:《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因此表现出难以保证其真实性甚至与文献历史相矛盾的倾向。这类所谓口述史因为借猎奇性生产经济利益就极其容易导致罔顾事实的结果。现代生活面临着许多重要的与广大民众利益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往往就需要对形成这些问题的历史原因进行认真的多方面的探索。口述史在这些原因探索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经验的总结还是教训的汲取都需要多视角的对历史的审视。只有那些与民众福祉相关的选题才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口述史课题。尽管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观成分,然而“选择什么事实”以及“赋与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通常是由“提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研究的前提假设所规定的。进一步地说,这些问题与假设同时也就反映出特定时期人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人们所关切的问题随时代的演变而变化。(2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41页。因此,那些以满足猎奇心从而谋取经济利益为宗旨的所谓口述史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这样的东西可能混淆视听,造成新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真实性是口述史和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生命保障及价值所在。口述史的真实问题当然也会发生在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当中。就口述史而言,如何克服口述者中存在的并非恶意的失真的问题是可以借鉴历史研究方法及滥觞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方法的。一般来说,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会与口述者的记忆问题有关。口述历史的访谈虽然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具有相似性,然而访谈的组织与展开常常需要与其他各类采访进行区分,考虑到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28)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这与民族志工作中必须在访谈前对相关问题进行资料准备相一致。访谈者事先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对问题有深入的把握是十分必要的。民族志工作中的文献法是来自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理应有助于口述史的发展。
口述史方法虽然“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间的关系”两个新维度,但口述访谈中采取行之有效的、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两个关系的方法是亟待探索的。(29)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对访谈人的选择是否合适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口述史价值的高低。一般来说,那些对历史事实有较为全面了解的人,尤其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是较为理想的访谈对象。此外,在访谈工作的开展中借鉴民族学家特别重视的参与观察法也是重要的。虽然,采访者不可能和受访者再去重新经历一次历史的过程,但采访者经过与受访者一段时间的相处,熟悉受访者的生活习惯,并对受访者的思维表达习惯有相当的了解对于访谈工作的开展会是十分有益的。对受访者的深入了解还是确定采取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或是其他访谈方式的重要依据。
民族志工作中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口述史工作来说也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在民族志工作中,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尽量克服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当地人的文化,把当地人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最终的判断。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用比较的和历史的观点看待民族志提供的材料。主位客位方法的结合是民族志研究者调查的基本方法。在口述史的采访与受访者之间,充分尊重受访者的表述并对这样的表述做出尽量客观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民族志“从根本上讲是在理解各种文化拥有者基于各自文化而进行的有关文化的共同阐释的阐释”,(30)马翀炜、覃丽赢:《复数位:独龙族“开昌瓦”节日研究及方法论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那么由采访者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口述史也是两者基于各自的历史视角而进行的有关历史的共同阐释的结果。
当口述被视为一种言说活动,那么言说活动的深层目的则需要被加以考量。演唱哈尼迁徙史《哈尼阿培聪坡坡》的歌手这样唱道:“祖传的古经,是真的我没亲眼见过,是假的我说不清,我把先祖的古歌传给后人。”在谦虚的表白之后,歌手基本是按他自己认为真实的历史来唱的。但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之间互相帮助的现实还是影响到了他的演唱。歌者朱小和将那些记恨汉人的内容一两句就带过,省略这些在他看来是不利于今天民族团结的内容是应该的,这也是他对新时代新生活充分肯定的结果。在整理者史军超不断解释那些民族之间存在矛盾乃至仇恨都是过去的事情,并不会对现在产生不良的影响,直到疑虑被打消后,朱小和才把那部分细节补充完整。(31)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6辑)哈尼阿陪聪坡坡》(汉文、哈尼文对照),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从这个事情中可以看到,人们在进行表达的时候并不会对于任何信息不加筛选地传递出去。人们是依照自己的观念有选择地对信息进行甄选并不断利用这些信息构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的。
此外,就采访者而言,充分意识到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图式的差异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除了采访者与受访者可能出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而产生文化图式的差异之外,采访者与受访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处于不同的时代,都有可能造成两者之间的文化图式上的差异。“在民族志工作中,要更好地认识与表达多元的世界,就必须认识到,作为传递信息的语言及人的世界的界限是多样性的。人们是以作为思维与直观的中介的图式去同化与整合生活经验的。在多元的生活世界中,文化图式的跨文化转喻是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一种认识与表达方式。”(32)马翀炜:《作为敞开多元生活世界方法的民族志》,《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受访者与采访者使用不同母语而引起文化图式的不同以及口述工作将口述材料转写为文字并出版发行等等因素而造成不真实的情况。(33)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在采访者和受访者中存在文化图式的差异的时候,跨文化转喻的方法就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跨文化转喻是指“以一种文化中的图式与另一种文化中的图式相联系来生产转喻,从而获得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在不同的文化间进行的图式转喻是否真正有助于跨文化理解,取决于民族志工作者对于自身文化图式及他者的文化图式的理解是否深入”。(34)马翀炜:《作为敞开多元生活世界方法的民族志》,《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对于口述史采访者而言,对于自身文化图式是否自觉以及对受访者的文化图式的理解是否深入直接影响了表达与接受之间的困难能否真正克服。
毫无疑问,口述史并不等于民族志,相对成熟的民族志工作方法可以为口述史工作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口述史的发展过程中,汲取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更加积极地探索能够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方法是更加必要的。这也应该成为口述史实践者的自觉的行动。
四、结 语
口述史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二者之间互补互益的差异使反思性知识与批判性知识可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检讨并对历史事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反思及批判过去的历史,其实都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之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积极的作用,即“以史为鉴”。现代社会具有碎片化、不连续性等特征,这都会影响人们切近历史事实。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事件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都还处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术语是不够的。”(3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4页。面对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的事实层面而说出不同的意见,会使人变得更谨慎,更加能够保持一种敏锐的证伪意识。以口头材料为基础的口述史和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历史可以互补互益,而根本不是互不相能、互相颠倒的。针对复调叙事,巴赫金曾指出,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多音调并不要在某种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每个声音都是主体,声音之间具有对话性。(36)[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口述史注重口头叙事材料,激励普通民众发出声音,这使得多声部的复调历史的形成具有了可能性。
口述史在巨人般站立在那里的文献历史面前还是稚童,但这稚童是可能成长为与巨人比肩的充满生命力的青年的。人们可以通过口述史的成长而迫使自己去反省文献历史,从而也在面对口述史存在的诸多问题时感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口述史是可以通过借鉴民族志研究的多种方法去更加切近历史的真实的,从而使真实性获得更大的保障,进而使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多元视角能够被接受,也会促使多声部的复调历史能够真正出现。事实上,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也在不断重写,对那些史料的重新解读也在不断进行。这些重写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要求,口述史的书写也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当这两种历史书写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而相互砥砺的时候,这些书写就有可能更加切近历史事实,从而使人们获得对历史、对世界的更加多方位的更加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