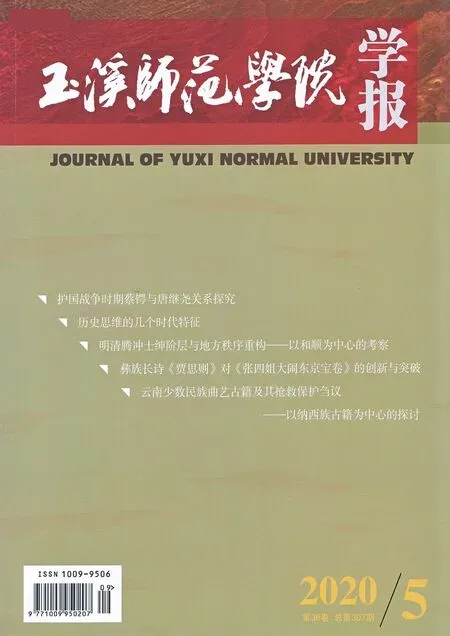彝族长诗《贾思则》对《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创新与突破
2020-12-15杨筱奕
杨筱奕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 昆明 650021)
《贾思则》作为一部滇南彝族叙事长诗,主要流传于云南省元阳、红河等县的彝族地区。以仙女贾思则对凡间男子的爱慕及私自婚配为基础展开,仙女贾思则用法术帮助夫家发家致富,结果引来山官嫉妒并设计陷害;丈夫受冤被捕,贾思则也被通缉。贾思则被逼用仙法打败了朝廷和天庭派来的官兵、将领;但在母亲劝说下,最终还是释放了前来抓她的人,并澄清了事件,得到了原谅,最终夫妻团圆。
作为滇南彝族民间文学作品,名为《贾思则》的长诗现存两部,一部为手抄本,一部为口传本。手抄本的《贾思则》,佚名撰,清道光二年(1822)抄本。开本高27厘米,广35厘米,每页17-18行,行17-21字,今藏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保存完好。口传长诗《贾思则》由李八一奎说唱,涅努巴西整理。两部彝族长诗均为篇幅宏大的叙事长诗,故事完整,情节跌宕;其表现手法和记述方式均采用了彝族传统的五言、七言体;故事主题也完全一致——都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智慧的奇女子贾思则,肯定和赞美了她正直善良以及不畏强权的正义感;同时,也劝诫世人相信姻缘天定,莫要强求,家庭要团结,夫妻要和美,不要作恶。故事起因都是仙女贾思则私自下凡婚配凡人;故事情节与主要内容均为“遭到嫉妒——计遭陷害——救夫——迎战——胜利——王母规劝——喜乐团圆”等;故事人物主角都是仙女贾思则和丈夫,也有山官、衙门大官、京城官员、凡间将领、玉帝、天兵天将和王母等。
虽然两部彝族长诗相似度极高,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异的。首先,流传方式不同——一个是手抄本,一个是口传;其次,描述的重点章节不同。比如,相比手抄本,口传故事对贾思则在天庭的生活和私自下凡前描写较多,用“寂寞”和“画像”两节作交代,“下凡”与楚维香相识的描写也是费了一番饶有彝族特色的笔墨(前情:四姐下凡,等候在楚维香即朱武斯挑柴经过的地方;楚维香却以为四姐是妖精、幽魂,内心十分惧怕,请求宽恕)(1)本文中关于《贾思则》原文的引注,主要参考:涅努巴西,整理.彝族叙事长诗选[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266-356.。两人对话中的比喻明显具有彝族特色——女子用八哥比喻诚实的男子,用鲜花蜂蜜来自比;男子用彩云来比喻年轻貌美、体态轻盈的妙龄女子,如:
象八哥一样诚实的阿哥/……/蜂蜜鲜花来结识/象彩云一样游荡的姑娘/……
同时,在四姐向楚维香表达倾慕、打消他疑虑时的比喻,也较为彝族化,如:
有壶没有杯/好酒难生辉/脚正不怕鞋子歪/说千道万理不亏/白雪喜欢落红梅/金雀喜欢银雀配/虎子一样胆小的阿哥/莫怕路旁有山鬼
但口传长诗对贾思则与官兵交战部分的描写却过于简单,甚至在情节方面也有所缩略;不过对于贾思则与天将斗法章节的描写又多费了点笔墨;而其结局是女儿说服母亲,让自己留在了人间、成就了自己理想中的姻缘;最后,口传长诗在语言表达和描写手法上更加凸显彝族特色的文学美和音韵美。

表1 云南彝族地区《贾思则》对比表
一、《贾思则》汉文本渊源及流变研究(2)此处及以下有关彝族长诗《贾思则》的内容参照手抄本文本。
《贾思则》在滇南彝族地区有两部流传,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是滇南地区彝族的原创作品。但笔者从贾思则身份和诗歌中“京城”一类的内地地名和封建王朝的官名等内容看,它应该与汉族传统民间文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据汉族神话传说,玉皇大帝膝下有七女(3)一说玉帝有九女。此处采用的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说法。;因此,四姐作为玉帝四女的身份基本是可信的。而在汉族地区流传的与四姐、四仙女有关的作品,多为流派较多的地方曲艺或戏曲,比如京剧《摇钱树》、黄梅戏《张四姐临凡》、东北小戏《张四姐下凡》、戈腔《摆花张四姐》、桂剧《四仙姑下凡》、河北梆子《端花》等;通过对故事内容和主要情节的文本对比,可以确定《贾思则》与京剧《摇钱树》(4)京剧《摇钱树》(又名《玉帝女摆花张四姐思凡》),戏曲演张四姐思凡下界,与书生崔文瑞成婚,幻化摇钱树,崔家骤富却遭员外诬陷。四姐将前来捉拿她的官兵拘入摄魂瓶中。玉帝召四姐,不从,乃遣天兵前往擒拿。诸神皆非其敌。最后其六姊妹劝之,始忍痛回天宫,并携崔同往。基本一致。
我们都知道,戏曲最直接的源头是故事,而这个故事可以是经文人记录的“史”,也可以是艺术加工的故事或被艺人加工渲染的传奇;而“稗官为传奇蓝本”不仅是某人对古代小说与戏曲二者关系的美学判断,也是明清之际的文艺理论家对戏曲创作借鉴小说题材这一现象的理论概括(5)沈新林.同源而异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比较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69.。在我国,小说改编为戏曲之风早在魏晋就初见端倪,随后大兴于唐代;而在整个文学历史发展中,以小说为蓝本改编为戏曲的作品也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有名的就有《莺莺传》改编成《西厢记》,《虬髯客传》改编为《红拂记》等等;戏曲《张四姐》也是如此。
根据京剧曲目的提示,笔者在《曲海总目提要》(6)卷四十《天缘记》中记载:“其名曰摆花张四姐思凡。”参见:曲海总目提要[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1745-1747.卷40中寻到了该剧;不过其名却是《天缘记》。其中所记:“按剧中指,张四姐为织女。虽甚诞妄,然太平广记所载:唐人郭翰乘夜卧庭中……剧盖本此。又韦安道遇后土夫人,天后以为魅物,令正谏大夫明崇严,用太乙符箓法治之……其后,安道随与俱去。夫人被法服,居大殿,奇容异人来朝。皆华冠长剑,被朱紫之服,此记言张氏灵通。包拯□察,不能知其根柢,天神与战,亦皆不胜。铺叙点染,仿佛近之。”(7)曲海总目提要:下:卷四十:天缘记[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1745-1747.由此即可探知该故事的基本源流和发展流变。
1.传奇、小说。根据《曲海总目提要·天缘记》中所示,《太平广记》卷第六十八《女仙十三郭翰》是该剧最早的母题故事——仙女对士子的钦慕。后来,仙女离开,郭翰也另取程家女。这时还只是一个奇幻怪诞的爱情小说,除了女主身份——织女与后来的仙女有点点关联之外,其余内容情节均与张四姐的故事大相径庭。故此才说“剧盖本此”。
又据“韦安道遇后土夫人……”一则,笔者查阅到了《韦安道传》。该故事是唐代张泌的著名小说,又称《后土夫人》;讲述武则天时京城少年韦安道婚配后土夫人。因韦安道之父怀疑儿媳为妖异,则天皇帝即让两位神僧和明崇俨去“除妖”,但均未成功;最终,韦安道不敢违抗父母之命,只好与夫人分手。此故事主角为仙女无疑,而且也有仙、凡斗法的故事元素。可见,《后土夫人》更多的是给予了《张四姐》情节——斗法的杂糅。因而也只能是初具了张四姐故事的部分元素。
另外,笔者在明代小说中搜集到一部与《张四姐》母题——仙凡婚配相似度很高的小说《崔生遇仙》。此小说讲述开元、天宝年间崔姓书生遇一女子之后自行婚配,母亲见儿媳美艳之姿恐为妖物,于是让二人分手;夫妻分别之际,女子将一白玉盒子赠予崔生;后来,崔生从购买白玉盒的胡僧口中得知,自己当初娶的娘子为王母第三女。可见,此故事也只是具备了仙女与凡人婚配的基础故事,并没有大战官兵、天兵天将等情节;因此,明代的“崔生遇仙”更应该是唐代“郭翰”的进阶版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同时期的小说中还特别关注到同名的《天缘奇遇》(8)笔者注:又名《祁生天缘奇遇》,共2卷;艳情小说,流行在明万历年间,不知作者。《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万锦情林》均收入其中。,但内容与今之所见戏曲《天缘记》相去甚远。
综上,“郭翰”“后土夫人”和“崔生”三部传奇小说均讲述唐代书生婚配仙女之事,但故事女主角还不是“四仙女”或“四姐”(郭翰故事的主角是“织女”,韦安道故事的主角是“后土夫人”,崔生遇到的是王母三女)。郭翰与织女的故事情节相对简单,结局也完全不同;《崔生遇仙》可算在“郭翰与织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小说,且具有了《张四姐》故事的基础元素:遇仙——婚配——媳妇遭驱赶——夫妻分离,但也缺少了“大闹东京”的故事核心;而“后土夫人”情节虽然相对丰满,但也只能勉强算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张四姐的故事雏形。如果非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只能说“郭翰与织女”催生了“崔生遇仙”,并吸收了“后土夫人”故事冲突,形成了张四姐的最早形态;而《天缘奇遇》则更多是被借名而已。因为,《崔生遇仙》与小说《天缘奇遇》作为两个独立的故事,一直是“各自流传”;直到明清两代,两个故事依然各自都有文本可循。如:《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中一卷(上层)有《崔生遇仙》,五卷(下层)有《天缘奇遇》;《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十卷》卷一、卷二上层中均有《天缘奇遇》;《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七卷《记类》中有《崔生遇仙记》(9)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沧州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308-310.。
唐代传奇小说,乃至到了明代的小说中,均未见《天缘记》或《张四姐》的原本。因此我们假设,是否在某一个时期或某种文学形式中,崔生故事与后土夫人“合流”了呢?此观点在《曲海总目提要·天缘记》中得到印证,《曲海》中记载该剧“出于鼓词”。那么,这个故事的“合流”是鼓词吗?
2.鼓词。从《摇钱树》中包拯、杨家将、齐天大圣等人物来看,“合流”应该是北宋以后的事情;而根据包拯故事较为流行是在明代、“崔生故事”为明代小说这两个方面来看,“合流”在明代以后的可能性更大;且“‘鼓词’作为一种文体或一篇篇的作品的称谓,是晚至明末清初的事情”(10)张正学.中国古代俗文学文体形态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639.。因此,“出于鼓词”在时间逻辑上是合理的。然在《清末上海石印说唱鼓词小说集成》中未见有关张四姐、崔生的故事;且从目前查询的情况看,与张四姐、大闹东京等有关的故事,比如《新编说唱摆花张四姐大闹东京传》《新刊说唱摆花张四姐出身传》《新刻张四姐下凡全本》《新刊张四姐摇钱树全本》等,几乎都是清末以来至近代的说唱词话文本。我们也知道,《曲海》作于清末民初,正是社会上流行鼓词较多的时候(11)“目前可确知,抄、刻(或石印)于光绪、宣统间的鼓词,至少也分别有66种和52种之多。”参见:张正学.中国古代俗文学文体形态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657.;但是,我们并不能以表演时“敲着鼓儿伴唱”就认定其为“鼓词”(12)如果说鼓词是表演时有鼓伴奏,那么在其他说唱艺术中也是有鼓伴奏的,比如戏曲。。因为,虽然在《中国鼓词总目》(13)李豫,李雪梅,孙英芳,李巍,编著.中国传统鼓词总目[M].大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537.一书“中国传统鼓词总目”(2 209)著录中有《张四姐大闹东京传》,但其版本信息却只有“赵景深《鼓词目录》”(14)李豫,李雪梅,孙英芳,李巍,编著.中国传统鼓词总目[M].大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537.。另外,赵景深根据其手头所得鼓词及其目录所列的“鼓词”《张四姐大闹东京传》(15)赵景深,编选.鼓词选[M].上海:古典文学版社,1957:7.也只见目录,不见文本;同时,他也认为“至于有些名目,如《打花鼓》《狄仁杰赶》等,究竟是否长篇鼓词,因不见原词,很难加以肯定,也只能暂把它们列入了”(16)赵景深,编选.鼓词选[M].上海:古典文学版社,1957:13.。
同样,按照张正学关于鼓词结构的研究观点,判断文本题材是否为鼓词,应结合表演、文本语言的散韵及文本结构三者综合考证。因此,在没有发现文本的情况下,还是不能断然肯定其体裁。另在《中国鼓词总目》“中国传统鼓词总目”“补遗”(2 350)中有《摇钱树影词》(17)李豫,李雪梅,孙英芳,李巍,编著.中国传统鼓词总目[M].大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565.,且从剧名来看或与京剧《摇钱树》有一定关联。但未见其文本,在《辞海》中也不见“影词”及其注释。可见,《张四姐大闹东京传》《摇钱树》是否能作为“鼓词”还是有待进一步考证。
3.宝卷。通过查找张四姐的“鼓词”文本,我们发现:有关张四姐的故事更多的是以各种唱本、唱词流行在清末到民国这段时期;而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张四姐的故事,为北方地区发现、抄写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天仙宝卷》(又名《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1册)(18)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8.;又从车锡伦先生对我国宝卷的研究中得知,“张四姐”故事主要以宝卷(念卷)形式存在于我国北方地区,如甘肃河西地区的《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又名《张四姐宝卷》)(19)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67.;包括流传至今的靖江宝卷中也有,只是名称唤作《月宫宝卷》(20)参见:尤红,主编.中国靖江宝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而已。因此,从时间上看,到了清代嘉庆年间,张四姐的故事已经完成了合流并定型。
既如此,又是什么促使北方地区将“崔生遇仙”与“后土夫人”结合,并杂糅进新的元素呢?以众多对“宝卷”的研究著述内容来看,自明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教派宝卷;到康熙年间,这些民间教派虽被官府取缔或剿灭,而宝卷撰写或改编之风也逐渐消歇,但这并未影响某些宗教性社团、或群众性组织、或个人,仍在民间的酬神、驱邪以及家中寿诞、禳解灾病等场合组织“宣卷”活动。而出于对现实客观环境的考量,所宣之卷便多为小说、民间传说等世俗故事和历史人物(21)张正学.中国古代俗文学文体形态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560.。
根据车锡伦先生的研究,《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属于俗文学传统故事宝卷。由此来看,张四姐故事的最终形成,或与传说、历史人物有关——事实上,张四姐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根据传说,她乃元代山西石州温泉县人(22)笔者注:温阳县即北宋河东路石州辖下的古温泉县,建于唐武德三年(620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温泉县更名为温阳县。,猎户之女。元代蒙古政权为镇压温阳县农民起义,屠焚县城,张四姐即率勇士起义,反元长达13年之久。就河西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23)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127-164.故事明确交代发生在宋仁宗时期的东京府。与仙女四姐有婚约的天庭金童崔文瑞被贬下凡。四姐私自下凡遇之婚配,遭到员外一干人等的嫉妒和陷害,并反抗包拯、杨家将等人。玉帝得知四女儿私自下凡,派天兵天将前去捉拿都被打败。最后四姐听从了母亲和姐妹们的劝说,与夫君一起回到天庭。来看,张四姐的故事,应该是在“宝卷”这一形式中完成了合流与定型。而彝文长诗正是受益于此定型了的宝卷故事。
4.其他衍化形式的张四姐故事。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还能窥见张四姐故事的影子,比如版画,清代绵竹墨线版印条屏的“摇钱树”画面,据说描绘的是《天缘记》传奇所说天女张四姐下凡,与贫士崔文瑞结合,点化“摇钱树”的故事(24)参见:王子今.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名象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带有浓郁神话色彩的年画虽然显得世俗化,也明显偏离了原著的初衷,但也印证:到了清代,张四姐的故事便已定型;同时,也提示了我们,《张四姐大闹东京》篇名易为《天缘记》,从宝卷转为戏曲、唱词等曲艺,至晚在清代就已完成了。
综合以上各时期、各类型的文学作品看,“郭翰”是为张四姐故事最早的母题;不断的发展中,杂糅了《崔生遇仙记》与《后土夫人》的故事元素,也加入了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最终到了宝卷这一文学形式中得以定型,至早在明代中后期便已形成,最晚不会超过清中期;而至于其更名《天缘记》,那应该是得益于清中后期以来盛行的戏曲,它与明代小说《天缘奇遇》只是同名而已。
二、《贾思则》对河西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的创新与突破(25)此部分有关《贾思则》文本内容主要依据:李涛,普学旺,主编.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第三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57-309;《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主要依据: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127-164.
通过对汉文本中张四姐故事的文学流变梳理以及与彝族长诗手抄本《贾思则》在主题、内容、情节等方面的对比,基本可以说,《贾思则》是《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彝文翻译本。但既已是彝族民间文学,那么,在经过彝族知识分子、民间艺人的“编译”甚至“编创”或“改编”后,它不仅成为区别于原著的新著,更成为具有彝族特色、饱含彝族文化因子的彝族作品。
《贾思则》作为一部彝族民间文学作品,其最大的创新就是篇名、文字与体裁的变换——通过彝族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的翻译、加工,使得《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从用汉文文本的宝卷转换成了彝族文字的叙事诗;不仅篇章结构,就连格律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方步和的研究,虽然“(河西宝卷)形势活泼多样……有一定的程式,但又不受程式的限制。”(26)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4.其“开经”虽然只有12句,但却将“开经偈”“举香赞”“安坛”乃至宝卷主旨与价值等熔于一炉,而起首尾都保留俗讲格式——劝善开经和结经的七言偈,如开经:
四姐宝卷才展开,王母娘娘降临来。/天龙八部生欢喜,保佑大众永无灾。/善男信女两边排,听在耳中记在怀。/各位若依此卷行,多做好事少凶心。/做了好事人人爱,做了坏事火焚身。/做了一本开颜卷,留于(与)世上众人听。
同时,“张四姐宝卷”作为散韵结合的宝卷,道白“可念可说可发挥”(27)同②。,调子有十字调、五更调,其整个结构和格律灵活多变,唱念活泼。如:
却说这宝卷出在宋朝仁宗年间。那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东京汴梁城有一秀才,姓崔名文瑞,父亲崔员外,家豪大富,骡马成群,金银广有。不幸父亲去世,家中又遭天火,房屋财宝化为灰烬,母子二人只得讨饭为生,夜里在古庙安生。那些平日和他要好的朋友,一见文瑞如此光阴,也就远远避开。
[十字调]:崔文瑞,他本是,金童下凡,/降下世,转秀才,卖文为生/……
却说文瑞讨饭奉母,受尽苦难,这且不提。再说玉皇大帝第四个女儿,名叫张四姐,一日在斗牛宫闲坐,忽见一股恶气冲天,掐指一算,方知金童有难,在凡间受罪,不觉暗动芳心,何不借来东海龙王三太子的镇海宝贝,一来去救金童,二来和他配成夫妻。想到这里,随即下凡向东京而来。正是:手拿金钗显神通玉女要配男金童/张四姐,看凡间,冤气不散,借宝贝,不顾己,下得天宫/……
而在彝文的编译过程中,彝族知识分子遵守了彝族诗歌的格律——五言,同时“押”“扣”“连”也十分严格。彝文长诗再翻译为汉语,全诗也严格遵守了“五言”体例。如:
“天神彻埂兹,/公主有七位,/他的四女儿,/名叫贾思则。/居住天宫里,/无心在天庭,/梳妆无打扮,/离别了宫殿,/下凡来投情。
在故事内容和情节方面,《贾思则》与“张四姐宝卷”的大纲和情节完全相同,均为“下凡——遇仙——婚配——发家——宴请——中圈——救夫——迎战官兵——查身世——迎战天兵——团圆”。然而,在具体文本中,通过阅读,我们还是发现了两者之间一定的“差异”,见表2。

表2 《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与《贾思则》异同对比表
在写作手法上,彝族文本相对地弱化了故事人物心理活动,更多的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相比之下,宝卷丰富的人物内心活动更有利于刻画和丰富人物形象,也更有利于读者、听众理解人物情感;而作为叙事长诗,通过对人物对话的描述,能够将讲述者以及听众作为“当事人”,并“置身事内”,以更好地参与到故事情景之中。
尤为重要的是,彝文本通过将男主“金童”的仙家身份转化为凡人,更加突出了“仙凡恋”的故事主题。仙凡恋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对于大多数“不得善终”的仙凡婚配故事,贾思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争取,不仅保护了丈夫,还求取了善果——不论是一起返回天庭还是返回人间,夫妻喜乐团圆的结局。
再通过对女主美貌的描述和在旧居翻新过程中凭一己之力完成的描写,我们看到译者对于女性美貌和勤劳的肯定;加之贫困潦倒的凡人男主惧怕刑罚,主动招认以致身陷囹圄等情节的描写,揭示了以朱武斯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在面对困难时也不够坚决;相对于贾思则的优秀,朱武斯就略显无能、胆小;贾思则的女主形象就更加坚定和饱满了。
总之,通过译者对文体的改变——削减宝卷的开经、结经和其他情节中的细微“创新”,我们看到彝族长诗《贾思则》在主题方面对原著《张四姐打闹东京宝卷》的突破——弱化内地宝卷故事的佛道宗教性,突出仙凡婚配主题以及对美丽、勤劳、能干、勇敢、不畏强权女性的赞赏和夫妻团圆、家庭和睦的美好期盼。
三、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流传于云南彝族地区的叙事诗《贾思则》是清代中后期伴随着内地移民而来的文学翻译作品。其原著《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是在我国文学作品发展中,经过不同时期吸收了多种文学形式才最终定型。而《贾思则》这一“翻译而来”的译注文献——除了情节、内容以及语言、文字外,甚至在文体等方面都与原著发生了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源于译者对于原著的理解以及与本语体系的参照。经过以彝族知识分子(本地译者)为代表的彝族人民对原著的“编译”和创新,我们既看到了清代以来内地汉文化对彝族文化的影响,也见证了以彝族为代表的边地少数民族对于我国主流汉文化的接受、吸收与认同;同时,由于匿名译者的“创新”翻译,使得《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得以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云南彝族地区呈现,这不仅延长了原著的生命,而且还赋予其第二次生命;在扩展原著受众及读者群体的同时,也实现了文学的创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