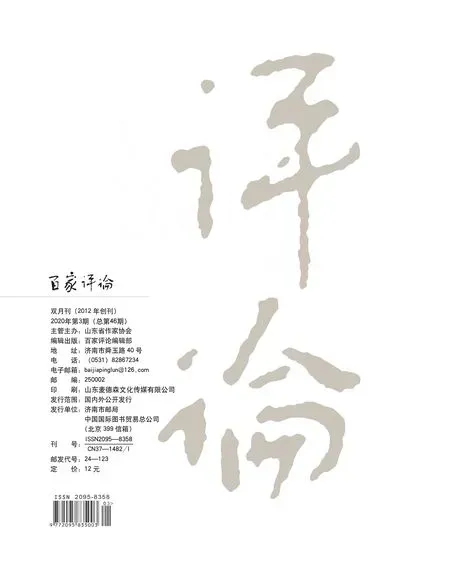“非虚构”作品多元叙事的可能性
——《中国在梁庄》的叙事研究
2020-12-14
内容提要:《中国在梁庄》是新时期中国“非虚构”文学作品中的发轫之作,本文结合“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点,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对作品的叙事模式、视角、语言进行分析,总结出该作品运用“归乡者”的经典叙事结构、“倾听者”的第一人称视角以及散文化的语言三个特色,以期对具体的“非虚构”创作实践和构建“非虚构”文学的叙事理论有一定裨益。
2010 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辟了“非虚构”专栏,相继刊发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祝勇的《宝座》、梁鸿的《梁庄》、李娟的《羊道·春牧场》等作品,“非虚构”这一在西方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文学类型,正式走入中国文坛,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几年来,关于“非虚构”的讨论长盛不衰,写作实践和评论研究一直是文学界的热点。在众多“非虚构”作品中,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无疑是发轫之作,该作品引发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荣获了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等众多奖项。梁鸿在前言中写道,“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事实上,她所要做的不仅于此,所呈现给我们的也不仅限于此。
梁鸿的梁庄系列被成为“当代乡土中国的心灵史”,绝大多数研究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分析作品与现实、与乡土中国的关系。但是,有无从其他角度进行阐释的可能?笔者认为,《中国在梁庄》首先是一部叙事性作品,它是作家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后对故乡梁庄的整体叙述,它有人物、有故事、有环境,面对这样一个备受推崇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叙事文本,可以从叙事学的基本要素出发进行解析。叙事学不仅仅是针对小说的,而是针对所有叙事性文本的。也有学者在详细论述了小说与非虚构作品的特质后认为,“‘非虚构’文学作品作为小说无疑是合格的。”在谈到“事实”的虚构性时,梁鸿认为,“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述只能是文学的,或者似于文学的,而非彻底的‘真实’。”“非虚构”作品与小说的异同,及两者与现实的距离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需要肯定的是,“非虚构”作品也需要对材料进行编码,也会用到很多小说的叙事技巧。“非虚构”是从个体经验出发进入生活现场的写作,这是这一写作形式的优势也是桎梏,如何避免流水账式的表象化的叙述,呈现出个体经验之上的真实存在,是“非虚构”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探讨《中国在梁庄》的叙事特色的意义所在。
一、归乡者的叙事模式
“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自从被鲁迅创造、使用以来,一直是乡土文学作品常用的叙述方式,似乎这是知识分子“回归”故乡的最有效的路径。梁鸿在叙述梁庄时也是运用的归乡者的叙事模式。作者最初的离去,是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求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带着强烈的离开农村的渴望,梁鸿终于通过考学离开了贫瘠的梁庄,在文本中我们能感知一个知识分子与故乡的距离。第一章“我的故乡是梁庄”是作者初回梁庄的经历:这是“我”从20 岁外出求学到现在第一次在故乡长时间地停留,在颠簸的火车上“我”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向往;亲人们浩浩荡荡地迎接、热闹的家族团聚、给母亲上坟,这些具有仪式感的场景暂时洗去了“我”的陌生感和错位感;美好的回忆与千疮百孔的现实相交织,让“我”迷失,因此必须走进村庄的内部,以完成一次自我归乡。在这一章中,作者还对梁庄的历史、宗族、人口流动作了介绍,为接下来的走进梁庄作好铺垫。作品的主体部分是作者在故乡的所见,以人物为视点分章讲述梁庄的环境、孩子、青年、中年人,以及乡村政治和道德等,面对残酷的现实、带着沉重的追问,生态破环、留守儿童、教育缺失等诸多问题被暴露出来。最后一章“何处是故乡”是作家的再次离去:乡村生活就像一个泥淖,让“我”感到沉重、乏力,又难以真正地进入;古老的村庄将以什么方式获得新生,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大课题;“我”带着乡愁似的情感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与故乡告别。自此,作者在行动上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经典叙事。
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梁鸿对自己的叙事方式有清醒的认识,在谈到如何塑造梁庄时,她说:“审视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当代的乡村‘风景’和叙事并没有超出鲁迅那一代的内部逻辑。我们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 的形象去理解并继续塑造乡村生命和精神状态,它已经变成一种知识进入到作家的常识之中。”在文本中,可以看到作者与鲁迅的遥远呼应。比如“救救孩子”这一章节,原题为“今天的‘救救孩子’”,一百年前鲁迅就在《狂人日记》中写下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显然,“今天”是与鲁迅的时代对应的,作者用这种历史的“再现”表达自己的忧虑,引起他人的警醒。“成年闰土”这一章节,写的是清立、昆生、姜疙瘩几个中年人的故事,他们卑贱地厮守、挣扎在土地上,却终究被生活碾压、抛弃,而作者就像《故乡》中的迅哥儿,心怀疼痛。梁鸿说:“我注意到,我总是不自觉地在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事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去面对村庄。”
但是,梁鸿的“归乡”又不同于与五四时期鲁迅式的“归乡”。他们的“归乡”只是形式上的相似,性质已经截然不同,如果说《故乡》《祝福》中的归乡者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梁鸿的“归乡”则是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返回。她在前言中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生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可以看出,作家对书斋里的生活产生怀疑,甚至羞耻之心,面对凋敝的、成为底层代名词的乡村,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走回去,她要完成的是返回故乡、了解乡村、呈现真实的乡土中国,是寻找生活的意义、实现自我精神的救赎。正如杨锦麟所说,“在‘必须要回去’的背后,有对自我精神和知识分子公共关怀的反思,有对故乡、大地和亲人的爱,有对乡村现状深深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出于‘爱’,而非出于‘愤’的行走和书写。”
二、倾听者的叙事视角
非虚构作品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我”的视角来讲述个人所见。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两种叙事视角的实质性区别是两者与“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第一人称叙述者生活在艺术世界之中,而第三人称叙述者置身于艺术世界之外,强调“在场”的“非虚构”作品显然第一人称更合适。但“非虚构”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与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不同,“非虚构”作品与纪实文学类似,作品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而不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叙述者。“非虚构”写作与自传式的写作也不同,自传式写作是向内的,倾听自我的声音;而“非虚构”写作是向外的,倾听他者之声。张莉在论及“非虚构”女性写作时较好地阐释了“非虚构”作品中“我”与所要表现的世界的关系,“以‘我’的视角书写‘我’眼中的世界,虽然带有‘我’的认识、理解、情感,但最终的写作目的是渴望‘我’眼中的世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即渴望‘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经验’。在非虚构写作的视野里,‘我’是大地、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也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以“我”为视点呈现梁庄,并且作者是以梁庄女儿的身份走回故乡的。“我”是村庄里的晚辈,这里有“我”的家族、亲人,这样的身份使“我”不会被村庄人拒斥;“我”以“父亲”“堂哥”“大伯”“堂婶”这些亲人的称呼来讲述他人的命运,更增加了“在场感”,为梁庄故事的真实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家呈现真实的村庄仅仅用“我”的视角是不够的,“我”携带着“先验思想”(比如可能不自觉地模范鲁迅的叙事方式),对乡村有主观判断,甚至文化偏见。如何排除“我”的主观干扰,看到村庄最真实的肌理?面对这样的困境,梁鸿选择做一个倾听者,“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是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在这种警醒意识中,作者选择了以“人物自述”的方式作为《中国在梁庄》的基本叙事方式,而叙述者“我”退居为一个谦卑的倾听者。即使是最了解的亲人,作者也不替他(她)代言,而是让人物自己讲述。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形式各样的“人物自述”:有个人对自己的讲述,比如哥哥毅志讲自己的打工史和爱情史,父亲讲自己的政治斗争史,焕嫂子讲自己的生育史;有他人对个人的讲述,比如堂嫂讲春梅自杀的缘由,父亲讲光河丧子的遭遇,哥哥讲清立砍人的过程;对于乡村教育、环境、政治等耳熟能详、具体可见的问题,作者也是让村民自己发声,如离职民办教师梁万明讲述梁庄小学的消亡,路见不平的老贵叔讲砖厂如何让百姓遭殃;有时候为了尽可能的全面,作者会让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件事,比如老支书、现任支书分别讲述乡村三十年来的权力运作,明太爷、教会大嫂各自讲述灵兰信主的事情。而“我”所做的只是记录他们说话的内容,同时也记录他们的生活背景,衣着、相貌、举止,和说话人自己都不察觉的神情。
在有关采访中,梁鸿谈到她曾反复寻找讲述梁庄的方式:刚开始是日记体,记录每天和谁谈话,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写了十几万字后发现日记体不足以呈现梁庄人现在的生活;后来,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还是不行;最后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中国在梁庄》中有近一半的内容是梁庄人的自述,有的篇章人物自述内容甚至远超过“我”的叙述。作者在交代自己的足迹或人物的背景后,通常会有一个引子让“采访”人自己讲述,比如“我让他讲讲关于砖厂的事情。站在那个机井旁边,老贵叔一手举着烟,一脚踏在那个机井的水泥座上,开始了他的讲述:”“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一番话。”这种倾听者的方式使作者文本中的梁庄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梁庄,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梁庄人的生活状态和梁庄的内在结构。
三、散文化的叙事语言
我们看到的“非虚构”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多是朴实无华的,这大概是因为“非虚构”作家并不是要通过作品展示自己的想象和才华,而是力图通过客观的叙述,从不同侧面呈现生活的真相。难道这一文类只需要“客观”,不需要个性化的语言?笔者认为,只要是文学的,就离不开语言的锤炼,对于“非虚构”写作,语言同样重要。作家阎连科评价《中国在梁庄》时说:“在优美的散文抒写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惊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这是一部具有别样之美的田野调查,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更是一扇认识当下中国独具慧眼锐思的理论之窗。从这里,正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具有“别样之美”的散文化语言正是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
梁鸿把优美的语言、女性的敏感细腻糅合进了对梁庄的叙述,这也是《中国在梁庄》成为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富有散文美的语句在文本中俯拾即是,尤其是作者在叙述记忆中的梁庄时,比如这段对河岸的回忆:“黎明,行走在寂静的村庄里,走过小路,走进树林,穿过长长的河岸。那各种鸟儿纠缠在一起的鸣叫,繁复、高亢,仿佛给人以最细微的震颤和愉悦。站在河坡的上端,朝霞茫茫,暖红色的太阳正在缓慢,没有霞光万丈的灿烂,在河水雾露的蒸腾中,一切都温润、宽广、柔和。逐渐地,河坡上出现了三三两辆的白羊和黝黑、笨重的牛群。大人在堤上蹲着,小孩奔跑者,时而发出清脆的笑声。……”(《河岸》)作者以简洁、明丽的语言描述了河岸“令人欣悦的生命力”和“阔大的自然之美”,读者不禁沉浸在作者描绘的画面里,勾起对童年故乡的怀念、对没有被破坏的美好自然的向往。进行采访时,作者常表现出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敏锐的洞察,这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比如写住在墓地的人家,“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人物的窘迫、高兴、慌张、害羞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文字背后我们还能看到温柔、善良的作者。阅读作品会发现,每篇人物采访都是一则优秀的记人散文。面对梁庄人的苦难,对乡村现实问题进行反思时,作者也很少显示出逼仄和尖锐,更多的是用回旋反复的疑问、错落有致的短句,形象地传递出自己的忧虑,以及内心的沉重。比如作者对乡村的思考,“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说,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生存境像》)这种低沉却有力的语言无法不在读者的心底激起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