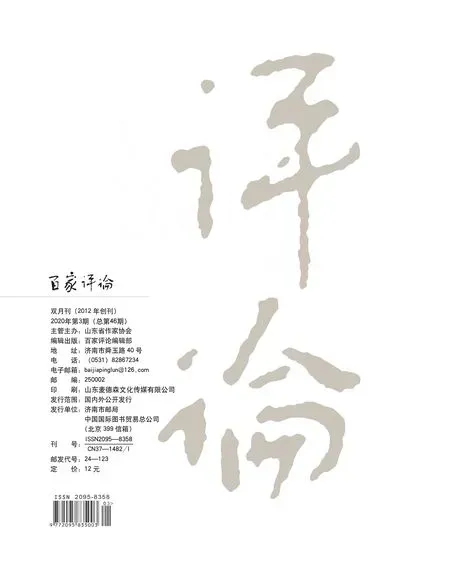毕飞宇《平原》中的叙述声音与转述语
2020-12-14
内容提要: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在叙事过程中,叙述层面话语的声音并非是一贯统一的,而是来自不同的叙述主体,呈现出多重与分裂性,这体现在声音源自的身份标识、与故事的时空距离及携带的情感态度差异等多方面。小说运用转述语的叙述技巧巧妙自然地将不同的叙述声音并置。不同声音间界线的含混,潜在的对话都使小说的语义更为丰富,使文本深具张力。而这种叙述声音的多源头性也使小说本应整体的叙述表层成为具有不同价值维度的多层叙述。
“声音”是叙述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曾经指出,“声音”这个术语在不同的研究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叙事诗学里,“声音”特指“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型人物”①。美国著名的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则从修辞的角度,对叙述中的“声音”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我想要把声音视作叙事的一个独特因素,与人物和行动等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但对叙事行为所提供的交流却有自己的贡献。”“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②正是由于声音的不同才使读者能够识别文本内不同的叙述主体。“声音”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同样决定着“故事”的呈现形态和小说的艺术与思想深度。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自发表之后,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誉,很多批评者对其思想内蕴和叙事艺术进行了深入而有价值的解读和挖掘。《平原》书写了1976 年“文革”末期这一中国特殊的历史时刻,以“王家庄”这一中国普通乡村为生命空间,展现了残酷又不乏苍凉、热烈而又孤独的乡村人民日常生存图景及人性、欲望的深渊。依作家自陈,《平原》的写作有两条核心线,“人物关系”和“文化形态”③。在《平原》中,以叙述者的全知视角对王家庄日常生活、民情风俗进行了精细还原,这种“‘乡土中国’的知识考古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民间的社会生态”④,其中有对乡村权力的洞察解析,对人性深度的探测,以及对特殊历史时空中惨烈的人性异化、压抑和扭曲触目惊心的表现。小说的叙述语言极具特色,具有明显的“讲述”性,从而使叙述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色彩,但小说的叙述声音却并非是一贯统一的,内在里呈现出多重与分裂性,从而指向具有不同时空背景和伦理准则的不同的叙述主体,而弥合这种分裂的正是在于转述语这一叙述语言技巧的巧妙运用。对此一点,研究者们还未曾关注到。本文即在细读的基础之上,探析《平原》中叙述声音的多源头性及转述语的使用,以及它给小说带来的更为复杂丰富的内涵。
一、《平原》中的多重叙述声音
先看小说中这样的两段话:
1、庄稼人不知道“国家”在哪里,“国家”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国家”是一个存在,一个指定的、很大的,无所不在的却又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样子呢?庄稼人就想象不出来了。……相对于王家庄来说,公社就是国家;而相对于公社来说,县委又成了国家。总之,“国家”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是由距离构成的,同时又包含了一种递进的关系,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关系。“国家”在上面,在期待。它不仅期待麦子,它同样期待着大米。⑤
2、(a)小吴才不是泼皮。在王家庄,小吴其实是一个最和气、最好说话的人了,对每一个人都好。……她的粗口极可爱,不仅不讨厌,不下流,相反,是不见外,是亲,完全是童言无忌的好玩。同样是一句粗话,别人说了,会翻脸,弄不好还会动手。可小吴说了不会,不仅不会,人家还会笑,乐出一脸的鱼尾纹和牙花。就觉得这孩子生错了地方,她怎么能是南京人呢,不可能哪,(b)她是我们王家庄的亲闺女哎。⑥(注:(a)、(b)为论者所加)
这两段话显然来自不同的说话人。第一段话的叙述者,从其对农民于“国家”认识局限性的说明,对“国家”绝对、相对的言说,显示了其远高于王家庄人的叙述视点。这也是小说中主要的叙述话语和声音,它是全知全能的,透析着王家庄每一个人的心理意识、隐秘和命运,总览着王家庄最深层的悸动,不管是土生土长的王家庄人,还是吴蔓玲、混世魔王这类下乡的知青、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顾后,都在这一叙述者的统摄之下,并在文本中以其丰富文雅的话语、理性的判断不时暴露出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如小说开端对麦熟大地的书写,写三丫下葬那个傍晚“出格的妩媚,无比的轻柔,袅袅娜娜”的炊烟和王大贵的笛音。而第二段话对吴蔓玲的介绍以“我们王家庄”的自称明示了说话者隶属于王家庄的身份特性,这是来自王家庄农民的声音,站在王家庄的立场上讲述身边的人与事,连王蔓玲的粗口都成了“不见外”“亲”,虽然这个叙述声音并不是来源于小说中明确的某一个人物。
小说叙述层面声音的不同,除了“我们王家庄”这样的身份标志,从叙述者与所述故事、人物的时空距离以及情感态度的差异等方面也在在昭示出来。小说中的叙述者相对于王家庄的故事存在着两种时空的距离。一种是“现在时态”的。第七章是“右派”顾后十多年来在王家庄的经历,他的思想行为的异化,他的性无知和压抑,自然是对“文革”的控诉。叙述者讲到顾后的字写得很好时说:“别的就不说吧,就说今年的春天,‘反击右倾翻案风’,那几个字就是顾后写的。”⑦“今年的春天”的时间明示呈现的是叙述者与王家庄1976 年共同的历史时空,它是“在场”性的。这样的叙述者,它也不可能预知“今年”以后的人、事的走向。另一种则是“过去时态”的。它显示的是故事整体的“后叙”性质,对每个人未来命运的了如指掌。同样第七章,顾后在端方走后,叙述者说他“把自己和端方的话重新回顾了一遍,放心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一颗地雷。顾先生睡着了,这个十年之后百分之百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十分放心地睡着了。”⑧三丫与端方的爱情悲剧也是发生于1976 年的王家庄,当三丫在合作医疗社的门口在众人的眼睛之下将端方的手拉到自己的胸脯上,叙述者直接站出来说:“三丫的举动惊世骇俗了,可以说疯狂。在三丫死后的四五年之后,王家庄的年轻人在热恋的时刻都能够记得三丫当初的举动,这是经典的举动,刻骨铭心的举动,……”⑨而此时的王家庄人固然惊骇,事实上并不可能知道三丫“一定”会死于非命,即使1976 年的王家庄已然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四五年之后”的事情,正如不可能预知“十年之后”的顾后一样。“十年之后”“四五年之后”,这些指示未来的时间呈现的叙述者与王家庄的时空距离显然远远大于“今年的春天”叙述者的时空距离。此外,还有如在混世魔王强暴吴蔓玲之后,叙述者给我们描绘了他为此受到的惩罚:“这是他的第一次。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在未来的岁月里,他的小钢炮就此变成了玩具手枪,除了滋水,再也不能屹立在自己的裤裆。”⑩对于三丫死亡的真相,三丫的哥哥红旗“永远不会知道了。”“过去时态”的这个叙述者站在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回叙审视着1976 年的王家庄,并且在情感态度上,不自觉地常常流露出自己与王家庄农民情感的、认识的、道德的差异或优势,评判、调侃与反讽。对于混世魔王整天吹口琴,“你说一个破马蜂窝你一天到晚地塞在嘴里做什么?又不甜,又不咸,混世魔王这个人少一窍。”在吴蔓玲和混世魔王之间,想当然的认为“当然是混世魔王不是他娘的东西!”都明显表现出王家庄农民式的人事的评判准则。而另一知识分子型叙述者在涉及口琴、箫、笛等乐器时所用的语言与此截然不同。当王家庄的农民听到孩子们在顾后的教导下背诵马克思主义时感到震惊,在这个叙述者眼里也是“愚昧,但满足”,认为王家庄的人很难理解顾后的悲伤和眼泪,顾后的笑也常常是“愚鲁、荒蛮”的,还能够反思混世魔王在和吴蔓玲较量中“方法论的错误”,即使对于顾后这一右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排雷”、性无知、性渴望等亦是用了调侃甚至带狂欢色彩的语气的俯视。它是具有自我权威化特色的,这种权威可以来自于更高的历史理性,以及更为丰富的知识。
由此可见,在《平原》的叙述话语层面,至少存在着两种叙述声音。一种是“现在时”的王家庄农民的声音,一种是“过去时”的历史更高阶段的叙述者的声音。这两种声音自然不是同一个层次,这正如小说的章节开端大都运用了带有先验的真理性色彩的“以天地众生开场的,代言式的群体叙事话语”,“现在时”的“王家庄人”叙述嵌入在“过去时”的叙述者叙述之中。这两种声音交互共同完成了王家庄的叙事。
这两种声音何以能够近乎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呢?一是,全知的叙述者以戏仿的方式使其叙述话语贴近于王家庄人的日常生活语言,这就与“我们王家庄”人的讲述在用词、风格等方面呈现出相似的特色,作为“存在之家”,这样的语言生动鲜活地复现了王家庄人的生存状态、思维习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文革”的时代色彩。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转述语叙事话语方式的使用。不同的叙述者在小说中都只具有叙述功能而并不具有角色功能,“我们王家庄”的叙述是被更高的知识分子叙述者以自由直接/间接引语的方式直接叙述出来的,省略了“王家庄人”这一叙述主语,这就给小说造成叙述人的含混。刘鑫认为《平原》中叙述者的身份在“‘庄稼人’和‘知识分子’间游刃有余的相互转变”,“叙述人的身份认同是复杂的”,以“上帝式”视角来概括《平原》叙述者的这种特点,显然看到了小说叙述层面上叙述声音的不同及情感色彩、价值标准的多元。然而,既处于“王家庄”的历史情境之内,又处于其之外的时空,对同一类人、物既肯定认同又嘲笑反讽,这样漂移多变的视点对于小说来说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也必然给小说带来价值混乱。即使将当下/未来这种历史时空的差异看作叙述者在现在和未来之间任意穿梭的先锋手法,依然不能解决价值视点的矛盾。而事实上,《平原》的阅读并不会产生如此的歧义。若从转述语的角度去看,则自然地解决了这样的困境。因为自由间接话语“可以使读者得以从‘出格的’语言技巧、不可接受的态度、甚至谎言中找出合理的意义,而不破坏作品或隐含作者的可信性”。而正是由于汉语语言的独特性使小说叙述话语层面的转述语虽然来自不同的叙述者,且这些不同的叙述者在文本中没有明确的标识,也可依据声音得以辨识。
二、《平原》中的转述语
直接引语式:
他犹豫了一下。他对自己说:“我看来搞错了。”
间接引语式:
他犹豫了一下。他对自己说,他看来搞错了。
间接自由式:
他犹豫了一下。他看来搞错了。
直接自由式:
不同的话语讲述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叙述距离、音响效果,以及叙述者的干预程度。“变换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成为小说家用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感情色彩及语气的有效工具。”其中,自由间接引语更是被语言和叙事学家们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因为“自由间接引语是19 世纪以来的西方小说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小说中极为常见,也极为重要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日本学者中里见敬即曾专门论述过鲁迅《伤逝》中的自由间接引语。汉语由于没有时态的变化,又常省略人称,其引语更有自己的独特性,“常出现直接式与间接式的‘两可型’或‘混合型’。”
《平原》的转述语中除了易于辨识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其叙述话语中还夹杂着很多自由直接/间接引语或“两可型”“混合型”引语,也正是它们造成了叙述的歧义。如前面所举的段2(“她是我们王家庄的亲闺女哎。”)以及“别的不说吧,就说今年的春天……”都带有鲜明的人物话语特色,如果不是省略叙述主体的自由直接引语而是叙述话语,那就应该是:她可是被那些王家庄人当作亲闺女啊。“今年的春天”也应该叙述为“那一年的春天”或“1976 年春天”。因为人称和时间指示词正是区分叙述话语和转述语的重要标志。而紧接“今年的春天”那句话,叙述者又对顾后的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尤其是“反”字:“顾后写的是魏碑,那个‘反’字写得尤其漂亮。‘反’这个字有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由‘撇’和‘捺’这两个笔画构成的,天生就有一股子杀气,静悄悄地就呼呼生风了。再加上魏碑霹雳的棱角,像大刀一样,像利剑一样,是烧光杀光、片甲不留的气概。顾后的字写得实在是好哎。”在“今年的春天”这种王家庄人叙述的语境下,这句话显然也应该被看作王家庄人的叙述,那么这几句话明显具有了自由间接引语的特色。因为其所用的语汇、用辞带有鲜明知识分子的色彩,而不是农民的语言。“间接转述语中的语汇、用辞、口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叙述加工后的混合式”。带有了叙述者的修辞、判断和情感。小说第九章开端广礼对吴蔓玲讲了大队部闹鬼的事。这一讲述并没有诸如“广礼说”之类的引导语,亦未用引号引起来,而是另起一节,直接叙述。闹鬼本来就是过去时,因此用的是“那时候”,广礼也非故事中的人物,亦无人称的变化。但从“王二虎有多少钱呢?这么说吧,你到赤脚医生王兴隆家走一趟就知道了,那三间大瓦房就是王二虎留下来的”之类的语句,有着明确的讲述对象“你”来看,这自然是广礼讲述语言的自由直接引语。“你”指称的是“听”这一传闻的吴蔓玲。否则,这样的语句就是讲不通的,叙述者不可能对隐含读者如此要求。但除了有明确对象“你”的这一句之外,讲鬼这一大段的其他话语则又可看作自由间接引语,带有“两可型”特点了。同样,前引段2 的(a)句以及“当然是混世魔王不是他娘的东西”等句子也都具有可直可间的“两可型”特色。而所有这样的叙述,因叙述主体的省略,不仅保持了无引号的直接式才有的几乎不受叙述干预的直接性和生动性,也使它与叙述语言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正是中国文学中这样的“两可型”具有的独特的双重优点。
《平原》中由于自由直接/间接引语的叙述主体大都没有具体确定的所指,除了如“我们王家庄”、“今年的春天”等少数有着明确的指称、时间及情感倾向的句子可以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声音的界线,在更多的讲述中则是界线模糊,既可以看作转述语,也可以看作叙述者的叙述。当端方发现了老骆驼的性扭曲之后,小说写道:“不能待在养猪场了,再也不能待了。这样会妨碍了老骆驼,会让老骆驼嫉恨的。”这是端方的心理再现还是叙述者的判断呢?由于“端方想”引导语的省略,便使它难以区分了。联系上下文语境来看,显然把它看作端方的心理更为恰切。其他如“王家庄的人最看不惯的就是这号人的阴,一天到晚藏着天大的心机。你这是对谁呢?谁对不起你了?谁还亏待你了?没有哇。这样的人不要指望别人对他有什么好。”“王家庄的人”既可以是自称,那就是“两可型”引语,也可以是一种他称,就成为叙述语。事实上,由于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王家庄”的自称以及时空距离、情感态度等认识到存在着不同的叙述者,《平原》中很多故事的讲述或段落、句子都具有了声音源头模糊的特征。
“当不同的片断最终能够归于可识别的说话者时,自由间接话语通过引进多重的说话者和态度的途径加强本文的双声性和多声性;而当不同片断最终不能归于可识别的说话者时更是如此。在说话者的身份含混不清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戏剧化地表明任何一段话语与其来源之间的这种不明确的关系。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对比乃是自由间接话语特有的双关效果所造成。”转述语的使用,给《平原》的叙述话语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意蕴,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话、反讽、含混等多重效果。如对于吴蔓玲和混世魔王的评价。一方面在“我们王家庄人”眼里,对这两个人物褒贬鲜明,高下立判,一个是“亲闺女”,一个“少一窍”“不是他娘的东西”。然而当历史另一端的知识分子叙述者觉得农民的笑也不免带着“愚昧”时,虽然这一叙述者并没有对吴蔓玲和混世魔王两人表现出明确的态度,人物的评判实际上已经开始复杂化,相应的有关事件也都折射出变幻的色彩,文本内充满了一种张力。即使是后来混世魔王为了离开王家庄对吴蔓玲的强暴,以及他等待并承受了王蔓玲吐在他脸上的那口痰,也不会再仅仅局限于人性“善/恶”的伦理判断了。其他的人物和事件同样如此。说话者与态度的多重性,提高了“本文的语义浓度”。何况自由间接引语体现出叙述者较强的干预性。在自由间接引语中,至少有人物和叙述者这两种声音在起作用,就形成了不同声音间的对话,而情感态度的不同,很容易产生出反讽的意义。对话、反讽正是《平原》这部小说的整体语言风格。
由于叙述话语中叙述声音的不同,我们识别出《平原》中存在着处于不同历史时空、具有不同情感倾向的叙述者。在叙述层次上,《平原》便也自然形成了具有不同价值维度的两层的叙述:外层叙述者的讲述,里面一层“我们王家庄人”的讲述。用一句话来表示小说的叙述方式,就成为:叙述者以后叙的视角叙述“王家庄”1976 年的故事同时转述了当时“王家庄人”的讲述。而叙述主体在小说中的普遍省略,也使《平原》的语言风格更为独特。
注释:
①[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 页。
②[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 页。
③毕飞宇:《〈平原〉的题外话》,《中华读书报》2012年4 月4 日第13 版。
④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