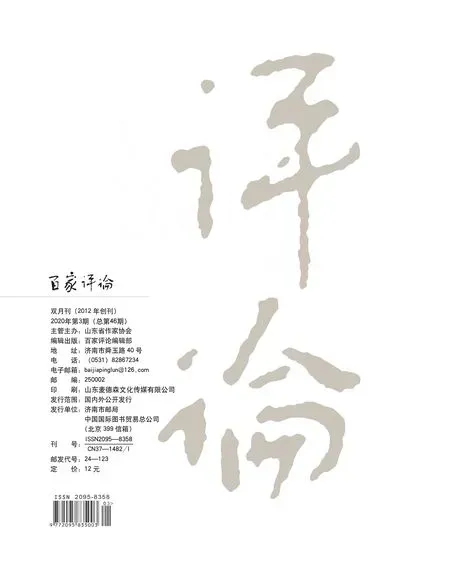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文学批评本土化建构的向度与限度
——以散文和戏剧为考察对象
2020-12-14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潮,其间持久闪烁着红色苏俄的影响;同时,它也一直在顽强地寻找自身的本土路径,建构根植于中国大地、回应现实创作的理论空间与批评实践。一方面,文学理论与批评要承担、呼应、阐释、佐证自身之外的意识形态要求;另一方面,一旦条件允许,又尽量为文学创作在艺术性、民族形式等方面开辟空间。
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潮,其间持久闪烁着红色苏俄的影响;同时,它也一直在顽强地寻找自身的本土路径,建构根植于中国大地、回应现实创作的理论空间与批评实践。一方面,文学理论与批评要承担、呼应、阐释、佐证自身之外的意识形态要求;另一方面,一旦条件允许,又尽量为文学创作在艺术性、民族形式等方面开辟空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在理论阐释上的延伸拓展,茅盾、侯金镜、魏金枝等人围绕《百合花》结构、风格、人物等展开的批评讨论,对《红旗谱》《创业史》中人物性格“传统性”的分析,都体现了理论家和批评家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因为小说文体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其讨论的尺度和空间均有限,反而在“边缘性”文体,如散文、戏剧的批评讨论中,艺术性、民族形式等问题的展开更充分,也更清晰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构文学批评本土性的向度与限度、可能性及局限性。
传统的“散文”概念泛指韵文以外的一切文体,现代文学“四分法”出现以后,对小说、诗歌、戏剧从理论上进行了文体界定,而对散文一直采取大而化之的处理,在研究中通常用“狭义”和“广义”来区分界定,狭义上的散文指表达个人情怀、体验的抒情性散文,也称作艺术散文;除此之外的叙事性文体报告文学、通讯、回忆录、议论性文章、杂文等统统在广义散文范围之内。在散文发展整体格局中,不同文体样式所占轻重、缓急往往与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艺术散文的繁荣,三十年代杂文的盛行,延安文学中报告、通讯的大量涌现,即是如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散文发展也与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延续了延安文学的“方向”,参与到“宏大叙事”的文学建构中,能够迅速反映社会生活的“写实”文体,如报告文学、通讯、特写等所占分量突出,而比较“务虚”的艺术散文式微,杂文几乎销声匿迹。
在这种文坛趋势和散文格局中,文学批评对散文的要求是充当“文学战线上的尖兵,是时代的感应神经,战斗号角”,做“鼓舞生活前进的推动力量”。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散文批评,一方面,政治激情、国家意志成为批评核心,对作品功能性、政治性的评价远超艺术审美的阐释;另一方面,在文学规范、意识形态相对缓和宽松的时期,对散文风格多样化、个性化、文体形式等艺术问题的讨论又会集中展开。同小说、诗歌、戏剧一样,散文批评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甚至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先声”,杂文的“命运”是最好的注脚。进入新中国后,杂文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百花文学”时期,杂文焕发出“生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草木篇》《小品文的新危机》《电影的锣鼓》等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反右运动中,对这些杂文的批评演变成政治运动的工具,1966 年,对“三家村”杂文的批判运动亦是如此。这种批评方式和策略是延安时期对王实味、丁玲杂文批判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过两次散文的“复兴”,一次是双百方针时期,对文学题材、风格的限制减弱,作家紧绷的神经有所松弛,涌现出一批体现个性精神、个人趣味的艺术散文,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庐山面目》、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端木蕻良的《传说》等风格灵动、文笔洒脱。但是由于双百方针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对散文艺术问题的理论讨论未能展开深入。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学界有限度地“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散文的多元化发展再次受到重视,很多学者和作家都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散文集。周立波概括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①,暗示了散文生态环境的改善,也阐明了散文创作的丰富。1961 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笔谈散文”,发表了老舍《散文重要》、李健吾《竹简精神——一封公开信》、吴伯箫《多写些散文》、师陀《散文忌“散”》、肖云儒《形散神不散》、柯灵《散文——文学的轻骑兵》、秦牧《园林·扇面·散文》等20 篇文章,探讨散文艺术问题,《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均刊发多篇谈论散文创作的文章。这次讨论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散文批评最重要的收获。散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实践与互动使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头两年里散文取得突破性发展,1961 年更被称之为“散文年”。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讨论中,散文创作中的艺术问题:个性与风格、意境与诗化、选材与主题,被广泛的关注,通过讨论,对散文创作进行了理论整合,最终形成了“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建构。新中国成立后,散文创作的主题集中在歌颂新时代、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朝鲜战争)上,这些作品在“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国家所作的伟大事业”②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艺术形态粗糙、题材狭窄、风格雷同、个性稀薄,散文在国家话语体系中“运行”,失去了个人话语空间。讨论中,很多参与者对这种散文创作的模式提出异议,提倡风格的多样化,重建散文艺术个性。秦牧认为,散文创作不应局限在“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新事”,“给人愉快的和休息”的“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也是需要的。③柯灵用“百花齐放”比喻散文园地,其中既需要“匕首和投枪”,也需要令人愉快的“小夜曲”、“轻妙的世态风俗画”,既可以是“激越的风暴”,也可以是“月光下静穆的流动”④。“自成一家”的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验、思想感情密不可分⑤,尊重作家的“喜欢”,“鼓励独创风格”,“这样才能够使文艺园地有万紫千红的气象”⑥。
现代文学以来,散文是最少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文体类别,丰富的古典文学资源和散文艺术经验为当代散文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刘白羽、杨朔、巴金都谈到古典诗歌和散文对其散文创作的重要影响。讨论中,批评文章也谈论到散文中“诗意”和意境的营造,代表了这一时期散文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探索方向。对于“诗意”的理解,有文章概括为“深刻新颖的思想和优美充沛的感情;丰富美丽的想象和耐人寻味的意境;精炼鲜明的富于美感的语言”⑦,也有理解为“诗意是鲜明的艺术形象,浓郁真实的生活气氛和旺盛的革命感情的有机的统一”⑧。两者的关系上,以营造意境为手段,达到诗情画意的艺术效果。对于诗意和意境的追求,一方面是体现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艺术旨趣;另一方面也是在当时文学环境下“无奈”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抒情成为散文的主要情感基调,为了避免作品中情感的单一、直接,散文开辟了另外一条道理,通过营造意境,把读者“带入”形象的氛围中,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联想力,从而达到具有一定艺术性的抒情感染力。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段,作品在完成功利性目的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艺术性和审美性。对意境和诗意的追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念外露、风格单一的弊端,但也导致另外一种窠臼,杨朔的“苏州园林式”结构、刘白羽的“图片连缀式”结构、秦牧的“串珠式”结构,都执着于意境和诗意的营造,结构“景-人-情”的固定叙事套路,丧失了散文本该具有的鲜活、生动的品质。
在“笔谈散文”讨论中,肖云儒的短文《形散神不散》引起高度重视。与小说、戏剧、诗歌相比,散文理论建设一直薄弱,无论是对文体形式的界定,还是文体本质的阐述,都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支撑。对于散文文体的本质,大多数观点认为,虽然散文是一种灵活自由的文体样式,“体例、题材”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但思想性“仍是它的灵魂”⑨,思想是串起材料的“珍珠”。对于“思想性”的理解各有不同,有的凸显政治性,“今天的散文更要求有特别锐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⑩;有的偏于知识性、社会性,散文“思想的光芒”是作家“对生活的见解和理想”,“揭示深刻的社会意义”。肖云儒提出散文是“形散神不散”,对文体进行了更形象生动的阐发,“形散”指取材随意,“不拘成法”;“神不散”,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珠玑,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不散”。通过“形”与“神”的比喻性表述,将散文的形式与内容的特征与关系高度凝练的予以概括。“形散神不散”也成为散文理论中最核心最基本的观念,影响至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散文讨论对散文艺术性的探索和散文创作的“复兴”都功不可没,但是讨论偏重于技巧和形式的经营雕琢,疏于对思想锋芒、艺术境界的高瞻视野,后者在当时的话语空间中依然是敏感话题,讨论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选择性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戏剧的“命运”与散文相似,创作延续了延安时期的戏剧“传统”,戏剧与政治、现实建立直接、紧密的关系,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占据舞台中心。为此,文艺管理部门一方面通过组织戏剧“会演”“观摩”活动,对创作加以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通过禁戏、戏改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的剧目加以整改。在题材上,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斗争是重点“培养”“鼓励”的创作方向,但是实际创作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现实题材戏剧因为紧密配合政治运动,作品中图解政治的痕迹明显,政治理念浮于艺术内容之上,只是在“双百方针”时期,第四种剧本的出现才使这种情况得到短暂的改观;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也因为既定意识形态的限制,缺乏穿透历史的视野和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历史剧创作因为有较大“虚构”和“想象”的空间而保持了持续的势头,历史剧创作繁盛也引发推动了历史剧理论的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都在讨论中涉及。
历史剧理论的讨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戏剧史上最重要的学术论争。五十年代初,戏剧创作中出现一种将传统曲目进行“现代”改编的潮流,一些剧作家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把当时社会思潮和政治观念直接“嫁接”到历史事件和人物上。于是,历史剧中“用耕牛象征拖拉机,喜鹊代表和平鸟等,将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治螟运动,反对美帝侵略,土地改革宣传这些内容,都缝在里面了”。这种创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杨绍萱,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改编了《逼上梁山》,用“当时”的历史观解构、重塑历史,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改编”风行的一个重要推力。杨绍萱认为,“历史剧的基本精神在于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史”,创作中“可以不管历史的时代性,只是它不免带有剧本产生时代的时代性”。首先对这种“改编”提出批评的是艾青。他认为,经过“现代”改编后的人物缺失了性格和思想,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常常前后矛盾,生硬加入的“新内涵”“新语言”反而模糊了原来故事的线索。马少波从历史观的角度质疑了人物评价的标准,他认为阶级不能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不能仅仅根据阶级出身来评定,应“与当时人民利益相结合的意义,给以应有的批判和应有的肯定”。何其芳、光未然、陈涌都参与到讨论中,批评杨绍萱的创作是“非艺术、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争双方的焦点是历史剧应该尊重历史“本来面目”,还是以“现代”立场重塑历史。如果按照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观,并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历史,对历史的“叙事”也是“当代”叙事。对“历史”的“颠覆性”改编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中就存在,田汉的《潘金莲》、郭沫若的《王昭君》即是如此。这些创作因为放置在五四启蒙的背景下而被赋予打破封建传统道德观的意义。杨绍萱的历史剧根本症结在于,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马克思唯物历史观重新阐释历史社会结构和历史事件,急迫服务政治的热情和功利性牺牲了最基本的艺术底线——对历史逻辑、常识的尊重,这种源于延安时期的戏剧“传统”在当时又是批评的“禁区”。批评者只能在“历史真实”上做文章,从学理上并不能服众,却也是迫不得已。正如傅谨所言,在没有任何的理论资源可资借用的场合,“知识”成为用以对抗流行政治理论的最后的武器。
历史剧讨论再次被提起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1959 年,郭沫若创作了为曹操翻案的《蔡文姬》,引起了文艺界对历史剧创作问题的关注,吴晗发表了《谈历史剧》《再谈历史剧》《论历史人物评价》等一系列文章,阐发自己对历史剧创作的一些观点,其间众多学者加入到讨论中,并形成两种相对的立场。对于历史剧的“真实”问题,吴晗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剧作家在不违反时代的真实原则下,不去写这个时代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原则下,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李希凡则从题材意义上理解历史剧,“它的题材是和重大的历史斗争、历史运动密切相关的”,“必须符合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在艺术处理上,“可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为情节线索”,“取材于真人真事的历史剧,应当尽量地符合基本的史实,但也必须允许虚构”。双方都认同历史剧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与虚构的统一,分歧在于虚构的尺度、统一的原则上,吴晗一方更强调以历史逻辑为依据,而李希凡一方看重艺术虚构的重要性。茅盾的长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对争论观点做了折中处理,一方面,“历史家不能要求历史剧处处都有历史根据”;另一方面,“任何艺术虚构都不应当是凭空捏造,主观杜撰,而必须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共同服务于历史剧“古为今用”的前提。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剧创作中大量运用“以古讽今”的改编策略,文艺界对此进行过一些理论探讨,对于历史剧既要有现实意义,也要以历史真实为依据这一点基本没有太多争议,可商讨的是“真实”是事实真实,还是精神真实,这两者认识差异也决定了历史剧虚构空间的大小,更深层次地决定了为政治服务的空间尺度。如果深入探究,问题甚至可能与抗日时期的文艺政策、社会思潮发生分歧,这显然不是理论讨论可以触碰的。最后,郭沫若“失事求似”的观念成为当时共识性结论,并对日后产生深远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争论可以视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续”,问题意识、理论立场都没有超出四十年代的范围,既然问题的形成和提出都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和功利性目的,那么对问题的讨论单纯放在学术范围内就不免简单。无论是事实真实,还是精神真实,都可以在学术范围内辨析,但决定“真实”与否的是现实观念,更一进步是现实政治观念,这是不容讨论的区域。同一个现实观念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古为今用”的文艺功能观是吴晗一方和李希凡一方共同分享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也取消了阐释历史和艺术表现历史的个人性视角,这种基本立场远比分歧更能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剧创作的主流观念。
注释:
①周立波:《1959-1961 散文特写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
②丁玲:《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1951 年4 卷3 期。
③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文艺报》1959 年14 期。
⑤⑩徐迟:《说散文》,《长江文艺》1962 年4 月号。
⑥秦牧:《园林·扇画·散文》,《人民日报》1961 年3 月11 日。
⑦李元洛:《散文的诗意》,《长江文艺》1962 年2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