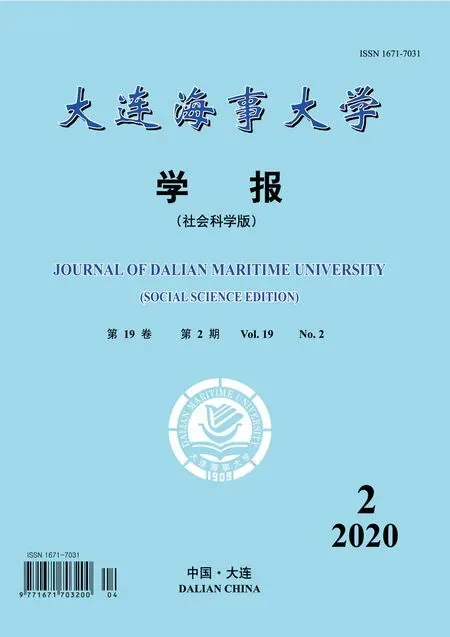论公海捕鱼自由变迁下的船旗国义务
2020-12-14王伟杰
王伟杰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问题提出
公海捕鱼自由不仅是国际习惯法规则,而且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中被明确规定。根据《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各国在公海上平等享有捕鱼自由,不受他国干预。船旗国对悬挂本国国旗的渔船在公海的捕捞活动,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管辖等方式进行管理。这种专属管辖不仅是船旗国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也是公海捕鱼自由的保障。
而随着公海自由原则从绝对自由转向相对自由,船旗国在公海享有的捕鱼自由不再毫无限制,公海捕鱼自由受到越来越多国际法的约束。[1]根据《海洋法公约》,船旗国在行使公海捕鱼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规定的义务。(1)《海洋法公约》第87条。船旗国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履行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的义务。[2]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主动加入一些全球性、区域性和分区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国家在公海上的捕鱼活动受到越来越多条约义务的限制。然而,单纯依赖船旗国履行条约义务不能根本解决当前公海所面临的过度捕捞问题,因为即使《海洋法公约》否定了公海捕鱼的绝对自由,并且规定了船旗国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的义务,此项义务对船旗国的约束也是有限的。并且,“条约不拘束第三国”原则目前仍被国际法理论和实践所承认。根据这一原则,条约对第三国不加损害也不予利益(principle pacta tertiis nec nocent nec prosunt)。[3]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很难通过渔业条约对非缔约国在公海上捕鱼做出限制。国际法并不禁止非渔业公约的缔约国国民在公海捕鱼,一些渔业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只能约束缔约国,对于条约的非缔约国却无能为力。除此之外,条约义务是否能得到有效履行也完全取决于缔约国。若作为缔约国的船旗国疏于履行自己在相关渔业条约下的义务,则仍不能有效防止其本国船只从事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 fishing)。目前,国际社会尚未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渔业专门组织来制定统一的渔业法律规范和标准,也未建立全球性的渔业执法力量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这些因素都给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船旗国在公海上的捕鱼活动还面临现实中国际法实践的挑战。第一,沿海国试图在临近其专属经济区的公海上对他国渔船实行管辖,与主张对公海渔船实行专属管辖的船旗国存在天然冲突。(2)See Fisheries Jurisdiction (Spain v. Canad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8.第二,一些区域渔业组织愈发活跃,试图通过统一本区域的公海渔业养护和管理措施,对船旗国施加更多的义务,以保护公海生物资源。第三,国际社会也通过其他措施解决实践中船旗国管辖不足的问题,例如通过采取港口国措施,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因此,明确船旗国在公海捕鱼中的国际法义务是具有意义的。一方面,船旗国在公海捕鱼相对自由下的国家义务具体内容和范围尚待明确。《海洋法公约》中关于船旗国在公海上的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义务的规定并不明确,而不断发展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裁判,为明确这些义务的具体内容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新的国际法实践是否能对当前船旗国对本国渔船在公海捕鱼的专属管辖产生影响,也值得深入检视和探讨。
本文通过重新审视公海自由原则的起源及发展,分析当前国际法实践对船旗国在公海上的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义务的影响,并考察《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国际渔业公约、区域和分区域的渔业协定对船旗国义务的规定,能否解决船旗国专属管辖在处理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上的问题。
二、公海捕鱼自由的历史变迁
公海捕鱼自由被学者认为是阻碍公海生物资源养护机制变革的首要因素。[4]今天,公海鱼类不再被认为是取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因为公海生物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每个国家在公海上的捕鱼活动都会影响其他国家在公海上的利益,一国对公海生物资源的过度捕捞会造成其他国家利用公海生物资源数量的减少,所以公海捕鱼的绝对自由已不复存在。
(一)公海捕鱼自由的起源
不同于陆地领土,国家不能通过持续占领的方式取得公海的主权。1609年,被誉为近代“国际法之父”的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其著作《海洋自由论》中主张,海洋不能被任何国家占有。在书中,格劳秀斯提出:“适用于航行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捕鱼,即海洋对所有人开放,所有人都享有在海上捕鱼的自由。”[5]在他看来,海洋是人类的共有财产,应当被所有人共同使用。在《捕获法》中,格劳秀斯说道:“大家一般都会承认很多人在陆地上捕猎或者河里捕鱼,森林里的野生动物和河里的鱼就很容易被捕尽打绝;而对于海洋,这就不适用了。”[6]格劳秀斯的结论显然是以公海生物资源不会枯竭为前提。尽管当时英国学者塞尔顿(Seldem)对其观点表示反对,他于1618年发表《闭海论》,主张英国有权占有周围的海洋,其观点成为日后沿海国主张领海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公海自由逐渐成为主流。公海的法律地位在19世纪被多数国际法学者所接受,并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
(二)从公海捕鱼绝对自由到相对自由
然而,进入20世纪,随着越来越先进的捕鱼技术出现,捕捞方式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7]同时,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公海捕鱼,导致公海渔业资源面临过度捕捞。
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公海公约》。《公海公约》第2条规定,公海对各国一律开放,任何国家不得有效主张公海任何部分属其主权范围,并列举了国家在公海上享有的自由,即国家享有航行自由、捕鱼自由、敷设海底电缆与管线之自由以及公海上空飞行之自由。此外,国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3)《公海公约》第2条。
1982年《海洋法公约》再次确认了国家在公海上的自由。虽然公海自由仍然支配着公海上的秩序,但“自由”的含义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自由”不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而是需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明确《海洋法公约》中公海“自由”的含义及范围是确定船旗国在公海上义务的前提。公海上,某些行为已经被《海洋法公约》明令禁止,这意味着国家不得允许其国民在公海上从事某些活动。例如,《海洋法公约》规定在公海上各国有义务禁止和制止贩卖奴隶、海盗、非法贩卖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物质等活动。(4)《海洋法公约》第99、100、108条。并且,《海洋法公约》很多地方对船旗国利用公海做出限制。《海洋法公约》明确要求船旗国在利用公海时应当考虑他国的利益,如禁止污染海洋。(5)《海洋法公约》第94条。至于公海捕鱼自由方面,《海洋法公约》第87条在规定公海捕鱼自由的同时,规定该自由受第二节所列条件的限制。《海洋法公约》第116条规定得更为明确,“所有国家均有权由其国民在公海上捕鱼,但受下列限制:(a)其条约义务;(b)除其他外,第63条第2款和第64至第67条规定的沿海国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和(c)本节各项规定”。同时,由于语言的含义和解释也在发展,《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公海捕鱼之“自由”,也随着环境变化发生改变。有学者认为,在《海洋法公约》中,公海上捕鱼是国家的一项“权利”,而不是无限制的行为“自由”。“权利”和“自由”的区别就在于:权利需受条件制约,以履行国际法下国家义务为前提,这和国家行为上的“自由”不同。[8]
《海洋法公约》中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的规定并不完善,一些国家试图订立更加有约束力的条约,这些条约义务进一步限制了缔约国在公海捕鱼方面的自由。1995年《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试图弥补《海洋法公约》对公海鱼类养护和管理的不足。《鱼类种群协定》对公海自由原则的限制明显大于《海洋法公约》。该协定明确了船旗国的责任,包括有关船舶注册和登记、授权以及协议的遵守和执法的责任。虽然该协定对非缔约国不具有约束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先没有签署和加入的国家,近年来也主动加入了该协定。这反映出《鱼类种群协定》虽然对船旗国做出了限制,但符合该国的长远利益。从《海洋法公约》到其他全球性、区域性的渔业条约对船旗国义务的规定来看,船旗国已经不再享有绝对的利用公海生物资源的自由。在这些条约下,船旗国的义务更加详细。无论是国际法理论还是实践,公海捕鱼自由都逐渐受到约束。公海捕鱼自由内容的变化是船旗国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义务变化的原因。
三、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中的挑战
由于船旗国对公海上悬挂本国国旗从事捕鱼的渔船拥有专属管辖权,因此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主要依赖船旗国对本国渔船的实行措施。然而,船旗国对本国渔船的专属管辖会导致船旗国不能对本国以外的渔船的违法捕捞活动进行监管,这就给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带来诸多挑战。此外,国家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的义务尚未构成国际习惯法规则,目前主要依赖船旗国履行其所加入公约的条约义务,这也造成一些区域渔业组织在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方面陷入强制力不足的困境。
(一)船旗国专属管辖带来的挑战
《海洋法公约》规定,国家可以对公海上的某些活动实行普遍管辖。公海上的违法活动诸如海盗行为,危害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其他国家对海盗行为可以在有合理怀疑的条件下,实行普遍管辖。(6)《海洋法公约》第105条。而公海上的过度捕捞以及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的危害性是否能与上述行为相提并论,是需要慎重讨论的问题。目前,在公海上,除非有条约特别规定,否则国家不能对非本国国籍渔船实行管辖。
在公海上,只有船旗国与悬挂本国国旗的渔船有最密切和直接的联系。Tanaka教授认为,船旗国专属管辖权原则具有双重作用。第一,这项原则防止其他国家对在公海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进行任何干涉。这样,船旗国专属管辖权原则确保了船只在公海的活动自由。第二,根据这一原则,船旗国有责任确保悬挂其国旗的船舶遵守关于在公海活动的国内法和国际法。[9]因此,船旗国在排除其他国家在公海对本国渔船的管辖后,可以要求本国渔船遵守其国内法和对本国生效的国际条约。
国家对本国籍渔船进行管辖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一环。在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方面,船旗国对本国渔船的管辖权体现在多个方面。即使船旗国由于某些原因尚未加入某渔业公约,也可以通过制定国内法律和规章的方式,要求从事公海捕鱼的本国渔船遵守国内法下的具体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23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远洋渔业的,应当经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远洋渔业企业资格,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或者参加的有关条约、协定和有关国家的法律。2019年8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我国当前《渔业法》内容做了大幅修改和补充。例如:根据捕捞强度和资源可承受程度,确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渔业船舶进出渔港应当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航次计划、适航状态、渔业船员配备、渔具及渔获物等情况,并服从其调度和监督管理。[10]
现实中,船旗国监管不力是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活动,阻碍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船旗国对本国渔船公海作业监管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监管,这导致船旗国在履行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义务时存在漏洞。《海洋法公约》中规定船舶应当与船旗国有真实联系,但在现实中,是否允许公海渔船注册取决于船旗国国内法,目前尚无国际统一标准。在国际法下,渔船与船旗国间的“真实联系”并不影响渔船国籍的有效性。[11]308-310这会鼓励一些从事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的渔船通过在相关国家注册、转换国籍来逃避监管。
(二)《海洋法公约》中船旗国义务需要明确和加强
船旗国对公海生物资源进行养护和管理是《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一项条约义务。《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在享有公海上捕鱼自由的同时,有为其国民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措施的义务,并要求各国在养护和管理公海区域内生物资源方面进行合作。(7)《海洋法公约》第117、118条。然而,《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强调船旗国的具体义务。《海洋法公约》中关于船旗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义务规定过于笼统,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有学者认为,《海洋法公约》中有关公海养护的条款是开放性条款,这些条款项下的养护义务的模糊性和分散性,使公海自由原则成为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阻碍。[12]还有学者认为,《海洋法公约》创造了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的国际法律体系,但是没有制定明确、具体的法律措施。从《海洋法公约》条款中的“一般接受的规则和标准”、“船旗国和沿海国合作”等用语可以看出,《海洋法公约》将具体措施交由其他国际性或区域性条约处理。[13]为弥补公约在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上的不足,越来越多的公海渔业公约将船旗国的责任具体化。例如,《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试图促进船旗国履行对本国渔船的责任,提高船旗国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的有效性。其中措施包括,要求船旗国建立渔船档案,各缔约方进行合作,加强船旗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信息交流等。《港口国措施协定》中规定,船旗国缔约方有义务在按照本协定执行的检验中与港口国合作。根据《港口国措施协定》,船旗国若收到港口国的检验报告,有理由相信有权悬挂其国旗的船舶从事了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或支持此类捕鱼的相关活动,一旦获得证据,应当采取执法行动,并将处理情况报告给其他缔约方和有关港口国。(8)《港口国措施协定》第20条。尽管港口国有权采取检查、拒绝入港等措施,但对于悬挂他国国旗渔船的最终处理权仍然归于船旗国。这些渔业公约虽然对船旗国义务的规定更加具体,但缔约国数量有限,远不如《海洋法公约》影响广泛。
(三)尚未构成习惯法或“对一切的义务”
除了条约义务外,船旗国的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义务,在目前并不构成国际法中“对一切的义务”(obligation erga omnes),或国际习惯法。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案”中指出,在国际法下的义务分为两类:对具体国家的义务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对一切的义务”从根本上不同于现有的对另一个国家的义务。(9)See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0.而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负有义务,通常是某些事项是所有国家的关切,所有国家对其保护都有法律利益。具体而言,确保本国渔船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遵守其法律,是船旗国对沿海国的具体义务,而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涉及所有国家的利益,是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目前,在国际法院中承认的“对一切的义务”包括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一些国际人道法规则。(10)See East Timor (Portugal v. Australi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5, p. 102, para. 29; see also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Second Phase,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0, p. 32, para. 33.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涉及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与“对一切的义务”有相似之处,并且《海洋法公约》也多次提到照顾全人类的利益和需要。(11)《海洋法公约》第140条。虽然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并不妨碍其他国家的捕鱼自由,但此类捕鱼方式无疑会对公海渔业资源造成极大破坏,对其他国家从公海获取利益产生实质的损害。船旗国确保本国渔船遵守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规定,是否构成国际社会的“对一切的义务”,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目前,将保护环境作为强行法规则并没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但有理由相信,船旗国实施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
若船旗国实施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那么,如果船旗国违反《海洋法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应当对谁承担责任?哪个国家有资格提起国际诉讼?《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第1款规定,“受害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有权按照第2款在下列情况下对另一国援引责任:(a)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承担的、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义务;或(b)被违背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理论上,当一个国家违反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的义务时,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均可提出诉讼。但国际实践中,尚未有国家将此类案件提交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此外,《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的相关措施是船旗国应当履行的“适当注意”义务。对于“适当注意”义务,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都没有对其内容做出具体定义。这是由于在不同的环境下,国家的“适当注意”义务是不断变化的。在2015年海洋法法庭咨询意见中,法庭已经指出,“适当注意义务随着变化而发展”(12)See Advisory Opinion of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 (SRFC),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2015.。也有学者对“适当注意”义务进行归纳总结,列出其应当遵守的几个关键要素,如制定合理的国内法履行其国际义务、签署相关国际渔业公约等。[11]323-324
(四)区域渔业组织措施强制力不足
区域渔业组织是各国通过合作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的最典型的方式。《海洋法公约》第118条规定了各国在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方面的合作义务,即各国在开发公海上相同生物资源时,或在同一区域开发不同资源的国家,应在适当情况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组织。《鱼类种群协定》要求各国应直接地或通过分区域、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合作,以确保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分区域、区域措施的遵守和执法工作。区域渔业组织通常以区域渔业协定为法律基础,区域渔业协定的内容较之于《海洋法公约》,对船旗国义务的规定更为详细具体。如今,除北冰洋外,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都设立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负责本地区公海渔业捕捞养护和管理。
一些区域渔业组织对本地区从事公海渔业的缔约方渔船做出资格限制,要求在没有得到主管机构授权的情况下,禁止缔约方的悬挂其旗帜的渔船在公约区域捕鱼。只有在缔约方有能力对悬挂其旗帜的渔船行使其在本公约与国际法下的责任时,方授权这类船舶在公约区域内捕鱼。(13)《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第25条。
区域渔业组织内部还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具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区域渔业组织的缔约国应确保悬挂其国旗的渔船在该公约管辖区域内进行生产时,遵守公约及其委员会通过的所有养护和管理措施,其船舶不得从事破坏这类有效措施效力的任何活动。这些具体措施通常包括:根据科学信息决定允许渔获量,决定进行或不进行捕捞的总体或具体位置、进行或不进行捕捞的期间、可保留的渔获最小捕捞规格、使用的渔具类型和技术或捕捞方式等。有的区域渔业组织要求缔约方报告每一渔船按照公约要求的所在信息,在公约区域内的公海区域捕捞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渔船,使用最新实时卫星报告仪器,并且,使用这类传送仪器的标准、技术要求和程序应当由委员会确立。某些区域渔业组织在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方面也做出了相关安排,在公约区域内,缔约国可授权其他缔约国登临悬挂本国国旗的渔船。《鱼类种群协定》第21条第1款规定,区域渔业组织的缔约方可通过经本国正式授权的检查员根据第2款登临和检查悬挂本协定另一缔约国旗帜的渔船,不论另一缔约国是否为该组织或安排的成员或参与方。有学者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公海登临检查措施确实有效地打击了渔船在公海的违规行为,未来缔约方公海登临检查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区域渔业组织所采用。[14]
尽管如此,区域渔业组织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公海捕鱼自由和《海洋法公约》下船旗国的权利。例如,《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第2条规定:“本公约任何条款均不应对任何缔约方有关其领水界限或根据国际法对其渔业管辖范围方面的权利、要求或观点造成影响。”《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第4条规定:“本公约不损害各国在1982年公约下权利、管辖权和义务。对本公约的解释和应用在范围上与1982年公约和协定相一致。”在区域渔业组织框架下,缔约方仍然享有《海洋法公约》和一般国际法下的权利。
四、加强船旗国义务的具体措施
通过措施加强船旗国义务,有助于弥补船旗国在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方面的不足。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国际公认标准与最低标准、制定软法规范对船旗国履行义务施加影响,以及加强非缔约船旗国的合作义务等。
(一)建立国际公认标准与最低标准
区域渔业组织在促进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标准建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建立起国际统一标准,至少是最低标准,是确保船旗国履行义务的有效措施。前文提到,目前国际社会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并无统一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但这不能否定未来设立国际统一规则和标准的可能性。《海洋法公约》中并未直接规定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的国际标准,但规定了各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决定可捕量和制定其他养护措施时,应当考虑任何一般建议的国际最低标准,不论是分区域、区域或全球性的。(14)《海洋法公约》第119条。这为区域渔业组织制定国际公认标准和最低标准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区域渔业组织制定本区域内养护和管理措施和标准时,并不排斥吸收其他区域渔业组织已经实行的标准和措施。《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第3条规定:“由一个或多个已经成立或可能成立的、依国际法运作并按照公认国际标准管理此类捕鱼的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所通过的、旨在对鱼类种群进行可持续管理的养护和管理措施……”这表明“公认国际标准”对区域渔业组织制定相关措施具有影响。《鱼类种群协定》中规定的预防方法和生态系统方法等,如今广泛地被区域渔业组织所接受。一些区域渔业组织已经开始采用很多新的管理方式,规定各缔约国根据相关公约和任何国际认同的标准、建议的方式和程序应用这些方法。同时,根据区域渔业协定建立起的委员会,还制定了具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并确立了一般建议的捕捞行为国际最低标准。一些制度性措施,如登临检查以及派遣观察员措施等,也已经被很多区域渔业组织所采纳。
(二)制定软法规范对船旗国履行义务施加影响
软法规范的发展也是影响船旗国履行其义务的重要因素。出于各种原因,如缺乏能力和资源,对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缺乏正确认识,或基于本国的成本考虑等,[15]船旗国在面对是否加入全球性、区域性渔业公约时都十分慎重,因此,软法规范在促进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相较于条约,软法规范具有灵活性。[16]一些软法规则是对某些条约的细化或补充,并且很多软法规范能够迅速反映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需要。《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减少延绳钓渔业中误捕海鸟国际行动计划》《鲨鱼养护及管理国际行动计划》《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等软法规范中的许多措施是具体的规则、技术性标准,并且通常采用建议、指导规范的形式,相对于严格义务的条约,船旗国更容易接受。此外,一些渔业公约和协定中也试图纳入某些软法规范。如《港口国措施协定》第5条规定,酌情考虑纳入《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国际行动计划》中的规范。
(三)加强非缔约船旗国的合作义务
长久以来,非缔约方的拒绝合作一直是渔业协定得到有效执行的障碍,因此,在渔业协定中,也非常重视非缔约方的地位,专门对非缔约方做出规范。一些渔业公约和协定鼓励缔约方和非缔约方进行合作。例如,《港口国措施协定》第23条规定:“各缔约方应鼓励本协定的非缔约方成为缔约方并/或采用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的法律和规章并实施相一致的措施。同时,各缔约方应采取与本协定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相一致的公正、非歧视性和透明的措施来制止非缔约方妨碍本协定有效执行的活动。”《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第8条规定:“各缔约方应以符合本协定和国际法的方式合作以使有权悬挂非缔约方旗帜的渔船不从事损害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效力的活动。”《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第8条规定:“缔约方应采取与国际法相一致的措施,制止有权悬挂非缔约方旗帜的船舶从事有损本协定有效执行的活动。”也有某些区域渔业条约明确提出对非缔约方进行限制。例如,区域渔业组织的缔约国可以限制不履行本组织船旗国义务的非缔约国渔船进入其港口或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国家对非缔约方的制裁措施也是促使非缔约方进行合作的重要手段。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欧盟对某些船旗国实行的贸易措施。[17]2010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欧盟打击非法捕鱼规则》,以贸易措施作为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的手段,要求船旗国改善对本国渔船的监管或完善其国内法律法规。根据欧盟的规定,欧盟可以限制进口来自不符合欧盟渔业政策和标准的国家的渔业产品,待这些国家改善本国监管、完善法规之后再解除这些制裁措施。对于某些不符合《欧盟打击非法捕鱼规则》中标准的国家,欧盟先以“黄牌”对该国发出警告,再根据该国改善的情形进行评估。如果该国在获得“黄牌”警告之后没有在期限内完成符合欧盟标准的改革,则该国将被“红牌”警告。收到“红牌”警告的国家的渔获产品将被限制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此类措施实施后取得明显的成效,一些船旗国完善了本国法律法规,加强了对其渔船在公海捕捞的监管。泰国、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因其各自渔业法规和监管措施不力遭到欧盟的“黄牌”警告。其中,泰国已经成功解决了渔业非法捕捞问题并弥补了行政管理缺陷,欧盟于2019年撤销了对泰国的“黄牌”警告。
五、结 语
公海捕鱼自由从绝对自由转变为相对自由,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船旗国对公海捕鱼活动的专属管辖。《海洋法公约》中有关船旗国的义务规定比较笼统,因此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渔业协定逐渐将船旗国的义务具体化。但这些渔业条约并没有试图削减公海上船旗国的专属管辖,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促进船旗国间的合作。通过区域渔业组织,加强对船旗国的管制,制定更加详细的船旗国义务,同时也从非船旗国角度采取措施,要求船旗国履行义务,这些措施都使船旗国在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中的义务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