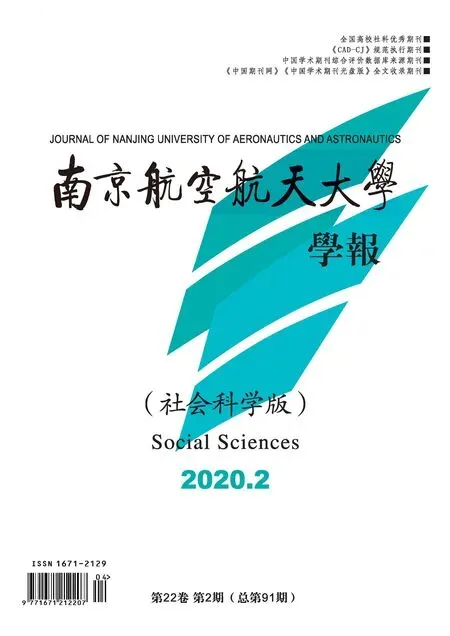直面现实生活:《神圣家族》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
2020-12-13任帅军
任帅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9月—11月合写的《神圣家族》,在他们科学世界观的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他们指出,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辨唯心主义的本身来讨论问题,是得不出任何正确结论的。因为他们从自我意识出发,用绝对的观念来代替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的人,从而抽象出一种独立存在的本质,并把它看成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这种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和研究进路就不正确,得出的结论必然也会走向谬误。鲍威尔没有看到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人,或者说,没有看到人要过现实生活的实践要求。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鲍威尔所鼓吹的思辨唯心主义已经成为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现实生活的代名词。实现人的解放,就要把人从思辨唯心主义的束缚中拯救出来,让人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从现实生活出发批判思辨唯心主义,不仅能彻底揭露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宗教本质,而且还能确证现实生活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理论地位。
一、思辨唯心主义成为脱离现实生活的代名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思辨结构的秘密”中,从认识论的高度批判了存在于思辨唯心主义之中的秘密。该章节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艺术表达。他们批判了塞利加①在中央编译局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用的是“塞利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中,“塞利加”又译为“施里加”。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一书的评论。马克思指出,塞利加“对《巴黎的秘密》所作的批判性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结构即黑格尔结构的秘密”,“塞利加先生对《巴黎的秘密》的论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具体运用”[1]276。在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塞利加的观点,而是马克思如何看待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结构。马克思以一般的果品和个别的果实的关系为例,艺术性地揭示了“思辨结构即黑格尔结构的秘密”,不仅颠覆了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而且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企图用绝对观念取代现实生活的妄想。
思辨唯心主义用绝对的观念取代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经历了三个相互取代的“秘密”过程。首先经历了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思辨唯心主义先从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品”这个一般的观念。“果品”这个一般的观念就成为独立于现实生活中各种水果的代名词。其次经历了从一般到本质的过程。思辨唯心主义想象“果品”这个被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是客观地存在于作为主体的我之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个别存在物的真正的本质。于是他们就用思辨的语言来宣布“果品”是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个别存在物的“实体”。这些个别存在物对于“果品”而言都是非本质的。它们的本质的东西并不是人们用感官和经验直接感触到的现实存在物,而是思辨唯心主义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并强加于它们的本质,即鲍威尔等思辨唯心主义者的观念的本质——“果品”。最后经历了从本质到样态的过程。此时,鲍威尔等人就宣布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个别存在物是“果品”这个实体的单纯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虽然感觉告诉人们,可以通过经验把苹果、梨、草莓、扁桃区别开来,但是理性却告诉青年黑格尔派,这些不涉及本质的感性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在苹果、梨、草莓、扁桃中看到了共同的东西,在各种具体的水果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简单存在形式的水果,即作为样态的水果只能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是“果品”这个“实体”。
“思辨结构的秘密”的要害在于,作为主体的人必须不仅设想一般是脱离个别而存在的本质①用哲学术语说,叫“实体”。,而且设想个别只不过是一般的存在形式②用哲学术语说,叫“样态”。。并不是你或其他的任何人,从个别中抽象出了一般,而是一般本来就先于个别而存在。与对象的这种二重性相适应,你的认识能力也是二重的,即一方面是被经验感觉所支持的理智③请注意,理智在《小逻辑》中文版翻译成“知性”,黑格尔是把知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否定的理性(康德的逻辑)、思辨的理性(黑格尔从费希特那里得来的逻辑)看作逻辑学的三个阶段,而我们通常所说的“逻辑”实际上仅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知性的逻辑,还没有达到康德“否定的理性”的逻辑或辩证逻辑,更不用说黑格尔本人那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理性的逻辑即“思辨的逻辑”了。或许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知识背景,所以尽管马克思举例一般的果品和个别的果实的关系的论述很重要,但是一直没有被准确地把握过。而这个例子的讨论又构成《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探讨辩证法问题时的背景。,另一方面是纯粹思辨的理性。由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关键是体现本质的一般,因此马克思就说:“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实体观点出发那样,说梨是‘果品’,苹果是‘果品’,扁桃是‘果品’;而是相反,必须说‘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梨,‘果品’把自己设定为苹果,‘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扁桃;把苹果、梨、扁桃彼此区别开来的差别,正是‘果品’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果品’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品’就不再是无内容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品’都给自己一个更为发展的、表现得更为鲜明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又是活生生的统一体。”[1]278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作为绝对观念的“果品”把自身设定为各种特殊的果实,从而使这些个别的果实成为“果品”在生活过程中的特殊环节。这样绝对观念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现实生活。如果你不能把作为绝对观念的一般当成是造物主,那么你就不能理解它像母亲一样生出了生活中的个别作为自己的孩子。由于一般(在举例中是“果品”)体现了绝对观念的本质,所以生活中的各种特殊(在举例中是“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人的感性的理智有意义,而且对通过思辨的理性认识一般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思辨的逻辑中,正如千差万别的普通果实只不过是统一的果品的不同的生命表现,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也不过是绝对的精神在展开自身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环节。这种唯心主义的方法,“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1]280黑格尔认定“实体即主体”,在于要把精神或观念独立化、绝对化和实体化,即把从个别中抽象出来的一般作为绝对存在的本质,并把它作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而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特殊的个别只不过是一般这个独立存在的本质的有差别的展开环节。因而马克思接着说:“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品’都给自己一个更为发展的、表现得更为鲜明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又是活生生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把每一种果实全都消融于自身中,又从自身产生出每一种果实”[1]278。在这里,黑格尔所期待的“果品”“概括”都不是这个词的日常含义,而是他自己赋予的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总体”含义。
根据黑格尔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既是绝对实体又是绝对主体的过程的做法,马克思认为,只要抓住“实体即主体”的逻辑,就不难理解,现实生活只不过是绝对精神或上帝展开自身的一个环节。因为生活只能来自“绝对”,而且人活着的时候离不开“绝对”、死后又必须回到“绝对”。可见,黑格尔不过是以逻辑的方式说出了圣经中用表象说出的同样的真理①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即“绝对知识”一章中承认了这一点。所以,思辨的结构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把整个宇宙理解为宇宙中作为唯一的主宰者。这个主宰者既是绝对主体,也是绝对实体。。但是黑格尔善于用思辨的手法来迷惑众人,用思辨的论证来取代现实的生活。一方面,他借助感性直观和表象把从个别到一般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是作为绝对实体和绝对主体相统一的本质所经历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常常在对本质的论述中做出把握本质的样态,即个别作为一般展开其特殊性的过程的叙述,使人误把具有思辨性的绝对观念看成是现实的,并把现实生活看成是思辨的。这就是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通过理性制造出了感性事物,也就是虚假的感性事物,从而把自己表现出来。这一过程就是把现实生活抽象化为绝对观念的过程,也就是用绝对观念取代现实生活的过程。
二、现实生活从思辨唯心主义中破茧而出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思辨唯心主义绕不开的理论桥梁和思想中介。费尔巴哈的贡献在于,他用“人和自然的关系”代替了黑格尔的“实体和主体的关系”,从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绝对的观念世界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促使他们开始关注市民社会中底层群众普遍贫困的生活状态。在《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二节“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a)欣里克斯②在中央编译局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用的是“欣里克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中,“欣里克斯”又译为“辛利克斯”。第二号中,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把主体变为人,把客体变为自然,对于他和马克思摒弃思辨唯心主义绝对、抽象、空洞的说教,重新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揭示人的关系的丰富性,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对此,恩格斯毫无保留地指出,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激起了批判的魁首的怒火”“批判在三月里读了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这次阅读的成果,同时也是认真阅读的标准,就是那篇驳斥欣里克斯教授的第二号论文”[1]294。
在马克思通过举例一般的果品和个别的果实的关系,指出思辨唯心主义想用绝对观念取代现实生活时,恩格斯就认为,费尔巴哈之所以能用“人和自然的关系”取代黑格尔的“实体和主体的关系”,是因为费尔巴哈的理论是用来解释当时市民社会生活的实践形态。这种生活所揭示的是直接的自然和现实的人,是世俗社会的具体利益,反映了地上的尘俗世界。费尔巴哈这样做就跳出并超越了黑格尔的逻辑的秘密。然而,以青年黑格尔派为首的思辨唯心主义却极力鼓吹“思辨结构的秘密”,并用这种秘密批判和取代现实生活。所以,恩格斯在代替以“批判”自居的青年黑格尔派宣告秘密已被揭露时,指出,“从未逃出黑格尔派考察方式的樊笼的绝对批判,在这里对着它的监狱的铁槛和围墙狂呼乱叫。‘简单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鄙弃。‘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历史的惊人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突然把它们取代了”[1]294。
在这里,恩格斯对“批判”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滥用的那些范畴:‘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历史的惊人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与精神的斗争’等等。”[1]295通过恩格斯的考察就能发现,思辨唯心主义用无限的自我意识取代人本身和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使自身在费尔巴哈面前威信扫地。费尔巴哈用他的反形而上学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使现实生活从绝对的观念世界中破茧化蝶,脱颖而出。费尔巴哈认为,观念并非是一切的总和。人才是主体,自然才是人确立自身存在意义的对象。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他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建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展开了关系的现实丰富性,而且还创造着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历史。然而,鲍威尔等人却以批判自居,把自己当成绝对精神,而把包括人在内的现实生活当成了“无限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消解了人直面现实生活的意义。
恩格斯在认识到费尔巴哈的贡献时,高度评价了他对推动思辨哲学解体的积极作用。恩格斯认为,在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所做的天才阐述以后,思辨唯心主义再用绝对的自我意识取代现实生活本身,然后把生活于其中的人当作无关紧要的废物,当作绝对观念展开自身的一个环节来否定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它并没有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解体做过任何贡献,相反还使思辨哲学从论证绝对精神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退回到了时刻以“批判”自居的主观唯心主义。然而,费尔巴哈彻底否定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自吹自擂。他不仅否定了把自然视为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做法,而且还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证代替了对绝对的精神或观念的鼓吹。对于费尔巴哈来说,黑格尔的“实体”的秘密就是自然界,而“主体”或自我意识的秘密就是人。费尔巴哈揭穿了黑格尔体系的秘密,也就摧毁了仍然困在黑格尔樊笼中的“绝对批判”的那些范畴。
在运用这些范畴取代现实生活本身时,鲍威尔跟黑格尔一样,把历史当成绝对观念在地上的行进,而人则被绝对观念当成了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黑格尔甚至认为,“理性”利用人们的“热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把这称为“理性的狡猾”。然而,人是作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物质统一体,以自然为对象同自然发生关系,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正是费尔巴哈否定和超越黑格尔、鲍威尔的地方。既然费尔巴哈已经把主体变为人,把客体变为自然,而且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那么,整个唯心史观也就崩塌了。并不是历史把人当手段,而是人在创造历史。历史只能是按照人类自己的目的来发展的人的活动的展开过程。对此,恩格斯专门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断:“在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之后,唯有‘批判’还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一个范畴,变成一整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最后的求生之路,因为对惊慌不安和受到查究的神学的非人性说来已别无他路可走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95
需要看到,费尔巴哈虽然把人从绝对观念中解放出来,却又重新陷入到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当中。他认为,人是凭借自己的本质来认识自然,而这种本质就是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物质统一性,所以人对自然的认识只不过是自然自己认识自己而已。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识到了费尔巴哈理论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局限于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而停滞不前。他们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学会了与自然打交道,而且还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对于人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历史的活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开始创立的[2]。“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95,表达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着手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在这部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的理论著作中,他们以费尔巴哈为理论武器展开了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而且彻底超越了神学。因此,是费尔巴哈解开了“各门学科的奥秘”,而不是绝对的批判解开了任何奥秘;是费尔巴哈超越了“唯灵论和唯物主义原先的对立”,而绝对的批判却“重新以最令人厌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且让‘基督教日耳曼精神’获得胜利”[1]296。
三、从现实生活出发批判作为宗教观的思辨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思辨唯心主义,是把自我意识宗教化,从而用自我意识取代现实生活。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集中批判,并在“序言”部分就表达了自己的鲜明立场:“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①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这句话中的“灵”,德文原文为“Geist”,通常译做“精神”。——原文编者注显而易见,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在鲍威尔的批判中,我们所反对的正是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日耳曼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通过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作自己的最后一次尝试。”[1]253只有对这种作为宗教观的思辨唯心主义进行批判,才能走出作为宗教世界的自我意识,使人作为现实的人重新回归到现实生活。
思辨唯心主义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在于把“自我意识”绝对化。自我意识作为现实生活的对立面,是绝对的、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鲍威尔等人就把自我意识信奉为是这样的东西,并且认为,相对于人的现实生活而言,自我意识才是唯一的真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因为掌握着这唯一的真理——自我意识,才会战胜现实生活中的对立面——群众。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职业就是在进行神学的批判,以自己的宗教观念为理论武器对自我意识的对立面即现实生活展开批判。只有这样做,思辨唯心主义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确立自己的绝对地位。青年黑格尔派才能通过“批判”的身份在群众中确立自己作为神的地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作为宗教观的思辨唯心主义的特点:“一切宗教观念的特点都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有一个最后总要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1]258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认为自我意识才是会“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对立面。他们为自己保留了自我意识这个绝对的东西,从而自说自话地确立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神的地位。
思辨唯心主义把自我意识与现实生活相对立,目的在于否定和取代现实生活。这与纯粹的宗教观乃是对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有着根本的不同。宗教观是通过对神的设定,来反映和引导现实生活的。只不过宗教观对现实生活的映现,乃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历史的异化反映,其展开方式是绝对的、抽象的、虚幻的,但其折射出来的内容却是相对的、具体的、真实的。也就是说在手法上,宗教观是把设定的东西绝对化、把具体的事物抽象化、把真实的东西虚幻化,从而赋予自然以超自然的神秘感,赋予现实生活以宗教信仰的意义。然而,思辨唯心主义只把现实生活看作是自我意识展开自身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单纯外化。现实生活离开自我意识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存在形式。只有自我意识才是绝对的东西。这样思辨唯心主义就以纯粹内在的自我意识消灭了现实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批判”自居的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取代现实生活,另立宗教之神的做法进行了嘲讽:“正如上帝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人一样,批判也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命运。所以创造命运的批判也像上帝一样是万能的。”[1]302这样“批判”就能像掌握命运的上帝那样无所不知,通过展现自己万能的力量来大刀阔斧地改造现实生活。
鲍威尔等思辨唯心主义者强调自我意识的宗教观,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宗教之间的对立之中,脱离了现实生活,因而只能以自我意识取代现实生活,在自我意识中无法自拔。在宗教与生活的关系上,鲍威尔等人只看到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而看不到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只会从宗教本身来讨论问题,只会关注宗教之间的冲突,只能得出否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犹太教为例,来说明作为神学家的鲍威尔的局限性。“在这位笃信基督的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看来,犹太教的世界历史意义已经必不可免地从基督教诞生的那一时刻起荡然无存。所以,他必然要重复那种认为犹太教是违反历史而保存下来的陈旧的正统观点;而认为犹太教只是作为神的诅咒的确证,作为基督启示的明证而存在的陈旧的神学偏见,则必然要在鲍威尔那里以批判的神学的形式屡屡出现。根据这种形式,犹太教现在和过去都只是作为在宗教上对基督教的超世俗起源的肆无忌惮的怀疑而存在,也就是作为反抗基督启示的明证而存在。”[1]307-308在这里,鲍威尔把犹太教看作是基督教的对立面,而不是深入到犹太教产生的世俗的基础中来进行解释。他不是用现实生活去说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关系去说明自己的宗教观。于是,就陷入到了对宗教问题讨论的自我循环的怪圈之中。这种只用宗教的方式来考察宗教问题的方法,只会把宗教问题看作是纯粹宗教的问题。这就是作为宗教观的思辨唯心主义在逻辑上的根本缺陷。
与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进路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宗教问题提出了科学的解释。他们认为,要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宗教本身,才不会陷入思辨唯心主义对宗教问题的错误认识方式。就拿犹太教来说,鲍威尔始终从纯粹宗教的视角出发来讨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只会把它当作是自我意识世界即主观的神学世界的一个环节,而不会把犹太教视为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念反映。这是由于,鲍威尔作为自我意识的忠实信徒,从来不会把日常生活中的人看作是人,而只会把在安息日里假装祷告的人当成是人。只有这样,他的眼里才有宗教问题。但是,在他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只会看到表面的宗教问题,而看不到宗教背后的生活问题,或者说发现不了宗教的世俗的基础是人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鲍威尔这种认识上的错误性,一针见血地提出:“在剥掉了犹太教的宗教外壳,使它只剩下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之后,才能够指明那种可以消除这个内核的实际的、真正社会的方式。”[1]307
这里的社会方式就是指,犹太教连同宗教的犹太精神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是在人的现实的生活中不断产生出来的。任何宗教都不是纯粹自为存在的理论,而只是用来说明人的现实生活的观念反映。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用现实的人的眼睛才能看到宗教的实质,即宗教只是以观念的方式来折射现实生活,而不是相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法年鉴》中就证明,“犹太精神是通过历史、在历史中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用神学家的眼睛,而是只有用世俗人的眼睛才能看到,因为这种发展不是在宗教学说中,而是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1]308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更是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指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已经不是犹太人要解决的特殊任务,而是犹太人在现实生活的普遍的实践中所要面对的真实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消除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1]308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作为宗教观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虚假的意识形态性。他们认为,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试图在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非人性的现实生活。“问题的关键不是宗教批判,而是对这种宗教所反映的存在着剥削、压迫之社会的批判,更具体而言即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3]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寻找宗教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活基础,进而通过现实生活来分析和批判宗教问题,将鲍威尔等思辨唯心主义者所否定和取代的现实生活再重新确立起来。
综上所述,以青年黑格尔派为首的思辨唯心主义,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使之成为绝对的自我意识,进而用自我意识取代现实生活。思辨唯心主义者们一方面,把自我意识当作唯一的宗教之神来崇拜,停留在就宗教来论宗教的思想旧时代;另一方面,用自我意识的宗教世界来否定和取代现实生活,并以职业的神学家——“批判”自居来对现实生活进行不食人间烟火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对于人的现实生活而言,没有比这种作为宗教观的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他们通过批判这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科学地超越了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错误性和意识形态性,并对生活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初期的认识和评价上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