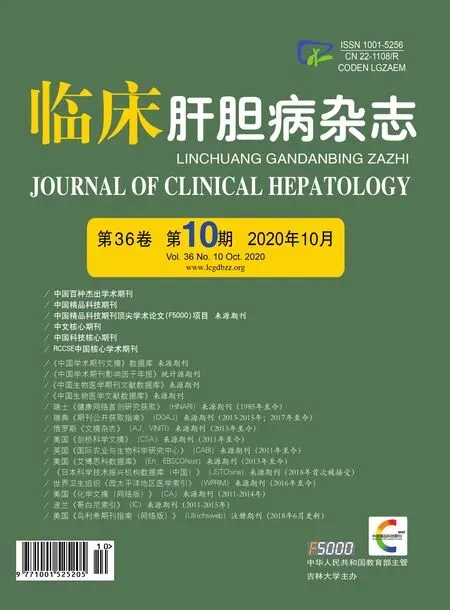精准医学时代肝细胞癌的系统治疗
2020-12-13祝桂琦史颖弘
祝桂琦, 唐 政, 史颖弘, 樊 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肿瘤外科, 上海 200030
1 精准医学的概述
自2011年美国国立医学院推出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概念以来,如今精准医学领域已变得炙手可热。美国已于2015年启动精准医学计划,我国也于2017年启动精准医学计划[1]。精准医学是在基于分子表型的疾病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基因测序技术和生物医学分析进行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志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寻找到病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分型,针对性的开发应用靶向特异性药物,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基于基因的个性化精准治疗[2-3]。
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的TowardPrecisionMedicine:BuildingaKnowledgeNetworkforBiomedicalResearchandaNewTaxonomyofDisease提出,基因组学成果促进生物医学信息学和临床信息学的整合[4],从而加速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多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平行测序的出现同时也为精确医学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3]。精准医学强调,通过强大的检测手段和临床特征的整合,可以将异质性疾病很好地分为更精确的亚型,从而使临床医生针对疾病亚型人群制订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策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5]。肿瘤领域一直是精确医学的前沿,因恶性肿瘤不同的遗传背景和驱动突变,肿瘤导致的死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肝细胞癌(HCC,以下简称肝癌)是一种异质性很高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5]。这种异质性会影响细胞内关键的信号通路,驱动其表型变异,影响肿瘤的进化,并对肝癌的治疗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精准医学的应用将对肝癌的治疗策略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讨论精准医学框架下肝癌系统治疗的最新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2 肝癌多学科治疗的发展
原发性肝癌具有发病率高、预后差、死亡率高的特点,最新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其发病率在全球恶性肿瘤中的排名为第五位,死亡率则排第三位。我国是肝癌大国,更是乙型肝炎大国[5-6]。既往肝癌早期诊断较困难,就诊时肝癌大多已发展至晚期,疗效极不满意[7]。近年来,随着B超、CT、MRI等影像技术的发展、外科技术水平的提高及新技术的应用, 对肝癌的诊断、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发性肝癌的治疗由早期的单纯手术治疗, 发展为包括手术治疗、局部治疗、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及中医中药等的综合治疗[8]。通过对肝癌发生发展分子遗传模式的研究,人们对肝癌的认识由早期的单一疾病发展为基因水平的认识, 对肝癌的治疗也由过去的单一疗法发展为包括系统治疗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疗法。笔者接下来将简要阐述肝癌系统治疗的历史和发展。
3 肝癌靶向治疗的进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学者们对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9]。相反,这又为开发新的分子靶向药物提供了机会,这些靶向药物可以抑制肝癌中失调分子的异常,也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10-12]。目前,许多临床试验正在寻找肝癌中作用于生长因子受体和细胞内信号通路的小分子药物,比如这些通路参与细胞分化 (如Wnt)、增殖(如表皮生长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干细胞生长因子及其受体c-MET、RAF/MEK/ERK)、生存(如AKT/m-TOR)、血管生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有助于肿瘤生长和转移。肝癌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潜在的分子靶标。靶向治疗药物具备靶向性、安全性、方便性等优点。
由于血管生成在肝癌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最重要的VEGF及其他的血管生成途径,因此开发有效的抗血管生成药物是目前抑制肝癌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以下是肝癌中确定的分子靶点和目前用于临床或正在研究的靶向治疗药物[9,13-15]。
3.1 索拉非尼 抗血管生成的多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第一个靶向的系统性治疗,于2007年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肝癌。索拉非尼通过阻断生长因子的各种受体酪氨酸激酶(包括VEGF、PDGF和c-Kit)来显示其抗肿瘤活性,从而抑制Raf/MEK/ERK介导的信号转导[9]。SHARP和Oriental的两项全球Ⅲ期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出索拉非尼能显著提高不可切除和晚期肝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9,16-17]。与索拉非尼相比,舒尼替尼、厄洛替尼、布立尼布等小分子TKI均未显示明显的临床获益。
3.2 仑伐替尼 十多年来,索拉非尼一直是FDA批准的治疗晚期、不能切除的肝癌的唯一一线治疗药物。仑伐替尼是一种VEGF1-3受体、FGF1-4受体、PDGFα受体、Ret和Kit的TKI[18],在Ⅱ期临床研究中发现仑伐替尼对不可切除肝癌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REFLECT试验(NCT01761266)是一项多中心随机的非劣效性Ⅲ期临床试验[19-20],研究发现仑伐替尼在总体生存率方面并不差于索拉非尼,而无进展生存率及客观缓解率更优。
3.3 瑞戈非尼 瑞戈非尼是与索拉非尼结构相似的TKI。瑞戈非尼抑制VEGFR2、3,PDGFR,FGFR-1,Kit,Ret和B-Raf[21]。在一项随机、双盲、Ⅲ期临床试验(RESORCE试验,NCT01774344)中[21],在索拉非尼治疗失败后使用瑞戈非尼与安慰剂作为二线治疗的对比中,瑞戈非尼的安全性与对照组相当。基于RESORCE试验数据,FDA批准了瑞戈非尼作为治疗肝癌的二线治疗方案。未来的试验正在探索瑞戈非尼与其他全身性药物的联合应用,希望能够作为对不能连续耐受索拉非尼和瑞戈非尼的患者的三线治疗[21]。
3.4 卡博替尼 卡博替尼是一种多重TKI,可抑制VEGFR 1~3、MET和AXL。对服用索拉非尼无效的不可切除肝癌应用卡博替尼的双盲Ⅲ期临床试验(NCT01908426)[22-23]表明,与安慰剂组相比,卡博替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明显延长(10.2个月vs 8.0个月,P=0.005),卡博替尼组与安慰剂组的平均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5.2个月和1.9个月[22];卡博替尼组少数患者可出现5级不良反应,包括肝衰竭、门静脉血栓形成、肝肾综合征和肺栓塞[23]。根据上述试验的数据,2019年1月,FDA批准卡博替尼作为曾接受索拉非尼治疗进展的晚期肝癌患者的二线治疗方案。
4 肝癌免疫治疗的进展
肝脏中免疫微环境和非免疫微环境共同参与肝癌的免疫耐受及应答,影响肝癌的发展与患者预后。传统的肝癌治疗方案由于无法逆转免疫耐受环境,免疫系统对药物的敏感性不足,疗效常不理想[6]。因此,临床医师应充分了解肝癌免疫微环境,完善治疗策略提高肝癌的治疗效果。肿瘤免疫治疗是通过激发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肿瘤微环境抗肿瘤免疫力,从而控制和杀伤肿瘤细胞的治疗手段。与传统肝癌治疗手段相比,免疫治疗发生严重毒性反应的概率更低,患者耐受性更好,可有效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延缓肿瘤的进展,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近年来,肝癌免疫治疗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在临床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部分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生存周期延长,复发率降低。常用的免疫治疗的方法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单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 单抗等]、过继免疫治疗 (嵌合抗原受体T淋巴细胞免疫) 和肿瘤疫苗治疗 (树突状细胞疫苗、溶瘤病毒疫苗等)[24]。
4.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 免疫检查点分子PD-1是1992年由日本京都大学的TasukuHonjo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首次发现的。它被命名为程序性死亡受体1,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它时正在寻找诱导T淋巴细胞凋亡的分子,后来发现它是一种负性调节免疫反应的受体。PD-1配体PD-L1和PD-L2也在2000年被发现[25-26]。后来发现,抑制这一途径可以通过逆转肿瘤的免疫抑制作用和恢复固有免疫活性来消除肿瘤,这促使后来在2002年开发利用这一机制的抗肿瘤药物。1995年,James Allison发现了CTLA-4,并发现抑制其功能导致小鼠肿瘤消失[25]。这种调节T淋巴细胞活动的分子称为免疫检查点分子,而抑制这些分子的药物称为ICI。目前正在研究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作为抗PD-1抗体,avelumab、durvalumab和atezolizumab作为抗PD-L1抗体,以及iplimumab和trelimumab作为肝癌的抗CTLA-4抗体的多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25]。
nivolumb是世界上第一个抗人PD-1的重组人IgG4单克隆抗体。在晚期HCC的Ⅰ/Ⅱ期试验(Checkmate-040试验)[27]中,其有效率为20%,包括两次完全缓解和67%的疾病控制率。nivolumab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它的作用持续存在于应答者身上。此后,增加了试验人数,最新结果在2017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公布,一线治疗的总生存期结果为28.6个月,二线治疗为15.6个月[27]。上述Ⅰ/Ⅱ阶段试验的结果,美国FDA指定nivolumab进行优先审查,并于2017年9月获批。pembrolizumab与nivolumab一样,是一种抗人PD-1的重组人IgG4单克隆抗体。在Ⅱ期试验中对肝癌进行了研究,结果与nivolumab相似[26-27]。但两项大样本的Ⅲ期研究checkmate459、KEYNOTE-240均未得出阳性结果,提示nivolumab及pembrolizumab单药疗效仍需提升[28]。
4.2 嵌合抗原受体T淋巴细胞(CAR-T)免疫 在评估CAR-T细胞治疗肝癌的少数研究中,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第三代疗法,其特征是CD28和CD134(或4-1BB)与CD3-ζ结合的共刺激域。一系列的肝癌生物标志物使用这项技术进行了靶向研究[29-30]。PC3靶向的CAR-T细胞可以根除GPC3(+)HCC异种移植物,但不能根除GPC3低表达的病变(NCT027239942、NCT02395250、NCT03084380和NCT03198546)[31]。类似的结果也在肝癌患者的异种移植模型中得到证实。静脉注射甲胎蛋白靶向的CAR-T细胞导致肿瘤生长抑制。抗癌胚抗原(CEA)的CAR-T细胞的临床活性可能对肝转移瘤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30-32]。抗CEA CAR-T细胞与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靶向药物联合治疗CEA阳性的肝癌[31]。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损耗能减少肿瘤源性PD-L1和PD-1在CAR-T中的结合细胞。其他生物标志物,如HBV、SP17、FAP、黏蛋白-1,EpCAM、c-Met/PD-L1、ET1402L1、glypican-3和EGFRvⅢ也已在Ⅰ/Ⅱ期临床试验(NCT03349255、NCT03672305、NCT02905188、NCT03980288、NCT03884751、NCT03146234和NCT02587689)开展[30-32]。然而,由于肿瘤相关抗原通常在正常组织中呈现低水平,因此若要利用肿瘤相关抗原靶向肿瘤细胞,研究者们仍需要考虑在实际过程中的脱靶效应和靶向非肿瘤细胞导致的副作用。为了降低风险,多靶点CAR-T细胞被开发用于治疗肝癌,例如GPC3和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1(肝组织特异性蛋白)可靶向CAR,CAR-T和T淋巴细胞受体基因转导的T淋巴细胞(NCT03941626)[33]。临床试验中经常遇见的障碍包括细胞转运、缺乏特定的肿瘤抗原以及CAR-T细胞在肿瘤部位的渗透[30-32]。考虑到肝癌发生发展的复杂机制,CAR-T细胞治疗联合其他免疫疗法或TKI可能是克服这些障碍的可行策略[33]。
4.3 系统治疗中的联合疗法
免疫治疗单药对肝癌的疗效并不满意,有可能的原因是肝脏对抗原具有相对较高的生理免疫耐受性,因为免疫抑制成分和因子如Treg、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IL-35的上调。另一个原因是PD-1、TIM-3、CTLA-4和Raf-1等多种途径参与了肝癌的发生和发展,为突变体肝细胞的生长建立了一个难治的免疫耐受性微环境,从而导致对单一免疫疗法的抵抗。此外,大多数免疫疗法都有严重的剂量依赖性副作用,例如皮疹、腹泻、肺水肿和细胞因子风暴,这些副作用随着剂量的增加而表现出来[34]。因此,将多种免疫治疗、免疫与靶向、免疫治疗与局部治疗等的结合,是联合治疗的一个重要方向。
4.3.1 抗血管生成治疗联合免疫治疗 TKI如索拉非尼、仑伐替尼、瑞戈非尼等已用于肝癌的一线和二线治疗。它们主要通过抑制VEGF受体(VEGFR-1-3)、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α和PDGFβ)、STAT3和激酶级联的各种蛋白质来靶向多种激酶[9,18,21]。尽管TKI在临床试验中有明显的益处,但耐药性和上述不良反应限制了这些治疗方法在少数患者中的应用。VEGF的抗体药物贝伐单抗等有类似的疗效及耐药问题。此外,TKI既可减少细胞周期失调或肿瘤细胞凋亡,又可通过诱导缺氧或调节代谢等途径调节瘤周免疫细胞的分子表达[9]。因此,将免疫治疗与TKI结合可能是治疗HCC的一种有前途的策略。近年来,ICI与TKI或抗体药物联合应用已成为肝癌治疗的一个热点。多项类似联合治疗的研究正在进行,部分甚至已经获得了40%~50%的客观缓解率数据。已发表的Ⅲ期临床研究显示,阿特珠单抗联合贝伐单抗对比索拉非尼用于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取得了总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双终点的阳性结果。因此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已将此组合疗法纳入肝癌一线系统治疗推荐[35]。仑伐替尼联合派姆单抗用于不可切除肝癌的Ⅰb期研究近期已发表,联合治疗获得了高达46%的客观缓解率(mRECIST)[36]。另一项名为COSMIC-312(NCT03755791)的Ⅲ期临床试验[37]发现,在既往未接受全身性抗癌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中,阿特珠单抗联合卡博替尼较单用索拉非尼具有明显优势。这些组合的最佳搭档还在不断探索,总体已显示非常高的治疗响应,成为肝癌系统治疗中最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4.3.2 系统联合局部治疗 目前一些研究[38-39]正在评估抗肿瘤免疫与常规局部治疗相结合的临床效果。先前的研究发现,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射频消融(RFA)甚至放疗都能激活宿主免疫系统,释放局部炎症因子和新抗原。对于接受根治性切除的肝癌患者,与仅接受手术的患者相比,细胞因子诱导的细胞毒性治疗加手术疗法显著改善了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40]。tremelimumab(替西木单抗)联合RFA或TACE(NCT01853618)被认为是晚期HCC患者的辅助治疗[41],约有26%的患者体现出较好的部分反应。最近,一项Ⅲ期研究(NCT03778957)评估TACE联合贝伐单抗和durvalumab对局部进展期肝癌疗效。另一项研究(NCT0281754)评估了durvalumab和替西木单抗与消融疗法(如TACE、RFA和冷冻消融)在晚期HCC患者中联合应用的效果。NCT03572582研究评价了抗PD-1抗体nivolumab联合TACE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总的来说,这些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有望为难治性肝癌确定合适的治疗策略。
5 系统治疗在肝癌多学科治疗中的价值
HCC的系统治疗过去仅限于晚期患者,而靶向肿瘤血管生成的TKI是开发新治疗方案的主要途径。在过去的3年里,分子靶向治疗和ICI试验的新数据为晚期肝癌的一线和二线治疗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24,39]。最值得注意的是,将PD-1途径的ICI与其他新型药物或常规抗癌治疗相结合,可进一步提高不同临床环境下的治疗效果。目前肝癌的系统治疗涉及多个学科和多种方法,并且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肿瘤生物学、全身状况、驱动突变基因的特性来选择不同方法,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国内建立肝癌多学科治疗最早的单位之一,肝癌多学科治疗的精髓正在于系统治疗,而系统治疗的关键也正是基于精准医学的理念[42]。
6 肝癌系统治疗中的精准医学理念的应用
肝癌是一种高异质性的恶性肿瘤,目前大多数临床试验的纳入标准主要基于肝功能和肿瘤分期(如Child-Pugh A级和肝外扩散和/或血管侵犯的存在)。然而,其实很多临床试验中招募的肝癌患者在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上并不一致。因此,最近提出了通过生物标志物(例如基因异常和表达的蛋白质)来优化患者选择[29]。例如,c-MET的过度表达被用作tivantinib 试验中的生物标志物[29],RAS蛋白被用作MEK抑制剂试验中的生物标志物。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使用FGF19作为生物标志物的FGF受体抑制剂的试验[43]。然而,在tivantinib 的Ⅲ期研究和MEK抑制剂的Ⅱ期研究的阴性结果之后[44-45],这两种药物的开发被中止。在肝癌的靶向及免疫治疗中,目前并无可以明确提示疗效响应的分子标志物。因此,单纯靠这些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来筛选特定符合某种治疗的肝癌患者人群,以此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目前来说这样的研究设计理念还不足以更精准地“靶向”不同肝癌人群。因此,对肿瘤细胞内部的深度测序,探索不同肝癌分子-基因层面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临床相关病理特征可以为肝癌提供更精准的预测和治疗。
随着新一代组学技术对肝癌多维度、多层次和跨组学的深度解析,基于转录组、蛋白质组和肿瘤微环境的分子分型研究也得到快速发展。由于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直接执行者,蛋白组学是寻找分子标志物有效方法之一[46]。同时蛋白组学也是寻找药物靶标的有效途径,目前以TKI为主的肝癌靶向药物以及以ICI为主的免疫治疗直接作用靶点均为蛋白质。近日,笔者团队[6]通过蛋白组学分析比较110例早期肝癌的分子特征,系统揭示了我国早期肝癌的异质性,并将其分为S-Ⅰ~Ⅲ 3个亚型。其中S-Ⅲ亚型高表达TGFβ等肿瘤增殖相关蛋白,预后差;S-Ⅱ亚型、 S-Ⅰ亚型以WNT、CTNNB1高表达为特点。在预后最差的S-Ⅲ亚型早期肝癌中,甾醇氧-乙酰转移酶(sterol O-acyltransferase,SOAT)1高表达,下调SOAT1后细胞质膜上胆固醇分布发生了改变,而且肝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得到有效抑制[6]。同时,SOAT1抑制剂avasimibe在人肝癌移植瘤模型中的抑制作用进一步表明SOAT1可能成为S-Ⅲ亚型即Hoshida S1亚型肝癌的新靶标。此外,笔者团队[6]对159例乙型肝炎相关肝癌进行外显子、转录组、蛋白组、磷酸化组的多组学分析,结果显示:肝癌被分为代谢驱动型(S-Mb)、微环境失调型(S-Me)以及增殖型(S-Pf)3个亚型。其中,S-Mb亚型高表达ACAT1、ADH1A、G6PC等代谢相关蛋白,提示其保留了部分正常肝功能,预后最好;S-Pf亚型的肿瘤中高表达PARP1、TOP2A、PCNA等增殖相关蛋白,预后最差;S-Me亚型低表达CD4、CD8A、S100A12等免疫、炎症和基质相关蛋白,预后介于两者之间。值得注意的是,36例蛋白组分型和转录组分型归类不一致肝癌患者的样本,蛋白分型可以提供更好的预后分析。基于上述中国人肝癌蛋白组学数据的分析结果,马兜铃酸的突变“指纹”与肿瘤突变负荷、肿瘤新抗原负荷、CD8+T淋巴细胞浸润、免疫微环境耐受(ICOS、OX40、PD-1和LAG3等免疫检查点丰度)呈显著正相关,提示该类患者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另一方面,CTNNB1突变患者微环境中表现为免疫豁免型,可能无法从免疫治疗中获益,进一步通过肝癌的多组学分析发现CTNNB1突变与果糖二磷酸醛缩酶A(fructose-1,6-bisphosphate aldolase,ALDOA)第36位丝氨酸的磷酸化相关。ALDOA磷酸化通过促进无氧糖酵解促进肿瘤细胞增殖,敲减ALDOA显著抑制肿瘤增殖。因此,ALDOA可能是CTNNB1突变亚型肝癌的一个重要潜在治疗靶点[6]。
7 小结与展望
中国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超过全世界50%。近几年肝癌药物治疗继索拉非尼之后,仑伐替尼、瑞戈菲尼、卡博替尼、抗EGFR抑制剂、以ICI为核心的组合疗法层出不穷,促进肝癌药物治疗的进步。但是,由于肝癌的高度异质性,上述药物的整体有效率依然有限,预测疗效的分子靶标依然缺乏。精准的肝癌分子分型不仅有助于肝癌个体化诊断与治疗的决策、个性化的药物治疗,而且将极大加深临床医师对肝癌复杂性和异质性的理解,以便制订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疗策略。肝癌的系统治疗更是要与新的分子分型体系,临床病理信息紧密结合,同时要结合精准的分子标志物疗效预测,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