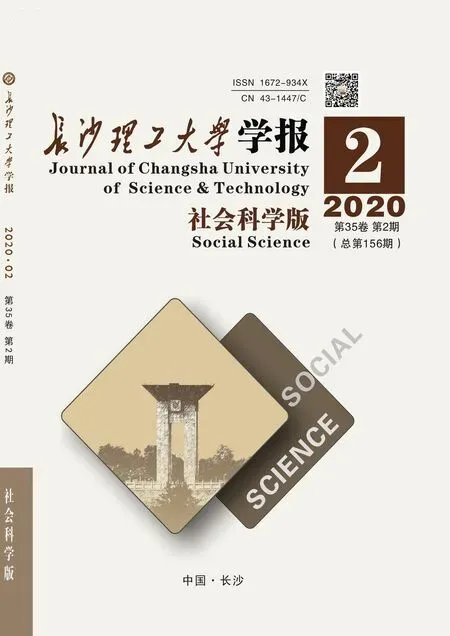人工智能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问题
——基于认识论史的研究述评
2020-12-13黎昔柒
黎昔柒
(长沙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伴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加速步入智能时代。实际上,AI不仅仅对人类社会的伦理规则产生了强烈冲击,而且在认知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认识主体、客体和中介。有学者指出,AI带来了“当代哲学认识论的尖端问题。它的产生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向哲学提出了挑战”[1]。基于认识论理论史探讨AI技术设计问题,有助于拓广AI研究的视角,也有助于厘清AI技术设计认识论问题的内在发展线索。
一、国外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相关研究
就认识论演进史而言,人工智能研究的认识论基础问题可追溯到希腊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以素朴的方式揭示了数字、逻辑、理性等与世界万事万物的关联,为将来理性主义乃至逻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前提,此种前提也是AI设计的理论前提。毕达哥拉斯学派阐发了“数学的原则就是所有事物的原则”[2](P12)的思想。此种观点认为世间万物的本源或本质是数,用数来标识世界是顺理成章的。这为之后用数字或符号、理性来表征世界奠定了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柏拉图提出“用理念来涵括个别事物”[3](P65)的观点。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不变的本质与原型,是脱离事物的存在。他认为,事物归根结底是对理念的模仿,这样就打通了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为用思想表征世界埋下了认识论伏笔。亚里士多德创建了逻辑学,发现了三段论式是一切思维运动的基本形式[3](P83)。之后,逻辑学构成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科。到中古时期,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此时期的哲学家极为重视逻辑研究,探讨了唯名论、共相论等认识论思想。唯名论与共相论思想蕴含了符号、名称、一般概念等对特殊事物的指代,这就构建了符号与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与人工智能符号主义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预设具有内在关联。
到近代,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争构成了其认识论演进的中心线索[3](P283-285)。此种线索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预设中得以体现。就唯理主义认识论而言,笛卡尔认为,直觉与推论“是知识的最可靠的路线”[2](P339)。莱布尼茨将物理世界视为一个“数学-逻辑”体系,由此提出了“通过计算可以解决任何问题”[3](P402-417)的观点。此种线索在人工智能符号主义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预设中得到体现。此种技术设计正是基于符号、理性可以表征世界的认识论预设,将人类认知过程预设为符号处理过程。就经验主义认识论而言,弗兰西斯·培根阐发了归纳法。洛克提出了白板论[4]。他认为,人类知识源自感觉与知觉的经验,人类知识建基于经验之上。此种理路在AI行为主义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预设得到体现。此种AI技术设计采用“自下而上”的设计路径,基于AI运行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反馈信息与数据来设计、运行人工智能,与经验主义认识论预设具有内在一致性。
20世纪以来,胡塞尔现象学阐发的“意向性”问题成为了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难题[5]。这个问题被人工智能哲学作为核心论题进行了大量探讨。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认为逻辑语言可以准确表达世界可说的一切。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则提出“家族相似性”概念,抛弃了在语言背后有一个逻辑架构的思想[6]。海德格尔追问了技术的“本质”,提出技术是“解蔽”知识的“真-理(Wahr-heit)之领域”[7]。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与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凸显了技术的“意向性”的一面,也凸显了AI技术设计在认识论预设方面面临的“瓶颈”难题。
从横向视角来看,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AI技术设计对人类认知影响的研究。此种维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揭示AI技术设计对人类认识主体、客体和中介的影响。如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认为,AI技术已经打造了全然的新实在,使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现象成为可能,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与方法论手段[8](P7)。Klaus Mainzer指出,只有AI才能使我们成为21世纪的人类,使社会成为一个“超级生物体”。Staff Economist认为,AI算法将带来“价值互联网”(Internet of Value)这样的“新数字世界”[9]。二是阐明AI技术设计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关联。比如,约纳斯(Hans Jonas)指出,技术设计过程与人类认知过程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10]。
第二,关于AI技术设计与认识论问题的关联研究。就AI技术与人类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言,米切姆(Carl Mitcham)曾提出:AI能否思考,AI是何种智能,算法的、启发式的、联结主义的和体现式的AI是否是与人类认知不同的认知形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计算机程序设计来解决认识论问题。比如格里姆(Patrick Grim)指出,AI技术设计领域的“工程学—认识论”“认识论的工程学”“类人的工程学”等在计算机建模领域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研究程序,此种程序使认识论假设以特定方式直陈出来,也使认识论假设得到富有成效的评判。萨迦德(P.Thagard)将ECHO程序开发成解释融贯性认识论问题的联结主义计算模型。Spirites、Glymour和 Scheines运用TETRAD程序研究因果推理与概率方面的认识论问题[11]。
第三,关于AI技术设计带来认识论革命的研究。Jean Gabriel 认为,AI技术不仅削弱了作为人类认识对象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而且创生了一个超记忆(hyper-memorisability)、超复制(hyper-reproducibility)和超扩散(hyper-diffusibility)的认识对象[12],这带来了认识论的巨大变革。K.Hayles将AI技术设计带来的认识论革命标识为“后人类”的认识论纲领。J.D.Bolter、J.S.Brown、P.Duguid和M.Dertouzos等将其称为“身—与—心”的“后笛卡尔主义” 认识论[8](P197-198)。此是一种克服笛卡尔二元分立的认识论纲领,其用反身认识论取代客观主义认识论,用具身化取代作为“思维的支撑”的身体,用人与机器之间的动态伙伴关系取代主体必定要统治控制自然的主客关系,从一种主客二元分立的客观认识论转向一种强调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构成我们关于世界知识的认识论。
第四,关于“图灵测试”的技术设计认识论研究。图灵(Alan Turing)认为计算机能够具备人类智能,并提出用人类表现来衡量智能机器的表现。Margaret A. Boden指出图灵的观点遭到三个方面的反驳[13](P5-11):一是Aaron Sloman拒绝图灵作为智能充分判据的模仿游戏;二是德雷福斯(Dreyfus)认为“图灵测试”依据的语言行为缺少运动行为,也没有活的身体外形,更不具备心理属性或意向性。塞尔(John R. Searle)则构想出“中文屋”思想实验反驳“图灵测试”;三是Lucas认为AI达不到人类心智的深度、广度和灵活性。纽厄尔(A. Newell)、西蒙(H. A. Simon)反对塞尔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灵就是一个计算系统,与计算机的计算是完全等同的。玛尔(Marr)指责纽厄尔和西蒙忽略了基础的、无意识的信息处理和模式匹配。之后,Mureika从类量子计算角度提出了一种意识涌现物理理论,Schroeder提出了用量子力学形式化代数来描述奇妙统一意识的观点[14]。斯洛曼在人工智能遇到瓶颈设计问题时,他转向哲学,寻找其理论上的帮助, 他基于空间结构维度,为解决人工智能的情感与认知问题提供一个理论支点[15]。
第五,关于“框架问题”的技术设计认识论研究。比如,D·C·丹尼特(Dennett)认为,“框架问题”技术设计是探讨常识性知识能否形式化的问题,它除了涉及AI技术设计的可行性之外,还有重要认识论意义[13](P198-230)。麦克德莫特(Drew McDermott)认为,常识性知识只能借助非演绎推理才能解决,由此,这一问题引申出了非认知现象形式化问题。玛格丽特·博登(Boden)指出,可以设计动机和情感模型等多目标系统来处理非认知现象。德雷福斯则认为,计算机无法认识动机、情感和情绪等非认知现象[13](P14-18)。就AI技术设计的情感表达而言,Ogiso使用人工意识流方法实现了一种机器人的情感表达,Igarashi开发了情感意识机器人并实现了一些情感模仿行为。
二、国内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相关研究
就古代认识论思想而言,与人工智能技术设计相关的主要体现在用数字、图形、逻辑来表征世界万事万物的观点。比如,西周时期的《周易》就蕴含用数字与卦象来表征宇宙的思想。《老子》一书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对自然界内在逻辑的素朴思考。墨子提出了“三表”“察类明故”的认识论思想是知识论的萌芽。到战国中期,各家渐次关注认识论问题,如惠施的“合同异”辨析、公孙龙的“离坚白”论难[16]。后期墨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知识论,探讨了知识来源、认识过程、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讨论了逻辑的规则、方法、程序和作用等[17]。汉唐时期,有董仲舒的“深察名号”、王充注重“效验”的认识论思想。宋明时期,周敦颐、邵雍和朱熹等用“太极”表征解释宇宙。王夫之提出了“能必副所、行可兼知”[18]的认识论思想。到近代,辨证唯物主义思想传入我国,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的方法,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总公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才开始直接研究AI技术设计相关问题。钱学森指出,我们可借助于AI,使我们知道自己思维的“当然”,也知道其“所以然”[19]。赵光武认为,AI技术意味着人类认识开始深入到认识自身的新阶段,其使认识中介系统发生巨变,也使认识论研究领域拓深[20]。冯国瑞认为,人工智能开辟了知识工程领域,可能导致复合智能、微观认识论的出现[21]。陈新权认为,人工智能对认知机制及认识方式也会产生深刻影响[22]。陈昌曙指出,对于技术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就包含对技术的认识史研究[23]。
21世纪初,我国技术认识论与技术设计哲学研究开始萌芽,这两者的研究一般呈现为二分态势,而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较为少见。
就技术认识论研究而言,一是强调技术认识论研究的意义。如陈文化、王大洲等指出技术认识论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24-25]。易显飞、陈伟认为,德韶尔、费雷、克罗斯和皮特关于技术认识的研究是欧美技术认识论的典型代表[26]。它的学理背景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它的理论内因是技术哲学理论本身的演进发展,它的现实土壤是现代技术实践的迅猛发展。国内学者应结合中国技术创新的现实土壤,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认识问题,实现从“欧美导向”到“中国导向”的技术认识论研究转变。二是探讨技术认识论的研究领域。如陈凡、程海东认为技术认识的研究是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基点[27]。他们指出,要研究技术认识论,就必须先探讨技术认识,要研究技术认识就必须先探讨技术的本质。他们认为技术认识有三重含义:一是借助于技术进行的认识;二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三是技术规则等。刘则(等认为技术认识论应研究技术知识及其发展模式、技术的认识结构等问题。陈真君认为技术认识论要研究作为知识的技术是如何发生和演进的[28]。赵乐静强调技术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反对照搬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来构筑技术认识论,因为技术知识具有意会性等非认知的特质是解释技术的前提[29]。
就技术设计哲学研究而言,主要有如下方面的研究:一是关注技术设计哲学的研究价值。如闫坤如认为技术设计对研究技术认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0]。郭芝叶、文成伟认为,技术设计构成了技术过程的源头和根本[31]。技术设计要着眼于实现一种生态技术,要在技术设计阶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达到一种“德性”的技术。二是讨论技术设计哲学的研究维度。比如,李伯聪认为,技术设计可以纳入工程哲学中进行探讨[32]。陈凡等认为,技术设计可放入技术哲学中讨论。张华夏、张志林认为,技术设计可植入技术解释学中研究。王以梁、秦雷雷认为,技术设计不能只追逐对自然的控制与效益,而要将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价值诉求介入技术设计过程及其成果,要借助于外在文化价值的规约,也要进行道德化的技术设计,才能实现技术设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协同进化与健康发展[33]。三是探讨技术设计的含义。比如,乔瑞金认为,技术设计过程是一种认识活动,其主要研究技术设计知识及技术设计过程中的认知结构问题[34]。程海东、陈凡认为,技术设计就是技术认识的形象化[35]。刘炜、程海东认为,技术设计与生物一样,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36]。技术“模因”是其进化的信息载体,其通过遗传、重组和变异进行自身进化,产生新的适应性更强的技术。四是探讨技术设计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比如,张秀武认为,技术设计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其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发生改变,提供了人类解放自己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是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与危机[37]。要将技术设计融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与生产,才能构筑起合理的健康的技术设计,才能设计出崭新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
此外,基于AI技术设计探讨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一是探讨人工智能认识论问题。有学者基于AI技术设计来探讨知识问题,比如,吴文俊提出了利用机器证明与发现几何定理的新方法;史忠植拓展了知识工程核心理论;张钹提出了基于统计推断的启发式搜索。胡景谱、易显飞认为,在人工智能的诸种探讨中,哲学研究处于顶层位置,其中人工智能哲学的认识论问题研究又处于核心地位[38-39]。学界以往探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认知科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认识论研究;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取代人类这一认识主体的讨论;人工智能认识主客体的关联与区别;人工智能认识论之于认识论的变革;等等。二是探讨AI认知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关系。如杨富斌认为,AI认识系统的认识主体演变成了“人-机-网主体系统”,认识客体虚拟化,认识中介计算机化和网络化,“赛博空间”成为了认识空间[40]。郑祥福认为,AI哲学问题不再是AI的本质问题,而是关于人的意向性、概念框架、语境以及日常化认识问题[41]。钟义信认为,AI具有认知能力,AI认知与人类认知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42]。三是强调AI技术认识论研究路线与研究目的。比如,易显飞等认为,基于信息技术哲学来探讨当代认识论的研究路向有三种:基于信息技术哲学出发拓展到对当代认识论的探讨、基于认识论出发延伸到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直接研究信息技术的认识论问题[43]。未来可进一步探讨现代信息技术各子领域诸多更具体的认识论问题,丰富信息技术哲学认识论的现实维度。宋惠昌认为,此种研究在于使AI发展遵循正确道路,并拥有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44]。
三、国内外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相关研究特色与不足
以往文献关于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哲学认识论、技术认识论、技术设计哲学、AI与人类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生发的认识论问题等方面的探讨。其研究凸显了一定特色,也还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一定空间。
就以往文献研究的特色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体现了AI技术设计与认识论问题研究的内在关联。AI技术设计的研究与认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如影随形。一方面,认识论研究为AI技术设计的演进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AI技术不断发展的需要及其面临的瓶颈促使认识论研究进一步拓深。二是奠定了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国内外自古代就形成了基于数字、图形和理性来解释、表达世界的认识论思想,尤其是国外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使得认识论问题得以凸显,并引发了后现代认识论思想的迸发。比如,“家族相似性”“生活世界”“意向性”“意识流”等认识论概念的阐发对AI技术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解决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三是提出了有待深入剖析的认识论问题。AI技术设计发展史面临一系列认识论瓶颈问题,如图灵测试的论争问题、框架问题和意向性问题等,此外还有AI技术设计不可避免要做的认识论预设,比如,AI是否能取代人类认识主体、AI能否创造知识等,也是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问题研究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四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以往学者有的从认识论研究拓展至AI研究;有的基于AI研究触及到了认识论研究;有的进行了AI与认识论的融合研究,这些都为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问题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益思路。
就以往文献研究的不足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学界以往研究技术认识论的较多,比如陈文化、王大洲等探讨了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性;陈凡、程海东等探讨了技术认识的本质问题;刘则(等探讨了技术知识及其发展模式、技术的认识结构等问题;陈真君探讨了作为知识的技术的发生和演进;易显飞等探讨了欧美技术认识论模式;等等。学界以往研究技术设计认识论的较为少见,研究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尤为少见,这为AI技术设计的认识论问题研究“预留”了一定研究空间。二是以往研究还未能将AI“遭遇”的认识论问题植入认识论史与AI技术设计史的“历史视域”来展开研究,其研究还可以进行历史维度的深入挖掘。如何从认识论的理论史透视AI技术设计,或者基于AI技术设计史来挖掘、提炼认识论问题,是学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三是以往哲学家、AI技术专家都是基于各自视角对AI视阈下技术设计认识论具体问题展开探讨,此种探讨还需要一个“视域的融合”研究,还需要揭明他们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打通他们思想之间的脉络,揭示他们思想之间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